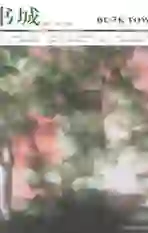吴冠中的两支笔
2021-03-04刘东
还记得,早在大学时代,我就越出了所学的专业,在阅览室的走马观花中,从《美术》杂志上,邂逅了“吴冠中”这个名字。尽管打从那一刻开始,就已知道那是位“画家”,然而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却毋宁更是位文章的“写手”,他能用很有个人特色的文笔,来讨论印象派之类的在当时还很新锐的问题。而且,我的这种第一印象,还在这以后暗自保藏了很久。
再到后来,当然就不断领教到他的画作了。不过可能还是因为,这种第一印象总是先入为主,我仍然觉得吴先生手中实则是握着两支笔,一支是用来画画的,另一支则是用来写作的。换句话说,他在当代中国画坛上,难得地属于勤于思考、敢发议论的画家;并且,大概还因为他久负画名,所以无论他发表什么样的议论,都马上占到了舆论中心。正因为这样,今天我的这篇小文,索性就把“吴冠中的两支笔”当作标题,因为根据我的私下体会,一旦说到了吴冠中的名字,其复杂性基本也就藏在这里了。
在以往发表的文字中,我曾以“调色板”或“万花筒”这样的比喻,来形容在“中国”与“西方”这两个极点之间,由“严守传统—中西合璧—全盘西化”这样的巨大摆幅,所呈现出的既断裂又连续的风格“光谱”。当然在这个五光十色的“光谱”中,也少不了提到“吴冠中”的名字:“有了如此多彩的调色板,在这里就既出现了像齐白石、吴昌硕、陈师曾、黄宾虹、潘天寿、李苦禅、丰子恺、陆俨少这类倾向于‘文化保守画风,也出现了像刘海粟、徐悲鸿、蒋兆和、傅抱石、李可染、关良、叶浅予、吴作人这类倾向于‘中体西用画风,甚至还出现了像林风眠、张大千(后期)、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这类倾向于‘西体中用画风。”(刘东《风火轮般的历史悖论:作为美育家的蔡元培》,《中国学术》第三十七辑,商务印书馆2016年)
不过,换到一般人的印象中,这个“定位”很可能会有出入,他们会更欣赏吴式的“水墨”色调,而这已经形成了一般的常识。正因为这样,张春旸有次拉我去中央美院,看看她那些学生的习作,等看到一幅江南水乡的油画,同样是笔触很轻、色调很高,同样在追求精致或精巧的感性,我不禁脱口喊了出来:“这也太‘吴冠中了吧?”我想在场的人也都能会心,我当时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无论如何,至少吴冠中最流行的画作,并不是“西体中用”的,反而是这类“中体西用”的。
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吴冠中后来也有所解释:“青年人也很喜欢悲剧。回到中国之后,当初不允许这种情绪,因此我向秀丽、秀美这方面走,这样很多人就能够接受。到了晚年之后,我又回复到了我的本性,觉得还是更重视作品的悲剧意识。悲剧的美比一般的美更有价值。”(张公者《艺术·生命——吴冠中访谈》,《中国书画》2005年第9期)只不过,要是从更高的美学理论来看,恐怕还不能只归结为“性格”问题,更要上升到对于“艺术”“悲剧”这类基本概念的理解。至少从我个人的研究出发,“艺术”世界中的人类感性,尽管是被高度地提炼和升华过了,却从来都不属于“纯粹感性”,而必须伴有“理性因素”的嵌入;也正因为这样,“悲剧”之所以更加震撼,根本不是因为它的“美”,倒是因为它那种毁灭性的力道与冲突。
可不管怎么说,吴冠中就是有他的两支笔。只要挥动起他手中的钢笔,他就总是偏向悲剧、偏爱梵高、偏袒鲁迅,一句话,是把目光盯住了不和谐的人间世,并要求“写真”出它的实际内容,哪怕在那样的理性内容中,既潜藏着深不可测的冲突,又爆发出了撕裂性的张力。可与此同时,一旦舞动起他手中的画刷,他就习惯性地回到了大自然,并且尽量寻找那个美好的镜头。由此一来,他“写生”出来的就是一片恬然,或者干脆不妨说就是在“写意”,轻盈得像梦幻般的回忆,光滑得像溜冰时的平面,营造出一个大人的“童话世界”。即使他并不满足于重复自己,所得到的变化也更属于形式上的,从未让他正在书写和谈论的东西,那些不断触动他的社会内容,变成扭曲跳动的线条和嘈杂纷乱的噪声,来打搅他那宁静单纯的画境……
说到这里,也就碰触了一个很深刻的美学问题。我在别处简略地提到过,苏轼曾经借着重新解释“辞达说”,突出强调那种在心与口或心与手之间的、了无断隔的自如创作状态:“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答谢民师书》,《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更深地体会那种行云流水、豁然贯通的苏文风格:“吾文如萬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苏轼《自评文》)
当然心直口快、笔头子更快的苏东坡,乃是难得与罕见的典范和例外。这个判断马上就反过来说明,只怕大多数人都会不同程度地需要克服“口不对心”的写作障碍。可即使如此,像吴冠中这样断然地“兵分两路”,仍然是并不多见,乃至是相当意外的,从而也很值得研究者们留意。虽说他本人未必自觉到,由他那两支笔写出的两方面,正好构成了他内心中的分裂,简直像有两股势不两立的力量,可着劲儿地把他往相反的方向拖拽。而我们从那句“丹青误我”的说法中,也可以发现他至少从其“写作之笔”的角度来看,他的“绘画之笔”反而让他部分地“失语”了。
更进一步地说,他口中的那个鲁迅,也只能被看作既不失其正面意义却又属于“想当然耳”的一个符号,来寄寓他自己对“社会内容”的关切。至少他的这种模糊朦胧的念头,并不能沿着必然会发生的逻辑,去层层递进地依理推演开来,比如联想到鲁迅与高尔基,联想到文联与美协,联想到徐悲鸿与库尔贝,联想到俄罗斯巡回画派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设若如此,我在前边所列举的那个五光十色、斑斓灿烂的光谱,也就要随之变得色彩单一了。
当然反过来说,“丹青”并非只是“贻误”了他,“丹青”也照样成就了吴冠中,他获得了受人艳羡的“成功”。
我又从电视上看到吴冠中是怎么去理发的,不过是随便找公园里的剃头挑子,每次花上五块钱草草打理一下。如此,这种不会花钱或不修边幅的,乃至有点对抗性的做派与性情,就既跟他的“市场效果”构成了反差,又不免使人有所触动和发生联想。我甚至由此猜想与捉摸,这种阴差阳错的“成功”对于吴冠中本人,怕也只能起到某种反讽的效果,也就是说,越是受到公众的普遍喜爱,越是受到市场的广泛追捧,他就越不能满足于自己的“大众化”,乃至怀疑自己的作品是否有“媚俗”的嫌疑。
不过,偏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由衷感到吴冠中的可贵。毕竟,当前美术界的突出问题,无非是表现在下述两方面:一个是醉心于“玩”,无论是玩笔墨、玩意境,还是玩山水、玩华屋;另一个则是迷恋着“钱”,并且毫不掩饰地把画价的高低当成检验艺术的“唯一标准”;而且这两个方面,最好还能够相互支撑。然而,回头再照照吴冠中的镜子,却可以知道这两个方面,至少是并不能满足他的,这反而又使我找到了某种安慰。在这个意义上,讲出他手中的两支笔,以及那中间的冲突与背离,并不是在“吹毛求疵”地挑剔他,而是要找出他想要完成的方向,以便再用今后的努力来接续他、继承他。
附带补充一点,以往还真没怎么注意过,只是写到这里才偶然读到,又有学者在直言不讳地批评说:“吴冠中写的字根本就不叫书法……混淆书法与绘画的界限……”
实际上,这又涉及另一种更复杂的困境,即在西方“艺术”观念的冲击下,中国书法所遭遇到的归类“两难”。只不过,真想厘清这个复杂问题的话,就需要长得多的论述篇幅,没办法在这里顺便讲清楚。所以,这里就仅限于再提一点疑问:如果我在前边希望“同情地理解”,才委婉地指出拥有“两支笔”的吴冠中,既画出了最能“吸金”的画作,偏又由此更不满足于自己的状态。看起来,在普遍都把“大卖”当作“成功”代名词的大环境下,也许艺术市场对于艺术心灵的掌控,比我原本预估的要更加全面和凶狠吧?
二○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于浙江大学中西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