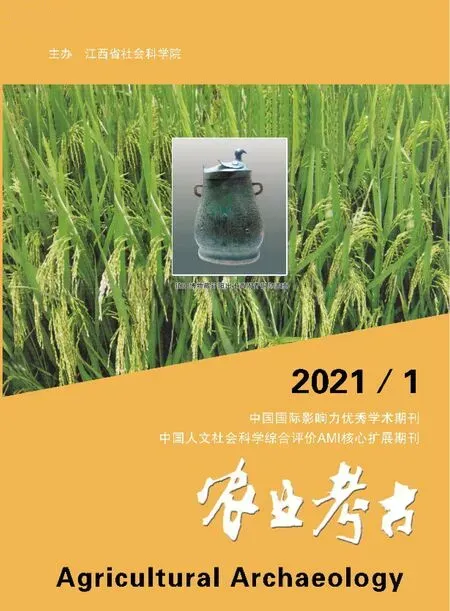荒野与聚落:20世纪上半叶川西北羌族的景观经营及生态意蕴*
2021-03-01黄学渊
周 莲 黄学渊 张 蕾
周莲,女,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景观遗产保护;黄学渊,男,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乡村景观历史价值与保护;张蕾,女,博士,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助理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业史、环境史。
20世纪以前,学界对羌族缺乏科学系统的认识,历史文献中常将川西北羌族地区视为蛮荒畏途,对其地理与景观的认知十分粗疏。自清末以降,伴随着西学的传播与中国西南科考活动的开展,尤其是在西方“种族-族群”概念的影响下,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有关川西北羌族的研究开始受到学界的重视。20世纪上半叶为川西北羌族研究的开端,兼有学者身份的西方传教士和中国知识分子纷纷进入川西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以亲历见闻的调查资料为主要成果。他们虽受限于自身文化背景,对羌族的认识并不全面,但作为羌族历史的见证者,其调查资料是建构羌族文化和历史的重要凭据。除此之外,羌人的口述史材料和石刻文献也从不同角度反映出羌族的历史景观特征。本文以生态视角分析20世纪上半叶川西北羌族地区的历史景观,梳理景观类型及其特征,力图兼顾主观的记忆、认同与客观的史实背景,探讨羌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内涵。
川西北区域群山万壑,山高而陡,山脊多为锯齿状,谷险涧深,水流湍急,属于高山河谷地貌。冯汉骥[1](P411)、李任培[2](P58-68)、胡 鉴民[3](P34-60)、杨 怀 仁[4](P11-29)等学者普遍认为羌族主要分布于川西北汶川县、茂县、理县、松潘县沿岷江河谷,及其支流之河谷。历史研究、田野调查、考古发现形成共识,传统羌寨分布于垂直高度1500米至3000米左右的山头与山坡,沿河流而居者仅占极小部分[3](P34-60)。本文主要以居高山和半山的传统羌族村寨展开讨论,他们保留着古老的信念与传统文化[5](P41),聚落选址布局独具特色,具有石砌民居建筑、高耸的碉楼和紧密联结的聚落景观。本文按照人为干扰程度的高低,将川西北地区的羌族景观分为居住景观、生产景观与荒野景观,并依此展开讨论,其中人为干扰程度最低的是荒野景观,其次为生产景观,最后为居住景观。
一、荒野景观
(一)荒野景观的表征及内涵
荒野景观是在自然规律主导下,没有人迹,或虽有人到过、干预过,但没有限制或影响其自然规律的非人工陆地自然环境,如原始森林、湿地、草原以及野生动物生存的迹地等[6](P64-69)。荒野的本意乃是纯粹的自然状态,象征着自然的秩序[7](P167)。川西北地区是人烟稀少的寡居之地,仅有小部分条件较好之地作为生产及居住之用,而大部分区域属于荒野景观。1934年中国影像人类学先驱庄学本在攀登杂谷脑流域高山森林时,以游记经历的形式记录了当时川西北羌族地区荒野景观的生动场景:“我们向一片大林中钻,合抱的灌木遮住了阳光,在黑暗中发现地上非常潮湿。拉人的刺藤很多,我们似乎在人丛中走,需要躲闪一棵一棵的大树。一会儿一条小溪从树林中泻出来,唱着忧郁的歌。”[8](P72)在庄学本笔下这是一片人迹罕至的土地,这里有着自然的原本面貌,也是生态之根,文化之始。地理学家刘恩兰在川西北地区考察时同样对当地的荒野景观有着极高的评价。受西方科学教育与北美、欧洲旅行经历的影响,刘恩兰对景观有敏锐的洞察力,她称赞川西北地区的荒野美:“紧接四川盆地西缘之高山地带,景色瑰丽,可以媲美美国洛杉矶之国家公园。区内草原起伏,与冰山相映,是华西高地聚落社会之乐土。”[9](P27-29)川西北高山河谷的地质奇景令刘恩兰联想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国家公园的壮观景象,传统羌族聚落社会与自然环境间的协调关系,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景观形态,具有自然美、野性美的特征。
羌族历史表明,迁徙是羌族先民生存的必然选择,川西北的地理环境构建了一个个封闭安全的生存空间,是避世的理想之地。川西北地区为东北西南走向之褶曲带,岷江及其支流将褶曲切割破碎,刻凿出不同的峡谷区域,也被羌族称为“沟”,羌族就分布在岷江河谷大大小小的“沟”之中。地理学家杨怀仁认为岷江河谷空间格局为近代下切V形峡谷套入昔日冰川所成之U形高山老谷中[4](P11-29),V形峡谷区气候干燥,风沙强烈,山体裸露,“山坡间只间有零碎生长之艾蒿及荆棘,除极小范围引山溪以资灌溉之区外,大部分为荒漠不毛之地”[4](P11-29)。而U形高山老谷风力较弱,气候远无峡谷区干燥,土壤湿度略高,施以灌溉,则可耕种进行农业生产。羌寨往往选址于地势高耸险峻的U形高山老谷(见次页图1)。杨怀仁刻画了一个生长于广大荒野中的羌族,在其环境中占极小比例的聚落是人性化的世界;相反,聚落周围放眼而顾的地表是看不到边界的自然荒野。刘恩兰发现山麓至山巅地理环境不同,导致地表景观与植物分布有较大差异。在生产生活中,羌人每天面对的是谷地汹涌的河流,峡谷区的干旱气候与雄伟的地貌,高山上的茂密森林、草原及雪山景观,这种自然环境孕育了羌族对天地、山川、林木、野生动物的亲切感与敬畏感。荒野带来的资源匮乏造成人群间冲突频繁,迫使羌人深入高山老谷,以高山峡谷为地理屏障,重视对山水形势的利用,选址大多位于半山有溪流的小台地上,以利于对高山森林资源的取用,半山山地资源的垦殖,峡谷荒地资源的利用。
(二)荒野景观中的和谐共生
羌人的生活十分贴近大自然,人与荒野是和谐的邻里关系,而不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在《分万物》[10](P256-258)经典中,羌人认为人类、动物、植物、山脉、江河都是同根分化出的邻居,体现出羌人认知到自身是自然的一部分。在《费伢由狩猎变农耕》[10](P2182-2193)经典中,阐明了林地、耕地、荒野地的范围明确、保持秩序,体现出羌人经济活动与自然系统相协调,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愿景。在《巴》[11](P12)经典中,描述了羌人为适应外在生态资源,生活在半山间,以便结合高山、半山和低坝三段不同的景观资源予以分别利用。在羌人的口述经典中,还记载了很多神话,其内容涉及到整个自然,反映出羌人对自然的认知。川西北地区整体环境恶劣,食物算不上充足,但资源丰富的荒野景观确实给羌人提供了多种生计方式以维持生存。王明珂在20世纪90年代对川西北羌人做有关“环境与经济生态”的口述访谈时,40岁以上的受访者均认为:“从前这一带地方都是森林密布。森林主要由松木林构成,森林上方近山棱的缓坡(高度约在海拔3500—4000公尺),由于日晒充足是良好的草场。森林下方的半山腰,被人们开辟成梯状的农地。整个山区除林木外,盛产各种药材、菇菌类以及野生动物。”[12](P328-330)可见森林密布、草地优质、野生动植物繁多的荒野景观使羌人居住地成为一个个自给自足的生态区。
羌人本身对自然万物及其运行规律的理解,不同于学者科学的态度与认知。羌人对于难以控制和征服的自然环境,衍生出对自然的敬畏心理,借助神灵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了古朴原始的生态观。以万物有灵的观念展开阐述是羌人解释自然的途径,他们相信周围的世界由神灵组成。在这种原始落后观念的影响下,羌人从自然界中获取任何的物质生活资料之前,都必须要面对神灵。刘恩兰记录了每年在端公领导下举行的祭山典礼:“五月初,当雪融解冻时,宰一羊以祀山神,然后居民始可入山樵猎……十一月间之‘关山节’,献六羊一牛以谢众神,自后封山。待来春开山节后,始可再入山工作。”[9](P27-29)祭祀作为羌人与神灵沟通联系的方式,其本质是协调羌人与自然关系的途径,羌人对神灵虔诚的态度和隆重的仪式体现了对自然的崇拜、敬畏和顺从。羌族传统祭祀活动的存在,不断提醒着羌人对待自然应该保持尊重的态度。川西北地区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民国时期的木材工业兴起,岷江两岸汉族居住与活动的河谷地带森林已经遭到严重破坏,而羌族传统活动领域内的森林生态体系破坏程度小,其中缘由在于羌人敬畏自然,“视森林为神出鬼没之所,不敢轻易侵犯”[3](P34-60)。1902年茂县牛家山护林碑言:“有不肖之徒,私自偷砍,并剥树皮,以致树林不茂,村中常有祸非。”[13](P1640)碑中描述羌人将树林的良莠与人类的福祸相联系,人为偷砍破坏树林会使整个村寨被神圣力量惩罚。这种对待荒野的态度是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产生的,但尊崇神灵比遵守规范更能为传统羌人所接受,将森林神圣化更有利于森林保护规范的落实和生态保护观念的传承。羌人顺应天时,遵循着荒野景观的内在秩序,不仅注重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和有限利用,其他渔猎采集活动也有规定时间。胡鉴民在羌区田野调查中发现:“除农牧害之打猎自无须有规定之时期……羌人则照例于每年八月半前后开始打猎……关于打猎的活动,羌民除遵照上述的传统外,遇到旱魃为虐的非常时期,亦有类似中国禁屠的习惯。”[3](P34-60)他十分赞赏羌人对荒野环境的敏锐感知能力,以及在危机条件下迅速调整生存策略的能力。羌族地区还保存着许多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14](P25),在羌族的民间故事中,野生动植物被赋予灵性,恣意浪费资源会引发天灾人祸[15](P323-327)。可见羌人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兼顾其他生灵的生存与发展,反映出尊重荒野、保护荒野的责任意识,是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体现。
二、生产景观
(一)生产景观的表征及内涵
以农业为主的多元化生产方式是羌人在具有明显垂直差异的荒野环境所做的适应。且资源匮乏使羌人必须走入深谷高山,以利用各种边缘资源。羌族的神话观念中十分重视土地神,反映出农业在羌族生产中的重要地位。《青稞和麦子的来历》[10](P2160-2176)经典描述了羌人的农业景观是从荒野中发展而来,且生产景观与自然环境相适应后具有原始的田野美。在《女神木姐珠》[14](P99-100)经典中,羌人读卡在一年的十二个月份分别送给女神妻子不同的花作为礼物,体现了羌人的农业生产不仅是满足物质层面的需要,也具有对田野景观审美的需求。
在对羌族的考察中,范文海观察到羌族景观布局的美感:“俯首下望,杂谷河如带,整齐的麦田,石砌的建筑,点缀着这幽深的河谷;平视,有皑皑的雪山屹立在波浪起伏不定的山里;后面有从未被人砍伐的松柏,人们都在鸟语花香安静的田里播种着金黄色的玉米粒子,高兴的时候唱起山歌,其乐陶然。”[16](P2-9)在范文海眼里,羌族景观具有高山河谷营造出的地形美、石砌建筑的艺术美、麦田整齐的造型美、农忙播种的人文美。羌人的生产生活与环境生态间呈现出良好的平衡,维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可持续景观。章松涛注意到羌族田野景观色彩的搭配:“在一座座巍峨的高山的山腰台地上,满种着玉蜀黍或是荞麦,一条条山沟的附近丛生着灌木,或是常绿的乔木。而在这些山沟的附近,玉米田中矗立着孤立的碉堡。排列着层层密密的堡垒式的建筑。黄色的墙衬着翠绿的背景,再加上蔚蓝的苍空,色彩是如此的鲜明而调和。如果在山野遍开着粉红的荞花的时候。这样的境界也许就成为诗的或者是童话的境界了。”[17](P2-7)荞麦具有很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在土壤贫瘠的川西北地区大范围种植亦可防止水土流失。除了作物的角色,其茁壮成长并形成粉色花海而带来的强烈视觉冲击附加了美学的价值。在群山巍然的荒野之间,古朴的黄墙搭配着蓝天、绿树和花海,羌寨融入周边自然环境,达到浑然一体的自然审美效果。
(二)生产景观中的生态智慧
杨利普等人看到岷江峡谷山势陡峭,风化强烈,水土流失严重,羌人进行农业生产十分艰难,“荒地占本区地面之百分之六十,坡度逾40度之地几全部荒芜”[18](P30-34)。“所有羌民的社会单位均各别分布在山谷中溪流(沟)两岸……现在的羌民是以农业为本的民族,当然有许多经验与方法。他们知道按农作物的性质选择土壤,决定培植方法;以及如何休养地力,节省劳力,如何施肥等等”[3](P34-60)。农业景观受环境的影响极大,岷江峡谷十分干燥,若不施以灌溉,则无法耕种,羌人“仅能勉强旱耕,且时常荒歉,尤苦旱灾”[4](P11-29)。受焚风效应和季节性洪水灾害的影响,羌人在农业生产中须时刻预防旱灾与洪涝。羌人的农业生产深受水的制约,“治水”成为羌族口头文学表达的重点主题,在羌族史诗尼萨唱词中详细描述了河流的起源和分布等情况[19](P166-171),体现了羌人合理运用自然规律来治理水灾。且在一代代流传的唱词中将治水经验传承下来,深刻影响着羌族在水危机环境中的景观经营。胡鉴民调查发现羌人农业生产中体现了因地制宜的生态智慧。一方面,“羌民所有的农作物差不多都是旱粮。但是多种旱粮间亦有差别。以小麦与青稞比青稞较能抵抗湿度与寒冷。血格三寨羌民似乎知道这种关系,因为他们在山坡梯地种小麦,而将青稞种在低湿地上。青稞因能抵抗湿度,故羌地凡有水田之处,均将青稞种在水田,且能收获两季”[3](P34-60),根据农作物的生长习性择合适湿度的土地。另一方面,“理番九子屯耳瓦寨之田亩中有泉水,不涸不涨,筑有水闸,积水地面颇广”[3](P34-60),羌人适应地形修筑水利设施以躲避水患。刘恩兰观察到羌人的农业生产景观还与日照、土质、土壤湿度、温度等因素相适应,因时因地而产生丰富的变化[20](P12-14)。羌人能辨别不同种类的土壤,不同海拔高度的土壤达到适宜作物生长的湿度、温度环境的时间不同。羌人根据土地的特质适时开展不同的农事活动,合理安排农业生产、牧业生产及建造房屋等不同用途的土地资源。王钧衡描述了山脚河谷十分贫瘠荒凉,而羌人的农业生产选择半山腰平坦开阔的土地,略加整理,形成层层相叠的梯田景观(见图2),与山脚河谷的景象截然不同[21](P42-45)。可见羌人在生产实践中积极协调人地关系,具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
生活在资源匮乏的川西北高山河谷地区,其生存会面临着许多风险,而互助共享是一种避免风险的手段。胡鉴民考察羌族多元的生计方式,认为羌族向大自然获取生活资料是以集体方式进 行 的[3](P34-60)。羌 人 务 农 时 通 常 为 邻 里 合 作,羌族的畜牧业除以家庭为单位外,也有大规模的合作的组织,有广大的公共牧场,保留着共同牧场制度。此外羌族每寨必保存或培植的“神树林”也具有悠远的历史。羌寨附近的“神林”,任何人不得随意砍伐[22](P15-24)。释比经典《祭神林》[10](P2227)中也阐述了神林的重要性。“其神林及山神,均为一寨所公有,而一寨又有一寨之公山,为该寨樵苏之所。”[1](P430)在羌族地区,许多公共土地被保护下来,所属区域的羌人拥有共同的开垦权、放牧权、打猎权和采集权。保留公共景观有着诸多优势:首先,有利于羌人之间共享互助,凝聚集体的力量用于改善和保护环境,学者们普遍看到川西北羌族地区有着修整统一的作物、天然美观的丛林丰草、瑰丽美艳的高山花卉、珍贵罕见的中草药材、遍布林间的珍禽异兽。其次,公共空间具有较强的转变能力,使得空间恢复力显著提高,能够有效利用资源,提高抗干扰能力,维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而议话坪作为羌族集体沟通交流的场所,村寨在这里民主协商、制定严格明确的规则。1907年萝卜寨议话坪护林碑道:“两村团、乡、保、甲、会首议论,东山所惜神林、家林、松木林护好,以培本村风水,不准开砍。花户所喂牛、羊、马匹,不准在林散放,践踏神林。”[13](P1647)记录了萝卜寨羌人在议话坪商讨对天然林与人工林的保护措施,共同制定了树林的保护边界、对象、目的以及行为规范。议话坪的存在,规定了打猎和采集活动的种类、数量及时期,对生活中取水、伐木亦有要求。一方面能够规范资源取用,限制人们对资源的过度掠夺,防止生态失衡;另一方面交流各自对环境变化的认识,以村寨集体智慧处理环境恶化问题,能高效、迅速应对与解决环境危机。
自然环境对生产方式起着重要作用,土地资源的匮乏带来了人口压力,影响了生产景观。在农耕景观方面,农业采取的是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并且扩展到边缘山地,形成天然梯田。梯田使得不同生长习性的作物在合适的土壤湿度、土地肥力下达到最大化的产量,以调适人口压力。而单一的农耕无法满足生存要求,尽可能地把精力投入到更多元的产业中,以集体方式获取生活资料,有效避免生存风险,才能保证在环境限制下可持续发展。遵循自然法则,效法自然,主动维护生态可持续循环,是羌人生产实践中的传统智慧。
三、居住景观
(一)居住景观的表征及内涵
荒野带来的资源匮乏造成人群间冲突频繁,使部分羌人选择居住在便于防守的高山村寨。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以及严酷的周遭环境使羌人有了安土重迁的观念,而聚落的日益稳固则会形成别具一格的景观特征。羌人仰赖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各种资源作为生存的重要依据,“寨之大小,须视耕地之广狭肥瘠而定,可谓全受地理环境之支配也”[23](P10)。聚落的分布与耕地的分布具有趋同一致性。川西北地区资源承载力有限,羌人遵循自然规律使人与土地资源达到和谐与平衡。学者范文海走访羌区时感受到羌区地土瘠薄,一个沟中有大小羌寨几个至十几个不等,村寨疏落,规模偏小,一个羌寨聚落的人口普遍偏少,人口密度低[16](P2-9)。高山环境缺乏平整宽阔的缓坡和台地,无法形成大规模聚居。同一片沟内的羌寨占据着各个土地平沃资源优良的区位,寨与寨之间尽管距离很近,彼此交通却十分不便,能有效防止族人的叛逆与出卖,因此构建了一个个封闭安全的生存空间。此外,羌寨往往立于险要处(见图3),“山下行人往来如织,从不一仰视,似不知山上有寨、寨中有人者”[21](P42-45)。利用地势使羌寨易守难攻,视野开阔,大大提高了聚落的安全性。
在英国旅行家伯德看来,羌寨外表单调,建筑的石墙高大又呆板,看不出进入的通道,独特突出的碉楼令人惊异[24](P270)。建筑黄墙平顶,堡垒森严,碉楼兀立云表,成为川西北地区独特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原始的建筑语言表达朴素的生态内涵。托伦士关注到羌族聚落牢固的团体聚居方式:“四五十家或更多的房屋为了聚居而修在一起。有时它们全都面朝里面,而连结在一起的后墙却成了外壁垒。为防御相宜起见。陡峭的山梁或悬崖可能被选作房址。房位这么高,密密地沿着山脉而建,其外观很像扩大了若干的中世纪城堡。”[5](P20)他描述羌寨选址在险要易守之地,并且以联结一体的景观布局对抗外来强敌,避免侵略带来的精神屈从与景观同化。聚落依山而建,随山势变化而变化,保存着稳固且独特的原始美。同时,在托伦士眼中,羌族新奇独特的景观被赋予了一层异域风情。羌寨整体景观氛围有着巴勒斯坦或中东聚落的朴拙风格,建筑形态像是典雅的中世纪堡垒,碉楼则像是规则且笔直的工厂烟囱。同样来自西方的葛维汉有着更科学严谨的观察视角,“在村寨,民居之间是紧紧相邻的。街道很窄,宽度通常在1米左右,很少有超过3米的, 这给村寨一种石筑高墙的筑城外观”[14](P20)。定居农业的生产方式依赖于河流,再加上狭小河谷阶地制约着聚落的分散性发展,聚落多结合自然地形紧密聚合并分层错落布置,一方面节约耕地、减少开挖,另一方面,紧密相连的房屋能够更方便族人之间生产合作与抵御危机。学者高中润在理县看到羌族聚落景观巧妙的与地理环境相适应,建筑布局自由且错综复杂,“屋舍毗连,走道湫溢。有时街路亦自私宅通过……羌戎各民族皆聚族而居。其数多寡不等,大者数十家,小者数家。依岗据险,屋舍层叠。望之如堡垒,近之似圈围。普通称之即寨是也”[25](P17-19)。羌族建筑间的界面相互穿插连接,为羌人的日常活动创造更多可能性,创造了丰富的景观形态,有着生气蓬勃的空间氛围。羌寨内部通过复杂多变的布局,外人进入如迷宫,而族人在其中则不受影响。除去战时防御功能,羌寨为羌人构筑了一个内向认同空间,与生产活动以及社会网络相辅相成。
(二)居住景观中的生态适应
羌族建筑依山势而建,所有材料都取自自然,是适应川西北特有自然环境的原生态民族建筑。1933年叠溪大地震给岷江峡谷带来了严重的破坏,震区房屋损毁严重,但李任培发现羌寨受灾情况较轻[2](P58-68),除了羌寨选址尽可能的避开山崩滚石地段,稳固的建筑也能有效避免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带来的进一步伤害。羌族建筑的形成是地形、气候及文化宗教等因素影响下的复杂产物[4](P11-29)。学者普遍认为,一般羌族住宅模式为五层堡垒式,门窗开口小,外形系一正四角锥台立体[23](P10-12)。从建筑结构来看,房屋地基夯实坚固,能防潮防震,是整个建筑的安全基础。四面墙体稳固方正,墙体下厚上薄,逐渐内收,形成汇聚中点的向心力,建筑即使只采用最基础的原料,也能凭借高超的经验技术异常牢固,在地质灾害多发的岷江峡谷屹立不倒。从地形地势来看,川西北山高而陡,平地弥足珍贵,建筑竖向发展有利于节省平地。从气候条件来看,川西北地区气候干燥雨量稀少,平屋顶足以避风雨,天晴则利晾晒。此外墙体厚重、门窗孔洞也较小,能起到良好的防风保暖作用,极大适应了寒冷的气候环境。另一方面,为节约耕地使得建筑层数较多,房屋底层囊括畜圈和草料堆放空间,中层有粮食存储空间,并以屋顶平台作为晒场。居民景观与生产景观结合紧密,平屋顶作为羌族建筑的一大特色,能适应多样的使用需求。如托伦士眼中的平屋顶,利用厚实的木板与柴板或竹子以土夯实的方式使屋顶坚固又防漏,其中放上荆棘以防鼠患,形态略微倾斜使其具有良好的排雨导洪功能,且利用低矮栅栏进行半围合,建立半开放半私密性空间,营造相对安全的环境氛围[5](P19)。范文海则提到屋顶作为瞭望空间可获得更多环境信息[16](P2-9)。胡鉴民认为平屋顶作为晒场是适应当地高山环境日晒短的结果[3](P34-60)。葛维汉描述屋顶作为乡间生活的公共空间,是羌人进行日常劳作与交往沟通的场所[14](P19)。此外,“至于各个住宅之交通,均借道屋顶”[23](P15)。羌人对环境的适应和对建筑的精心营造,成为人地关系和谐的重要力量,自然、居民与建筑共同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四、结语
(一)生态环境变化与川西北羌族面临的挑战
通过以上对荒野景观、生产景观和居住景观三方面的讨论,可以看出,羌族景观中体现出一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具有自我调适功能的生态文化(参见图4)。当前川西北羌族聚落景观呈现明显的恶化趋势:石漠化、森林破坏、水源污染、土地贫瘠、化肥农药过度使用以及震后安置区景观千篇一律。原有的生态环境已不足以支撑起人类活动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的恶化严重威胁着羌族的传承与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当初为响应政府的号召,过度开发川西北地区的森林、矿产、药材等自然资源,乱砍滥伐现象严重,造成羌族聚居区生态环境严重失衡。地表植被的破坏导致土地涵养水源的能力有限,原本稀缺的可耕种土地更加贫瘠,传统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再加上商业经济的诱因,许多羌寨中的男子都在农闲时外出打工、做生意,羌族传统村落人气差,呈现破败之势。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疾病得以控制,羌族人口大幅度增长,人口压力使得羌人扩大耕种区域,选择在更适宜农业的河谷地发展,缩短了生产的间隙,导致过度消费地力;且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造成局部地区土壤板结、酸度增加、耕作层变薄、水土流失及土壤肥力明显不足等问题。到了21世纪,许多羌人并不住在村寨,大批青壮年远离家乡外出打工,在家乡与城市之间流动。绝大多数羌族年轻人已完全汉化,对羌族传统文化不甚了解。汶川“5·12”大地震给川西北地区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灾难,古老的羌族文化遭受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不少羌族民居在这次极端震灾中损毁,羌文化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因此面目全非。在震后政府异地安置政策的引领下,新的生活环境又引起生产方式、生活习俗的改变,导致民族的进一步汉化。
(二)羌族景观经营的现代建构
生态文明时代之前,人们谈环境基本上不涉及荒野,或者说不重视荒野,而在生态文明时代,人们对环境的认识,使荒野具有重要地位。地球上的生态主要是靠荒野来维持的,荒野是地球生态之根,是实现地球生态修复的希望所在。如果地球上的荒野保护地过少,地球的生态修复就难以维持。因此川西北羌族地区的荒野景观具有多元价值,其主要价值为生态价值与民族价值,同时还包括社会、文化、精神、经济等多重价值。应将荒野景观保护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我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和自然保护地体系重构的背景下,探讨建立少数民族地区荒野景观保护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依托政府政策提升荒野景观的保护力度和管理质量,以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景观,为当代与后代留下弥足珍贵的自然与文化遗产。
生产景观是自然和社会条件相互作用下的表现,人类对生产过程的干预能力,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提高。合理的生产景观有利于区域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生产景观需要得到不断的维护和发展,对其进行科学控制和管理。居住景观是羌人世世代代的生活方式和经验累积在外部世界的具象化表达。羌族聚落、民居、碉楼都可能成为羌人内心追求稳固安全理念的外在表现形式。应在自然发展的基础上,结合不同的地理条件,建立现代化景观分区保护体系,进行核心保护区、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的划分。川西北羌族地区的景观本身具有高度的文化审美价值,应以此为基础,适当发展全域旅游项目,让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和独特的景观资源吸引外来游客,带动地方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