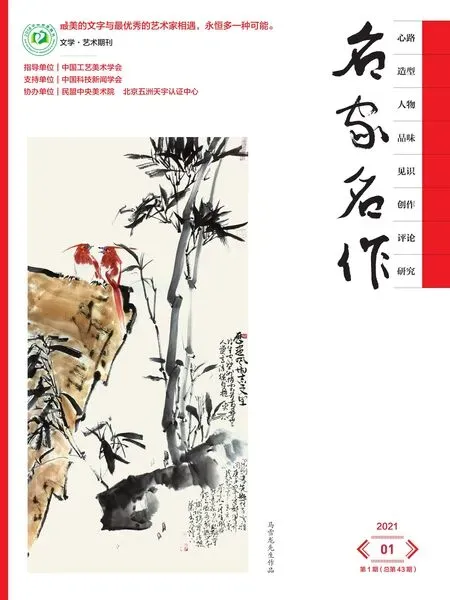董其昌与云居寺“宝藏”
2021-03-01翟杜鹃
翟杜鹃
一、“宝藏”
1.“宝藏”
董其昌书“宝藏”,质地为青石,长方形,高45 厘米,宽96 厘米,厚11 厘米。刻石镌刻于明崇祯四年(1631 年),原嵌于石经山第六洞窗上,现存云居寺。碑记如下:
宝藏
董其昌书
司爟氏新安许立礼,同侄中秘志仁,文学谢绍烈、黄玉虬、何如霖、田鐩、李自杰游小西天勒石。大明崇祯四年三月四日。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上海松江人。万历十七年(1589 年)举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太子太保等职。崇祯九年,卒,赐谥“文敏”。董其昌才溢文敏,通禅理、精鉴藏、工诗文、擅书画及理论,是晚明最杰出、影响最大的书画家。存世作品有《岩居图》《明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册》《昼锦堂图》《白居易琵琶行》《草书诗册》《烟江叠嶂图跋》等。著有《画禅室随笔》《容台文集》《戏鸿堂帖》(刻帖)等。
许立礼,字季履,号莲岫,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今属安徽)人。明代官吏。荫生。历仕中书舍人、工部主室、员外郎、云南府知府。许立礼的父亲许国,是董其昌的老师。
许国(1527—1596),字维桢,明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今安徽歙县)人。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考中进士,历仕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先后出任检讨、国子监祭酒 、太常寺卿、詹事、礼部侍郎、吏部侍郎、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万历十二年,因“平夷云南”有功,晋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死后,朝廷追加谥号为“文穆”,著有《许文穆公集》。
董其昌为许国作《太傅许文穆公墓词记》中,“公之诸子季履中舍辈以为是役也,天子给秘器以宠之,命皇华以督之,虽莬裘之卜经,始于达生”,其中季履指的就是许立礼。
除董其昌与许立礼外,题记中游玩的其他人,皆不可考。

天津图书馆藏《许文穆公集》,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许立言、许立礼刻本

房山云居寺石经山董其昌题“宝藏”拓片
2.董其昌“宝藏”与米芾“宝藏”
董其昌题“宝藏”,一方面应该是感慨房山石经刊刻这一浩大工程,以及古人佛教信仰的虔诚深远;另一方面很可能是对他高度关注、推重并引为楷模的米芾的致敬。
米芾(1051—1107),初名黻(fú),后改芾,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鹿门居士。祖籍山西太原,迁湖北襄阳,后定居润州(现江苏镇江)。曾任官校书郎、书画博士、礼部员外郎等职。米芾是北宋著名的书法家、画家、书画理论家,能诗文、擅书画、精鉴别,尤精擅篆、隶、楷、行各书体,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合称“宋四家”,其传世书帖、碑帖、书卷散见中外博物馆,名重四海。
米芾书“宝藏”碑,历史记载有过两次。一次是在北宋崇宁三年(1104),米芾任安徽无为县军使知州时为千佛禅寺所书。再一次是在熙宁年间(1068—1077)任广东英德县、浛洸县县尉时为浛洸司所书。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两通碑刻均遭毁坏,仅有无为县千佛禅寺复刻“宝藏”木匾一纸拓片传世。
董其昌书“宝藏”与米芾所书“宝藏”均为行书,雄浑有力,纵横奇宕,豪逸有气,以势为主,天然痛快。
董其昌论书主要是以提拔形式集中于他的《容台集》《容台别集》以及《画禅室随笔》中,其中关于米芾的题跋就有百条左右,由此可见他对米芾的推崇。
《画禅室随笔卷一》中董其昌直接用“宋朝第一”来评价米书:“米元章尝奉道君诏,作小楷千字,欲如黄庭体。米自跋云:‘少学颜行,至于小楷,了不留意。’盖宋人书多以平原为宗,如山谷、东坡是也。惟蔡君谟少变耳。吾尝评米书,以为宋朝第一,毕竟出东坡之上。山谷直以品胜,然非专门名家也。”同卷另有一条评价:“然自唐以后,未有能过元章书者。”而且,从董其昌对其他书法家的评价中,也能看出其对米氏的重视,《容台别集卷四》中有:“元之能者虽多,然禀承宋法,稍加萧散耳,吴仲圭大有神气,独云林古淡天然,米痴后一人也。”云林即倪瓒(1301—1374),初名倪珽,字泰宇,别字元镇,号云林子、荆蛮民、幻霞子,江苏无锡人,元末明初画家、诗人,“元代四大家”之一。董其昌在“元四家”中独推倪瓒,称其书法古淡天然,是米芾后第一人。可见在董其昌这里,宋、元、明三代书家以米芾为魁首。

安徽无为县千佛禅寺“宝藏”木匾拓片
二、董其昌与房山石经
董其昌不仅参访房山石经并题字“宝藏”,他还参与了明代房山石经的镌刻,明代刻经中留有题记“华亭董其昌助”。
明代房山石经大规模刊刻已经停止,明初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曾派名僧道衍(姚广孝),前往石经山视察。洪武二十一年(1388 年),姚广孝到达房山石经山,惊叹于静琬以来历代刻造石经事业之宏大,题诗《石经山诗》并序,“镌于华严堂之壁”。之后,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朝廷曾拨款修理过云居寺和石经山一次。又,据《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三载:“永乐十八年三月,旨刻大藏经板二副,南京一藏,六行十七字;北京一藏,五行十五字。又旨石刻一藏,安置大石洞。向后木的坏了,有石的在。”但明代官刻石藏后来似未实现。所以明初虽然对房山云居寺和石经进行了考察、保护和修理,但并未见续造的石经。
明代房山石经较为特殊的一点是明中期有道士募刻道教经典《玉皇经》贮藏石经山。宣德三年(1428 年),有全真教道士陈风便和正一教道士王至玄等,募刻道教《高上玉皇本行集经髓》《太上洞玄灵宝高上玉皇本行集经》《玉皇本行集经纂》《无上玉皇心印经》四部,共刻石八块,送至房山石经山贮藏(藏于第七洞)。根据跋文《无上玉皇心印经终传经始流》所记,这几部道教刻经的目的在于“刻金石,藏之名山,传之万世也”,这与石经山藏经洞开辟者静琬大师“镌凿华严经一部,永留石室,劫火不焚”的心愿非常一致。
成化年间,云居寺的住持以及保定府新城县信徒张普旺等,对云居寺和石经尽力维护,但是到万历高僧达观真可与憨山德清到云居寺访问时,云居寺石经山又趋于衰落。
明末佛教复兴,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年间,时有南方在京做官的居士葛一龙、赵琦美、冯铨、董其昌等以及佛门僧人等,在北京石灯庵续刻佛经《华严经》《法宝坛经》《宝云经》等10 余部,送至石经山瘗藏,因当时山上洞窟已满,便另辟一石洞贮藏,即今石经山第六洞。至此,房山石经较大规模的刻造活动停止。
三、董其昌与佛教
房山石经明末的续刻,一方面是由于晚明四大高僧之一的达观真可禅师在石经山雷音洞发现佛舍利,敬献慈圣皇太后,云居寺在京城声名大振;另一个原因是晚明时期,晚明四大高僧接引文人士大夫广泛学佛参禅,形成了一种居士化浪潮。陈垣在《明季滇黔佛教丛考》中指出:“万历而后,禅风寝盛,士大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欲与士大夫接纳。”这种居士佛教的兴起,支撑了大规模的佛教刊印活动的展开,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方册本《嘉兴藏》的雕造。
万历七年(1579),达观真可禅师感叹佛教经书卷帙重多,因此想要刻造方册,使佛法流通方便。万历十二年(1584),在慈圣皇太后的支持下,达观真可、憨山德清与陆光祖、冯梦祯、曾同亨等人商议刊刻方册大藏经,正式开始雕造《嘉兴藏》。《嘉兴藏》的雕刻,历经129 年,规模巨大,仅仅依靠僧侣们的力量难以完成,达观真可门下的居士们,比如陆光祖、焦竑、袁宏道、冯梦祯、汤显祖等,他们从人力、财力上都对《嘉兴藏》的雕刻起到推动作用。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房山石经的续造自然也成为晚明居士捐刻佛经,实现他们虔诚信仰的一种表现。作为捐助人之一的董其昌,在对他的书画研究之外,他的居士身份和佛教信仰,值得我们探讨研究。
1.明代佛教概况
明清以后,中国佛教步入衰微时期。明朝建立初期,明王朝推崇理学,强化专制统治,对佛教采取既充分利用又严格控制的政策。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设立善世院,管理全国佛教。其下又设置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员,实现对佛教教团的全面有效控制。洪武十五年(1382),又将天下寺院分为禅、讲、教三类,要求所有僧众分别专业。同时为了便于管理,对各类僧侣的服色也做出规定,不允许混淆。同年,又诏令禁止寺田买卖,在经济上加强对寺院的控制。明初废除僧侣免丁钱,度牒免费发放,但是对剃度有严格限制,度牒发放严控,限制良多。到明代中晚期,因为政治腐败、宦官专权、战事与自然灾害影响,为缓解财政压力,代宗景泰二年(1451),开始实施卖牒救灾,后世沿袭此法,直至明朝末年。这直接导致僧尼人数膨胀。
从佛学思想上来说,理学的兴起进一步制约了佛学的发展,理学家一方面批判佛、道,另一方面却吸收了佛、道的哲学思想和修行方法。在形式上,理学是以儒家为主导,维护宗法礼教制度,而在内容上理学则实现了儒、释、道三教的融合。面对理学的这种冲击,佛教努力适应宗法制度需要,不断推进世俗化。为了满足一般信徒的现世利益和个人愿望,明代佛教思想与儒、道思想结合得更为紧密,甚至吸收了民间信仰和神话传说。
在这种情况下,到明中叶时,佛教衰微已极。从宣德(1426—1435)到隆庆(1567—1572)近150 年内,禅宗、净土二宗均毫无声息。但是从万历(1573—1620)起,因“四大高僧”的积极推动,佛教复呈繁荣返照之象。
2.董其昌的佛教之路
晚明四大高僧中,董其昌与达观真可、憨山德清和云栖祩宏都有交往。
达观真可(1543—1603),俗姓沈,吴江(今属江苏)人,字达观,晚号紫柏大师。门人尊他为紫柏尊者,是明末四大师之一。达观大师一生广研经教,振兴禅宗,“始从楞严,归至归宗、云居等,重兴梵刹一十五所”,倡导刻造《嘉兴藏》多部。达观真可禅师的弟子门人众多,“入室缁白弟子甚多,而宰官居士尤众”,董其昌就是他的弟子之一。
董其昌与达观禅师的交往,在他的《容台集》《画禅室随笔》以及达观真可禅师的《紫柏老人集》中都有记载。《居士传》提到董其昌尚为诸生时,听真可禅师讲述文章与禅理,后又得真可弟子密藏道开的“激扬”,参禅悟道,渐入佳境:“参紫柏老人,与密藏师激扬大事,虽博观大乘经,力究竹篦子话”。“竹篦子话”是与禅师大慧宗杲有关的著名公案。达观禅师逝世后,董其昌为其做赞:
不妄视。眼不坏。不妄听。耳不坏。不妄言。舌不坏。不妄动。身不坏。不弄精魂不捏怪。这回方验真持戒。要与人天插个标。何妨地狱还些债。咄。债已还。有甚待。端端坐待老憨来。打破从前旧皮袋。一道神光火电飞。风流铁汉今疏快。
关于二人的交往,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四载:
达观禅师初至云间。余时为书生,与会于积庆方丈。越三日,观师过访,稽首请余为思大禅师大乘止观序。曰:“王廷尉妙于文章,陆宗伯深于禅理。合之双美,离之两伤。道人于子,有厚望耳。”余自此始沉酣内典,参究宗乘。复得密藏激扬,稍有所契。后观师留长安,余以书招之。曰:“马上君子无佛性,不如云水东南,接引初机利根,绍隆大法。”自是不复相闻。癸卯冬,大狱波及观师,搜其书,此书不知何在。余谓此足以报观师矣。昔人以三转语报法乳恩,有以也。
观师答问,常有不经人道语。余曾问:“菩萨处胎受生之后,还知前生为谁,如所云宿命通否?”师曰:“圣人无我,但受生之后,前生所作,循业发现,宛然如一日,安用自知为张三李四?许多我相。”又,余时方应举,日用攻举子业。余问:“此于学道,宁不相妨否?”师曰:“譬如好色人患思忆病,此人二六时中,宁废着衣吃饭一切酬应否?虽复着衣吃饭一切酬应,其思忆病相续不断,即作意断之,其病益深。”李太白诗曰:“抽刀断水水更流,是也。”有患烦恼尘缘能障道者,若为扫除。师曰:“如一男子,有杀父仇,怀愤欲报,拂拭纯钩,毕生寻觅。初闻张三,二十年后知此真仇本是李四,便舍张三,直觅李四。诸人欲扫除烦恼,正为未知真仇也。”此语与张拙断除烦恼重增病,更觉透彻。
今《紫柏老人集》,乃不见载,知法语所遗,多矣。
《紫柏老人集》中也收录了这两段,并载有真可禅师给董其昌讲解佛法的信,不过此信从内容来看似乎并非是董其昌提到的导致二人“不复相闻”的信。
缘起无生之旨,祖佛骨髓,而像季黑白,千万人中,求一二信者不可得。今足下于此独能信入。非夙具灵种缘因熏发,那来现行暂露。何快如之?
来书谓:“初颇畅快,兹又不活泼,若将失去,病在何处?”此既现行暂露,熏力稍微,自然隐没,不必生疑。惟宗门语句,不可草草。若以足下信入者,拟通其关棙,所谓“鲁君以己养养鸟”也。昔兜率悦问张无尽:“宗门葛藤,有少疑否?”无尽曰:“惟德山托钵因缘未了。”兜率厉声曰:“此既有疑,其余安得无疑?!”迳入方丈不顾,无尽由是发愤参究,然后大彻。今足下十有二三不透,则去无尽尚远,极当发愤,此生决了,不得自留疑情,遗误来世。
来示又谓:“念念起处,索头在手。”敢问足下。为念起处本即无生?为了念本空,乃契无生?若念起本即无生,则知无生者,念耶?非念耶?若了念乃契无生,则了者,谓有念了耶?谓无念了耶?有念则早乖无生,无念则无生谁契?于此透脱无疑,席几草庵借宿,犹非宝所。
第来示所谓“如何践履?如何保持?待力之充,及涉境试验”云云,自知时节矣,岂待贫道饶舌?贫道不惜口业如此,总是钵盂添柄。惟足下或宗乘中,或教乘中,大著精神,作个仇讎,务必搂破其窠窟,捣其栖泊,再共商量未晚。
从以上董其昌自述以及达观禅师的回信来看,对于这位学生的学佛思想和他的虔信程度,达观禅师似乎有所怀疑,从他的《与黄慎轩书》以及《与冯开之书》中提到董其昌的部分也可见端倪:
近见董思白,拶及此事,渠于不知不觉中,佛法习气渐觉生疏,横口褒贬古德机缘,判寂音决非悟道之僧。道人从容谓渠曰:“汝信大慧杲禅师悟道否?”渠曰:“是一定大悟彻的。”又问曰:“寂音乃大慧平生所最仰者,脱寂音果见地不真,大慧难道作人情,仰畏他耶?”思白俯首无语。
唐一所董玄宰辈,得一纱帽盖头,惟快情恣识,逞其素所不逞,宁暇及此。赵定老近有信占,宇泰中甫,当委曲时警家之。
憨山德清(1546—1623),俗姓蔡,字澄印,号憨山,法号德清,谥号弘觉禅师,安徽全椒人,明朝佛教出家众,为临济宗门下。其复兴禅宗,是明末四大高僧之一。董其昌与憨山德清的交往见于他自己的散文集《画禅室随笔》:万历十六年冬(1588),董其昌与唐元征、袁伯修、瞿洞观、吴观我、吴本如、萧玄圃同会于松江龙华寺,听憨山禅师谈“戒慎恐惧”之道。
云栖袾宏(1535—1615),俗姓沈,名袾宏,字佛慧,别号莲池,因久居杭州云栖寺,又称云栖大师。其提倡禅、净双修,是明末四大高僧之一。万历二十年(1592),董其昌题《金刚经》:“送云栖大师,藏云栖寺库。”董其昌自述,“每有追荐,大师出余手书,令僧持诵”。万历三十二年(1604),五十岁的董其昌应莲池大师之请,为云栖寺书写了《重建云栖禅院碑记》。万历四十二年(1614),董其昌六十岁。此年,他书《净土经》纪念莲池大师八十初度。董其昌称:“云栖莲池大师,甲寅正月八日初度,余以师纯提净土,扫彼狂慧,行在《梵纲》,志在《观经》。”《梵纲》是菩萨戒经,《观经》就是《观无量寿经》,是净土宗的重要经典。
董其昌的佛学之路,一方面来看是因为当时禅风盛行,士人居士受社会风气影响,另一方面与他本人的性格也有很大关系。从他的仕宦经历可以看出,他对政治异常敏感,一有风波,他就坚决辞官归乡,几次反复起用,在晚明政坛诡谲无常,成了难得的善始善终的一位士大夫。他在官场上不激不随甚至适时退隐的态度,可以看出他性格上的圆滑与谨慎,而这种性格也反映到了他的佛学信仰之路上,从他的老师达观真可禅师给他的回信以及提到他的评价来看,达观禅师认为这位学生的佛修之路有相当的功利性,以至于将“学道”与应举做官相比较。
明万历年间,达观真可来到房山云居寺,感慨:“涿州石经山为天下法海。自隋琬祖以来,龙象蹴踏,振扬宗教,代不乏人。逮我明,珠林鞠为草莽,金碧化为泥涂!”达观禅师在石经山上发现了佛舍利,并敬献慈圣皇太后,后又募缘修理了琬公塔。憨山德清撰写《涿州石经山琬公塔院记》记载此事。董其昌在他的晚年支持房山石经的续刻,游玩石经山并留下“宝藏”题字,不仅是对他书法上的“第一”米芾的致敬,还表达了对他老师达观禅师的敬意。理清这段历史,对我们研究明代房山石经,对了解明末居士佛教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