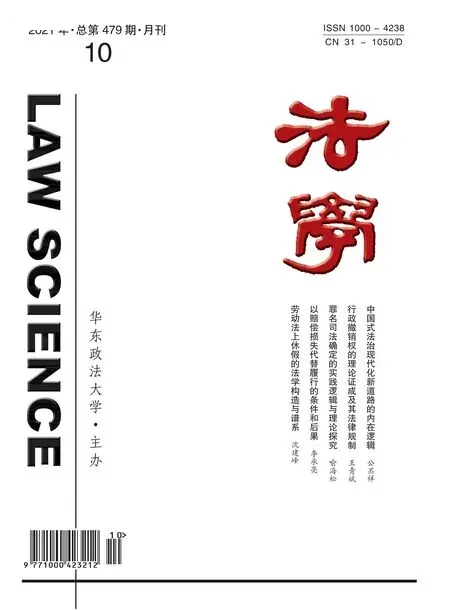结果归责与危险替代:介入型因果关系的教义重塑
——以医疗介入类伤害案因果判断为例
2021-02-27李川
●李 川
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介入因素的介入型因果关系认定问题一直是困扰刑事司法实践的难题之一。尽管在理论上持续发展中的因果关系诸学说为介入型因果关系的认定提供了相对丰富的教义学资源,即不管是传统的必然因果关系论、偶然因果关系论,还是后来发展的条件说、合法则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论等都试图为介入因素影响因果关系的判断提出一定的原理标准;但司法实践却体现出采纳上述理论成果的程度非常有限,尚未能形成判断介入型因果关系相对明确合理的清晰标准,由此导致围绕这一问题讼争不断,形成实践难点。这一方面是因为不同因果关系理论仍然存在明显差异与争议,实践中即便希望采纳理论成果也受限于理论抉择的困难而可能无所适从;〔1〕参见杨建军:《刑法因果关系的司法证明》,载《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6期,第82页。另一方面,刑事司法实践中借助典型判例,形成了一种实践中相对承继的、广泛接受的独特判断逻辑。〔2〕比如以《刑事审判参考》《最高人民法院案例选》中的诸多典型判例逐渐形成的、被司法广泛接受的介入型因果判断三重性标准。对其形成过程与判断标准,下文有详细论述。受此影响,目前因果关系理论上的新发展还不能说对司法实践中介入型因果关系认定产生了明显的积极影响。因此有必要在反思臧否介入型因果关系已有原理的基础上,将司法实践传统逻辑与因果关系理论新发展结合起来,为介入因素下复杂因果关系的判断提供更明晰、合理的参考基准。考虑到医疗介入类伤害案是介入型因果关系的典型情境,也是集中形成前述典型判例与司法逻辑的关键场域,以医疗介入类伤害案典型案件为例,可以最大程度体现介入型因果关系判断的核心争议,也可以明确检视因果关系相关教义学原理在适用介入型因果认定时的有效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以医疗介入类伤害案因果判断为例
(一)医疗介入类伤害案因果判断典型争议
相较于构成要件定型性已经解决了因果判断问题的犯罪,如盗窃等,人身伤害类罪案更容易产生因果关系争议,“由于杀人、伤害等罪的实行行为缺乏定型性,所以,当结果表现为他人伤亡时,引起该结果的行为是否属于刑法上的杀人、伤害行为,就难以下结论。”〔3〕张明楷:《刑法学》(第5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82页。而在本就易生因果判断争议的人身伤害案件中,介入因素导致因果关系判断更加困难,表征这一困境的典型情形就是医疗介入后的结果与伤害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难题。人身伤害行为发生后被害人得到医疗救治的情形非常常见,然而医疗过程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导致医疗结果受到诸如被害人不遵医嘱、被害人亲属放弃治疗、医疗过错等多重介入因素影响更加难以预测,进而时常引起伤害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争议;作为争议核心的医疗介入是否中断因果关系之判断时常存在着认定标准模糊与认定结论随机的问题,类同案例结论相反的现象时有出现。以如下两个典型判例为例。
【案例1】 2010年12月2日,谢某等将被害人许某殴打在地。许某于受伤当日被送到医院住院治疗,经积极治疗病情相对稳定。经鉴定许某系头部重伤昏迷,伤残程度一级。2011年3月24日医院应许某家属的要求,对许某拔除气管插管,降低用药档次,并于同年4月1日停止输液。许某在拔除气管插管和停止输液9个多月后,于2012年1月8日死亡。〔4〕本案为“巫仰生等故意伤害案”。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第1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4页。
【案例2】 2015年5月3日,曾某持钢管抡打被害人许某头部,致其脑部重伤。当日许某被送往医院救治,经紧急治疗后呈植物生存状态,8月9日经鉴定,右额颞顶部损伤程度为重伤二级,伤残等级为一级伤残。在病情稳定后被转入普通病房。2016年3月1日因未能续付护工工资,许某家属将其滞留在医院,不再负责护理,医院为许某提供基本生命支持用药和基础护理。2016年4月15日,许某因突发呼吸、心跳骤停经抢救无效被宣布临床死亡。〔5〕本案为“罗望、屠德宽等聚众斗殴、故意伤害案”。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第8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77-78页。
案例1与2对比,典型体现了人身伤害案件中介入因素影响因果判断的困境与争议:一方面,两个判例从案情来看有其共性,都是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了严重伤害行为,但被害人都被及时送医治疗。初次鉴定都是重伤或严重伤残,在医疗过程中,被害人家属都存在放弃治疗的行为,最终结果都是被害人死亡。然而另一方面,就家属放弃治疗的行为作为介入因素是否中断因果关系的判断而言,两个判例的结论却截然相反:案例1的判决认为,先前伤害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因被害人家属要求医院拔除气管插管、停止输液等拒绝治疗的行为所中断,因此不能成立。原因在于先前伤害行为之后,又介入了被害人家属主动要求拔除气管插管、停止输液等多个独立于伤害行为的积极因素,并最终导致被害人死亡。〔6〕同前注〔4〕,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书,第23页。相反案例2的判决却认为,先前伤害行为是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根本原因,被害人家属消极不配合治疗护理这一介入因素不足以阻断先前伤害行为致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即伤害行为造成被害人身体遭受严重伤害,死亡不可避免,外力因素介入后加速了被害人死亡,行为人仍然应对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承担刑事责任。〔7〕同前注〔5〕,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书,第78页。由上可见,这两个案例在类同的重伤案情下对介入因素是否中断伤害行为与死亡结果的因果关系作出了相反的结论。诚然,不同案例中具体伤情、家属阻碍治疗的程度及被害人延后死亡时间有所差异,但是两个案例的判决也并未明确表达这些具体差异对介入型因果关系的影响如何,判断介入因素中断因果关系标准如何,仅直接给出了介入因素是否中断因果关系的结论。这两个案例的对比体现出由于缺乏相对统一的判断标准与相对明确的论证过程,介入型因果关系的个案判断难免易生争议。
(二)介入类因果判断的实践三重性标准及其问题
《人民法院案例选》对案例1的注解说明该案因果判断结论的具体逻辑:即综合考虑介入因素本身是否异常、独立,以及在先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大小进行介入因素是否中断因果关系的认定。〔8〕同前注〔4〕,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书,第24页。若介入因素本身异常、受行为派生不独立,且伤害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大,则介入因素不能中断因果关系;反之,则介入因素中断因果关系。这一来自权威判例选编的介入型因果判断逻辑具有代表性,相关典型判例反复显示出对这一认定逻辑的确认和发展,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介入因素影响因果关系判断的实践三重性标准。因此需进一步检视的,就是这种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逐步发展的、用于判断介入型因果关系的实践三重性标准是否能有效解决前述两个案例代表的实践争议困境。
【案例3】 陈某用一支一次性注射器从自家农药瓶中抽取半针筒甲胺磷农药后,潜行至陆某家门前丝瓜棚处,将农药打入瓜藤上所结的多条丝瓜中。次日晚,陆某及其外孙女黄某食用被注射有农药的丝瓜后,出现中毒症状。送医后黄某经抢救脱险;陆某因甲胺磷农药中毒引发糖尿病高渗性昏迷低钾血症,医院对此诊断不当,而仅以糖尿病和高血压症进行救治,陆某因抢救无效于隔日早晨死亡。〔9〕本案为“陈美娟投放危险物质案”。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2卷),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34-35页。
案例3是刑事司法领域介入型因果关系判断的重要判例,经由这一判例明确形成了介入型因果关系判断的实践三重性标准。案例3的判决认为,尽管有医院诊治失误这一介入因素,但被告人的投毒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其主要理由是:投毒行为所诱发的糖尿病高渗性昏迷低钾血症是一种较为罕见的疾病,很难正确诊断;镇医院医疗水平有限,诊治失误可以理解。所以出现医院诊治失误这一介入情况并非异常,该介入情况对死亡结果发生的作用力较小,被告人本身的投毒行为具有较大的致死可能性,因此因果关系仍然成立。本案的判决理由中较为系统地归纳了支撑上述结论的介入型因果关系三重判断标准:“如果介入情况并非异常、对结果发生的作用力较小、行为人的行为本身具有导致结果发生的较大可能性的,则应当肯定前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10〕同前注〔9〕,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书,第35页。由此可见,这一案例明确了介入因素是否中断因果关系的三重判断指标,即在先行为对结果的作用力大小、介入因素的异常性、介入因素对结果的作用力大小。〔11〕这一标准参考了前田雅英的关于介入因素中断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并在涉介入型因果关系的判例如“龚晓玩忽职守案”(《刑事审判参考》第294号案例)“王俊超故意伤害案”(《人民法院案例选》2009年第2辑)等中被反复确认。参见[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第6版),曾文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9-121页。这个三重性判断标准在之后的“张校抢劫案”的判决理由中得到进一步确认与形塑:“成立中断的因果关系……具体判断标准为:一是先前行为对结果发生所起的作用大小。作用大,则先前行为与结果有因果关系,反之则无。二是介入因素的异常性大小。过于异常,则先前行为与结果无因果关系,反之则有。三是介入因素本身对结果发生所起的作用大小。作用大,则先前行为与结果无因果关系,反之则有。”〔12〕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编:《刑事审判参考》(总第79集),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1页。
这一实践三重性标准无疑对司法实践中判断介入型因果关系起到了一定的明晰标准功能。但是接踵而至的问题是这一实践三重性标准是否足够解决争议、形成相对合理一致的因果判断结论。不得不说从判断有效性与合理性分析还存在一定的疑问:一是受“作用力”“异常”等用语自身模糊性的影响,这一标准具体适用时可能因主观看法差异而结论不一。案例1与案例2中家属因没有财力放弃治疗是否算异常因素、放弃对昏迷的被害人的治疗是否属于对死亡结果的较大作用力等都可能产生见仁见智的不同看法。二是对因果关系有无的定性判断却以作用力大小比较的定量判断为依据,容易产生判断困难。作用力大小是相对何种基准而言不甚明确,在先行为与介入因素的各自作用力大小到什么程度才能发生质变的中断因果关系的效果也难以明确。进一步而言,还会出现在先行为与异常介入因素“作用力”性质可能根本不同而难以具有可比较性的问题。案例3中投毒行为、被害人疾病特异体质与医疗疏失三种不同性质的因素对被害人死亡结果的作用力大小其实存在比较上的困难,在分散投毒尚未达到一般致死剂量的情形下,投毒本身并不足以产生致死的作用力,被害人死亡是在有毒物质、被害人自身疾病及医疗疏失的合并作用力下导致的,三者作用力孰大孰小即使判决理由中也难以给出明确的比较标准。三是三重标准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判断逻辑也不明确,容易导致判断困难。比如在先行为与介入因素对结果的作用力都需要判断,二者是否是此消彼长或有先有后的逻辑关系都可能影响最终判断的结论,但实践三重性标准并未形成明确的先后判断层次,这造成了可能因为三重标准之间的判断层次逻辑不清而导致结论的不明确。比如案例1与2中,如果认为被害人家属放弃治疗的行为异常,是否也就不需要再判断两个作用力大小的问题而直接确认伤害行为与死亡结果的因果关系成立了,这一标准就未能明确。
(三)介入型因果判断的实践新发展及其困境
刑事司法实践中承继形成的实践三重性标准虽能提供一定的介入型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但仍难有效解决介入型因果关系的判断争议。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除上述标准自身的主观性与模糊性问题外,更深层次的根源在于这一标准是在因果关系的范围内试图以事实归因的逻辑解决结果归责的问题。受传统因果关系理论影响,司法实务中较少在刑事因果关系判断时区分事实归因与结果归责,而通常将因果关系的认定视为纯粹基于事实的因果律判断。〔13〕参见周光权:《客观归责方法论的中国实践》,载《法学家》2013年第6期,第126页。然而,刑案的因果关系判断不仅具备事实因果关系认定的作用,也在客观上承担着对行为归责的规范评价的功能。〔14〕参见张明楷:《也谈客观归责理论——兼与周光权、刘艳红教授商榷》,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2期,第304-305页。单纯基于必然因果关系说或条件说进行事实因果判断,在存在介入因素时无法有效明确介入因素是否造成实行行为与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中断。这是因为在事实层面上,无论是在先行为还是后发介入因素,只要能证明事实上参与结果促成通常都是造成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也就都是事实上的等价原因。如案例3中,投毒行为、被害人疾病与医疗疏失合并导致被害人的死亡,就事实层面而言都是导致死亡结果的原因。然而因果关系判断承担的功能不仅是确定事实上的原因,更关键的是要在事实认定的基础上判断结果是否归责于行为,以合理划定刑事责任的范围,否则就会出现通过因果链条无限回溯追责的不合理局面。如案例3中就会出现即使投毒剂量远小于致死量,死亡结果也会因为事实上的因果判断而被归因于投毒行为进而追责的问题。因此判断介入因素是否中断因果关系主要不是解决事实归因问题,而是解决基于规范判断的合理归责的问题。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提出的实践三重性标准本应以基于规范判断的归责评价为核心,但其主张的介入因素异常性、先前行为与介入因素的作用力等指标仍然是特定意义上套用了事实判断的逻辑:在司法实践中,异常性判断常常追求发生的事实概率足够大、作用力判断依赖于司法鉴定中参与度的定量分析,这就造成将本应进行规范价值判断的归责评价问题仍叠床架屋地进行事实归因判断,导致未有效解决介入类因果判断的争议。
意识到实践三重性标准在应用时仍然很可能落入过于追求事实因果律的窠臼而难以起到应有的归责功能,“李放故意伤害案”的判决理由提出对过度依赖事实定量判断的做法应进行调整:“医疗过错的鉴定意见只能作为判断被告人刑事责任大小的依据之一,而不能作为判断被告人有无刑事责任的依据”〔1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编:《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25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36页。,不能以鉴定意见中介入因素的事实参与度比例作为刑事责任的直接依据。此外,部分医疗介入类伤害案判例更进一步,通过规范意义上的责任分配来判断存在介入因素时的因果关系。
【案例4】 邵某与被害人许某发生厮打,邵某将许某左手拧伤,造成左手中指近指间关节脱位,经法医鉴定构成轻微伤。许某未按照主治医师医嘱进行理疗锻炼,出院后左手中指指间关节僵直,经法医鉴定构成轻伤。〔16〕参见贾宝祥:《不积极进行康复治疗不构成被害人过错》,载《人民司法》2015年第10期,第30页。本案判决认为邵某犯故意伤害罪,造成被害人轻伤,伤害行为与轻伤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成立。其理由在于“医疗行为作为阻断伤害结果发生的因素,不是多因一果案件的致害原因,致害人不能给被害人设置接受医疗、理疗和锻炼的义务,被害人不进行理疗和锻炼不构成过错……致害人不能因此对扩大的伤害减免责任。”〔17〕同上注,第30-31页。本案作为典型判例,首次从规范意义上基于义务与责任分配来推断因果关系,以被害人不负自我治疗义务为理由认为其不应承担伤害后果扩大的责任,即便被害人不遵医嘱造成伤情扩大也应由行为人负责,由此倒推扩大的轻伤后果与伤害行为之间可认定存在因果关系。相较于传统判断基准,这一判例在介入型因果关系判断上迈出了规范认定与结果归责的重要一步,但困境也随之而来。由于过分采用责任分配的倒推逻辑来判断因果关系、进行事实归因,这一判断逻辑也走向了忽视事实因果关系、单纯强调规范评价的另端,因果关系的判断成为一种划分责任的规范评价的产物,因果关系的客观性与事实性反而难以保证。科学的介入型因果关系判断基准应是一种兼顾归因与归责,在事实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合理划定归责范围的分层判断标准。
前述4个典型判例代表了人身伤害案件中医疗被害人可能存在的三大类介入因素:案例1与2介入的是被害人家属有碍医疗行为(如要求或直接实施停止医疗行为),案例3介入的是医疗疏失行为(未治疗、未及时治疗或错误治疗),案例4介入的则是被害人有碍医疗行为(不接受治疗或错误妨碍治疗)。而这4个案例也同时典型地体现出当前刑事司法中判断介入型因果关系的诸种具体困境:要么缺乏明确标准或理由(案例1与案例2),要么以事实归因的逻辑来错位解决结果归责问题(案例3),要么走向纯粹责任分配与规范评价的另端(案例4)。这就表明,实践中亟待在深入分析介入型因果关系教义原理的基础上,为解决介入因素影响因果关系的判断问题提供相对合理、有效的判断基准。
二、结合归因与归责:介入型因果关系的基本立场
(一)决定因果判断立场的因果关系概念界定
要在理论上分析介入型因果关系的具体原理,首先要明确关于因果关系概念的基本立场。当前理论上对因果关系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界定:狭义的因果关系将因果关系视为是物理的、事实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具体联接,因此判断范围仅限于事实上确定结果可归因于行为的联系;〔18〕参见林钰雄:《新刑法总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页。而广义的因果关系将因果关系视为具备事实与规范两种属性的行为与结果的联接,因果关系的范围不仅包括事实上结果对行为的归因,还包括规范意义上的结果归责。〔19〕参见劳东燕:《风险分配与刑法归责:因果关系理论的反思》,载《政法论坛》2010年第6期,第97-98页。基于对因果关系属性不同的观点预设,可能形成不同的因果关系范围的判断立场。如果坚持狭义的因果关系界定而将因果关系视为事实判断问题,就需将因果关系判断与结果归责判断进行区分,在因果关系认定之外单独处理归责问题,但如果使用广义的因果关系概念,就要在因果关系判断中,既认定事实的归因流程,也认定规范的归责评价。
(二)介入型因果判断应采归因与归责结合的广义立场
基于介入型因果关系的判断语境与刑事司法实践的当前逻辑,介入型因果关系应采用广义因果关系立场,实现归因与归责的结合判断。
一方面,介入型因果判断作为多因素的复杂因果关系判断,其特殊之处在于:通常在事实上形成明确的多因一果局面,介入因素与实行行为作为共同的促果条件在归因意义上不存在前者对后者的中断与替代的关系;〔20〕参见晋涛、刘士心:《刑法中因果关系认定新探——兼论介入因素因果关系》,载《华侨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第64-65页。因此作为介入型因果关系认定核心的,所谓介入因素中断因果关系的判断主要就成为一种归因之后的归责判断,必然也应具有明确的规范评价的属性与机能,由此只有采用广义的因果关系界定才能涵盖必需的归责判断与规范评价部分。介入因素影响下的复杂因果关系判断中,只要能证明客观上实行行为与介入因素都是结果的事实促成因素,事实上的多因一果就已经具备,这点并不受介入因素是否独立于实行行为及本身是否异常的影响。但仅凭事实归因的分析并无法进一步判断介入因素是否能够中断因果关系的问题,而只能说明实行行为与介入因素都是事实因果流程中的促果原因;〔21〕虽然因果关系中断论作为条件说的补充理论专门针对介入因素是否中断因果关系提出了具体的标准,但是与条件说明显的事实归因属性不同,因果关系中断论的具体标准中,无论是介入独立因素异常性的判断还是介入故意行为的判断都已经超越了纯事实分析的层面,而进入规范评价的层次。参见[日]野村稔:《刑法总论》,金理其、何力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因此单纯事实因果分析对介入型因果关系判断远远不够,只有进一步通过规范评价来明确结果归责于实行行为还是介入因素,才能明确介入因素是否中断因果关系而阻却归责。
另一方面,就医疗介入类伤害案所代表的刑事司法判断逻辑而言,刑事责任体系中并未具备在因果关系外客观判定结果归责的规范评价空间,若不采纳广义的因果关系界定、不在因果关系的范围内进行归责评价,则结果是否归责于行为就无法得到完整的判断,刑法上不可或缺的归责认定也就不能有效展开。刑事司法的核心目标是依据刑法实现对不法行为的妥当评价,要达到这一目标不能仅在存在论意义上进行事实分析,必然需要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根据刑法的规范评价机能明确结果对行为的归责。〔22〕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犯罪原理的发展与现代趋势》,王世洲译,载《法学家》2007年第1期,第154-155页。当然,刑法评价可根据先不法后有责、先归因后归责、先客观后主观的判断逻辑而区分层次展开;基于归因与归责、主观与客观的层次区分,有观点认为归责评价是客观构成要件判断后的主观归责的问题,与在客观构成要件层次判断的因果关系认定无涉:主观归责要么通过故意的判断,要么通过单独的主观归责判断实现归责评价目标,因果关系的判断仅需进行客观事实上的因果认定就可以实现其应有机能。〔23〕参见陈璇:《刑法归责原理的规范化展开》,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237-238页。将归责视为单纯主观判断从而排斥因果关系归责属性的观点在实行行为与结果归属具有构成要件定型性的情形下与结果归责的立场没有明显的实质差别,因为“构成要件及其关系解决了因果关系与客观归责问题,故不需要另行判断”〔24〕同前注〔3〕,张明楷书,第181页。;但在实行行为不具定型性的多数情形下,主观归责论排斥在因果关系中进行客观归责判断的立场会造成刑事司法实践仍难解决因果流程偏离与不当回溯的归责问题,从而体现客观的结果归责之必要性:一方面,虽然主观归责通过对因果流程的主观认识要求(如要求故意应包含认识到可能的因果流程)部分明确了归责范围,〔25〕参见庄劲:《客观归责还是主观归责?一条“过时”的结果归责思路之重拾》,载《法学家》2015年第3期,第59-60页。但由于行为故意发生时具体因果流程还远未实现,此时主观上对因果流程只是盖然性的认识,从而在事实因果流程偏离的情形下可能造成归责判断的困难。如案例3中,投毒者所认识的因果可能性是通过足够剂量毒药致使邻居死亡,而事实上投毒剂量并不足以致死,只是毒药合并邻居自身疾病与医疗疏失致使邻居死亡。在投毒者同时知道邻居有疾病的情形下,到底是否确认构成要件的认识错误就因一般人标准与行为人标准致生争议,从而难以确定是否能够主观归责,最终不得不依靠客观上的归责评价解决这一问题。另一方面,受限于因果流程可能性认识的主观模糊性与识别困难性,主观归责难以起到明确阻却过度因果回溯的机能。如卖刀人在特定意义上知道每一个买刀人都有持刀行凶的可能性,但其难以判断可能性大小,因此是否某一买刀人行凶造成的结果就应该归责于他,难以通过主观归责否定因果链条上的归责回溯,最终需要依靠规范评价卖刀人的行为而进行结果归责的判断。
主观归责的观点在归责上的困难来源于其对归责客观性的视而不见,正如罗克辛所指出,归责并非故意与否的判断问题,而是基于判断法益侵害的风险是否实现为结果的客观问题。〔26〕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页。要在客观上判断行为的法益侵害风险是否实现为实害结果,在当前刑事司法判断逻辑并未接受单独的归责判断步骤与规则的情形下,只能置于因果关系的判断领域进行分析。换言之,在当前的刑事责任判断框架之下,因果关系判断应包括事实意义上的结果归因与规范意义上的评价归责之双重认定。
三、基于危险替代的结果归责:介入型因果关系的教义形塑
(一)结果归责:因果关系理论有效性的对应检视
在明确了介入型因果关系应包含归因与归责的双重内涵之基础上,进一步就需要明确介入型因果关系判断的具体理论基准。而为了保证得出这一理论基准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如前所述,就需要在归因与归责的双重语境下,检视已有的相对丰富的因果关系基本理论,择取因果关系判断的基本原理。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传统因果关系理论中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偶然因果关系说,还是后来因果关系理论发展形成的条件说、合法则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论,都是从不同角度与立场对因果关系认定提出的各自理解,在具体适用时还常得出殊途同归的结论;这表明诸理论各自提出的因果关系判断标准没有绝对的正确或错误之分,而是需要结合不同的因果关系认知视角与立场才能进行具体评判。本文仅基于归因与归责的双重判断语境及刑事司法的适用有效性目的对因果关系诸种理论进行分类检视,也主要限于介入型因果关系所代表的复杂因果关系判断场域。考虑到对事实归因判断的普遍接受性,以及前述介入型因果关系领域主要在归责标准上的判断缺失问题,应重点以是否能够为归责判断提供有效的理论基准作为检视因果关系教义原理的核心标准。
首先,从归因与归责相区分的立场审视,传统因果关系理论中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偶然因果关系说及后来的条件说、合法则条件说主要是基于事实归因的立场提出的因果判断原理,难以解决结果归责问题。一是必然因果关系说强调行为要合乎规律引起某一结果发生,其合乎规律主要指的是基于事实形成的实存因果律〔27〕参见陈兴良:《刑法因果关系:从哲学回归刑法学——一个学说史的考察》,载《法学》2009年第7期,第23-24页。。二是偶然因果关系相较于必然因果关系进一步明确了介入因素判断的复杂情形,在危害行为本身并不合规律产生危害结果,而介入因素合乎规律地引起结果时,前者是偶然因果关系,后者是必然因果关系,都被视为刑法因果关系。〔28〕参见李光灿、张文、龚明礼:《刑法因果关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9页。将偶然与必然因果都纳入因果关系中可见,这一理论仍然遵循着多因一果的事实因果判断逻辑,是基于归因视角的具体判断。三是条件说相对于必然、偶然因果关系说进一步提出了更明确的条件认定标准,但这一标准所依据的条件关系仍然是一种事实判断,并不带有归责色彩。〔29〕参见陈兴良:《从归因到归责:客观归责理论研究》,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2期,第72页。四是合法则条件说要求在条件因果判断的基础上增加对具体因果关系是否符合科学因果法则的判断,以排除偏异因素。〔30〕参见邹兵建:《合法则性条件说的厘清与质疑》,载《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3期,第63页。由于科学因果法则的判断仍然是基于事实的经验认知判断,因此并未超出归因判断的范畴。总而言之,必然、偶然因果关系说、条件说、合法则的条件说尽管在归因判断上有其各自原理,但是都因未能涉及归责判断层次而难以成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解决结果归责问题的有效标准。当前刑事司法实践在认定因果关系时已经较普遍适用了条件说的事实因果关系判断标准,因此事实归因问题争议相对较小,介入型因果判断时亟待解决的恰恰是必然、偶然因果关系说、条件说、合法则的条件说所难以解决的归责标准的欠缺问题。
其次,为限制条件说归因的扩大化而提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虽超越了事实因果判断逻辑而部分进入归责判断领域,对介入型复杂因果关系的判断也更为有效,但其也因未区分归因与归责的不同层次造成观点讼争,限制了其在归责判断上适用的有效性。相当因果关系说以“相当”为核心基准,在条件说的基础上通过相当性的认定排除条件因果关系中异常的不合理因素,从而部分进入规范评价意义的归责判断领域。〔31〕参见周光权:《客观归责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兼与刘艳红教授商榷》,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4期,第233页。然而由于相当性概念缺乏清晰的定型化界定,在具体适用时形成了主观说、客观说、折中说的不同观点讼争:主观说以行为人认识到的事实为基础进行相当判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主观归责的属性;而客观说以行为时一般人认识到的事实为标准进行判断,从而可以体现一定的客观归责属性;折中说则以行为时一般人认识到的事实及行为人能认识到的特殊事实进行综合判断,〔32〕参见[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第3版),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页。在客观归责还是主观归责属性上模糊不清。而更为复杂的是,相当性不仅涉及归责判断,还涉及归因意义上的特殊情形判断,所谓介入因素的异常性判断等都可以纳入相当性的判断之中。〔33〕参见邹兵建:《论相当因果关系说的三种形态》,载《清华法学》2019年第3期,第83页。由此不区分归因与归责而包罗万象的相当性概念导致适用时难以为刑事司法提供明确、清晰的判断基准,从而影响了适用的有效性。
最后,因果关系理论中相对明确区分了归因与归责的是客观归责论,其以行为危险的产生与实现的规则为结果归责提供了较为明确的判断理据,从而对解决介入型因果关系的归责标准缺位问题最具借鉴意义。不过就理论总体定位而言,客观归责论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判断原理,其“对行为与结果进行实质性的价值判断,因而超越了因果关系的范畴,进入到了归责的范畴”〔34〕陈兴良:《客观归责的体系性地位》,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6期,第44页。。客观归责论是教义学上刑事归责的一般理论,可贯穿于整个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判断过程之中,甚至涉及行为定型、认识错误、被害人承诺、过失判断、结果加重等方方面面的判定问题。作为客观归责首要规则的“产生法所不容的风险”与其说是对结果归责判断,不如说是对实行行为的判断,〔35〕参见李川:《不作为因果关系的理论流变与研究进路》,载《法律科学》2016年第1期,第46页。因为这一规则本身主要通过危险创设来判断行为可归责性,而并不涉及结果对行为的归属问题;而“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内”的规则用于补充判定实行行为与结果要素是否总体上在构成要件的规范评价范围之中,〔36〕同前注〔34〕,陈兴良文,第47页。超越了单纯的结果归属行为判断,其基于规范评价的第三人负责与被害人自我答责的判断都是总体上既排除了对实行行为归责,也排除了对结果的归责。因此,直接适用于结果对行为之归责判断的主要是客观归责理论的危险实现规则,即“实现法所不容许的风险”。危险实现规则首先建立在事实因果关系判断的基础之上,进而通过结果回避可能性、规范保护目的等丰富的检验标准判断行为危险是否规范意义上实现为具体结果,从而为结果是否可归责于行为提供了直接、具体的判断基准,因此也就可以针对性地解决介入型因果判断归责标准缺失问题,应被采纳为介入型因果判断中归责的基础标准。
(二)归因基础上的危险替代:介入型因果关系的核心教义
如前所述,在归责层面上明确以客观归责论的危险实现规则作为判断原理,再结合相对已得到普遍认可的归因层面上的条件因果关系判断,就实现了广义因果关系立场上归因与归责相结合的基本要求。而将这一机理进一步适用于介入型因果关系的场域,就以结合介入因素的复杂语境具体形塑介入型因果判断的教义原理。
1. 事实的条件归因:介入型因果关系的确立前提
按先事实后规范、先归因后归责的逻辑顺序,广义的因果关系必然要建立在事实因果关系成立的基础上。介入型因果关系判断也不例外,其首要层次就是先判断事实因果流程的有无,这是因果关系认定的基础层次,如无法认定事实因果流程的存在就无须进行后续规范判断。判断事实因果流程应基于存在论的立场根据条件说展开。基于这一立场,通常介入型因果关系中,只要能证明在先行为与在后介入因素在事实上对结果发生起到条件作用,行为与介入因素就都与结果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37〕当然不排除有所谓择一因果、重叠因果等作为条件说补充的事实因果判断的特殊情形。条件说通过特殊认定规则补充认定这些特殊情形,条件说补充规则仍然基本遵循经验事实判断的逻辑。在介入型因果关系为代表的复杂因果关系中,多因一果的事实现象极为常见,行为与结果的事实因果关系成立也不受介入因素是否受到在先行为诱发、本身是否是第三人行为或被害人行为、是否异常等因素的影响,因为事实判断上诸原因均是等价条件。〔38〕同前注〔18〕,林钰雄书,第122页。具体到医疗介入类的伤害案件中,伤害行为与医疗后的伤亡结果间,只要存在条件上的促发关系,无论在后的医疗介入如何发生发展,都具备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这一点不受被害人是否接受医疗,以及如何接受医疗的影响。因为从事实因果流程出发,如没有前置伤害行为,被害人就不可能受到医疗救治,也就不可能有所谓的接受医疗后的结果。前述案例1与案例2中,即便被害人家属停止医疗的行为是被害人死亡的直接促发因素,但仍不会对伤害行为与死亡结果的事实因果关系构成影响,因为伤害行为仍是死亡结果事实上的条件因素。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条件说补充的所谓中断说或回溯禁止理论认为有意识地影响结果的有力行为如第三人加害会切断在先实行行为的因果关系,〔39〕参见莫洪宪、黄鹏:《论结果客观归责中的溯责禁止》,载《法律科学》2017年第6期,第79页。如家属有意放弃被害人的治疗导致的被害人死亡可能会切断伤害行为与死亡结果的因果关系。不能否认这种观点从整体因果关系判断上的可能成立,但所谓中断说或回溯禁止理论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条件说所处的事实因果判断层次而包含了一定的归责判断,所以是规范评价层次的问题。在早期没有清晰区分归因与归责时,作为补充的中断说或回溯禁止理论可以起到在归因框架内部分解决归责问题的有效作用。但实际上应把所谓因果关系中断或禁止回溯要解决的问题放到归责层次加以讨论。
2. 规范的结果归责:介入型因果关系的核心层次
在介入型因果关系通常体现为事实上的多因一果的情形下,如果仅考虑事实因果关系,将可能导致结果无限回溯行为的因果关系判断困境。单纯的事实归因无法解决结果应归属于在先行为还是在后介入因素的关键问题,因此能够通过划定责任范围来明确结果归责于在先行为还是介入因素的结果归责就成为介入型因果关系判断的核心层次。这就需要在事实因果关系成立的基础上,在介入型因果判断语境下讨论规范意义上结果能否归责于行为的问题。
在规范评价意义上判断结果归责,如前所述,其核心是对行为危险实现的判断,即危害行为所制造的法所不容的危险是否规范的实现为实害结果。要进行这一判断,客观归责论确立了三个下位规则:〔40〕同前注〔26〕,克劳斯•罗克辛书,第243-245页。第一,结果发生应在行为危险的范围之内。如果最终结果发生超越了行为危险的可能致果范围,就不是行为所致结果发生,不能归责。对于这一点的判断首先需要明确行为产生的是何种危险及其涵摄的结果范围,才能进一步判断结果发生是否在行为危险范围之内。所以尽管如前所述,对行为产生的危险的判断虽然不是因果关系判断的内容,但因涉及行为危险范围的确定,应视为是归责判断的前提,应从行为时一般人标准来判断行为所造成的危险范围。第二,结果发生对行为发展来说具有回避可能性。如果结果发生相对于行为来说本不具有回避可能性,则行为没有实现不被允许的危险,“一个人不能因违反了一项即使履行了也无法避免危险发生的义务而受到刑事处罚”,〔41〕同前注〔29〕,陈兴良文,第79页。不能进行结果归责。这一规则旨在将不具有回避可能性的结果排除在危险实现的规范评价之外。第三,结果发生符合规范保护目的的要求。如果结果发生在行为违反的注意规范保护目的范围之外,则不能归责于行为。通过规范保护目的可以保证危险实现的流程不会脱逸注意规范的评价范围之外。〔42〕参见于改之:《法域协调视角下规范保护目的理论之重构》,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2期,第209页。
3. 从危险实现到危险替代:介入型因果关系的教义转换
介入型因果关系判断有其独特之处,不同于一般因果关系判断仅需考虑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结,介入型因果关系因为行为发生后介入了其他促果因素,从而需分别考察在先行为与在后介入因素与结果间的因果联结,并进而明确介入因素是否中断了在先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才能得出因果判断的最终结论。〔43〕参见张绍谦:《论刑法因果关系的介入和中断》,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第66-67页。因此作为一种复杂因果关系的判断,介入型因果关系认定即便在归因层面上可通过条件说将在先行为与介入因素都认定为多因一果的事实因果要素,但在归责层面上则必然使得原来相对简单的单一行为危险实现的判断问题变成多重危险交错实现的认定问题;这是因为不仅在先行为可能产生危险并存在危险实现的归责判断问题,在后的介入因素也可能致生危险并产生危险实现判断问题,并且不同的介入因素还可能产生多元的危险实现问题。由此介入型因果关系的归责判断标准相对一般的危险实现归责基准就必然变得更加复杂:在先行为危险的实现进程与介入因素危险的实现进程既可能出现相互排斥也可能出现并行不悖的情形,既可能出现择一实现为结果也可能出现合并实现为结果的情形;作为介入型因果判断核心的、所谓介入因素中断因果关系的判断究竟在危险实现的归责意义上是指多重危险实现进程的何种关系情形就必须进一步加以研究明确。
如前所述,归责意义上因果关系的成立以危险实现为基准,只有行为创设的不法危险实现为实害结果才能进行结果归责。将这一标准转换为介入型因果关系的判断语境之中,要达到介入因素中断因果关系的程度,在归责意义上就体现为介入因素完全中断在先行为的危险实现,导致在先行为的危险并未实现为实害结果,而是介入因素的危险替代性地实现为实害结果,即介入因素的危险实现进程达到了完全替代在先行为的危险的程度。由此,在介入型因果关系的判断语境下,作为一般归责判断原理的危险实现规则就转换为危险替代的规则,介入型因果关系判断的核心就表现为,在先行为的危险实现进程是否完全被介入因素的危险实现所替代。
(三)危险替代原理之教义展开
为了确定介入型因果关系而进行危险替代的判断,即判断行为的危险实现过程是否完全被介入因素创设的危险实现进程所取代,仅依靠一般的危险实现的下位准则无法满足判断要求,需要根据介入因素影响危险实现进程的特点形成新的危险替代判断规则。危险替代规则应起到规范意义上判断介入行为是否中断因果关系的机能:即如果介入因素的危险实现进程完全替代了在先行为的危险实现进程,介入因素就足以中断因果关系,结果不应归责于在先行为,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成立。为满足这一机能要求,危险替代应按照如下教义学规则逐步判断展开。
1. 在先行为的危险朝向结果发展
危险替代的前提是在先行为与在后的介入因素都产生了可能导致结果发生的危险。因此要判断危险替代,首先需要判断在先行为的危险是否朝向结果发展,从而产生与介入因素的危险交错进而被替代的可能性。如果在先实行行为的危险即便在没有介入因素时也不会实现为结果,则自始就无法结果归责;只有在先行为的危险在向结果发展的进程之中,才有进一步判断危险替代的必要。因此,在先行为的危险朝向结果发展是危险替代判断的首要规则。这一规则的判断与前述一般的危险实现的判断并无本质不同,因此,可以比照前述危险实现的下位规则进行认定,主要判断结果是否在行为的危险范围之内、结果是否具有回避可能性,以及是否符合规范保护目的的要求。〔44〕参见于改之、吴玉萍:《刑法中的客观归责理论》,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3期,第60-63页。
2. 介入因素创设了新的致果危险进程
在明确了在先行为危险进程持续向结果发展的前提下,如果介入因素没有创设新的向结果发展的危险进程,则介入因素就不可能中断因果关系;只有介入因素创设了向结果发展的致果危险进程,才有进一步判断危险替代的必要。
一方面,需进一步明确的是,介入因素创设的向结果发展的危险实现进程与在先行为的向结果发展的危险实现进程具有属性上的不同,前者并不要求危险本身必须是法所不容许的危险,也不必遵循规范保护目的的要求,应基于介入因素发生时一般人认识到的事实综合判断。这是因为在介入型因果判断中,所谓归责评价是指结果是否可归责于行为的规范评价,〔45〕参见许玉秀:《主观与客观之间:主观理论与客观归责》,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40页。而非结果是否可归责于介入因素的规范评价,因此介入因素的危险创设并不受基于客观归责论而形成的评价规则的影响,客观归责的行为产生法所不容许的危险的原理也对介入因素自身的危险创设不产生意义。即判断介入因素是否创设了向结果发展的危险实现进程之目的是下一步进行是否存在着危险替代的判断,而非对介入因素产生的危险自身进行规范评价。此外,介入因素本身并不限于可规范评价的被害者或第三者行为,还包括本身难以进行规范评价的事实或事件,〔46〕参见商凤廷:《介入因素下客观归责理论之借鉴》,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5年第6期,第24-25页。如被害人治疗过程中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医院失火、停电等因素,因此介入因素及其创设危险本身也不具备一般的进行规范评价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另一方面,要判断介入因素是否创设了新的向结果发展的危险实现进程,就需按如下下位规则进行逐次认定:第一,应明确判断介入因素是创设了新的致果危险,而非只是延续了在先行为已经导致的旧有危险。如果介入因素并未创设新的致果危险,只是延续了在先行为已经创设的危险,则无论介入因素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这一行为危险,介入因素都无法中断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前述案例1与案例2中,伤害行为所导致的致死危险在医疗过程中经历了先降低后升高的过程,医疗救治降低了死亡结果发生的危险,后续被害人家属放弃医疗的行为又升高了死亡结果发生的危险,但被害人家属放弃医疗的行为只是延续了伤害行为的危险向结果的发展进程,但放弃医疗行为本身并未创设新的被害人致死危险,因此并不能中断因果关系。第二,进一步应根据介入因素发生时整体事实综合判断,明确结果应在介入因素创设的危险的范围之内。介入因素虽创设了新的法益侵害危险,但如果结果本就不在介入因素创设的危险范围之内,自然介入因素也无法中断因果关系。如前述案例3中假设可以查明,虽然存在被害人救治时的医疗疏失,但此医疗疏失只会造成轻微加重的危害且不存在直接致死危险,则死亡结果本不在医疗疏失这一介入因素创设的危险范围之内,则医疗疏失就不能中断因果关系。第三,最后还应判断介入因素创设的致果是否朝向结果持续发展。如果介入因素创设的致果危险并未持续发展,而是在与先行行为危险发生交错作用之前就已经灭失,则介入因素也不可能中断因果关系。例如,前述案例3中虽然发生了医疗疏失,但假设如果在被害人死亡前医疗疏失已经被及时纠正,医疗疏失所产生的致死风险已经在毒药致死结果前消失,介入因素就不可能中断因果关系。
3. 在先行为的危险实现进程被介入因素的危险实现进程所替代
在明确在先行为与介入因素创设的危险进程都在向着结果发展的前提下,介入型因果判断的关键步骤就是明确介入因素创设的危险进程是否完全替代了在先行为的危险进程而实现为结果。在介入因素创设的危险实现进程替代了在先行为的危险的情况下,就可以在归责意义上判断介入因素中断了因果关系,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成立。
在先行为的危险进程与介入因素创设的危险进程在各自发展过程中可能形成复杂的相互关系:一是有可能在先行为的危险实现进程排斥介入因素创设的危险实现进程而单独实现为结果,介入因素创设的危险没有实现。二是有可能在先行为的危险进程与介入因素创设的危险进程合并作用实现为结果,在先行为与介入因素共同促成了结果的实现。三是有可能在先行为危险实现进程被介入因素创设的危险实现进程所完全替代,在先行为的危险进程并未实现为结果。
归责意义上介入因素中断因果关系仅指上述第三种的危险替代的情形,即介入因素创设的危险实现进程以完全替代的方式阻却在先行为的危险实现进程,单独实现为结果,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在先行为与结果间才无法认定存在因果关系。而只要在先行为的危险进程持续发生影响,如上述第二种情形,即便在先行为只是对结果发生起部分作用,是与介入因素合并促成结果的实现,亦应认为在先行为危险并未被介入因素创设的新危险所替代,而是实现为结果,介入因素仍不能中断因果关系,结果归责仍然成立。〔47〕参见陈璇:《论主客观归责间的界限与因果流程的偏离》,载《法学家》2014年第6期,第106页。此外,如果在先行为危险完全排斥介入因素危险的实现,如上述第一种情形,表明介入因素甚至未能对在先行为的危险实现进程发生影响,更无法认定介入因素中断了因果关系。
四、危险替代的归责原理适用:以医疗介入类伤害案为例
(一)基于归责的医疗介入类伤害案因果认定基准
就医疗介入类伤害案因果关系的判断情形而言,如前所述,由于伤害行为在条件意义上对医疗的接入具有促成作用,伤害行为与治疗结果的事实因果关系通常都能够成立。因此,结果归责就成为医疗介入类伤害案因果判断的核心。将前述危险替代的判断基准适用于医疗介入类伤害案的常见因果争议情形进行结果归责判断可形成其认定基准。
第一,如果基于一般人标准从行为时所有事实可以判断,伤害行为仅具备导致较轻实害结果的危险,被害人接受治疗后反而出现了更严重的结果,即便无法查明医疗过失或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行为等介入因素与更重结果的因果关系,也不能将结果归责于伤害行为,因为较重结果已经超出了伤害行为的危险范围。
第二,如果伤害行为本身有造成诸如致死等严重后果的不法危险,经过医疗有效降低了发生严重结果的危险;但由于医疗疏失、被害人行为或其他阻碍医疗行为等介入因素,导致本已降低的危险再次升高转化为实害后果,此时介入因素并不影响结果归责于伤害行为。这是因为按照危险替代的判断规则,介入因素并未创设新的致果危险而只是延续了已有的行为致果危险,伤害行为的危险依然实现为结果。在行为危险朝结果发展过程中,介入因素只是导致行为危险暂时降低或升高的情形并不影响结果归责于行为。当然危险实现为结果也要经过结果可回避性与规范保护目的的规则检验。
第三,如果医疗疏失、被害人行为或其他阻碍医疗行为等介入因素创设了新的引发伤害结果危险,并完全替代排斥了原伤害行为危险,则实害后果不能归属于原伤害行为。此处医疗过错、被害人行为或被害人家属行为是否为犯罪行为、偶然行为等行为性质问题都与伤害行为与结果的因果判断并不相关。但如果可以证明在先伤害行为的致果危险与医疗疏失等介入因素创设的新的致果危险合并实现,共同作用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则仍应认为伤害行为的危险已经实现为结果,无论在先行为与介入因素影响结果发生的所谓“作用力大小”,介入因素都无法中断因果关系。
(二)危险替代标准在典型判例中的应用展开
按以上标准来分析前述医疗介入类伤害案因果关系的典型案例,可以发现这些案例中现有的支撑因果判断的案件事实并不充分,从而需要更多案件事实信息,以分析更多可能存在的复杂情形。
首先,案例1与案例2在运用危险替代原理进行因果判断时,都需要先判断暴力伤害的在先行为是否有造成死亡的危险。第一,如果可以判断伤害行为只会造成伤害危险而无死亡危险,则在被害人经过治疗病情平稳后,其家属停止治疗而使得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就超出了伤害行为的危险范围而不能归责于伤害行为。第二,如果暴力伤害较为严重有致死的危险,归责与否就需要进一步判断介入因素是否创设了新的致果危险并替代了伤害行为的危险而实现为结果。案例1中,虽然被害人死亡时间上距离伤害行为发生时间较远,但是最终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危险仍然是来自伤害行为。被害人只是经过有效的医疗而病情稳定,有效医疗只是暂时控制了危险不会持续地向死亡结果实现,被害人家属要求停止治疗的行为并未创设新的死亡危险,只是使得本已控制的行为危险重新向结果发展并最终实现为死亡结果。因此介入因素并无法中断因果关系。案例2与案例1稍有不同,虽然同样被害人家属要求停止护理治疗,但医院仍然维持了对被害人的基本治疗,最终被害人依然因伤势过重而死亡。可以说医疗行为并未有效控制伤害行为的致死危险持续发展为死亡结果,被害人家属停止护理治疗作为介入因素甚至都未能升高风险,因此更无法中断因果关系。尽管存在被害人家属放弃治疗的介入因素,但因介入因素并未创设新的危险,死亡结果仍然来自伤害行为的危险实现,伤害行为与致死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成立。
其次,案例3也可以用危险替代标准予以进一步的归责分析。第一,需要结合行为时一般立场分析用注射器在丝瓜中投毒行为所造成的危险范围是否包括致死结果。考虑到被害人死亡是由于合并自身疾病与医疗疏失的事实,因此难以直接推断投毒剂量是否足以致死。因此应先明确行为人分散向丝瓜注射的投毒剂量是否有致死危险。如果未达到可致死剂量,则难以认定投毒行为产生致死危险,致死结果不在行为危险的范围内而不能归责于行为。但如果投毒人投毒剂量是通常的致死剂量,致死则在危险的范围之内而有归责的可能性。第二,假设投毒行为可能存在致死危险的前提下,接下来归责就需要判断行为的致死危险是具体实现为死亡结果,还是被介入的被害人特异体质、医疗疏失所替代。被害人死亡结果在事实上是由中毒、被害人自身疾病与医疗疏失因素所共同导致的。被害人自身疾病、医疗疏失作为介入因素确实创设了新的致死危险,但这一危险是与投毒后的中毒危险合并实现的死亡结果,因此,介入因素的危险并未完全替代排斥原投毒行为危险的实现,投毒行为的致死危险仍然得以部分实现,因此致死结果仍应归责于投毒行为,因果关系可以认定成立。
最后,以危险替代标准认定案例4的因果关系也需要区分情形:第一,伤害行为是否存在可能造成轻伤的危险,如果能够确认才有进一步判断归责的必要;第二,假设伤害行为创设了轻伤危险,接下来的判断要看被害人不遵医嘱而致使轻伤的行为到底是原有伤害行为危险的实现还是被害人新创设的危险的实现。如果被害人只是不遵医嘱消极不理疗与锻炼,则轻伤结果只是原有轻伤危险的延续实现,因果关系成立;但如果被害人不遵医嘱还体现为不顾伤势强行活动受伤指关节而创设新的致害危险并进而实现为轻伤后果,则介入因素创设的危险实现了对原有伤害行为危险的替代,则轻伤后果与伤害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就不能成立。
通过结果归责与危险替代的规范评价原理形塑介入型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可以为医疗介入类人身伤害案的因果判断提供更为明确的适用指标,部分缓解传统实践标准中所谓“作用力”“异常”判断相对模糊、随机的问题。可以将原有的实践三重性判断话语体系按照危险替代的判断指标进行语境转换:将所谓在先行为与介入因素对结果作用力大小的判断转换为在先行为与介入因素分别有无致果危险的判断,解决前述以定量分析解决定性因果判断的逻辑困境;将介入因素异常与否的判断转换为介入因素的危险是否替代在先行为的危险的转换,以客观归责的危险判断基准缓解所谓“异常性”判断过于主观化与随意化的不足。由此可见,危险替代原理不仅可以相对更明确地厘清部分因果判断争议,也可以为司法实践判断因果关系时提取有效相关案件事实信息、明确关键案件事实范围提供更为精细科学的指引。
五、余论:特殊认知与客观归责主观化问题
虽然基于危险替代的结果归责原理提出了介入型因果关系判断的更精细标准,但并非意味着危险替代就是因果关系理论上没有争议的完美立场。危险替代立基的客观归责立场在理论上还有所谓特殊认知的判断问题需进一步厘清。特殊认知被称为是客观归责论的黑洞式问题,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让客观归责论者如芒在背的客观归责主观化质疑,在具体应用时更造成了介入型因果关系认定中先主观后客观的判断逻辑悖论。特殊认知是指客观归责论在判断行为危险范围时,将超过一般人认知水平的行为人特殊认知情形作为一般人判断标准的特例,此时行为危险范围的判断中不再以一般人认知的事实为标准,而直接以行为人特殊认知的事实为标准,〔48〕同前注〔45〕,许玉秀书,第7-8页。比如行为人在行为时已相对一般人认识到了行为危险现实化中的特殊介入因素及其促果作用,就应该将对该介入因素的认知作为行为危险范围的判断基础,此时对介入因素的特别认识,已经开始改变行为危险范围的边界。由此导致在行为自身等客观构成要素不变的情形下,仅因行为人超越一般人的主观认知内容的改变,就导致了创设危险的范围的改变,进而引起因果关系认定的改变,客观归责的所谓客观性受到直接冲击。
如前述案例3中,如果投毒者认识到被害人有糖尿病这一介入因素可能导致其对有毒物质耐受力差、非致死剂量的投毒都有可能导致被害人死亡,则投毒者即便投出非致死剂量的毒药,仍然考虑到行为人已有对被害人疾病的特殊认知而认为投毒行为创设了对被害人的致死危险,因此合并了疾病因素导致的致死结果仍然在行为危险的范围内且已是行为危险的实现,因果关系成立。但如果投毒者并未认识到被害人有特殊疾病这一未来介入因素,从而也未认知到非致死剂量的投毒也可能导致被害人死亡时,同样投出非致死剂量毒药的行为,从一般人标准出发,行为危险的范围就并不涵盖致死结果,因此毒药合并被害人疾病导致的死亡结果就不能归责于投毒行为,因果关系难以成立。在投毒剂量不变的情形下,本应被客观归责论视为客观的危险范围与因果判断却根据投毒者是否认识到被害人特异疾病体质的主观特殊认知而改变,出现客观因果关系受主观决定的客观归责主观化问题,也难以符合先客观后主观的构成要件判断逻辑。
对特殊认知及其引发的客观归责主观化问题,形成了诸多不同角度的成因理解与观点回应。罗克辛认为只要保证归责的结论认定是客观的就能保证客观构成要件之客观性,归责过程并不需要完全以客观要素为基础。〔49〕Vgl. Roxin, Strafrecht AT, Bd. I, 4 Aufl., 2006, § 11 Rn. 56.格洛克承继这一立场,认为为实现归责的目标,特殊认知的主观要素可以成为客观归责的基础。〔50〕Vgl. Greco, Das Subjektive an der objektiven Zurechnung: Zum Problem des Sonderwissens, ZStW 117(2005), S. 536-537.此种回应虽然通过过程与结果的区隔在理论上缓解了对客观归责主观化的质疑,但是并未解决在客观归责的具体适用中,主观的特殊认知决定客观因果归属,从而违背先客观后主观的构成要件判断逻辑问题。还有一类观点认为应该放弃对客观归责的坚守,不必过分追究归责意义上主客观的划分〔51〕参见何庆仁:《特别认知者的刑法归责》,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4期,第1035页。,甚至认为应以主观归责为重〔52〕Vgl. Hirsch, Zur Lehre von der objektiven Zurechnung, in Festschrift für Armin Kaufmann, 1989, S. 249.。这些观点虽然各有其理论来源与立场基础,但仍然没有为具体适用时解决主观要素与客观要素混淆的问题提出具体解决方案。
而部分缓和的客观归责论者则相对明确地提出了具体的适用解决方案,认为应该将特殊认知问题置于主观归责层面予以解决,而非客观的因果关系的判断领域;应通过故意或者单独的主观归责判断体现特殊认知的归责意义,否则就在客观层面过早地考虑了主观归责问题,混淆了客观要素与主观要素。〔53〕Vgl. Frisch, Tatbestandsmäβiges Verhalten und Zurechnung des Erfolgs, 1988, S. 588ff.所以在因果关系的归责判断时,无论特殊认知是否存在,只要作为特殊认知内容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就应该纳入行为危险判断的基础因素中,并承认对后续因果关系的影响。即在上述案例假设情形中,只要被害人患病的特异体质是行为时的事实,无论是否存在投毒者对这一事实的特殊认知,其都应纳入行为危险的判断范围。因此投毒者行为时就创设了致死危险,且在因果发展中实现为结果,因果关系自然成立。而投毒者对被害人特异体质的认知仅对杀人故意还是伤害故意的主观罪过判断有所影响,从而最终影响刑事责任。但是这一适用方案的问题在于,将行为时全部事实纳入行为危险的判断基础,就又回到了基于条件说的事实因果关系判断的逻辑起点〔54〕参见陈璇:《论客观归责中危险的判断方法》,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3期,第155页。,只要是导致结果发生的必要原因事实就一律纳入危险作用的范围,客观归责就不再具有必要意义了。
就解决这一适用难题而言,弗莱希给出了相对既能够维系归责客观性,又能将特殊认知纳入因果考量的相对合理解决方案:即应有效地区分特殊认知与特殊认知的事实,前者虽然是主观的,但后者是客观的,而对行为危险进行归责判断起作用的只是后者而非前者。〔55〕Vgl. Frisch, Straftat und Straftatsystem, in Wolter/Freund(Hrsg.), Straftat, Strafzumessung und Strafprozeβ im gesamten Strafrechtssystem, 1996, S. 183-184.所谓特殊认知并不能直接决定行为危险的判断,而只是通过特殊认知确定了纳入危险考量的事实的范围。特殊认知并不直接被纳入客观构成要件判断,只是从机能主义的立场上成为归责的辅助手段。造成因果关系判断差异的并非是特殊认知因素的存在与否,而是参与行为危险判断的事实范围的差异所致。即前述假设案例情形中,影响行为危险是否包括致死结果从而最终影响因果关系判断的并非是投毒者对被害人疾病的特殊认知,而是被害人疾病这一介入事实因素本身是否一开始就纳入行为危险的判断范围。
特殊认知的问题在刑法理论上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归责与构成要件判断的联系与区别、主观归责与客观归责的关系、主观要素与客观要素的区分等诸多教义学体系划分与定位问题,注定是一个需持续研究推动的命题。而通过特殊认知对介入型因果关系认定的复杂影响也可以看出,因果关系是需要紧密结合理论与实践进行持续深入研究的问题,介入型因果判断原理的形成与发展正是这一过程的典型代表:一方面,刑事司法实践在认定介入型因果关系上的具体困境推动着对介入型因果判断教义学的研究;另一方面,新发展的介入型因果关系的教义原理又需在刑事司法中加以适用验证,体现其理论有效性。正是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推进中,基于结果归责与危险替代的介入型因果关系原理还需通过特殊认知等问题不断在理论与实践间反复验证完善,最终推动因果关系理论的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