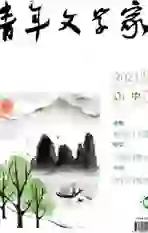探究侯孝贤《恋恋风尘》中年轻人的现实处境
2021-02-26苟爽
摘 要:侯孝贤指导的电影《恋恋风尘》由吴念真和朱天文作为编剧,电影的故事是以吴念真的亲身经历改编而来,从主人公阿远的角度来讲述那个时代的农村年轻人逐渐步入社会的青春路径。影片将阿远和阿云的爱情作为主线,从他们青梅竹马的感情来展开故事的叙述,最终也以这段感情的失败而结束故事的讲述。其中映射出了二十世纪末台湾城乡之间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诸多改变以及由此引发的城乡之间二元对立的诸多问题,同时表现了那个时代的变迁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影片的镜头里总是隐含着这些年轻人的无助和迷茫。每个人身上所捆绑的家庭和血缘关系,对于阿远这一代年轻人来说,既是束缚也是依托。
关键词:代际;家庭;城乡二元对立
作者简介:苟爽(1996.7-),女,漢,四川巴中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1)-02--03
《恋恋风尘》作为侯孝贤的一部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延续了他的一贯风格,这部作品也成为了 台湾新电影史上的一部重要的影片。故事以编剧吴念真的初恋为原型,讲述阿远与阿云这对来自偏远山村中普通年轻人的成长经历。影片的剧情平实舒缓,展露出每个人物的真情与质朴。“我觉得我们平常看事情并没办法很进去的看,很进去那是因为你自己很主观的思维方式,所以我就想用沈从文那种‘冷眼看生死,但这其中又包含了最大的宽容与深沉的悲伤。从这个客观的角度来拍,我觉得我的个性比较倾向于此……”[1]侯孝贤受到《沈从文自传》的影响,将人物与环境的距离巧妙融合,“夹裹着中国传统的美学和哲学,他的镜头总是眉目含情。‘思乡的惆怅,青春的记忆,成长的苦涩,原来生命就是生活。”[2]在他的电影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剧情平缓发展下去的同时,回荡在人们心中的是真实与宁静。
影片中主人公阿远阿云所代表的年轻一代,反抗着老一代人的因循守旧,努力抹平落后乡村所刻下的印记,却时常碰壁,与城市格格不入。这些企图逃离家庭捆绑的人,却又在每一次遭遇挫折之后选择回乡疗愈自我,关于冷漠和温情的相互交替,坚定与迟疑的相互转换,使得影片结局以阿远与阿云恋情失败的悲剧和阿远回归故里变得成熟而结尾。
一、代际之间 现实境遇的差异
电影中出现了阿公,父亲和阿远三代人,每一代人的社会定位以及代表的角色差异明显。阿公代表着已然老去且即将消失的纯粹的乡村文明;父亲作为煤矿工人处在山村的原乡文化之中,却因为乡村文明逐渐被城市文明所冲击和侵蚀,其所代表的角色开始被快速发展的城市文明所淘汰;阿远阿云这一代年轻人出生在乡村,是在新式教育和新知识中成长起来的,成年后陆续涌向城市,融入新的文化,成为了 城市文明的接受者。
电影中祖父阿公的形象被赋予了代表着乡村文明的文化符号,一生待在大山之中,常年埋头于黄色的土地,他们将自己的大半岁月付出在农业的耕作上,遵循着老一代的准则。为了追随整部电影的节奏,符合侯氏电影缓缓漫谈着人生的风格,侯孝贤打破人们对待乡村老人的刻板印象,没有将阿公塑造成一个落后愚昧的形象。反观其他人,阿公的晚年岁月生活得更加通透。就如他在阿远阿云恋情终结时说“这是缘分,勉强不得的”;在结尾处,阿公对这个历经了世事变迁的孙子阿远归来时,有一搭没一搭地谈论着庄稼的收成和天气的变化;包括当初给儿子默默地做好拐杖;亲自送阿远服兵役这一系列事件,阿公看淡了人生的起伏和生命的离合,可以看出,在他的质朴和淡泊中,还透露着丝丝温情。阿公的老去,代表着美好纯粹的乡村文明即将消失,阿公的淡泊,又传达着这种纯粹文明的消逝是后来的人必须坦然接受的事实。
阿公这一代人是原乡文化的接受者和实践者,可能一生都未走出大山,遵循着老一代人的信仰。阿远年幼时发高烧,阿公坚信是阿远父亲违背诺言的后果,并要求立即改正,兑现当年的诺言才能够治愈阿远,阿公说:“人常说:‘要靠人,也要靠神”,在他的价值观中,相信神的存在,所以与城市的大部分人来说,他们这代人始终克制着自己的一言一行,相信因果报应,恪守着自己心中的执念。由于生命的慢慢消逝,高寿的年龄使之极少接触外面的世界,城市的发展也往往难以触及他们生活的范围,所以被隔离在现代都市文明之外,电影中也时常出现阿公时常坐在门前阶梯的镜头,独自一人抽着烟,时而自言自语。
阿远父亲这一代人则是处在城市与乡村文明的交汇处,陷入尴尬的境遇中,既不能够全身心投入田间劳作,又无法进驻城市。影片中有一个片段是关于电视中报道煤矿工人的工作环境和待遇,引发了像阿远父亲这类当初冒着生命危险下井挖煤的矿友们一起罢工,商量着如何争得工人的权利的事件。城市文化的影响使得当初只埋头苦干的工人们懂得了为自己争权的必要性,然而这计划又半路夭折,工人们不敢主动站出来发声,期待着他人能够代替自己争夺权益,害怕被城市人蒙骗,所以对于这场无实际意义的罢工运动,他们的内心常常伴随着失望。父亲和矿友们时常借着商量抗议的名号聚众喝酒,喝醉了又如同小孩子般做搬石头的游戏,作为一家之主,他们承担着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压力,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表现出中年人的无奈。他们已经被开始改变的社会环境慢慢淘汰,又肩负着家庭予以的责任,无法融入新社会的境遇致使他们选择躲避这一切和做一些无能为力的反抗。
初中毕业之后辍学的阿远选择去台北淡水打工,因为去车站接阿云时打翻了盒饭,被老板娘痛骂一顿从而失掉喜爱的工作。另外,影片中也有提到邻居的孩子向家人隐瞒着自己在外打工被老板打骂的事件,而处理这件事的方式便是伙伴们一起隐瞒事实的真相,相互之间介绍着待遇好的工作。在当时,这群年轻人即便被伤害得遍体鳞伤,也要相互搀扶着走向城市。在城市中努力寻找出一点余地,在城市立足成为了他们这一代人的目标与愿望。就像几年后阿远的朋友恒春仔欣喜的给阿远的来信中讲到,他学会了开挖掘机,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种,同时和新的女友安顿在城市的一角,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由于出生在大山之中,童年身处的环境往往很难直接接触现代文明,这群来自偏远山村的年轻人一开始很难融入城市的生活,在外打拼的岁月中,他们相互取暖。电影中快乐轻松的时光并不算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片段是,他们在繁闹的街市上一起聚餐喝酒,唱着关于“乡愁”的歌曲,“今夜又是风雨微微异乡的城市,路灯青青照着水滴,引起我悲意……青春男儿,不知自己,要往何处去,漂泊万里,港都夜雨寂寞时。”这是这群年轻人在城市中打拼之时最温暖的时光。随着社会的快速变迁,对于他们来说,在城市中谋求生路,这种方式使得他们既面临着现实的残酷,又能够把握住更多的改变命运的机遇。选择主动走出相对落后的大山,遇到打工不被老板认可的委屈,他们在不断探索和改变中。明白及时更换掉工作。
二十世纪末,在城市文明不斷侵蚀乡村文明的过程中,社会的发展对三代人的影响各有不同,尤其是父亲和阿远所代表的不同社会角色,中年和青年一代,他们的人生和命运与社会变化的现实紧密相连。代际之间 彼此有着血缘和感情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又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势必吞噬着阿公这代人所代表的乡村文明,而阿远或者其子孙会选择慢慢远离偏远的山村,融入到城市的生活,三代人之间无形的隔阂成为了 城市文明侵染乡村文明的必然结果。
二、对家庭的皈依还是叛离?
随着父亲的腿被砸伤,阿远一家的收入出现了严重的赤字。弟弟为了填饱肚子开始偷吃父亲的药品,家中的经济负担加大,作为家中长子的阿远必须挑上这份重担,为父亲减轻压力,初中毕业的他决定辍学去淡水打工。成绩不错的阿远仍然是想要把握学习的机会,到了台北坚持边打工边上夜校,然而这只是自我安慰的最后砝码,阿远始终没能够参加高考。家族经济的重担落在他的身上,时常和工友们酗酒的父亲因为腿伤无法工作,什么都不懂的母亲是一个极为传统的家庭妇女,而阿公与儿子儿媳的关系都不够亲密,常常一个人自言自语。后来阿云也追随他去了台北,两个人省吃俭用将自己的工资带回家以补贴家用。
在外打工生病没有家人知晓,无法感受到家人的关心,与家人之间不够亲密,这是阿远这一代人的悲哀。生活的重压与亲情的缺失是这一代年轻人想要叛离家庭,在外闯荡的缘由之一,打工受到老板的苛责辱骂甚至抽打也无法阻止他们离开家庭的脚步。阿远因为摩托被偷,自己赔光了赚来的钱,他选择的是独自去海边散步,而非回家疗愈。他们逐渐远离原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代青年人们,戴着枷锁走出了大山迈向城市,正当青春的年纪里被迫成长起来,在外打拼的日子里也无法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致使他们过早的成熟。
亲情的缺失成为他们成长过程中的遗憾,也是迈向成熟的必经之路。侯孝贤在电影中尝试着弥补这种遗憾,阿远去台北打工时,安排了阿远的父亲送他一千多的手表,在入伍的前也收到父亲买的新式打火机。入伍的前一夜受到父亲的许可一起抽烟喝酒,父子之间的关系得到缓和。同时父亲懂得不读书就要遭罪的道理,他依然为自己没能让阿远完成学业而心有余悸。
家庭带给阿远这一代人的温暖虽然不够多,却又紧紧地拉扯着他们每个人。无法向家人倾诉关于在外闯荡的压力和人生迷惘的痛苦,往往又在历经一切挫折,变得足够成熟之后回到家乡疗愈创伤,这一切又加强了他们对原生家庭的依赖,希望受到家人对自己的认可。阿远退役回来后第一时间回到家中,喊着妈妈,看见母亲在屋酣睡便去田间与阿公淡淡的谈论着关于庄稼的收成。女主阿云在电影的最后嫁给邮递员后,带着邮递员回到家乡,也是渴望自己的婚姻得到家人的认可。
对家庭的皈依还是叛离的探讨,答案并非绝对,离开原乡和家庭是现代城市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承载家庭经济重任唯一的选择,有无奈也有期许,因为在他们的人生之中会出现更多的机遇,能够接受山村和城市二者完全不同的文化。而初入社会闯荡的少年们,在城市里处处碰壁,早年的他们无法全身心的融入新的生活,所以回归家庭是最简单的选择,他们可以在这里收到家人的关心,获得家人的尊重,家庭成为了 他们身心的最佳疗愈所。
三、城乡的二元对立
原乡与都市文化的碰撞带来了火花也带来了伤痕。出生在农村的年轻人们难以配合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和认同城市人的价值观念,但努力拼搏的他们,又渴望在城市中立足或站稳脚跟。人生的改变需要岁月的沉淀,侯孝贤在电影中没有提到阿远后来的人生,而电影里将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做了对比,影片对乡村文明做出了歌颂的姿态。电影中给予乡村的镜头永远是广阔和宁静的,而在城市中的镜头往往都是狭隘与局促的。镜头切到山村时,侯孝贤利用他纯熟的长镜头拍摄方式缓缓地拉远镜头展示大自然绝美的风光,起伏的山脉,漂浮的白云,和稀疏的飞鸟,侯孝贤用它们来诠释着大山的平静和淡远,同时绿色为基调的背景给人舒服安宁的视觉感受和审美体验。反观城市,总是充斥着杂乱和拥挤,灰色调的背景使得城市蒙上了更加沉郁的面纱。然而与乡村格格不入的城市急匆匆地发展着 ,逐渐啃食着原乡的文化,乡村慢慢被新的文明所侵染。就如同阿远和阿云的恋情一般,注定无法给结局画上圆满的句点,阿云阿远的爱情悲剧也透露着城乡之间的对立关系。
阿远与阿云作为青梅竹马,从小生活在偏远的山村,他们相恋在自己的家乡,相伴在陌生的城市,又在城市中相离。阿远回到山村,阿云嫁到了城市,这是两人恋情最终的结局,是城乡文明之间格格不入的结果,城乡文化的二元对立是导致恋爱悲剧的根本因素。邮差所代表的是城市文化,他看上这个时常写信收信的外乡姑娘,主动追求,给她讲有趣的故事,邀请她看电影约会等,他知晓如何表达自己对阿云的爱念之情,并通过这种方式夺得阿云的倾慕。反观阿远,即使与阿云青梅竹马般的生活学习在一起,也难以表达自己深厚的情感。故乡山村赋予他内敛的个性,沉默寡言,守旧朴实,虽对阿云无微不至,却始终无法外露关于自己对这段感情的期许与规划。阿远责怪阿云在朋友们聚餐时喝酒,难堪地看着阿云当着其他男生的面脱掉外衫,向着手被烫伤而不去治疗的阿云生气。他对阿云无微不至的照顾所表现出来的方式没有足够的温柔,将担心与关爱掩藏在心底。正如家乡的大山一般,阿远只是懂得在身边默默地守候 着阿云,将爱情轰轰烈烈的情感内隐于心,影片中这对小年轻也没有任何肢体的接触,甚至甜言蜜语也未曾出现。
原乡作为疗愈伤痕的地方,阿远选择回到山村,一切的经历成为他成长的必修课程,阿远生活在一个老旧的电影院后面,他们工作在杂乱狭小的空间里。
导演有意将城市与乡村作为对照,将二者所体现的价值内涵相比较。乡村代表着守旧内隐,宁静和归属,城市代表着开放忙碌,冷漠与无助。大山里的人更加守旧,遵守祖上所传承的传统习俗。
七月十四是鬼节,有一个很长的镜头里记录着阿远帮母亲点纸烧香,祭拜祖先的片段。作为习以为常的传统习俗,阿远与阿云会在这种时刻必须回到家乡参与祭拜的一切事宜。乡村的传统守旧的观念根植于出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包括阿远阿云这一代人。阿远小时候生病,阿公劝导父亲做法事给阿远驱邪,阿远长大之后生病时常常能够回想起当年的这一经历。乡村守旧内敛的思想与城市外向张扬的性格发生着冲突,难以调和二者的关系,即使有人作为先驱者去打破这种二元对立的关系,又被他人而抵制。阿云最后嫁给了邮差,两人的婚姻选择在城市里公证结婚,这是阿云母亲无法接受的一大缘由之一。首先认为阿云不能从一而终地选择阿远是让家人羞愧的举动,其次,无法遵循乡村的习俗完成婚礼是不能被认可的婚姻。
在忙碌的城市里面,阿远阿云作为打工仔跻身于狭窄的空间里面,暗灰色的城市中,狭小昏暗的电影院,破旧的宿舍,与杂乱的编织坊与印刷坊,构成他们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场所,压制住了他们的前进脚步,隐忍着老板的辱骂,失业的迷惘与关于未来不确定的幻想。城市逐漸将他们的善良质朴异化,将人逼到道德的底线,使还未成熟的年轻人被这些文化侵染。阿远陪阿云买礼物时摩托车被偷走,情急之下阿远首先想到的是偷其他人的车来弥补损失。城市的黑暗吞噬着这群年轻打工仔,迷惘与失落常常萦绕于他们。作为城市的边缘人,无法融入城市的生活的时候,时常坐火车回到家乡,这是他们与城市难以跨越的疏远的距离,位于山村的家乡是回归平静的疗愈所,他们成为了城市和原乡之间的纽带,在二者之间反复地来回穿梭着。
根据吴念真真实的经历改编,被侯孝贤进行了二次创作,他在《恋恋风尘》中漫谈着每个角色的人生遭遇,特别是阿远阿云这一代年轻人的现实处境,在影片中,相较于前两代人的人生,他们的命运更加带有不确定性,所经历的一切更加的跌宕。因为二十世纪末的城市文明的发展,社会的快速更迭带给他们太多的挑战和诱惑。但侯氏电影平缓的镜头下,有意减化现实社会的艰难,美丽的乡村是放空一切的地方。“结尾阿远穿了阿云以前做的短袖衫退伍归家,看母亲缩脚举手卧睡,出去与祖父扯谈稼穑,少年历得风雨,倒想一树的青果子,夜来风雨,正担心着 ,晓来望去却忽然有些熟了,于是感激”,[3]影片在这一舒缓平淡的镜头下结束。
参考文献:
[1]张靓蓓.《悲情城市》前与侯孝贤一席谈[J].北京电影学院,1990.
[2]黄洁.飘散在恋恋风尘中的浅吟[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
[3]阿城.且说侯孝贤[J].今天,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