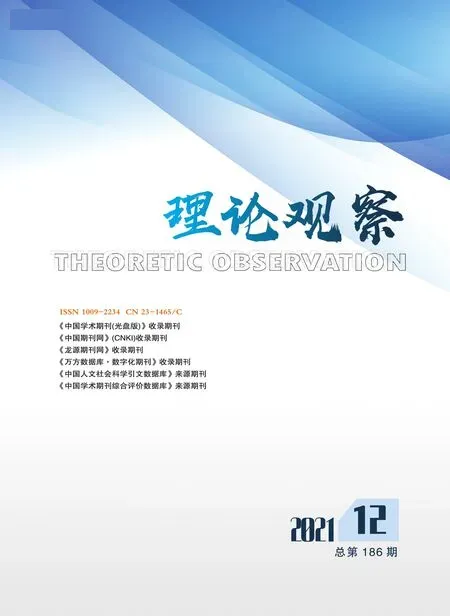现代熟人社会下的非正式规则对东北法治环境构建的桎梏
——以“人情关系”异化为视角
2021-02-25魏小来
魏小来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哈尔滨 150076)
一、检视:现代熟人社会下“人情关系”的异化
(一)“熟人社会”的存在基础
费孝通老师曾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①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什么是“乡土”? 意即长期、连续、家族世代生活的地方,“落叶归根”、“告老还乡”是中国人传承下来的乡土情结, 错综复杂的裙带关系渐编织了一个关系网,随着人员固化、流动性降低,关系网逐步扩张, 从封建时期注重血缘关系的宗亲世族逐渐发展为直系、旁系、远房乃至朋友在内的现代“熟人社会”,它以人与人的血缘为纽带、情感为依托而建立,按照部分专家的观点,基于经济基础的变化和经济体制的转型中国事实上整体完成了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再到“陌生人社会” 的转变, 但这种观点忽略了中国区域性明显、各区域文化不同及经济阶层的分化,②韩波.熟人社会:大数据背景下网络诚信建构的一种可能进路〔J〕.《新疆社会科学》.2019 年第1 期:130-136。以黑龙江省为例,根据黑龙江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第一产业产值同比下降为三种产业中最少的,为1.6%③黑龙江省统计局官网:一季度全省宏观经济运行情况,http://www.hlj.stats.gov.cn/zxfb/202004/t20200426_77561.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 5 月 11 日。,说明黑龙江省仍处于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期, 经济基础尚不足以带动社会文化、形态的转型,“熟人关系” 仍是思考问题的逻辑起点,这种思维搭建起来的社会本质上仍是“熟人社会”。
(二)“人情关系”异化背景下的非正式规则
东北地区的“熟人社会”呈现一种现代形态,现代“熟人社会”的场域形态与太阳系较为相似,它以“人情关系”为内核,“人情关系”属于非正式规则的一种又对非正式规则构建法治环境产生影响,因此,非正式规则受“人情关系”异化影响越大,对东北构建法治环境的负面影响也越大。 事实上,我国“人情关系” 异化的趋势源于人们对金钱观的重塑和对人情原有认知的解构,致东北地区“人情关系”逐渐利益化、虚荣化,④刘津,王晓星.人情关系:市场的非价格协调机制〔J〕.《天府新论》.2019 年第 4 期:84-93。最终是以非正式规则功能的凸显使正式规则预防、教育、约束功能遭到弱化。⑤张杨波.当正式制度遭遇非正式规范:小产权房成因的新思路〔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6 期:649-653。
“人情关系” 异化改变了乡规民约的地缘文化。 乡规民约虽然是法律的非正式渊源,但它却是当地聚居群体形成的共识性规范, 它在区域范围内定纷止争的作用不可忽视,“人情关系” 从封建时期的井田制开始就深深植根于这种规则之中,但随着市场经济转型、 城乡二元制向城乡一体化转变,乡村“人情关系”的内涵产生了转变,乡村对“礼治”与“法治”、非正式制度的重塑以及权力博弈达成了新的共识,“幕后权力” 打破了乡规民约原有的政治性选择。
“人情关系”异化造就“潜规则”盛行。 “潜规则” 违背了非正式规则为弥补正式规则在地域性适用、 文化差异性适用中的瑕疵而辅以补充的原则,“人情关系”从单纯维系家族关系向功利性、虚荣性转变的过程中,“潜规则” 作为非正式规则被广泛运用,逐步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风气,这种妨碍社会资源正常流动、 造就商品经济虚假繁荣的“潜规则”成为相当一部分群体中“不言自明”的非正式规则。①李彬.论潜规则文化的道德治理〔J〕.《伦理学研究》.2020 年第 1 期:114-121。
“人情关系”异化减损法经济学的预期价值。非正式规则的形成往往是一种既往存在的事实得到了绝大部分群体的认可, 由个体的理性逻辑转变一种社会逻辑,法经济学的内涵“社会价值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发展为非正式规则的一种,②熊秉元.正义的效益〔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 年。它的实证方法和后果式思维为我国的立法和司法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但“人情关系”异化的出现,模糊了规范和实证的主次、应然和实然的边界,成本和均衡的分析方法被束之高阁, 法经济学定纷止争、处理价值矛盾的属性被掩盖,被人恶意利用为以非法权利推动经济权利的工具, 在东北地区形成了经济性与法适性分离的情形。
二、洞察:现代“熟人社会”下的非正式规则对东北法治环境构建的制约
现代“熟人社会”的场域基本等同于“人情关系”异化影响下的场域,因此,我们如果以现代“熟人社会”为研究场域,则范围过大,若以其核心“人情关系” 异化为研究场域更有助于聚焦东北法治环境构建的问题。
(一)乡规民约:乡村社会秩序的“孵化器”
电影《秋菊打官司》为我们勾勒了一幅法治意识和法律制度艰难下乡的图景, 农村社会属于典型的“熟人社会”,其建立了以村长为首、“人治”为框架的乡规民约,秋菊在“讨说法”的过程中,本质是想以法治主义对抗人治主义, 而除了秋菊,村民、村长、民警都没有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而是想私下化解此事, 反映出现代的乡规民约在处理纠纷的时候既要在法律和道义上给秋菊以帮助, 又急于维护其自身及作为其外在表现形式——村长的权威, 本质上是乡村的社会环境与法律规制价值的矛盾。 自古以来,人们心中的理想世界是“无讼”,乡村社会中对“对簿公堂”更是避而不及,在纠纷中乡绅、名门望族发挥了重要的调解作用, 这种符合乡村主流价值观的处理方式慢慢以地方性共识的形式保存了下来——乡规民约,由于村民的法治意识淡薄,乡规民约对村民具有更大的内在驱动力, 但随着东北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青年人纷纷入城务工,加之长期被第一产业主导、 小农意识浓厚的东北农村地区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 传统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取向发生瓦解,新的价值观和规范尚未完善,新型的“熟人社会”在东北农村出现,“人情关系”不再是联结亲缘关系的纽带,反而成为了资源分配不公、与法治建设相博弈的“保险栓”,致使乡规民约的本质也从定纷止争逐步转变为谋取利益、无视法律的“遮羞布”。
1.对东北地区选举制度的破坏
村民自治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及充分保障人民依宪法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手段, 其选举制度自然成为法治环境建设的重要一环,新型的“熟人社会”对选举制度的破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贿选,乡村贿选的问题在东北地区一直未能根除, 表层看来是乡村治理能力滞后以及监督机制不完善, 实际上是贿选人自己盘根错节的“人情关系”、将乡规民约作为对村民的道德约束以及当选后所附带的非法价值,以黑龙江省“宫艳臣贪污犯罪”案件为例,通过一审刑事判决书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村支书的宫艳臣仅仅通过协助政府征地补偿一项就利用职务便利获得非法利益51886.80 元①黑龙江省克山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黑0229 刑初80 号。;二是无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7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积极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意见》,其初衷之一就是打击村霸凭借在当地盘踞多年积攒的人脉关系和势力破坏选举、操纵选举的行为,甚至一些乡镇干部也借用所谓的“人情关系”非法干预农村选举,这种新形态的“熟人社会”和异化的“人情关系”借用与正式规则相冲突的乡规民约悄然成为了东北地区基层民主政治和法治环境的毒瘤。

图2:2019 年村主任贪污贿赂案件数量柱状图
2.对东北地区政法体系运行的阻碍
东北地区乡镇的政法体系包括司法体系以及公安局的派出机关, 司法体系包括人民法院的派出法庭和人民检察院的派驻检察室, 这些机构对农村矛盾的化解、 群众诉讼的便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一旦触及乡村“熟人社会”的权威,比如村两委成员带头骗取征地补偿款、 阻碍解决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等, 被法律赋予司法权和行政权的机关被迫成为缄默者, 履行法定职责却成了政法机关与乡规民约的政治博弈, 这就是下乡普法简单易行而树立法治意识却困难重重的根本原因,②谢锐勤.权力下乡的逻辑与现实——从白雪梅被拐卖谈起〔J〕.《法治社会》.2019 年第2 期:22-30。因此,法律真正想在乡村做到强制力的保证实施,不仅牵涉到乡村的权力结构和政治选择, 更牵涉到村民对利弊的衡平、 法律与乡村共同意识的融合程度。
(二)潜规则:“权势”和“圈子”下的非正式规则
“潜规则”与正式规则就像一个铜板的两面,基于规范模式和利益分配的不同永远都不会有重叠和交叉,事实上“潜规则”原本是弥补正式规则对规范社会行为不足而提出的中性概念, 俗话说“画皮画虎难画骨”, 正式规则无法照射到的地方可以通过“潜规则”利用道德的规范手段对人们进行约束, 但是随着以第一产业主导的东北地区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商品经济的非道德属性使“人情关系”出现异化,“潜规则”的原生价值受到人们金钱化的利益观影响,“潜规则” 逐渐成为圈子文化和权势文化的附庸, 正式规则的权威在这个过程中也受到了反公共伦理的削弱。
1.“潜规则”的属性使其成为法治建设的顽疾
首先,“潜规则”的“潜”证明其有较强的隐蔽性,不同于正式规则对全社会的行为进行规范,它仅在特定圈子内部进行利益交流, 法治环境的本质意义就是全社会都要依法而治,“潜规则” 的圈子文化试图以自身的边缘文化打破社会秩序,正式规则很难予以规制, 法治环境建立的标准之一就是权力真正的受到制约,但“灰色地带”的“隐形权力”如何真正制约值得深思;其次,“潜规则”具有非道德性,随着“人情关系”的异化,“潜规则”逐渐由中性词语转为倾向性表达, 其以获取不平等的非法利益为目标,如上级单位到下级单位检查,有人违反规章制度为下级单位通风报信的行为就是非道德性的“潜规则”,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9 年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 提出要防止科学研究领域出现“圈子”文化,也就是从国家层面正式反对并打击非道德性文化;最后,“潜规则”具有承继性,印度电影《流浪者》中有句话:“法官的儿子就是法官,贼的儿子还是贼”,背后凸显出的法理就是非正式规则的承继性, 它与正式规则承继权利与义务不同,“潜规则”似乎只承继权利,我国自隋唐就创立了科举制, 意图打破上层权贵的世袭, 为唐朝律法的完善和政治的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现代的逢进必考制度限缩了“潜规则”的生存空间, 但东北地区一些偏远的乡镇由于人口稀疏、监管不严、地方豪强盘踞,致使很多入职考试流于形式、“潜规则”成为打通“关节”的不二法门,严重影响了当地的人才引入和法治环境的构建。
2.法治建设的滞后为“潜规则”打开方便之门
按照体系解释和历史解释,“潜规则” 的盛行也受到东北法治建设滞后的反作用,首先,中国法治应用首次记载是在《晏子春秋》的“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狭于今,修法治,广政教,以霸诸侯”中,我们可以推测最早推行法治的是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封建领主经济瓦解的齐国,齐国位于今天的山东和河北一带, 而春秋时期的东北主要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仍以“人治”思想占据主导,春秋时期少数民族的畜牧文明及生产力落后为 “潜规则”的游民文化和世俗文化提供了土壤,法治建设从起步阶段就已经落后;其次,国家在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前的试点范围往往以直辖市、 沿海的发达省份为主,以民事诉讼繁简分流试点为例,试点范围包括北京、上海以及江苏、广东等沿海省份的部分地区,基本未涵盖东北地区,因此,在前沿法治建设中, 东北地区往往只是在水土不服中机械的效仿、套用、跟随,制度改革的红利并未真正落实,结果只是新壶装老酒,“潜规则” 被掩盖的更加隐秘。
(三)法经济学:法治环境建设中的双刃剑
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和“运行成本的最小化”,为了具体实施,熊秉元老师在《法的经济解释》一书中又提出了“加总”和“均衡”的理念,“加总”先处理微观价值最后得到宏观价值的最大化,而“均衡”是力求达到政治、经济和法律三者之间的平衡, 熊秉元老师又将 “加总”进一步解释为“水滴石穿”,将均衡进一步解释为“路径相依”,①熊秉元.法的经济解释〔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7 年。事实上“加总”和“均衡”通过对民俗、 规则的反复适用指引非正式规则的形成,如“民间法”,但是这种法治建设的理念却随着“人情关系” 异化被歪曲, 别有用心的人追求低位阶的“均衡”,以行贿、受贿、贪污妄图达到一种政治的制衡,倡导“存在即合理”但刻意隐瞒了存在的局限性, 以权力义务的不对等互动换取自身价值的最大化,以社会效果思维模式建立新的道德体系,为自己披上道德外衣从而改变法律的工具性内涵,从思想根源上成为法治环境建设的最大阻碍,以黑龙江省“魏文利滥用职权、受贿犯罪”一案为例②黑龙江省汤原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黑0828 刑初103 号。,根据刑事一审判决书内容,魏文利利用危旧房改造的时机非法报取资金共计2760.50 万元,但其辩护人以其动机是使改造顺利完成为由进行辩护,也就是认为魏文利的微观行为(滥用职权)是为社会的宏观利益谋取最大化, 将自己因逾越职权给国家的经济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行为披上合情的“道德外衣”,这种诡辩严重背离法经济学的实质内涵。
三、破题:以矫正非正式规则推动东北法治环境构建
(一)以“法律多元主义”夯实非正式规则理论基础
“法律多元主义”的理论是苏力老师最早提出的,③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年。其目的是以《秋菊打官司》为背景解决移植的法律体系与根植于传统社会的民间法之间的冲突,消弭外来与本土、现在与过去、东方与西方、公权与私权等二元对立问题,事实上,中国封建时代的“奉法者强”也并非强调法律的一元化,从周朝时“礼治”就已经出现,随后“礼法并行”的局面确立,这应该是我国法律多元化的雏形,元朝的“袓述变通”“附会汉法”“因俗而治” 的多元化法律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在近现代,随着中国的经济建设进入快车道, 法治建设的现代化时代随之来临, 但是在移植的过程中却不知不觉确立了法律的一元化,而对于秋菊本人来讲,内心却产生了法治与人治、 法律的大众化与精英化甚至是公了和私了等单一抉择的纠结, 这说明社会规范的多元化不是突然出现的, 而是深深的存在于我们的本土社会中, 以我们不同的价值观为土壤生根发芽。④强世功.告别国家法一元论:秋菊的困惑与大国法治道路〔J〕.《东方学刊》.2018 年第2 期:43-55+130。但中国地大物博,地域性价值观和生产力发展的差异是我们无法回避的, 以黑龙江地区和重庆地区为例,2019 年黑龙江第一产业增加值为3182.5 亿元, 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6815.0 亿元,⑤黑龙江省统计局官网:http://www.hlj.stats.gov.cn/tjsj/tjgb/shgb/202004/t20200413_77332.html,访问日期:2020 年5 月18 日。2019 年重庆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551.42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2557.51 元,⑥重庆市统计局官网:http://tjj.cq.gov.cn/zwgk_233/fdzdgknr/tjxx/sjjd_55469/202003/t20200330_6686040.html, 访问日期:2020 年 5月 18 日。对比发现,第一产业增加值黑龙江具有明显优势, 但第三产业相差近一倍,说明两地的经济发展方式、集约化程度相差较大, 以完全相同的正式规则来管理两地否定了因地制宜的发展方式, 再以东北地区不同行业为例,中共黑龙江省委办公厅、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曾于2016 年印发过《黑龙江省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和规范建设实施方案》,该《方案》赋予行业协会对行业会员在监管、分工、财产、人事、管理方面的自治权,推进多元群体的自我管理,这也是基于不同行业主体价值观、综合素质、利益目标不同而适用不同规则规范来促进行业繁荣的有力措施。 因此,东北地区制定规则吸收“法律多元主义”,增强正式规则的包容性,使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形成优势互补, 使非正式规则由幕后走入台前, 有利于非正式规则的合理适用和制度的完善,防止“人情关系”异化下的非正式规则被恶意利用来扰乱社会秩序, 破坏东北地区多元群体和多元社会的法治环境建设。
但吸收“法律多元主义”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问题:首先,正式规则和法律效力位阶要成为“法律多元主义”和公民行动的红线,非正式规则的制定事实上是为了平衡南北区域差异、 东北地区行业健康发展而对部分群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多的约束, 引入的非正式规则要隶属于正式规则的内涵和外延之下并服从于上位规则;其次,非正式规则的来源和界限要明晰, 非正式规则一般应当来源于东北地区内某一区域历代传承的或者某一行业内达成共识的合法规则, 适用范围限缩至必要区域或者必要行业内,防止“法律多元主义”被恶意滥用。
(二)以回避制度贯穿法治环境建设始终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 年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配偶父母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此版本相较于2011 年的版本在适用主体、回避范围界定等方面更加严格,充分保障了审判、执行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中立性和廉洁性, 但是一个地区的法治环境不仅指司法环境,还包括政务环境、营商环境、监察环境等,因此,构建一个地区完整的、贯穿于整个法治环境的回避制度才能防止“熟人社会”中“人情关系”异化下的非正式规则对法治环境构建的非法干预。
首先,回避程序要具有一定的整体性,以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整体知识水平为基础, 将地方的立法、司法、执法活动与回避制度整体勾连在一起,如在地方立法活动中,引入委托起草文件、专家论证、公开听证的全流程透明制度,在地方执法活动中,扩大回避适用事项范围、建立行政主体与管理对象的利益屏障等, 并使之在所有非正式规则中具有普适性;其次,回避要有合理的提起程序,例如行政审判活动中,一般包括申请回避、自行回避和指令回避,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中,承办人和行政相对人可以以口头或者书面的方式提出回避申请,因此,对于人事关系复杂的东北地区,畅通回避申请的渠道尤为重要, 申请方式采取网络提交申请与线下邮寄佐证材料相结合的方式,由专人负责收发并保密,防止在申请阶段受到“潜规则”的干预;再次,设立明确的范围界限,一般应当为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但在东北地区可适当限缩回避范围, 如囿于东北地区人才流失的现状,涉及到专业技术性判断的事项,再如,在行政部门参考乡规民约处理纠纷的过程中, 利用当地有名望的村民或利用亲缘可能产生更好的效果;再次,设立回避报告制度,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已经设立了较为完善的案件插手、 过问报告制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东北地区可以尝试以司法机关的制度为框架构建区域内整体的回避报告制度, 在正式履职前主动报告可能会影响自己履职的人员及事件;最后,确立合理的救济机制,杜绝机械执法,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提出要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回避制度实质就是道德体系中的一环,依主观见之于客观,设立合理的回避复议制度是以权力层级打破 “人情关系”干预的关键,若将回避制度与非正式规则中正确的道德理念相结合, 使复议人员的价值观符合社会文化的演进方向, 可以更好的处理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