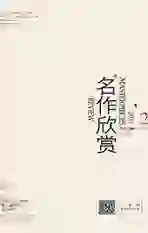小时代与女性意识的“穿越”
2021-02-23陈红
摘 要:《延禧攻略》是新世纪以来颇具症候性的一个清宫剧,开篇就呈现了“复仇”“反言情”主题,在以“爽”“怼”为特质的大众文化中构建了一种女性主义的镜像,演绎的也是小时代的情绪。然而,该剧在女性觉醒的表象下,并不是一个自觉的女性主义文本,呈现的女性意识也是有限的,依然遵循着男权社会的叙事逻辑。
关键词:《延禧攻略》 小时代 女性意识 镜像
《延禧攻略》的热播,带来了一种基于网络传播、网络狂欢的“爽文化”“怼文化”。“爽”“怼”开始成为一种大众文化思潮,一种颇具小时代气质的话语,不仅迎合了新世纪平民或中产阶层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还带来了现实生活中难以突破的快感。该剧的“爽文化”“怼文化”直接颠覆了传统清宫剧的故事情节设置和礼仪之邦的文化性格,开篇就直接呈现“复仇”主题。爱憎分明、冷静果敢的“大女主”形象不仅颠覆了传统剧中贤淑、纯情女主的人设,也颠覆了近年来宫斗剧、清穿剧的“玛丽苏”想象。相比较而言,同年热播的《如懿传》依然还是传统清宫剧的内核,属于古装言情剧范畴。《延禧攻略》仿佛是一部穿越清代的女性主义电视剧,带来了前现代女性觉醒的幻象。然而,通观全剧,在开篇就开启的“怒怼”模式下,在“反言情”的表象下,在网络热搜、微博热议的“爽”“过瘾”“痛快”之外,并没有呈现一种自觉的女性主义意识。
一
康乾盛世,是大清帝国的鼎盛时期,也是几千年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巅峰。“天朝迷梦”“九龙夺嫡”以及不同于历朝的继位制度,给清宫剧创作带来了无限的想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清宫剧持续发热,从历史剧到戏说,从前朝到后宫,不一而足,但大多还是以男权/男性秩序为中心的正统剧。家国建构、民族认同以及大时代的历史情怀,是传统清宫剧的内核,而后宫争斗、儿女情长不过是其点缀。
新世纪以来清宫剧逐步转向以女性为中心,开始走向“穿越”“宮斗”或“架空历史”的新模式。如果说20世纪末的《还珠格格》还是以言情为主,女性自我意识尚属将萌芽的自发状态,新世纪穿越剧《步步惊心》就已开启了“反言情”模式,女性意识开始萌发,后宫情感让位于现实生存,但最终结局还是落入俗套,女主在爱情与生存的双重夹缝中,现代气质也逐渐消失,还是以皇权/男权文化认同为归依。《甄嬛传》进一步凸显了女性意识,至此,琼瑶式的“爱情至上”已不见踪影,有的只是后宫生存法则。然而,甄嬛最后走向后宫权力巅峰之时,却陷入了无限虚空,感伤如影随形。《延禧攻略》则是一个女性复仇的故事,全然没有甄嬛那种从单纯少女到腹黑妃嫔、从心怀柔情到冷酷无情的逐渐“黑化”的一个过程。女主魏璎珞从进宫之日开始,就带着明确的复仇目的,一出场就呈现出彻底的反言情姿态。魏璎珞入宫之初就清醒、成熟、干练,其性格没有传统宫斗剧中那种从天真到复杂、从青涩到成熟的转变。正是这种果敢决绝、快意恩仇的出场姿态,抛弃了传统剧中的层层悬念设置,带来了畅快感、优越感和代入感,从而带来了“爽”的观剧体验。
《延禧攻略》不是“清穿”,却胜似“清穿”。魏璎珞代表的平民阶层“穿越”到乾隆王朝,在进宫之初就发出了“我,魏璎珞,天生暴脾气,不好惹,谁要是再叽叽歪歪,我有的是法子对付她”的宫斗宣言,“怒怼”模式由此展开。在和皇后那拉氏宫斗时,也摆出了“魏璎珞从来不怕斗,越斗越精神”的战斗姿态。魏璎珞恰如一朵暗自盛开的黑莲花,有仇报仇,有怨抱怨,以暴制暴,完全颠覆了以往古装剧中富察皇后式的以德报怨、与世无争、深明大义的“白莲花”人设。后宫如职场,情场如战场,魏璎珞的战斗姿态暗合了现代女性的职场生存境遇和都市婚恋境遇,带来了强烈的代入感。她的成功逆袭,也缓解了女性现实生活中的焦虑。魏璎珞的暴脾气从来就不是小燕子式傻而天真的“傻白甜”套路,她将暴脾气转化为一种率直、果敢的斗争智慧,敢爱敢恨,有勇有谋,精通后宫游戏规则。《延禧攻略》火爆银屏,无异于一种平民文化的崛起。
二
平民文化是小时代的产物。小时代是相对于启蒙时代而言的,以网络文化为特征。互联网时代让启蒙者悄然退场,精英文化开始式微,平民文化浮出历史地表。郭敬明的《小时代》是很有症候性的文化现象。他以四个年轻女性在“魔都”的职场体验和情感生活开启了一个充满消费欲望和媚俗意识的小时代,成为新一代上海写作的宣言。小时代不在意宏大历史叙事,不追求家国同构情怀,也不灌输自上而下的启蒙意识。小时代赋予中国故事另一种写法。小时代关注的是普通人具体而微的日常和消费。历史不再以庄重、严谨、宏大的面貌出现,也不再以温情脉脉的姿态呈现,而是在清宫这个历史现场来演绎小时代的情绪,叙述新世纪的焦虑,大历史不过成为一种点缀或者说是背景。小时代生产的清宫剧不可避免会带有小时代的情绪,历史剧不过是当代剧的一种折射。包衣出生的魏璎珞为何能圈粉无数,就在于魏璎珞身世、颜值平凡如你我,最能够代表广大的中产阶层或者说平民阶层,通过自己奋斗,成为古代职场版的杜拉拉。
小时代回避宏大叙事,认同市井文化的凡俗面和琐碎面。魏璎珞身上那股不服输,不隐忍,在任何境遇中都追随内心的那股劲儿,是笑傲紫禁城的市井生存智慧,颠覆了宫廷装模作样的雅文化。活泼泼的市井文化和向上拼搏的战斗精神,是与广大中产阶层的进步意识相通的。魏璎珞步步为营、过关斩将的复仇之路与中产阶级对于进化式进步的信念是相通的。魏璎珞自称从来不是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而是睚眦必报的普通人,然而又有良善的底线。她的宫斗,不在争宠,不在权势富贵,一旦复仇目的达到,就可以随遇而安,在自我的小天地里开启游山玩水、品茶插花的日常生活。即使延禧宫沦为人人践踏的冷宫,她依然能把冷宫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充满新奇感,成为偏安冷宫的“生活家”。魏璎珞常常以俗人自居,敢于揭开帝王高高在上、附庸风雅的面具,认为“皇上本来就很俗”,甚至把乾隆帝在名画《鹊华秋色图》上盖的四十多个印章比作天桥上看到的狗皮膏药。魏璎珞和明玉在插花时也感叹道自己的插花艺术远不如富察皇后,自有一股市井文化/俗文化的韧性和自知。“书法、绘画、琴艺,都可以后天弥补。可是眼界和气度却要数年浸淫。皇后娘娘是出生于大家,我从小出生于市井,自然是比不上了。”“一日不行就一年,一年不行就十年。天赋不高,我就勤能补拙。琴棋书画可以不精通,但是每次皇上问起来,我也不能是睁眼瞎啊。”魏璎珞的自知无异于一种自嘲,更是对自身境遇的清醒认知。比如魏璎珞并不喜欢以清雅著称的兰花图,认为越俗艳越好。她的平凡出身造就了她的审美意识。对俗文化的认同,其实是对上流社会附庸风雅的一种嘲讽,也是对精英文化的一种反叛。这倒和心高气傲、艳压群芳的高贵妃途殊同归。高贵妃关于兰花有什么好看还不如韭菜实用的言论无异于是对传统精英文化的反叛,也是对传统女性形象的超越。身居高位的她偏不喜欢这类“阳春白雪”,而心甘情愿在深宫中扮作社会地位低贱的戏子,为皇帝也为自己唱一出深情的戏。
三
《延禧攻略》彻底颠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清宫戏说剧的感伤传统。“现世感”“当下感”和女性意识的“穿越”,带来了“反言情”的镜像。该剧虽不是“清穿”,却有着强烈的“清穿”特质。“‘清穿——‘穿回到启蒙前,通过消解爱情神话的幻象而解构爱情的主体,从而缓解人们的价值危机和情感焦虑,形成‘反言情的言情模式。”a在《延禧攻略》中,不会再有“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的等待”(《戏说乾隆》主题曲)的感伤,也不再有“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只因为相遇太美”(《还珠格格》片尾曲)的纯情。宫斗的惨烈、生存的危机让“言情”变得奢侈,变得不可靠。天真纯洁、贤淑柔婉的女性传统标签在这里被一一撕毁,魏璎珞从一出场就具有强大的“大女主”气场,她天生反骨,屡屡僭越,敢于与皇帝共膳,蔑视“食不言寝不语”等老祖宗传承下来的规矩。换言之,魏璎珞是整个紫禁城中唯一一个没有奴性意识、不争宠不言情的现代人,是穿越到乾隆王朝的独一无二的“他者”。
魏璎珞的“独一无二”在于颠覆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规范和认知。“反言情”“爱自己”是魏璎珞宫斗的双重武器。富察皇后和皇后那拉氏的悲剧在于因“言情”而迷失了“自己”,她们统管六宫,却都无限渴望得到皇帝的爱,殊不知帝王只有宠没有爱。魏璎珞是“反言情”的,无论对富恒还是对皇帝。魏璎珞在情感上更像一名男性,从不拖泥带水,当断则断,干脆利落。与之相反,富察皇后则是把自己紧紧包裹起来的人,她的悲剧命运在于崇善自由、多愁善感而又身居后位身不由己。富察皇后屡屡保护魏璎珞,是因为魏瓔珞如同她在深宫中被压抑被丢失的自我,是她残存的希望。多愁善感从来都是后宫生活的大忌,魏璎珞则不同,不管是面对傅恒的痴情守候还是乾隆居高临下的不对等情感,她如同一个钢铁直男,从没有恋爱中女性的多愁善感,或者说她根本不谈爱情。赢得皇帝宠爱,达到复仇目的才是她的游戏规则。就如帝王一样对后妃只有宠没有爱,魏璎珞也是“彼此彼此”,所有的邀宠、争宠只是为复仇铺平道路。她更像一个穿越到大清王朝的帝王。也可以说,魏璎珞之所以能在宫斗中如鱼得水,就在于她颠覆了自身的女性角色,是男性化的魏璎珞,而且,最终还是依靠皇帝/男权的帮助,才取得了宫斗胜利。换言之,女性再如何强大,也无法逾越性别权力的设置,只能处于最高权力的附属地位。结尾处成为皇贵妃的魏璎珞和皇帝的深情/男女对视大概也只是宫斗之后的副产品,仿佛言情剧“大团圆”的一种延伸。正是因为这一“败笔”,该剧又落入了言情剧的窠臼。魏璎珞以“反言情”的姿态,有限的“女性意识”带来了女性觉醒的幻象,最终还是落入了“反言情的言情模式”。
无独有偶,除却“反言情”,还有“爱自己”。诚如皇后那拉氏所言,富察氏最爱自由,魏璎珞最爱自己,全紫禁城只有那拉氏最爱乾隆却无法赢得他的心。如同富察皇后在“母仪天下”中丢失了自己,皇后那拉氏的悲剧恰恰在于在爱中迷失了自己。她是最能看透魏璎珞的人,“本宫看她天底下谁都不爱,就爱她自己,爱得如珠如宝”。不掺杂质的“爱自己”正是魏璎珞最有利的宫斗武器,是女性自我意识的一次“清穿”,颠覆了千百年以来封建传统对女性的规约束缚,自我意识的觉醒让魏璎珞傲娇于所有以权势富贵、皇帝宠爱为目标的六宫粉黛。当“竞争对手”顺嫔出现之后,魏璎珞依然最爱自己。剧中反复出现“魏璎珞就是魏璎珞”,“魏璎珞她本来就是独一无二的”之类的话语。她冷眼质疑女性不顾自身安危以子嗣为中心的传统观念,认为女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女性,女性自身的意义高于一切。这其实非常具有现代性了,无异于女性意识的觉醒。“爱自己”让魏璎珞拥有强大的内心和战斗力,正如她对庆贵人所言:“要想保护家人,必须要拥有力量。依附于强者,不如自己变成强者。”然而,这些“女强”意识并没有打开突破传统权利逻辑的可能性,不过是女性自我意识的一次任性、浪漫而有限的“穿越”。
四
原本以网剧为预设的《延禧攻略》无异于一场女性自我发现之旅,尽管有限,但毕竟有了清晰而独立的女性意识。网络热搜和弹幕流量证实了这部横空出现的清宫剧的火爆程度。魏璎珞从一开始就摈弃了儿女情长,她更像封建皇权/男权体系之内的一个另类的“他者”,她并没有达到女性主义所倡导的男女平等高度,也没有跳出传统的权利逻辑体系设置,只是在“爽文化”“怼文化”蔓延的幻象空间中顽固地“爱自己”。
在面对这些“大女主”作品时,学者戴锦华认为这些作品虽然更换了角色性别,但是丝毫没有改变故事的权力逻辑,这些女性面对的仍然是文化上的“花木兰境遇”。“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妇女在她们获准分享社会与话语权力的同时,失去了她们的性别身份及其话语的性别身份;在她们真实地参与历史的同时,女性的主体身份消失在一个非性别化的(确切地说是男性的)假面背后。”b诚然,历史剧不过是当代剧的特殊表现,花木兰式的境遇即使在倡导男女平等、在女性解放达到一定程度的今天依然存在。在稳固、严密而不可僭越的男权秩序之下,女性无法建构另外一种逻辑,只能在故事原有的叙事逻辑之中,有限地演绎自我。虽然魏璎珞并没有改变男性社会主导的权利逻辑,但至少是对女性传统身份的一种僭越。
a 邵燕君:《在“异托邦”里建构“个人另类选择”幻象空间——网络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之一种》,《文艺研究》2012年第4期,第16页。
b 戴锦华:《昨日之岛:戴锦华电影文章自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1—82页。
作 者: 陈红,文学博士,现就职于北京市圆明园管理处,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