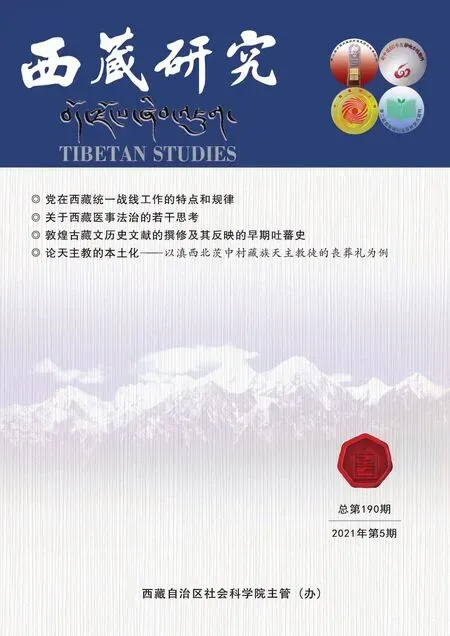明代对藏册封问题研究
2021-02-14陈武强
陈武强
(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陕西 咸阳 712082)
一、引 言
册封,也称“册立”“册命”“策命”等,始于周代,后世沿承。其内涵有多种,一为中国古代皇帝封立太子、皇后、王侯、公主、郡主等,并举行仪式,宣读册授圣旨。二为宗主国对藩属国的册封,由此形成一种册封体制。册封体制源于商周分封制,“册封体制也可以称为朝贡关系,是以宗主国和属国两方面构成的相互关系制度”[1]。三为中原王朝对边疆民族首领的册官封爵,所谓“加以侯王之号,申之封拜之宠,备物典册以极其名”[2],以定“君臣”之位。如唐朝试图通过册封,“来确定其对边疆民族的统治地位”,而接受唐王朝册封的民族政权,也就意味着“其承认唐王朝的最高统治”[3]。
明朝时期,中央对藩属国或边疆民族地区首领进行了大量册封。一方面,册封是确立明朝地位最重要的表现和环节,如明朝对朝鲜、日本、琉球等东亚诸国都曾进行过册封。另一方面,册封也是羁縻边疆民族首领、维护“华夷安危之道”的重要手段,如明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政教首领的册封、对蒙古首领的册封等。承担册封使命的大臣,称为册封使者(简称“册封使”)。
对明代册封问题已有大量研究成果(1)参见米庆余《明代中琉之间的册封关系》、于默颖《明代蒙古顺义王的册封与嗣封》、侯甬坚《由沧水入黑水——明代册封船往返琉球国的海上经历》、赵连赏《明代赐赴琉球册封使及赐琉球国王礼服辨析》、朱淑媛《新发现的明代册封琉球国王诏书原件》、连晨曦《明代册封琉球使臣的福州行迹》、陈沛杉《明朝对西藏地方政教首领的册封及其演变》等成果。另有刘月《明清两代册封琉球使及其从客海洋诗研究》、郑毅《明代闽籍册封琉球使及其作考证》等学位论文,也从不同角度对明代册封问题作了讨论和研究。,但主要是针对册封藩属国王、国君的研究,对于边疆首领的册封虽有一定的探讨,但研究成果并不多。关于明朝中央政府册封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政教首领问题,如册封方式、过程、作用、册封使的派遣诸问题,目前尚缺乏专文进行研究。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考证,以期说明其在西藏与祖国关系中发挥的历史作用。
二、来京册封范式与“限封”主张
综观明代册封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首领,主要有两种方式:(一)对朝贡来京或迎请的政教首领、头目、番僧等直接册封;(二)朝廷派出使者前往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奉敕册封。两种册封方式中,第一种即明朝对来朝的首领、头目、僧侣等人直接册封者最多,且册封时间、地点、形式等灵活多样。
按明朝中央政府册封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政教首领的数量,永乐年间是明代册封比较频繁的一个时期。从1402年到1424年的22年间,明成祖朱棣先后册封吉剌思巴监藏卜、著思巴儿监藏、释迦也失等人为政教王、法王、大国师、禅师等大小不等封号封爵,“番僧之号凡数等,最贵曰大慈法王,曰西天佛子,次曰大国师,曰国师,曰禅师,曰都纲,曰剌麻。”[4]卷27:684其数量,仅永乐一朝,计有“西天佛子者二,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十有八,其他禅师、僧官不可悉数。”[5]8577其册封方式极其灵活,而最重要的册封是藏族五大政教王和两大法王。
西藏五大政教王的册封是在永乐四年(1406)至永乐十一年(1413)间完成的。其中,阐化王为永乐四年敕封帕木竹巴第四任教主吉剌思巴监藏卜的爵号[6];赞善王者,“灵藏僧也,其地在四川徼外,视乌斯藏为近。成祖践阼,命僧智光往使。永乐四年,其僧著思巴儿监藏遣使入贡,命为灌顶国师。明年封赞善王,国师如故,赐金印、诰命。”[5]8582护教王者,“名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馆觉僧也。成祖初,僧智光使其地。永乐四年遣使入贡,诏授灌顶国师,赐之诰。明年遣使入谢,封为护教王,赐金印、诰命,国师如故。”[5]8583阐教王者,“必力工瓦僧也,成祖初,僧智光赍敕入番,其国师端竹监藏遣使入贡。永乐元年至京,帝喜,宴赉遣还。四年又贡,帝优赐,并赐其国师大板的达、律师锁南藏卜衣币。十一年乃加号灌顶慈慧净戒大国师,又封其僧领真巴儿吉监藏为阐教王,赐印诰、彩币。”[5]8584辅教王,“思达藏僧也,其地视乌斯藏尤远。成祖即位,命僧智光持诏招谕,赐以银币。永乐十一年封其僧南渴烈思巴为辅教王,赐诰印、彩币,数通贡使。”[5]8585
两大法王中,大宝法王哈立麻(即却贝桑波)为永乐四年十二月抵达南京后次年(1407)封,“(其间)却贝桑波为皇家讲经、灌顶并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资福。皇帝所赐礼品无数。皇帝亲赐却贝桑波以‘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封号。”[7]210大乘法王昆泽思巴(即贡噶扎西),为永乐十一年二月来南京后被封(2)1425年,大乘法王贡噶扎西贝桑布在萨迦大殿去世,大乘法王一职由萨迦昆氏家族成员世袭。参见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2页。。永乐十三年(1415)二月,明成祖还敕封格鲁派宗喀巴的首席弟子释迦也失(又译作释迦益西)为西天佛子大国师。次年,释迦也失返藏,明朝赐予他金银、绸缎、佛像等大量财物。《新红史》称:“燕王皇帝掌政二十二年。此皇帝最初也曾派人迎请宗喀巴,但是未去。因此,迎请了噶玛巴法王却贝桑波、萨迦巴衮嘎扎西及塞热哇释益西等三人。遂后他们依次被赐以封号:如来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及大慈法王。此皇帝又向尊者佛像献了衣服供物等(之丰)不可思议。”[7]50-51显然,较之洪武时期,永乐年间在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的册封规模更大、数量更多、体制更加完善。五大政教王、两大法王的封授,是明初边疆治理史上一件重大的事件,明人郑晓的《今言》道:外夷封王者,只有琉球三王、北虏四王、西域二王,而西番七人:“正觉大乘法王、如来大宝法王、阐化王、阐教王、辅教王、赞善王、赞化王”[8],足见西番封王最多、地位极高,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西藏事务在明朝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
继永乐朝之后,宣德九年(1434)宗喀巴弟子释迦也失来京觐见明宣宗皇帝,被封为“大慈法王”。明宣宗敕封大慈法王一事,《新红史》中说:宣德九年,释迦也失再次抵达北京,明宣宗封“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净般若弘昭(照)普慧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自在大圆通佛”,即大慈法王[7]51。《明史·大慈法王传》记载:“大慈法王,名释迦也失,亦乌斯藏僧称为尚师者也。永乐中,既封二法王,其徒争欲见天子邀恩宠,于是来者趾相接……宣德九年入朝,帝留之京师,命成国公朱勇、礼部尚书胡濙持节,册封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净般若弘照普慧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自在大圆通佛。”[5]8577《万历野获编》亦载:“宣德九年六月,遣礼部尚书胡濙同成国公朱勇,持节封释迦巴(也)失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净般若宏(弘)照普应(慧)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自在大圆通佛。”[4]补遗卷4:914各文献中记载基本相同,即释迦也失来京觐见宣宗朱瞻基后被封为“大慈法王”。至宣德年间“大慈法王”册封完成,明代共计封授了西藏五大政教王、三大法王,他们在当地地位最高、最受尊崇。研究者认为,明朝册封三大法王和五大政教王的过程有所不同,“封授五王仅用了10年时间就告完成,而大法王的封授过程颇为复杂曲折,直至宣德九年才最终完成,历时几达30年。”[9]47除五大政教王、三大法王之外,明朝还对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僧俗首领封以大国师、国师、禅师等封号以及大大小小的僧官,“不可胜纪”[8]8578。
由此可见,明朝前期,中央政府适时册封西藏地方政教首领,根本目的是要达到所授官员“统束各番”、确保地方统治。因此,得到明朝册封者,或者是当地有势力者,或者是在当地具有威信者,特别是高德大僧,“我朝洪武六年,因其故俗,以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后分封为大宝、大乘、赞化、阐化、阐教、辅教等六王,皆僧也。”[10]
明代中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政教首领的册封制度照例进行。景泰三年(1452)十月,明代宗封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札释为大智法王,赐以诰命。景泰七年(1456)六月,明代宗听从礼部尚书胡濙的奏请,敕封答苍地面王子喃噶坚粲巴藏卜袭为辅教王,赐诰敕、金印、彩币、僧帽、袈裟、法器等物,并敕封番僧葛藏为灌顶广善慈济国师、烈藏为静觉持正国师、领占巴丹为静觉佑善国师、班卓儿坚参为戒行禅师、桑结远丹为慈化禅师、罗竹聪密为翊善禅师、坚参烈为妙觉禅师、远丹绰为静范禅师、领占三竹为清修禅师、罗竹札失为崇善禅师,“各赐印及诰命。”[11]卷267:5672同年七月,明代宗册封西番净修弘智灌顶大国师锁南捨剌为净修弘智灌顶大国师西天佛子、广通精修妙慧阐教西天佛子大国师沙加为广通精修妙慧阐教弘慈大善法王、剌麻占巴失念为崇修善道国师、加弘善妙济国师捨剌巴为灌顶弘善妙智国师[11]卷268:5683。十月,明代宗封番僧札失尾则儿、班竹儿星吉俱为左觉义,桑儿结巴为右觉义,锁南班卓儿、锁南坚粲、锁南捨剌、远丹罗竹、锁南札、南葛藏卜俱为都纲,给印并诰敕,一年之内敕封的僧官达二三十人。
然而,自明代中期以来,朝廷对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政教首领的册封已不再节制,“尤其是对寺院番僧的无限制地封赐,导致了进京冒贡人数剧增。”[12]明宪宗时,朝廷对乌思藏僧俗首领“分封赏赐泛滥”[13],带来了一系列边疆和社会治理新问题。于是,朝廷内部出现了限制册封的声音。六科给事中魏元、十三道监察御史康永韶、翰林院编修陈音等人分别向明宪宗提出在册封问题上的建议。尽管建议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都认为朝廷应当限制册封,减少负担,从根本上解决朝贡无度带来的财政危机状况。如魏元在成化四年(1468)九月提出:“革去番僧法王、国师等名号”[14]卷58:1176,发回西藏,追回赏赐,以赈饥民。同年,康永韶也指出:“今朝廷宠遇番僧,有佛子、国师、法王名号,仪卫过于王侯,服玩拟于供御,锦衣玉食”[14]卷58:1176,应当对此进行甄别查审,遣回本地。陈音在成化六年(1470)三月提出:“当今号佛子、法王、真人者,无片善寸长可采,名位尊隆,赏与滥谥。伏愿降其位号,杜其恩赏。”[14]卷77:1482对于朝廷内外各种反对册封的奏疏甚至批评,明宪宗搪塞说,“此事累有人言,俱已处置矣。”[14]卷77:1482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摇摆不定,明宪宗最终以“祖宗旧制”[14]卷77:1482、不能辄变为理由否决了封建士大夫们的限封主张。故明宪宗统治时期,册封事宜照旧实行。在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趋动下,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僧俗首领不时违制朝贡[15],进京朝贡人数更多、次数更频,故册封数量更多,“冒贡”“滥贡”“滥赏”“滥封”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明孝宗朱祐堂即位后,一改宪宗时期的政策,对边疆少数民族政教首领册封制度有了较大的转变。明孝宗是成化二十三年(1467)九月即位的,十月丁卯(1487年10月17日),礼部即颁定一项册封番僧法案:自法王、佛子、国师、禅师各降职一级,自讲经以下革职为僧,“各遣回本土、本寺或边境居住,仍追夺诰敕、印信、仪仗,并应还官物件。”[16]经明孝宗改革,弘治时期对藏册封数量大为缩减,册封得以控制,“虽然明孝宗对于番僧的态度在弘治中后期略有变化,但在整个弘治时期,中央王朝对西藏地方的册封数量仍得到有效限制。”[17]
明武宗时期,虽有太监刘允进藏迎请活佛之举,但明朝朝野上下对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僧俗首领册封一事反对者甚众,“中央王朝对西藏地方的限封和降封已经逐渐成为全朝野的共识”[17]。到了嘉靖时,明世宗即位后诏令:“正德元年以来,传升、乞升法王、佛子、国师、禅师等项,礼部尽行查革,各牢固枷钉,押发两广烟瘴地面卫分充军,遇赦不宥。”[18]卷1:10此诏以最严厉的法律从理论上宣告了明朝初期以来实行的对藏册封制度的全面停止。
明臣反对对藏册封的根本原因,皆因明代中后期的滥封无度偏离了册封制度的初衷,给国家治理造成了危害。适时停止已经具有消极影响的无限制册封,“因时而易”地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真正维护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安定应该是明智之举,也是与时俱进之策。当然,明朝的一些封建官僚、士大夫们强调册封“无益于治道”[14]卷58:1176,即它对于国家治理边疆没有任何好处,这也难免有些偏颇。因为从特点和效果上看,明朝对藏册封,前期与后期并不相同。总体而言,前期册封少而精,后期册封杂而乱,因此它们对边疆治理的作用和意义是不相同的,并不是所有阶段的册封都“无益于治道”,要理性地分析。值得肯定的是,明代前期的册封在政治上无疑意义重大,只不过中后期的滥赏滥封才使其大打折扣。
三、遣使册封“旧例”与成、嘉时期改革
明朝对藏册封是确保中央政府对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有效统治的有力保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了加强中央政府与地方之间的联系,确保治藏政策的顺利落实,对影响较大的寺院高僧或势力较大的世俗地方官员,朝廷均主动派遣京城寺僧为使者前往册封,这是从明初直至嘉靖四十二年(1563)之前实行的册封“旧例”,即对藏册封的基本制度。
此外,当明朝所封藏族政教首领年老不能处理政教事务时,即奏请中央政府由其子侄、徒弟袭职,中央得到奏请便会派出使者前往册封新首领。如天顺元年(1457)九月,乌思藏辅教王喃葛列思巴罗竹坚粲巴藏卜奏陈:自己已年老不能理事,请其子袭职。明英宗诏命灌顶国师葛藏为正使、右觉义桑加巴为副使,率使团到乌思藏封其子答苍喃葛坚粲巴藏卜袭职辅教王[11]卷282:6064。如果藏族聚居地方报告所封头目已死,朝廷便遣使吊祭,同时册封新的首领。弘治十年(1498)十二月,乌思藏阐化王死,其子班阿吉汪束札巴乞袭封,明孝宗立即诏令番僧剌麻参曼答实哩为正使,锁南窝资尔为副使,前往西藏封其子班阿吉汪束札巴袭职阐化王。
考终明一世,派遣到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的册封使,见于文献确切记载者如下:

表1:明代对藏册封使
表1中永乐四年(1406)至正德二年(1507)间出使使者有:宣德五年,沈羽;宣德九年,刘浩、朱勇、胡濙;正统五年,葛藏、昆令;正统十年,锁南藏卜、札什班丹、斡些儿藏卜;天顺元年,葛藏、桑加巴等;弘治十年,参曼答实哩、锁南窝资尔、札失坚参等18人;正德二年,札巴也失、锁南短竹。这些册封使中,国师、禅师、剌麻等僧职使者人数达到68.7%。
由于册封对中央政府统辖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所以朝廷在派遣册封使时充分考虑其地域性、民族性及能力、官职大小等身份因素,使派遣的册封使能够代表朝廷、具有话语权,并能处理好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而汉番僧人在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社会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且有语言、身份之便利,所以,以汉番僧职人员充任册封使者最多。这是其一。
其二,此表中的使者身份是指出使时的身份。使者出使任务完成后,因功升职的情况很常见,所以身份发生变化者多。从表1中所列册封使的身份考察,明朝中央政府派遣的册封使者中,官职最大的是成国公朱勇和礼部尚书胡濙,使者官职为正二品大员甚至王公亲往,无疑反映了明朝对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僧俗首领册封的高度重视。
其三,上表所列并非全部遣藏册封使,考察明清时期文献,还有诸多无姓名使者。《明太宗实录》卷52:
(永乐四年三月壬辰),遣使赍诏封乌思藏巴里藏卜为灌顶国师阐化王,赐螭纽王印、诰命,仍赐白金五百两、绮衣三袭、锦绮五十匹、彩绢百匹,茶二百斤。其所隶头目并必力工瓦国师大板的达律师锁南藏卜,颁赐彩币、衣服有差。[19]775-776
(永乐四年三月壬寅),遣使命灵藏著思巴儿监藏为灵藏灌顶国师,授札思木头目撒力加监藏为朵甘卫行都司都指挥使,切禄奔、薛儿加俱为都指挥同知,各赐诰命、袭衣、锦绮。命馆觉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为馆觉灌顶国师,陇答头目结失古加之子巴鲁为陇答卫指挥使,赐诰命、银、币。[19]780-781
此二例史料,除了册封使是何人并不知晓外,其他册封时间、地点、目的等皆十分清晰。
像这种无姓名记录的册封使者还有许多。《明实录》载:明朝中央政府于永乐四年三月、正统三年正月、正统五年三月、正统十二年二月、景泰三年十月、景泰七年六月、景泰七年七月、成化四年四月等分别遣使册封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首领,但使者名未记载。如永乐四年三月,明成祖“遣使赍诏封乌思藏巴里藏卜为灌顶国师阐化王”[19]775;正统十二年(1447)二月,明英宗“遣官赍诰敕封故安定王亦班丹子领占斡些儿袭安定王,赐织金、衣服、彩币、表里。”[11]卷150:2947景泰七年六月,明代宗“遣官封答苍地面王子喃噶坚粲巴藏卜袭为辅教王,赐诰敕、金印、彩币、僧帽、袈裟、法器等物。命番僧葛藏为灌顶广善慈济国师,烈藏为静觉持正国师,领占巴丹为静觉佑善国师等。”[11]卷267:5672他们之中,可能仍然以国师、禅师、剌麻、都纲等僧职人员作为册封使主要成员。
景泰之后,中央册封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首领的次数和频率明显下降。成化三年(1467)七月,明宪宗朱见深诏命灵藏僧塔儿巴坚粲袭封为赞善王。按照明代“旧例”:
番僧封王者,赐诰敕并锦绮、衣帽诸物甚备,又遣官护送至彼给授。礼部以今西事未宁,事宜从省。乞降敕一道,惟赐袈裟、禅衣、僧帽各一,顺付来朝番僧赍回灵藏给授。从之。[14]卷44:918
这条史料明确反映了一个重要信息:按明朝规定,凡是番僧封王,不论是新册立还是袭职,中央政府必须派遣使者到当地给授。可是,景泰、成化年间,大批蒙古部落开始进入青海一带活动,西宁边事变得异常复杂,故礼部建议简化对藏册封形式,暂停遣使册封旧规。明宪宗认为,礼部所奏合理合情,遂降敕一道:“顺付来朝番僧赍回灵藏给授。”[14]卷44:918此敕表明,这次册封西藏赞善王,朝廷不再遣使前往而是交于西藏地方来京贡使返藏后给授。此敕也预示着遣使册封正在悄然出现变通。
成化三年册封方式的变通,为以后册封制度的改变留下了伏笔。嘉靖四十二年十月,乌思藏阐化等王请封,明世宗朱厚熜和礼部的回应是:
上以故事,遣番僧远丹班麻等二十二人为正、副使,以通事序班朱廷对监之。比至中途,班麻等肆为骚扰,不受廷对约束。廷对还白其状。礼部因请自后对藏请封,即以诰敕付来人赍还,罢番僧勿遣。无已,则下附近藩司,选近边僧人赉赐之。上以为然,令著为例。[18]卷526:8576
从礼部的处置可以看出,礼部是要把原来遣使册封制度进行改革,即废除“封诸藏遣京寺番僧例”。对此,明世宗表示赞同,批准颁行,这就是嘉靖四十二年的《封诸藏不遣京寺番僧例》。新“例”明确规定:自今后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首领请封,即以诰敕交于贡使返藏时给授。不久,又调整为由临近这些地方政府派遣边地僧人赍敕给授,并“著为例”[18]卷526:8576。
关于此例,《典故纪闻》卷17亦有载:“旧例,乌思藏请封,皆遣番僧为正副使,而以通事监之。嘉靖四十二年,遣番僧远丹班麻等封阐化等王,比至中途,肆为骚扰,不受通事约束。礼部因请:自后请封,即以诰敕付来人赍还,罢番僧勿遣。封诸藏之不遣京寺番僧,自此始。”[20]也就是说,自嘉靖四十二年起,明朝册封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首领,不再派遣中央使者前往。
综上,明代遣使册封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首领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洪武至景泰年间,遣使册封比较频繁;第二阶段是成化年间的变通,第三阶段是嘉靖年间《封诸藏不遣京寺番僧例》的颁行,遣京寺使者册封停止。第二、第三阶段,即成化、嘉靖时期,明朝中央政府对其册封制度进行了改革。对于来京册封,依然执行过去的旧政策。成化四年四月,明宪宗册封西僧札巴坚参为万行庄严功德最胜智慧圆明能仁感应显国光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刚普济大智慧佛;札实巴为清修正觉妙慈普济护国衍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锁南坚参为静修弘善国师、端竹也失为净慈普济国师。俱赐诰命。但对于遣使册封,朝廷探索实行“领封”政策,依照新的《封诸藏不遣京寺番僧例》实施。新“例”的颁行,标志着嘉靖四十二年之后中央遣使册封停止。
需要说明的是,新“例”的实施只是停止了派遣京城寺僧册封的惯例,并不是说对这些地区首领的册封完全停止了。实际上,在此“例”颁行前后,尽管朝野内部“册”与“废”的争论激烈,但明朝官方对藏族头目来京或遣使来京请职、请袭等要求依然予以应允,并基本按其要求封授:
如新“例”颁布前,西番剌旺藏卜于成化四年四月遣使入贡求请(职),“升西番剌旺藏卜为都指挥佥事。”[14]卷53:1077正德十年(1377)二月,“番僧完卜锁南坚参巴尔藏卜遣人朝贡,乞袭封大乘法王,许之。”[21]卷121:2434正德十一年(1378)四月,“西番僧短竹叫等四人、桑呆叫等十人来贡方物,请袭国师、禅师职,从之。”[21]卷136:2690当然,对藏族首领的请职,朝廷有时也会酌情考虑。如成化十五年(1479)十二月,乌思藏阐化王遣剌麻锁南领占请求升(锁南领占)为国师,“命升为禅师,不为例。”[14]卷198:3478必须说明的是,藏族头目请职,有时朝廷需要派出考察官员前往考察实情,方可授予。成化四年十月,管民万户舍人阿哈来朝贡方物,请袭职。“自称其祖合丹思叭所辖地方十七,其印犹元至正间所授。乞换印袭职,开设衙门。”事下礼部会议认为,“宜移文四川镇守等官,遣官出境,勘其端由”[14]卷59:1205,之后方可册封,体现了明朝中央对边地册封的谨慎态度。
新“例”颁布后,乌思藏阐化王南札释藏卜于万历六年(1578)二月“差番僧来西海,见其师(番)僧活佛在西海与顺义王子孙等说法,劝化众达子为善,因托顺义王俺答代贡方物,请敕封。”[22]1558经礼部复议,明神宗“各授大觉禅师及都纲等职,赐僧帽、袈裟及表里、食茶、彩段有差。”[22]1558可见,即使是嘉靖朝颁行了新的《封诸藏不遣京寺番僧例》,但中央政府的对藏册封制度并未完全停止。当然,此时的对藏册封已与过去的无序册封大相径庭,并在某种情形下发挥着其特殊的历史作用。
四、对藏册封之评价
明朝中央册封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政教首领,根本目的是为了加强和巩固明朝在藏族聚居地区的统治。因此,册封在国家治藏治边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第一,基于中央政府“多封众建,因俗以治”的治藏方略,一方面朝廷对于藏族聚居地方来京觐见或朝贡的政教头目、大小僧人等均予以册封;另一方面,对居于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政教领袖遣使赍敕册封,使其在各自辖区合法行使管理权,抚治民众、忠勤朝廷。换句话说,正如明太祖“授端竹监藏信武将军加麻世袭万户府万户的制诰”中如是说:“今授尔信武将军,加麻万户府万户,俾尔子孙世袭。尔其招徕远人,绥端边疆,永为捍御之臣。”[23]
第二,明代对藏册封有一整套严密的制度,包括册封仪式、受封者的爵号、对受封者诏书的宣读及印玺的授给等方面,“举行仪式时,由天子派遣相应的大臣为使者,向受封者及有关人等宣读册文,并授以印玺,受封者的地位由此即得到承认。”[24]凡是明朝中央政府册封地方政教王、法王、国师等大小官员,均有册封诰敕文书。《松窗梦语》卷3:经明初封官授职,于是西番番僧各有封号,“凡诸王嗣封,皆有赐诰。”[25]封诰文书还十分讲究诏书、诏敕、诏诰等不同类型和不同金银丝织质地,以此显示这些高僧的不同地位及其中央政府对他们的尊崇。《南村辍耕录》卷2《诏西番》曰:“累朝皇帝于践祚之始,必布告天下,使咸知之。惟诏西番者,以粉书诏文于青绘,而绣以白绒,网以真珠,至御宝处,则用珊瑚,遣使赍至,张于帝师所居处。”[26]兹录“明太祖赐噶玛噶举教派楚布寺”诰敕文书之内容如下:
敕书:明太祖赐噶玛噶举教派楚布寺(3)楚布寺,在今拉萨市西堆龙德庆县境。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正月下达宣谕诏书的时候,楚布寺的寺主为黑帽系第四世转世活佛乳必多吉(1340—1383)。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藏自治区社科院、中央民族学院研究所、中国第二次历史档案馆编《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4页;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拉萨文物志》,咸阳:陕西咸阳印刷厂1985年版,第164页。
圣旨原文:
“皇帝圣旨:中书省官我根前题奏,西安行都卫文书里呈来,说乌思藏哈尔麻剌麻卒尔普寺在那里住坐修行,诸色人等休教骚扰,说与那地面里官人每知道者。”
末行为“洪武八年正月日”[27]907
此为明洪武八年(1375)正月明太祖朱元璋颁发给楚布寺喇嘛乳必多吉的圣旨(4)乳必多吉是噶举派的一个支系——噶玛噶举黑帽系的第四世活佛,时颇有名望,曾应元顺帝召于1360年至1364年住元大都5年。洪武七年(1374年,藏历第六饶迥木虎年),派贡使往返朝廷,深得明廷器重。参见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拉萨文物志》,咸阳:陕西咸阳印刷厂1985年版,第164—165页。,圣旨质地为白棉纸,方形,边长76厘米,行文88字。墨笔楷书,字体秀劲工整。文后钤“制诰之宝”朱印一方[27]907。由于各官员的品级不同,诰命敕书封赠的范围及丝织质地、轴数、图案也各有不同。
诰敕、印章是明朝中央政府颁给藏族政教首领任官的主要凭证。这些凭证要么是任官时当面赐予,要么在任官后遣使赐予。一般情况下,普通政教首领在来京时颁予,或由贡使返回时转赐。成化三年十二月,“番僧法王札巴坚参、西天佛子札实巴、国师锁南坚参、端竹也失、禅师班竹星吉、礼奴班丹以升职奏乞诰敕、印章,与之。”[14]卷49:1001但地位至高者,必须经明朝中央政府遣使颁赐诰敕印章。
第三,事实证明,明代中央政府册封西藏及其他藏族聚居地方首领的政策十分有效和成功,如“大慈法王”册封后不久返藏,在西藏修建了色拉寺,并向格鲁派僧众积极宣扬明朝的形象,增加了藏族同胞的民族认同。册封的历代大乘法王,“都按明朝的规定定期向朝廷朝贡,为维护西藏地方的安定和加强与朝廷的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9]171。由此可见,经过册封,明朝在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的统治得以巩固,藏族政教领袖也获得了中央政府颁赐的管理各自地方的合法权力。
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册封的西藏地方政教首领,按照中央政府的规定和要求定期朝贡、积极宣扬和维护明朝的形象,必然增加了藏族同胞的民族认同意识,客观上加强了西藏地方与祖国之间的亲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