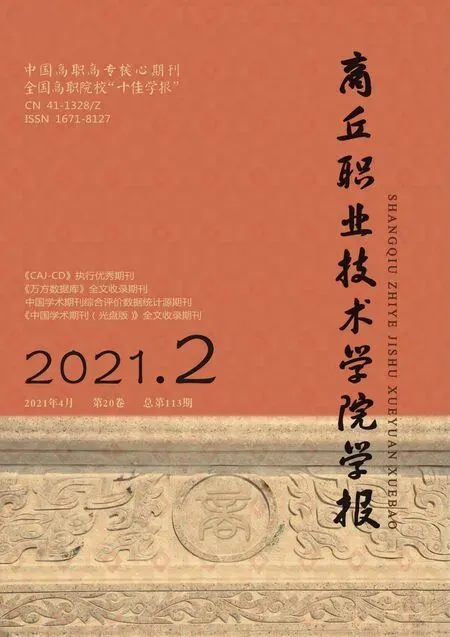《夏日》的复调式叙事手法分析
2021-02-13刘文娟
刘文娟
(平顶山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00)
《夏日》(Summertime, 2009)作为约翰·麦克斯韦尔·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即J.M.库切)“自传体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其副标题“外省生活场景”也是库切前两部自传小说《男孩》(Boyhood, 1997)和《青春》(Youth, 2002)的副标题。研究者经常把这三部作品放在一起进行分析,研究视角主要放在“自传三部曲”关于“自我”的真相等方面,也有学者运用后殖民理论来解读这三部作品中的文化身份问题。本文将运用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尝试对《夏日》的叙事手法进行解读。
从叙事方法的角度来看,《男孩》和《青春》是线性叙事法,是由一个单一的声音完成;《夏日》没有直接的叙述,而是多种声音的复合[1]617。《夏日》所讲述的故事与现实之间形成了强大的张力,其在对话的过程中展示了创作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小说以未完成的库切笔记手稿以及英国学者的采访记录形式出现,这种‘元小说’的叙述形式本身就使文本视角呈现暂时性与不确定性”[2]。
一、“大型对话”艺术的展现
在1929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一书中,巴赫金所提出的“复调小说”,是与传统的“独白小说”相对应的“多声部性”的小说、“全面对话”的小说[3]2。巴赫金认为,两个声音,即对话,才是生活的基础、生存的基础[3]11。他提出了结构上的“大型对话”理论,即故事线索、人物组合原则的“对位”[3]5。在《夏日》这部作品的创作中,对话精神贯穿始终,形成结构上的“大型对话”,即作品与生活的对话和主体与客体的博弈。
(一)作品与生活的对话——平行世界里的交响曲
《男孩》和《青春》运用第三人称叙述方式,其主人公名叫“约翰·库切”,与作者同名。在《夏日》中,“约翰·库切”已经是一名“已故”的“伟大作家”,英文“传记作者”文森特希望为他立传,并解释为何选择集中记录“约翰·库切”在1972—1975年这个阶段的相关事件:“我集中记述库切先生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二年间回到南非后,直到一九七七年他得到社会大众承认,这一时期的经历。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时期,重要,却被人忽视,他在这段时间里觉得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作家。”[4]233也就是说,在这部虚构的传记中,读者可以看到一个青年在成为“作家”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段时期的经历,只是该经历是根据日记和旁观人的叙述而得来的。“知情的读者会发现库切无论是在翻译,还是在自己创作的小说中,总显现出一个模糊的、他自己生活的轮廓”[1]183。 《夏日》描写了一个青年成为作家的关键几年,而真正的库切本人也是在1970年开始其第一部书——《幽暗之地》的创作的。
小说中青年的这段经历与真实生活中库切本人所走过的路程有一定的相似性。现实生活中,库切本人是在1965年前往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汀分校攻读博士学位,1969年被授予博士学位,1968年7月15日接受了以学术自由而闻名的布法罗大学助理教授的职位。随着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及其局势的恶化,1970年3月15日,包括库切在内的45位讲师聚集在教学楼前和平抗议警方驻扎校园,因而遭到逮捕并在监狱待了一天,虽然被控告“藐视法律和非法侵入”的指控在一年后撤销,但该“违法案底”造成了库切本人入境签证被撤销。因此,1971年,库切决定辞职,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离开美国,飞往他“曾不惜一切代价想要逃离的祖国”[1]202。
《夏日》也描述了这次逮捕,并认为这是主人公库切职业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但小说中的库切单身,他是因为参加了一次游行而非静坐才不得不离开美国,回到南非后,他与鳏居的父亲住在开普敦一间破旧的房子里。
此处,静坐换成了游行,与妻儿的生活被改写成与失意的父亲的相处——小说披上现实的外衣,但却并不是一部忠实于事实的“自传”,而是改了款式和色彩的戏仿。
(二)主客体的反转——“约翰·库切”与被采访者的博弈
库切曾无数次地拒绝评论自己的作品:“我一直认为,作品不应该背负着作者的诠释……我一直不愿进入一种状态,就是由我来‘解释’我的作品。”[1]486但是,《夏日》中的主人公被命名为 “约翰·库切”却直接混淆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
小说中的“传记作者”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主要充当引导和连接的作用:引导并连接五位受访者回答或陈述一些相关问题,并在第一部分和最后一部分展现作家“约翰·库切”的笔记。在作品中,除了一些标明和未标明的零散笔记外,“约翰·库切”基本是一个缄默者,一个权利话语弱化的“小说主体”,而那些与他有交集的五位受访者却反客为主。在与“传记作者”讲述时,这些受访者往往以“约翰·库切”为出发点,但在叙述过程中却偏离了轨道,“朱莉亚的中产阶级隐私,玛戈特的家族农庄,阿德瑞娜的底层移民背景,还有‘马丁’和‘苏菲’这两个章节中的学院小景,串联起20世纪70年代南非社会的一幅图景”[4]7。这种主客体的反转也造成作品的反讽和幽默效果。
自传体小说绝不等同于自传,而是既可借助真正发生的事件,又可以加上虚构;既可以发表自己真实的想法,阐述真实的观点,又可以歪曲事实,曲解现象,表明与实际相悖的观点与看法。在小说中的库切承担着舆论的指向,他既是现实生活中库切的传声筒,又是他的挡箭牌,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在《夏日》中,库切通过虚构的传记作者文森特之口,直言不讳、冷静客观地讲述了“传记”对现实的戏仿:“我们都是虚构者。”[4]234
但《夏日》中的“虚构”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以生活为基础,通过作家那似乎具有哈哈镜功效的创作之笔,经过夸大、歪曲、错位等艺术手段对生活进行了戏仿。
二、多声部曲调的合奏
除了结构上的“大型对话”之外,巴赫金还提出了建立在人与人的对话关系、人的自我意识的双重性基础之上的“微型对话”[3]13。《夏日》最为典型的就是“微型对话”,主要表现在主人公与主人公的非封闭式的对话之中。几位接受采访的对象在回忆与库切有交际的生活片段时,都会不自觉地把自身当作事件的主体,他们不是在被动地回答传记采访者的问题,而是在主动地描述他们自己当时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同时,他们对采访者的一些记录提出质疑甚至是给出建议,从而构成了多声部曲调的合奏。
(一)隐秘的中产阶级
文中第一个接受采访的对象茱莉亚是已经移居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心理医生,在访谈中,她讲到了1972年至1975年的南非和她个人的感情生活。从她的谈话中,我们看到了塞满囚犯的开往普尔斯莫尔的车子、关在罗本岛的曼德拉以及不允许有色人种走进的超市,这从侧面描写了20世纪70年代南非种族隔离最残酷的社会现实。
在与“传记作者”文森特的对话中,茱莉亚是主导者,也是话语权的掌控者。虽然谈话是以“约翰·库切”为开端,但在谈及他的事件时,茱莉亚用更多的言语在描述自身,在剖析自我。通过一段“开诚布公的聊天”[4]22,她讲述了自己的两段恋情:初恋与婚姻,以及婚后丈夫所在的那个封闭的小圈子里人们的精神状态:女人们在男人们的世界里各种周旋;男人们“想要别人的妻子委身于自己,却又想让自己的妻子保持贞洁——贞洁而又有魅力”[4]24。
在与“约翰·库切”相处的每一个阶段,茱莉亚是二人关系的掌控者,而“约翰·库切”则成了一个离群索居、无家可归的配角儿。“约翰是我生活出现麻烦时的一个朋友。他是我有时会拿来使用的一副拐杖,但他永远不会成为我的爱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那种爱人。”[4]83尤其是当写到“约翰·库切”要求茱莉亚配合舒伯特的音乐与他做爱的情节时,“约翰·库切”更像是一个滑稽的、酸楚的书呆子,古典作品中勇猛的扮演英雄的“男人”在这里被消解刻画成一个缺乏男子汉气概的、软绵绵的、没有力量的“男孩”形象。
(二)白鸟喷泉农庄的“幸存者”
在访谈中,“约翰·库切”的表妹玛格特回忆了农庄的“过去与当下”。通过农庄的“过去与当下”的对比,读者看到了库切家族庄园生活的兴与衰:“在过去的年代里,圣诞节期间,一大家子都会聚集到家族农庄来……那一个星期全是欢声笑语和怀旧的思绪。……但是,时至如今,20世纪70年代,令人悲哀的是参加家族聚会的人数越来越少了……聚会的幸存者中,玩笑话变得越来越不好笑,越来越压抑了,大家在缅怀旧日的同时越来越变得心情悲哀,饮食也越来越节制。”[4]89读者能够从中看到白鸟喷泉农庄的凋零现状:年复一年的干旱让草原一片荒芜,曾经朝气蓬勃的壮年们成了一群无精打采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老骨头”[4]89。
同时,作品中还用大量篇幅让玛格特来描写自己的妹妹卡罗尔和妹夫克劳斯,以及丈夫卢卡斯和患病住院的母亲。所以,在访谈结束时,玛格特非常疑惑:“如果这是一本关于约翰的书,为什么要塞进去那么多我的事儿?谁要来读我的故事——我和卢卡斯,还有我母亲、卡罗尔和克劳斯的?”[4]161
此时的作者似乎失去了对作品的掌控,居然让其中的一个主人公站出来对“作品”进行质疑,同时对“传记作者”提出要求:“不能这样发表,不能。我要重新梳理一遍,你答应过的。”[4]162
“复调小说”的一个特点就是“强调主人公的独立的自我意识,”“重要的不是主人公在世界上是什么,而首先是世界在主人公心目中是什么,他在自己心目中是什么。”[3]4“微型对话”成为《夏日》中主人公自我意识展现的手段,而这种自我意识也是作品中艺术描写的主要成分。约翰表示自己干了很多手工活儿,目的是“我想表达一种姿态。我想打破关于体力劳动的禁忌”。他认为,在当时种族制度严苛的南非普遍盛行的思想是“如果一个白人碰了一把镐头或是铁锹,他马上就成了不洁之人”。而玛格特却反驳:“你这完全是胡说!这根本不是事实!只是诋毁白人的偏见!”[4]116随后,为了给“约翰·库切”一个台阶下,玛格特又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是对的:我们的双手,我们白人的双手,可能保持得太洁净了。”[4]117在很多类似的描写中,我们看不到作者的参与,取而代之的是主人公自我思想、自我意识的展示。在上述的描写中,无论是“约翰·库切”还是玛格特,他们的思想是完整的、独立的,对待时局有不同的观点,敏锐度也不同:“约翰·库切”直截了当地表现出对国家的不满,对种族制度的反感,并试图通过自己的行为表明一种姿态——白人应该与黑人一样参与各种劳动——包括体力上的。玛格特却持不同意见,虽然最后做了让步,那也只是因为不想在寒冷的荒野,除了疲惫和厌倦,还要对付这个被自己逼入死角的男人的“怨气”[4]177。
通过对话,不同的主人公表达了“世界在心目中是什么”这一命题。不同思想的碰撞表现的是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个性,而在实现这些目标时,作者退居幕后,所有的一切都是通过主人公直接的对话、主人公与自己的对话而表现出来的。“主人公在叙述自己的故事,他们变得与作者本人平起平坐了”[3]7。
(三)移民世界的声音
原本是国家芭蕾舞剧院演员的阿德瑞娜,因国内时局动荡而和丈夫马里奥从巴西移民到了南非,从事保安工作的马里奥在晚上执勤时被砍成重伤,后被留在精神病医院中经受“电流疗法”,最终不治身亡。一人带着两个女儿努力谋生的阿德瑞娜,怀疑并且也担心自己的小女儿玛丽亚·瑞吉娜被英语补习老师“约翰·库切”先生诱惑,因此,她出面做了种种干涉,但她没想到,“约翰·库切”在看到她的那一刻却开始追求她,还在她工作的舞蹈室报名学习舞蹈。在接受文森特的访谈时,阿德瑞娜讲到了在南非那段时间自己的经历和感受:生活的坎坷、官僚机构的不作为和社会上的不平等、追求者的“愚蠢”和女儿的反叛……这一切都让她疲惫不堪,因此,她说:“回忆那个年代的事情总是让我悲伤。”[4]166
看到这里,读者会忘记《夏日》作者的存在,忘记这是作者描写下的主人公的言行——以致让人觉得是主人公在叙述自己的故事。按照巴赫金的理论:“在‘复调小说’里出现了一种令人瞩目的变化,这就是小说艺术视觉的重大变化:原来的客体向主体转化,客体意识相应变为主体意识,原来作家的主体意识,却转向客体意识。”[3]6-7《夏日》是一部“已故”作家库切的传记小说,主人公之一的阿德瑞娜却对“传记作者”文森特,这样说道:“对你来说,约翰·库切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是一个重要人物……可是对我来说,完全是另一回事——对我来说,他什么都不是。……他就是个傻瓜。”[4]204
阿德瑞娜讲述着自己对伦理、道德、爱情以及社会问题的看法,并与“传记作者”文森特进行争论,表达着自己对“约翰·库切”作为一个作家尤其是大作家身份的怀疑。在她看来,“已故”的“约翰·库切”什么都不是,像是一个僧侣,一个内心没有火焰,不冷不热,没有灵魂、不能感受韵律的木头,一个算不上是真正的男人的家伙,一个成天埋首在古老的哲学书里的孤独而有怪癖的年轻人。而文森特也表达了自己对“已故”作家作品的观点:“当你读他的书的时候,‘火焰’是最不可能想到的词儿……他有一种沉静的凝视。他不会轻易被表象所迷惑。”[4]208
这两个人物把作品中真正的传记对象抛之脑后,坐而论道,侃侃而谈,他们通过对话的方式吐露自己的观点,这也正是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中的一个显著特征:主人公与主人公通过对话或者种种内省的方式,即自己与自己的内心对话,来展现内心的隐秘。“复调小说”中的主人公经常想到的是别人会怎样看待他们自己,会怎样议论他们,并随时同人们进行争论[3]7。所以,阿德瑞娜建议把传记命名为《木头人》,要对谈话记录进行增补或删减,并质疑能否把挂在脖子上“库切先生的女人之一”的标签扯掉,随后又调侃文森特未必允许这样做,因为这样会毁了这书。此刻的阿德瑞娜的思想完全是独立的、自由的,她的主题意识得到了加强。
“‘复调小说’中的主人公不仅是作家描写的对象、客体,同时也是表现自己观念的主体。”[3]3正如巴赫金用“复调小说”来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是“破碎的整体”一样,《夏日》的叙事策略也会让读者在阅读这些文字时,不会把作品中人物的语言和观点当作库切本人的,而会不自觉地忘记真实作者的存在。“这篇专注于自我的叙事便逐渐成为积累不同侧面的小说。”[4] 7
三、结语
《夏日》这部现时的文本不断与过去的文本进行对话,并对将来可能产生的疑问进行试答,以表面疏离的方式,让人物走入纷争,走入尘世,让作品与生活进行对话,形成了两个平行世界的交响曲;让被采访者与传记对象进行博弈,让主客体的地位得到翻转,形成了结构上的“大型对话”艺术。
库切对自己的作品所秉持的一贯态度就是不做任何评价,不回答他人对作品的各种疑问,却在《夏日》这部多声部“复调小说”中,通过虚构的“传记作者”文森特与几位受访者的对话,对小说作家以及创作过程“评头论足”。作品中众多声音和意识是独立自主、脱离了作者而自成一体的,他们平等地各抒己见,从而构成了多声部曲调的合奏,在内容上形成了“微型对话”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