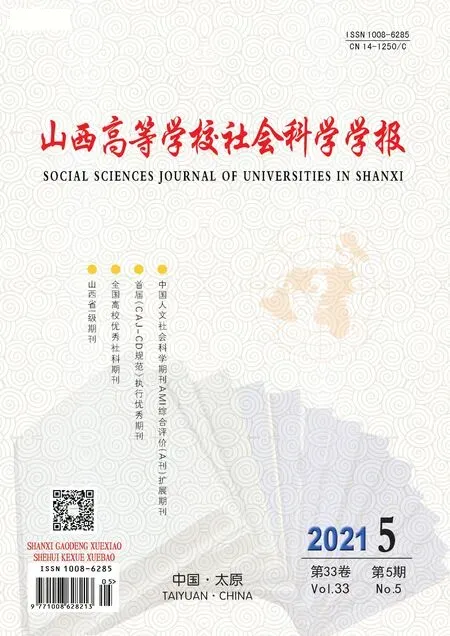王阳明“立圣人之志”的现象学探究
2021-02-13陈清春蒋丽英
陈清春,蒋丽英
(山西大学 哲学社会学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志”之概念在儒家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通过对“志”之概念的字义探源及儒家之“志”的历史梳理,可以看出“志”蕴含着丰富的哲学含义。其中,“立志”作为为学成圣的重要工夫在儒家思想中传承已久,“立志成圣”作为儒家学者的最高追求,更是受到强调和重视。王阳明继承了儒家先贤的思想传统,将“立圣人之志”作为贯穿整个心学理论体系始终的一个重要观点,作为为学的第一环节和求学致道的最重要基础之一。本文采用胡塞尔和舍勒的现象学理论来分析王阳明“立圣人之志”的意识行为本质及其本体依据。
一、儒家之“志”的历史渊源
“志”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具有漫长的发展过程。从“志”的金文、篆书、楷书等字形上看,其上下结构中的下部一直是由“心”字旁组成,这表明“志”是心的一种活动。“志”字的上半部分有“止”“之”“士”三种字形,胡家祥教授据此指出,“志”的含义可训释为“心之所止”“心之所之”“志者士之心也”三种[1]。“止”有终止的含义,可以引申为停止、停留在一个东西、事情上;因而“心之所止”就可以看作是心停留在某个事物上,并以之为终点。“之”作为助词有“的”的意思,作为动词有“往”“至”的意思,作为代词则代指人、事,因而“心之所之”就是心趋向并想要达到的一定目标或事物。至于“士”,孟子认为“士”是“有恒心而无恒产”之人,士以“志”为事,所以“志”是士的一种人生目标。从先秦至宋明,“志”的含义有一定变化,但基本上是以上三种含义的延伸。
儒家重“志”传统由来久远。孔子思想中,“志”就已经包含了多种含义。《论语》中“盍各言尔志?”中的“志”是志向、目标的意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中的“志”不仅仅有志向的含义,还有作为意志主体的意思。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志”,并提出了“持志”思想和“夫志,气之帅也”“气壹则动志”的志气观。至荀子,他在《天论》中说:“若夫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生于今而志乎古,则是其在我者也。”将志与意合论,更加突出了“志”的主体意志含义。汉代学者在著述和注释先秦典籍时,将“志”作“心之所向”解。许慎的《说文解字》并没有收录“志”字,但他认为:“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从心从音。”可见“意”与“志”的含义非常相近。郑玄在注《礼记·学记》时,释“志”为“心意所趋向”,可见,“志”与“意”有着紧密联系。唐朝时期,孔颖达提出了“情志一也”的命题。他在《春秋左传正义》中说:“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宋明时期,儒家诸多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志”与“立志”作了一定解释,并将“立志”作为为学成圣的重要工夫。如张载认为“志于学”,可以有“胜其气与习”的作用;此外他还提出了“志公意私”的观点。在二程这里,他们认为“志立则有本”,并认为学者要志于大道,要以圣人自期。此外,他们还对“志”与“意”、“志”与“气”作了辨别,认为“志存意发”、“志”与“气”相互影响。至理学集大成的朱熹这里,他继承了“心之所之”的观点,并对“志”作了自己的阐发,认为“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2]232,又认为“志”的内容“只是直截要学尧舜”[2]280。同时他对张载的“志公意私”作了解释:“意又是志之经营往来底,是那志底脚。凡营为、谋度、往来,皆意也。”[2]232朱熹的弟子陈淳对“志”作了更加详细的解释:“志者,心之所之。之犹向也,谓心之正面全向那里去。……一直去求讨要,必得这个事物,便是志。若中间有作辍或退转底意,便不谓之志。志有趋向、期必之意。心趋向那里去,期料要恁地,决然必欲得之,便是志。”[3]即是说,“志”是“心”对事物或目标的一种趋向活动,且这种活动具有一定的持续性。
通过对“志”的字形字义探源及儒家之“志”的历史梳理,可以认为“志”的含义有以下三方面。首先,“志”从心,由心而出,是心之所向,从而属于心的一种追求活动,并且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色彩。其次,“志”作为“趋向那里”的追求活动,其活动对象在实际活动中表现为一种志向,即一定的目标。最后,“志”在儒家哲学中对成圣之道具有重要作用,要发挥“志”之作用,就要去做“立志”的工夫。
二、王阳明的“志”与“立志”的意识本质
王阳明时期,“心之所之”作为“志”的一般含义已经被当时的学者普遍接受,且“志”之含义切合王阳明的心学理论。由于阳明心学的简易性,他没有像朱熹那样对“志”进行详细的概念解释,而是直接采用其一般含义。王阳明在《大学问》中说:“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则志有定向,而无支离决裂、错杂纷纭之患矣。”[4]800即是说“志”这一追求活动的开展不是向外,而是在心上开展的,这符合“心之所之”的基本含义。又言:“人苟诚有求为圣人之志,则必思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安在。”[4]259这里的“志”就是志向、目标。他认为,人要以成圣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他还说:“晚得友于甘泉湛子,而后吾之志益坚,毅然若不可遏,则予之资于甘泉多矣。”[4]231“吾之志益坚”表明“志”这一活动是主体意志力的体现。此外,王阳明对于“志”的功夫含义特别重视。他说:“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所谓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4]57王阳明之前的大多数儒者仅仅将“立志”看作为学之初的“立定志向”,“立志”思想在他们的哲学体系中并没有占到一个重要位置。而王阳明将“立志”提到了为学之本的地位,将之作为为学成圣的最重要基础和贯穿整个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观点。
王阳明在“志”的基本含义之上,还对“志”进行了明确的分类。他说:“昔人论士之所志,大约有三:道德、功名、富贵。”[4]1664人的一生中有各种追求,追求的具体内容不同,“志”就不同,世人所求志向主要包括道德、功名、富贵三种。在这三种志向中,王阳明选择道德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和实践所在,即“立圣人之志”。此外他还说:“但近世所谓道德,功名而已;所谓功名,富贵而已。”[4]161近世以道德为志的人实际上是求功名之志,以功名为志的人实际上是求富贵之志;这就意味着“志”有主观理想和客观现实之分。近世多数人虽然主观上的理想之志是道德,在客观现实生活中却是追求功名利禄之志。就王阳明本人的经历来说,他从小“立志做圣贤”,做圣贤之志就是他的理想志向,在现实中他也是以圣人之志作为自己的真实目标。但他自己也说:“我今与世间讲学,固以道德设教,是与人同善不容已之心,我亦未能实有诸己。一念不谨,还有流入富贵时候。”[4]1664“道德设教”即是主观理想志向,“一念不谨,还有流入富贵时候”则表明他的客观现实志向有时还会有富贵之念。
在王阳明的心学理论中,他不仅吸收了前人对“志”的概念规定,还进一步对它进行了本质上的解释,这种解释中蕴含着现象学理论。首先他揭示了“志”作为一种心之活动的实质——“心之所发即是意”。“心”所发出的一切活动都是一种意识活动,而“志”既然是由心而发的一种追求,那么这种追求就是一种意识活动。对于意识活动,王阳明还指出了其根本性质——“意之所在便是物”。意识活动以“物”来呈现自己,即是说意识活动都有自己的活动对象——“物”;而“志”作为一种意识活动就有了自己的意识活动对象,这个对象就是“志”所追求的目标。王阳明所揭示的“意”与“物”之间的关系就是现象学中的意向性,即所有的意识活动都是“关于某物的意识活动”[5]251。“关于某物的意识”就是意识指向并构造某物。也就是说,某物是由意向行为所意指和构造的意向对象或意向相关项。从意向性来看,王阳明不仅仅和前人一样将“心之所之”作为“志”的基本含义,还对其性质作了深入揭示,即“志”不仅仅是一种意识活动,这个意识活动还指向并构造了自己的对象——“志向”或目标。
“意向性”这一性质是所有的意识活动都具有的,“志”所属的意识活动也不例外。但是“志”属于哪一种意识活动?王阳明并没有给出具体答案。杨国荣先生在分析王阳明的“志”时说:“王阳明所说的志,首先是指专一的志向与行为的坚毅性,这二层含义大体上属于意志的品格。”[6]但通过上文对“志”的字义分析可以看出,“志”是一种对志向的趋向、追求活动。此时并没有对志向进行选择和实践,何谈志向之专一与行为之坚毅,所以不能将之笼统地看作是一种意志活动。依现象学的理论来看,人的意识活动纷繁复杂,包括感知、感受、想象、意欲、意愿、意志等种种意识行为。在所有的意识活动中,首先与“志”相符合的是意欲行为。舍勒认为:“意欲是一个追求,一个内容在这个追求中作为须要实现的内容而被给予。”[7]150王阳明的“志”是一个追求,且“志”的对象——人生目标,作为需要实现的内容是“志”这个意识行为所给予的,所以“志”首先是一种意欲行为。意欲行为是一种被动生成行为,其对象实质上是一种图像。但是“志”有目标的含义,目标即是人主观去欲求的一种观念,如王阳明的圣人之志就是一个具体的观念目标,不是一种图像。这就意味着“志”不仅仅停留在意欲行为阶段,而是进入了意愿行为阶段。意愿是意欲以观念的形式表现在主观意识中,即是说意欲进入人的主观意识之后进行了一种观念化处理,其对象由价值图像转变成了价值观念,意欲也就变为了意愿。所以说,王阳明的“志”作为一种追求首先是一种意欲行为。当这种追求的内容具有主观观念化的形式之后,即表现为观念化的目标时,就是一种意愿行为了。
“立志”从字面意思看就是立下或者选择“志”。“志”的内容不同,所表现的人生目标或志向也不同,所以“立志”就是对不同的目标进行一个选择,这与在意欲和意愿阶段的“志”明显不同。王阳明认为世人的志向主要有道德、功名、富贵三种。在这三种志向中,王阳明认为志于功名与富贵都是“一有谋计之心,亦功利耳”[4]161,是出自现实的功利主义欲求,不是人生真正的志向;“道德之志”才是他认为的真正人生志向,而“道德之志”即是儒家所追求的“圣人之志”。
据《传习录》记载,何廷仁、黄正之、李侯璧、汝中、德洪侍坐,先生顾而言曰:“汝辈学问不得长进,只是未立志。”侯璧起而对曰:“珙亦愿立志。”先生曰:“难说不立,未是必为圣人之志耳。”[4]104“未是必为圣人之志耳”表明:“志”不仅包括“圣人之志”,还有功名、富贵等志向,但只有“圣人之志”是人生真正的志向,因而“立志”也应当是“立圣人之志”。由此看出,王阳明的“立志”立的是“圣人之志”,他对“志”的内容进行了一种抉择,在各种志向中选定了“圣人之志”作为真正的“志”。在王阳明的思想中,“立志”不仅仅是一种对人生目标的选择行为,更是一种实现选择目的的实践行为。他在《示弟立志说》中说道:“盖终身问学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4]259即是说,一切为圣贤之学的实践工夫都是为了实现“圣人之志”。他还经常把“立志”的选择和实践志向阶段比喻为种树的过程:“立志用功,如种树然……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4]13“种树”有“种根”和“栽培灌溉”两个阶段,“种根”即是选择“圣人之志”,“栽培灌溉”即是对“圣人之志”的实践工夫。
王阳明的“立圣人之志”行为可以看作是一种追求,但其中还有选择人生目标和实现人生目标的实践含义,就不是意欲和意愿了。这种将意愿或动机抉择为实践目的并通过实践活动使之得以实现的意识行为是意志行为,它所构成的意向对象就是作为实践目的的未来的、有待实现的观念价值[8]。也就是说,意志行为包括实践目的的选择和实践目的的实现两个过程。王阳明在众多志向中选择“圣人之志”是意志行为的目的选择过程,对实现“圣人之志”的实践是意志行为的目的实现过程,所以王阳明的“立圣人之志”最终是一种意志行为。
三、“立圣人之志”的本体依据
人的意识中除了意欲、意愿、意志三种意识行为之外,还有感知、感受、想象、回忆、判断、推理等种种意识行为。现象学的开创者胡塞尔将所有的意识行为划分为客体化行为和非客体化行为两类,而客体化行为为非客体化行为奠基。这些意识行为中只有感知是客体化行为,其他意识行为都属于非客体化行为。也就是说,其他的意识行为都奠基在感知之上,其意向对象都以感知构造的对象为基础。胡塞尔还认为:“感知是存在意识,是关于存在着的对象的意识,并且是关于现在存在着的……这里存在着的对象的意识。”[5]502这里是说感知指向和构造的对象是存在意义上的对象。不同于胡塞尔对感知、感受的划分,舍勒认为:“感受活动原初地指向一种特有的对象,这便是‘价值’。”[7]313感受行为的原初性在舍勒那里又被认定为:“感受活动自身原本就是一个‘客体化的行为’,它不需要任何表象为中介。”[7]315就是说在舍勒这里,感受与感知一样都是客体化行为,都为其他意识行为奠基,而且感受行为与感知行为是互相独立的,只是感知行为的对象是存在,感受行为的对象是价值。对于意欲与感受的关系,舍勒说:“只要有一个追求(在这个阶段的追求),就会有一个对其目标内容价值组元的感受在为它奠基。”[7]44意欲作为一个追求奠基在感受行为之上,并以感受行为的内容为自身内容的基础。
王阳明的心学观点与舍勒的感受现象学观点相类似。他说:“见孺子之入井,必有恻隐之理,是恻隐之理果在于孺子之身欤,抑在于吾心之良知欤?”[4]44恻隐之心这种感受行为的指向和构造对象是恻隐之理,恻隐之理不依赖于作为感知对象的孺子之身,而是依赖于恻隐之心。所以在王阳明这里,感受行为同样独立于感知行为,而感受行为与感知行为一样也都为其他意识行为奠基。所以,“志”作为意欲行为和意欲观念化之后的意愿行为奠基在感知与感受行为之上,“立志”作为对“志”的内容进行选择和实践的意志行为,同样是奠基在感知与感受行为之上的。由于感知行为构造的对象是存在,感受行为构造的对象是价值,所以感知为“志”与“立志”活动提供了基本客观环境和必要客观条件,感受为“志”与“立志”提供具体价值指向。总之,王阳明所说的“志”,如富贵、功名、道德三种志向都是不同价值的体现,“立志”在表面上看是选择和实践自己的人生志向,实质上是选择和实践自己所选定的价值目标。
在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中,与感知、感受行为的奠基性地位相对应的概念就是心之本体——良知。王阳明在其理论后期提出“致良知”之后,他就将心学的本体依据确认为“良知”。他认为“意之本体便是知”。而本体的“知”既是“知善知恶是良知”,具有创造价值的作用;又是“良知是造化的精灵”,具有创造存在的作用。这就表明“知”作为一切意识行为的根本,既是感受行为,又是感知行为,并为其他的意识行为进行奠基。“志”与“立志”是心之所发,而“良知”是心之本体,所以“良知”就是“圣人之志”能够立得起来的本体根据。也就是说,王阳明的“立圣人之志”这一意志行为是依据“良知”在道德、功名、富贵这三种主要志向中选择并实践道德之志、圣人之志,他因此提出了“心之良知之谓圣”的命题。
由上述可知,“圣人之志”之所以立得起来的根本所在是“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良知。但良知具体怎样立得“圣人之志”呢?王阳明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他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4]111在四句教中他又说:“知善知恶是良知。”是非、好恶、善恶皆是价值的指称,良知知善恶,是个是非之心,即表明良知先天地能够对万事万物进行一种“知善恶辨是非”的价值判断,从而对万事万物的价值秩序进行规定。对此,王阳明举例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4]6即是说见到父亲、见到兄长、见到孺子入井之后,人依据良知的价值判断和价值秩序便能自然而然地知孝义、知敬爱、知恻隐同情,从而行孝义、为恭敬、救孺子。
因为良知能够“知善恶辨是非”,所以王阳明对“志”进行了价值判断和秩序的排列。他说:“昔人论士之所志,大约有三:道德、功名、富贵。圣学不明,道德之风邈矣。”又言:“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谓道德,功名而已;所谓功名,富贵而已。”[4]161这就表明,这三种志向中道德的价值是最高的,功名的价值次之,富贵的价值最低。而当人面对这些志向时,依据良知便可以选择其中的最高价值——“圣人之志”。王阳明的“立圣人之志”不仅仅是选择“圣人之志”,还要对此进行实践,而实践的依据依旧是良知。他说:“学者既立有必为圣人之志,只消就自己良知明觉处朴实头致了去,自然循循日有所至。”[4]196良知是每个人成圣的内在根据,人人都能够选择圣人之志,只要在良知呈现发觉处,时时处处致良知以实践圣人之志,便可立得圣人之志,最后成就圣人。
在王阳明这里,良知作为心之本体有“知善恶辨是非”的价值判断和价值秩序。这种判断和秩序在舍勒那里同样具有,而且更加详细,他将之表述为“偏好法则”和先天价值秩序。舍勒认为,一切价值都分为肯定(更高)的价值和否定(更低)的价值,如善与恶、美与丑等;这种“更高”的价值在“偏好”中被给予,而“更低”的价值在“偏恶”中被给予。依据“偏好法则”,舍勒又将价值样式划分为感性价值、生命价值、精神价值、神圣价值四个层级的秩序,感性价值最低,神圣价值最高,而且这个秩序就是绝对不变的先天秩序。但是由于他的感性与理性、心与物的二元论前设和神学前设,对精神价值和神圣价值的划分存在一定问题。因此笔者依据价值感受的实事考察,将价值样式区分为感官价值、身体价值(生命价值)、心理价值、精神价值四个类型,并将与之相应的感受活动区分为感官感受、身体感受(生命感受)、心理感受、精神感受四个阶段;这四种价值类型从低到高的顺序同样就是先天价值秩序。这种划分避免了舍勒的两个错误前提,从而能更加合理地解释王阳明的理论。舍勒的“偏好法则”和先天价值秩序与王阳明“良知”的“知善恶辨是非”具有一定的相通之处:是、善就是肯定价值和更高的价值;非、恶就是否定价值和更低的价值;知、辨就是对价值进行高低的判断,并表现为先天价值秩序。所以,王阳明的“立圣人之志”的本体依据——“心之良知是谓圣”,用现象学来解释的话,就是“立志”这一意志行为依据作为感受行为的良知中的“偏好法则”和先天价值秩序,指向并实现圣人之志所代表的最高价值的过程及成就圣人的结果。在儒家的价值论中,向来以成就圣贤人格为最高价值。自孔子始就以成就圣人为最高志向,并且在各种价值中,偏好高的价值,偏恶低的价值,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义利之辨。王阳明传承了儒家传统,反对功利主义和私欲,毕生追求最高的精神价值,因而在各种现实志向中特别强调要“立圣人之志”,甚至将此看作为学的第一环节。
四、结语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志”可以看作意识行为主体对于人生目标的欲求,“立志”就是选择具体的人生目标并开展对于这一目标的实践趋归。在王阳明心学体系中,“立志成圣”是贯穿王阳明一生的根本问题和终极追求。通览王阳明的为学历程便可知,“立志”乃是他终生强调而无有变化者。结合现象学的角度分析王阳明的“立圣人之志”,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其意识行为本质和本体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