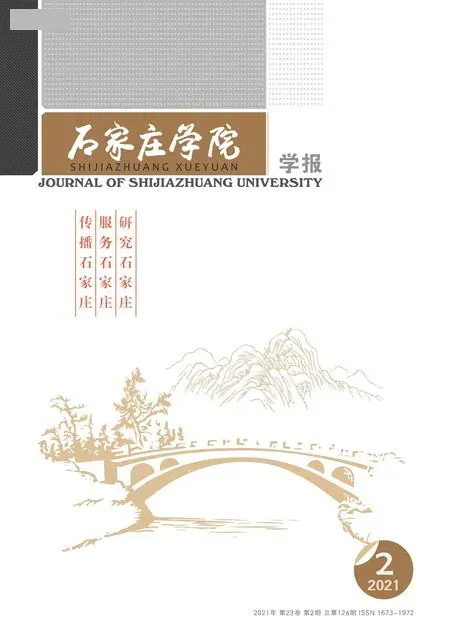“物转向”背景下当代小说物叙事研究现状及新路
2021-02-13张细珍
张细珍
(江西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330013)
“人类”一词,是一种叫智人的动物以自我为中心建构起来的超级神话。在人类中心主义这个大神话思维下,所谓的人类文明、新兴科技都是一种人为的设计,或次生神话。戴锦华在2020年7月17日“人类之维”的网络讲座上说,从空中看地球,地球是一个整体;但从地上看地球,地球到处是壕沟、壁垒、墙。在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人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已经为时太晚了,自然不需要被拯救,需要被拯救的是人类自己,是人性。2020年,新技术神话面对看不见的新冠病毒束手无策,溃不成军的人类如何结成命运共同体?在这样的疑惑下,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物本位的物叙事,可谓面对危机的一种努力。
物,包罗万象,涵盖有形无形。《说文解字》注:“物,万物也。”[1]30《荀子·正名》则视物为万物的大共名。《庄子》曰:“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2]503在此,“物”特指除人之外的世界万物,包括动物、植物、矿物、食物、器物、衣物、风景、地理、生态、科技等。“小说物叙事”特指关于物或以物为主体的虚构叙事。近年,在西方“物转向”思潮推动下,物与物叙事研究成为国内外前沿热点。由此,本文希望通过梳理物叙事研究兴起的背景、现状,探索当代中国小说物叙事研究的本土新路径,以期与西方对话。
一、作为学术背景的“物转向”
当前,继“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之后,国内外人文研究呈现“物转向”的新趋势,物研究成为一个新兴的热点。它兴起的背景是“后人文主义”“去人类中心主义”影响下的“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3]7,即打破人类中心论与本质主义偏见,回到物本身,相信物自体的存在,承认物的力量,追寻物的本真,旨归于人/物平等,实现物的生态主义。
20世纪的西方,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较早研究物。他认为,人与物本是无所取用的一体关系,但技术理性的膨胀使人把物对象化、客体化、资源化。21世纪,推动“物转向”的重要力量是近10年来兴起的哲学流派“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代表人物包括昆丁·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雷伊·布雷西亚(Ray Brassier),二者持“消灭论”(eliminativism)立场,旨在想象无人的真实世界,认为物的存在前提是偶然性和非理性。此外,格拉汉姆·哈曼(Graham Harman)、列维·布赖恩特(Levi R.Bryant)则重点描述物的运作、物与物的互动关系。他们立场各异,但核心观点相同,即:相信物自体的存在,相信物自体虽然理性无法企及,却是可以想象的。“思辨实在论”引发“物转向”思潮,国外物理论研究呈现不同的态势,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突显“物”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格拉汉姆·哈曼突显“物”的本体实在性,伊丽莎白·格罗兹(Elizabeth Grosz)突显身体的“物质性”,比尔·布朗(Bill Brown)突显“物无意识”(material un-conscious)的“物”理论,等等。[4]
近些年,“物转向”思潮波及中国,国内学者从不同视域出发研究“物转向”。《多领域中的物转向及其本质》①参见杨庆峰、闫宏秀《多领域中的物转向及其本质》,载《哲学分析》2011年第1期。认为,“物转向”是当前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动向。伦理学中的“物伦理学”、符号学中的物体语义学、分析哲学语境中的人工物研究等都是这一动向的展现。但是,物转向的实质却不相同。在科学技术哲学中,物转向意味着其摆脱先验研究路向,关注经验研究;在伦理学中,物转向意味着其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关注物的伦理性;在生存哲学中,物转向意味着开始摆脱理性传统,关注身体研究;在现象学中,物转向意味着摆脱先验意识,关注语境。物转向可以看作是对传统语言学转向的回应。《物转向》②参见汪民安《物转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3期。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直接后果是人和物越来越尖锐的对抗,为了克服这种主体中心主义原则,海德格尔后期提出了天地人神共存嬉戏的观点,而它们正是在物中统一起来的。受海德格尔的影响,拉图尔提出了准客体概念。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各种分离要素也正是统一在这个准客体中而发生总体性关系的。但是,最新的思辨实在论潮流则反对这种关系论,他们意图将物独立出来,认为物可以脱离主体而存在,认为物有自己的本体论。《西方文论关键词:物转向》③参见韩启群《西方文论关键词:物转向》,载《外国文学》2017年第6期。认为,物的话语内涵在当下语境中的演变及拓展构成了当前很多学科领域“物转向”的核心推力。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们从“物转向”话语中汲取丰富的理论滋养,推动了文学批评领域的“物转向”,并逐渐形成具有独特研究旨趣与范式的“物转向”批评话语。该文主要从西方哲学社科领域“物转向”研究起源与概念假设入手,重点探寻当代西方文学批评领域“物转向”擢升衍进的话语背景,并通过梳理新世纪以来西方学者的文学研究实践,归纳“物转向”批评话语的主要议题与路径、研究范式与特点,思考“物转向”批评话语如何有效拓展与塑造当代西方文学研究空间,以期为国内同行及同类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此外,还有论者从物转向视域出发,研究机器人伦理学的发展。
关于“物”,中国传统哲学早有相关论述。儒道等哲学流派从天地万物的宏大视域出发,在心/物、道/物、人/物关系中洞晓物义。张岱年认为,心/物问题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汤一介指出,心性物关系模式是儒家心性学说的基本框架。陈鼓应认为,老子首创的“道与物”理论框架,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本原论、生成论,形成本体论雏形,对庄子、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影响深远,构成中国哲学史的一条主线。在人/物关系上,钱穆认为,儒墨均重人轻物,至庄子始,人物并重、物我齐一。天地一气、万物一体、未始有物成为庄子宇宙论的基点。
庄子“物”概念包含正反两个向度的意义:第一,“乘物游心”的“物”,是道、性的体现,具有自然而然的无为性,人应顺物自然;第二,“物不胜天”的“物”,指物/天、物/性对立意义上的有为,人应不为物役。庄子“物”理念沿着“齐物—逍遥游—物化—混沌”的思路演进,即以天地万物之一体的“齐物”论为价值前提,通过心斋坐忘,进入物我合一、自然自由、游乎天地一气的“逍遥游”,旨归于独化之真、同于大道的物化之境,最后道通为一、归于未始有物的“混沌”,实现以天合天、以物观物、顺物自然、即物即真的东方生命美学。牟宗三认为,庄子冲破二分法,平是非,齐万物,抵达方生方死的物化之境。齐物论,无物不然、无物不可,体现了超越的绝对立场,是体现天理良知的普世价值。以庄子为发端,程颢、王阳明等人提出了“万物与我为一”“与物同体”和“心外无物”等观点。
若说西方物论基于人/物二分,为反人类中心主义而转向物本位,以求恢复人与物的再度和谐;那庄子物论则是秉持齐物思维,旨归于人/物一体的原始和谐,以实现物我合一的生命境界。人/物的对立与齐一,是中西物论的不同之处,也是对话的节点。由此,笔者认为,在近年“物转向”的学术背景下,以庄子物论为参照研究当代中国的物叙事,或许可以与西方的物叙事研究对话。
二、物质文化研究
在“物转向”的背景下,国内较早译介国外物质文化研究的成果有孟悦、罗钢主编的《物质文化读本》④参见孟悦、罗钢主编《物质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该书从消费和商品、礼物和互惠性、流通、技术发展等方面研究物质文化。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启示是围绕商品与非商品之区别的讨论,这实则是马克思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争论点之一。前者探讨商品、生产方式、价值、异化、消费、深层结构和上层结构的关系,认为“商品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物质文化的梦想逻辑和享乐逻辑的体现;后者关注的则是礼物、交换、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通、身份、互惠性、不同文化间的关系,认为物质商品生命的终结之后,会开始文化和社会生命。马克思主义侧重研究物质的商品价值,后殖民主义则延长物质的时间维度,研究其“去商品化”以及衍生社会文化生命的过程,要“为物质作传”。后殖民主义物质文化研究还从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权利关系的角度,探讨“物恋”背后主体/他者间的跨文化根源。把文化间权利关系带入物质文化研究,为非西方文化或本土文化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此外,物质文化与技术的关系是近十年来物质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因为技术发展挑战物的观念,甚至造成人物不分、界限模糊,如生物机器、全球脑、智能人等。研究者提出疑问:人的物化、物的人化、人/物混杂的描述所反映的,究竟是人的危机,还是人的未来?
值得一提的是,此书主编孟悦的序言《什么是“物”及其文化?——关于物质文化的断想》对国外物质文化研究进行了学术梳理。它从考古学、人类学到民俗学,从社会人类学到结构主义人类学,从殖民主义到后殖民主义,梳理西方物质文化研究的脉络:考察文物、部落生活的他者性与帝国的不平等关系;提出被看的“物”以“他者性”的批评眼光回视、教育解读者;关注“物”作为礼物的互惠性,作为商品的“强迫消费性”;等等。作者尝试厘清意义无法自明的物质文化的概念:既重合又溢出于商品文化。在此基础上,将问题由“什么是物质文化中的物质”变为“什么文化”“改变了物质”,进而提出物质作为符号或语言,本身具有类似文字、象征、叙事、历史的性质。该序言在与西方学者对话过程中,呈现了中国学者关于物研究的重要思考。
不仅国内学者译介国外物质文化研究成果,国外学者也研究中国物质文化,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开放的艺术史丛书”。该丛书囊括了中英美多位学者关于中国画像、美术、墓葬、书法、青铜器纹饰、图形文字、图像铭文、风景园林等著作。英国牛津大学学者柯律格(Craig Clunas)的专著《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①参见[英]柯律格著《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高昕单、陈恒译,洪再新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以明代文震亨《长物志》一书为例,从物品视角切入艺术史,同时也跨越学科界限,参照社会文化理论,讨论明代绘画、书法等“多余之物”在明代社会生活中的意涵,考察它们如何被鉴赏、使用、成为消费品以及怎样流通,是一部有关晚明文化消费的重要著作。柯律格的系列著作还有《大明帝国:明代的物质文化与视觉文化》等。另外,德国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教授的《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也是有影响力的成果。
若说国外学者研究中国物质文化能带来他者的陌生化视角,那国内学者的中国物质文化研究则是身处其中的感同身受。近年来,叶舒宪主持文学人类学专题“神话中国”,以物研究重建失落的历史世界,推动当代人文学科的人类学转向。他认为,神话不应该下属文学,而应是统领文史哲等一切人文学科。神话思维支配所有文化传统的原编码,包括文字出现之前的一级编码,如图像叙事和物叙事。他主持“玉成中国”丛书,以文学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作为显圣物的玉石。此外,他还研究史前动物形酒器的萨满致幻意义、彩陶鱼纹、熊图腾、蛇神话、玄鸟、蛙人、虎文化、戈文化等。此外,孙机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扬之水的《物中看画》等也是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
除了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当代物质消费文化、商品拜物教也是目前国内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陶东风、周宪主编的《文化研究》就当下诸多物质文化现象展开了专题讨论。其中24辑、36辑发表系列物质文化研究论文,话题涉及当下诸多物质文化现象:手机与日常生活的变迁、交通工具的变迁、墨镜折射的技术狂想中的主体焦虑、消费时代特产的再地方化与诗性资本化、网购背后从物欲症到物控症的病理逻辑、旅外游记中博物馆书写的身份意识、咖啡与茶背后中英民族认同、汉服审美中的情感体验。“物·人·世界——‘物质文化与当代日常生活变迁’”会议②此次会议由2015年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学科、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文艺研究杂志社联合主办。围绕物质文化理论、新媒体与当代社会、空间与文化、消费意识形态研究、物与日常生活、文艺作品中的物质呈现六个议题展开讨论。该会议取得如下重要成果:对物质文化和现代社会构建问题的探讨,对技术社会的批判,对消费社会的美学批判,对日常生活器物的研究,对艺术与物性的关系以及艺术中器物的研究。其中,陶东风归纳了物的三种形态:一是物的自然形态;二是人工制品,它构成公共空间的物质基础,也是人能够从事公共领域的政治实践的条件;三是消费社会的商品。他认为,物的意义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环境中不断变化。对“物”展开文化研究,能让我们对当代文化与日常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更深入的思考,从而拓展文艺理论的学术视野。周志强强调,走向“拜物”,即按照物的逻辑理解人的社会,是不提倡的。人类所追求的抽象的、神圣的价值观一旦全部以物质衡量,则会出现那些所谓的物化的、合理化的世界。由此,他发掘出奢侈品和私通机制、违禁快乐的共通之处。他提出“物”的五张面孔:人的生活本身、生活经验的创生者、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所说的吊诡的欲望符号、人的异化、现代社会的异托邦,认为文化研究关注物质如何构造、影响人的日常生活,最终如何以意识的、文化的形式构成了人的生存。汪民安论述了垃圾与商品相互转化的过程,工业城市对垃圾的驱逐与遮蔽,尤其是关注到那些和垃圾一样被漠视的拾垃圾者。此外,汪民安的《论家用电器》①参见汪民安《论家用电器》,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将家用电器作为传记的对象,探讨了洗衣机、电冰箱、手机、电视机等电器在家庭生活中所展现的空间权力结构。他重新审视物我关系,书写新的物的生和死的传记,而不是人的传记、观念的传记。
三、物叙事研究
中国物叙事研究方面,傅修延的《物感与“万物自生听”》②参见傅修延《物感与“万物自生听”》,载《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一文联系5G时代万物互联的前沿话题,基于中国人/物无差别的齐物思维,从听觉角度赋予传统物感命题以新的美学阐释,开拓了中国物叙事研究的新空间。他认为,人也是万物之一,物虽然为人所用,但物也作用于人。中国古代文学有一个以物见人的叙事传统,这一传统主要表现为:讲述人的故事时往往把物也卷入其中——通过描写那些与人相随相伴之物,达到衬人、代人、名人、助人和强人的目的。古代文论中的物感,指人作为万物之一与他物之间的沟通。感应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常以不限于耳根的“听”来指代,较之于其他感知,“听”可以让万物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彼此沟通。与感应相关的万物互联已成为时下流行话题,自然科学如今尚未强大到能够解释万物之间的一切感应,与感应问题关系紧密的人文学科应当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奉献出自己的认知与思考。傅修延的专著《中国叙事学》③参见傅修延《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立足文学小文本与文化大文本,回溯中国叙事传统,建构中国叙事学。他认为,中国叙事传统向来注重描写“物”,体现了“万物相互依存”的文化思想。该书从太阳神话开始,探寻中国的元叙事。它摆脱了西方你/我二元本质主义思维,从中国小我/大我整体主义的思维模式出发,论述《山海经》万物相互依存的原生态物叙事理念。器物篇将器物纳入叙事学范畴,从“纹/饰”“编/织”“空/满”“圆/方”“畏/悦”五对范畴出发,研究青铜器上的元叙事;从瓷与稻、《易》、玉、艺、china关系角度出发,考察镶嵌在社会文化意义网上的中国瓷,以追根溯源的方式重构中国形象。此外,扬之水的《诗经》物象、《金瓶梅》物色研究,都是古代文学物叙事个案研究的重要成果。
外国物叙事研究方面,唐伟胜2018年的国家社科基金“物叙事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研究”是目前国内较有代表的成果。作为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文化符号、主体性、实践性:论“物”的三种叙事功能》④参见尹晓霞、唐伟胜《文化符号、主体性、实在性:论“物”的三种叙事功能》,载《山东外语教学》2019年第2期。一文详细回顾了哲学领域的“物转向”及其对文学研究的启示,界定“物叙事”概念:既指那些有“物”参与其中的叙事,也指那些以“物”为主要再现对象的叙事。他提出“物”在文学叙事中可能承担三种叙事功能:一是作为文化符号,映射或影响人类文化;二是作为具有主体性的行动者,作用于人物的行动,并推动叙事进程;三是作为本体存在,超越人类语言和文化的表征,显示“本体的物性”。关于第三点,笔者认为,文学叙事中的物说到底是一种符号建构,其本体物性的显示是作家意识的呈现,无法超越人类语言和文化的表征。《使石头具有石头性——“物”与陌生化叙事理论的拓展》⑤参见唐伟胜《使石头具有石头性——“物”与陌生化叙事理论的拓展》,载《思想战线》2019年第6期。一文则从物理论作为反思其他叙事理论(如陌生化理论)的角度,认为“物转向”给文学叙事理论和批评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如物叙事与性别、种族、环境、历史、全球化书写之间的互动关系;物叙事与中国本土学术资源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从本土的道家传统中汲取营养。尤其是中国哲学思想里也蕴含了丰富的“物”思想,比如道家强调“物各有性”,也就是说,“物”有自己的本性和功能,人与“物”是平等的,没有本体级差,由此可以挖掘古代经典作品中“物”的叙事功能和文化含义,并联系哲学传统中的“物”思想,用中国视角来夯实“物”叙事研究的理论基础,并将中国文学文化传统带入当代国际学术前沿对话中。
在上述学术背景与思想的启发下,笔者认为,立足中国的物理论,从庄子物论视域出发研究当代中国小说的物叙事,或许可以发掘中国文学物叙事的本土经验与问题,从而既与国外物叙事研究对话,又为如何立足本土经验讲好中国故事提供理论启示。那么,目前关于当代中国小说物叙事研究的现状如何呢?
四、当代中国小说的物叙事研究
早在1988年,就有学者研究动物小说中人拟兽化、兽拟人化的原型意象以及万物有灵、动物崇拜的原型情感。近年,研究者热衷研究莫言小说的动物叙事,如陈思和认为,《生死疲劳》“用两条生命链建构起西门家族的兴衰史,轮回隐喻的生命链连接了畜的世界、阴司地府;血缘延续的生命链连接了人的世界、人世间的社会”,两条生命链的结合,使叙事体现出人畜混杂、阴阳并存的结构特色。[5]不少论者从陌生化角度研究莫言小说的动物叙事,笔者觉得还可从听觉叙事角度研究《生死疲劳》如何通过六道轮回中动物的声音,恢复感觉的天真,实现声音的民主。小说将人与兽、视与听的关系错置互换,呈现异样的生命图景与音景。莫言通过动物的声音打通视听的壁垒,通过感觉的挪移赋予动物声音以政治性的解构功能与荒诞的美学色彩。
近年,从生态主义、儿童文学角度解读小说中的动植物、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成为热点。其中,从生态主义角度考量迟子建、阿来小说的自然书写、动植物叙事是一个聚焦点。吴义勤从狗道与人道角度,阐析迟子建《穿越云层的晴朗》中毁灭的诗意、凄楚的美感以及对“残酷美学”的深度揭示。[6]也有论者跳出生态主义人与动物二元对立的预设态度,从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的“生成—动物”视角出发,解读迟子建笔下人与动物互相“生成”的温情混沌关系,以及共同的越界、逃逸乃至游牧,从而反衬人与人的对立,开拓人性反思的维度。[7]有论者从阿来“山珍三部”中的“虫草”“松茸”“岷江柏”出发,研究他如何巧妙地借助藏区的奇珍之“眼”,将浓郁的康藏文化风情与当今社会物利交易、欲望泛滥等普遍社会现象全面铺排,镜像出历史发展的蜕裂之痛。[8]或从生态主义角度出发,从现实环境的破坏、传统文化习俗的失落以及神性与人性的双重消弭等方面入手,讨论阿来、迟子建笔下的“空山”“空林”、古老村落、部落的固有秩序所受到的毁灭性打击,从中折射传统文化的当代命运。[9]汪树东的专著《天人合一与中国当代文学》①参见汪树东《天人合一与中国当代文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从生态批判、动物叙事、生态人格与理想、生态诗学建构的角度阐析当代生态文学。《中国当代动物叙事的类型学研究》②参见陈佳冀《中国当代动物叙事的类型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则将当代动物叙事作为一个叙事学意义上的类型进行整体考察,包含概念诠释、伦理资源、叙事传承、类型衍生、功能形态、深层结构、基本叙述模式以及神话根源等多个层面。
衣食为本,饮食现象是物叙事研究中一个有意思的角度。如《论莫言小说中的饮食现象》③参见张立群《论莫言小说中的饮食现象》,载《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6期。认为,莫言笔下的“饮食现象”在聚焦于“肉”“酒”“植物”三个基本意象的过程中,寄寓了作者本人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及相应的文化想象和叙述焦虑。服饰研究是物叙事研究中的另一个切入点。如有论文探究沦陷区上海女作家的服饰情结及所折射的生存状态,阐释服饰对作家创作产生的影响。衣食之外,日常生活中的住宅、日用也是研究者关注的新点。暗袭古典世情小说的传统,王安忆的上海书写离不了日常事物的细织密缀。有论文解读王安忆笔下人与物、人事与物事中蕴藏的人情、物理、事理、世情之真[10],或从技术政治化、器物历史化的思路,城市、建筑与怀旧叙事的悖反,家屋书写与认同构造等角度解读王安忆的《考工记》;从格物、恋物角度研读王安忆《天香》《长恨歌》中的绣品物件等。还有论文梳理孙犁土改小说中人/物关系,考察“物”的意识形态属性与批判反思功能[11];或解读莫言、迟子建小说中的“河流”意象。笔者就曾解读史铁生小说《务虚笔记》中的“葵林”“白色鸟”等物象或结构小说、或制造氛围、或突出主题、或预示人物命运等叙事功能。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小说物叙事多基于西方人/物二分立场的生态主义研究,且停留于作家作品的个案解读,而从庄子物我合一的物论出发,系统梳理新时期至今物叙事的成果尚无。由此,笔者认为,在庄子物论视域下考察当代小说物叙事,既能观照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自然生态、社会心态的变迁,又能提炼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展示其当代价值、世界意义,还可从中国本土经验出发参与物叙事研究的国际性对话。
那么,关于庄子与当代文学的关系,目前学界的研究现状又如何呢?
五、庄子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研究
作为优秀传统文化,庄子以精神基因的形式,通过影响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情调、人格、心态来影响中国文学创作。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年以来,学界一直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承。百年新文学与道家文化的关系,一直被关注。杨义的《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①参见杨义《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探究受外来思潮冲击的20世纪中国文化和文学中的道家文化在中西文化冲突中调适与融合的活性,以及在现代生活和现代文学进程中的价值。研究者还从悲剧意识、母性崇拜、自然精神、逍遥美、诗化美、畸人真人形象、个人主义、反异化等角度探析道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联。
作为道家的领军人物,庄子代表了中国本土最古老的文化精神,其逍遥游的美学、汪洋恣肆的文风与五四浪漫主义思潮呼应,一度引起学界的关注。现代中国文学自觉的几个时期,如五四文学与新时期文学自觉既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也与庄子有内在的关联。关于现当代文学与庄子的关系,学界也有关注。樊星的《当代文学与庄子》②参见樊星《当代文学与庄子》,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指出了极左思潮下庄子思想作为消解政治狂热、抵御政治暴力的解毒剂回归的必然性。该文将新时期庄子思想的重新流行看作极左思潮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表征,描述了庄子的思想与文体对当代作家汪曾祺、王蒙、马原、顾城的复杂影响。刘剑梅的《庄子的现代命运》③参见刘剑梅《庄子的现代命运》,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一书以庄子的现代命运为基本主题和内在逻辑,梳理庄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思想史上的命运变迁,展示其个体自由独立精神所遭遇的困境。作者超越文学而跨入大文化领城,涉及文史哲诸人文向度,涵盖的中国的作家、学者包括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沭若、林语堂、废名、关锋、刘小枫、汪曾棋、韩少功、阿城、阎连科等。不过,此书并未论及史铁生、莫言、王蒙等与庄子的关系,这是需要补充之处。陈世旭的《庄子艺术精神的当代价值》④参见陈世旭《庄子艺术精神的当代价值——传统美学与当代文学论列之三》,载《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从“至人,透彻的人生观念”“至乐,极度的心灵自由”“至美,态肆的艺术表现”三个方面探讨庄子艺术精神的当代价值。“现代作家对老庄的三种态度”⑤雷文学的“现代作家对老庄的三种态度”是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将现代作家对老庄的态度归结为三种——批判、继承和发展,特别强调了现代作家在基于现代生活的基础上,将老庄朴素、超然、无目的性的哲学与积极进取的现代思想相结合,进行了现代人格的塑造。
个案研究上,《〈棋王〉与道家美学》⑥参见苏丁、仲呈祥《〈棋王〉与道家美学》,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3期。较早从大智若愚的王一生、大巧若拙的白描技法方面阐述阿城《棋王》中的道家美学。孙郁的《鲁迅对庄子的另类叙述》⑦参见孙郁《鲁迅对庄子的另类叙述》,载《文艺研究》2016年第3期。认为,鲁迅绕过传统士大夫以词章之学描述庄子的旧路,通过西方哲学来重新理解庄子,在作品里嘲笑道家思想面对现实问题时的尴尬。这种批判有着尼采的影子,也是对卢那察尔斯基文本的戏仿,背后是俄国诗学的余影。鲁迅批判道家思想、远离庄子的过程,也是告别浪漫主义诗学传统的过程。他把殉道感和搏击精神引入自己的世界,形成一种新的审美意识。张清华认为,莫言叙述体验中主客关系的融合,近似于古典美学传统中庄子“神与物游、物我合一”的一种境界。《红高粱》中铺排和夸张的叙述,只能在中国古典传统中、在庄子《逍遥游》类铺排式韵文中找到它的原型。[12]汪树东发现,迟子建小说中有浓郁的道家色彩。与道家的反智主义相关,迟子建喜欢塑造弱智者形象,借之表达人生理想。道家深谙祸福相倚之道,倡导安柔守雌。迟子建也强调“必要的丧失”,他还像道家一样主张返回自然、与物共情。道家思想使迟子建小说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13]此外,还有论者将沈从文、史铁生与庄子的生命哲学进行了比较,等等。如有论者认为沈从文早期的湘西小说之所以呈现出强烈的道家意蕴,实是源于湘西巫楚文化背景与道家的相通。认为他并非是在道家影响基础上去理解湘西,而是在自身承传的湘西巫楚文化及以此为基础建构起来的生命思想中去理解和吸纳道家文化的。至20世纪40年代,他则开始有意识地批判地吸纳道家因子,其重构之“神性”与庄子的“道”有着极大的共通性,体现在“心役于物”的现代性反思,美在自然的体道途径、至人无己的体道状态。[14]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多立足庄子哲学思想与生命诗学,研究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由此,立足庄子物论,从物叙事角度探析其与现当代文学的关系,既可激活庄子的当代价值、世界意义,还可发掘中国文学物叙事的本土经验,并与西方物叙事研究对话。
六、新路
以上学术背景与研究现状的梳理,目的在于探索当代中国小说物叙事研究的新思路。目前,国内学者既立足本土之物建构中国叙事学,又借西方物理论进行文学物叙事批评。用西方物理论研究中国文学物叙事,能提供陌生化的视角;用中国物理论研究中国物叙事,也能发现本土问题。细加辨析,东西方物叙事有不同的逻辑路径。西方物叙事的出发点是人/物二分,从人本位转向物本位,反人类中心主义,还原物的自性。叙事过程是通过无人/去人化零度写作,让物走出人类的控制,以物的方式说话,呈现自在的物性。叙事归宿点是物性自显,恢复物的主体性,借物叙事呈现并感受物的实在性、感性,通过感觉的陌生化,打开人的感觉边界,刷新人的感受力,进而恢复人与物的和谐。庄子物叙事的出发点是物我合一,从人本位转向物我一体。叙事过程是通过感物、物感,情随物迁,实现人的物化。归宿点是借物恢复生命的本真与感觉的天真,使万物自证自得、自在自为,人物齐一、通真通灵,实现物我泯合、物我两忘、即物即真的东方式混沌生命美学。尽管东西方物叙事出发点不同,但在恢复人/物平衡的归宿点上,二者呼应对话。
人类中心主义引发人/物关系的失衡,面对生态环境破坏、新冠病毒肆虐的现状,我们再来展望一下未来。21世纪的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使智人面临智能人、生化人的威胁。《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预测,人类可能进入后人类时代或超人类时代。新技术革命加大数据霸权,让一群智人成为结构性的弃民,智能人主宰智人。“美丽新世界”到来。过去,上帝被人造出来,又被人杀死了。将来,智能人被人造出来,反过来把人杀死?对此,笔者认为他过分夸大了科技力量,将人的物化与物的人化极端化。但人类中心主义的科技神话能引发人/物关系失衡的生态崩溃与破坏性创造的科技颠覆,却是极有可能的。面对数据霸权挤压人类中心这一新的议题,人类如何以自我反省的精神与讲故事的方式重建新的价值形态与未来愿景?
面对人物变成物人的命运危机,人类唯一自救的希望是否仍在于爱的能力?所有对他者之物的凝视,都是回望自我。看见物,才能看见自己。每一个“它”,都是“我”。庄子主张爱人利物,体现了万物皆一、圣人贵一的宇宙精神。利物便是爱人,人应摒弃人类中心主义话语霸权,超越人类第一人称视角局限,一物一世界、全息地包孕世界真相,借此实现审美救赎,恢复人/物平衡。正所谓与物同乐,最终返真者在人,如此建构绿色生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说到底,人,物也;物,亦物也。民胞物与、物我一体的齐物思维是中国物叙事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的独特贡献。
由此,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小说物叙事研究应立足古老中国的道家哲学智慧,从庄子物论出发,探究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作家如何从人本位转向万物一体,秉持爱人利物的叙事伦理,以万物皆一的宇宙精神书写自性自化的物伦理,通过全息的温情叙述进行物性自足的审美救赎,恢复人/物关系的平衡,建构绿色生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传统智慧与新兴科技的有效嫁接,以重塑新的世界观。这或许是中国物叙事与西方物叙事研究对话的一条新路径。该研究思路的理论价值在于,以庄子物论为支点,既探究当代文学物叙事的中国经验,又提炼优秀传统文化庄子的精神标识,呈现其当代价值、世界意义,为以中国方式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彰显文化自信提供理论支撑。现实意义在于,改革开放40多年来,商业化进程带来社会物欲心理由压抑、释放、膨胀到异化的变迁,而非典、新冠肺炎的蔓延则源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通过研究作家爱人利物的叙事伦理,反思近年自然生态、社会心态的失衡,为恢复人/物关系的平衡,建构绿色生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现实的经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