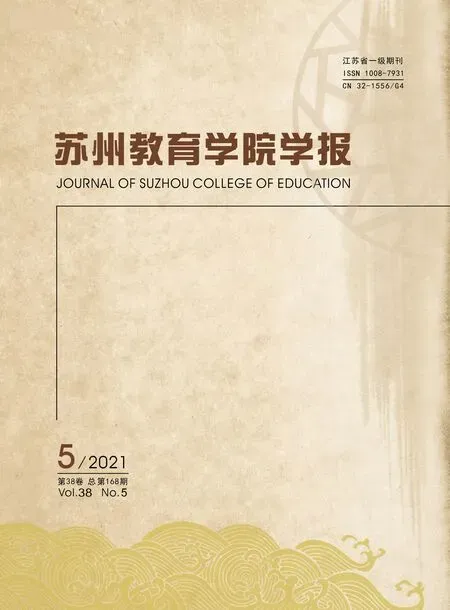镜,还是灯:金庸武侠小说中女性形象探究
2021-02-01余冰清
余冰清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武侠小说中的女性素来是英雄侠客柔情的寄托,装点了无数男性读者的武侠梦。金庸武侠小说对女性的描写更是令人叹为观止,深受读者喜爱。尽管如此,相较于男性人物在武侠小说中占据的重要地位而言,女性角色的定位显得暧昧不明,具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武侠小说作为通俗文学的一种类型,对人物形象的探究,应该立足于这一文类自身的特点。陈平原教授认为武侠小说的中心是“以武行侠”[1]76,由此可见“武”是手段,“侠”是目的;“侠”是驱使侠客行正义之事的道德感,“武”则是决定侠客行侠能否成功的能力。小说家一般认为“侠”的意义重于“武”[2]。“侠”的内涵相当丰富,可以分为“知”与“行”两个方面,如舍己为人、自尊自爱的思想觉悟;或是行惩恶扬善、守疆卫国等正义之举。一个侠客可以不具备高深的武功,但思想行为不能有违侠义之道。
当然,金庸小说中不乏如黄药师、谢烟客和杨过等特立独行的奇人异士,他们游走于正邪之间,无论是正还是邪,这些男性人物的行动和自身思想指向基本上是一致的。与之相反的是,哪怕是相当正面的女性形象,也总带有一种蒙昧的色彩。这不是因为她们的智慧与领导能力不如男性,而是由其自身价值观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的。如黄蓉和赵敏的智慧令男性敬佩甚至畏惧,但其人格是在被男主人公塑造之后才变得相对完整的。有学者认为这类女性是被男性带入正轨的曾经的“脱轨者”[3],事实上,她们的思想可能最终都没有步入“正轨”,即自发地渴望成为一名女侠,并自觉践行侠义之道。在《射雕英雄传》中,黄蓉为防泄密而欲杀傻姑,但因郭靖的一个眼神,她才没有滥杀无辜,并不是因为她心中有侠道,而是不忍违备郭靖善良的本性,此时的黄蓉还带有三分邪气。在《神雕侠侣》中,她尽管已经成为众人敬佩的女英雄,但其目光依旧聚焦于郭靖,心中满是说不尽的爱慕和眷恋。类似的还有赵敏,她为爱张无忌而背弃父兄,离家去国,由于作者预设的是民族主义立场,肯定了赵敏的“弃暗投明”;但对赵敏而言,她仅仅是为了爱情而已。她既不认为蒙古族对汉族暴虐的统治为“暗”,也不将以张无忌为首的反抗势力视为“明”。可以说,大到国家、民族立场,小到日常生活,女性都自觉地向男性靠拢,但其本人对男性价值观的认同与否并不重要。《笑傲江湖》中的女性群体似乎是例外的。这一群体中既没有金书中常见的因爱情失落而作恶多端的魔女,也没有如黄蓉、赵敏那般思想蒙昧的女性,她们都是以知行合一的正面形象出现的。因此,有研究者认为作者在该书中将拯救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女性身上,如林保淳的《解构金庸》[4],张立杰、郑言的《用解构视角重读〈笑傲江湖〉》[5]。女性似乎成为江湖黑暗中的一盏明灯,足以照亮未来的路。
事实上,这种观点值得商榷。虽然林、张等学者都论证了《笑傲江湖》中的女性人物全部是正面形象,从而得出“女性是希望”的这一结论,但不严谨之处在于论者忽视了男主人公令狐冲,或者说忽略了武侠小说中以男性为中心的特质,如果女性形象无法超越男主人公的正面意义,那么将女性视为希望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一、阳刚之镜:黑暗江湖中女性斗争的必要性
为什么金庸在《笑傲江湖》中塑造了如此众多的迥异的女性群像,首先需要明确该小说所设定的独特的江湖环境。金庸在这部作品中放弃了“擅长的记人写史的叙事手法”[6],没有渲染侠客行侠仗义、快意思仇的江湖环境。江湖不再作为朝廷的对立面而存在,不是以往侠客的江湖,而是政客驰骋的场域。从这个意义来看,江湖即庙堂。左冷禅、任我行等人都有君临天下的野心与欲望,而不只是武功无敌于江湖。因此,这里的江湖环境看似远离朝堂纷争,但其自身环境却变得异常复杂和恶劣,整个江湖已被权力、欲望和野心所腐蚀,原本应当热衷于惩恶扬善的侠客变得沉默而低调。如小说开篇即描写福威镖局惨遭青城派灭门事件,其根源在于余沧海觊觎林氏的“辟邪剑法”,而导火索则是林平之为维护江湖正义而误杀了青城派的恶徒这一事件。令狐冲为帮助仪琳逃离魔窟而遭到采花贼的暗算,侠之大者甫一出场便呈垂死之状,可见行侠的代价是巨大的,因此连少林、武当这样的“名门望族”也在故事的前半场中缺席,只是在后来自身受到威胁时才有所行动。
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世界本来是一个虚构的理想化空间,作者塑造的解危济困、重义轻生的侠客形象寄托了人们对正义公平的向往。当众多江湖人物不再行侠仗义,转为党同伐异的“政客”时,这就与“侠义”精神背道而驰;有威望的武林中人又不敢站出来主持公道,同样失去了侠之为侠的品质。此时,那些不受法律约束、身怀武功的江湖败类的所作所为便具有了巨大的破坏性,暴力横行,江湖成为弱肉强食的修罗场。尽管有研究者认为金庸所构筑的武侠社会已经建立了成熟的侠义准则,“其中的成员已深刻了解在此社会里如何生存与活动”[7]。而金庸却不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江湖是一个“不讲法律,完全暴力来解决问题”[8]的社会,无疑,在《笑傲江湖》中,只是放大了这一残酷的事实而已。
在黑暗的江湖中,女性面对的不再是以拯救者姿态出现的男性侠客,而是遍布于江湖的“野心家”和“伪君子”。于是,作家将女性设置为与反面男性相对立的正面群体,女性性别作为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代表了正义的象征。与正义方的男主人公令狐冲一道,站在了同一立场。
利欲熏心的左冷禅为称霸武林,合并了五岳剑派,并收买了泰山派,面对其种种暴行,衡山派掌门莫大选择了明哲保身,避其锋芒;华山派掌门岳不群虚与委蛇,并筹划如何夺权,而由女性组成的恒山派则态度鲜明,坚决同左冷禅进行斗争。值得注意的是,宁中则与岳灵珊作为华山派掌门人岳不群的妻女,她们反对岳不群的妥协,并希望其能与左冷禅进行斗争,维护华山门派的独立与尊严。正直刚烈的女性与卑鄙懦弱的男性形成了《笑傲江湖》中阴与阳对立的奇妙图景,作家如此刻意地将性别与道德挂钩,突出地表现了男性与女性割裂式的对立而不考虑故事的逻辑性与情节的合理性,显然是别有一番用意的。女性人物被定义为正面形象的同时,也被简化为具有积极意义的象征符号。女性所代表的这种不畏强暴、重义轻生的侠义精神,正是令狐冲所具备的。但令狐冲的性格也有缺陷,他优柔寡断、顾虑重重,尽管对师父岳不群的所作所为不满,但又不敢进行任何反抗。此时,女性发出的反抗声音就显得尤为特殊而响亮。
中国古代以“天地君亲师”为人之五伦,当男主人公处于父权体系之中而无法公然忤逆“父亲”时,父系之外作为妻子的女性,却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就妻子而言,一方面“夫—妻结合是统治者—臣民关系的一种隐喻”[9],妻子由此具有一种非正式的可支配权力,可以发出反对的声音;另一方面,“出嫁从夫”的男女从属关系,使得女性的价值附属于丈夫而不同于男性的“子”所具有潜在的威胁性,规劝是“贤妻”的行为与职责,不是女性的反叛。从这一角度来看,宁中则其实是代替令狐冲发声的。女性作为男主人公的镜像,其作用在于彰显勇于抗争的阳刚特质,以及发出限于其身份而只能规劝的反对声音,这并不能证明女性的主体意识更强。
由此可见,女侠的“侠”之特质不足以超越男主人公成为照耀黑暗的明灯,而“武”的缺乏,更是导致女性在行侠的道路上困难重重。无论小说家如何重视“侠”多于“武”,但不可否认“武侠小说很大成分是靠精彩的打斗场面来吸引读者的”[1]76,神奇幻想与文化底蕴兼具的武功描写,更是展现侠客魅力的重要因素。书中的女性没有被赋予“独孤九剑”般高深的武功,看似颇费笔墨宣扬的“无双无对,宁氏一剑”也早被魔教所破。因此女性不仅无力行侠仗义,还被负面男性贬低为“性的对象”,有的女性还屡遭性暴力的威胁,仪琳、岳灵珊与宁中则等则是在令狐冲的保护下才幸免于难的。
三、阴柔之镜:困于情感的女性与其斗争局限性
美丽的容颜是女性特质的外现形式,女性特质不是独立存在的,只有与男性特质相配合才具有意义。如果某一女性不与任何男性产生情感联系,那她的女性特质就被淡化,表现出“双性同体”的特征,如形貌举止都相当男性化的定逸师太。围绕在男主人公身边的女性们既有美丽的容颜,也有丰富的情感,她们与令狐冲有种种的情感联结,包括亲情与爱情。女性的温情抚慰了令狐冲在江湖上受到的创痛。
女性的多情也是男主人公镜像的另一面,孟悦和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指出,男性文人自比于女性的书写是出于“阉割情结”,即将自我置于等待被男性取用的女性一样的贱位,期待君王的顾盼与采撷。[10]由于这种意识的存在,男性作家对女性形象的书写意图变得复杂—通过女性表现男性的阴性一面。“阴性”不是特属于女性的特质,而是男女共有的。这种“阴性书写”在《笑傲江湖》中体现为将女性人物作为男主人公的镜像,两者形成互文。
陈岸峰对令狐冲身上的那种“魏晋风度”多加注目,尤其是在其好酒、善琴、个性狂放这一面上,认为这是令狐冲自由精神的体现。[11]但纵观全书则发现,任性不羁的令狐冲特别渴望回归华山派,渴求岳不群的认同。正如鲁迅先生所言:“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12]只是礼教为政治家所利用,“老实人”觉得这是一种“亵渎”,才会貌似反对礼教。因为作家对令狐冲的落拓狂放刻画较多,导致读者往往忽略其依赖性人格。这种依赖性人格是通过令狐冲的“重情”体现出来的。令狐冲对岳灵珊的痴情是毋庸置疑的,而他对岳不群怀有深厚的情感,并对其敬重有加也是事实,对岳不群扮演的“君子”角色也深信不疑。在令狐冲心中,岳不群就是正直的父亲。有评论家认为“无父”的令狐冲是江湖之上的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作家在其身上超越了“寻父”这一武侠母题[13],在武侠小说中,师徒关系几乎不逊色于父子关系,师徒伦理是不能僭越的,因此当令狐冲与岳不群进行斗争时,又体现出他的局限性和游离性的特点。
无论是宁中则、岳灵珊还是令狐冲等都反对岳不群的不义之举,他们的反对都是出于人道主义,从本能上排斥杀戮行为。但同时他们也为伦理关系所束缚,无法做到彻底反对,又由于个人情感的原因,始终不愿相信岳不群是江湖上人尽皆知的伪君子。“所有传统的态度总是不承认个体的独立性……总是把个人认作‘依存者’(dependentbeing)”[14],不仅女性从属于男性,令狐冲也宁愿“阉割”自由意志而维持与岳不群的关系。他们唯有在与岳不群建立的二人对应关系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这种对“从属”的执着是人格依赖的表现。而“妻”与“子”的轻信,是因为他们习惯于被男性家长统治以获得庇护的依赖心理。正是这种价值导向与弱者心态使他们的反抗精神出现了裂隙,斗争的锋刃只能对外而不能向内。令狐冲始终无法完成“弑父”的使命,即使岳不群威胁到他的生命,他也没有产生动手杀他的念头,是仪琳替他除掉了岳不群。与令狐冲有师徒之实的任我行去世后,其女任盈盈继承了教主之位,从此消弭了江湖中的斗争。
就仪琳和任盈盈而言,女性似乎具有以柔克刚的能力,以自身阴性特质修正了江湖的恶劣风气。作家似乎认同马尔库塞的女性观念:“在根本意义上‘包容’着和平、快乐和结束暴力的希望。”[15]然而,武功低微的仪琳之所以能杀掉岳不群是因为运气和巧合因素使然。而任盈盈从未动过弑父的念头。岳灵珊和宁中则的死则证明了温情感化的失败。令狐冲无法理解宁中则自杀的原因,任盈盈则将之归为“嫁了这样卑鄙无耻的丈夫,若不杀他,只好自杀”[16]。金庸以不能用“现代人功利心代入武侠人物”[17]的观点来回应读者对宁中则之死的质疑。事实上,以“功利心”来解释读者的疑问不够准确,现代读者惋惜的是宁中则对自己生命的轻视;而作家将宁中则自杀与史可法、文天祥的死相提并论,也不可信。任盈盈的答案已经透露出宁中则之死有殉葬意味,不过这种殉葬不是在封建礼教等外力压迫下的被动行为。岳不群编织的“利他”谎言,即光大华山派以慰先师之灵与保护华山门下弟子,以此欺骗宁中则,掩盖自我权欲的膨胀。这谎言的基础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和合”的代际关系[18]之上的,一旦其“利己”的真相被揭露,那么从属于岳不群的宁中则也就失去了合法性的存在,她生无可恋,便选择与正义和信仰一同死去,表现出她刚烈和血性的一面。岳灵珊被爱人所杀而毫无怨怼,则表现其情感的宽恕性。
与宁中则和岳灵珊的结局不同,令狐冲最终实现了“笑傲江湖”,但这一结局是作家的有意安排,而非通过人物自身的抗争取得的。同时,应当注意到喜剧结尾中的悲剧性意味,如莫大在令狐冲与任盈盈的婚礼上奏出凄凉哀音,以及令狐冲的低落情绪。只有将女性视为男主人公之镜像,才能理解令狐冲的低落情绪从何而来。令狐冲对岳不群的不抵抗,流露出与宁中则、岳灵珊别无二致的忠诚性与宽恕性。他后来选择归隐山野,将自己完全融合于大自然之中,进入“一种个人不复存在”[19]的精神境界。后来,作家又增加了令狐冲对“涅槃”的思考,更明显地表现出令狐冲对自我意识和个人情感的放弃,又喻示了其精神和情感之死。
四、结语
中国古典文学有借“香草美人”的意象抒发情感、抨击时政的传统,这种传统最早或可追溯到《诗经》和屈原的《离骚》。男性文人借“香草美人”之口,可以表达怀才不遇的忧愁和不平,如白居易的《琵琶行》等;或是通过“香草美人”的赴死明志,表达对黑暗现实的嘲弄,如孔尚任的《桃花扇》等。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作者的书写无论是客观上为保证自身的安全,不至于背上诽谤君主的罪名;还是主观上对高高在上的天子深怀敬畏,不愿直言其非都是合情合理的。闻一多先生对这种书写传统一言以蔽之,即“男人说女人话”。这种写作增添了女性之柔美色彩,也更符合“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中国古典美学法则。
《笑傲江湖》中刚柔并济的女性形象也具有类似性。首先,女性的刚直与侠气,冲淡了小说营造的黑暗绝望的氛围,女性的细腻多情又带来了一丝温馨的柔美。其次,女性作为男主人公的镜像,丰富了人性的内涵,尤其与令狐冲“重情义”而“轻生”的特点相呼应。最后,通俗文类出于接受美学的需要,往往要安排一个类似于喜剧的结局来收束全文,即女性为破灭的理想和感情殉葬,而男主人公却活下来了。
金庸表示“对女性的崇拜和描写,是想间接否定男性在社会中扭曲人性、轻视真情的这一切”,认为女性往往“专注于爱情与家庭”。[20]现代女权主义者波伏娃认为这种被赞美的女性特质并非女性天生具有的,“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21]金庸的女性观念比较传统,尽管他笔下的侠女很少被封建礼教所束缚,能够更充分地展现自我,但“雌伏”往往是她们最终的归宿,这固然是作家的“男权思想”作祟和对女性主义进行隐喻式的批判。
金书中的女性人物往往“侠气”不足,只专注于爱情而带有蒙昧色彩,[22]但专注于爱情同样是自我意识张扬的体现。金庸笔下的男侠并非为传统武侠小说中抽象化的“寄托芸芸众生被拯救意愿的文化符号”[1]81,而是有血有肉、情感丰富的“个人”。金庸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们,除郭靖、胡斐之外,其余男性主角大多以归隐为归宿。他们曾凭借高超的武功行侠仗义,结果却发现个人在现实面前是那样的渺小无力,于是雄心锐减,热血渐消,不如携爱人远去。在男性的思想转变中,女性也起到了或显或隐的作用。为爱情不顾一切的女性在“侠”与“我”的纠结中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后者。出于种种原因,她们不关心男性所专注的侠义理想或权欲野心,她们关心的是“我”,这与为国为民的大侠郭靖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比如,深受小龙女与郭靖影响的杨过也曾在选择“为我”与“为侠”而摇摆不定,他在远离小龙女的十六年间已经成长为“神雕侠”,在他与小龙女重逢之后,还是选择了“绝迹江湖”。从中可以看出小龙女对杨过的影响显然要大于郭靖。重义轻生、舍己为人是侠客的高贵品质,其崇高性不言而喻。金庸笔下的男女主人公同样不看重性命,但他们看重的是情,行侠的理想终究抵不过一个纯粹的自我世界的诱惑。
尽管《笑傲江湖》中的女侠形象已经成为理想的化身,但在本质上依旧是男侠的镜像。“中国古典悲剧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封建儒家思想观念的影响”,因此“悲剧人物被束缚在现存总体秩序的罗网中而无法游离,从而损失个体自主意识和对命运的反抗精神”。[23]16在《笑傲江湖》的虚构世界中,作家淡化了儒家封建思想和外界舆论的压力,肯定了令狐冲和宁中则的伦理道德。而令狐冲和宁中则反抗更多的是他们自身的情感,当男主人公囿于情感而无法彻底地进行斗争时,作为男性镜像的女性注定走上一条更狭窄的路,二者均免不了超越自由的失败。[24]此时,女性“镜”的属性显现,终难成为烛照江湖的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