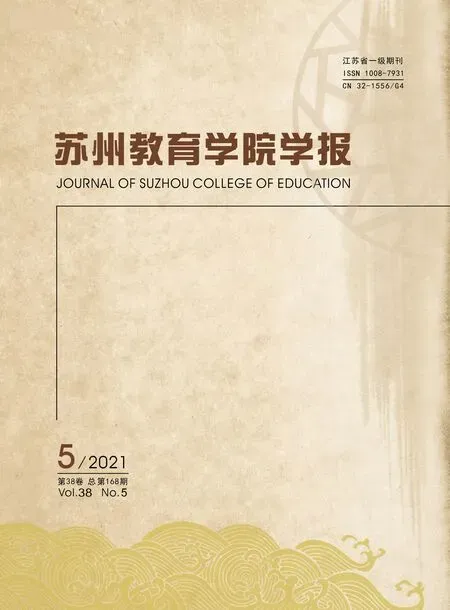《笑傲江湖》莫大先生的文化内涵及其意义
2021-02-01罗立群
罗立群
(暨南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珠海 519070)
学界关于金庸小说的研究成果颇丰,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研讨金庸小说中的文化意蕴、人物形象、情节结构、叙事手法、渊源影响等。但在这其中,《笑傲江湖》①金庸小说有三个版本:一是连载合订本;二是修订本,又称“通行本”,即自1970年3月起,金庸用10年时间修改完成的作品;三是新修本,即1999年至2006年再次修订的版本。本文引用的是通行本,即2002年广州出版社出版的“金庸作品集”丛书。中的莫大先生这一形象却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关注。
在《笑傲江湖》中,莫大先生为衡山派掌门,江湖绰号“潇湘夜雨”。“莫大”先生之名的来源,书中没有交代,《庄子》云:“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1]“莫大”之名,或许来源于此,用“心死”来概括莫大先生,虽不够准确、全面,但也有几分贴合。
莫大先生在书中着墨不多,只出现过七次:第一次是在衡山城中的小酒馆,一剑削断七只茶杯;第二次是在衡山野岭中,用衡山剑法绝招诛杀了费彬;第三次是在鸡鸣渡口,与令狐冲欢饮畅谈;第四次在少林寺出现,一句话也没有说;第五次是在嵩山封禅台,参加比剑夺帅;第六次在华山思过崖山洞里,聚精会神地观看石壁上刻着的衡山剑法,没有说话;第七次是在杭州西湖孤山梅庄,用琴声贺令狐冲、任盈盈新婚之喜。在这屈指可数的七次登场里,有两次莫大先生人虽出现,却没有说话,有一次只有琴声,连面都没露。莫大先生在书中的出场次数虽然很少,但给人的印象却极深。
一、“潇湘夜雨”:莫大先生的形貌、气质
“潇湘”原是地理名称,潇,指湖南省境内的潇水河;湘,指的是横贯湖南的湘江。“潇湘”并称,多指今湖南地区。潇湘一带,景色清幽迷人,且有着凄美伤感的民间传说,历代文人墨客于此浏览风光,寄意山水,吟诗作赋,抒发感慨。唐代诗人刘禹锡以《潇湘曲》寄托思古幽情:“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诗人运用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借湘妃神话描绘了一个虚实交织的艺术境界,将远古传说、逐臣的哀怨与自己被贬湘地的愁思融为一体,以“斑竹泪”“潇湘夜”和“楚客怨”烘托其哀怨之情,赋予这首小词以深邃的政治内涵,以此抒发自己政治受挫和遭无辜贬谪的怨愤。
自古以来,“潇湘”就被视为官吏贬谪之地,屈原遭流放,在湘水之滨留下足迹;汉代名士贾谊被贬谪,途经湘江,感而作赋。隋代文人孙万寿因此感叹:“贾谊长沙国,屈平湘水滨。江南瘴疠地,从来多逐臣。”(《远戍江南寄京邑亲友》)唐代诗人刘长卿亦云:“独恨长沙谪去,江潭春草萋萋。”(《谪仙怨》)历经积淀,在文人的诗赋里,“潇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多的是一个充满了凄怅寥落之情境的文化意象,具有丰厚的人文内涵和深广的文化意蕴。
在中国古典诗词里,“雨”这一自然现象也是具有浓烈的感情色彩的。一般来说,“春雨”表达欢乐情绪,“秋雨”则象征悲哀浓愁。而“夜雨”一词,其审美意蕴就愈加深沉、厚重、复杂,它往往成为诗人忧伤凄凉、悲苦惆怅的情怀表达,诸如国恨家愁、思乡之苦、离别之情、人生失意、仕途不顺,等等。如唐代诗人王昌龄云:“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芙蓉楼送辛渐》)秋寒夜雨,清晨送客,以凄冷的“夜雨”“孤山”形象地表达出作者的离情别绪。又如南宋诗人陆游有词云:“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诗人用夜卧听风雨来激发披铠甲、跨战马驰骋疆场的梦想,以此表达诗人忧国忧民的一腔情怀。
至于“潇湘夜雨”一词,因描摹主体的主观感受而被赋予了无比丰富的情感内涵,作为诗文意象,它承载了历代文人诸多复杂的情思。宋代胡铨写道:“一片潇湘落笔端,骚人千古带愁看。不堪秋著枫林港,雨阔烟深夜钓寒。”(《题自画潇湘夜雨图》)诗人用枫林和潇湘夜雨的环境,衬托出内心的孤独愁绪。马致远更是以“潇湘八景”为题材,创作了八首小令,从不同侧面描述了潇湘地域的旖旎风光,其中,《寿阳曲•潇湘夜雨》就是以“潇湘夜雨”为题名的名篇:“渔灯暗,客梦回,一声声滴人心碎。孤舟五更家万里,是离人几行情泪。”作者用极为简洁的语言,描绘出潇湘夜雨中漂泊在湖面上的一叶孤舟,孤舟里闪烁着昏暗的灯光,更增添了客居在外的游子的孤寂清冷和羁旅乡愁,雨水混杂着泪水,游子辗转难眠。这首曲子情调格外凄凉,意境则灵动悠远。“潇湘夜雨”是莫大先生的江湖绰号,它的诗文意象清幽凄冷、孤独惆怅,这种文化意象与莫大先生的形貌、气质十分贴合。
莫大先生的形貌在第一次出场时,作者就给予了简洁而精准的描述。在衡山城中的茶馆里,茶客们谈论着江湖事,有人说衡山派掌门莫大与其师弟刘正风不合,添油加醋,言语颇有不敬,于是莫大先生忍不住现身“示武”,震慑住了那些妄议之人:
忽然间门口咿咿呀呀地响起了胡琴之声,有人唱道:“叹杨家,秉忠心,大宋……扶保……”嗓门拉得长长的,声音甚是苍凉。众人一齐转头望去,只见一张板桌旁坐了个身材瘦长的老者,脸色枯槁,披着一件青布长衫,洗得青中泛白,形状甚是落拓,显是个唱戏讨钱的。[2]59-60
莫大先生的形貌是通过众茶客的视角呈现出来的:手拿一把破旧胡琴,身着旧长衫,身材瘦长,脸色枯槁,形状落拓,一副串街卖艺乞讨的模样。
莫大先生的第二次出场是在衡山野岭中,其时嵩山派费彬正欲行凶,莫大突然现身:
忽然间耳中传入几下幽幽的胡琴声……琴声突然止歇,松树后一个瘦瘦的人影走了出来。令狐冲久闻“潇湘夜雨”莫大先生之名,但从未见过他面,这时月光之下,只见他骨瘦如柴,双肩拱起,真如一个时时刻刻便会倒毙的痨病鬼,没想到大名满江湖的衡山派掌门,竟是这样一个形容猥琐之人。[2]232-233
莫大先生的这次露面,其形貌是由令狐冲的眼睛“看”出来的:骨瘦如柴,双肩拱起,形容猥琐。莫大先生的两次出场都是通过他人视角予以表述,形貌是清瘦如病,状态是潦倒失意,与其名门大派的掌门身份极不相符。两次出场都伴随着幽幽的琴声,琴声响起,莫大先生慢慢地走来,琴声渐渐消歇,他的背影也隐隐消失。他的行为有些怪异,所奏琴音也是一味凄苦,引人泪下。他虽是名满江湖的衡山派掌门,却远离大众视线,独来独往,不受羁绊,言行举止透露出内心的孤独惆怅。莫大先生的形貌、气质配得上他的江湖绰号“潇湘夜雨”,可谓清幽凄冷,孤独惆怅。
类似莫大先生形貌、气质的描写在武侠小说史上屡见不鲜,唐代剑侠小说《兰陵老人》中的剑侠便是“埋形杂迹”,形容苍老,隐居市井。[3]袁枚《卖蒜叟》中的内功高手卖蒜老人“龙钟伛偻,咳嗽不绝声”,略施手段,便让精于拳勇的杨某跪地求饶。[4]54-55宋永岳《响马盗》中的黄胡子“形瘦似病,衣敝衣,跨蹇驴”,却身怀绝技,令众武举大惊失色。[4]162-163俞超《金瞎子》中,跛足落拓的老叔竟是名震武林的“江湖第一高手”。[4]253-254金庸对莫大先生的形貌设计当有所承袭。
二、幽深苍凉:莫大先生的性格特征
从莫大先生屈指可数的几次出场来看,其性格特征犹如他的“百变千幻衡山云雾十三式”剑法,如梦如幻;又似他奏出的琴声,幽深苍凉。他的性格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神秘莫测。莫大先生喜欢独处,行踪诡秘,神龙见首不见尾。每次来去总是伴随着凄苦的胡琴声。如在衡山野岭中,费彬欲对令狐冲、仪琳、曲非烟等人行凶时,孤寂苍凉的胡琴声突然响起:
忽然间耳中传入几下幽幽的胡琴声,琴声凄凉,似是叹息,又似哭泣,跟着琴声颤抖,发出瑟瑟瑟断续之音,如是一滴滴小雨落上树叶。令狐冲大为诧异,睁开眼来。
费彬心头一震:“潇湘夜雨莫大先生到了。”但听胡琴声越来越凄苦,莫大先生却始终不从树后出来。[2]232
莫大先生现身后,先假意向费彬示好,麻痹对手,随即出其不意,突施杀手:
寒光陡闪,(莫大先生)手中已多了一柄又薄又窄的长剑,猛地反刺,直指费彬胸口。这一下出招快极,抑且如梦如幻,正是“百变千幻衡山云雾十三式”中的绝招……一点点鲜血从两柄长剑间溅了出来,费彬腾挪闪跃,竭力招架,始终脱不出莫大先生的剑光笼罩,鲜血渐渐在二人身周溅成了一个红圈。猛听得费彬长声惨呼,高跃而起。莫大先生退后两步,将长剑插入胡琴,转身便走,一曲“潇湘夜雨”在松树后响起,渐渐远去。[2]233
费彬仗着嵩山派的势力,欺压同门,滥杀无辜,罪大恶极。生死关头,莫大先生果断出手,以暴除暴,事了之后,拂袖而去,来无影去无踪。真可谓“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李白《侠客行》)。
对于莫大先生诡秘的行踪描写,作者是有所借鉴的。古代小说中的剑侠,或藏匿于深山,或隐居于陋巷,隐姓埋名,处世十分低调。乐钧《末坐客》中的剑侠神色灰暗,体态不堪,衣衫破旧,众人均瞧不起他,吃饭时总是坐在末位[5];吴陈琬《瞽女琵琶》中的女剑侠,双目失明,“挟琵琶漫游遍宇内”[4]44-45,走街串巷,弹唱算命;冯梦龙《李汧公穷邸遇侠客》[6]中的隐侠,身处陋巷,落魄失意,整日烂醉,东倒西歪,然而他们都身怀着惊世骇俗的“剑术”,韬形敛迹,行踪不定,自掌正义,神秘难测。一旦干预世事,身份暴露,即刻便人去屋空,不留一点痕迹。剑侠的利剑或藏于口中,或藏在指甲里,平时看不见,用时犹如一道寒光射出。①文学作品中的剑侠形象源于历史上的刺客,至唐代小说趋于成熟,其特征是具备神奇的剑术,潜踪匿迹,不事张扬,行踪诡异,飘忽不定。唐代小说中的剑侠形象嗜血成性,恩仇观念极重,缺乏道德内涵。五代及宋,剑侠开始关注并干预社会,锄奸扶弱。明清以后,剑侠嗜杀喋血的性格明显淡化,行为趋于理性,言行举止受到约束,行为逐渐规范,剑侠在注重“剑术”修炼的同时,也十分强调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关于剑侠形象,参见罗立群:《中国剑侠小说史论》,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莫大先生神秘莫测、来去无踪的行为举止,不求闻达、不图功利的性格特征,以及“剑藏琴底,剑发琴音”的攻敌不备的突袭方式,明显是受到了古代小说中的剑侠形象的影响。
第二,为人正直。令狐冲洒脱自在,任性而为,被岳不群逐出华山派,遭到江湖名门正派的误解。莫大先生不被江湖俗见所困,因为亲见令狐冲出面阻止费彬行凶杀人,对他心生好感。莫大先生为人正直,是非分明,恒山派定闲、定逸两位师太赶赴少林寺,为任盈盈向方丈说情,将一干弟子交付令狐冲照顾,于是莫大先生一连五个夜晚去船上窥探,查证令狐冲的人品,终于认定他是后辈中了不起的少年英雄,两人倾心相交。他告诉令狐冲,任盈盈被困少林寺,江湖群豪要去围攻少林寺,希望令狐冲去约束群豪。令狐冲得知任盈盈为救自己,甘愿被囚少林寺,心情激荡,恨不能立刻前往营救,可是他受定闲、定逸两位师太之托,要一路护送恒山派众姊妹,难以分身,十分着急。
令狐冲道:“莫师伯,小侄既知此事,着急得了不得,恨不得插翅飞去少林寺,瞧瞧两位师太求情的结果如何。只是恒山派这些师姊妹都是女流之辈,倘若途中遇上了什么意外,可又难处。”
莫大先生道:“你尽管去好了!”令狐冲喜道:“我先去不妨?”莫大先生不答,拿起倚在板凳旁的胡琴,咿咿呀呀地拉了起来。
令狐冲知他既这么说,那便是答允照料恒山派一众弟子了,这位莫师伯武功识见,俱皆非凡,不论他明保还是暗护,恒山派自可无虞,当即躬身行礼,说道:“深感大德。”[2]905
莫大先生一口应承护送恒山派众弟子的重任,让令狐冲放心前往,终于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莫大先生虽不理帮务,隐身市井,但他是一个“老江湖”,对江湖局势看得十分清楚,早就洞察了左冷禅的狼子野心。在嵩山封禅台,面对左冷禅的淫威,莫大先生毫不畏惧,当众揭穿他的谎言,表明自己反对左冷禅并派阴谋的立场。他明知自己的剑法敌不过左冷禅、令狐冲,也绝无半分要当五岳派掌门的念头,但身为衡山派掌门,形格势禁,自然不能做“缩头乌龟”,更不会附和左冷禅之流。莫大先生仗剑出场了,他本是挑战岳不群的,岳灵珊却硬要出头,二人交手,他打败了岳灵珊,及时收手,却遭到对方暗算,但他并没有计较,只淡淡说一句:“将门虎女,果然不凡。”足见其宽容仁义,气量不凡。[2]1180-1184
第三,外冷内热。在《笑傲江湖》第二十五章中,莫大先生与令狐冲在鸡鸣渡口交心畅饮,这是莫大先生在书中话语最多的一个场景,让我们得以更好地认清这位衡山派掌门的内心世界。请看书中的几段描写:
莫大先生续道:“我见你每晚总是在后艄和衣而卧,别说对恒山众弟子并没分毫无礼的行为,连闲话也不说一句。令狐世兄,你不但决不是无行浪子,实是一位守礼君子。对着满船妙龄尼姑、如花少女,你竟绝不动心,不仅是一晚不动心,而且是数十晚始终如一。似你这般男子汉、大丈夫,当真是古今罕有,我莫大好生佩服。”大拇指一翘,右手握拳,在桌上重重一击,说道:“来来来,我莫大敬你一杯。”……两人举碗一饮而尽,相对大笑……几碗酒一下肚,一个寒酸落拓的莫大先生突然显得逸兴遄飞,连连呼酒,只是他酒量和令狐冲差得甚远,喝得几碗后,已是满脸通红,醉态可掬……
莫大先生点头道:“……令狐兄弟,你现下已不在华山派门下,闲云野鹤,无拘无束,也不必管他甚么正教魔教。我劝你和尚倒也不必做,也不用为此伤心,尽管去将那位任大小姐救了出来,娶她做老婆便是。别人不来喝你的喜酒,我莫大偏来喝你三杯。他奶奶的,怕他个鸟卵蛋?”他有时出言甚是文雅,有时却又夹几句粗俗俚语,说他是一派掌门,也真有些不像。
……
莫大先生叹道:“这位任大小姐虽然出身魔教,但待你的至诚至情,却令人好生相敬……”[2]900-904
莫大先生外冷内热,遇到投缘的令狐冲,立刻引为知己,把酒言欢,倾心交谈。他称赞令狐冲的人品,钦佩令狐冲的光明磊落,理解令狐冲的江湖处境。他是非分明,有敏锐的江湖嗅觉和政治眼光,不为正教、魔教的俗见所囿,身为正派掌门,却夸赞任盈盈的至诚真情,断然劝说令狐冲娶魔教公主任盈盈为妻,还要亲自登门喝喜酒,可见他骨子里是一个不拘于俗见又重情重义之人。莫大先生武功奇高,擅长音律,年轻时当是江湖上的风雅俊彦,他对令狐冲的赞赏和劝勉,或许是在这位年轻人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这就是莫大先生。他的性格幽深苍凉,令人有点捉摸不透,有时觉得他孤傲冷峻,有时感到他有些窝囊,有时认为他是明哲保身,有时又会发现他竟很有担当。莫大先生的性格不是单一的,是复杂多面的。无论如何,莫大先生的内心是坦荡的,处世是睿智的,在低调隐忍中仍流淌着男儿热血。
三、半隐江湖:莫大先生的处世之道
金庸在《笑傲江湖》后记中说:“(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2]1451在作者看来,莫大先生是政治人物,但与书中其他热衷于权力斗争的人物,如左冷禅、岳不群、任我行等相比,他似乎涉足政治并不深,权力欲也不强,半隐江湖,是具有隐士行为特征的政治人物。
《论语》称隐士为“逸民”①《论语正义》注:“逸民者,节行超逸也。”参见刘宝楠注:《论语正义•微子十八》,《诸子集成(一)》,影印本,中华书局1954年出版。《孟子•公孙丑》:“柳下惠……遗佚而不怨。”参见焦循:《孟子正义•公孙小丑章句上》,《诸子集成(一)》,影印本,中华书局1954年出版。逸,指遗佚;逸民,指被遗落的人才。,并将其分为三类:一类,“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一类,“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再一类,“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7]396
孔子认为,伯夷、叔齐是一类隐士,他们坚守自己的道德理想,维护自己的尊严;柳下惠、少连是一类隐士,他们为了大局作出相应的牺牲,但言行合乎情理,绝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虞仲、夷逸又是一类隐士,他们避世隐居,直斥时弊,但绝不参与权力斗争。
“隐”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儒家主张立身处世因势而异,隐现变通。孔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7]163并以赞赏的口吻说:“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7]335孟子也认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8]儒家的隐逸是与政治环境、理想抱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道家则不同,道家的隐逸是要挣脱一切羁绊,放任个体生命,达到一种永恒的、绝对的精神自由,也就是庄子说的“逍遥游”的人生境界。
小说中的风清扬、令狐冲、莫大先生,他们的处世方式都有着隐士的文化内涵,虽有着不同的行为特征,但大体不出儒道两家。我们不妨用《论语》的三类隐士的眼光来审视他们。
风清扬看透世情,对江湖争斗心灰意冷,于是避世隐居,远离争斗,放飞自我。他虽然隐居华山,但并没有违背自己做人的原则,在传授令狐冲剑术的同时,也教他做人、处世之道。风清扬如同伯夷、叔齐,是真正的脱尘离俗的隐士高人,剑术和人格都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像风一样清逸,像云一般飞扬。
令狐冲任性自然,没有野心,但放荡不羁的言行使他身陷江湖各派的矛盾纠纷之中,招来各种流言蜚语。他与魔教中人相交,却行得正,走得直;他不得已做了恒山派掌门,门下众多女弟子,他始终遵守男女防线,对众姊妹以礼相待;他被逐出华山派,仍一如既往地尊师重道,不忘养育之恩;他在极其恶劣的环境里备受欺凌,可谓“降志辱身”,却依旧侠骨仁心,不忘初衷,自始至终如行云流水般逍遥自在。令狐冲的经历、处境好似柳下惠、少连这一类隐士,顾全大局,甘愿作出一些让步,但绝不会屈从于恶势力。
与风清扬、令狐冲相比,莫大先生似乎活得有点窝囊。他洞察世道人心,识破江湖阴谋,有心做一番事业,却无法改变格局,更不愿随波逐流,于是选择韬晦隐忍,伺机而动;他身为衡山派掌门,却不理世务,流浪江湖,任由嵩山派上门指手画脚;他诛杀费彬,却害怕别人知晓,甚至探问令狐冲的口风;他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能放胆直言,维护正义,却始终混迹于市井底层,有意远离江湖纷争。
莫大先生没有风清扬超脱,不算世外高人;他没有令狐冲洒脱,不能一意孤行;他以半隐的方式游走江湖,虽避开了诸多纷扰,却未免有些消沉和无奈,但他一直坚守原则底线。他恰似在官场上遭受打压的正直官员,一方面对权臣显宦的倒行逆施非常愤怒,另一方面又因为对手过于强大,只能忍气吞声地在夹缝中求生存。责任和忍耐让他的心灵备受煎熬,于是拿着把破旧的胡琴,拉着凄苦的音律,诉说着内心的悲凉。
莫大先生虽然隐居避世,但他对名誉却并没有完全看透,他虽然不沽名钓誉,但也容不得别人对自己胡乱抹黑。在衡山城中的小茶馆里,当他听到别人对自己造谣诽谤时,忍不住出剑示威,震慑谣言生事者。莫大先生虽然避世逍遥,却仍然执掌衡山剑派,可见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心中的抱负和理想,而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抗击邪恶势力。
莫大先生的形象,既有着柳下惠、少连的“降志辱身”,又有着虞仲、夷逸的“隐居放言”,但唯独做不到像伯夷、叔齐那样,全身隐逸,绝不涉足江湖。莫大先生苟全性命于乱世,半隐江湖,韬晦示弱,其人物形象无情地揭露了他身处的生存环境的险恶,展示给我们的是一幅生动而又值得思索的人生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