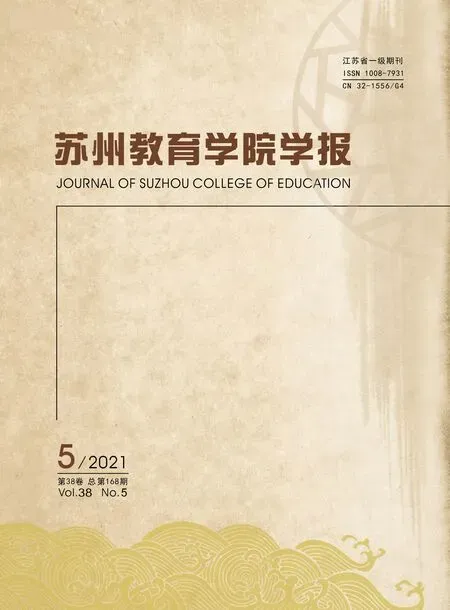当代显性鬼传说的“大小历史”和“嫁接”现象
2021-02-01陈冠豪
陈冠豪
(上海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44)
作为我国重要的民间文艺类型,鬼传说虽流传广泛,研究成果却寥寥可数。笔者参考西方都市传说(Urban Legend)理论,立足国内实际的文化现象,将鬼传说定义为:以人类鬼魂为叙事主体、结构完整的传说类型;通过强化人鬼差异所带来的矛盾危险及仿真人真事的情景渲染,突出事件的当下性,激发阅听人①阅听人,指读者和听众。紧张不安的情绪和感同身受的联想,由此营造恐怖感与真实性,进而实现人际交流的娱乐目的。[1]
据此,我们先将鬼传说归入人为想象的叙事作品,指出冥界既是人间的仿写,亦是死生困惑的投射。由此,便可进一步理解鬼传说文本的骨、肉、皮实可对应现实生活、虚构时空和艺术手法,且阅听人之个人忧惧也有代入的转换特征,从而梳理出情节虚实的结构组合。接着,聚焦自身与他者的形象意识,笔者针对鬼传说提出“双影”的概念,将其分为内外之别,前者指文本中生者和亡者各自的遭遇,后者则指阅听人能分别从生者和亡者的遭遇中产生的共鸣。此外,“双影”模式还发现鬼传说中的所有角色,包括虚实、死生在内的情节设定均会视立场变异而有自身和他者不断换位的现象。[2]
在对鬼传说的组成方式有一定了解后,本文将以“双影”概念为基础,试图从实名性和历史书写等视角继续深入挖掘我国当代鬼传说文本内部的建构模式和文化作用。②笔者参考西方都市传说的时代性特质,以大陆改革开放、台湾经济起飞,社会发展迈入现代化阶段为分界点,即大陆的20世纪80年代、港台的20世纪60年代皆为分界点,在此之前的传说是传统鬼传说,之后的便为当代鬼传说。
一、“显性”“中性”和“隐性”鬼传说
按照鬼传说文本的实名程度,即作为主要情节的事件外,包括人物、时间、地点等在内的背景信息,视其完整性由强至弱可分为“显性”“中性”和“隐性”三类。
首先,“显性鬼传说”有着相对全面且明确的实名信息。以北京鸿福宾馆的鬼传说①为避免现实争议等不良影响,笔者采取了田野到学术的符号化转换策略,将传说的讲述者、记录者,包括文本中的主、配角和标题名称,凡在世的或与在世人群紧密相关的常见人名一律改为化名;同理,真实存在的单位如学校、医院、商场等,以及既有品牌和物件如畅销书、电子产品、奢侈品等,也视文本内容予以化名处理;但涉及人员职业,所处时空、地区的历史,风土民情等具体关系到传说分析的信息则不作改动。由于城市是本文研究对象的限定范围,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故城市名称全部保留,具体的行政区划、街道名称等内容则视情况尽量虚化,并在保证文本有效性的学术伦理前提下,删减其中并不影响理解和分析的背景信息。为例:
这是我姐亲身经历的,那是1990年的冬天,当时她为19岁的技校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城区的鸿福宾馆实习。同年宾馆的5层曾发生火灾,不过我姐是后来才知道的。
事发当天她和一名同事在前台值夜班,约凌晨2点多,客房来电,是我姐接的:“我渴啊……能给我送点水吗?”听声音是位老太太。“好的,请问您几号房?”我姐说完,过了十来秒,对方才回答:“502。”我姐便让身旁的同事查阅当天的房客登记薄确认入住信息,自己则提着暖壶上楼。
我姐走到502房时,门是虚掩的,开了条巴掌宽的缝儿,但屋内漆黑一片,还飘出一股肉类烧焦的味儿。她敲了敲门,但无人回应。正纳闷时,房间的座机突然响了起来,把我姐吓了一跳。听见电话响了几声却没人接听,她赶紧往楼梯口奔,这时耳边先传来一声叹息,接着是苍老的声音说:“我渴……给我送水!”我姐吓得加速跑下楼。当她慌张地回到前台时,撞见同样惊恐的同事,他立刻问:“你进屋了吗?”我姐摇头说:“我看门虚掩……”同事赶紧说:“502今天根本没人住!怎么会有人打电话?门更不可能开啊!”“我正要进去的时候,听见屋里座机响了!”我姐补充道。“那是我打的,怕你出事,多亏你没进去。”那天夜里,我姐和同事就再没回502房。
事隔多年,我姐已不在鸿福宾馆任职。在离职前的一次年会上,她曾听领导们讨论5层火灾的事,说当时502有个老太太没能逃出来,最后被烧死在卫生间里。[3]
此传说的背景信息分别为:人物是讲述者的亲姐,事发时为19岁的技校毕业生,任职于酒店;时间为1990年冬季某日的凌晨2点多;地点为北京东城区的鸿福宾馆。由此可知,该文本的实名性是相对完整且详细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该宾馆的确曾于1988年遭遇祝融。[4]
第二,“中性鬼传说”,此类文本介于“显性鬼传说”和“隐性鬼传说”之间,背景信息多点到即止,尤其是清晰可辨的实名内容常予以省略。以上海某公园的鬼传说为例:
去年我接了一个烘焙类新媒体运营的项目,得频繁跑上海,认识了很多当地朋友,自由摄影师大瓶子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我们常约在嘉定郊外的某公园里,搭起帐篷彻夜畅聊。
那晚我和大瓶子喝完酒已凌晨3点多,公园里早没其他人,秋风瑟瑟。我们决定先去上厕所,然后睡2个小时后再起来拍日出,便一起走去卫生间。一般搭帐篷,我都不会离厕所太远,路程会控制在3到5分钟内。但那一次我们走了10分钟,却还没走到卫生间。
而且走着走着,我还发现另一个问题:我们基本没离开搭帐篷那片50平方的草地,因为草地边上那棵桂花树的香气,一直未曾散去。顿时,我们的酒醒了大半,觉得这一定是摊上事了。大瓶子不信这些,便开始大声喊叫:“有种你出来啊,绕着本大爷,算什么本事!”我心想:“不好,这下要出事。”果然,当他喊完之后,我们都听见了小孩的笑声,就像幼儿园里孩子们吵闹的声音,忽远忽近,时不时出现。大瓶子被吓出了一身冷汗,我也不知该怎么办,只好先回帐篷里,两人紧挨着等天亮。
翌日上午5点多,我俩醒来一瞧,发现昨晚我们的帐篷竟搭在湖边上,要是翻个身就会掉进湖里,真是有惊无险。这件事之后,大瓶子就再也不敢去户外露营,哪怕是又喝到凌晨也一定打车回家。[5]
相较前一则的“显性鬼传说”,这篇传说的背景信息便精简不少:人物是担任新媒体运营的女性主角和作为摄影师的男性配角,除交代二人的职业外,其余如年纪、学历、籍贯等都未涉及;事发时间则仅说了在“凌晨3点多”,阅听人需从文本的蛛丝马迹如“新媒体”和“秋风瑟瑟”去推测该传说的时间背景应为近年的某个秋季;事发地点也同样未具体说明,只知晓可能为上海嘉定郊外的某个公园;物件虽有桂花树,可惜也不具有指向性的识别作用。
第三,“隐性鬼传说”,此类文本完全没有任何实名信息,以一篇农村鬼传说为例:
这是同事父亲的亲身经历:那个年代因为怕野猪拱坏玉米苗,村里人会轮流去农地守夜。事发当天是隔壁李二伯守夜,刚好半夜李二伯家出了事,李二娘一着急,便来让我爸去替一下李二伯。
凌晨三四点,我爸打着手电筒走在半路上,当他手电筒晃到前方时,看到有个穿白大褂且没拿照明用具的男人正走着。我爸叫了几声,那人没应。因为左侧是会有落石的山壁,右侧则是大斜坡,摸黑行走非常危险。我爸就大步赶上去,表示愿意帮忙照明。结果那人还是没回应,依旧不疾不徐地在前面走着。我爸以为他没听见就又想跑上前,奇怪的是,那人看起来步伐很慢,但自己怎么都追不上。我爸觉得可能对方不想与人说话,于是就没再搭理他。
走着走着,前方拐弯处出现亮光,走在前面的人便突然不见了,我爸心想可能是对方在自己没注意时转弯了。这时,迎面走来两个村里人,我爸就上前搭话,顺口问他们是否看到一个男的和他们擦身而过。结果他们说这一路就只遇到我爸,没看见其他人。之后我爸一个人继续往农地走时,越想越后怕。忽然,他感觉有人在跟着自己,就回头拿手电筒一照,竟看到穿白大褂的男人出现在身后!我爸大惊,便头也不回地狂奔。结果,后头那人也跟着自己跑了起来。我爸吓坏了,边跑边向李二伯大声呼救,离得不远的李二伯听见声音便向我爸跑去,两人碰头后,他看我爸身后啥也没有,拉着我爸就回地里的草棚子。我爸把事情经过跟李二伯说了一遍,也讲了他家里的事,李二伯不怕那些玩意儿,便急忙回家了。我爸一人在地里守夜,喝了几口酒,胆子大起来也就不怕了。[6]
显而易见,该传说的实名状态基本属于空白:人物只介绍了是“同事父亲”,和都市传说典型的“发生在朋友的朋友身上”的叙事模式并无二致;时间仅知晓在凌晨三四点,其他包括地点在内的更具体的背景信息均无从判断。
以前文的鬼传说为例,若尝试将北京鸿福宾馆“显性鬼传说”的背景信息作虚化处理,如人物只透露是朋友的姐姐,其余内容则隐去不提;时间仅说是凌晨2点多,省略年份和季节;地点则完全不交代。反之,将农村“隐性鬼传说”的背景信息作实名处理,如人物是朋友的父亲,35岁的当地农夫,小学学历;时间是1960年夏季某日的凌晨三四点;地点则是北京怀柔郊区的农村。如此一来,会发现实名程度的详略差异,其实仅对文本真实性的感染力有强弱的影响,无法在根本意义上改变鬼传说的本质。换言之,只要符合基本的叙事原则,即便是背景信息最详尽的“显性鬼传说”也不会因此被视为新闻事实,反之,就算是不具备任何背景信息的“隐性鬼传说”也不会就此被归作童话故事。
关于传说的体裁特征,学界有几种观点如“实存说”“相信说”以及邹明华提出的“专名说”[7]。笔者认为,撇开主观判断的“相信说”,其余不论是依托实际存在的“实存说”,或是藉专有名词来强化传播者和阅听人心理作用的“专名说”,其实都离不开以背景信息来营造真实性。[8]而从上述三例可知,和一般传说不同,鬼传说作为一种特别的民间文艺形式,具有实名的使用弹性,即便在缺乏人、时、地、物等背景信息的情况下,依旧能较好地渲染出使人信以为真的叙事效果。视当下的叙事需求,文本中的实名信息可弹性地增减和置换,故同一则鬼传说,受不同时空、传播者、阅听人、载体等外在条件的影响,呈现状态均能在“显性”“中性”和“隐性”三类中灵活变化。
二、“大小历史”和“嫁接”现象
1985年,黄仁宇在台北版《万历十五年》的自序中第一次提出“大历史”的概念。“大历史”与“小历史”不同,前者不计较人物短时片面的贤愚得失,也不是只抓住一言一事,借题发挥,而是要勾画当日社会的整体面貌。[9]254其观点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10]305,注重非人身因素所产生的作用[9]256。赵世瑜则立足区域社会史,将“小历史”视为“局部性”的历史,比如个人性、地方性的历史,也就是那些“常态的”历史,即日常生活、喜怒哀乐、社会惯制的历史;“大历史”则是“全局性”的历史,比如改朝换代、治乱兴衰的历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典章制度的历史,等等。[11]10而钱茂伟是以历史建构单位着眼,以国家政府为对象的历史书写,即为“大历史书写”;反之,以社会民众为对象的历史书写,便是“小历史书写”,其可再分为个体史如传记、组织史如家谱两大类。[12]
可以发现,黄仁宇强调的是归纳法下的“大历史”综合,而赵世瑜和钱茂伟着眼的是地方个人的“小历史”分析。尽管三位学者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在区别“大历史”“小历史”的基本思路上仍存在一定共识,用黄仁宇的话说,正是“宏观与微观亦不过放宽视界与计及精微之不同”[13]。
(一)“大小历史”和“嫁接”的定义
我们在前文中将鬼传说依实名程度划为“显性”“中性”和“隐性”后,以其情节悉由现实生活、虚构时空和艺术手法共同组成的观点为基础,并借鉴史学诸家关于“大历史”和“小历史”的概念。据此,笔者以我国当代“显性鬼传说”为主要研究对象,进一步提出“大小历史”和“嫁接”的概念。
鬼传说中所指涉的“大小历史”有广狭之分,首先,广义的“大小历史”为基本原则,是绝对意义上的大小区别,完全依照所述内容的宽窄和精微程度而定:“大历史”,指国家史、政经史一类,多见于官方编订、学界推广的通行正史、名人传记、各级教材中,是广为人知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主流文化常识;“小历史”,指区域史、社会史一类,多见于民间知识分子的文字记载、地方传媒的新闻报道或邻里街坊的口耳相传,随时间推移会渐为当地人所淡忘,外地人则多无从知晓。其次,狭义的“大小历史”则为弹性但书,为语境意义上的大小区别,视所处时空、文本内容、参与人文化水平等条件的变化,以及各历史事件间的关联程度,“大小”的判断标准存在伸缩的弹性,其虽不全然按广义“大小历史”的划分方式,但仍会谨遵广义的基本史观。比如,“1988年3月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等代表性事件[14],多被视为“大历史”,但此类史事与上引北京鸿福宾馆“显性鬼传说”的“小历史”—1988年8月5日发生火灾,烧毁建筑面积达2620平方米,烧死1人,损失近45万元[15]—似乎并无直接的逻辑关系,这便属于绝对意义上的“大历史”,语境意义的“大历史”则应与鸿福宾馆在近现代几经易名和更改用途相关[16]。换言之,在鬼传说中,广狭二义的“大小历史”是并行不悖的,且“大小历史”的合称正是为体现“大历史”和“小历史”在鬼传说中本为一体,为人民群众集体性的历史,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因果关系,并无雅俗高低之别。诚如赵世瑜所言:“历史本来就是一个,就像生活本来就是一个那样。”[11]10
“嫁接”,指民众以鬼传说对“大小历史”进行联想、附会、填空与融合的一种叙事现象。比如北京鸿福宾馆“显性鬼传说”中将主角半夜遭遇诡异客房服务的经历和宾馆曾发生火灾的史实进行组合便是典型的“嫁接”。通过“嫁接”,鬼传说对“大小历史”的纪实性会起到一定的稀释作用,同时“大小历史”也能为鬼传说提供事发背景的史料依据。
“大小历史”的“嫁接”现象主要呈现载体为“显性鬼传说”,“中性鬼传说”次之,“隐性鬼传说”再次之,使用频率和实名程度成正比。
(二)案例—台湾矿坑“显性鬼传说”
以基隆清溪矿坑“显性鬼传说”为例:
曾华超是矿工的儿子,从小家境清贫,为贴补家用,他上学之余需和父亲一同工作。
某天,曾华超在矿坑看到一名中年矿工在哭泣,便上前关心。那名矿工说自己妻小都病了,却没钱看医生。当时只有十几岁的曾华超允诺出坑后会借钱带他家人去看病,矿工一听立刻向他磕头致谢。下工后,曾华超向亲戚借了三百元,找到了地址,便带矿工的妻小去看医生。看完诊后,矿工妻子问他怎么会知道他们需要帮助,曾华超如实以告,矿工妻子大惊:“我先生是矿工没错,可他已死在矿坑两年多了!”曾华超才恍然大悟,但隔天仍照常下坑工作。尔后,矿工一个月会出现两三次,指点他哪可以挖,哪不能碰。
玄的是,该矿坑不久便发生大灾变。曾华超仍记得矿灾发生的前两晚,鸡鸣狗吠,声音凄厉,令人毛骨悚然。矿工们虽感觉有一股不祥之兆,但为了生计,事发当天仍都硬着头皮下坑。因为那天中午曾华超的父亲已答应要替人办宴席,便要曾华超一起来帮忙,于是父子俩便提早出坑。没想到他们刚回到坑口,就听到身后一声大爆炸,五十一名矿工,四十九人罹难,曾家父子成为幸运的唯二生还者。曾华超认为,他们父子能逃过一劫,该是那名矿工冥冥之中的保佑。事后,曾华超仍下该矿坑工作,但再也没见过那名矿工。[17]
这篇“显性鬼传说”在台湾广为流传,在基本的情节框架下,坊间亦流传不少异文版本,比如有的会明确交代矿灾的日期是1971年12月14日,地点是在基隆清溪矿坑;[18]或介绍事发时曾华超仅13岁,且父子出坑的原因是亲戚来电话,[19]等等,对传说整体并无实质影响。文本的主体部分是主角曾华超援助已故矿工家属和死里逃生的离奇情节,“嫁接”的“小历史”则为1971年的基隆矿灾。据史料载:1971年12月,基隆煤矿公司清溪坑因瓦斯爆炸造成矿工死伤,矿方未对矿工遗属有任何抚恤,引起不满。后经协调发放抚恤金。[20]74
由此可知,该传说悉以史实为背景加工创作而成。不过该文本的“大历史”是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对台湾煤矿史需有初步的认识,约略可分为六个阶段:
1.1945年至1953年,光复初期,为提供省内工商复苏之能源所需,省政府采取了鼓励及辅导增产措施。
2.1954年至1956年,台煤产量已超过200万吨,且逐年增加至250万吨。
3.1957年至1961年,为支持经济建设计划,省政府对煤矿展开大规模探勘和开发,此期间年煤产量已达420余万吨。
4.1962年至1972年,省年煤产量已突破500万吨,而此时国际廉价石油进入市场,省内工业和经济迅速发展,自产煤炭供不应求,省政府遂鼓励以油替煤,发布低油价政策,台煤遭受打击,收坑者甚多。
5.1973年至1983年,1973年10月,爆发第一次世界能源危机,自产能源再次受到重视,省政府颁布“当前煤业政策”以鼓励煤矿恢复增产,而产量已受影响,光景不再且逐年下滑。
6.1984年至1998年,1984年下半年连续发生三次重大灾变,此后无论生产量、煤矿矿数、矿工人数均逐年大幅下降,加上“收矿政策”,台煤快速走入历史。[21]160
台湾在光复后的半个世纪里,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在此过程中,煤炭是唯一稳定的自产能源,为经济起飞的重要幕后功臣。1968年以前,台煤供应省内约60%的能源需求,包括火力发电厂、火车铁路运输、水泥厂,等等,不仅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更提供了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以1967年为例,矿工数达5.8万余人,连同产业相关就业人数共8.1万人左右,若以每户5口人计算,即有超过40万人仰赖煤业生活。[20]179-180尽管煤矿业对台湾的经济发展功不可没,但本质上它仍属高危行业,1946年到2001年间,省内因矿灾的死亡人数就有4042人。[20]116-120其中,1984年6、7、12月,台北县土城海山、瑞芳煤山、三峡海山一坑煤矿,就分别发生煤尘爆炸、坑内火灾等三次重大灾变,死亡人数达270人之多。[21]159
综上所述,对基隆清溪矿坑“显性鬼传说”而言,广义的“大历史”当为台湾光复,狭义的“大历史”则为省内各项鼓励措施、经济建设计划及国际廉价石油进入市场。虽然这两类“大历史”在文本中只字未提,但却和1971年清溪矿灾的“小历史”一起构成“大小历史”,再搭配“嫁接”使这篇“显性鬼传说”成为民众视角的历史解读。
(三)见微知著的“大小历史”
鬼传说在“大小历史”的编排上,和一般由大至小的史实讲述习惯相左,也和常见的历史书写多忽略“小历史”的情况有所不同。鬼传说是以小窥大,多先聚焦“小历史”,再逐步推进至“大历史”,甚至对鬼传说而言,“小历史”的重要性有可能会远大于“大历史”。比如前文的北京鸿福宾馆和基隆清溪矿坑两篇“显性鬼传说”,二者的“小历史”分别为发生于1988年的火灾和1971年的矿灾,而这些“小历史”和文本的主要情节有着直接关联,讲述者可以不交代我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政经变化的“大历史”,但若省略关键灾情的“小历史”,这两篇鬼传说在取信于人的程度上便会有所削弱。
因此,在鬼传说中,除存在“大小历史”均完整交代的情况外,还常见对“小历史”巨细靡遗地介绍,却将“大历史”隐而不显、默认阅听人均心知肚明的现象。如基隆清溪矿坑“显性鬼传说”便是典型案例,文本中虽只交代“小历史”,却能唤醒民众对相应“大历史”的印象,即便我们说不出台湾历年“煤矿业”的诸项政策,也可能讲不全当时“经济计划”的所有举措,但对“经济起飞”“亚洲四小龙”这些“大历史”仍会有基本的认识,无形中便成为心照不宣的文化背景,这正是鬼传说见微知著的叙事功能。虽然“大历史”有时在鬼传说中不会被提及,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文本背景的理解,对叙事效果也不会造成颠覆性的影响。因为“大历史”的作用无处不在,它紧紧包裹着“小历史”,由此形成一种强大、坚韧的叙事张力。不仅促使鬼传说形成了一种表面割裂,但内核却紧密相连的状态,更确保文本立足于“现实生活”的根基屹立不摇。换言之,无论鬼传说的内容表述如何变化,“大历史”始终和“小历史”作为“大小历史”的集合体共同藉“嫁接”来维系情节的内在逻辑。
由于鬼传说强调的多为“小历史”,依据广义的“大小历史”概念,“小历史”有别于侧重政经话题的“大历史”,其更关注民众的生活日常,故一般官方正史较少记载。比如基隆清溪矿灾“显性鬼传说”,其中于1971年发生的矿灾“小历史”,笔者推测可能正因该矿灾的伤亡人数、损害规模、事故原因等均未具特殊性,故该矿灾在相关行业志书中,不是未见记录,便是一笔带过。但经由鬼传说的传播,这段原先湮没在“大历史”中的“小历史”反倒更广为人知,鬼传说于此成为历史书写的合宜载体之一。因为鬼传说中的“大小历史”均为可考据的史实,故情节中融入“大小历史”的鬼传说不仅在记录庶民生活、保留时代现象、传承传统文化的功能上格外突出且重要,还能发挥鉴古知今的作用,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对当下社会亦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四)同类相吸的“嫁接”
从“双影”模式中可知鬼传说的情节是由“现实生活”“虚构时空”和“艺术手法”共同建构而成的。而进一步说,“大小历史”是“现实生活”的组成内容之一,且无论“大历史”或“小历史”均格外强调国族集体性。“大小历史”的“嫁接”对象鬼传说则兼具“现实生活”“虚构时空”和“艺术手法”,故即便不具备“大小历史”,本身情节和逻辑也已完整,其强调日常琐事、无名氏的个人性,包括生活经验、文化知识、新闻报道、影视作品等均为虚实情节的素材来源。不过有别于“大小历史”的忠于事实,鬼传说中“现实生活”的内容多具无从考证或经多次改编、重组的特征。
“嫁接”一词无论对鬼传说或“大小历史”来讲,均是对其本身内容进行扩充、延展之义。在本文的语境里,“嫁接”借鉴当代惯用词意—“剪取母株上的一段枝条或一个芽,接到另一植株上,使接合成新的植株”[22]。意即两个本质不同但具一定亲缘关系的植物,因组织和肌理结构彼此相同或相近故能结合为一体。关于历史和传说的争辩,史学家和民俗学家虽众说纷纭,然二者存在共同点却也是学界共识。[11]99在承认历史和传说的本质相近后,二者的“嫁接”便成为可能。对“大小历史”来说,“嫁接”鬼传说不仅是参杂了风格迥异的内容并拉长叙事的长度,更着实丰富了历史事件的理解视角和记忆方式。当我们分析鬼传说的史料价值时,实是针对文本中涉及“现实生活”的部分立论的,因“大小历史”和鬼传说各自均程度不等地记录世事,故二者都应予以关注。如此看来,鬼传说中“大小历史”的“嫁接”现象,不失为一种关于史实的民间艺文表现形式。
需要注意的是,因“显性”“中性”和“隐性”鬼传说均可独立成篇,故无论是否“嫁接”“大小历史”,其叙事逻辑的稳定性都能自给自足,比如前文所引的上海某公园“中性鬼传说”和农村“隐性鬼传说”二者皆完全没使用“大小历史”,但仍能成功营造真实性与恐怖感。即便是北京鸿福宾馆“显性鬼传说”,倘若将文中涉及“大小历史”的部分删去,显然对文本的叙事效果也不会造成根本性的影响。“显性”“中性”和“隐性”的判断标准,悉据文本中与主要角色和情节直接相关的背景信息的详略程度而定,和是否具有“大小历史”也无关。换言之,“大小历史”对鬼传说而言是非必要的情节配置,视叙事的需求可弹性地“嫁接”,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鬼传说在“嫁接”时,因杂糅使用断简残篇、道听途说的传闻轶事,若尺度把握不当,容易模糊文本内部的因果关系和事实真相,使“大小历史”失焦甚至失真,从而让人忽略其史料价值。事实上,若二者比例搭配得当,“嫁接”可为“大小历史”增添戏剧性和娱乐效果,避免后者流于史书或新闻的条列式记载,从而引起人们的传播兴趣,使“大小历史”能真正历代流传并持续地为民众所铭记。就像施爱东说的:“民间传说‘历史文学化’的处理方式让历史变得生动有趣,‘文学历史化’的实际效果又让历史变得丰富完整……”[23]
三、小结
中国地方史的叙述,长期被置于一个以抽象中国为中心的框架内,导致许多本土性知识的流失,比如广东这类“边缘”地区。[24]事实上,即便如京沪港台这些处于“中心”的地区,其地方文化和庶民史也常湮没在“大历史”中,不为世人所知。庆幸的是,“区域社会”必有一套自己的历史观念及书写历史的方式。[25]王尧便认为通过传承和改造传说来重述本族历史、宣扬族群特性,已成为社区和族群建构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26]鬼传说显然也是地方民众赖以传承历史的方式之一,但鬼传说和一般区域社会史所关注的乡镇、亲缘、行业的口述史不同,因为鬼传说的主要功能并非记录特定地方、氏族和行业的发展连续性,而多是呈现个别、零星、片面的“大小历史”,故其保留下来的史料,恰恰是一般学科专著和民众日常生活中,甚少留意的、游走在遗忘边缘的琐碎环节,而这正是我们欲全面理解中国史时不可或缺的那片拼图。换言之,鬼传说中的“大小历史”与社会大众息息相关且影响甚巨,这或许也是鬼传说能历久弥新、广泛传播的动力之一。
正如托尔斯泰所说,世事如行星相互运转,举一而反三,彼此互证。①转引自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九州出版社2019年出版,第6页。若无“大历史”的发生,就不会出现“小历史”;若没有“大小历史”为背景,有时也无法催生出可“嫁接”的鬼传说;而缺失了鬼传说,“大小历史”便和一般的史事纪要无甚区别,更和民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叙事无关了。“大历史”和“小历史”之间是这样,“大小历史”、鬼传说和“嫁接”之间更是如此。《万历十五年》的英、法文版由富路特作序,其中一段译文为:“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将来的警戒。但同时也要忠告读者,保全有价值的事物。”[10]303-304鬼传说中的“大小历史”均为真人真事的史实,是集体性地追忆过去;而鬼传说虽多为无名氏虚实交融的艺文创作,但其中“现实生活”的部分却不失为是对现世的摹写,是个人性地直面当下。如此说来,鬼传说的“嫁接”现象还具有继往开来的文化作用,值得我们正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