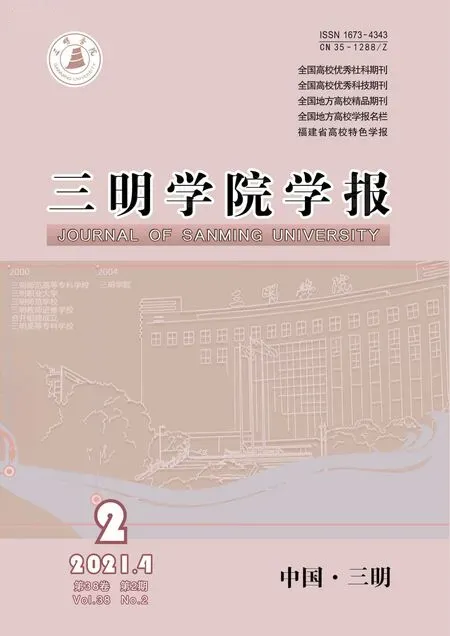大众文化视野下真人秀节目的解构与建构
——以《乘风破浪的姐姐》为例
2021-01-31王海刚
王海刚,陈 冉
(湖南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2018年被誉为“中国偶像元年”,随着《创造101》和《偶像练习生》两档节目的制作播出,内地选秀节目正式进入男/女偶像团体选拔时代。此类节目短时间内以星星之火掀起燎原之势,制造出一批批年轻偶像。到2020年,爱奇艺、优酷、腾讯的八档选秀节目已经向市场输送了800多名偶像,创造出巨大的经济利益。因缺少成熟的运作模式,绝大多数偶像在节目结束后只能面临没有通告的尴尬境地,最终泯然众人;观众也对模式化的节目和脸谱化的偶像产生审美疲劳。
正值此时,芒果TV推出的女团成长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却以黑马之姿闯入观众视界,从立项到开播热度不断。在未提前进行具体时间宣传和微博热搜暂停一周的情况下,第一季节目低调开播。在上线不足24小时内便登顶“猫眼综艺热度榜”第一,播放量突破2亿次,豆瓣评分达到8.6分。《乘风破浪的姐姐》突破传统选秀模式,将大龄女性作为焦点,以“三十而骊,青春归位”为口号,召集30位“30+”的女艺人,通过3个月的培训与比赛,在专业制作团队的帮助和观众的投票选拔中,最终优选五位“破龄成团”。节目通过构建独立、成熟的多元女性形象,展现大龄女性的风采与力量,引发了媒体和大众的广泛讨论,话题热度节节攀升。
一、文献综述
真人秀一直是娱乐节目中的常青树,深受观众的喜爱。2000年广东卫视推出的《生存大挑战》开启了真人秀的本土化历程。随着国内真人秀节目热度和影响力的提升,学界也开始了对真人秀的研究。
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探讨真人秀在国内的演进过程及形态变化,与国内外同类型综艺进行对比研究。早期国内真人秀创新力度不足,抄袭、模仿现象严重,节目形态以户外冒险和选秀节目为主。当下,本土原创真人秀节目成为市场主流,节目类型也扩展至旅游、亲子互动、婚恋、职场、历史文化等领域。网络综艺成为真人秀的主力军,爱奇艺、腾讯、优酷、芒果TV等网络平台推出大批具有影响力的节目。二是从真人秀的制播流程出发,研究影响真人秀制作的各类元素,涉及节目的叙事结构研究、节目传播策略研究、嘉宾的形象构建、主持人价值评估等方面。随着“她文化”的崛起,以女性为主角的综艺数量增加,“她综艺”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成为普遍研究课题。三是真人秀的“真实性”研究,结合节目的叙事技巧、人设打造来探讨节目塑造的“拟象”与现实社会的偏差。“在真人秀中,‘真人’的存在是前提和表象,但本质却是‘秀’。但其本身却是一个以消费为主旨的商品。”[1](P55-56)四是运用社会学、传播学相关领域理论探讨真人秀所反射的社会现象及引发的社会效应,对真人秀节目进行批判分析。如从媒介批判的视角分析真人秀对女性形象的构建,过度化娱乐的设置加剧了女性角色的符号化。
作为大龄女性选秀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是文化工业与女性意识碰撞的产物,具有天然的话题性。本文从大众文化视域出发,结合女性主义理论解读《乘风破浪的姐姐》节目文本,剖析节目背后隐含的消费社会商品生产逻辑。
二、真人秀节目的文本叙事
(一)解构文化工业标准,建构多元女性形象
1.抵抗年龄规训,消解年轻崇拜
“在这个女性主义维权的时代,男性还是心仪于女性萝莉般的身心,因为小萝莉容易受伤,柔弱无助,不那么让人感到不安。真正让人不安的是熟妇的身心。”[2](P87)作为权力与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文化工业自然而然地以男性的眼光塑造、传播女性的审美标准与价值标准。由此,当下的文化语境充斥着对“青春感”“少女感”的崇拜,“衰老”缺席。中年女性成为媒介环境中的异类,被迫失声。逐利的娱乐圈则将这一现实放大、明显地表露出来:年轻崇拜之下,众多中生代女演员陷入无戏可演的窘境,只能以单薄的配角出现在荧屏上,此时同年龄段的男星还在演着“霸道总裁”与软萌少女对戏。同年龄男女明星身材对比更为惨烈,男演员发胖是可爱,女明星发胖随之而来的便是源源不断的负面报道。
“大众传媒对人体审美化具有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通过制造偶像的方式来完成的。即是说,通过生产出特定时代和文化中为公众趋之若鹜的人体偶像,来塑造人们的理想自我形象。 ”[3](P336)作为偶像工业的典型商品,女团则将青春与少女发挥到极致。回顾近几年大火的女团形象——韩国女团F(X)、少女时代无一不是拥有完美身材、精致容颜的甜美少女,即便是虚拟偶像(如洛天依)都是以少女(萝莉)的形象出现。女团以女性身体为消费品,其标准化、模式化的“偶像”生产即遵循了父/男权制社会下“白瘦幼”的审美需要,“青春”成为女团的最大卖点之一。由《青春有你2》出道的女团THE9是近几年出道的年龄最大女团,平均年龄为24岁。这是普通人刚刚大学毕业步入社会的年纪,但是在娱乐工业的标准里,24岁的女偶像已经不受市场欢迎,无法创造更多的利益。成团后,便有媒体将THE9称作“大姐”团,唱衰团体前景,媒介对女性的年龄歧视体现得淋漓尽致。
正如约翰·费斯克所说,被主宰、被规训的大众并不总是被动的、毫无抵抗力的,被规训的大众会采取规避策略和游击战术与主宰力量周旋,并从中获得精神满足。随着女性性别意识的增强,女性开始寻求更大的话语权力和表达空间,媒介中充斥的年轻崇拜遭到抵抗,我们愈发渴望看到成熟女性绽放自我。《乘风破浪的姐姐》选择了30位30岁以上的女明星,年龄最大的伊能静已经52岁,这已经颠覆了女团的年龄标准,对年轻崇拜提出挑战。
2.抵制媒介刻板印象,解放女性身份符号
作为文化工业的产品,“明星”具备鲜明的商业属性,“人设”是其卖点,以满足受众需求为目的,吸引受众为其买单。由人设构建所带来的粉丝经济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利益。然而,人设就像一个面具,将诸位明星真实的喜怒哀乐掩藏起来,每一个明星都成了“套中人”。偶像工业的标准之中,女团的人设都是乖巧的,不可以锋芒毕露,不可以直抒胸臆。即便是虞书欣的“小作精”也是在观众心理红线内的个性展现,只会加深观众对她的喜爱。《创造营2020》的陈卓璇因接不到广告而发出疑问“是我站得不够高吗”,却遭受了“群嘲”。
与“妹妹”们毫无缺点的乖乖牌相比,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却在摒弃标签与人设,不畏惧人设崩塌,不畏惧缺点暴露。正如其主题曲《无价之姐》歌词所传达的那样,“一顿刻板的开场再议议男友和裙妆/千人一面 万人一腔/少女感高仿 雕刻标准形象/保持独有的锋芒 尤其遍地已偶像/狂我的狂妄 荒我的荒唐/打翻青春的鸡汤 管你的脸方不方 ”。宁静直白的“那我这十几年不白干了”,在社交网络引起热议,没有网友嘲笑其自大而是纷纷表示赞同。张雨绮的“我说帮什么帮,我们自己这里还一塌糊涂呢。我就要站中间……”,不仅不让人讨厌,还因为直爽更加让观众认可。黄圣依录制节目太饿找工作人员要牛奶、要零食虽受到争议,反而使“少奶奶”的名头传得更响。蓝盈莹自称是 “狼性女子”,节目中她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和欲望,也接受了来自网友的一大波支持。节目中姐姐们敢于和节目组叫板,敢于质疑评委,在冲突碰撞之中释放真实个性,打破了标准化的面具,让“野心”和“欲望”复活。
因此,当评委杜华用“青春靓丽、整齐划一”等女团标准评价各位“姐姐”时,遭到观众的强烈批评。对于以杜华为代表的偶像制造工业来说,这是他们摸索出的可复制的成功准则,简单有效;但是对于观众来说,他们对文化工业强制输出的这套游戏规则和畸形的评判标准已经抱有强烈的抵抗情绪。无可避免地,《乘风破浪的姐姐》成为了资本权力与受众文化斗争的角力场。资本进行意识形态的强力输出,受众也通过微观层面的意义解读活动,对其加以抵制和利用。而节目组的花字“仅代表杜华老师个人女团标准”,姐姐们对杜华打分的质疑则顺应了观众的抵抗情绪,观众在此基础上进行意义的生产,实现了对文化工业模式化标准和流量经济的解构,获得了暂时的胜利。
(二)建构女性主体地位,赋予女性话语权力
1.媒介形象再生产,获取女性观众认同
费斯克认为,快感是大众文化最基本的内部驱动力量和根源。大众快感主要通过规避(或冒犯)与生产两种方式产生。“规避就是对现存的权利、意识形态及其他社会规范的逃避;生产则是对对象的体验、认同。”[4](P61)
《乘风破浪的姐姐》作为一档真人秀节目,它提供的是对生活的“拟像”和“仿真”,就像一面镜子将真实的日常生活映射出来,虚拟的网络与现实社会混杂在一起。真实缺席的情况下,这种“超级真实”更具有真实感。在《乘风破浪的姐姐》节目组刻意营造的真实感的原生态剪辑吸引之下,受众会不自觉地进入节目建构的媒介景观之中,将自身的情感和经历投射到节目嘉宾与节目环节设置之中,进行自我情感的释放,获得心理满足与愉悦,也通过对嘉宾情感和经历的参与达到情感和身份的自我认同。
根据艺恩发布的数据,相比于 《创造营2020》,《乘风破浪的姐姐》的女性受众达到了82%,其中25岁至34岁的女性受众超过六成。25~34岁的女性观众或是初入职场,对复杂的职场生活和所谓规则无所适从;或是刚过30岁“门槛”,被催婚催育的焦虑包围,对之后的人生规划充满迷茫。《乘风破浪的姐姐》的出现给这些女性观众提供了打破焦虑进行自我确认的机会。如节目开篇的文案——“女人从母亲开始就是我们一生中 最早记得和最后忘却的名字/而每个女人 砺砺一生都在面对性别与年龄 生活与自己的锤问”,就将女性生活中受到的压制道出,引发观众共鸣。随着节目进行,有不少观众表示,相比其他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的代入感更强,看到姐姐们的生活状态就像看到了自己。观众在“姐姐”们开场社交的尴尬、表演前的紧张不安、练习遭挫疲惫的眼泪中,看到熟悉的自我;也在姐姐们说哭一起哭、敷着面膜唱歌、宿舍夜话讨论中,看到自己熟悉的学生时代。墨维援引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提出“自恋”的快感,指出:“婴儿会对镜中自己的影像产生认同和误认一样,观众也会对银幕上的‘自我’产生认同和误认。‘自恋’的快感则通过让观众着迷的方式,使其将银幕上的那些与自己具有相似性的客体认同为另一个理想化的自我。”[5](P131-132)观众在观看节目时,将自我形象(带着压制的欲望)投射到诸位独立、自信、成功的姐姐身上,在这种“自我认同”的基础上获得了愉悦满足。节目中一条弹幕——“有点不那么害怕变老了”——无意间引爆社交网络,也印证了这种效果。
也有不少观众通过解读节目中姐姐们的表现和互动将其投射至现实生活。如某条微博中,网友将黄圣依投喻为“嘴碎话多,爱指使人,家里能开建材厂的娇惯班花”,伊能静是“表演欲、证明欲和控制欲强,教了三十几年语文的妈精班主任”等,并称“每一个都是踩中普通人或成长路上会向其翻白眼的人物形象”。通过将各位姐姐解读为生活中的典型人物产生代入感,并对其所作所为进行价值观评判,宣泄情绪,获得共鸣的快感。
2.抵抗父权制度,赋予女性话语权力
《乘风破浪的姐姐》中权力反转带来的狂欢快感也是其广受欢迎的原因。在过去的选秀综艺中,我们看到的是参赛选手规训地服从于节目组与评委老师的意见安排,提出反对意见甚至可能会遭到攻击。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原本处于弱势地位的参赛选手与节目组所代表的无可置疑的权威地位的颠倒——伊能静在接受采访时对导演组说“不要让我配合你们”;郑希怡将三位评委定义为“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中餐厅》里“我不要你觉得,要我觉得”的黄晓明变成了“我是来伺候大家”的端水大师,频频为照顾各位姐姐心情而向评委使眼色;丁当在微博公开质疑评委杜华的评判标准;节目组与姐姐开会询问其意见,定时定点提醒吃饭,0.5倍速小心翼翼喊起床。在这里,资历深厚的“姐姐”们不必唯唯诺诺,相反的是代表着男权的“黄晓明”,代表等级秩序的“评委”与“节目组”要服从于“姐姐”的安排。
如此种种,将我们带到了巴赫金的“狂欢世界”。《乘风破浪的姐姐》节目成为狂欢的广场,舞台上下表演者与受众产生互动,场内外的观众跟着“姐姐”挑战权威、质疑赛制,与台上之人一起大笑、呐喊,宣泄自己的情绪,又通过投票表决的仪式实现加冕,现实世界森严的等级秩序不复存在,“人们在狂欢节上通过加冕、脱冕、化装、戴上面具等各种仪式,暂时地、象征性地实现自己试图改变地位和命运,拥有财富、权利和自由的美梦”[6](P21-27), 体验到了一种狂欢的生活。节目之外,节目组发起主题曲《无价之姐》舞蹈挑战赛,诸位姐姐、主持人黄晓明一马当先,响应挑战,随之该舞蹈风靡抖音、微博等各大平台。与此同时,观众又通过戏谑的方式对主题曲进行再生产,不同版本的《无价之姐》层出不穷。观众一旦点击、模仿,就参与到了这场全民化的狂欢盛宴之中。
三、消费社会的生产逻辑与女性主义话语的矛盾
阿多诺在《文化工业再思考》中说:“在文化工业的发展中,不断由文化工业贡献的东西,仍然是永远雷同的伪装;在所有变化的外表下掩盖着一个基本的骨架,这个骨架很少发生变化,就像利润动机本身自从第一次赢得了对于文化的优势以来就没有什么改变一样。 ”[7](P200)《乘风破浪的姐姐》固然打出了“女性独立”的口号,进行女性价值观的输出,但是依然没有逃脱作为文化工业产品的桎梏。现实中,对于节目消费女权的质疑也甚嚣尘上。细细观察节目,我们也能看出其依然走着“隐私窥探”“美色消费”的老路子以满足观众的“窥视”快感,其输出的女性价值观也频频翻车,所谓的“姐姐”成为了空洞化的标签,呈现出强烈的矛盾和撕裂感。
首先是对生活隐私的窥视。正如鲍德里亚所说:“后现代媒体社会是围绕着一条淫秽法则来运转的,这条法则导致了公共领域和私人空间的内爆。 ”[8](P25)作为真人秀,《乘风破浪的姐姐》构建的场景主要有舞台(演播厅)、练习室、宿舍,姐姐们的日常生活也都是在这三个场景里完成。而在这三种场景里遍布摄像头,简直就是“全景敞视监狱”的翻版,将姐姐们的生活隐私全方位地呈现出来,满足了作为监视主体的观众的“窥淫癖”。观众乐此不疲地想象女明星之间的明争暗斗,将姐姐们的一言一行放大、审查以佐证自己的观点。
其次是对肉体的展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迷恋青春、健康及身体之美的时代,电视与电影这两个统治性的媒体反复地暗示柔软优雅的身体、极具魅力的脸上带着酒窝的笑,是通向幸福的钢匙,或许这是幸福的本质。 ”[9](P165)作为真人秀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里自然不缺少对躯体的展示。观众跟随着摄像师的镜头,跟随剪辑师剪辑好的片段来“窥视”节目中的嘉宾。第一集开头,姐姐们下车来到现场,我们便跟随镜头对诸位姐姐的身体进行扫视,对其身材、样貌、穿着打扮等等做出判断。签到时,节目组安排姐姐选择的不同色号的口红并使用唇印签到,以典型的具有女性气质的物品模糊了女性主体的存在。纵观节目的赞助商、中插广告,其策划也遵循一贯思路,使用姐姐紧致的肌肤、诱人的肢体进行化妆品的展示。
女性价值的宣扬上,节目中所构建的女性角色仍旧是“被看”的具有女性气息的形象,其价值评判离不开身材与外貌。张雨绮总结诸位姐姐第一次见面寒暄的内容与样貌有关:“第一句就是你瘦了,你怎么这么瘦。”宁静对自己队员的要求是 “男人看了想娶,女人看了想成为她”,节目打出花字“静姐选妃”。节目组偷偷上线又匆匆删除的三分钟片段里“男人都是孩子”“男性引领女性”等话语背离了其宣扬的理念。舆论中,姐姐们的讨论也偏离了女性价值,“丁当太难了”“黄圣依说话”等热搜都与姐姐们的表演本身无关,对女性自我价值进行否定。此外,姐姐们所拥有的美依旧是主流认可的,并非我们所期待的经过岁月沉淀的阅历之美、沧桑之美。在观看节目时,观众之所以能对“30+”甚至“50+”的女明星真情实感地喊出“姐姐”,诸位姐姐不输二十岁女孩子的身材和样貌加了不少分。节目传达出也是“只有一直保持少女感,才能在三十岁之后还能被称作姐姐”。与其说姐姐们正在打破传统的审美标准,不如说她们以更高的自我要求顺应了这些标准。本质上,节目仍旧是为观众造梦,为女性贴标签。观众迷失在这场梦里,看似凝视着屏幕上的女明星,“却在不知不觉间通过自我规训的方式默然顺从了节目所宣扬的美学标准与行为规范”[10](P131-132)。 观众为姐姐们加油呐喊,称赞姐姐好飒,渴望成为屏幕上的姐姐,凡此种种又何尝不是规训的结果?
随着女性意识的崛起,“她综艺”近几年成为行业的新热点。此类综艺以女性情感逻辑为主导,围绕着女性的婚恋、职业、生活等方面展开,折射出当下社会普遍的女性价值观,引发广泛讨论。作为“她综艺”典型代表,《乘风破浪的姐姐》顺应了女性主义的社会思潮,为女性跳脱传统社会架构、解放女性身份符号做出有益的尝试。节目以“30+”的成熟女性作为叙事主角,让原本处于媒介边缘的中年女性受到关注,有助于缓解其年龄焦虑和身份迷思,唤起其自我意识和抵抗意识,完成女性主体地位的建构。但是,节目里人物造型、表演形式与传统女团并无差别,仍然深受偶像工业的影响。成团夜邀请大量男嘉宾做评判,其构建的女性形象,照旧遵循着父权制社会的审美标准,充满着男性凝视。节目文本背后遵循的仍是消费社会商品的生产逻辑,缺少对现实社会普通女性个体和尖锐性别议题的观照,所谓的“女性主义”与“抵抗规训”只是资本攫取利益的工具。
《乘风破浪的姐姐》的火爆开启了“她综艺”的新阶段,女性综艺节目进入井喷期。但是,如何在内容与形式上实现突破仍需深入研究。期待节目能够真正反映出女性的社会生存状态,展现女性魅力,避免成为资本的传话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