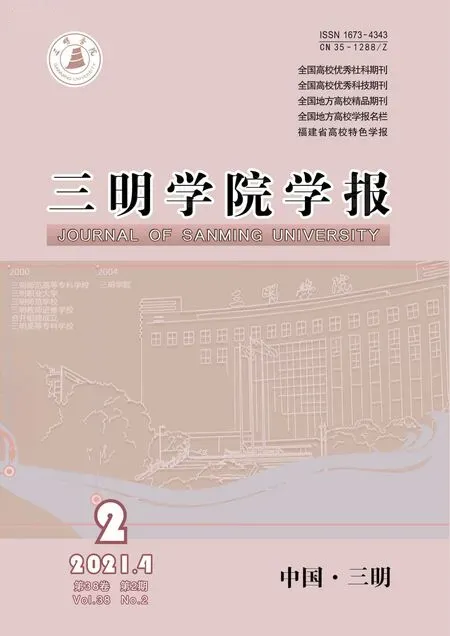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一体多元特征及其成因论析
——以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
2021-01-31肖艳平
肖艳平,胡 丹
(赣南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中国音乐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河南舞阳县的贾湖骨笛至今,中国音乐绵延了九千年的辉煌灿烂文明历史。这种从未中断的文明,以海纳百川的方式吸纳了来自各民族、族群的文化智慧。中国传统音乐是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传承至今的活态见证。在我国国家级等四级保护体系之下,在历次发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我国各级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立足当前所能见到最具代表性的活着的音乐历史。在民族国家的视域下,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具有中华文化 “一体多元”的特点,这种特点的形成又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
一、“一体多元”与中国音乐文化
“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是当前学界运用较为频繁的学术名词。它们产生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代表了两种视角,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中国社会文化的理念与思维。1988年,面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着复杂的族群关系,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次讲演中,提出中华民族具有“多元一体”格局。他认为应从中华民族整体性角度研究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存在规律。中华民族虽然具有多元特征,但是它具有文化与思想上的共性。费先生这个富有见地的观点逐渐得到众多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学者的认同。此后,学者们对此观点在历史发展中逐渐由多元形成一体的过程作了较多论述。近年来,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所形成的“一体”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学者在沿着国家既定“一体”的社会格局中研究统一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存在的多元性特征,同时关注多元性表达。在此基础上,学界又逐渐从这一视角延伸出文化领域的 “一体多元”新理念。[1](P51)就目前而言,关于“一体多元”的阐释与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领域,学者较少从音乐学角度阐释与关注文化一体多元特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在中华民族背景下的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共同创建的传统文化共同体,这已是学术共识。传统音乐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具备整体文化的特征,包括具有“一体性”特征。
中国民族音乐先驱王光祈曾将世界音乐分成三大乐系:中国乐系、欧洲乐系、波斯-阿拉伯乐系。其所指的中国乐系是以包含中国汉族和诸少数民族音乐的特征为基础。由此可以看出,从世界意义的角度来看,我国的传统音乐具有整体一致性特征。音乐学家王耀华对 “中国乐系”的内在特征进行进一步概括,他认为主要表现在:第一,音乐的带腔性;第二,音调组织的无半音五声性;第三,节拍节奏的灵活性;第四,织体思维的横向性。[2](P168-189)在这种整体一致性思维之下,因地域与民族的差异,在自身历史变迁与地理环境中也逐渐形成各自特色的地域与民族文化。
自2006年至今,我国颁布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简称“非遗”)名录,共有1709项入选。此外,各省、市、县颁布多批次的“非遗”名录,形成了庞大的项目库。在各级名录中,所入选的传统音乐类型均是在历史中传承而来,且具有活态性的特点,是立足当下能够看到的历史与传统,也是通过不同种类能够清楚看到我国的文化概貌。以我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对象,既可以看到中国音乐的历时性特征,也可以窥见跨地域的共时性特点。例如,以我国的民歌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同属第二批“非遗”名录中的藏族民歌、蒙古族民歌以及汉族的陕北民歌、湖北潜江民歌、重庆秀山民歌、浙江嘉善田歌、浙江舟山一带的舟山渔民号子等,均属中国乐系范畴,但在音列、旋律走向及节奏上都有不同的特点,彼此存在一定的风格差异。若仅以汉族民歌而言,南北之间也存在风格差异,豪放的北方民歌与婉约的南方小调各具特色。一体多元形式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特征。
二、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一体多元特征
(一)旋律形态的一体多元
五声性音调特征是中国音乐最具特色部分。在五声音列中,音与音之间以大二度、大小三度结构。在这种音调基础上形成宫、商、角、徵、羽五种常见五声调式,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共性特征。各地音乐也有不同,有些地方偏好宫调式,有些地方多倾向于徵调式。就以中国传统音乐的某一支脉来看,其中亦存在不同的特色音调结构,例如以荆楚支脉为例,其中包含三种音调结构:楚徴体系(以徴音为中心,由商徴宫以连续四度进行排列而成的音调体系)、楚宫体系(以宫音为核心,由宫角徴三音为骨干所构成的音调体系)和特性羽调式(自下而上的角、羽、宫、角、徴是骨干音)三种结构类型。这些不同的音调体系与调式偏好成为多元地域风格特征的基础。
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五声是中国音乐调式的基础。根据文献记载,在此基础上还存在“唯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的记录。在五声音调基础上,存在变宫、变徵、清角、闰等音级。黄翔鹏通过苗族民歌找到相应例证,认为中国在五正声基础上还存在九声音阶,文献的“九歌”即指这种音阶。[3](P3-7)在一般旋法中,五正声依然是骨干音列,而五正声外偏音成了旋律中必不可少的加花与点缀,形成音乐润腔的重要因素。正是这些看似并不重要的音调,使各地音乐独具特色,构成一体多元特征。
从乐器的视角看,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俗乐乐器是筝。古筝艺术被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在中国筝派中,虽然流派不同、风格各异、题材多元,但是不同流派、地域之间,存在相同、相通的一致性特点。例如分布于我国古代中原核心区的河南筝具有激昂豪放、铿锵有力的风格特点,与形成于齐鲁大地具有活泼灵动的山东筝风格具有明显的差异。然而,它们在乐曲上却存在诸多的共通性,例如河南筝母曲《天下大同》是具有典型河南风格的传统乐曲,然而在山东筝乐中的代表性乐曲是《天下同》,二者之间在演奏风格上看似差异明显,但是在作品调式、基本结构、旋律骨干音等方面均存在鲜明的一致性特征。如果说山东与河南在地理上存在关联,在文化上存在对应的关联性,然而处于中原地区的河南传统筝曲《天下大同》与分布于福建一带具有清淡儒雅、不施华丽风格的客家筝曲代表作品《出水莲》《崖山哀》之间也存在紧密的关联。在旋律形态上,《出水莲》与《崖山哀》的音乐主题均源自《天下大同》的主题音调,并在放慢加花的基础上发展而成。[4](P43)经过严密的形态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在乐器的流传地域、所属流派、表演风格上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在音乐旋律形态上存在明确的、一致性关联。可以这样说,从乐器学的视角看,我国的筝乐艺术具有明显的一体多元特性。
当视角进一步放宽到整个中国传统音乐形态的范畴之中,其一体意义下的多元特性也很鲜明。音乐学家田青说:“由于地理环境、社会背景、经济发展的差异,每一个民族都历史地形成了自己固有的思维性格和思维方式。与以复音音乐为代表的西方音乐不同,主要是单音音乐的中国传统音乐,体现着一种独特的线性思维。”[5](P58)从音乐特征看,中国传统音乐以单音线性思维为主,这是音乐织体思维中具有 “一体”性特征。然而,在广布中国大地的少数民族地区,单音性音乐并不是唯一的音乐特征,如侗、壮、苗、瑶、布依、毛南、仫佬、佤、傈僳、纳西、景颇、彝、高山、维吾尔、蒙古等民族均存在多声现象,多声性的复音音乐也是这些民族的重要部分。以侗族大歌为例,樊祖荫先生说:“其和声音程以三度(尤其是以小三度)与四五度为多,总体上呈现出和谐、亮丽的和声色彩。”[6](P36)此外,壮族的多声部山歌、贵州布依族多声部歌曲、汉族的号子、畲族“双音”、新疆麦盖提县的维吾尔族麦西热甫等歌种、乐种亦存在大量的多声性音乐现象。从音乐形态的角度来看,有些多声性乐曲也出现具有类似西方复调特征音乐特点,强调与注重纵向和声效果。然而,就某一个特定乐种与歌种而言,或以一个整体性区域音乐而言,多声音乐特征与复调思维并不是主流,其主要音乐思维依然是以单声音乐为主的线性思维。
(二)艺术意象表达的一体多元
禽兽花鸟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意象中的重要主题,是历代画家笔下表达的传统题材。在音乐文化中,禽兽花鸟也成为民间艺人们表情达意的重要艺术题材,是民间乐曲表达的重要主题。以禽鸟为例,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有大量的民歌,其中涉及的禽鸟达41种之多,既包含传说中的神鸟,也包括现实中的常见禽类。综观当下活态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仅仅以禽鸟作为曲名的例子俯拾皆是,从多个流派共同传承的古琴名曲《平沙落雁》到潮州音乐十大套曲之一《寒鸦戏水》以及广东音乐《鸟投林》,西安鼓乐经套中的 《雁儿落》《黄莺儿》和潮州大锣鼓的《双咬鹅》等,都把禽鸟作为艺术表达的重要主题与呈现意象。而且,在历史发展中,上述曲牌与乐器、乐种之间形成连带关系,许多带有禽鸟名字的曲牌成了特定乐种、乐器的标志性乐曲。此外,以民歌类“非遗”项目为例,禽鸟类民歌更是数不胜数,诸如灵动活泼的赣南客家民歌《斑鸠调》不仅作为赣南民歌的经典,更是江西民歌的重要标志性民歌;内蒙古乌拉特民歌《鸿雁》是游牧民族的经典创作,不仅作为蒙古族的代表,经过影视传播后更是成为老少皆知的传统歌曲,成为青少年心中对于蒙古族文化的民歌标识。此外,其他民歌类“非遗”项目中的禽鸟主题曲目更是比比皆是,如陕北民歌《一行行大雁》、贵州侗族大歌《布谷催春》、哈萨克民歌《云雀呀云雀》、彝族海菜腔《金鸟银鸟飞起来》等。上述民歌均作为一个区域(民族)的重要代表性歌曲。可见,在音乐艺术意象的表达中,我国各民族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相同的主题来表达民族情感与族群文化。
然而,将视角转向我国各地区音乐文化,对艺术意象表达的喜好的确存在差异性选择。以处于闽粤赣交界的客家地区为例,画眉鸟意象在该地区各种类型的“非遗”项目中出现,成为其中的重要题材,它出现在梅州客家山歌(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中,如反映对过番时期的民歌《画眉飞过别人笼》:“白纸写信红纸封,寄到番邦分相公;再过三年都么转,画眉飞过别人笼。”在广东汉乐(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中,也有风格鲜明的“画眉跳架”曲牌。在赣南采茶戏(第一批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的名剧 “四小金刚”《钓≧》中就有以画眉比喻人美心巧的特色化唱段。就客家族群而言,画眉不是一种普通的鸟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当地客家人文化自喻的一种艺术意象。然而,在我国西南边陲的傣族地区,孔雀是傣家人心目中的“圣鸟”,是吉祥幸福的象征。在傣族地区,以孔雀作为艺术意象的相关音乐舞蹈曲目较为常见,如《孔雀》《金色的孔雀》《孔雀飞来》《金孔雀轻轻跳》等。其中既有舒缓灵动的傣族民歌 (云南省第三批 “非遗”),亦有异域风情的创作歌曲,其最具代表性传统舞蹈亦是以孔雀命名的孔雀舞 (第一批国家级“非遗”);此外,在 20世纪80年代初红遍大江南北,在国际上屡获大奖反映傣族文化风情的电影《孔雀公主》也是以孔雀作为表达的意象。孔雀之于傣族就像是人民心中的神圣之物,以此作为重要艺术意象是传达对美好精神的向往与追求。其实,客家音乐中的画眉鸟与傣族音乐中的孔雀都是作为族群文化的重要艺术意象,均与历史地域特点有着紧密关联。从整体来看,它们虽然各具个性,然而却又同属于中国音乐文化乃至中国传统艺术中以花鸟禽兽意象为主题的一致性表达的范畴。
中国传统音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旋律形态是音乐构成的核心,而文化表达则是艺术呈现的目标。从当下活态的音乐类“非遗”项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音乐形态方面存在鲜明的一体多元的文化特征,艺术意象的传达方式同样具有相似的文化特征。总而言之,一体多元是中国传统诸类型音乐文化具有的共同性特征。这种特征的形成并不是偶然为之,而是有着独特的原因。
三、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一体多元特征形成原因
(一)地理特征产生的内倾型文化交流是形成中国音乐一体多元格局的基础
我国地域幅员辽阔,东部是漫长的海岸,在古代,大海被视为无法征服的神秘领域,“观于海者难为水”。大海实际上成为古代中国与彼岸交流的天然屏障。西部帕米尔高原,是东亚与西亚的自然分界,阻隔了两边文化的充分交流。西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把两个独立发展的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有形地分割开来,使两者未能充分交融。北部东起库页岛,中经茫茫大漠,西止巴尔喀什湖,与西伯利亚相邻。大漠之北原本人口稀少,加之寒冷的西伯利亚锁住了北部边疆。大海、大漠、高原、山脉遏阻了中国人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封闭性的地理环境中,逐渐形成了以语言、心理、经济和文化等综合因素为基础的生活统一体。[7](P121)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由于外界自然条件的阻隔,内部之间的文化交流就变得更加频繁。政治经济中心自然成为文化最终汇聚的中心。由于文化交流的内倾型,产生了向内部中心区域走向的趋势,因此在人们的心理趋势中也产生了倾向于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区域的内聚性心理倾向,这就为中国文化的多元环境中的一体性提供了基础。在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史中,产生了许多文化的交流,相比起与外部的交流,内倾型音乐文化交流远比外延性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密切。
在频繁的文化交流中,逐渐形成了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的融合,在此基础上逐渐由于共同文化产生对共同区域与国家的认同。从周代八音至当下种类繁多的民族乐器,大多数都是内倾型文化交流产生的结果。许多原本属于少数民族的乐器,现已是中国民族乐器中不可或缺的乐器种属。例如管子(古称筚篥、觱篥),它起源于古代波斯(今伊朗)。在两千多年前(西汉时期),流行于中国新疆一带,传入中原后,管子技艺得到丰富和发展,广泛流行于民间,成为我国北方人民喜爱的乐器,现在也成为我国民族乐队中重要的管乐器。此外,作为拉弦乐器的主奏乐器二胡也是如此,它始于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奚琴,现已成为民族乐队中最重要的拉弦乐器。
由于民族内倾型文化交流,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逐渐向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区域转向。边疆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向中心区域不断流动,在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逐渐形成中国传统音乐一体多元特征。
(二)中央集权为中国音乐一体多元格局的形成创设了制度性保障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文化本应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色。然而,在地理环境的包容与裹挟之下,尤其是在中央集权制下,中国音乐文化具有一体性意义。纵观中国历史,从中国历史准确纪年至今,统一的时期远远长于分裂对立的时期,大一统思想深深地烙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
在大一统的格局下,政治家注重对管辖范围的控制。以秦始皇嬴政为例,在统一六国后,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度量衡等,将各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面互通有无,促使统治区域内的交流更加密切。在此基础上,实行郡县制,统一朝廷命官,即使后来元代始设的土司制度,也是受朝廷之命。各地礼仪、风俗均遵国家制度。凡是在国家体制之中禁止的文化活动在地方文化中亦被禁,而中央所推崇的文化类型,各地方机关必须效遵。在各地州府县中,传达国家意志的各机构,同时也是统治者文化思想的传递者。各级机构的各级别乐营、乐户,其音乐代表了国家制度下的音乐礼仪,与礼制对应。在吉、嘉、军、宾、凶五礼中,音乐与之成配套。而这些制度下的音乐文化,正是烙上国家一统的文化符号。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这种统一的文化逐渐在民间文化中不断地沉淀,形成了中华文化特征。在当下的传统音乐曲牌中完全可以看到这种例子,例如流传全国各地曲牌“感皇恩”“朝天子”“沽美酒”“山坡羊”“傍妆台”“清江引”等,就说明它在制度下所形成的一体化倾向。在一体化制度下,形成礼乐与俗乐对应关系,而礼乐就是一体化制度下的典型代表。分布在各地民间的音乐,则由于民间地域文化因素的影响,在风格上又赋予其多元特性。
(三)历史上的移民为中国音乐一体多元格局的形成创设了条件
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原作为中华文明主要发源地的核心地带,开发较早,是居民的主要聚居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核心地位,人民在和平年代不断往政权中心区域迁徙,形成庞大的都城与大型城市。由边缘到中心的人口移民,使边缘的民间文化传播到政治中心,形成文化交融。
由于都城的繁盛,历史上的边沿势力及乱党对富庶的城市和广袤沃原垂涎不已。控制主要大都市就控制了政权,顺利完成权力转移。因此,由于战争的纷扰与政权的更迭,官宦巨族与普通百姓一道举家、举族迁离繁盛都市,在历史上形成迁散四周的移民大潮。客家就是一支为躲避战事或天灾而徙至南方的族群。他们将中原文化与生活方式带到南方,在客居地与原住民叠合交融,形成了文化特征鲜明的族群文化。作为具有离散特征的族群,客家族群至今依然流传“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之说,就是对处于传统深处精神文化的坚守。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文化往往是由优势一方向弱势文化渗透的过程。客家文化对闽粤赣地区的瑶、畲、苗族文化产生一定影响。在赣南少数民族音乐中,就有许多音乐包容着客家文化信息。例如江西瑶族民歌《文章考来十八洲》,无论从音调或歌词内容都与客家民歌存在极大的相似性。当然,在文化的融合中,客家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兄弟文化。以赣州客家地区的“九皇会”仪式为例,玉虚观正一道“九皇会”崇信主体也呈现出多民族性。除汉族客家道士、信民外,畲族文化角色也没有淡出九皇信仰及“九皇会”。可以说,九皇信仰经过在赣州漫长的流布传衍,已被畲客信众共同接受、奉祀,“九皇会”科仪音乐也成为畲客共享的音乐文化样式,起到了沟通、凝聚汉族客家和畲族崇信者精神世界的媒介作用。
中华民族的文化交融并不是一朝一夕之形成,而是不同民族在中华大地上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经历了一个漫长跨地域传播的结果。当文化与文化之间不断产生交融,作为文化核心区的文化随移民与不同时代的文化制度不断地传到边远地区。通过政权更迭、人口迁徙、商贾贸易等因素的推动,官府与民间之间、中央与边地之间进行了音乐文化上的内在关联。因此,在如此的历史动力综合联动之下,整个中国范围内逐渐形成一体多元的中华文化特征。
总之,中国音乐文化的一体多元性,在历史中形成,是一笔重要财富,也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中国文化的一体性具有同样的思想、意识形态与文化认同,这是文化的核心;多元文化则是因地域不同,形成不同表达与文化个性。这两种形式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蕴含“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林谷芳说:“欧洲可以分成二十几个、三十几个国家,但中国却保持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一种文化轨迹。如果没有一元性,不会合在一起;但如果只有一元性,又会缺乏适应性,在遭遇变迁时,文明就会覆亡。所以谈中国文明的长续永存,必须注意到这一元性与多元性并存的一个文化特质。”[8](P23)中国文化正是在一体多元的背景之下,文化之河才不至于出现断流,而变得气韵生动,展现出蓬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