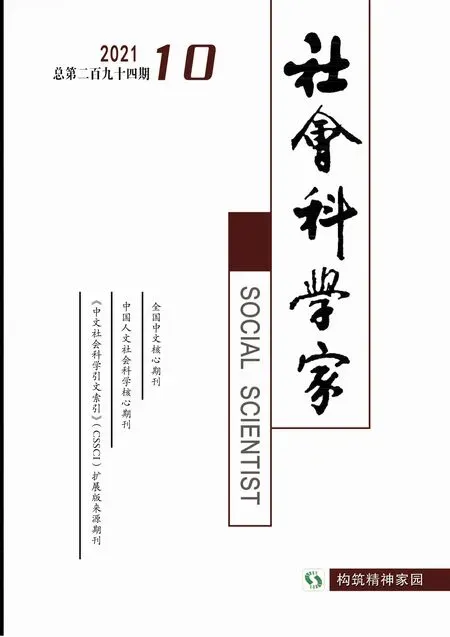互联网时代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
2021-01-30周大鸣
周大鸣
(中山大学 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一、引言
农民工这一概念,产生于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与城乡二元结构。最早的农民工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现代的二元户籍制度确立之后。20世纪50年代,部分厂矿开始招收农民工,农民工开始大量出现是在20世纪70年代,彼时的社队企业在乡村出现,大量农民工进入集体工厂工作。而农民工这一群体真正开始被学术界关注,要在改革开放后,这一时期人口开始快速地流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进入包括矿山、建筑工地、个体工商业等非农行业[1]。农民工是一个需要有历史维度认识,才能够进行深入研究的话题。现在严格意义上的农民工研究,大概经历了五十年。20世纪70年代的社队企业,就存在大量雇用农民工的现象,农民工们在公社与大队所办的企业即“社队企业”中工作,回生产队计工分。自知青运动兴起后,许多公社、大队利用知青的关系,办社队企业,承接国营工厂的零件加工、农机修理等。政府还普遍设有社队企业办进行管理,这些单位雇用的工人,可以说基本都是农民工。由于这些农民工很多是兼业型的,所以与过去的农村副业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并没有引起学界和其他领域的普遍关注。
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大量的劳动力从土地中释放出来,纷纷前往外地寻找出路。由此农民工开始成规模的出现。故而若欲真正地考察农民工的历史,应该至少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至今已逾半个世纪。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腾飞,与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是分不开的。截至本文撰写时,在中国知网以“农民工”为主题词进行搜索,能够发现7.34万篇文献,其中学位论文就有1.25万余篇。笔者曾基于过去的研究,提出了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形式的若干概念,如“散工”[2]等。可以说,改革开放后的前三十年,中国主要是依靠农民工的积累进行发展;但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后的三十年,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要依靠培训农民工才可继续前进。在进入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农民工将以何种面孔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何种贡献,是一个非常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二、农民工的多样性
农民工作为一个人口过亿的群体,常常被我们的社会污名化。农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地区,需要通过在农村普遍发展经济提高收入的方式治理贫困,然而事实上中国的农村贫困是结构性的,分散的小农要获得与城市工业化大致均衡的收入水平,在目前的生产方式与人口密度的条件下是很困难的。2020年中国已经消灭了绝对贫困,与此同时怎样将影响相对贫困问题的贫富差距有效地缩小,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重要问题。这便是解决不平衡与不充分的发展矛盾的重点所在。虽然我们一直以来希望通过农村的内源性发展来克服贫困[3],但真正依靠本地发展产业获得脱贫的农村,实际上屈指可数,外出务工一直以来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最重要手段[4]。
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现如今再将农民工作为一个单一的同质性人群是不合时宜的,在多年的发展积累下,农民工的内部也存在着大量的职业与阶层流动。笔者在十五年前就将农民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劳工型,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第二类是技术型,拥有一技之长可以通过技术获得更高的收入;第三类是经营型,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可以通过自己的经营获得收入;第四类是投资型的农民工[5]。我们在过去的田野调查过程中,了解到实际上大量的建筑公司都是一个壳,它们的内部实行的是分包制,建筑公司将绝大部分的工程分包给不同的农民工团队。工地上的工程机械,包括推土机、吊车、挖掘机,绝大部分也是属于承包的农民工团队的,而非公司所有,公司最重要的工作是做一个漂亮的标书,然后把它们分包给农民工们。笔者在湖南攸县调查时,发现一个镇里有7000多辆挖掘机,主要是服务于从深圳到佛山的整个珠三角核心区内部的建筑施工队,而其他镇也各有自己的特色工程机械,种类各异,仅挖掘机一项就能够形成一个产业链,它需要有运输车辆与其他方面的配合[6]。因此,农民工早已告别了作为一个单一人群的历史,只是我们还是抱着固有的思维将他们视为一个一成不变的群体。农民工内部早已复杂化,产生了大量的专业团队,在某些领域已形成了自身的产业链。
农民工如今的分布也十分的广泛,不仅在我国的偏远地区,甚至在国外在非洲都有大量的农民工走出去,伴随着我们的国企前往非洲进行工程的农民工超过百万之巨。在“一带一路”各国施工的中国企业,在营建基础设施项目时,基本需要从国内派遣农民工去当地进行施工,由于语言和其他一些因素,国内企业走出去还是倾向使用中国农民工。还有一些农民工在国外进行经营性活动,比如笔者指导的一位博士发现,在老挝遍布着湖南邵东的农民工经营的超市,在老挝开超市的邵东人约有三十万之巨。实际上“一带一路”在民间早有自己的实践,这是民间自发走出去的一个模式,现在从老挝万象每天都有航班直飞长沙,足见两地交往密切[7]。
所以农民工分布的地区与行业都很广泛,不能再停留于过去刻板的农民工印象,认为他们只是打工者、卖力者,这是片面的研究思路。实际上到如今,农民工真正仅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只剩下很少一部分了。十年前笔者在湖南攸县做农民工调查时,这一类农民工数量已不到外出农民工总数的20%,虽然可能存在一些地域差异,但是农民工中以单纯出卖体力为生的个体,已经逐渐不占主流了。在如今的时代,大量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主要从事技术性与经营性活动的新型技工,农民工这个群体一直在不断地转型与流动。在不断地变化的就业大军中,从事经营的与以技术谋生的农民工,他们的收入就相对较高,这批农民工在回流时,很少选择回到村里,而是更多地回到老家的县城买房,让孩子在县城接受教育,这些都会给过去的社会结构带来新的变化。再举攸县的例子,现在攸县的房价早已超过株洲市,经营类与技术类农民工回流的结果使很多县城的房价比管辖它们的地级市的房价要贵得多。这种情况现在在中国的中部地区相当普遍,当然这也是多因素造成的,并不是单纯与收入相关。现在很多的农村结婚习俗,普遍要求男方在县城置办一套房产,这也是重要的原因,这一现象在河南、河北等地区非常普遍,在河南的平原地区,如果一户人家没有在县城拥有一套房产,是很难娶到媳妇的。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所以房屋在中国的供不应求状态,主要是文化性的,是随着现代化所改变的习俗造成的。笔者在青海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当地农民都在县城购房买车,平常回到农村的最主要的目的,是领取扶贫的物品与补助。在这样的一个大趋势下,培训农民工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因为单纯出卖劳动力是很难获得与维持这样的消费的,单纯的农业也只能堪堪温饱,难有寸进,培养外出务工者成为一个掌握技术的农民工,势在必行。
三、互联网时代的农民工就业
如今,外卖骑手与快递小哥作为最接近我们的服务群体,吸纳了大批农民工。所以笔者认为,在互联网时代的农民工就业,与过去的就业有一定的差别。这个判断建基于新生代的农民工与老一代的农民工具有本质的差别,老一代的农民工进城打工主要是为了谋生存,生存是第一大问题,只要能够养家糊口他们就愿意做活。过去笔者用了“打工经济”这一概念去概括他们。因为在过去的江西、湖南、四川等地区,生计的维持是靠外出务工而不是在本地务农,因为在本地务农无法养家糊口,只能被迫外出打工,其实这在内地过去是普遍现象[8]。
但是新生代的农民工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求生存变成了求发展,他们的诉求不再是获得温饱,而是为了获得发展,可以理解成新一代农民工的中国梦。这一代农民工的主要特点,首先,是受教育的程度变高了,过去很多的老一辈农民工可能初中都没有毕业;其次,是对职业的期待也变高了,现在哪个单位的待遇好,农民工就会用脚投票转到哪里;然后,是新一代农民工对物质与精神的享受要求变高了,老一代农民工赚到钱以后,都倾向于存起来回到家乡起一座两层的小楼房,娶妻生子,而新一代农民工有了精神的追求,他们更加追求活得更精彩与体面[4];最后,新一代的农民工对于工作的耐受力也普遍降低了,笔者在调查中,雇用农民工的企业家总是强调现在的农民工比以前的农民工难伺候,动不动就“提桶跑路”,对于工作的忍耐能力与他们的前辈相比差得远了。
纵观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近期农民工就业曲线的变化稳定地在向第三产业转移,在2019年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51%,其中,从事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和住宿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均为6.9%。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48.6%,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重为27.4%,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8.7%[9]。农民工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从事建筑行业,而现在农民工大举进入第三产业,人数已然过半,显示出农民工的就业转移形式非常明显。当然还有“离乡不离土”外出务农的农民工,但那早已成为少数了,比如在广州附近种花的花农,大多是外地来穗的农民工。
目前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2020年的农民工有2.91亿,其中50岁以上的只占24.6%,40岁以下的农民工占了50%以上,这充分显示农民工已经完成了世代交替,它是以青壮年为主的一个队伍。按照广东省的1.13亿外来务工人口计算,新生代农民工所占的比例已经到了60%以上,虽然这个数据存在一定的争议,主要原因是农民工的流动性很大,统计数字不一定准确。整个中国的农民工情况还是比较类似的。农民工的数量根据每个地方的情况有些微的不同,西部的农民工增长速度在现在是要超过东部的,大概除了东北地区的农民工一直不成规模以外,全国的农民工群体都很庞大。比如2019年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有15700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54%。其中在珠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有4418万人。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有6223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21.4%。在西部地区就业农民工有6173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21.2%。在东北地区就业农民工有895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3.1%。
玉米粗缩病也称玉米条纹矮缩病,是由灰飞虱吸食叶片汁液后,使玉米植株中毒感染病。染病症状是:植株扭曲生长,有的植株发生矮化、节间缩短,呈丛生型(君子兰苗),叶色浑绿,叶片厚短而宽,硬而脆,密集丛生。背面叶脉上产生粗细不一的蜡白条纹突起,用手摸有明显的粗糙感,植株矮化严重,一般是在四至五叶片染病,一般不能抽穗,造成绝产,七叶片之后感病的植株能抽穗结实,但发育不良,减产幅度很大,因此玉米粗缩病是玉米生产上的指名病害。
新生代农民工大举迈入服务业的更重要原因,是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在大幅增长,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8.6%;数字经济增速达到GDP增速3倍以上,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动力。数字经济占中国GDP的比重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快速提高。中国的数字经济总量在全球的排名也稳居第二,增长速度稳居第一。中国的数字经济企业在全球前十已经占据了五席。过去我们的社会是人与物的双向结构,现在的社会已经成为人与物和信息的三元互动结构了,每一个人都处在人、物与信息之间成为这样的世界的一部分。在这样的世界里,社会结构必然要发生改变,所有的问题都需要重新评估。如今的经济都是以数字作为抓手,笔者在调研中深刻体会到了每一个地方的地方政府,在介绍地方经济时,首先提及的就是本地怎样发展数字经济,这不仅仅是一个潮流,更是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的体现。
高度发达的数字经济为新生代的农民工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前半程中,在国家强大的网络基础设施助力下,数字消费成为引人注目的前台,这也在就业端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方式。淘宝、美团、京东等大型电商平台的兴起,为物流业与依附于整个产业上的大量农民工提供了触网的机会。物流业的顺丰和“三通一达”,雇用了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这些众所周知的大企业,带来了整个数字产业链上丰富发达的私营小企业。而小企业集群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要远远高于大型企业,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新型的小企业容纳了更多的农民工。京东就是充分地利用了中国数量众多的农民工,建立了自己的物流体系从而使自身脱颖而出,因此也创造了众多的就业机会。过去纸媒时代《羊城晚报》等报纸能够迅速崛起,也是通过农民工建立了自己的整套投递体系,京东只是复制了它们的成功。可以说,谁懂得使用农民工,谁就能够在市场中获得成功。在中国经济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的过程中,农民工的就业也从制造业迅速地转向服务业,推进了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
以美团为例,外卖骑手作为一种新的就业形态,创造了巨大的就业机会,2019年,通过美团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达到398.7万人,比2018年增长了23.3%。外卖骑手作为一种新的就业形态,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在珠三角有大量的原来工厂内的农民工辞工转到了骑手的队伍中。在所有骑手中,男性骑手占比为93.3%;20~40岁骑手的占比超过83.7%;高中及以下学历的骑手占比超过82.0%①数据来自美团研究院。。这些骑手共同撑起了中国外卖行业的半壁江山。以珠三角为例,过去很多在企业中打工的农民工转到了外卖骑手行业,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在疫情期间,大量工厂工人转为骑手,也体现了互联网背景下农民工经济具有的极大就业弹性。互联网经济在农民工层面,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疫情所带来的就业危机。
四、产业数字化场景下的就业新模式
数字化社会中的就业模式,核心变化在于在数字化的链接下,新业态利用互联网的链接特征,让不同企业与工种通过互联网相互连接,实现人力资源与社会需求智能匹配,有助于解决人力资源的结构性矛盾。由于中国的经济模式中,大量人口属于兼业型就业,并不束缚在某一特定的行业中,人们除了主业以外,还会同时兼职其他工作,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打几份工。有时候人们的主业并不一定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这种情况现在被人们称为“斜杠青年”,笔者也曾玩笑地称自己为“斜杠老年”。
美团骑手中,兼业的比例是很高的,很多在其他行业工作的农民工,在结束主业后的用餐高峰期兼职骑手,既增加了收入也熨平了高峰期骑手供给不足的市场需求。数字时代,使得人的兼业更为便利,我们常见的除了外卖骑手和快递员之外,还有网约车等。在互联网时代,兼业成为一种很重要的模式,笔者曾在出差过程中,通过打车软件约车,结果司机是一位大型企业的管理人员,驾驶着十分高档的轿车。带着疑惑询问后得知,这一打车路线实际上是司机每天上下班的路线,他只是顺带做一单打车,既希望了解网约车的运行模式,又服务了需要打车的人,还能为自己跑回一点油钱,这种形式的兼业在如今的数字经济中,在大数据的算法之下,精准的资源配置成为可能。企业的生产程序分解与劳动力的组织,都可以在互联网的算法中实现,这是一种全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不是以单一的企业组织的方式进行生产,这个状态下的就业组织是需要重新评估的。个人通过闲余的时间从事自主多元的职业的状态下,这种职业模式是互联网为新的经济组织方式提供的机会,它能够将每个人的技能、知识与时间通过产业链合作充分发挥作用,创造价值。
对于农民工的调查与所有的社会调查一样,如果从社会最基层的调查开始做起,就容易发现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对淘宝村的研究,我们的研究者就希望从一家一户的产业选择开始探讨这个现象。结果我的研究团队发现,淘宝村的出现大多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很多的案例告诉我们,往往一个淘宝村的兴起,是村里的一户人家在某个行当的淘宝店获得了成功,他们又将整个村子带动起来进行产业的发展,就形成了一个淘宝村。现在阿里巴巴有计划每年要发展一定数量的淘宝村,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方式。
五、流动与链接
在审视如何在新的社会形态下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时,首先需要明白在这个时代需要关心什么样的关键概念。笔者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关键的两个概念就是流动与链接。我们流动的速度越来越快,链接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广州有一个超算中心“天河二号”,天河二号的负责人曾经向笔者介绍,“天河二号”之所以有那么快的计算速度在于它有32000个处理器,它是将这32000个处理器链接起来的平台。决定超算中心计算速度的最核心问题,是处理器之间的链接方式。过去是电子的链接方式,现在是使用光作为链接方式,将来会使用量子作为链接方式。所以在如今的时代,决定我们交流速度的最重要的要素是链接。人与人之间的链接,组织与组织之间的链接,都是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在互联网时代思考我们人类与社会怎样链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怎样将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链接起来,是一个问题。互联网的核心就是链接,它使过去社会中的单链变成网链,互联网的初心就是让一切在“网”,有了网链,任何一个节点的断裂都无法让全网停下来。新生代农民工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之下,最需要被研究的是他们是如何被链接起来的。过去的农民工可以被乡村的血缘与地缘链接,而如今链接他们的成为互联网,这是在社会组织层面上,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的最本质的差异。
数字化就业网链通过与产业物联网的联通有助于解决大规模生产、产业链复杂、需要大规模合作的产业发展问题。这一系统的出现,有助于降低组织运行成本,以产品为核心的生产组织形式能明显减少人员和设备的闲置带来的企业成本,提高产品的专业度。如果每一个大公司都接入了互联网共享人员和设备的信息的话,以后组织部与人事处这一类的部门还是否有在企业中存在的必要,都是需要重新思考的。每个人在大数据面前都是赤裸裸的,没有任何隐私可言。过去说“你永远不知道屏幕对面是不是一条狗”,现在变成了“你真的知道屏幕对面的是不是一条狗”。新的就业方式和生产组织方式必然带来企业的转型升级,珠三角地区企业的转型升级中这个问题被重点的关注。数字经济发展势不可挡,传统产业的转型也势在必行。劳动力的全网流动和配置,进一步地对农民工的技术专业化提出了更高、更细的要求。数字经济将会带来用工结构的调整:数字时代对普通工人的需求相对减少,对技术工人的需求迅速增加。这就是笔者提出后三十年需要以培训农民工作为经济继续发展的动力的原因。
珠三角的产业是由无数家中小企业构成的,过去是前店后厂的订单型经济。现在的数字化转型对这种模式的冲击很大,如果利用互联网的优势优化资源配置,整合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本优势和弹性生产优势建设全面的物联网体系,再通过培训农民工增加农民工的技术能力,适应更加专业的技术分工,那么面向未来的经济发展会更加具有竞争力。实际上这么做的本质就是把大量的小微个体,整合到一个大的网络中。过去我们在珠三角的传统中有非常多这样的实践,比如说遍布珠三角的专业市场,都是由无数的小个体与小企业组成的。
六、结语:数字时代农民工的双重移动
数字时代的农民工存在着双重移动的特点,一个是从乡村到都市,一个是从线下到线上。从乡村到城市,就面临着怎样获得对城市的认同感、怎样获得一种城市的认同方式,这两个问题。第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风格迥异,他们的城市梦也有所不同,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比老一辈更执着于留在城市。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务农的技术也没有务农的经验,他们不太可能愿意在打工若干年之后再回到农村,更不愿意务农。实际上他们即使想回乡务农可能也当不成农民了。相对于他们缺乏的务农经验,他们的数字素养却非常高。这样的状态下,他们留在城市不论是从内心的认同上还是物质技能上,都是最现实的选择。
从第一代农民工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历史演进中,可以透视社会转型所导致的文化转型。如今的中国社会,正在从地域性城市向移民性城市发生转变。过去我们的印象中,每一个城市都以讲某一种方言的人为主,但现在这个状态被改变了,现在的中国城市讲各种语言的人群都存在。这样复杂的移民城市,成为中国城市的常态。与此同时,中国的文化也在经历着一种从地域性文化向移民性文化的转变。进入互联网时代后,空间的限制变得越来越小,人们可以通过各种软件,看见不同时空中的各种人群的文化展演。在城市中可以看见很多乡土性的内容,同样在乡村也可以通过这一套技术手段看到城市里的生活。互联网使我们的城乡关系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农民工文化并不一定会被城市倡导的主流文化所同化,它们很有可能在网上寻找到一个新的空间。年轻农民工们借助互联网进入了一个城乡文化并存的网络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城乡之间的差别不再给他们身份的认同产生障碍,他们不会再因为自身携带的乡土文化的属性而被歧视。与此同时,借助网络他们可以更加自由地呈现自身所理解的都市文化和时尚。以往的城市化的研究中,城乡之间发展权力的失衡使得城乡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单方面地表现为都市文化的霸权,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这种关系被一个全新的场域重新定义。“农民工”文化并不必然被吞噬和同化,反而以一个新的形式成为农民工自身重要的文化标签[12]。
互联网提供了一个虚拟链接,在这里人们可以与全世界的亲朋好友进行链接。但我们可能会对周边的人们显得极为陌生。互联网所提供的虚拟链接虽然可以帮助农民工暂时脱离繁重的工作,克服空间上的分离所造就的困难并摆脱自身相对糟糕的生活处境,然而所有的网络关系的开展和维系都是以个人为原点的,它与真实的社交关系具有很大的不同。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交往关系中同质性极高,因此透过网络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可能性已然微乎其微。这样固化的阶层流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不对社会造成进一步的影响,至少笔者认为并不完全乐观。
过去的中国城市并不是一个疏离感与陌生感很强的组织形态,与美国城市社会学所描述的不同,过去芝加哥学派认为城市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中国的城市过去的制度是将农村的一套熟人社会的体系搬到了城市,本质上还是一个熟人社会,不是那种陌生感疏离感很强的城市。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进入移民社会的今天,可能真的要向一个陌生的社会发展了。农民工与都市居民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得越来越频繁和复杂,农民工甚至成为一个城市日常生活秩序的维护者,没有了他们,我们的生活会变得一团糟。技术的移动性和可获得性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越来越容易,然而社会的流动乃至阶层的跃迁并没有伴随着技术的普及而变得更加容易。
总之,新生代农民工在互联网时代的目标,并没有比在前互联网时代的老一代农民工更为复杂,实际上某种角度上看他们的目标变得更为简单。新生代农民工的终极追求似乎是人们不再将他们当成一个农民工,而是真正地将他们当成一个城市里的市民,这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归乡梦想有截然不同的终极取向。如果从这一点来审视我们的研究,就会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