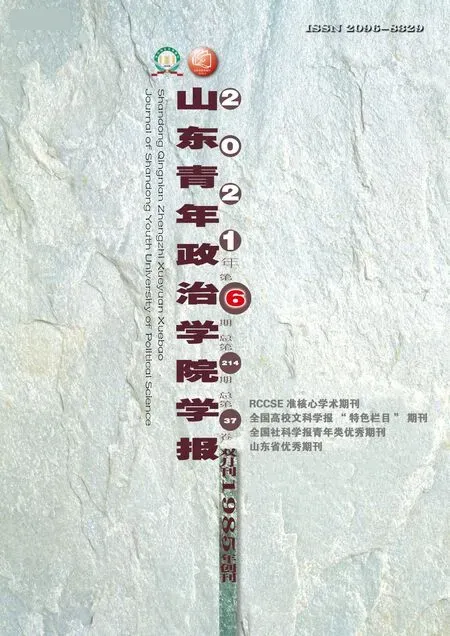王船山对宋易图书学及朱子易学的批判与新诠
2021-01-29嵇雪娇
嵇雪娇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济南 250100)
一、引言
开端于宋代的图书易学,朱震在《汉上易传表》中作了总结:“濮上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颐,程颢。”[1]朱震构造的传承谱系疑点众多,历来是宋代易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之一。但是,抛开传承谱系不论,他把宋易图书学分为《先天图》(以邵雍为代表)、《河图》《洛书》(以刘牧为代表)、《太极图》(以周敦颐为代表)三类,则得到了后来易学家以及现代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可。在朱震的传承谱系中,三类图书学共同源自陈抟——这尚未得到有力的证实。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三类图书学在朱子手中却汇归同流,成为朱子易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后世获得了准经典的性质。
明末天崩地解之际,学者们纷纷进行文化反思并诉诸六经,其中宋易图书学尤其与朱子经学体系密切相关的部分成了众矢之的,遭到了无情的批判。与大多学者的彻底否定不同,王船山对邵雍的先天易学进行了彻底批判,对周敦颐的《太极图》和朱子的《河图》《洛书》则进行了重新诠释。①
船山对宋易图书学的批判与重新诠释,基于他对易学史清晰而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孔子之后的易学史表现为“占-学-占”[2]的循环演进,均偏离了文王、孔子“即占即学”的易学宗旨。尽管船山强调占《易》与学《易》“二道并行,不可偏废也”[3],但更为重视学《易》[4]。因此,他对以王弼开端至程颐偏重“学”的易学史阶段持积极的态度,尤其表彰程颐、张载和周敦颐之易学。而对“占”的易学史阶段,则批评较多。在船山看来,邵雍的易学在易学史中无疑是属于“占”的,且“徒以占吉凶,而非学者之先务也”。[5]并且,朱子也是属于“占”的,他专言象占“与孔子《系传》穷理尽性之言,显相抵牾而不恤。”[6]至于《河图》,由于明确记载于孔子之《系传》,船山便作出了全新的诠释。
二、对易图书的定位与新诠
船山对《周易》的诠释以及其自身易学体系的建构,都有着强烈的经学意识,他认为:“《六经》一以夫子所定为正。董仲舒言,‘道术归于一,诸不在六艺之科者,勿使并进’,万世之大法,为圣人之徒者勿能越也。”[7]就《易传》来说,船山除了不承认《序卦》为圣人之作外,把《系辞》《文言》等都归为孔子的作品,因此这些文本中的说法就绝对不能够怀疑。而《河图》《洛书》恰恰就记载于《系辞》之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对船山来说,便有着绝对的权威性,只能去理解而非怀疑。船山对《河图》的诠释,一则致力于《河图》与《洛书》彻底区分,一则证明《河图》为伏羲画卦作《易》之所则。
(一)《河图》《洛书》之别
船山对《河图》《洛书》的看法直接承袭了朱子学的《河图》《洛书》观,即认为“五十有五,《河图》垂象之数也”[8],“《河图》之数五十有五……《洛书》之数四十有五”[9]。《河图》从数上来说,就是《系辞上传》的天地之数,其和为五十五。至于《洛书》,则为九宫图之数,其和为四十五数。
《系辞上传》中,“圣人则之”的既有《河图》又有《洛书》,但是船山认为,《周易》只与《河图》有关。在对《系辞上》“是故天生神物”一节的注释中,船山指出:
《洛书》于《易》无取。上兼言蓍龟。《洛书》本龟背之文,古者龟卜或法之以为兆,而今不传。说者欲曲相附会于《周易》,则诬矣。[10]
可见,船山是以蓍龟之别的角度,来区分《河图》与《洛书》,《洛书》为龟背之文,古代的龟卜可能与之有关,但是与龟背之文有密切关系的是《洪范》而非《周易》。船山持严格分判《河图》与《洛书》的态度,认为二者决不能混淆,比如他认为:
其以五行配《河图》者,盖即刘牧易《洛书》为《河图》之说所自出。《易》中并无五行之象与辞,五行特《洪范》九畴中之一畴,且不足以尽《洛书》,而况于《河图》![11]
按照宋代河洛易学的发展脉络,刘牧以五行配《河图》(五十五数,刘牧以之为《洛书》)的做法是最先出现的。而在船山看来,《河图》就是《系辞》天地之数五十五,具有经典的支撑而无可怀疑,《周易》经传中均不涉及五行之说,因此不可用五行来解说《河图》,刘牧之说是对经书说法的移易。我们知道,朱子河洛易学也对《河图》《洛书》进行区分,但是朱子同时又讲“《易》《范》之数诚相表里”,[12]“《洛书》固可以为《易》,而《河图》亦可以为《范》矣”。[13]互为表里的说法,是船山无法承认的。
分判《河图》《洛书》也就意味着《周易》与《洪范》的区别,船山认为:“《易》以知天,《畴》以尽人。”[14]而其原因则可以从数的角度进行说明,船山说:
乃其所以然者,天固于《图》《书》而昭示之矣。《河图》之数五十有五。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五位相得,而五十有五之数全。天无不彰之体,固有其五十有五而不容缺。《洛书》之数四十有五。四十有五则既缺其十矣。缺其十者,尽人之用止于九,四方四隅之相配,故可合之以成天,而必待人用以协于善。[15]
五十五数是天地之全数,那么四十五数就意味着“缺数”。数之全与缺不仅区分了《河图》与《洛书》、《周易》与《洪范》,而且就其本身是天与人、体与用的区别。但这并不意味着天与人、体与用的割裂。船山认为《洛书》可由人而合之于天,《河图》亦可由天而示于人,船山通过象数关系的分辨指出了这一点:
象数相倚,象生数,数亦生象。象生数,有象而数之以为数;数生象,有数而遂成乎其为象。……《易》先象而后数,《畴》先数而后象。《易》,变也,变无心而成化,天也;天垂象以示人,而人得以数测之也。《畴》,事也,事有为而作,则人也;人备数以合天,而天之象以合也。故《畴》者先数而后象也。夫既先数而后象,则固先用而后体,先人事而后天道,《易》可筮而《畴》不可占也。[16]
《畴》即是《洪范》九畴的略写。从象数关系来看,尽管象数相倚生,但是《易》与《畴》有“先象后数”、“先数后象”的差别。“先象后数”意味着由天道而人事,“先数后象”则意味着由人事及天道。“《易》可筮而《畴》不可占”是船山对蔡沈范数之学的批判,认为蔡沈不懂得“象数相因、天人异用之理”。②
由上可知,船山对《河图》《洛书》的区分,在结果上跟朱子河洛易学保持一致,但其致思方式和具体内容均与朱子有着较大的差别。在船山看来,《河图》《洛书》之别究其实质是天人之别。
(二)圣人则《河图》画卦
尽管船山承袭了朱子易学中《河图》为天地五十五数的观点,也同样认为《河图》之“象”中蕴含着伏羲画卦作《易》的奥秘,但是他对《河图》的诠释跟朱子“貌合神离”,完全是一种崭新的理路。船山说:“圣人始因《河图》之象而数其数,乃因其数之合而相得,以成三爻之位者著其象,故八卦画而《易》之体立焉。”[17]这是以象、数的角度,展开对圣人则《河图》画卦之具体过程的阐发:
天之一、三、五、七、九,地之二、四、六、八、十……“相得”: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相与以得。位“各有合”者,越其位而合三为一卦也。一、五、七合而为《乾》,二、十、六合而为《坤》,三、十、八合而为《坎》,四、五、九合而为《离》,一、三、二合而为《兑》,二、四、一合而为《艮》,九、六、八合而为《震》,八、七、九合而为《巽》……此圣人所以因《河图》而画八卦,八卦既成,又从而两之,以极其所合之变化,则六十四卦成……[18]
这是船山对《系辞上传》“天一地二”至“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一节的说明。“相得”是说《河图》中数的排布,“各有合”则是说每三个数字可以构成一个三画卦。船山每组三个数字的组合看似毫无规律,其实是着眼于数字的奇偶或阴阳属性,用数字的阴阳来代替卦爻的阴阳。比如乾卦由三阳爻构成,在《河图》中表示乾卦的三个数字就都是阳数;又如离卦卦象为两阳爻夹一阴爻,在《河图》中就由四、五、九两阳数一阴数组成,并且在《河图》图式中四处于五、九之间,保证了阴爻为两阳爻所夹。可知,船山是直接通过组合《河图》中的奇偶数字得出了八经卦,解决了圣人则《河图》而画八卦的问题。
对于六十四卦的产生,船山一方面认为六十四卦是八卦“从而两之”产生的,另一方面则直接从《河图》中解读出了六十四卦。船山说:
圣人则《图》以画卦,八卦在而六十四卦亦在焉,因而重之,五位十象交相错焉,六十四象无不可按《图》而得矣。……《河图》中外之象,凡三重焉:七、八、九、六,天也;五、十,地也;一、二、三、四,人也。七、九,阳也;八、六,阴也。立天之道,阴与阳俱焉者也。至于天,而阴阳之数备矣。天包地外,地半于天者也,故其象二,而得数十五,犹未歉也。人成位于天地之中,合受天地之理数,故均于天而有四象,然而得数仅十,视地为歉矣。卦重三而为六,在天而七、八、九、六皆刚,而又下用地之五、人之或一或三,而六阳成。地五、十皆阴,五,刚也;刚亦阴之刚。又用天之八、六,人之二、四,而六阴成。此则《乾》《坤》六爻之象也。一、三皆阳也,《乾》虚其一而不用者,天道大备,《乾》且不得而尽焉,非如地道之尽于《坤》也。是知圣人则《河图》以画卦,非徒八卦然也,六十四卦皆《河图》所有之成象摩荡而成者,故曰:“圣人则之。”[19]
在这段引文中,船山直接把《河图》之“象”分为中外三层,分别表示天、地、人。最外层的七、八、九、六为天,有阳数有阴数,其数总和为三十;第二层的一、二、三、四为人,亦阳数阴数俱有;最里层的五、十则是地,有阴数也有阳数。就六十四卦的生成来说,在天的七、八、九、六四数皆属于刚,八、六虽然是阴数,但从属于天,因此是为阳之柔,便可视为阳数。由此,在天的四个阳数、地数五、人数中的一(或三)三者相组合,就共有六个阳数,便是《乾》卦。同样,地数五虽为阳数,却是“阴之刚”,可视为阴数。由此,地数五、天数八六、人数二四相组合,共有六个阴数,意味着六个阴爻,象征着《坤》卦。船山只从从《河图》中解读出《乾》、《坤》两别卦,而其他六十二卦则是“《河图》所有之成象摩荡而成”;可见,船山只是并建了《乾》《坤》,其他六十二卦均由《乾》《坤》二卦生成。
三、对周敦颐《太极图》的肯定与展开
“乾坤并建”说是船山易学的基石和根本义理,船山自己就说:“以乾坤并建为宗。”[20]“乾坤并建”的思想蕴含于伏羲所画之卦象中,至文王被阐发出来而为《周易》,与《连山》首《艮》、《归藏》首《坤》不同,《周易》不是以《乾》为首,而是以“乾坤并建”为始;但是孔子之后,以《乾》为首才是《周易》诠释的主流,“乾坤并建”之旨一直隐没不彰,唯有张载和周敦颐一言“太和”、一主“太极”,对《周易》并建《乾》《坤》之旨有所发明。但是,张载之“太和”是“就人之德以言之”,[21]而周敦颐《太极图》则紧贴《易传》“太极”之义。
船山对周敦颐《太极图》的重新诠释,主要集中于三点,第一是对《太极图》整体“形象”的说明,第二是对《太极图说》中“无极而太极”一句的诠释,第三是《太极图》第二图的解读。
对于第一点,船山通过对比环与珠在形状上的差异,来表明《太极图》的性质,他说:
绘太极图,无已而绘一圆圈,非有匡郭也。如绘珠之与绘环无以异,实则环珠悬殊矣。珠无中边之别,太极虽虚而理气充凝,亦无内外虚实之异。从来说者,竟作一圆圈,围二殊五行于中;悖矣。此理气遇方则方,遇圆则圆,或大或小,絪缊变化,初无定质;无已而以圆写之者,取其不滞而已。[22]
“太极”从根本上就不可以用图的形式表达出来,因为它没有“定质”,“遇方则方,遇圆则圆”。因此《太极图》不得已而画一个圆来表示太极,此“圆”不是与方相对而言的,只是为了表明“太极”是“不滞”的。在船山看来,珠与环都是圆形,二者之间却有着极大的差别,《太极图》与其说相似于圆环,毋宁更为接近圆珠。圆珠的中和边是一体的,恰如太极图从内到外都没有虚实的差别,不象圆环边是实的而中则是虚的。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船山认为太极虽虚但却实有,而非虚无的不存在。
第二点,关于“无极而太极”,船山认为这是对《系辞上》“易有太极”一节之蕴涵的进一步阐明。船山在注释“易有太极”时认为:
“太极”之名,始见于此,抑仅见于此,圣人之所难言也。“太”者极其大而无尚之辞。“极”,至也,语道至此而尽也;其实阴阳之浑合者而已,而不可名之为阴阳,则但赞其极至而无以加,曰太极。太极者,无有不极也,无有一极也。惟无有一极,则无所不极。故周子又从而赞之曰:“无极而太极。”阴阳之本体,絪缊相得,和同而化,充塞于两间,此所谓太极也。[23]
高职院校的学生大多数处于17~22周岁,是处于青春期后期的特殊群体,这一年龄阶段的学生面临着的社会竞争,除此之外还有知识学习和技能学习的艰巨任务。不少高职院校的学生因为饮食习惯和生活规律而忽视了均衡营养,造成当代大学生群体中亚健康人群比例位居不同人群的第二位,仅次于白领阶层[1]。文章以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学生为研究对象,提出如何对高职院校学生进行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使高职院校学生的营养配餐更加科学合理。
“太极”的实质就是阴阳极至的浑合而已,阴阳的本来面貌就是“太极”。但是只说阴阳不足以表达出“极其大”而“至”的意思,因此“太极”就是对阴阳之极至的赞词。“无有不极”就是说阴和阳都达到了“极”“至”,但是阴阳之“极”“至”,不是屋极那样存在于固定的空间中,因此又是“无有一极”。“无有不极”而“无有一极”,概括言之,就是周子所谓“无极而太极”。船山在其著作中不止一次表达这一观点,比如:“是故《易》有太极,无极而太极。无所不极,无可循之以为极,故曰无极。”[24]“太极”为阴阳之极至,阴阳之极至就是纯阴纯阳,而纯阳卦为《乾》,纯阴卦为《坤》,由此“太极”就是“乾坤并建”。船山说:“太极者《乾》《坤》之合撰,健则极健,顺则极顺,无不极而无专极者也。”[25]阴阳无有不极,健顺无有不极,即是“无极而太极”。以“乾坤并建”为“太极”,在船山对《太极图》第二图的诠释中,有着更为具体的展开。
第三点,关于《太极图》第二图,从学术史渊源上,船山并不否定其与道教学说的关系,他说:“太极第二图,东有《坎》,西有《离》,颇与玄家毕月乌、房日兔、龙吞虎髓、虎吸龙精之说相类,所谓‘互藏其宅’也。世传周子得于陈图南,愚意陈所传者此一图,而上下四图,则周子以其心得者益之,非陈所及也。”[26]这里船山似乎认为,《太极图》中周子有心得的是除第二图之外的上下四图,但这只是从《太极图》的形成渊源说,实际上在船山看来,第二图对于表达“乾坤并建”之旨也是至关重要的。船山说:
《乾》《坤》并建,为《周易》之纲宗……盖所谓“《易》有太极”也。周子之图,准此而立。其第二图,阴阳互相交函之象,亦无已而言其并著者如此尔。太极,大圆者也。图但象其一面,而三阴、三阳具焉。其所不能写于图中者,亦有三阴、三阳,则六阴、六阳具足矣。特图但显三画卦之象,而《易》之《乾》《坤》并建,则以显六画卦之理。乃能显者,爻之六阴、六阳而为十二,所终不能显者,一卦之中,向者背者,六幽、六明,而位亦十二也。十二者,象天十二次之位,为大圆之体。太极一浑天之全体,见者半,隐者半,阴阳寓于其位,故毂转而恒见其六。《乾》明则《坤》处于幽,《坤》明则《乾》处于幽。《周易》并列之,示不相离,实则一卦之向背而《乾》《坤》皆在焉。……呜呼!太极一图,所以开示《乾》《坤》并建之实,为人道之所自立,而知之者鲜矣![27]
从《太极图》来看,“易有太极”“无极而太极”均对应第一图,表达的是《周易》“乾坤并建之纲宗”。第二图呈现出“阴阳互相交函之象”,表达的也是“乾坤并建”之旨。但是与第一圈有所不同,第二图只呈现出了三阴三阳,而非六阴六阳,而究其原因则在于,“乾坤并建”之十二位阴阳无法同时得到显现,因为每一卦只有六个爻。但是十二位的结构是颠扑不破的,因此对于每一别卦来说,“见者半,隐者半”,共有十二位阴阳。从这个角度来看《太极图》第二图,它只呈现出六爻对于六十四卦每一卦来说,都是普遍适用的。如果与第一图比较的话,第一图直接指明“乾坤并建”十二位阴阳的结构,而第二图则以“向”“背”、“幽”“明”、“见”“隐”的方式保证了十二位结构在每一卦中的存在。
四、对“典要”化的邵雍易学的彻底批判
不同于对《河图》与《太极图》的认可和重新诠释,船山对邵雍易学持坚决的批判态度。不论是“先天易学”“加一倍法”,还是六十四卦方圆图,船山均认为是对易学“不可为典要”原则的悖离。船山对邵雍易学的批判充斥着几乎船山所有的易学文本,但举起荦荦大者,两点足以尽之:一是对“加一倍法”的批判,二是对《先天图》及先天易学整体性的批评。
第一,就对“加一倍法”的批评而言,船山基于经学立场,得出了与胡渭等人相似的结果。船山说:
邵子挟其加一倍之术以求天数,作二画之卦四、四画之卦十六、五画之卦三十二,于道无合,于数无则,无名无象,无得失之理,无吉凶之应,窃所不解。加一倍之术,无所底止之说也。可二画,可四画,可五画,则亦可递增而七、八、九画,然则将有七画之卦百二十八、八画之卦二百五十六、九画之卦五百一十二,渐而加之以无穷无极,而亦奚不可哉!邵子之学如此类者,穷大失居而引人于荒忽不可知之域,如言始终之数,自《乾》一而以十二、三十相乘,放《坤》之三十一万、三千四百五十六万、六千五百六十三、万八千四百万,运算终日而得之,不知将以何为?《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学《易》者知其数:一函三为体,阳九阴六为用,极于万二千五百而止。畏圣人之言,不敢侮也。[28]
在《周易》经传中,只有三画卦和六卦画,但是在“加一倍法”的卦画生成理路中,难免会产生二画、四画、五画这些于经传无征的东西出来。如果说二画还可以用四象来勉强解释的话,四画、五画根本就无法运用经传中的学术术语加以解释。对于邵雍乃至朱子易学来说,这是他们易学理论中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船山就着眼于此,对邵雍易学进行了批判。船山认为这些卦画“于道无合,于数无则,无名无象,无得失之理,无吉凶之应”,并进一步指出,“加一倍法”无法解决卦画何以止于六画的问题,将会出现七画卦、八画卦……无穷无尽。船山的这一点批评也颇为中肯,尽管朱子他们可能同样基于经学立场会自觉止于六画卦,但是理论的豁口确实没有被堵上。此外,船山对邵雍的卦数说也进行了批评,认为其数繁复,不符合《周易》“易简”之理。
邵子之图,如织如绘,如饤如砌,以意计揣度,域大化于规圆矩方之中。尝试博览于天地之间,何者而相肖也?且君子之有作也,以显天道,即以昭人道,使崇德而广业焉。如邵子之图,一切皆自然排比,乘除增减,不可推移,则亦何用勤勤于德业为邪?疏节阔目,一览而尽,天地之设施,圣人之所不敢言,而言之如数家珍,此术数家举万事万理而归之前定,使人无惧而听其自始自终之术也。将无为偷安而不知命者之劝邪?于《彖》无其象,于《爻》无其序,于《大象》无其理,文王、周公、孔子之所不道,非圣之书也。而挟古圣以抑三圣,曰伏羲氏之《易》;美其名以临之,曰先天。伏羲何授?邵子何受?不能以告人也。先天者,黄冠祖气之说也。故其图《乾》顺《坤》逆,而相遇于《姤》《复》,一不越于龙虎交媾之术,而邵子之藏见矣。程子忽之而不学,韪矣哉!朱子录之于《周易》之前,窃所不解。学《易》者,学圣人之言而不给,奚暇至于黄冠日者之说为?占《易》者,以占得失也,非以知其吉而骄、知其凶而怠者也,又奚以前知一定之数为?[30]
引文可分为四个层次:首先,船山认为邵子的《先天图》是通过“意计揣度”绘制出的,有着“自然排比,乘除增减,不可推移”的特点。而这就意味着天地万物普遍的律则化,因此通过掌握《先天图》,就可以“如数家珍”而无所不知。这在哲学上就导致了“前定”,命运早已被安排好而不可改易,那么一切向上的努力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就邵子自身的易学来说,未必有这层意思,但在船山批判的视野中,这样一种学问导致的后果不可谓不严重。其次,船山认为邵子的先天易学,缺乏《周易》经传的经典依据。这表现在文王、周公、孔子都未曾言说,亦无法从《彖辞》《爻辞》《大象传》中推出。再次,船山认为邵子先天易学的实质是,“黄冠祖气之说”“龙虎交媾之术”,从而把邵子易学判定为道教异说。最后,船山从“学《易》”“占《易》”的角度认为,邵子之学就“学《易》”而言,不学圣人之言;就“占《易》”来看,则不占得失,导致“知其吉而骄、知其凶而怠”的后果;于“学《易》”“占《易》”之本旨两失之。
五、对朱子“《易》本卜筮之书”的批判
船山对朱子易学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对朱子“《易》本卜筮之书”[31]观点的批驳上。
首先,船山通过提出“四圣同揆”的易学史观批判朱子的四圣分观。船山说:
伏羲氏始画卦,而天人之理尽在其中矣。……文王起于数千年之后,以“不显亦临,无射亦保”之心得,即卦象而体之,乃系之《彖辞》,以发明卦象得失吉凶之所繇。周公又即文王之《彖》,达其变于《爻》,以研时位之几而精其义。孔子又即文、周《彖》《爻》之辞,赞其所以然之理,而为《文言》与《彖》,《象》之《传》……盖孔子所赞之说,即以明《彖传》《象传》之纲领,而《彖》《象》二传即文、周之《彖》《爻》,文、周之《彖》《爻》,即伏羲氏之画象,四圣同揆,后圣以达先圣之意,而未尝有损益也,明矣。……繇此思之,则谓文王有文王之《易》,周公有周公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而又从旷世不知年代之余,忽从畸人得一图、一说,而谓为伏羲之《易》,其大谬不然,审矣。[32]
伏羲之易虽无文字而只有卦画,但是天人之理已经蕴含于其中,文王依卦象作《彖辞》,使卦象中蕴含的天人之理得到开显,天人之理亦即“卦象得失吉凶之所繇”。文王之后,周公依文王之《彖辞》作《爻辞》,孔子依文王《彖辞》、周公《爻辞》作《文言》《彖传》《象传》等,所阐发的均是伏羲卦象中的天人之理,没有丝毫的损益。在这种易学史观的视野中,朱子的四圣分观说便成为批评的对象。朱子四圣分观的易学史观之根据,恰恰就在于“《易》本卜筮之书”的提出,其基本观点是,孔子之前的伏羲易也好、文王周公易也罢,本质上都是用来占筮的占筮书。因此,就“本义”着眼,《周易》的本来面目就是“卜筮之书”。
几乎所有的易学家都不会反对《周易》的“卜筮之用”,船山也不例外,他依《系辞》认为“占筮”只是《易》之一道。所以当船山说:“《易》之为筮而作,此不待言。”[33]我们决不能误会船山也认为《周易》本是卜筮之书,“《易》本卜筮之书”是朱子极其个人性的创造性观点,否则船山对朱子的批评就无法理解。因此,船山对孔子之前易学史的重新理解,就意味着对朱子“《易》本卜筮之书”从根源上的否认。
船山认为,孔子之前的易学史是“四圣同揆”的而毫无损益,但是孔子之后的易学史,则表现为“学”与“占”交胜的历史。船山把朱子易学归为“占”的范围,他说:“京房、虞翻之言《易》,言其占也。自王弼而后至于程子,言其学也。二者皆《易》之所尚,不可偏废,尤其不可偏尚也。”[34]朱子易学对王弼至程子尚“学”而废“占”的传统有矫正的作用,但是朱子无疑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船山说:
朱子学宗程氏,独于《易》焉尽废王弼以来引伸之理,而专言象占,谓孔子之言天,言人,言性,言德,言研几,言精义,言崇德广业者,皆非羲、文之本旨,仅以为卜筮之用,而谓非学者之所宜讲习。其激而为论,乃至拟之于《火珠林》卦影之陋术,则又与汉人之说同,而与孔子《系传》穷理尽性之言,显相抵牾而不恤。繇王弼以至程子,矫枉而过正者也,朱子则矫正而不嫌于枉矣。[35]
朱子在“《易》本卜筮之书”的立场上,确实曾把《周易》比为《火珠林》,这是船山坚决不能接受的。船山认为,朱子不仅对程子尚“学”的传统有所偏离,而且还悖离了孔子“言天,言人,言性……”的传统。对此,船山说道:“朱子师孔子以表章六艺,徒于《易》显背孔子之至教。故善崇朱子者,舍其注《易》可也。”[36]
其次,船山通过“占”也对朱子之崇占提出了批评:
《易》之为筮而作,此不待言。王弼以后,言《易》者尽废其占,而朱子非之,允矣。虽然,抑问筮以何为,而所筮者何人何事邪?至哉张子之言曰:“《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然非张子之创说也。《礼》:筮人之问筮者曰,义与?志与?义则筮,志则否。文王、周公之彝训,垂于筮氏之官守且然,而况君子之有为有行,而就天化以尽人道哉!自愚者言之,得失易知也,吉凶难知也。自知道者言之,吉凶易知也,得失难知也。所以然者何也?吉凶,两端而已。吉则顺受,凶无可违焉,乐天知命而不忧。前知之而可不忧,即不前知之,而固无所容其忧。凶之大者极于死,亦孰不知生之必有死,而恶用知其早暮哉!惟夫得失者,统此一仁义为立人之道……故圣人作《易》,以鬼谋助人谋之不逮,百姓可用,而君子不敢不度外内以知惧,此则筮者筮吉凶于得失之几也。固非如《火珠林》者,盗贼可就以问利害。[37]
不难发现,船山的占筮观比较特别。船山提出占学一理的观点,实质上是用“学”改造了“占”,他认为:“占《易》者,以占得失也,非以知其吉而骄、知其凶而怠者也。”[38]占《易》主要是为了占得失,而非仅仅是知吉知凶,从而趋吉避凶。由此,船山进一步重申“《易》为君子谋”的立场,认为对于君子来说吉凶无关紧要,只需要顺受就可以,所谓“乐天知命而不忧”。引文最后“《火珠林》云云”显然是针对朱子而发。朱子的占筮观比较“亲民”,“圣人因作《易》,教他占,吉则为,凶则否”,[39]认为人人皆可就《周易》得到趋吉避凶的指导,这即是圣人针对淳质古人的设教。显然,这与船山的说法大异其趣。船山反对通过《周易》之占筮来趋吉避凶,认为这是小人的行径,《周易》“不为小人谋”。
最后,船山还批评了朱子的筮占之法。船山认为,王弼至程子的尚“学”传统,专言理而废弃了占筮,“听其授受于筮人,则以筮玩占之道,不能得先圣人谋鬼谋、百姓与能之要。”[40]导致《周易》占筮之道沦陷于筮人之手,失去圣人“人谋鬼谋、百姓与能之要”的占筮本意。直到朱子,又重新开始讲筮占之法,但是朱子之法本于程沙随,专主“之卦”,亦属于焦赣等的筮人传统,不合于圣人之古占。[41]
六、结语
船山对学术创新性有着自觉的追求,所谓“六经责我开生面”。他曾在《周易内传发例》中,对自己的易学作了全面的总结:“以《乾》《坤》并建为宗,错综合一为象。《彖》《爻》一致,四圣一揆为释;占学一理,得失吉凶一道为义,占义不占利,劝诫君子、不渎告小人为用,畏文、周、孔子之正训,辟京房、陈抟日者黄冠之图说为防。”[42]就本文的考察主题来说,涉及到了引文所总结船山易学的方方面面。对于北宋以来的易学图书学传统及朱子易学,船山作出了深入的批判和诠释:(1)针对《河图》,船山站在经学的立场,认为《河图》为圣人作《易》画卦所则,从中引申出了“《乾》《坤》并建为宗”的思想。(2)《太极图》在易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周子着力阐发的太极大义,其实质也是“《乾》《坤》并建”。(3)而邵子的先天之学,悖离圣人之易,属于“京房、陈抟日者黄冠之图说”,必须批判之,方能彰显“文、周、孔子之正训”。(4)朱子提出“《易》本卜筮之书”的观点,有见于王弼至程子尚“学”传统的偏失,却陷入筮人的传统,于“四圣一揆”“占学一理”“劝诫君子”之圣学均不契合。一言以蔽之,对宋易的批判与重新诠释,是船山易学创建的必由之路;反过来我们可以通过船山对宋易的批判与重新诠释,更好地理解船山易学的思想价值。
注释:
①学界对船山易学的研究,已部分涉及船山对宋易图书学的评价,参见梁韦弦.船山先生对邵雍、朱熹易学的批评[J].船山学刊,2004(04):22-25;周建刚.王夫之对《太极图说》的发挥[J].船山学刊,2018(05):34-37;苏晓晗.船山易学思想研究[D].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马倩倩.王夫之易哲学研究[D].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刘明山.船山易学研究[D].辽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但对于船山对宋易图书学的批判与新诠,仍然缺乏一个整体性的把握与理解。
②见王夫之.尚书引义[M].北京:中华书局,2011:89。船山对蔡沈的批判,可参见谷继明.论王船山对《潜虚》与《洪范数》的批判[J].周易研究,2019(01):45-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