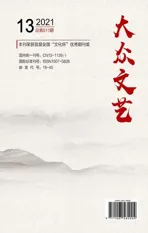“新青年”的困境
——从鲁迅《伤逝》中的小狗“阿随”谈起
2021-01-28飞思懿
飞思懿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081)
一、“狗”的形象译解
鲁迅反复不断地着意塑造动物。鲁迅作品中的“动物意象系统”,实际上构成了“人的世界”的镜像,在“人的动物性”和“动物的人性”的互文关系中,映照出的是人的思想意识和精神世界。
鲁迅对“狗”这一动物有无间断的批评之声,“狗”的形是奴性的隐喻。鲁迅所创造的“狗”的形象,基本作为否定性的形象出现。
不过,鲁迅不同文本中的“狗”并非全然同质性。就《伤逝》来说,“小狗阿随”的形象便无法纳入鲁迅所建构的狗的否定性形象序列中。因此,“狗”的形象存在着丰富的面向,是鲁迅写作上的一种工具,是对人、社会的前途命运的转喻。
二、小狗阿随与子君的关系——“娜拉”启蒙话语的“蒙骗性”
《伤逝》中的“狗”——阿随,并非仅仅是涓生和子君生活境遇变化的一个外在反映,其名字也并非全然指涉着子君对于涓生的依附(这一点经常被当作这一爱情悲剧的内在动因)。阿随的命运还分别和子君、涓生两人的命运构成不同侧面的转喻关系。通过这样的双重转喻,阿随变成了五四“新青年”组成的“现代家庭”的一道棱镜,也作为一组社会镜像的集合,指称着“新青年”所信仰的“娜拉”等借自西方的启蒙话语在被挪用、误读与嬗变的中国社会语境中暴露出的狭窄性。
《伤逝》中,由于涓生婚后在子君情感中的缺席,阿随是子君最亲密的存在。与子君截然相反,涓生则时刻对阿随保持着疏远、警惕与排斥的态度。从一开始不喜欢“阿随”这个名字,后来责怪阿随给他经济上带来的“沉重负担”,最后将阿随抛至野外,甚至当阿随带着本能的眷恋回到吉兆胡同时,涓生也决然将它抛弃,任由它自生自灭。
子君的“亲”狗,涓生的“斥”狗,鲁迅通过这样人与动物的关系,展现了冲破封建大家庭的“新青年”重组的小家庭从构想到尝试再到破灭的过程。阿随作为五四时期“现代家庭”的象征性存在,是借自西方资本主义的“核心家庭”的观念。这种资本主义式的家庭中夫妻两人,有儿有女,有猫有狗,构成了现代家庭想象的理想“蓝图”。这里,“狗”的身份相较于封建大家庭中的身份有所转变: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狗是看家护院的家畜。在子君的家庭中,阿随则是子君心里的家庭成员。但“狗”——阿随这个连接,这种情感的寄托被涓生驱逐出去,子君的对“新式家庭”的美好幻想也随之破灭了。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中,这种由自由恋爱“新式家庭”不过是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出走的“玩偶之家”。脱离了封建宗族社会的束缚,便会以极不稳定的形态存在:完全脱离封建家庭的经济支撑,便很难再继续“新”下去。这种“新式家庭”其中一种结果便是《伤逝》所暗示的,丈夫将妻子驱逐出门,并认为她“可以毫无牵挂地做事”。
离开新式家庭的“娜拉”,并非真的能去寻找一条新生的路。《伤逝》中的小狗阿随被涓生驱逐出去之后,又半死不活地回到吉兆胡同。阿随的出现把涓生吓得“心脏一停”。再一次回到家中的小狗阿随作为子君被迫离开吉兆胡同后的另一种命运的影射,带有着子君“幽灵”重返的意味。即被驱逐出夫权家庭的“娜拉”再一次回来,她们被逐出了现代家庭,回到封建大家庭后又被驱逐,后来又回到现代家庭。在这次的“重返”行动的设置中,涓生依然没有任何的悔意与自责,并没有将阿随留下,而是离开了吉兆胡同,逃到会馆里去,再一次决然抛弃了阿随。这也暗示着,即使真正的子君再一次出现在涓生面前,再一次回归到他们的小家庭当中,仍然会面临再一次被抛弃的命运。
这里来自鲁迅对“娜拉”挣脱“父权”,投入“夫权”,再次离开“夫权”后会怎样的一种再思考,也是对五四时代“娜拉出走”神话的戳破。《伤逝》构思于1924年,这样,1924年4月26日作《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也就有了特别的意义。1918年《新青年》杂志创办的《易卜生专号》,后发表了胡适和罗家伦发表的《玩偶之家》中译本,这个离开夫权家庭大门的“娜拉”,经过“跨语际实践”①的过程,在引入的过程中不断经历着转化,裂变,重组与再创造,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巨大社会潮流的本土环境中取得了“主方语言”的巨大能动性,逐渐成为代表一代知识分子追求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的人格范型和价值目标的“本质性话语”。“娜拉”在中国成为用来抵抗封建社会、家庭的话语,在这样获得极大“合法性”的女性启蒙话语之下,中国的青年女性,都变成了出走的“娜拉”。中国的“娜拉”们,与本身被单薄的、狭窄的“启蒙话语”启蒙的“新青年”的自由恋爱,逃离封建“父权”大家庭,又陷入了“夫权”家庭。鲁迅试图对中国的“娜拉”进行解剖,从而发现新女性启蒙话语的裂痕。在《伤逝》中,展示当时的中国并没有给觉醒“新女性”提供经济独立的社会条件,女性出走之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的《伤逝》也只是对“娜拉”走后怎样给出一种回应和设想,鲁迅也无法给出答案,但绝不是如《伤逝》中的子君,寄托于来自所谓的“启蒙主义”下的男性。鲁迅以小狗这种象征性的设置,实现了对“娜拉”命运思考、五四以来的“娜拉”话语的再反思与去魅。
三、小狗阿随与涓生的关系——“新式家庭”的困境
在《伤逝》中,涓生没有去思考“女性命运”这个现代命题,“新式家庭”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该处于怎样的社会位置。由此,涓生是不彻底的“新青年”,涓生接受的启蒙话语,也只是作为其“反抗”封建的一种片面性话语。
涓生的自我讲述,是未完全脱离封建思想“新式知识分子相”的自我暴露。涓生与子君找住处的时候,惧怕巷子里的人的眼光;婚后的涓生将家务全留给子君,最后却认为子君完全沦入了叭儿狗和油鸡之间;涓生将自己经济上的窘迫归因于子君与阿随;在寒冬中独自去图书馆取暖却不顾子君……阿随从集市上被带回吉兆胡同,最后再被涓生蒙着头带到荒野中一脚揣进土坑,最后又自己回到吉兆胡同。在涓生单向度的叙述中,子君的命运与在阿随身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前后相关,阿随的命运成为子君命运的转喻。这转喻不断暗示着:子君似乎没有脱离过“玩偶”的命运。
涓生对阿随“前半生”(阿随的出现到被抛弃)的叙述中,只要阿随出现必然伴随着子君的出现:“还有一只叭儿狗,从庙会买来,记得原有名字,子君给它另起了一个,叫作阿随。我就叫它阿随,但我不喜欢这个名字。”②从集市上被回家,给小狗取名都是子君的安排,涓生认为这一切都与他无关甚至有些排斥,在他单向度的视角中,已经把子君和阿随作为自己生活的对立面。往后的家庭生活中,在涓生眼中的子君完全沦为家庭主妇,等待着涓生的经济“赏赐”,家务也是非她不可的工作。涓生责怪子君“忘掉了先前所知道的东西”,就像阿随忘掉了自己作为一个宠物职责,成了必须被喂养的对象,加重着涓生的经济负担。涓生潜意识中已将子君当作玩偶,需要子君不能忘记要时刻做一个“新女性”,也不能忘记成为一个称职的“家庭主妇”。涓生像扔垃圾把阿随一样抛在荒野不久之后,也抛弃了子君。在涓生的眼中,子君实际上是像小狗一样“玩偶”般的存在。即使涓生如何标榜自己是“新青年”,在他的一系列言行的暴露之中,呈现出的仍然是封建男权在他身上“余韵绕梁”般的存在。启蒙激荡了青年的心,却无法让他们与封建思想“割袍断义”。身上扔上残存着封建性、大男子主义。在逃脱“父权”这个大家庭的过程中,涓生的觉醒远不如子君的更彻底,更清醒。
“新青年”和“新女性”,没有社会、民族、国家的大解放,他们组成的“小家庭”也无法安身立命。
四、结语
鲁迅提出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新青年利用这种“神话”式的信仰逃离封建大家庭之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该如何寻找真正的出路。这也就让文本的指涉溢出个人的范围,延展到关乎“国族”的集体维度。
《伤逝》中象征“现代家庭”的小狗阿随的命运,连带出狭窄的“启蒙话语”下成长起来的“新青年”身上的“新”的不彻底,以及“新式家庭”在半封建的社会中运转的极小的可能性、“启蒙话语”的不可靠性片面性、狭窄性。社会的整体改革滞后于“新青年们”的觉醒,所带来的生存困境。
阿随这个名字,就并不仅仅指向子君对涓生的依附,也可以理解为五四“新青年们”对“启蒙”话语狭窄的随附。
注释:
①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M].宋伟杰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2014:1-3.
②鲁迅. 鲁迅全集·第二卷[M].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