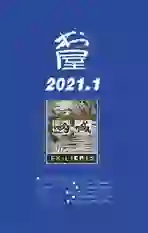戴名世的史学人生
2021-01-27华庆生
华庆生
志在明史,戴名世的史学人生有两个截然相反,却又内在统一的阶段:“凤凰于飞”和“考槃之境”。
“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傅于天。蔼蔼王多吉人,维君子命,媚于庶人。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菶菶萋萋,雝雝喈喈……矢诗不多,维以遂歌。”这是《诗经·大雅·卷阿》中的一段,诗人以凤凰展翅,百鸟相随,比喻贤臣对周王的拥戴;贤臣献诗,为答周王尽情高歌,渲染出一种君臣相得的和谐气氛。
戴名世在《傅天集序》曾记录下高不骞所说的一段话,可谓“傅天”情结影响深远。高不骞(1678—1764),江苏华亭(今上海)人,字查客,晚号小湖。工诗赋,善书画,长考据。岁乙酉(1705),康熙帝南巡至松江,诏求名士,不骞以布衣召试,拜迎道左,恭献诗篇。康熙览之嘉叹,多次召试,恩宠频颁,后授翰林院待诏。高不骞求戴名世为自己《傅天集》写序,戴除介绍作品内容外,更多的是借“凤凰于飞”抒发自己的“傅天”情怀。戴名世称高不骞的《傅天集》“盖皆纪恩述事之作”,并引用高不骞所言:“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傅于天。此《卷阿》之诗人所为歌诵其主之寿考福禄,而兼及于吉人吉士之多也。今天子仁圣迈于成周,搜奇拔滞,銮舆所至,无遗贤焉。一时人士无不踊跃淬砺,以赴功名之会。在昔余先人为侍从近臣,沐雨露而亲日月,实与在廷诸臣雝雝喈喈,同鸣国家之盛。不骞之于先人,譬犹凤凰之一毛一毳而已,而滥叨异数,其何敢自附于吉人吉士之列?然而歌咏盛美,道扬休烈,窃欲自拟于《卷阿》之诗人,故名其集曰‘傅天,所以志也。”
和“凤凰于飞”相反,《诗经·考槃》中的“考槃”,是丘樊渔钓的隐者形象。《毛传》说:“考,成;槃,乐。”成乐者,谓成德乐道也。在自我的天地之中,独自一人睡,独自一人醒,独一个人说话,早已是恍然忘世。戴名世《傅天集序》中的高不骞也曾是这样一位视天壤间无一足以欣羨其心者,“其为人也,飘然高寄,有潇洒自得之趣。爱名山水,每扁舟独往,经旬不归。性不耽荣利,谢举场者已数十年,读书赋诗无求于世。闻者莫不高其志行”。真可谓“芥千金而不盼,屣万乘其如脱”。同为一人,一旦“凤凰于飞”,一朝“纽金章,绾墨绶”,便“焚菱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忙着感恩戴德,裒然成《傅天集》。怎不叫人频生感慨:“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
《傅天集》中的高不骞形象是矛盾的,“傅天”情结和淡泊名利硬生生地凑合在一起,显得突兀不协调,读来让人觉得诙谐好笑。其实,这也正是戴名世矛盾心境不自觉地流露。
“出世入世”也让戴名世纠结。戴名世长期处于两难之境,欲仕不成,欲隐不能。悠闲自得的“出世”生活,应该有起码的物质条件,起码的生活必需,必要的亲情慰藉,是在这一切基础上的返归自然。然而戴名世难有此条件,生活困窘,“非卖文更无生计”,“与世往往不合,人之所不趋者就之,人之所必争者去之,萧疏寂寞,其意象独宜于山林之间”。自二十岁起,戴名世往来于燕、赵、齐、鲁、吴、越之间,教家馆,做幕僚,辗转各地三十多年,自谓“以笔代耕,以砚代田”。因此确切地说,徜徉山水间,其实是戴名世穷愁潦倒之际的一种精神寄托。在《成周卜诗序》中,有一段他和里老父的对话将此表露无遗。他说:“余少而学文,耻为趋时之作,有里老父谓之曰:汝之所好者,何境可以象之?余曰:远山缥缈,秋水一川,寒花古木之间,空蒙寥廓,独往焉而无与徒也。”直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友人赵良冶以戴名世十五、六年来储存在他身边的一千两银子,为戴名世在桐城南拙冈(按戴氏称之为“南山”)买地五十亩,房宅一座,称之为“砚庄”。可惜戴名世只隐居半年就出山了。一以生计所迫,一以经世之志未泯,重蹈久弃的科举之途。
同样是“考槃”之境,对高不骞来说是终南捷径;于戴名世而言却是“以兹所居名焉,著其志也”,就是以班、马自命,志在明史。这一点和历史上丘樊渔钓的隐者有很大不同,与不执着于实有,无欲念之系累,追求一个实际并不存在的逍遥世界相比,戴名世有实在追求。他对待人生持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把庄子物我一体、心与道冥人间化了。戴名世在《与余生书》中曾透露心声:“余夙昔之志,于明史有深痛焉。”“终明之世,三百年无史,金匮石室之藏,恐终沦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诸书,缺略不详,毁誉失实。”“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尤云鹗在《南山集偶钞》跋中也曾说:“先生留心先朝文献,十余年来,网罗散轶,次第略备,将欲成一家之言,与《史记》、《五代史》相颉颃。”
戴名世对明朝灭亡深表惋惜,甚至主导着早期对清廷的看法。对于“明史”,更是揆以“春秋”之意,将“本朝年号削除,写入‘永历大逆等语”。这种从“明史”情结所体现的自由意志、独立见解和心甘情愿听命于别人的“傅天”情结是矛盾的,这是他的宿命。悲剧的帷幕已拉开,只不过闭幕的方式不同而已。
随着清代政权的逐渐巩固,“康熙盛世”的出现,社会生活的日益太平,戴名世对清廷采取顺从与合作的态度,不再处处与世“龃龉扦格”,从钟情于丘樊渔钓之迹,到心系“凤凰于飞”,要人们“左提右挈,共维挽风气于日盛”,为巩固清廷统治出力。他评价高不骞的《傅天集》:“余读之,清辞秀句,妙绝一时。以查客之才如此,宜乎其不终沦落于山水之间矣。他日珥笔承明之上,拜手扬言,所谓铺张对天之弘休,扬厉无前之伟绩,可以勒之金石,垂于无穷。”梁启超论及这一问题时便指出:“看起来南山不过一位普通文士,本绝无反抗清廷之意。”
戴名世于桐城南山砚庄“隐而复出”,就是他改变态度与清廷合作的突出标志。“志不欲苟焉以没世”,这是戴名世在《倪生诗序》中评价倪山堂的一句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自况。他在砚庄稍作逗留后,即抱着“果有真才实学,何患困不逢年”的信心,以老迈之身开始了其科举道路上的艰难攀登。不料,当他刚刚迈近武英殿,即在“《南山集》案”中死于非命,成为一个悲剧角色。他嘴上说耻为时文,但一直不愿意抛弃读书应举这一旧业而转向他途。康熙四十四年(1705),戴名世应顺天试,中举人,逾年参加会试,中进士第一名,殿试授一甲第二名(即榜眼),被任命为谕林院编修,时年五十二,终于实现“凤凰于飞”的人生理想。而金榜题名却没给戴名世带来幸运,虽然身在魏阙,却纷纶于折狱,还未张英风,驰妙誉,就陷入和左都御史赵申乔儿子的“名次之争”,引发了他的人生悲剧。戴名世会试第一,而殿试只得个“榜眼”,状元为赵申乔儿子赵熊诏所得。当时便有传言,是赵申乔幕后活动的结果。康熙五十年(1711),左都御史赵申乔为泄私愤,竟据《与余生书》采录了同邑方孝标《滇黔纪闻》所载南明桂王事,主张修《明史》应保留“南明小朝廷”年号,参劾戴名世“恃才放荡,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祈敕部严加议处”。戴名世于是被捕入狱。康熙五十二年(1713)二月被处死,时年六十一。此案株连数百人,凡集中诗文提到的时人“皆获罪”。这就是清代最大的一次文字狱“《南山集》案”。
讽刺的是,《南山集偶钞》雕刻行世时,戴名世已买“宅里中之南山,将归隐,故取以名其集,志归隐之地也”,只是门人尤云鹗在刻《南山集偶钞》时,“一时疏略,此书(《与余生书》)未及删削,亦并列于集中”。清末藏书家、桐城人萧穆曾说,戴名世“年少气盛,择言不精,轻论史实,实非熙朝臣子所應出此。然至是已二十余年矣”,为戴名世未能“越名教而任自然”,礼玄双修而惋惜。
“凤凰于飞”其实是一种伦理境界,和自适其适的“考槃”境界不同,讲的是君臣关系的和谐,核心是“忠”。而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学理念是与之相悖的。史上有名气的史家,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如南史、董狐仗气直书,不避讳权势;韦昭、崔浩之奋笔直书,无所取媚于人。
戴名世的悲剧就在于对清王朝尽忠竭诚时,仍以《春秋》之义对“南明小朝廷”,著其名号,触犯了大忌,被认为不忠不孝,在“凤凰于飞”之时死于“文字狱”。这是戴名世史学人生内在矛盾的时代悲剧。甚矣,先生之祸之烈也,后之人为之悲歌咏叹于无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