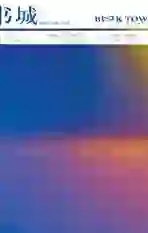小说在“现在”展开
2021-01-25许志强
许志强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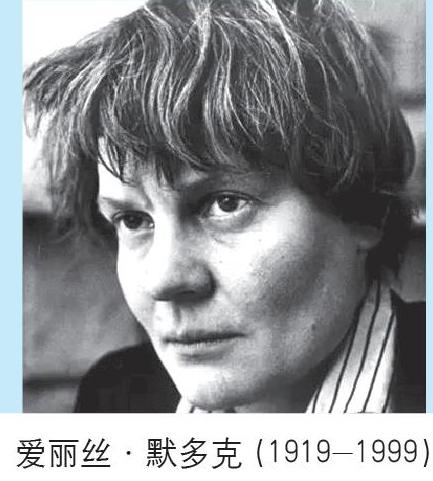
想起大江健三郎作品中,有一组名为“鸟”系列的小说,即贯穿了一个绰号叫“鸟”的主人公的短篇故事,因其描绘青年底层生活的流荡与不安,而为我所喜爱。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的主人公也是“鸟”,软弱恐惧的“鸟”—有一次喝醉酒去他岳父的学校代课,在课堂上胡言乱语,几乎瘫倒在讲台下,类似的细节读来令人忍俊不禁。这篇故事也预示“鸟”系列小说的终结,因为“鸟”结婚生孩子了,那种虽然贫乏悲酸却也不乏自由感的岁月宣告终止了。这和萨特的《理智之年》的主人公马蒂厄的状况有些相似;一个终结近在眼前,而终结前的挣扎,散发着垂死小动物的疲弱的气味。
爱丽丝·默多克的长篇小说《在网下》(贾文浩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18年),和上面提到的作品属于同一个家族。当然,源头都是在萨特那里,这一点是不难辨别的。用迷离恍惚的纯精神的语言刻画官能和物质环境,此种写法尤可见出萨特的文脉。大江健三郎笔下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东京有一股小县城的荒芜气息,富有底层青年的梦幻感;而默多克描述的二战后的伦敦和巴黎则呈现出时尚、机遇和消费,其活动的人物不管多么波西米亚,底子里还是别具“资产阶级生活的隐晦魅力”。《在网下》的主人公杰克一无工作二无居所,被曾经的同居女友扫地出门,照样诗酒流连,往返于伦敦巴黎,与歌星、教授、掮客、资本家、左翼人士打交道,虽不能说左右逢源,却也显得洒脱有趣;大江健三郎小说里的同类人物是过不上这种生活的。这里我不打算探究差异的缘由,虽然这种探究不乏趣味。仅从小说的结局来看,《在网下》的基调相比之下显得不那么绝望,甚至都没有马蒂厄和“鸟”的那种日益浓重的窒息感—借用木心评论存在主义的话说,那种“闷室里的深呼吸”。

存在主义的小说人物当然不必在一个模子里铸成。不过,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共同点。《在网下》结尾,杰克说“我要去找工作”,“我要在一家医院找个兼职”,“但是我先要找个地方住”,這时我们听到一个时代(或一种个人的体验)终结的声音。为什么偏偏要去医院工作呢?答案或许可以从塞缪尔·贝克特、胡里奥·科塔萨尔等人的作品中去找。
贝克特的《莫菲》和科塔萨尔的《跳房子》表明,将乏味单调的病房转化为存在主义的哲学操练的场所,这是一门必修课;存在主义作家经常写到医院,更像是在描写精神病院,那些地方适合于没有身份的人练习完美的自杀或寻求“狗熊般的幸福”。《在网下》第十七、第十八章叙述的是这个主题。杰克在医院做护工,杰克在医院和雨果相聚。那些场所也有点儿像兵营或牢房。等到哥俩儿破窗而逃,跑过黎明时分的青草地,医院作为“闷室”或囚牢的象征意味就突显出来。“闷室”的背景对于反体制行为,尤其是对于年轻人的古怪有趣的思考来说,或许也是不可少的,只是在贝克特、科塔萨尔的笔下,“闷室”还有一层避难所的意味,这一点《在网下》体现得不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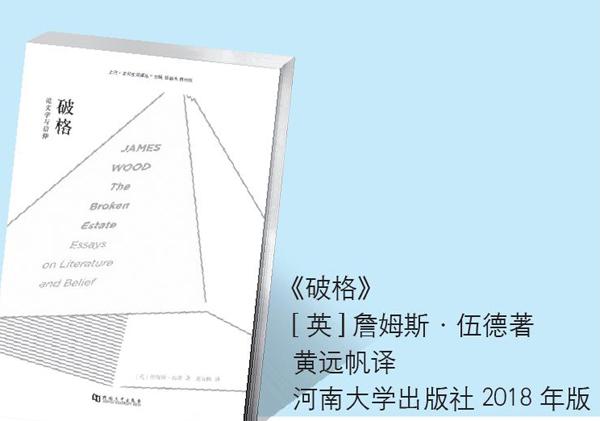
在传统小说中,感化院或精神病院的存在只有负面的意义,而在存在主义小说中,它们的含义就要暧昧多了,既是囚禁也是自由,既是病症也是救赎。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感化院的少年》演绎了一个反社会的乌托邦想象,它是《万延元年的football》的“暴动”的先声。相比之下,《在网下》就显得文雅一些,主人公在巴黎和伦敦之间兜兜转转,忍受些微幻灭的悲哀。杰克逃离医院,最后又想回到医院,此一时彼一时也,他已到了需要“正常”生活的阶段,谈不上反抗,也谈不上归顺,似乎时间的沙漏漏掉了最后一粒沙子,而他获得了一种“一切都很简单,一切都很奇怪”的感悟。他在阳光下轻轻抓住这个感悟,这便是故事正该结束的意义。
二
詹姆斯·伍德在一篇评论爱丽丝·默多克的文章(出自《破格》,黄远帆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中指出,亨利·格林以后,英国小说并“没有创造出什么有深度有生活的人物(四十年来只有毕斯沃斯先生和简·布罗迪)”。文章点名批评了默多克以及A.S.拜厄特、马丁·艾米斯等一干文坛健将。伍德说,默多克笔下的人物像牵线木偶,反面角色写得也不好。不过,默多克本人对此大可不必恼怒,这么说是在和亨利·詹姆斯的反面角色做比较,标准还是定得高的。
谈到默多克的创作中引人注目的知识论倾向,伍德认为,英国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都曾靠近“大陆论文的传统”,该传统养育了托马斯·曼和雅克·里维埃这样的作家,“他们写的是一种喂得很肥的哲学”。伍德不是指默多克的非虚构著作,如《萨特:浪漫的理性主义者》《存在主义者和神话》等,而是指她的虚构作品。

以《在网下》为例,姑且不论该篇的人物塑造是否“有深度有生活”,若干人物身上确实是体现了一种哲学意识。它不是指泛泛而谈的那种,不是指威廉·戈尔丁那类象征和寓言,而是指与默多克的论文所涉及的知识领域(康德、黑格尔、萨特、加缪、西蒙娜·薇依等)相呼应、具有严肃的哲学意蕴的思考。
《在网下》从标题到内容都有哲学意涵。中译者贾文浩在其译序中这样解释该书的书名:
“网”的概念来自默多克的同行前辈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即语言不能表述经验以外的东西。语言自诞生以来一直被使用,用语言编织的理论也无处不在,然而用来表述真实世界,却如同隔靴搔痒,事与愿违,形成一个个似是而非的矛盾。所谓“在网下”,简单地说,就是我们处在一张语言构成的大网底下,网把人与真实经验阻隔开来,我们都在这张网下爬行挣扎。
小说还借人物之口宣称:
人只要一开口说话,就背离了真实世界,换句话说,只要开口就是撒谎。“一切理论阐述都是思想的飞翔。我们必须跟从情况本身,这是无法言说得具体的。实际上,是我们从未足够接近,不管使多大劲在网下爬,都无济于事。”

引号中的文字别有来源。小说交代说,杰克出版过一本书,题为《无言》,记录的是他和雨果的对话。“无言”这个书名的含义同样涉及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即其语言哲学中的沉默概念:面对无法言说的经验感受,我们无法用意义固定的语言表达,最好是保持沉默。在《逻辑哲学论》的结尾部分,我们便能看到这个思想的警句式表述。在小说中,这些思想都是通过雨果之口传达的。
雨果的身上有维特根斯坦的影子;不仅是思想,还有行为也像。身为资本家、大富翁,他把钱财都送给人家,净身出户,去诺丁汉给一个钟表师傅做学徒。受此影响,杰克打算去医院做护工。这让人联想到受维特根斯坦影响的一些剑桥学子的选择,如德鲁利等人,放弃高校学术生涯而去做药剂师。这种选择是有哲学意味的,不仅是体现斯多葛式的坚忍和自守,更包含某种批判性,针对当代文化内在的紊乱状态。雨果在谈到其选择时说,“指手画脚说废话的人太多”,而“钟表业是个老行当,像烤面包”,有清晰的守则和边界,容不下似是而非的胡话。归根结底,这是针对普遍的价值虚无的一种反应。我们看到,维特根斯坦对学院生活(理论生活)的不信任,他的迷茫感和流浪癖,在雨果这个形象中是有所反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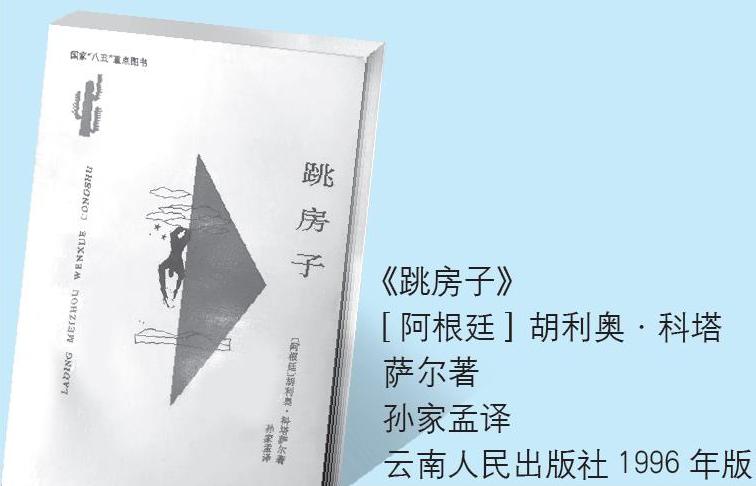
以维特根斯坦的生平为素材创作的小说,最有名的当属毛姆的《刀锋》,好像少有人提及《在网下》。实际上,该篇的一些思想概念,包括人物形象,都有维特根斯坦的痕迹。除了上面谈到的雨果,还有一个名叫戴夫的兼职哲学教师,也明显有关涉。戴夫的住处常有一群崇拜他的年轻人进进出出,一群形而上体系的狂热求索者,然而—
他们许多人来的时候是通神论者,走的时候是批判现实主义者,或是布拉德利主义者。戴夫的批评好像经常都纯粹是分析式的。他气势夺人,像太阳射出愤怒的光芒,荡涤乾坤,但并不烤干他们形而上学的做作,而只是记录他们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变。我从这一怪异的事实中想到,别的先不说,戴夫也许是个好老师呢。偶尔,他能办到把一些接受能力特别强的年轻人,转变成他那种语言分析类型;经此转变,青年们往往对哲学彻底失去兴趣。看戴夫教导这些年轻人,好比看人修剪玫瑰花丛。总是那些最强壮旺盛的枝条被剪掉。修剪后,也许也開花;但不是哲学的花朵,戴夫对此深信不疑。他的最高目标,就是说服年轻人离开哲学。他也老警告我离开哲学,态度特别真诚。
文中即便不提分析哲学这个词,对熟悉掌故的读者来说,这段描述也是颇富维特根斯坦特色:通过一番诊断式的分析造成对方世界观的转变,说服年轻的形而上学者离开哲学研究,等等。这些确实是维特根斯坦做的事,而不是罗素、摩尔或其他分析哲学家做的事。剑桥有天赋的学生(如品生特、斯金纳等)更容易接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和改造,这也说得没错。默多克将维特根斯坦的标志性轮廓分派到两个角色身上,尽管有些叙述只是一笔带过,有些细节从维特根斯坦的角度看是含有讽刺性的(例如戴夫给《心智》杂志写文章等),我们却明显地感到该篇和著名哲学家之间的关联。较之于毛姆的《刀锋》,默多克的小说更接近于人物形象的原型—她的小说中有些东西和原型还对得上,而毛姆的就比较远了。
当然,默多克也好,毛姆也好,他们都是从维特根斯坦的传奇中取用素材,而不是在写一个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小说。默多克的哲学素养好,能够把分析哲学的一些东西写进小说,哪怕只是一些标记,一点概论性质的东西,置于恰当的情境也能够富于启迪。杰克和雨果的几次对话,《无言》一书的片段展示,就有这种效果。可以说,小说包含着一点哲学的冥想,读来不乏意趣。至于它是否反映了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精义,这是不能苛求的。
在小说中,雨果、戴夫谈玄论理,扮演思想助产士的角色,他们是任何自择群体中都不可或缺的那种精神导师(guru)。好像只要有杰克、芬恩这类无所事事的流浪汉,就一定会有雨果、戴夫这类古怪的思想者。或者可以说,只要有杰克这样易受影响的气质,就一定会有那种难以捉摸也难以抗拒的思想者,像懵懂的看客遭遇一出奇妙的哑剧表演。那么,什么叫作现实?对杰克来说,现实是那种能够构成吸引力的存在,正如衣帽间的内景对他有特别的吸引力一样。
雨果对杰克说:“你的问题,是你想以同情的态度去理解一切。这是不行的。这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真理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雨果与其说是在谈论真理,不如说是在谈论死亡和美。他是澄澈的思想者,是人海中埋没得很深的一个姿态,一如钟表匠那种“无言的单纯”。有时你会感到,这个人物身上还真有那么一点维特根斯坦的余韵。
三
《在网下》出版于一九五四年,是爱丽丝·默多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创作精神而言,该篇属于法国派,糅合巴黎的左岸文化和存在主义;叙述别具情调,体现那个时代的梦想和不安。
左岸文化需要落拓不羁的文艺青年,需要很多酒水、很多谈论,需要小圈子和聚散无常的男男女女;这些巴黎有,伦敦也有。英语存在主义小说中,《在网下》既不是最早恐怕也不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但是就左岸文化的一般情调和特点而言,它的表现是比较典型的。贝克特的《莫菲》是一部关于自杀的小说,是在非存在的意义上探讨自杀的小说;描绘一面熔解的镜子中的光彩和映像,它的美感和幽默是在一个渊深的本体论层次上显示的。默多克的《在网下》既不涉及自杀的主题,也不涉及精神避难所的主题;它展示的是一种乐观情调的存在主义。它给个体化原则注入活力和生存的兴趣。所谓自杀,也只关乎某种生活信条,诸如稳定的生活等同于自杀之类的信条。像萨特的《理智之年》,它描绘人的境遇、选择和行为,叙述自择群体中的男男女女的纠葛。小说中有些配角,像躺在桌子底下听人谈话的芬恩,那条上了年纪、名叫“火星”的狼犬,等等,则是存在主义小说中通常见不到的可爱角色。它像一部正常的小说那样充满细枝末节的印象和观察,也像一部有魅力的小说那样使读者心生羡慕和感喟,后者具体说来正是左岸文化所赋予的魅力。
说到这一点,必须论及萨特的小说创作。米歇尔·莱蒙在其《法国现代小说史》(徐知免、杨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中指出了卡夫卡的叙事对萨特(《恶心》)的影响,包括暗淡的基调、故事性的消失、小说和哲学的结合等,卡夫卡的影响都显而易见。莱蒙的看法有道理。不过,也不能忽略另一重来源:萨特从德国的现象学和存在论哲学提取精神内核和思想方法;他把这些观念和巴黎左岸文化混合起来,形成其独特的存在主义文学。
谈到萨特的文学创作,我们通常会把它们当作是哲学的代用品,或者至少会把纯哲学的东西视为其创作前提,总要先解释一下“存在先于本质”等公式,追溯克尔凯郭尔和胡塞尔这两大来源。不能说这样做不对,但总给人远水救不了近火的印象。因为有一點不可否认,萨特小说中的哲学已呈溶解状了;它不是作为一个过硬的范畴和另一个叫作文学的范畴加以兼容,事情不是这样的;它是时而溶解时而结晶的情绪化合物,是一些多半处在悬置状态的格外令人焦虑又特别富于活力的心结与执念。萨特小说的基调再怎么和世界对立,再怎么晦涩暗淡,也都不是卡夫卡的寓言模式,而是关乎特定的群体和倾向,显示左岸文化的纯艺术和哲学性的一面。海德格尔所谓的“虚无”或“本真的通达”被放在了一个特别具体的环境中,并且被赋予浓郁的波西米亚风味。拉丁区的酒吧咖啡馆,穷诗人的奇行怪谈,风流女子的机智,这些都能展示左岸文化的魅力。即便是《恶心》这样背景设在外省小城的作品,它的咖啡馆哲学的风味也纯然属于巴黎。《理智之年》写巴黎夜总会女郎的步态,说那个女子“走路的样子像是在嚷嚷‘我撒尿去喽!我撒尿去喽!”此类描写令人莞尔,粗俗而不失俏皮,说明巴黎的风味不只是在于哲学。说实在的,年轻人有谁不喜欢左岸的波西米亚风尚呢?
总之,萨特开辟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创作模式。米歇尔·莱蒙评论说:“在法国小说中,《恶心》是巨大山脉的最后一座高峰:这些高耸的山峰就是巴尔扎克、福楼拜、普鲁斯特、萨特。”这个评价实非过誉。当然,名单中如果添上路易-费迪南·塞利纳,就更妥了。
说这些是为了表明,默多克的《在网下》继承萨特衣钵,关键在于如何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伦敦的部分场景左岸化,如何使青年自择群体在一个物化的世界里动作—用列维纳斯的话说,就是如何使“存在”这个词语动词化。这一点要稍作解释。我们知道,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对萨特等人的启示包含这样一个意涵:存在不是实体,存在即存在之发生。海德格尔并不认为萨特的哲学和他的哲学是有关系的,但萨特坦言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令他受益。事物和所有存在的东西是“正在存在的过程之中”的东西,是“担当起存在职责”的东西。这是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的思想。从叙事学的角度讲,萨特对叙述应该展现“思想意识的现在性”的强调,契合于所谓的存在之“发生”这个观念。
米歇尔·莱蒙谈到萨特小说的叙事特质时指出:
老实说,《恶心》之后,作为小说家的萨特,他致力的就是反对用叙述故事的方式来写小说。要知道,所谓“现在”是不确定而复杂的,这期间各种事物正在发生,因此人们无法讲述故事,因为讲述故事则意味着人站在一个高点上,从这里出发,时间就不再是在意识里生活过来的现实,而是为理智的推论所组织起来的故事的某种背景说明,这样,就永远跟大声讲述故事的“我”分开了。
即便是故事性较强的长篇小说,如《理智之年》《在网下》等,基本的叙述也是为了凸显“现在”,“就是注意不把某一事件用于说明接下去的事物;注意不让人一下子懂得并奇迹般地告诉别人,要让人物一点一点地去了解他所见到的事物的意义”。用萨特本人的话说,“小说,就像生活一样,在‘现在展开……在小说中,什么也没有决定,因为小说中的人物是自由的。一切在我们眼前完成;我们的焦灼、无知和期待都跟书里的主人公相同”。如此说来,小说这种体裁倒是非常适合于存在主义的自由观了。本质上讲,我们不存在一个先验的舒舒服服的上帝视角。但萨特恐怕不算是用小说凸显“现在”的开创者。实际上,在司汤达、福楼拜等人的小说中,不确定的复杂的“现在”已经表现得很引人注目了。
讲述“从意识里生活过来的现实”,而非“为理智的推论所组织起来的故事”,这应该就是存在主义小说的一大特质了;想想萨特、贝克特、科塔萨尔、默多克等人的小说,包括受存在主义影响的新小说,阿兰-罗布·格里耶、克洛德·西蒙、娜塔莉·萨洛特等人的作品,确实是这么回事:现在是意识的轴心;过去的记忆及未来的向度并未失去,而是向轴心收缩,绕着轴心旋转。
因此,阅读《在网下》这部小说,不是光看主人公杰克的波西米亚生活方式,还要进入他的意识状态。杰克似乎比左岸青年还要左岸,从一种寄居过渡到另一种寄居,包括前女友的化妆间、前女友的妹妹家、朋友家、情敌家等,显得落拓不羁,实质是在犹豫和混乱中步步为营,没有什么是确定和清晰的。生活场景(事件)纷至沓来,令其意识受到揉搓挤压。或者说,场景就像一连串滚动的烟圈,他像被驱赶的小猎犬,玩杂耍似的从烟圈中不断奔跳过去。《在网下》的场景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诸如表演哑剧的小剧场、关押狼狗的公寓楼、电影公司骚乱崩塌的摄影棚、烟花之夜的塞纳河畔等;杰克目睹眼前的景象却被阻断了理解的通道,世界便犹如迷宫,显得幽深莫测,不知道这时时刻刻面对的东西是否就成为其未来命运的关键,也不知道走出迷宫的路径是否就等同于所谓的自由之路。
萨特说:“你想叫你的人物活起来吗?那你就让他们自由。不需要你去指出特征,更不需要加以说明……你只要表现出激情和一些无法预料的行为就行。”
大体上讲,这是存在主义文学的创作指南,《莫菲》《瓦特》《跳房子》《万延元年的football》《晃来晃去的人》《在网下》等篇也都是照此原则去做的。不过,詹姆斯·伍德一定会提出异议,也许他会像马塞尔·阿尔郎那样反驳道:“萨特说,因为人物是自由的,所以他才是活的,而我看,因为他是活的,所以他才是自由的。”这是说,如果人物塑造得不好,不够鲜活,你给他(她)自由又有什么用呢?
人们是基于不同的方法和立场在谈论小说,好像谁也说服不了谁。詹姆斯·伍德不是说,英国文学最近这半个多世纪里,只有奈保尔(《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和穆丽尔·斯帕克(《简·布罗迪小姐的青春》)塑造了像样的人物,其余皆不足观吗?如果说萨特及其弟子和同路人的小说似乎从来都不接近普通人的真实,那么在表现主观意识和难以预料的行为方面,这些小说无疑有着独特的真实感和抒情气息,而且颇具一种抵达狂热的主观性才具有的史诗韵味(我想,这是萨特如此崇拜福克纳的缘由)。
我觉得,默多克的《在网下》尚不具备这种狂热的主观性,但它是一部值得品读的小说。它对我们理解二战后占优势的“主观现实主义”,尤其是强调“思想意识的现在性”的叙述模式是有帮助的。该篇入选一九九八年美国兰登书屋《当代文库》的百部优秀英文长篇小说,当是实至名归。它虽然没有特别感人的人物塑造,但也不至于像詹姆斯·伍德所说的那样,人物都是提线木偶。篇中的昆廷姐妹(安娜和萨蒂)就写得很有生活气息;这些伦敦的熟女,代表大都市练达的风情,世故灵敏,难以驯服。她们的身影在库切的自传体小说《青春》中仿佛瞥见过—闪现于殖民地青年的小心窥望的视线中。
二○二○年十一月八日,杭州城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