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断,应激,文化断层?
——从COVID-19 期间的艺术机构网络实践谈起
2021-01-20李航
文|李航

伦敦当代艺术学院(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在新冠期间每日早晨十点向订阅者进行邮件推送,包含看、听、申请、读以及今日专辑(Watch, Listen, Apply, Read and Track of the Day)等几个版块©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
1.
新冠病毒在全球流行的今天,人们已无法像以前一样把在城市空间中的移动视为理所当然。艺术品无法流通,展览无人光顾,博览会与双年展被迫推迟。几个月前的国内艺术机构以及当下的西方艺术机构都不得不思考如何在今日的限制条件中迅速作出反应、转换计划,通过线上实践来实现机构使命。
在众多的艺术机构网络实践方式当中,以下三种被广泛采用:一、利用照片与视频来代替原本计划展示的作品,将其穿插于策展人的文字中形成“线上展览”;二、将线下展览通过视频导览、3D 建模与全景照片的形式展示在线上形成“虚拟展”;三、将机构的藏品或档案进行数字化并进行邮件或社交媒体推送。表面看来,机构们结合自己的资源与能力,在新冠期间表现了出色的危机处理能力。然而通过对部分艺术从业者与艺术家的调查,笔者发现了一个吊诡的事实:我们仿佛并不真的需要艺术机构的每日推送。1. 来源于笔者于2020 年4 月对艺术工作者们针对网络艺术实践与艺术机构责任进行的采访与观察。虽然尊重、感谢机构们在数字网络工作方面的尝试和投入,笔者也开始反思,是否今天便捷的网络连接和信息推送带给我们某种错觉:我们仿佛觉得艺术与理论可以被转化为堆叠的文字、图片与超链接,成为一条条推送信息以及一个个虚拟展览,并作为一种合理可行的方式通过网络分发在病毒肆虐的现实之中畅行无阻。

K11 Art Foundation 的虚拟导览 —“另辟物径:重塑可再生世界” © K11 Art Foundation
诚然,当展览的筹备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放弃计划展期内的展览或许将造成可观的资源浪费与经济损失。将既有工作成果数字化并在网络上进行一对多信息分发可以最大化工作产出比,并在短时间内为机构争取更高的媒体曝光率。这样既可以规避由展览取消而引发的商业赞助撤资危机,同时也可以摆脱活动“空窗期”的尴尬。然而与艺术机构的生产焦虑和信息过剩同时发生的,是社会集体焦点转移。在新冠病毒蔓延时期,更多人选择将时间与精力倾注在追踪病毒数据、资助困难群体以及对政府工作的监管中。人们于新冠期间为之心焦的是社会中行动与表达的无力,及其背后种种的道德失范与价值缺失。而在集体反思社会结构问题的同时,艺术行业也开始自问:在繁华表面之下,当代艺术的社会价值是什么?艺术机构的运行方式和价值观能否支撑艺术兑现其社会承诺?
2.
如今有越来越多以“当代”“今日”甚至“未来”命名的艺术机构与项目出现。在很多机构的声明中,“新时代”“拓宽艺术边界”“改善人们生活”“社会责任”“社会价值”“全球化语境”等字眼也频频出现。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艺术机构们有责任去讨论当代性(contemporaneity)。艺术机构对当代性的承诺不仅意味着其将不断探索当下与未来中复杂而多重的文化和社会意义,更意味着艺术机构需要对自身的观念和运作模式不断进行反省、自我推翻和重建,以寻求有效的、反映当代社会文化状况的艺术途径。2. Terry Smith, 'What Is Contemporary Art? Contemporaneity and Art to Come', Konsthistorisk Tidskrift/Journal of Art History, 71.1–2 (2002), 3–15.然而如今艺术机构的组织与生产方式已经逐渐固化在一个由展览、教育、出版等活动所支撑的产业链条中。机构们也已经逐渐习惯通过参观人数、阅读量、转发量、话题讨论热度甚至艺术作品市场情况来估算其权力、影响力及知名度。机构作为品牌的“价值”仿佛因为这些数字、流量与热度而变得不证自明。而机构对反思社会文化和调整实践方式的承诺已逐渐贬值成为由物理生产所推动的在推广、参与、记录与再生产等环节之间的无限循环。
新冠为这个循环按下了暂停键。曾经的“当下”变成了一个公众通过网络而与社会连接的当下。而所谓的“未来”也正在成为一个全球化梦碎、国际公共卫生与信任崩盘的未来。如果说对当代的思辨与批判以及对未来的承诺曾经帮助当代艺术机构们完成身份建构与其自身合法化的论证,此时此刻,艺术机构又是否愿意并有能力转入线上、进行有效的社会定位并通过行动实现其承诺?3.来源于笔者于2020 年4 月对艺术工作者们针对网络艺术实践与艺术机构责任进行的采访与观察。
很多艺术从业者坦率承认,艺术机构实现这一点并不容易。毕竟现代艺术很长时间以来都通过撇除社会语境以及对功能的考虑来实现艺术与审美的自治(autonomy)(“为艺术而艺术”)。4. Clement Greenberg, 'Avant-Garde and Kitsch', in Clement Greenberg: The Collected Essays and Criticism, Vol. 1: Perceptions and Judgements, 1939–1944, ed. by John O'Bria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5–22.而这种现代主义的艺术定义曾经于二十世纪演化出了以白盒子突出艺术物(the art object)、以线性历史演进关系来组织艺术品收藏等整套的艺术行业运作体系。其中展览的作用在于使艺术作品能够存在于纯粹的艺术语境和历史中被观众凝视与欣赏。这样的现代主义欣赏习惯演化出了当代艺术行业中的一系列通过以物理空间为依托的、对艺术物和活动的展示手段。这些手段往往重视展厅中观众的体验,并以此为艺术作品展示的基础,而观众的“观看”与“体验”也成为这种展示文化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价值的重要环节。展厅成为一个反映社会文化的“半社会空间”,其中的作品也往往凭借这样的展示方式,以一种超脱于当代现实文化的姿态去对其进行再现(representation)。在这样的行业背景下,将艺术作品嵌入到网络语境中一方面消解了传统意义上艺术与审美的自治,同时也消解了通过物理展厅而成立的艺术交流方式,因此扼杀许多艺术作品被解读的必要条件。如同艺术家冯梦波于笔者的调查中指出的悖论:“(传统意义上的)艺术要‘端’着,这上网就很失效了,但是现在又都只能上网。”5.来源于笔者于2020 年4 月对艺术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冯梦波针对网络艺术实践与艺术机构责任问题进行的采访。
而另外一方面,当代文化的表达方式已经逐渐与现代主义脱钩。留恋于现代主义运作方式的美术馆逐渐成为历史遗产,已从真正意义上的当代文化价值生产阵地中撤出。6. Victoria Walsh and Andrew Dewdney, 'Temporal Conflicts and the Purification of Hybrids in the 21st-Century Art Museum: Tate, a Case in Point', Curating the Collection, Stedelijk Studies, 2017.相应的,数字网络在今天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的主要土壤,网民们实则构成了当代文化生产、参与和传播的主力。直至今日,当代艺术机构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挣扎于营造物理空间环境来展示艺术物以及艺术活动,以此来反映和代表当代文化。而这种挣扎所体现的,更多是对现代主义艺术运作模式的捍卫,而非对当代性的追求。当代艺术工作者们面对网络文化已经趋近于文化他者。
这种矛盾也反映在了艺术机构对实体空间的执念中。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的尤洋副馆长表示,“某些美术馆的空间在历史上所捍卫和保护的‘前进’思想已经在当下成为了‘后卫’思想。现在视觉的生产、展示与传播方式已经因为数字网络发生了可观的变化。面对这些变化,美术馆的形态却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所以说艺术机构与网络实践不仅存在历史与观念上的冲突,更是在空间层面上难以自洽。”面对这样的矛盾,不少艺术工作者们认为在新冠背景下,很多当代艺术机构可能无法针对数字网络的大众文化属性与媒介特点而找到有效的、契合网络语境的实践方式。
通过近几日的艺术动态来看,艺术工作者们或许低估了主流当代艺术对网络的热情和野心。《艺术新闻》3 月底透露,画廊们已经在全民皆线上的今天为了“提升艺术品的观赏和购买体验”而更加关注“AR、VR 之后扩展现实(XR)高科技平台的开发”。7.“艺术时刻丨疫情带来二战之后最大的挑战,各国出台救助政策,病毒给文明带来的创伤开始显现”,《艺术新闻 The Art Newspaper》,30 March 2020
3.
机构们通过数字网络分发艺术品信息、机构档案,以及虚拟化物理空间的线上展来应对新冠危机的现象,可被解读为主流当代艺术对物理实体的集体戒断症状。而在这场集体戒断反应的背后是机构对现代主义审美所发展出的物理空间以及艺术物的长期过分依赖,这种依赖进而导致了主流当代行业对数字网络作为营销渠道的固化认知。
对物理实体的依赖在近二十年来与新自由主义一同为艺术生态带来了种种红利,并使一些当代艺术机构们陶醉于对美术馆展览、双年展、博览会等活动的持续准备、参与、庆祝、记录与报道之中。在这样的产业运作链条中,数字网络往往被视为推广、体验、娱乐与消费的引擎和媒介。今天的很多艺术机构已经成为熟稔网络营销的弄潮者。而文章开始所提到的一系列艺术机构的网络操作套路也在新冠时期合情合理地应运而生。在数字网络媒介成为艺术机构们将曝光率转化为利益的工具时,不断更新的网络科技产品也为展览所用,形成了新媒体艺术的参与式呈现和沉浸式视听盛宴。网络于艺术而言或许不再是社会、文化与技术,也不再是这个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与漏洞、权力与操控,而是“后网络”艺术实践中,将“网络思维”折合为艺术物时的“视觉修辞”。8.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后网络艺术”,2020
在种种线上与线下的浮华盛宴背后,是艺术机构处于网络带来的社会文化转型中,为了实现自我增长而进行的精准定位。虽然白盒子十分重要,但今天的许多艺术机构已不再单独依赖物理实体,而是有策略地将这种对实体的依赖附着于网络的传播效应与科技红利之上。艺术行业也因此晋升成为实体经济、网络经济与城市复兴之间价值流通的关键媒介。它们是创意产业的支柱,也是资本和权力计算中尤为重要的同谋。新冠病毒对当代艺术常规操作的悬置可以说是给了我们一个在“美术馆疲劳”与“双年展创伤”中喘息的机会。艺术行业终于可以暂时慢下来,让作为艺术工作者的我们得以安静地反思与探讨艺术究竟为谁而做,机构又为谁而活。在威尼斯双年展宣布因新冠而推迟后,社会学与数字理论学者本杰明 · 布拉顿(Benjamin Bratton)于4 月发推文:“也许威尼斯双年展应该永远都不要再发生”。10.此处为笔者翻译,原文为“Perhaps the Venice biennale should never happen again.” 原文见Benjamin H. Bratton 于2020 年4 月5 日11:21 的推特发文。威尼斯双年展的命运如何我们暂不做推测,而在新冠时期我们仿佛看到艺术对网络与数字的情趣与偏见是如何通过种种线上实践潜回网络,遍布于公众号、网页、邮箱以及视频与购物平台之中,由此形成了又一轮的视觉与信息奇观。
伴随这个初具规模的数字奇观的将会是“艺术”对公共数字资源的抢占与对网络环境的污染吗?伴随机构种种线上应激措施的将会是新一轮的审美疲劳与浏览创伤吗?今天艺术机构们的网络实践让人不得不担心,在不久的将来,人们也许将如抵触威尼斯双年展一样默默期许某些艺术机构的网络实践也“应该永远都不要再发生”。
4.
一些艺术机构面对数字网络的操作套路与偏见长期受制于一组紧张关系。这组张力存在于受现代主义影响的艺术运作常规与直接影响了后现代理论、并推动当下社会结构性变革的数字网络之间。前者专注于去社会情境化的白盒子与“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物,并已衍生出一套以此为轴的艺术生态与价值体系。而后者则代表了数字网络科技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之间的纠缠(entanglement)与内在互动(intraaction),及这些纠缠与互动带来的对时间、空间、地域、权力与价值的重新定义。

本杰明 · 布拉顿的推特页面 图片来源:网页截屏
对于数字网络,曼纽尔 · 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或许可以提供一个关乎经济却又直指社会文化的注脚。11. Manuel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ume1, 2nd ed.,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0).卡斯特尔认为,互联网与无线通信带来的是多重的通信和交往模式,和与其紧密结合的、本质性的文化变革。曾经所谓的“虚拟”在今日成为必不可少的现实。数字网络在今天已经无法与社会组织和实践分离,因为它直接关系着社会组织与实践的行动方式、场域、价值流通、作用范围与社会影响。在今天,网络已经成为了“网络社会”(the network society)。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冠危机对艺术套路的暂停反而带给了机构们一个接受并了解网络社会的窗口。相应的,艺术机构也必须开始面对网络社会提出的双重命题:当代艺术的社会责任究竟是什么;以及机构如何在网络社会中将这个社会定位转换为行动。
针对当代艺术如何对数字网络进行有效反应与实践的问题,艺术史学者与评论家克莱尔 · 毕晓普(Claire Bishop)曾于2012年在《艺术论坛》发表文章,呼吁艺术界正视网络文化和技术对日常生活带来的本质性改变,及其对当代艺术定义的直接影响。12. Claire Bishop,"Digital Divide: Contemporary Art and New Media", Artforum, September 2012
保守来看,当代艺术的数字网络实践的快速增长与成熟期可以追溯到万维网(World Wide Web)开始普及的上世纪90 年代。从早期由JODI15.居住于荷兰的艺术家琼 · 希姆斯克特(Joan Heemskerk)与德克 · 帕斯曼(Dirk Paesmans) 组成的艺术团体。与欧莉娅 · 利亚利娜(Olia Lialina)代表的net.art,到本世纪初扎根于软件编程、开放源代码社区、战术媒体(tactical media)、区块链技术、骇客主义、以及社交媒体的一系列互联网艺术(Internet Art),数字网络艺术往往继承激浪派反艺术常规的跨媒体实验(intermedia)的方式,并将其与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具有政治力量的社会情境构造的实践结合,形成了针对网络社会与其技术基础的探索、批判和介入。16. Dick Higgins and Hannah Higgins, "Intermedia", Leonardo, 34.1 (2001), 49–54.影响此类艺术实践的还有行动主义艺术、草根文化与其社会组织方式、海盗/私人电台、朋克音乐与文化、独立音乐、科幻文学与电影、街头艺术合作等。同时,也有一部分以Furtherfield 为代表的艺术组织(organisation)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不断探索艺术与网络文化科技在社会中的角色。受数字网络去中心化组织方式的启发,这些替代性组织从自身开始反思并改革艺术机构运作模式,将艺术机构定位为揭示并重构网络科技、以及其承载的社会文化关系的开放社区,以此来支撑数字网络艺术对技术与文化的双重介入。这种情境内的、有政治文化动能的艺术实践和替代性组织,可以看作是对现代主义审美支持的文化再现以及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文化消费奇观的替代与反叛。由此观之,网络艺术实践其实与毕晓普对社会参与艺术的研究以及她对当代艺术权力结构与去政治化倾向的批判可谓是目的一致、殊途同归。17. Claire Bishop, "Sweeping, Dumb, and Aggressively Ignorant! Revisiting 'Digital Divide'", in Mass Effect: Art and the Interne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2015), pp. 353–56.因此,在网络艺术实践已进行了二十多年后,毕晓普质问当代艺术对网络的不作为,便显得尤为吊诡。毕晓普对当代艺术整体的指责不仅揭示了她对数字网络艺术的忽视,也真实地反映了主流当代艺术对网络技术与文化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主流艺术长期将网络作为一个热点话题,而另一方面,无论这个话题被重提多少次,都无法扭转艺术行业对网络艺术实践的不解与排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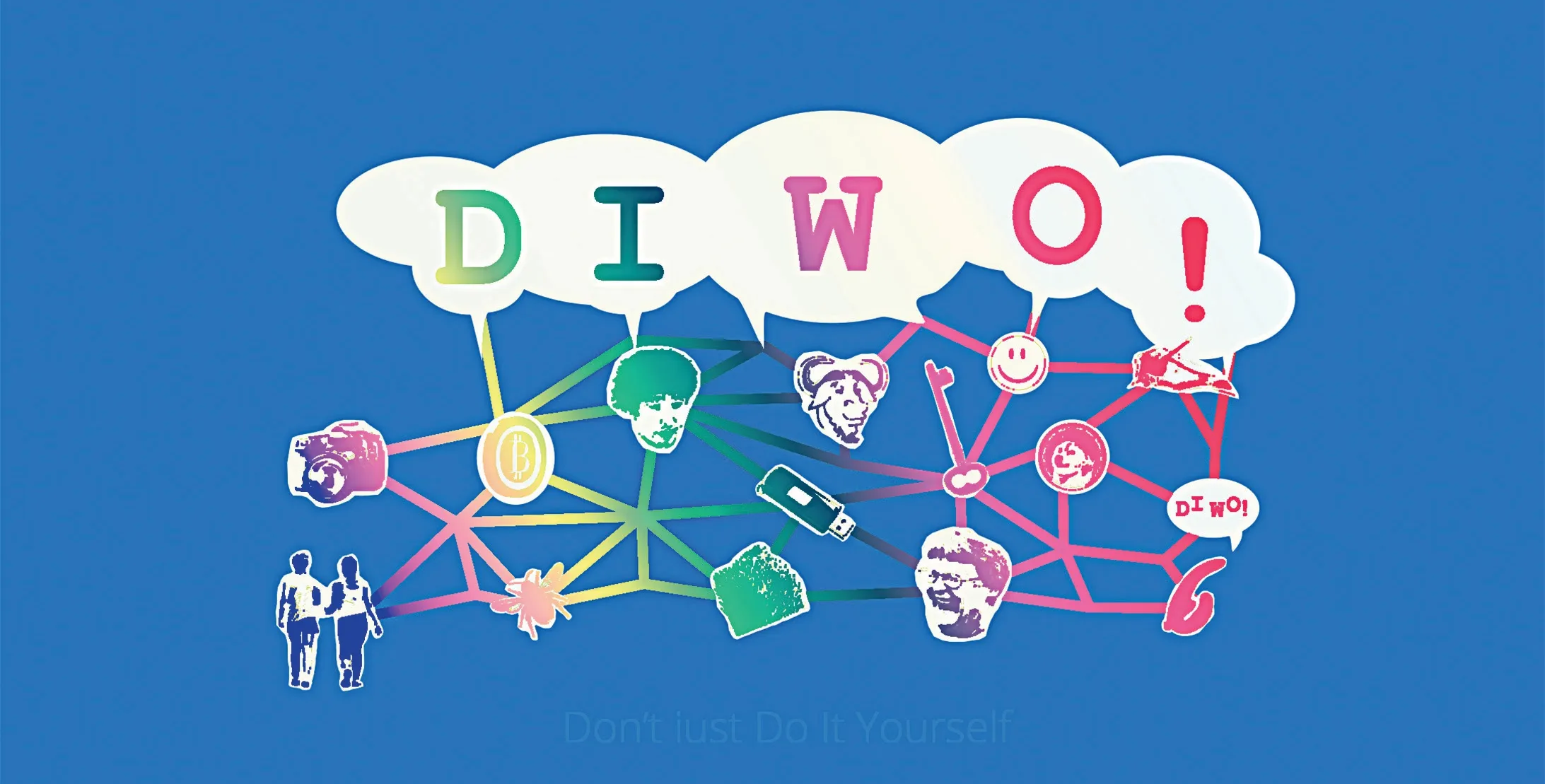
Do It With Others (DIWO): E-Mail-Art at NetBehaviour, 2007(Furtherfield 的邮件艺术项目 © Furtherfield)Furtherfield 是伦敦最早的艺术与科技(去)中心。其于1996 年至今一直致力于探索与数字与物理网络相关的艺术实验与合作。此项目是对沿袭激浪派艺术邮件艺术的数字网络尝试,其目的是探索在数字网络中与其他人连接、交流和合作的方法。DIWO 作为对DIY(Do It YourSelf)文化的拓展与修正,已经成为Furtherfield 的精神,长期指导该组织对去中心化艺术实践的探索,并启发其对艺术与科技在当代社会中角色的讨论。对艺术生态中精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反思,和对科技行业中的权力扩张与专家统治(technocracy)的替代性方案的探索,是Furtherfield 长期以来的使命。
5.
毕晓普于2014 年曾在纽约新美术馆(New Museum)与MIT 出版社合作出版的Mass Effect中对2012 年的争端作出回应,称其两年前的文章其实是面对主流当代艺术的批判和号召,并没有抹杀数字网络艺术实践的意图。18. Claire Bishop, "Sweeping, Dumb, and Aggressively Ignorant! Revisiting‘Digital Divide'", in Mass Effect: Art and the Interne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2015), pp. 353–56.在同情毕晓普两难境遇并为网络艺术实践的边缘化打抱不平的同时,毕晓普的两篇文章所反映的当代艺术文化对网络艺术实践的纠结现状也许更值得我们关注。
直到2014 年,网络艺术实践与大多数艺术机构的关注点之间仍然隔着很远的距离。两个阵营所关注的方向截然不同,网络艺术实践追求反常规、反资本、对艺术与网络均有扰乱作用的网络情境主义艺术实践,而主流机构往往致力于批判性修正现代主义美术馆的展示方式与价值取向。两者有着知识背景上的差异,其间的沟通也因此充满了傲慢与偏见。而两者之间的距离又由无数个对政治敏感、对资本警觉、却对网络和科技知之甚少的像毕晓普一样的艺术研究与从业者填满。

新时线艺术中心在线特展“We=Link:十个小品” © 新时线艺术中心 (CAC) 展览委任十个艺术作品,每个作品都是“互联网原生形态”。此展览通过十二个国际机构联合主办,目的在于实现国际媒体艺术社区的互助,并合力探讨“处于自然与社会动荡及危机中的人类之普遍状况”。
与此同时,在主流当代艺术生态中还有着另一个断层。这个断层存在于毕晓普们和Ta 们所批判的保守现代主义艺术运作体系之间。用毕晓普本人的话来形容,后者所指代的是那些“模拟艺术与档案恋物癖们”(The analog and archive fetishists)以及那些“被特富龙(不粘锅)涂层隔离在金融圈之中的画廊们”(The gallery world is so Teflon-coated in finance)。19. Bishop, "Digital Divide: Contemporary Art and New Media".毕晓普们所希望的是艺术机构可以在资本— 物质的绑定关系中得以松动,以此为社会、政治、环境参与艺术(socially,politically and environmentally engaged art)腾出一片喘息空间。而资本的追逐者对毕晓普的呼吁至今也并没有什么主动的、实质性的回应。在这些资本弄潮者们的眼中,毕晓普关于数字网络的争论更是有如无物。毕竟这些话题离资本风口与流量红利着实太远了。
面对艺术生态内一层层的沟通障碍、知识鸿沟与价值观冲突,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代艺术重新认识“数字网络”可谓是道阻且长。
6.
新冠带给了艺术生态太多冲击。同时,向当代艺术机构介绍更多网络艺术实践的丰富与可能,或许也并不能让其在主流当代艺术中得到更多关注或认可。因为阻碍了艺术生态对网络艺术实践的接受与认知的实则为艺术生态中价值观的撕裂,以及艺术实践者之间逐渐固化的沟通阻隔。如果乐观一些来看近期的实践,从“UCCA × 快手‘园音’线上音乐会:良樂”20.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UCCA × 快手 “园音”线上音乐会:良樂 | UCCA”, 2020
在机构艺术项目的层面上,两个机构的实践也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位新冠危机和网络社会。比如UCCA 的“良樂”旨在突破“艺术传播项目或者艺术营销项目”的思维方式,通过对线上项目的探索,来与众多“有机的观众”连接,并“在艺术表达上和连接公众上展现出新的魅力”,来实现艺术“实质上的文化意义”。23.尤洋&榴莲,“ 坂本龙一在快手的直播红了,我们和促成这件事儿的 UCCA Lab 聊了聊 | SocialBeta 专访”, 2020
尽管“We=Link”和“良樂”两个项目均存在自身的意识形态局限,但它们在新冠时期将情境化的、有社会使命的实践带入网络环境,可以说代表了机构们带有数字网络意识(digital consciousness)的有力尝试。25.尤伦斯艺术中心对社交媒体的实践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将其看作是大众媒体推广平台。而这样的实践方式屏蔽了艺术对数字平台功能、规范、限制以及技术基础的批判性探索。艺术对科技潜在的人文约束也因此被收窄,转化为单纯的、通过网络分发的疗愈性艺术表演甚至文化狂欢。同时,新时线的"We=Link"则是并未在策展层面对已有的线上展览作出专业上的突破。该展览采用一种统一化(使用与艺术作品们脱离的集中型展览界面)、商业化(众多logo 簇拥,CAC logo 常在)、甚至传统美术馆的策展方式(使用文字解释与艺术家简介介绍艺术作品)来呈现其委任的十个网络艺术作品。艺术家们对这种策展手法的反应很微妙,例如JODI 在"We=Link"中的作品介绍如下:“name@mailbox/My%Emotica/RSS_CUT_Agency ICTI !Subscribe!!!_@%20%2... //202/NEWSLETTER-%;#--- Re:-N3WW$$W0RLD-EMPYRE@XXX$$$UPDATE!UPDATE!UPDATE!!!UPDATE!! UPDATE!UPDATE!UPDATE!!!UPDATE!!UPDATE!UPDATE!UPDATE!!UPDATE!UPD TE!_!UPDATE!! !UPDA ”在这段作品介绍旁边,我们没有看到文字解释。JODI 对展签的抵触由来已久:“只要我们能做到,我们就会试图拒绝(新闻稿、展签和艺术家信息)”。的确,既然网络艺术实践足以在网络环境中自洽,并长期试图挑战现代主义对表现(representation)的执念,策展人又何必通过文字来破坏人们与作品的直接连接和交流呢?JODI,“Interview with jodi”, (1997)
面对网络社会对关系和价值的重新定义、数码网络对艺术行业运作常规的挑战和艺术实践对网络情境介入的探索,机构们需要调整定位,寻找与真实社会文化对接的运作方式。“我们的体制让行业中的院校、策展人与美术馆拥有一种掌握当代文化的幻觉。实际上,今天的文化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平行的世界。而我们作为艺术行业的从业者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掌握一些新的文化。所以美术馆在相应文化资源转换方面做得有所欠缺。”“良樂”的策划人之一尤洋在笔者的采访中指出:“这种文化资源转化的不适应造成了今天艺术行业的一些困境。比如(有些机构们)一做项目就说没钱、无法实现。(比起经济上的困难)我们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对文化的认识不足和对文化资源的转换不准确。我们在这个时代不是有‘文化’的人。那么美术馆如何发挥平台作用,吸引懂‘文化’的人一起合作来进行文化实践,就变的尤为重要。”艺术机构面对自己在网络社会背景下的文化理解障碍,摒弃对网络的傲慢与偏见也许的确是第一步。然而这种跨行业合作的普遍化与合法化是否会将当代艺术机构定格成为科技公司合伙人,此刻下结论或许为时过早。
可以肯定的是,专注于网络真实情境的艺术项目可以帮助艺术机构尝试摆脱常规、理解网络社会现实,并在复杂多重的当代社会文化中寻找新的定位与表达途径。在这些尝试之中,机构能够与艺术实践共同探索当代艺术的边界与艺术为谁而做,如何做的问题。27. Christiane Paul, "Challenges for a Ubiquitous Museum: From White Cube to the Black Box and Beyond", in New Media in the White Cube and Beyond: Curatorial Models for Digital Art, ed. by Christiane Pau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Garrett.在其间,我们或许可以看到更多机构带领当代艺术超越对消费、服务、资本和经济的关注,在不回避网络的社会现实中重塑能够驱动艺术发生的共同体和公共地带(commons and public realms),并以此将今天已经趋近边缘的、对社会、文化与政治的探讨重新引入当代艺术生态之中。
7.
新冠与否,艺术与生活都仍将继续。此时此刻,国内的艺术行业或许迎来了至暗时刻后的一丝喘息,而当代艺术的艰难也开始在全球同步。多国的艺术机构们正在探索跨越国界的互助与支持途径时,国内的艺术机构或许也可以与全球的艺术机构们一道做出更多尝试。当越来越多的中国艺术机构将自己定位为兼具本土艺术责任与国际化视野的机构时,我们应当期许它们在国内外蔓延的种种焦虑、恐惧、排斥与谣言之中,通过网络帮助中国当代艺术发出一点微弱但有力的声响。
当瘟疫过去,或当机构不再视当下为例外,有些机构或许会回归常态,继续其在现代主义框架下的角色设定,并保持其对网络科技与文化的营销套路和艺术情趣。也有些机构或许将继续对网络社会的关注与探索,反思把网络作为话题与趣味与将网络作为自己需要关注的当下现实这两种态度之间的区别,并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重塑机构使命。站在网络社会与当代艺术交汇的界面,笔者深知行文与实践之间的距离,行文间最大的希望是艺术机构们可以平安度过此次瘟疫的冲击。但同时,也希望机构能够利用新冠瘟疫导致的强制刹车来促进行业内的反思和讨论,帮助自己真正进入这个正在被数字网络重新编制的当下,而不是用数字技术和网络去延续那些物理空间中的既定进程。毕竟,曾经设想的“未来”属于过去。而身在这场全球风波之中的我们所经历的当下,也许就是因新冠而提前到来的,最真实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