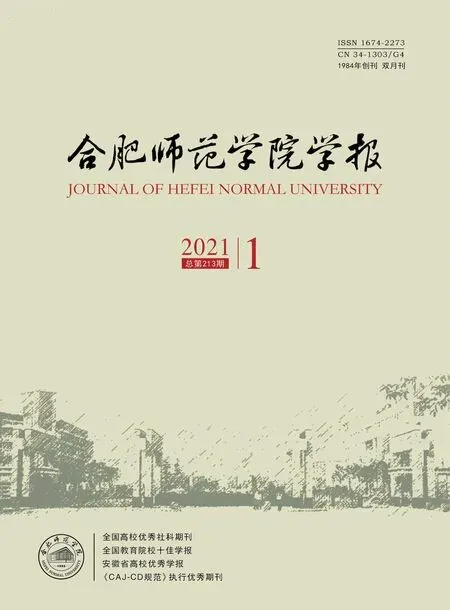爱伦·坡《丽姬娅》中的“暗恐”解读
2021-01-17鲍忠明
郝 情,鲍忠明
(北京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1)
爱伦·坡大部分作品聚焦美丽女子的死亡主题,与他在《创作哲学》中所推崇的理念——“一个美丽女人的死亡,无疑是世界上最具诗意的话题”[1]323——相契合,极具哥特之风的恐怖短篇《丽姬娅》尤为典型。该小说以第一人称有限视角,即叙述者的口吻,讲述“我”的妻子丽姬娅因病死亡却在小说结尾处突然复活的故事,堪称弗洛伊德所谓“僵直和死人的复活[是]最暗恐的主题”的典范案例[2]236。《丽姬娅》以陌生化手法,运用大量模糊、碎片化的语言与记忆、恐怖的意象和内心独白刻画人物,描绘环境,令丽姬娅的身份和形象之谜深陷争议与诡怖之圈,使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叙述者与丽姬娅之间的男女权势关系,“暗恐”效果呼之欲出。
“暗恐”着重塑造诡秘恐怖的印象与氛围,引发人与非人、熟悉与陌生的模棱两可的状态,并与心理学中的压抑重现和阉割情结存在较大关联。在概念层面,童明基于心理分析,概述弗洛伊德文章《暗恐》的情节,归纳出“暗恐”的五大特征:非家和家并存、在忘却状态下的“记忆”、压抑复现、负面情绪以及历史的方法,并探讨了其负面美学现象及现当代研究意义[3]。王素英与童明在研究内容上存在交叉,从心理分析、存在论、否定美学以及现代性四个层面详细阐释了“暗恐”(恐惑)概念[4]。在文本实践层面,何庆机、吕凤仪重点关注对福克纳《献给艾米莉的玫瑰》中双重性的解读,体味其怪异之感[5],于洋则以雪莉·杰克逊的短篇《摸彩》为例,以怪怖者(同“暗恐”)理论分析小说的恐怖特征,创新性地结合拉康的能指理论和“自动机”概念来阐明主体关系[6]。值得注意的是,坡的作品虽是国内“暗恐”研究偏爱的对象,而且身份、记忆和自我的问题早已引发有关《丽姬娅》文学阐释的激烈争论,目标故事中的女性“暗恐”却少为国内研究涉及。此类论争的焦点集中在:丽姬娅是叙述者的另一自我,还是坡的另一自我?她到底是人,还是非人的暗恐事物?譬如普洛斯佩(R. C. De Prospo) 抛弃传统的二元性别对立观,集中以人的视角来探讨丽姬娅的真实身份,并提及了记忆的模糊性[7]。再如玛丽塔·纳达尔(Marita Nadal)曾提到,丽姬娅于叙述者而言是创伤般的存在,她提醒叙述者,试图回归被记忆阻隔的过去是徒劳的尝试[8]。此外,叙述者还显示出了由丽姬娅的神秘身份而引起的阉割焦虑。鉴于此,本文首先对心理分析中的“暗恐”予以界定, 然后从情节、意象、叙事三个层面分析《丽姬娅》中的诡秘元素和陌生化、丽姬娅的女性特质及其产生的“暗恐”印象。
一、心理分析中的“暗恐”
弗洛伊德在《暗恐》中强调,“暗恐”是可怕的,“它会让我们回到我们早已熟知、曾经非常熟悉的事物上”[2]223-224。换言之,“暗恐”未必产生于人所不熟悉的事物,相反,它极有可能产生于人曾经的经历。“暗恐”一词是德文“unheimlich”的直译,意为“隐秘的”。巧合的是,弗洛伊德发现其反义词“heimlich”也具有“隐秘的”的含义。但这并不意味着“heimlich”本身是歧义性的,它只不过具有完全相反的双重意义,包含“一种矛盾和模棱两可”[4]132。“Heimlich”另一重含义为“如在家的,舒适的”,蕴含着“安全的,熟悉的”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unheimlich只不过是heimlich的亚等级而已”[2]226,这代表了熟悉的事物具有变成暗恐诡异的事物的性质,同时也印证了弗氏的主张:“暗恐”是由人们熟悉的事物所引发的[2]。因此,“暗恐”是“熟悉和不熟悉的并存”[3]112。
众多论者参与了“暗恐”的源头之争。庞特(Punter)认为暗恐提醒我们 “生命或思想并没有明显的开始,我们由先前的痕迹构成,其中一些痕迹可用于有意识的记忆,但大多数痕迹沉陷于原始的过去,该过去无法通过有意识的方式恢复,但会继续产生影响,甚至可能决定着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9]132。弗雷德·博廷(Fred Botting)所谓的“暗恐”指涉“古老欲望和恐惧的颠覆性回归,扰乱了人们对现实和常态的熟悉、亲切和安全的感觉”[10]11。因此,读者和叙述者或许会因无法辨识现实与虚构而模糊两者之间的界限。弗洛伊德则认为暗恐的另一特征是强迫性重复,亦即曾经发生过的痛苦或可怕的经历的不可控制式的回归[2]。在多数情况下,由于其强迫性,它以一种不可抑制的方式不断侵入并模糊人物的记忆,困扰和折磨着他们。弗洛伊德将这种心理现象定义为“创伤性神经症”,最初表现为士兵从残酷战争中归来后出现的精神休克、错乱的症状[11]。战争中的某个场景压抑于士兵的无意识之中已久,造成遗忘的假象,后又突然复现于其噩梦中,士兵被迫重历创伤回忆。
谈及“暗恐”效果的产生机制, 弗洛伊德引用了恩斯特·詹池(Ernst Jentsch)的论断。詹池认为心智的不确定性是其机制运转的必要因素:“在讲故事时,轻松制造暗恐效果最成功的方法之一就是让读者不确定故事中的某个人物是人还是机器人”[2]227。譬如,文本故事中丽姬娅的身体是否具有生命就引发了读者的怀疑,该点可从叙述者将其描述为“影子和裹着尸布的东西”的话语中得以管窥[12]34, 54。然而,德国小说家霍夫曼(Hoffmann)以其《沙人》的故事否认了詹池的观点。“沙人”是一个邪恶的家伙,专挖孩子的眼睛,他用极度可怖、血腥的方式在孩子的眼睛中灌满沙砾,然后等待眼珠自动蹦落。而后,这些眼珠会被“沙人”拿去喂养他的孩子。主人公纳撒尼尔(Nathaniel)的母亲常用此故事来吓唬她的孩子不要晚睡。后来,在纳撒尼尔的认知中,他父亲的合伙人科佩留斯(Coppelius)就是可怕的“沙人”。如果不是纳撒尼尔父亲的阻拦,科佩留斯差点夺走了他的眼睛,科佩留斯于纳撒尼尔而言也就成了阴影般的存在。对纳撒尼尔来说,占据他意识的一直是对失去双眼的恐惧,霍夫曼将这其中的“暗恐”印象归因于“被人夺走双眼的念头”[2]229。弗洛伊德则从心理分析的角度,以俄狄浦斯刺瞎双眼为例,将失眼之惧指涉为阉割之惧。
二、情节设计的神秘性与陌生化
《丽姬娅》在故事开篇便奠定了“暗恐”基调。当叙述者谈到丽姬娅的本源时,两人初次相识的记忆似乎被抹去了:“天哪,我不记得我是如何、何时、甚至确切地在哪里认识丽姬娅女士的了”,叙述者把这归结于他“微弱的记忆”[12]33。令人惊讶的是,作为丽姬娅的丈夫,叙述者甚至不知道她的“父姓”[12]34。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叙述者,一个声称自己因记性不好以致于忘记了丽姬娅的背景和他们初次相遇的人,却能准确描绘出丽姬娅的外貌:“高阔苍白的额头”,“与最纯净的象牙相媲美的皮肤,威严的程度”[12]35。坡将本应互相熟知的夫妻关系陌生化处理,为丽姬娅的身份平添神秘之感,蒙上“暗恐”面纱,暗示着丽姬娅虽是叙述者心爱的妻子,却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角色。丽姬娅失去了表露自己身世的权利,也被排除在叙述者的表述之外。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曾提到,“在一种普遍使用男性主义的语言中……女性是无法被表征的。换言之,女性是不被考虑的,女性代表了语言的缺失和不透明”[13]13。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丽姬娅被描绘成一个笼罩在叙述者生活中的影子,总是悄然进入叙述者的封闭书房而不为所知。进一步言之,在叙述者的认知中,丽姬娅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飘荡的影子,不被察觉且令人恐惧,这种陌生化的塑造使她的形象更具“暗恐”之感。同时,丽姬娅影子般的存在暗示了其对叙述者无形中施加的巨大压力,丽姬娅具有“渊博的学识……悦耳迷人的口才”[12]33,这或许使叙述者的光芒黯淡许多。
叙述者认为丽姬娅是一个绝色美人,然而他“觉得有很多‘奇异’弥漫其中(丽姬娅的美丽),但要想找出什么不规则的地方,追溯感知中的‘奇异’,却是徒劳无功”[12]35。事实上,叙述者早已观察到,丽姬娅的奇异之处表现在她的黑眼睛里,“那双又大,又闪,又神圣的球体”,超乎凡人般地,“比我们这族人的普通眼睛大的多,比诺耶哈德谷部落最圆的羚羊眼睛还要圆”[12]36-37。凭借对丽姬娅那双深不可测、非人的眼睛的描述,叙述者将她排除在人类种族之外。那双眼睛背后的奥秘总是驱使着他对它们彻底审视,并怀着“接近其表达的全部知识”[12]37的热情。此外,叙述者痴迷式的解密实际上反映了他对丽姬娅眼睛异常之处的极度不安与焦虑。他热切地思考着那双眼睛背后的内容;“我琢磨了好长时间!整个仲夏之夜,我多么努力想要看透它啊!它是什么——比德谟克利特的井更深奥的东西?”[12]36-37。苏珊·森辛迪夫(Susan Sencindiver)认为,在一个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建构中,“真正的女性是缺席的”,男性主人公声称女性是对其身体完整性的侵犯,而女性生殖器则是阉割的象征,它激发了男性对阴茎缺失的恐惧[14]4。此处的德谟克利特之井便是女性生殖器的代指,该文本将丽姬娅的眼睛与该井作比,印证了叙述者的阉割焦虑,并赋予丽姬娅以垂坠感和阴森感,从而产生了“暗恐”效果。
三、丽姬娅的女性暗恐特质
心理分析学派在对女性的讨论中,总是无法规避其母性特质。为此,俄狄浦斯情结应运而生。俄狄浦斯因其弑父娶母的罪过深感愧疚与羞耻,选择以刺瞎双眼这一自我阉割的弱化版的方式来惩罚自己。弗洛伊德在评述《沙人》时明确表示,对失明的恐惧“往往足以取代对阉割的恐惧”[2]229,亦即一个人的双眼失明是阉割情结的象征。身体器官如眼睛的丧失,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男性阳具的丧失,从而诱发人产生“暗恐”情感。
叙述者的俄狄浦斯情结主要体现在他对丽姬娅母性特质的强烈情感依恋中。譬如,叙述者以婴儿的姿态自愿屈服于丽姬娅,并甘心听凭她的指引“探索混乱的形而上学世界”[12]39。叙述者甚至说,“没有丽姬娅,我只是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孩子罢了”,这种母子般的情感依附为叙述者提供了安全感和稳定感[12]39。因此,丽姬娅的逝去在很大程度上给叙述者以沉重打击,成为萦绕在他心灵深处不可磨灭的记忆。弗雷德里克·斯维那乌斯(Fredrik Svenaeus)讨论了弗洛伊德著名的“去/来(fort-da)”游戏——“其小孙子把一个带线的玩具扔到他看不到的地方,随即说出‘去’字,之后,再凭手中的线把玩具拉回来,说出‘来’字”,以此反复,以尝试摆脱失去母亲的痛苦,总结出孩子失去母亲是一次创伤经历,会刺激他对暗恐的敏感度[15]248。另外,孩子与母亲的分离实则是其“自我”形成的开始,但叙述者显然一直未能完全脱离丽姬娅的影响。
此外,丽姬娅拥有一种“狂热的渴望”——“言语无法传达她与死神搏斗的那股强烈的反抗力”[12]40。丽姬娅对生之渴望和对死之抵抗如此炽热,“她那双狂热的眼睛闪耀着灿烂的光芒”,费力发出求生的信号,丽姬娅坚定的意志似乎预示了她结局的重生[12]40。故事所引约瑟夫·格兰维(Joseph Glanvill)的话进一步证实了该判断:“人既不臣服于天使,也不屈服于死亡,除非他意志薄弱”[12]43。这句题词指出了一种理性逻辑,即只有意志薄弱的人才会屈从于死神,显然丽姬娅并不包括在内。
从文本蕴涵的开放意义层面看,丽姬娅可化身为多种形象,具有多重身份。帕特里克·奎因(Patrick Quinn)引述了波德莱尔(Baudelaire)的观点:“坡笔下的人物……就是坡本人。还有他笔下的女性……她们也是坡”[16]220。因此,丽姬娅是坡的另一自我,映射出坡万千面孔中的一面。卡特(Carter)说,丽姬娅自身特有的奇异特质如“大而闪的眼珠”、渊博的学识以及超凡的美丽促使她成了一个“他者”[17][12]。换句话说,丽姬娅既是坡的一部分,也是坡的“他者”。她代表了坡熟悉面与陌生面的结合。因此,卡特否认丽姬娅的女性身份,声称她是一个被谋杀的缪斯女神,其存在是为了刺激叙述者的思想,促进他的发展。类似地,劳伦斯(Lawrence)直接否定了丽姬娅作为自由人以及女人的身份,称丽姬娅为“一种试剂,一种反作用力,近乎虚幻”[18]177。
文本话语也同样证实丽姬娅被赋予了人类以外的多重形象。譬如,丽姬娅被描绘成“居于神龛里”的天使,拥有“所有神圣的东西”:“更狂野圣洁的”容光和眼睛、“完美无暇的”额头、闪耀着“圣光”的牙齿,承载着“天上人间之美”[12]35-37。叙述者合理地将丽姬娅所表现出的奇异性归因于她的神圣特质。然而,文中描述的丽姬娅黑影的迭现与其天使意象形成鲜明对比。另外,丽姬娅特有的诡异特征,一头浓密的黑发,独特而骇人的眼睛,疯狂的话语,压抑的活力,再加之文中蠕虫所经历的血腥场景,使她俨然成了一个吓人的怪物。
《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一书的书名借用了《简·爱》中罗切斯特原配妻子伯莎·梅森的形象。同丽姬娅一样,梅森象征着书中时代怪物般的“他者”,她也是一个充满激情、可怖的外来者。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Sandra Gilbert and Susan Gubar)刻画了两种极端的女性本质,一种为传统意义上顺从、温柔、善良的“家中天使”,另一种则是“阁楼上的疯女人”,指向女性被禁锢的自由、愤怒和力量[19]。目标文本通过“六等星,双重星”[12]38的隐喻,使读者相信丽姬娅天生便承载着易变的特质。叙述者在观察“生长的葡萄藤蔓、蛾子、蝴蝶、虫蛹、流水、海洋、流星”[12]37时均注意到了丽姬娅眼中的“暗恐”。丽姬娅难以捉摸的本性在这些流动而缺乏整体性的繁杂意象的映衬下得到凸显,进一步强化了叙述者感知的不确定性。伊丽莎白·洛佩斯(Elisabete Lopes)认为丽姬娅的可塑性也体现在“五角形婚房的空间布置”[20]45上。婚房暗示了她爬行动物的本质——窗外一棵“陈年藤曼爬上了塔楼厚重的墙壁”,“拱形的”天花板“奇高无比”[12]45。显然,丽姬娅向往自由且多变。然而,丽姬娅虽融合了两种极端的女性本质,文本却更侧重对其怪物形象的塑造。
关于小说中的这首诗,加里森(Joseph M. Garrison)指出最后一个诗节预示着丽姬娅无法复活。他认为,叙述者从认识论的角度试图寻求人类无法理解的本质,也只是徒劳[21]。“爬行状”和残忍血腥的意象,如“血红色的东西”、“害虫的毒牙”和“人血”,明显给丽姬娅增添了怪物的气质[12]42。正如霍华德(Howard)所言,评论家倾向于将诗中的蠕虫与“爬行状”、“坟墓和撒旦”联系起来,强调“蠕虫是蛇的古时称谓”[22]40。简言之,丽姬娅和恶魔蛇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联系。婚房的装饰便反映了她蛇形的特征:巨大的香炉中不断散发出的翻滚烟雾和斑驳火焰以及螺旋状的窗帘,都印证了丽姬娅的蛇性[12]。而蛇的形象极易让人联想到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美杜莎,丽姬娅同样是美杜莎的化身,文中叙述者“浑身发冷,冻成了石头”[12]53,“暗恐”印象也由此产生。基于女性主义来看,美杜莎的意象不仅表明了丽姬娅的恐怖,还揭示出其女性的愤怒。此外,弗洛伊德在《美杜莎的头》中指出,在心理分析中,由于某种视觉原因,对美杜莎的恐惧等同于对阉割的恐惧(1)Freud, Sigmund. Medusa’s Head.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XVIII (1920-1922):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Group Psychology and Other Works[M]. 1922.。这与女妖美杜莎头上的蛇形毛发有关,它是阴茎移位的替代性比喻,而阴茎的缺失是恐惧的根源。因而,蛇出现在最显眼的位置实际上是在警示阉割焦虑的存在。叙述者的僵硬象征着他的阴茎的存在与勃起。因此,丽姬娅的在场是叙述者减轻恐惧的一种替代形式,代指阴茎的缺失。
此外,婚房里诡秘阴森的装饰显然是有悖常理的。房间到处弥漫着死亡的窒息气氛,覆盖物比比皆是:顶篷、窗帘、垂饰、挂毯和裹尸布,而这些物品均是用来掩盖某些不能披露的东西。这实则是叙述者刻意抹杀丽姬娅真实身份的体现。丽姬娅被裹尸布包裹着,被禁锢在密闭的房间里。即使丽姬娅再次复活,她的身份却依然隐形,无法被人识别,不被男权承认,永陷神秘之渊。
总而言之,丽姬娅在文本中被构建为身份模糊不定、“暗恐”凸显的“怪物”女性。尽管丽姬娅激情万丈、学识罕见、声音纤柔,却仍是男权社会中的失势者与异类,自身的存在只是对于叙述者阉割焦虑和俄狄浦斯情结的在场证明。此外,丽姬娅大而闪的黑色眼睛、无声的脚步、变幻的形象、诧然的复活等神秘诡怖的特质均赋予了其“暗恐”之感,叙述者也因此深困于模棱两可与压抑恐惧的印象牢笼。
四、不可靠叙述
坡在其哥特式短篇中往往以第一人称有限视角展开叙述,以此拉近读者与人物意识之间的距离:叙述者意识牵引着读者感知,诱发读者真实感的产生。但与此同时,读者只能透过叙述者的主观视角来间接接触故事,获取由叙述者意识加工过的讯息,因而无从得知文本所述是否为客观事实,《丽姬娅》当然也不例外。坡以叙述者的第一中心视角描摹丽姬娅的女性与“暗恐”特质以及这些特质对叙述者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小说结尾处丽姬娅的复活,其怪怖效果令人不寒而栗。然而,文本种种迹象表明叙述者实则并不可靠。再者,叙述者眼中的丽姬娅亦人亦怪、亦真亦假、亦生亦死,处于一种阈限空间之中。
首先,叙述者作为读者获知丽姬娅信息的唯一来源,开篇即言其记忆衰退以致对丽姬娅的本源一无所知,后文却准确记得丽姬娅的面貌以及婚房的布置,“我清楚地记得这个房间的一切细节”[12]44,叙述者波动的记忆与前后相悖的言语难免令人生疑。此外,文本叙述多次涉及鸦片。叙述者“成了禁锢在鸦片枷锁中的奴隶”,其“工作和习惯都沾染着梦境的颜色”,丽姬娅具有“鸦片梦境中的容光”[12]35 , 44。叙述者对鸦片的疯狂同样使读者怀疑他是否具有辨别现实与幻想的能力。叙述者所言所见究竟是客观事实?亦或只是其嗔于鸦毒而虚构的幻象?文本中模糊话语的出现:“也许”、“好像”、“模糊不定的影子”等,既是叙述者对自身意识不确定的体现,同时也为整篇故事营造了朦胧氛围[12]33, 48, 49。
其次,第一人称局限于叙述者的主观意识,而叙述者在叙事时明显带有偏见。他视罗威娜(Rowena)为“丽姬娅的替代者”,不久便对她厌恶至极,与其追忆丽姬娅的思念至深形成了强烈反差[12]44。此外,文本叙事中多次提到丽姬娅总是乍然惊现于叙述者的梦中或回忆里,扰乱其心神,而罗威娜对叙述者的躲避与恐惧竟让他心生窃喜,不由得使读者怀疑他的精神状态。更有甚者,叙述者不顾客观科学原理,暗示丽姬娅具有超自然的能力,她的复活似乎是通过某种原始的神秘仪式占领了罗威娜的身体。罗威娜并没有看到落下的“三四滴明亮的红宝石色液体”,便一口吞下了酒,然后在叙述者的眼前死去[12]49。叙述者故意向她隐瞒了几滴血液的存在,这表明他在实现其愿望的途中很有可能沉浸在对丽姬娅复活的期待中,并无视罗威娜的死亡,或者叙述者是在掩盖他毒死罗威娜的事实。这样分析令小说的“暗恐”效果刹那间陡增。
再次,叙述者对丽姬娅也只是进行了粗糙浅薄的描述:个高、纤瘦、黑发、黑眼睛、白皮肤、额头高阔、声音温柔等,缺乏具象化的细节辅证。这些基础、碎片化的特征并不能使读者拼凑出完整的丽姬娅,相反,丽姬娅的形象更加抽象与模糊。类似地,叙述者的叙事也并不能使读者确定丽姬娅是人或非人,或两种身份并存。叙述者对丽姬娅外貌特征的刻画的确表明了她具备人的特质,但同时,黑影、奇异的眼珠以及藤蔓、飞蛾、蝴蝶、蠕虫、蛇形烟雾等零散诡异意象的涌现又体现出了丽姬娅的非人特征。丽姬娅的身份在不断变化更迭,这说明叙述者自身的意识也无法确定丽姬娅的真实面貌,或是或非,既是亦非,这也是引发“暗恐”印象的一大原因。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凭借其意识对丽姬娅的形象进行勾勒、整合和塑造,其关于丽姬娅的信息只是片面、主观的理解,而丽姬娅只在临死前发出了对上帝和死神的愤怒控诉,“上帝啊!难道事情就一直如此吗?难道这个征服者没被征服过吗?难道我们不是上帝的孩子吗?谁又能知道意志的奥妙和威力呢?人既不臣服于天使,也不屈服于死亡,除非他意志薄弱”[12]43,并且读者从该段话中根本体会不到叙述者视角里丽姬娅音色的低柔、甜美或如歌般婉转的语言。除此以外,读者根本无法直接接触丽姬娅,只能凭借叙述者的意识来推测丽姬娅的语言。缺乏话语权的女人,是由男人来感知和定义的。丽姬娅在文本中被建构为失语症女性。露丝·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在《痴呆的语言》中提出“女性话语”的概念并指出痴呆症患者与女性之间关于语言内部结构的类比[23]。女性同痴呆症患者一样,倾向于成为被讨论的对象,而不是讨论的真正主体,最终沦为过时的发声器。女性在男性中心话语中多处于被动地位,话语权与发言权被剥夺。正因为如此,文中由丽姬娅创作的诗歌也只能从叙述者的口中听到。因此,读者无法得知叙述中的丽姬娅是否是真正的丽姬娅。至于丽姬娅是生是死,读者也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当叙述者描绘活着的丽姬娅时,黑发与煞白的皮肤、黑影与蠕虫、话语权的缺失似乎暗示了她的死亡;而在丽姬娅死后,她却一直活在叙述者的记忆和梦中,似乎从未离开过叙述者。如此一来,丽姬娅的神秘“暗恐”并置于相悖的生死之间。
总之,凭借叙述者主观局限的视角以及不可靠的叙事,读者无法勘得事件的全貌,也无法置评故事的真假。读者不得不根据零碎的信息自行推测或拼凑出丽姬娅的形象。坡利用叙事的模糊性来展现丽姬娅的诡异身份,加强了丽姬娅所激发的“暗恐”之感,给人以混乱、不定、流动的印象。
五、结语
丽姬娅作为坡小说中女性“暗恐”的典范,尽管来历不明,却被赋予了多重身份——黑影、女性作家、非人的怪物、美杜莎等,其真实身份仍难以裁定。丽姬娅神秘的身份本源、微弱且难以察觉的脚步声以及大而圆、非人的眼睛既是陌生化手法的巧妙运用,也是其“暗恐”效果的体现。弗洛伊德认为,对双眼丧失的恐惧实则是对阳具丧失的恐惧,这更加深了丽姬娅的眼睛在叙述者心中的恐怖之感。此外,女性生殖器同样象征着男性的阉割。因此,丽姬娅的在场于叙述者而言是危险信号的持续性传达,警示叙述者的阉割焦虑。身为父权制文化中被压抑的弱势女性角色,丽姬娅被建构为可怖的怪物,其话语权被剥夺,却仍然能凭借火山迸发般的激情和勇气反抗强加其身的束缚与死亡,获得重生。从心理分析视角来看,丽姬娅的失去象征性地替代了叙述者在婴儿期时母亲的失去,这种创伤经历揭示了困扰叙述者心灵的俄狄浦斯情结。换言之,丽姬娅的逝去代表了叙述者自我形成的失败。此外,叙述者的不可靠叙述既反映了其意识的混乱,也使读者对文本事实疑虑重重,加深了“暗恐”效果。然而,丽姬娅的复活实际上也只是其女性身体的短暂复活,其诡秘的、不确定的身份从未得到确切的界定,由此而生的“暗恐”效果也在不断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