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北极海豹相伴相随的岁月
2021-01-16刘少才
刘少才
海员自有海员的苦,海员最大的苦不是值班、晕船,而是寂寞。海员也有海员的乐,最大的乐趣就是钓鱼,其他的休闲方式也有,那叫自我找乐,比如我,养过海豹,是海员中养海豹的第一人。
那年5月初,我随船到达北欧挪威的摩城港。
那是我船第一次来此港,代理还没办好登陆证,不能上岸,没有允许钓鱼的明确通知,我们不会私自在码头钓鱼。所以,我们只能下船在码头上转转,这已经是港口出于对中国的友好感情而特许的了。
我突然发现一个水泥墩与海水的接缝处似有一只大白鼠,仔细一看又不太像,出于好奇,我来到它跟前,那竟是一只海豹幼崽,只有一只脚那么大。小徐说,你要当心,要是有大海豹在附近,你就危险了。我站在高处一望,附近什么也没有,只有海浪声。也许这是一只走失的小海豹。
我抓起小海豹,身上未见有伤。出于好奇,我什么都没想,就将小海豹抱到船上。我不了解海豹的习性,当时又没有网络,便想当然地喂它奶粉。它只是闻闻,根本没有吃的意思。
船长闻讯而来,先看了看小海豹,又看了看束手无策的我和小徐,无奈地说:“海豹能吃奶粉吗?你得喂鱼啊!”
我茅塞顿开,赶忙从冰箱里取出留作钓鱼用饵的鱼肉,切成碎块。别说,小家伙真的张开嘴了,看来它是饿坏了。我们分析,它应该是跟母海豹远游时走散了。
我把浴盆洗干净,用卫生间的海水龙头注入海水。我把小家伙放到水里,它便快活地游了起来。
小海豹一天天长大,我发现它很聪明,就训练它跳跃、翻跟头等动作,它也乐得配合。
我怕远航时食物不够它吃,便在房间的冰箱里储满了鱼,平日里不受船员欢迎的鲅鱼、别人不要的小鱼,也被我拾来收拾干净储藏起来,因为相对来说,鲅鱼的骨和肉容易分开,而且小海豹很爱吃。
十五天的靠泊卸货作业很快结束,我曾为是否放生小海豹做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望着汹涌的大海,我忧心忡忡,它这么小,又失去了母亲和海豹群,放归大海能行吗?直到船远离了锚地,我才下定决心将它留在船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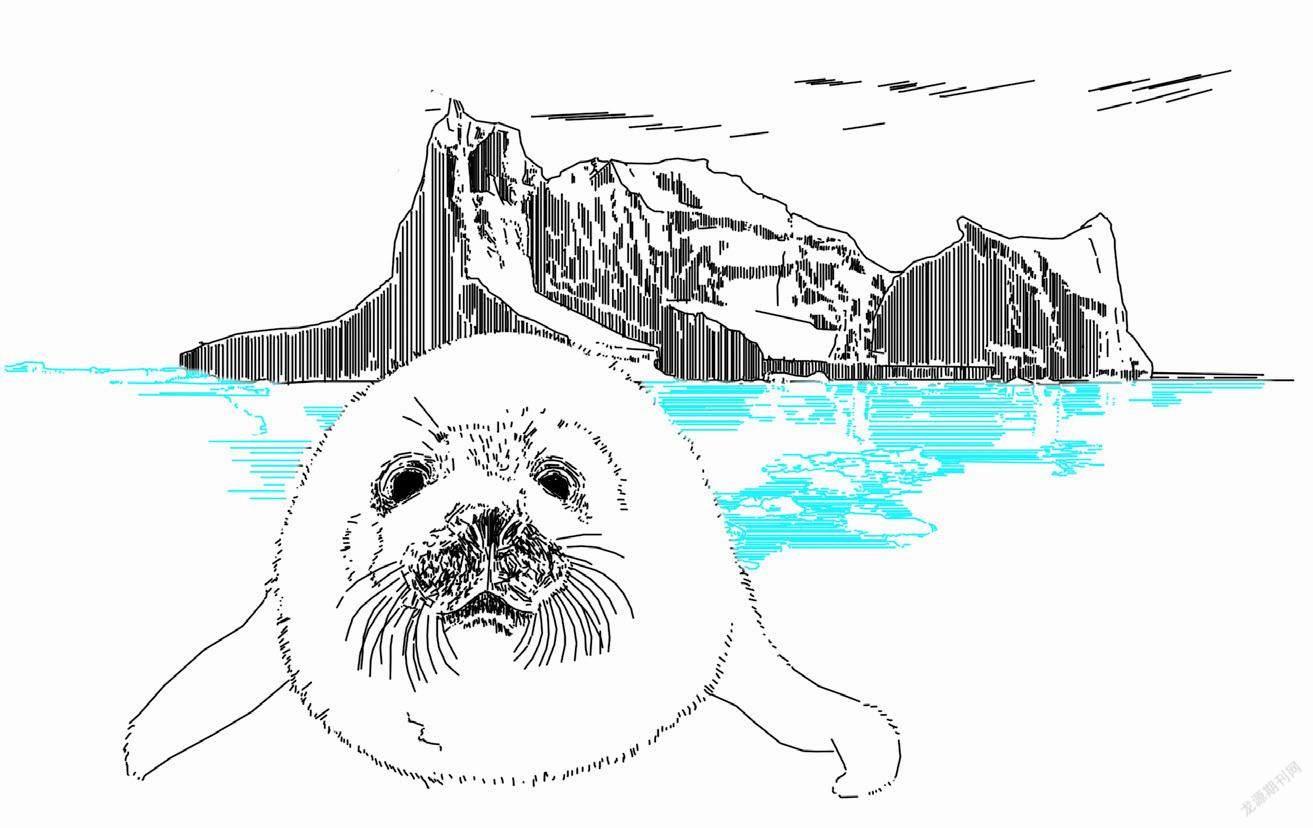
船开航,南下过北海、过比斯开湾,进入地中海,到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装货回国。我晚上工作完毕,一有时间就教它做些游戏,还给它起了个名字——“洋洋”。
风平浪静时,我还抱它到甲板上遛遛,它总是好奇地看着大海,听涛声,还会在甲板上跟在我的脚后追着玩耍,但它一点没有跃进大海的意思,倒好像离不开我了。
尽管我尽量控制它的食量,可是它的体重仍吹气似的疯长,不到两个月就从一只脚大小长到十多公斤,若想让它到甲板上散步,得用上下船的行李车拉着它。它也乐得享受,像个乖孩子任你拉着玩,一点也不吵闹。
船又在外面停了几个港口,到国内已是7月中旬,“洋洋”的体重已增到了25公斤,看上去肥肥胖胖的。它还学会了出门,只要在房间待不住了,就爬到门口敲门,表示要出去玩玩。
有时因工作忙,我没时间看管它,就放它出去自由活动,它在楼梯上摔得直翻滚,却也乐此不疲,且从未走失过。要回来时,它就在门外轻轻地敲门。最通人性的是,我的房间与电台挨着,只要我在电台工作,或者说,它一听到嘀嘀嗒嗒的电报声,就不吵不闹老老实实待在门口,不论时间多长,从来不打扰我工作。
船到青岛北海船厂修船,有人慕名来买小海豹,开口就给500元人民币,这在当时不算少,但被我拒绝了。我有我的想法,我要找机会将它放生,而且要放回它的故乡——挪威的北极圈附近,那才是我的初心。
在船厂,妻子来船探亲,她劝我休假。我很矛盾,我怕接班的船员对“洋洋”没有感情,更怕它被人卖掉,回不到它的故乡。
妻子说:“你真犯傻,海那么大,你放到海里去,命大它就活着,你心理平衡了就行了吧!”
我想想也是,便找一个中午,与妻子下船,用行李车拉着“洋洋”来到船厂西边一个工人专用的小浴场,妻子说:“你就带它下水,它要走就走,它要回来再说。”
正值退潮,岸边的水刚刚齐腰深。“洋洋”见到久违的大海,几下子就无影无踪了。我想放走它是真心实意的,但那一刻我丢了魂似的,哪还有心思游泳。我站在齐腰深的水中,连喊几声“洋洋”,都没有回应。
妻子说:“别指望它回来了,咱们走吧!”
我穿好衣服,高喊一声:“洋洋,再见了!”恋恋不舍地一步三回头向船上走去。
没走出几步,我回头时突然发现,“洋洋”的小脑袋竟然钻出水面,它见我们几个已经离开水边,也爬了上来,甩甩头,发出一句我永远也无法破译的语言,然后很笨拙地向我们追来。妻子见状,不顾一切地跑回去抱住了它。看来几天下来,她也喜欢上“洋洋”了。
这年10月末,天遂人愿,我船又一次来到挪威,在摩城外港斯托克沃格港锚地抛锚,等待进港消息。
这是我发现“洋洋”的海域,是它出生的北极海域,我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再不能犹豫了。
一天晚饭后,我请水手长和几名水手帮忙,用一个上菜用的大竹筐将它放入海里。“洋洋”不知水的深浅,一个猛子扎下去,好半天没有露出头来,不会出什么状况了吧?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其他人已经没有耐心等待了,甲板上只剩下几个钓鱼的船员。天渐渐暗了下去,只有我还在幻想着它能露出头来向我求援,那样我会立即将它打捞上来。
我既煎熬又自责,心滴血般难受,用度秒如年来形容也不为过。我一次次在心里说:“洋洋,对不住了,你走吧!”可还是盼着它能露一下头让我再看一眼。
又是天遂人愿,我终于等来它露出头来的那一刻,而且它的状态很不错,并无受伤求救的意思。它在船舷旁转了几圈,像是在向我告别,然后向苍茫的夜色游去,彻底游走了。
那一刻,我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感,又有一种心愿完成的满足感,两种情感交织在心头,大颗大颗的泪珠便挂在脸上。
上半夜,我独自到甲板上向海里看了两次,确信“洋洋”真的走了,才返回房间。我躺在床上輾转反侧,不知什么时候睡着的。睡梦中,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打开床头灯,发现才凌晨5点。电话那头是值班驾助,他跟我说,“洋洋”回来了。
我丢掉电话,穿上衬衣就向外跑。甲板上已聚集了几个早起垂钓的船员,我向下一看,几十只大大小小的海豹在船舷旁游来游去。一只海豹将头抬得老高,生怕别人不认识它似的。我大叫一声“洋洋”,它竟高昂着头喷出一口水,像是在回应我。
这一大群海豹在船舷旁转了好长时间,我只是傻傻地看着,我知道“洋洋”毕竟不能与我用语言进行交流,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它,是祝它好运一路顺风,还是希望它上来。
我天真地问了一句:“你还上来吗?”
只见“洋洋”将头立起,并使劲地摇了摇,像是在甩头上的水,也像是在回答“no”。
然后,这一大群海豹就一直向北游去。
与我相伴半年多,被我喂养长大,跟我风雨同舟的“洋洋”游在最后,它还回过两次头,最终还是追随它的同类融入自由的海洋空间之中,不见了踪影,只剩初升的霞光在海面闪闪发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