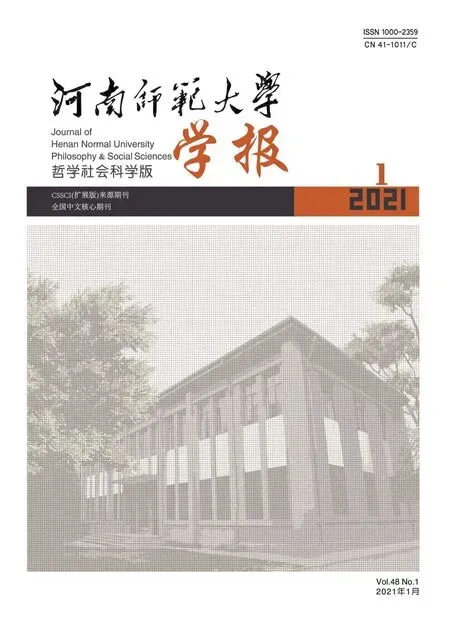论儒学术语意义的融贯性
2021-01-16杨宇威
杨宇威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15)
一、儒学术语拥有共同的源头
儒学术语拥有的共同源头,即“六经”和孔子的思想。中国哲学的“理论型”范式在殷周时期通过宗法制的确立而初步建立,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统治者,吸取夏商灭亡的教训,以史为鉴,提出“尊天敬德”“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思想。周公等周初统治者所确定的文化发展方向,为中国传统哲学奠定了精神基石,它不仅对“六经”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而且为其后两千多年的哲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西周时期学在官府,官学继承了夏礼与殷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礼记·表记》)。春秋以后,学术下移,原来依附于官府的士人开始独立讲学,社会生态的改变为士人们提供了展现自我的机会,儒学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儒学由孔子所创立,他认为周礼继承了夏商二代的优良传统,应该继承下去,“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子一生都在力图恢复周代以来遭受破坏的文化传统,希望重建西周的人文秩序。所以,儒学“是一种世界观,一种社会伦理体系,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一种学术传统,一种生活方式以及一种有着多种特征的文明体系”(1)郭尚兴:A History of Chinese Confucianis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523页。。它注重道统,是巩固、促进古代社会的完善和发展的学说。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记载:“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在与其门人以及同时代哲学家的辩论中编撰和阐释了“六经”,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意义,儒学思想就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
儒学思想的源头是“六经”,“六经”中的哲学术语构建了儒学思想的基本内容。术语是思想的精华,儒学思想体系的建立便是由诸多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儒学术语构成的。“十三经”作为儒家的核心经典,不但是儒学的基础,而且也是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从 “六经”到“十三经”,儒家经典经历一个从逐渐集结到不断扩充再到最后定型的过程,所以,儒学术语具有共同的源头,这一点毋庸置疑。张岱年归纳总结了先秦时期哲学典籍中的主要哲学术语(2)张岱年:《张岱年全集》(卷四),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58-459页。,简述如下:1.西周至春秋时代的概念范畴:天命、德、五行(《尚书·周书》);气、阴阳、和同(《国语·周语》);天道人道、仁、礼、不朽(《春秋左氏传》)。2.孔子哲学范畴:道、天道、德、仁、礼、忠、恕、孝、弟、智、勇、美、善、中庸、两端、性、习、学、思、一贯。3.孟子哲学范畴:仁义礼智、孝悌忠信、志、气、心、物、理、义、觉、诚、良知良能、浩然之气、良贵。4.《周易大传》 中的哲学范畴:太极、阴阳、健顺、生、易、变化、动静、道器、形上形下、神、儿、日新。 5.荀子哲学范畴(与孔子相同的不列):事理、法则、积、类、群、诚、神、征知。6.《礼记》 中的主要范畴:中和、德性、诚明、慎独、明德、至善、本末、格物致知、大同、小康。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六经”的思想,“六经”中的哲学术语,是孔子构建儒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概念和范畴。张立文认为:“先秦哲学思潮的核心话题是‘道德之意’,诸子各家则各据己见理解、体认、阐释‘六经’。”(3)张立文:《经典诠释的内在根据—论先秦诸子与六经的关系》,《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儒学的发展是“站在宗法家庭的立场上,以血缘分析的方法理解自然和社会,注重传统,突出群体,强调等级,追求和谐”(4)张立文,李甦平:《中外儒学比较研究》,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27页。。孔子之后的儒学典籍中无论是单一术语还是对偶术语,最早都现于“六经”或孔子的著作中。
二、儒学术语的发展遵循一以贯之的学术传统
儒学家们认为国家社会的运转和历史的发展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和法则,如“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荀子·天论》);又如“天生万物,日月星辰施其所性;地生万物,水火金木运其气;人生万物,仁义礼智行其道”(《五峰集皇王大纪序》);再如“若论道之常存……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灭之物”(《答陈同甫朱文公文集》),等等。为了证明这些规律、法则的稳定性和不变性,先哲们常常会诉诸历史经验,或者向历史典籍中寻求帮助,这样一来也就逐渐形成了相应的经验意识和经典意识,久而久之,这些意识成为一种认知传统,即传统中蕴含着一以贯之的原则和精神,璀燦的文化、完备的制度以及崇高的道德就是在这种原则和精神的感召下,不断地向前推进(5)吾淳:《中国哲学的起源:前诸子时期观念、概念、思想发生发展与成型的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37页。。
儒学因时代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如两汉的谶纬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其表象皆异,但是它们诉诸历史典籍的诠释性方式却始终没有改变。《论语》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先哲们出于对先贤的敬畏之心,认为著书立说是圣人先贤的事情,后人只能陈述他们的思想。孔子对《诗》《书》《礼》《乐》的修订,就是诠释经典的例子,后世的《论语义疏》《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字义疏证》也可等而视之。冯友兰认为,孔子所说的“述而不作”实际上是以述代作,孔子以六艺教人,时有新意(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3-44页。。孔子讲《诗》不是只练习应对,而是看重书中的道德意义,同样,孔子讲《易》的重点也不是为了占卜,而是意在阐释它的哲学意义。作为“六经”的整理者,孔子一方面将散落于民间的周代王官典籍搜集起来,一方面通过教化弟子,推行平民教育的方式,将它们传播开来,由此来看,中国学术从孔子的时代就开启了诠释的传统,此后新学说、新思想的创立,依靠的就是对经典的不断诠释,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引经据典”成了哲学家们最常用的方法,而无论这些新思想、新学说多么有创新性,或者多么有挑战性,哲学家们依然将之视为经典的固有真理(7)王中江:《儒家经典诠释学的起源》,《学术月刊》,2009年第7期。。
中国哲学可分为天道系统和人道系统:天道系统指的是世界的存在和它存在的形式;人道系统指的是对人的生命构成、认知过程、道德本质和价值观念,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等问题的认知。孔子既讲人道也讲天道,后世儒学家遵循这一传统,不断地对其加以发展和完善,呈现出一个动态的运转系统。
在天道系统中,人们相信天为至上存在,但是在春秋时期之后,人们对于天的认识发生了转变,认为世界是一个多样同一的整体。随后,人们开始用“五行论”解释世界,后来又演变成用“气”来解释世界,再后来,经过“阴气”“阳气”“道器”“有无”等术语发展,宋代逐渐将“理气”看作是宇宙论中的最高范畴。在人道系统中,孔子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此后,这一术语逐渐由心性范畴转变为仁义范畴,再沿着“性善”“性恶”“性情”“名实”“知行”的方向不断演化,儒学也自然就由对人、自然、社会的认识上升到了对历史活动的认识。
天道系统和人道系统中的儒学术语,纵横链接又相互交错,既有区别又有统一。儒学术语丰富的内涵不但体现了儒学一脉相承的传统,而且也体现了儒学思想的多样性。共同的源头和一以贯之的学术传统,使儒学家的创新思想必须在经典中找到例证之后,才能显示其合法性。又因为儒学的诠释性发展,极少出现用旧词取代新词的情况,这就使得后世儒家在发展儒学思想时,需要不断地扩充既有术语的内涵,儒学术语的意义也因此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
三、意义的融贯源于观物方式与思想旨趣的融合统一
儒学术语具有融贯性,它不仅在内涵上是各家思想的融会贯通,而且也是不同理论形态之间的相互诠释和印证。如果把对社会伦理道德的研究划分为人道范畴,那么对世界本原和宇宙自然的认识就属于天道范畴。在儒学中,天道和人道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关系,如“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论语·季氏》)。孔子把天命与人事放在一起讨论,天命对人事有影响作用,孔子所讲的天,既是社会规律也是自然规律。冯友兰称之为“主宰之天”(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7页。。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认为天是世界的主宰,有自己的意志,强调“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孟子·离娄上》),天是一种必然性,对国家政治和道德伦理都有制约作用。天是道德的本原,天道与人道的本质都是仁,如“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孟子·公孙丑上》),这就把天与人性贯通起来,使伦理学具有了本体论的意味。又如“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心、性与天是贯通的,孟子对“天”的诠释,对宋明理学有很大影响。在荀子的思想中,天为自然之天,他认为天和人各司其职,天化育万物,人治理社会自然。这样他就把天和人的职能综合起来,既不降低天的客观自然性,也不损害人的主观能动性。
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认为,天是至上神,把天拟人化,“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王充反对这种学说,认为天应为“自然之天”和“天地之天”。在王充的思想中,天为体,气为用,天和地是自然实体,人和万物都是合气而成。隋唐时期,柳宗元认为天人不相预,天无意志,反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他认为天地之间只有理、数、势,反对宿命论,人们把无法名状、不可捉摸的必然性当作天的支配,是一种主观主义。这时期的儒学还没有涉及宇宙本原和第一性物质的问题,柳宗元只说天地万物统一于气,强调天的有形性,从客观实际出发,认为万物都有规律,人可以认识规律,也就说明了天的“可测度性”。把天与势、数、理结合起来,论天道也兼论人道。刘禹锡认为天人交相胜,发展深化了荀子的思想,天人各司其职,不能互相代替。天人交相胜的观点,相对于天人相分的相互区别,与天人合一的相互结合,是分与合建立在唯物论上的辩证统一。刘禹锡对天人作出了唯物主义的界定,如“天,有形只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论》),天指的是自然之天,天人关系就是自然与人的关系。
宋明理学中,儒学家对天的认识,已经摆脱了某种物质特性或结构的看法,纷纷从客观物性中抽象出来,与他们各自思想体系中的最高范畴联系起来。张载认为天为太虚,又因太虚即气,也就解决了自王充、柳宗元以来无法统一的天与气的联系,但是在张载的思想体系中,天为“主宰之天”。二程认为张载把形下的气与形上的太虚等同起来,混淆了术语的哲学形态。二程提出“天为理”,理也可以称为天理,天理即是宇宙本原,又是社会伦理。天理的提出便把自然界客观规律与道德义理统一起来,这是伦理学与宇宙本体论在哲学形态上的统一,既保留了各自内涵的特殊性,又体现了天道与人道辩证统一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等同。朱熹提出了“人不胜天”的观点,天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代表的是命运之天,是不可捉摸的必然,有宿命论的内涵。王守仁主张尽心、知性、知天,把心、性、天三者融合起来。清代王夫之继承了荀子、王充、柳宗元等人的思想,否认天的意志,认为天为自然之天和自然规律,它既是客观事物又是客观规律,从而把唯物论和辩证法结合起来。他还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可以利用客观规律改造自然。
可见,儒学家无论持有何种关于天人的理论,以及他们之间对天人关系的理解有何种不同,他们都把天、社会人伦、自然规律、世界本原和第一性物质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统一的逻辑结构。从天人合一的观点来看,孟子不仅承认主宰之天,并且以心释天,从天的道德属性出发,认为天的德性内含于人的心性之中。孟子这一观点影响了宋明儒学,无论是理学家还是心学家,他们一方面讲主宰之天,认为天是宇宙本原或是把天与宇宙本原统一起来;另一方面,他们还讲道德之天,力图把道德伦理与宇宙本原统一起来,把人类社会中的道德准则与宇宙的普遍规律统一起来,形成永恒的道德,为道理伦理提供本体论的依据,试图把主宰之天、道德之天和人性结合一起,这些都体现了儒学术语中伦理学与本体论的贯通思想。
四、意义的融贯源自天人圆融和谐的整体性思维
儒学术语间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既相互渗透又相对独立。术语的发展是一个范畴化和多元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有不同的流派、思想与诠释方法参与其间,所以这一过程并不是孤立和不变的,而是在相互联系与影响下发展的。术语所代表的不同思想共同构成了儒学的思想体系,儒学思想体系结构的有序性和思想的整体性互为因果,一以贯之的儒学传统与多元化的儒学发展并行不悖。
儒学中这种天道、人道相辅相成的关系,取决于儒学家对于儒学思想体系的整体思考:从内容上来看,儒学家秉承一以贯之的学术传统,历史上并没有出现革命性的变革,总是在不打破原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对以往的学说进行批判继承,发展出新的学说。如前所述,术语形式相对恒定,思想的不断进步促使术语内涵不断丰富。因此,儒学中的基础性术语,是儒学家在发展其思想时不可回避的话题,所以在纷繁复杂的哲学流派和理论思想中,同一个术语往往具有不同的诠释角度。不仅如此,对单个术语的诠释,是在儒学家整体思想体系中进行的,这也势必会涉及体系中的其他术语,所以在诠释的过程中加入对其他术语的讨论,目的是试图通过术语间内涵的部分重合,多角度地诠释此术语。例如在历史上,对“理”的诠释就能充分展示这一现象:儒学家从“理”的相邻术语出发诠释其含义,如以心释理,以天释理,以道释理,也从多个理论角度研究诠释其含义,如从伦理学、本体论和宇宙论的角度出发,而且它们之间也互相诠释,特别是理学中的伦理学诠释,往往以本体论和宇宙论为理论依据,许多本体论和宇宙论的诠释,最终会回到伦理学中内圣外王的境界说和功夫论上来。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此过程中不断深化,以“天”为“自然之天”“主宰之天”“道德之天”“命运之天”以及“义理之天”的多种诠释,与对“人”“性”“心”“理”的诠释融会贯通,形成“天理”“天心”“天性”和“天人”等对偶术语和在此基础上的各种新思想,儒学术语不仅在形式和内涵上得到了丰富和深化,而且在哲学思想上和谐并存。这一方面体现了儒学动态系统中各术语间的必然联系,另一方面体现了儒学思想的整体性,即通过对某一术语的诠释来表达一种理论思想,又借助思想的整体性,从全局出发诠释此术语在其思想体系中的内涵,及其与各部分(术语)间的联系。这不仅丰富了思想体系中各个部分(术语)的内涵,而且也深化了整体思想体系。正如施莱尔·马赫所认为的那样:“部分必须置于整体之中才能被理解,而对部分的理解又加深对整体的理解,部分与整体在理解中互为前提,相互促进,形成了理解的循环运动。”(9)潘德荣:《西方诠释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56页。术语间的融会贯通形成了儒学的整体思想体系,各个术语只有置身于思想体系中才能被理解,术语的发展深化又相应改变了儒学整体。在儒学发展的历史上,术语和整体思想体系融而为一,部分是整体的部分,整体是部分的整体,术语的发展不是作为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在量上的扩张,而是在与整体的关联中丰富了自身的内涵,各个术语的内涵不尽相同,它们以独特而又部分重合的内涵改变着儒学思想体系。儒学诠释的循环是一个生产性循环,其目的是从经典中发掘出新的意义,不断深化、丰富思想理论,从而扩展儒学的理论框架。
有学者认为,中国哲学基本问题可以概括为宇宙论、本体论、功夫论和境界论(10)杜保瑞:《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与概念范畴》,《文史哲》,2009年第4期。。这是把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套用在中国传统哲学上的做法,属于格义的一种,中国佛学史上的以儒释佛、以道释佛就是这种方式。用中国哲学的话语表达,就是人道与天道。西方哲学中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就是儒学中研究天道的部分。西方哲学中的人生论,相当于儒学中的人道。然而,西方哲学中的方法论,指的是追求知识的方法,而这种哲学“在中国思想史之子学时代,尚讨论及之;宋明而后,无研究者”(1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页。,中国义理学中的方法论,关注的是修养求善的方法,包含了功夫论和境界论两方面的内容。所以,“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宇宙哲学与道德哲学,或者说,本体论与伦理学密切结合,认识方法与修养方法密切结合,所以许多范畴既有本体论意义,又有伦理学意义,两个意义可以分而分布不开”(12)张岱年:《略论中国哲学范畴的演变》,《求索》,1984年第1期。。《周易·说卦传》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之中把世间万物分为天、地、人三才。天与地,实际上是指天道范畴,是客体范畴,讨论关于世界本原以及存在形式;人之道就是人道范畴,属于主体范畴,讨论人的生命构成,人的认识过程、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天道、人道、天人关系和理想境界共同构成了儒学的全部内容。“天道是被人格伦理化了的自然,人通是被自然而然化了的人事伦理”(13)张立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8页。,天人合一就是天道与人道的融会贯通,人可与天地参,人道不断外在化,天道不断内在化。天道与人道各司其职,相互不可替代。同时,它们相互协调,天人合一即体现了本体论和道德论的统一,即宇宙最高本体既是道德最高原则或宇宙本原,又体现了认识论和境界学的统一,即求知方法与修养方法一致。
儒学术语以道德伦理为中心,同时兼具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内涵。从前文的论述可以看出,一方面,儒学术语具有共同的源头,遵循一以贯之的学术传统:术语的形成都是以经典诠释为起点,在随后的发展进程中,后继的儒学家对先哲的理论成果进行吸收和改造,既有在原有思想基础上的不断深化,又有结合时代思潮的理论创新。另一方面,儒学术语的发展是一个内涵和功能由单一到复杂、由普通到特殊的过程:许多儒学术语,既有本体论、宇宙论意义,又有伦理学意义;既有认识论意义,又有境界学意义。术语的多元内涵,既体现了纷繁复杂的哲学流派和理论思想的独特性,又体现了个性之中的共性,即同一术语在不同流派的诠释中,内涵有部分重合的现象。综上所述,儒学术语的发展是一个共性与个性并重、对立与统一共存,各种学派思想交互交织、融会贯通的过程。对术语意义的认识,不但要考察其发展脉络,而且要探究其多重内涵和功能。忽视术语的多元特征,只从某一个内涵或视角出发,是无法从整体上把握和认识儒学术语的意义的。
五、结语
六经是中国哲学的源头,六经的形成是一个长久的过程,并非成于一人或一家之后,六经反映了周代到春秋战国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孔子对六经的整理和编订,并非简单的文献整理。孔子用六经作为教材培育弟子,教化世人,目的是为了恢复周礼,以实现尧舜之治为奋斗目标。所以孔子对六经搜集和整理的过程,就是儒学的建立过程。儒家的主要经典,均形成于先秦时期,之后的儒家各派,无论其诠释方法和思想的差异,无不以尧舜之世、三代之治为其思想目标,追求圣贤气象。汉代之降,儒学成为学术正统并与政治紧密结合,儒学以经学的形式发展。儒学的发展不仅有很强的政治意味,而且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孔子之后的儒学各家,其思想无不建立在对先哲思想借鉴和吸收的基础之上,又结合了自身所处的时代特征和学术背景。儒学中的原始术语也因此增添了新的含义。
随着儒学对经典诠释的不断革新,进而产生了不同的流派和义理。这些不同流派和义理,不仅使儒学术语的内涵不断丰富,也使得儒学术语的哲学功能不断丰富。不同的流派和义理,使儒学术语不仅在内涵上,也从其哲学功能上,实现了从单一到丰富、从简单到完备的发展。由于汉语在语言表达上的模糊性和暗示性,使得术语的意义相互联结,也促使了术语间的吸收和改造。
因此,儒学术语的发展不仅仅是不同诠释形态间的相互借鉴,也是各家思想的融会贯通。儒学术语的发展是一个形式、内涵及其意义和理论形态共同进步的过程。对中西方诠释理论的评述,以及对儒学术语历史文化特征的研究,目的在于在术语意义认知的阶段,就建立起儒学的文化主体性。儒学术语的意义认知,不但要从本原处自我认同、自我理解,更要有哲学的自主诠释。只有厘清了中西方哲学间的共性与分野,诠释出儒学与西方哲学的相异之处,我们才能在文化传播的进程中,让中华传统文化显示出它的自主性和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