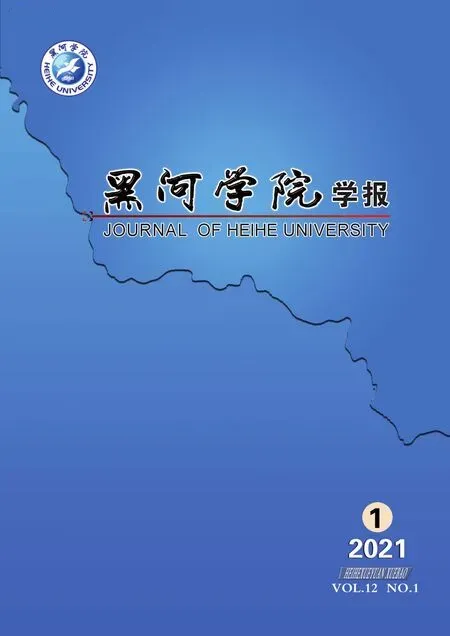《史记·太史公自序》与《汉书·司马迁传》异文探析
2021-01-16曾鸿雁
曾鸿雁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史记》和《汉书》是两汉史学著作的双璧,加之两书的部分篇章内容类似,自然会引起学者的关注。从古至今,学者比较分析两书的异同之处,得出许多精妙观点。然而,诸家在论及《史记》与《汉书》相似篇章时,对《史记·太史公自序》(以下简称“史”)及对应的《汉书·司马迁传》(以下简称“汉”)的关注不多。南宋倪思《班马异同》开拓了班马异同比较这一新的领域,对两书大部分篇章的字句详细进行比勘,却没有提到《史》《汉》。刘辰翁《班马异同评》重点评价两书中的人物形象、性格等文学内容,也没有关注《史》《汉》。后继学者在讨论班马异同时,同样很少提及《史》《汉》两文。有鉴于此,本文对《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内容重叠部分进行详细梳理,整理这两篇文章的异文并探析其产生的原因,祈请方家指教。
一、《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司马迁传》异文整理
《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中有大量异文。这些异文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脱文、衍文、倒文、讹文,第二类是通假字、异体字。王彦坤《试论古书异文产生原因》一文将这两类异文分别称为“辗转讹误”和“字有异体”[1]。前者与版本流传有关,后者则源于文字发展。这两类异文属于校勘学和文字学的范畴,不纳入本文的讨论范围。本文讨论的是第三类异文,即班固对《史记·太史公自序》的修改与删削。这类异文主要包括语言和非语言两方面。
(一)语言方面的异文
1.班固改《史记》中的今字为古字①严格来说,古今字也属于文字学研究范畴。但班固改《史记》中的今字为古字,与他的作史思想有关,也影响到《汉书》的文章风格,所以本文将古今字纳入研究范围。
《史》“晋中军随会奔秦”,《汉》作“晋中军随会犇魏”,颜师古注曰:“犇,古奔字也”。
《史》“赡足万物”,《汉》作“澹足万物”,颜师古注曰:“澹,古赡字”。
《史》“小子何敢让焉”,《汉》作“小子何敢攘焉”,颜师古注曰:“攘,古让字”。
《史》“是余之罪也夫”,汉作“是余之辠夫”,《王力古汉语字典》曰:“‘辠’,古‘罪’字”。
《史》“俟后世圣人君子”,《汉》作“以竢后圣君子”,颜师古注曰:“竢,古俟字”。
2.班固删去《史记》中的虚词
《史》“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汉》作“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
《史》“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汉》作“愍学者不达其意而师誖”。
《史》“必以此为万民之率”,《汉》作“必以此为万民率”。
《史》“成一家之言”,《汉》作“成一家言”。
《史》“使人拘而多所畏”,《汉》作“使人拘而多畏”。
《史》“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汉》作“君唱臣和,主先臣随”。
《史》“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汉》作“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
《史》“故发愤且卒”,《汉》作“发愤且卒”。
《史》“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汉》作“春秋上明三王之道”。
《史》“而君比之於春秋”,《汉》作“而君比之春秋”。
《史》“於是卒述陶唐以来”,《汉》作“卒述陶唐以来”。
《史》“於是汉兴”,《汉》作“汉兴”。
3.班固删去《史记》中语义重复的实词
《史》“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惠襄之閒,司马氏去周适晋”,《汉》作“当宣王时,官①“官”字属于校勘学研究范畴,本文不作讨论。失其守而为司马氏。……惠襄之间,司马氏适晋”。
《史》“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汉》作“蘄孙昌,为秦王铁官”。
4.班固精简《史记》词句
《史》“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汉》作“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史》“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汉》作“不为物先后,故能为万物主”。
《史》“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汉》作“明主贤君,忠臣义士”。
《史》“必陷篡弒之诛,死罪之名”,《汉》作“必陷篡弒诛死之罪”。
5.班固删去《史记》中重复的感叹句
《史》“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汉》作“是余之辠夫!身亏不用矣”。
《史》“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钦念哉!钦念哉”,《汉》作“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钦念哉!”
(二)非语言方面的异文
《史》“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汉》作“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史》“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汉》作“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
《史》“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②“时”“言”二字属于校勘学研究范畴,本文不作讨论。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汉》作“余闻之董生:‘周道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时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虽然《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重叠部分的内容相似度极高,但从《史》《汉》异文可以窥知司马迁和班固处理文本细节的诸多差异。探究这些异文产生的原因,有助于深入了解《史记》《汉书》。
二、《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司马迁传》异文形成的原因
通过梳理,可知《史》《汉》异文大体分为语言和非语言两方面。这些异文产生的原因各不相同,以下分别论之。
第一,语言方面异文形成的原因。从这些异文来看,司马迁和班固运用语言时有明显差异。司马迁善用虚词,如“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句,多一“而”字,“有一种娟峭之美,清脆之声”[2]222;又如“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句,多一“也”字,“让文字格外多了一番从容,有舒缓悠扬之致。”[2]222同时,他叙事不避重复,如“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反映了司马迁遭遇李陵之祸后屈辱愤懑的感情;又如“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钦念哉!钦念哉”是司马谈临死前追述家族历史、嘱托司马迁继承家族事业的话语,体现了司马谈对其子深切期望。这些感叹句的重复都表达了人物强烈的情感,也使文章富有生气。此外,与先秦诸子散文相似,《史记》长短句交错,如“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前两个短句对仗工整,有圆融和谐之美;后一句较长,避免文章因重复运用对偶句产生板滞沉闷之感。这些都使得《史记》的语言富于生气、行文疏放迭宕。
与司马迁相比,班固在语言运用方面有不同的习惯。首先,司马迁多用今字而班固喜用古字。王先谦《汉书补注》引苏舆曰:“班书多存古字,以视学者,故云‘正文字。’”[3]1748虽然班固用古字的目的是“正文字”,但客观上影响了《汉书》的风格。正如郑鹤声所言,“古字多则雅而有致。”[4]班固喜用古字为《汉书》增添雅致的韵味。其次,班固频繁删减《史记》中的文字。他删去《史记》中的虚词,淡化文章的气势。譬如,删《史》“成一家之言”中的“之”字,作“成一家言”。删《史》“故发愤且卒”中的“故”字,作“发愤且卒”。删去《史记》中重复的感叹句,使《汉书》在情感表达上更为克制内敛、叙述显得客观理性。譬如,删《史》“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中的“是余之罪也夫”,作“是余之辠夫!身亏不用矣”。删去《史记》中语义重复的实词,使语言更加凝练。譬如,《史》“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汉》作“蕲孙昌,为秦王铁官”。前句已经提到司马靳的孙子是司马昌,根据“就近原则”这一语法规则,后句提到的“秦主铁官”应该是司马昌的工作。且前文有“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与此句句型结构一样,两相对照,也可知该句含义。《汉书》删去后句的“昌”字,表述简洁精炼。最后,班固对《史记》的词句进行精简。譬如,《史》“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汉》作“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汉书》用一“亡”字,包含《史记》描述的“死亡”和“逃亡”两层含义,语言简练且对仗工整。因为班固的删改,使《汉书》的文章具有含蓄典雅的风格特征。正如范晔《后汉书·班固传》所言:“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5]
关于司马迁和班固的语言风格迥异,郭预衡《班固的思想和文风》有精到的见解:“贾谊、晃错、司马相如、司马迁诸家之文,或‘疏直激切’、或‘虚词滥说’、或‘纵横变化’,大抵都带有先秦诸子的余风,都带有过渡的时代性质”、“班固,生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百几十年之后,风气移人,已经形成一套正统思想;所为文章,也就很富大汉王朝一统天下的时代气息和特征。”[6]正如郭文所言,西汉初期社会环境较为宽松,思想文化比较自由。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汉代君主逐渐统一思想。汉元帝“纯任德教”,石渠阁会议、白虎观会议强化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士人入仕需精通儒家经学。两汉之际朝堂动荡,谶纬与经学结合,臣子大多称颂祥瑞。在这样的思想风气的影响下,文学风格由昂扬巨丽变为醇厚典雅。具体来说,西汉前期的文学作品大都显示出追求巨丽的时代特色。如,贾谊的政论文将强烈的情感贯注于气势高昂的论辩中,在说理的同时唤起读者感情的共鸣。又如,司马相如的散体大赋篇幅宏大、气势磅礴。《史记》与同时期其他作品一样,与先秦诸子散文的文学风格一脉相承,同时也体现了西汉初期昂扬巨丽的时代特征。与西汉前期相比,东汉时期的文学风格已经发生较大变化。扬雄的赋典丽深湛、词语蕴藉;刘向的奏疏,“旨切而调缓”[7]。受时代风气的影响,班固的著作也呈现典雅的特色。
第二,非语言方面的异文。《史》《汉》中非语言方面的异文数量并不多,仅有三条。这三条异文的其成因各有不同。具体来说,第一条异文:《史》“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汉》作“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王先谦《汉书补注》曰:“《史记》‘功臣’下有‘世家’二字”[3]1234。《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这段文字是司马迁本人说的话,表明他写《史记》是为了记载圣明天子的功业,记述功臣、世家、贤大夫的事迹。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删去“世家”二字,说明他与司马迁对“世家”的认识存在分歧。
众所周知,两书在体例上诸多不同之处。譬如,班固新增《艺文志》和《地理志》,变《史记》“八书”为《汉书》“十志”;新增《百官公卿表》《古今人物表》并删除《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变《史记》“十表”为《汉书》“八表”;删除“世家”,变《史记》“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的五种体例为《汉书》“纪、表、志、传”。显然,《汉书》与《史记》体例方面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有“世家”。
这种体例变化与第一条异文两相对应。《史记》“世家”主要记载诸侯王和功绩堪比帝王之人的事迹,而《汉书》则删去“世家”。两书体例不同与书写对象发生变化有直接的关系。《史记》和《汉书》都是纪传体史书,根本区别在于书中记载历史事件的时间范围不同。《史记》记载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的历史,而《汉书》记载汉高祖建立西汉王朝直至王莽篡汉的历史。与先秦时期相比,西汉诸侯王的政治地位急速降低。具体来说,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属于先秦时期独立的政治力量;刘邦封赏的王侯也是西汉前期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司马迁将这些人物的传记放在“世家”中,表明他们特殊的政治地位,即“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8]3319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汉代诸侯王的政治地位不断下降。西汉初立,汉高祖封赏有功的异姓诸侯王。随后除了长沙王吴芮,其余异姓诸侯王被刘邦逐一消灭。接着,刘邦又封同姓诸侯王,订立“白马之盟”。然而,随着皇权逐渐集中,“至景帝中元年间,参加白马之盟结盟的三方中,诸侯王国和以功臣列侯为代表的汉初军功受益阶层,皆已经不再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存在。”[9]所以汉景帝之后,西汉时期的诸侯王不再享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此外,对于陈胜、项羽、孔子等历史功绩堪比帝王之人,司马迁和班固的态度也有所区别。司马迁从实际历史功绩高低的角度评价其作为,将陈胜、项羽和孔子纳入比帝王等级稍低一层的“世家”中记述他们的事迹。而班固从政权合法性的角度评价,并不认为他们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因此,当书写对象的特殊性消失,班固也就不再需要凸显政治地位的“世家”这种体例。
同时,两书写作目的的不同也导致体例方面存在差异。司马迁和班固写作史书的目的与各自的时代有关。西汉前期人们多探讨秦亡汉兴的原因,司马迁也不例外。他希望从历史事件中总结王朝兴衰的规律,为西汉的统治者提供借鉴。即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0]2735。东汉王朝的统治者更注重宣扬政权的合法性,所以史家大多以此为目的来写史书。班固的父亲班彪在写《史记后传》时就取消了“世家”这种体例,班固则延续了班彪的做法。“班彪修改《史记》结构,取消世家,将本纪变成只写汉朝刘氏君主在位时期大事记的专用形式,已表露一种意向,就是‘非刘氏而王’的政权,在先如陈胜、项羽,在后如王莽、刘玄、隗嚣、公孙述等,都属于‘外不量力,内不知命’的所谓神器潜窃者。”[11]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班固在《汉书》中取消“世家”。这种编写史书的观点反过来也会影响班固对司马迁“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的解读,从而产生异文。
《史》《汉》非语言方面的异文还有两条。一条是《史》“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汉》作“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这条异文的内容跟司马迁叙述自己的游历有关,不同之处在于班、马二人对孔子的称呼。这条异文并非个例。在《史记》《汉书》中,班、马二人对孔子的称呼有明显差异。具体来说,司马迁和班固在引述其他人的话语时,如实记录他人对孔子的称呼;二人提到孔子时,司马迁习惯用“孔子”一词,而班固多用“夫子”一词。汉代称呼某人为“夫子”是表示对他的尊敬。如《汉书·司马相如传》“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严忌夫子之徒”,颜师古注曰:“严忌本姓庄,当时尊尚,号曰夫子。史家避汉明帝讳,故遂为严耳。”[10]2529可见,他们对孔子的态度有所不同。与司马迁相比,班固更加尊重孔子。两人对孔子的排序同样证明这一点。在《史记》《汉书》中孔子的地位均高于其他先秦诸子。不同的是,司马迁将孔子列入“世家”,与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王并列。而班固将孔子列入《古今人物表》中“上上圣人”一栏,与远古帝王并列。与司马迁相比,班固将孔子的地位抬的更高。
另一条异文是《史》“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班固删去“天子退”三字,将“贬天子,退诸侯”改为“贬诸侯”。韩兆琦认为,“‘贬天子’,或者这是司马迁个人对《春秋》的一种理解;或者是一种借题发挥,他写《史记》显然有一种‘贬天子’之意,这是他为了打鬼而借用钟馗。”[12]本文认同这种观点。司马迁在《史记》中如实记录西汉前期几位皇帝的事迹,包括一些有损君王颜面的细节。而班固不认同司马迁“贬天子”的观点,在《汉书》中删去这些描写。比如,同样描写鸿门宴,《史记·项羽本纪》作“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8]313《汉书·高帝纪》作“羽因留沛公饮。范增数目羽击沛公,羽不应。”[10]27鸿门宴上汉高祖刘邦座位向北,并没有坐在尊位。班固删去司马迁对在场众人座次的描述,维护了刘邦作为西汉开国皇帝的高大形象。
通过前文分析可知,这两条异文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其一,司马迁和班固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产生诸多变化,从而产生异文。具体而言,随着时代的发展,儒家思想的影响力逐渐扩大。西汉前期,“在思想学术领域,虽号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一些活跃并取得不同成就的士人,却兼修道家、刑名纵横等学派,而在各自领域显示出独特的创造性。”[13]90“从西汉宣帝至东汉章帝,汉朝廷推进汉家文化制度建设,强化官方话语,主流意识与儒家思想强势结合,汉家文化在以儒学为官方学术的前提下发展。”[13]184与西汉前期的人们相比,东汉时期的人更尊崇儒家思想,司马迁和班固也不例外。因此,班固将孔子置于更高的地位,并且在史书中维护帝王的形象。其二,外部力量的干预极有可能导致这两条异文的产生。司马迁写史书时并未受到皇帝的关注,而班固属于奉诏编写国史。同时,永平十七年汉明帝下诏书,把是否歌功颂德作为品评文人优劣的标准。这道诏书极有可能影响了《汉书》的写作。正如邵毅平所言,“班固在《汉书·叙传》中强调史学的歌功颂德作用,强调用断代史体的《汉书》突出‘绍尧运’的大汉的地位,很明显地是受了明帝诏书的影响。”[14]
三、结语
司马迁和班固作为作者,势必在自己的作品中留下不可磨灭的个人印记。而他们身处不同的时代,在创作作品时也会受到各自时代的影响。作者的特质和时代的变化共同导致《史》《汉》异文的产生。通过对这些异文进行分析,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两书的认识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