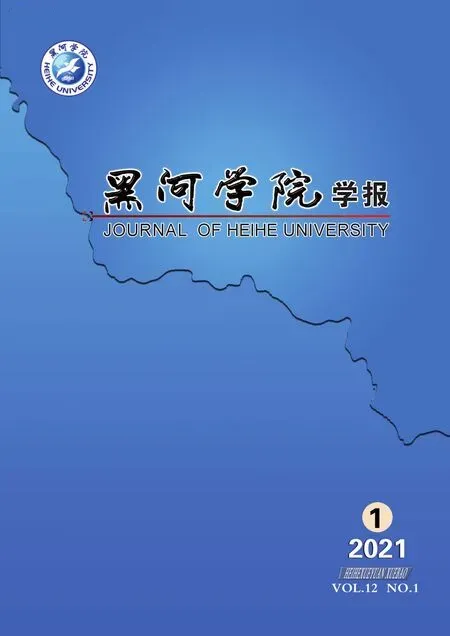女性主义视阈下《莎菲拉与女奴》中的矛盾冲突分析
2021-01-16段继芳郭玉鑫
段继芳 郭玉鑫
(黑龙江外国语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薇拉·凯瑟是美国20世纪杰出的女性作家,被评论家们称为与亨利·詹姆斯、福克纳、海明威,以及菲茨杰拉德并列的美国杰出小说家[1]。她是一个高产作家,一生共发表中长篇小说16部,短篇小说55部,此外,还著有诗集、散文集和其他论著等。
在其诸多著作中,人们将其作品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作品是以《我的安东尼亚》《啊,拓荒者!》等为代表的荒原系列小说;中期小说以《一个迷途的女人》和《教授的房子》为代表;后期作品则脱离了草原背景,充满了浓厚的怀旧情绪,主要有《大主教之死》《岩石上的阴影》等作品,以及以其故乡美国南部为背景的《莎菲拉与女奴》。近年来,在对薇拉·凯瑟的作品研究方面,中西方评论家们日益重视,并从女性主义、反女性主义、叙事学、生态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等不同角度解读了其主要作品,这不仅丰富了薇拉·凯瑟作品的内涵,同时也有助于人们更深层地了解其作品。但在其作品的文本研究方面,大多集中在比较出名的拓荒系列小说上,如《我的安东尼亚》和《啊,拓荒者》等,由于国内没有凯瑟后期作品的中译本,国内学者对凯瑟第三阶段小说的研究并不多见。作为凯瑟写作生涯最后一部小说,《莎菲拉与女奴》发表于1940年,小说的大致情节是南方种植园女主人莎菲拉自身家庭婚姻不幸福,夫妻长期分居,当得知丈夫喜欢一个叫南希的黑人女奴,她便设计了种种手段想卖掉或除掉南希,最终南希在莎菲拉的女儿瑞吉尔的帮助下假扮成尸体,被送往加拿大。小说中的诸多女性形象都在通过自己的方式实现自身的独立,而在抗争与追求平等的过程中步履维艰,不得不直面诸多矛盾冲突:女性与男性的矛盾冲突、女性与家庭的矛盾冲突、女性与社会的矛盾冲突,以及女性与自我的矛盾冲突。本文以女性主义的视阈探讨了小说中的诸多矛盾冲突,并且分析了形成这些冲突的个人原因、社会原因、历史原因。
一、女性主义批评
女性主义(Feminism),又译作女权主义。《剑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解释:“指的是一种坚持女性应当和男性一样享有平等对待的信仰,以及为达到这一理想状态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2]在其发展的三个阶段(两性平等、两性平权,以及两性同格)的过程中,对文学批评的影响从未间断。自20世纪初,弗吉尼亚·伍尔芙开始关注到大部分文学作品中女性只是说着男性作家要她们说的话,做着男性作家让她们做的事,女性主义批评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女性主义批评以女性主义为基础,以妇女为研究核心,重点关注女性形象、女性创作和女性阅读。作为20世纪杰出的女性作家,薇拉· 凯瑟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塑造了一个个独立自主、个性十足、不同于传统男性视角下的女性角色,而小说《莎菲拉与女奴》中对女性的刻画,则是作者对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现状,以及女性对平等权利的追求的深刻思考。这种思考在小说中女性所面临的重重矛盾中抽丝剥茧般展现给读者。在薇拉·凯瑟的作品中,没有道德说教,没有歇斯底里的控诉,更没有非黑即白的刻板人物,有的只是对事件和人物矛盾冲突的描述。
二、女性与男性的矛盾冲突
关于两性关系,在基督教文化中早有描述。在《圣经旧约》的《创世纪》部分,上帝率先造出了第一位男性——亚当,又从亚当的身上取下一根肋骨造出了第一位人类女性——夏娃,来陪伴亚当。这个故事暗示着,女性自被创造之初便是以男性的需求而存在的“第二性”。在小说《莎菲拉与女奴》中,处于男权社会中“第二性”地位的女性在追求自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男性产生矛盾冲突。不论是一生争强好胜坚持蓄奴制的主人公莎菲拉,还是倡导解放奴隶的女儿瑞吉尔,抑或是深受种族主义与性别主义压迫的黑人女奴南希,她们在反抗压迫和追求自身权利的过程中,都在与男性权利博弈。小说的女主人公莎菲拉是一位作风强势敢于挑战传统父权的女性形象,这一点在其不畏人言,一意孤行地离开原生家庭远嫁他乡之时就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正是其强势造成了与丈夫亨利的矛盾。在父权社会中,即使男性的经济实力与个人能力不及女性,也不能容忍女性作为“第一性”存在于自己的生活中。婚后,丈夫亨利生活在妻子的阴影中,渐渐失去了对莎菲拉的爱。对莎菲拉的态度从忍耐到冷漠,最终回到自己的世界中,完全不顾妻子。因此,在短暂地冲破社会传统的桎梏后,莎菲拉在自己建立的新家中担当女主人,事无巨细都由她掌管,表面上风光无限,实则内心落寞。摆脱了父母的束缚后,莎菲拉并没有得到想得到的幸福,丈夫亨利作为新家的男主人,用冷漠和忽视对她施以“刑罚”,并且表面上家里的主人是莎菲拉,实际上在社会的认同范围内,丈夫亨利依然是真正的主人,这一点在黑奴买卖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无论莎菲拉如何跋扈专断,但只有亨利签字后才能对家里的黑奴进行处置。在父权社会中,无论莎菲拉是如何独立的女性都不可避免地与男性发生冲突。此外,除了女性与男性的直接冲突外,女性会因为男性而与同性产生冲突,小说中莎菲拉与女奴南希的矛盾冲突就源于此。该矛盾冲突的直接原因是莎菲拉的丈夫亨利所制造的,当莎菲拉得知亨利喜欢的人是黑人女奴南希时,南希就成为了情敌,她把自己所有的不幸都归结到南希的身上,像所有得不到丈夫的爱的女性一样,疯狂地仇视和丈夫有关系的女人,即使这个女人没有犯下任何错误。莎菲拉虐待南希,试图将南希卖给邻居,然而由于必须得到亨利的同意才能变卖奴隶,这个计划只能以失败告终,后来莎菲拉指使侄子马丁强奸南希,丧心病狂地报复亨利。莎菲拉与南希的对立是女性与男性矛盾冲突的牺牲品,作为南方女人,莎菲拉骨子里根深蒂固的主仆思想和种族主义思想,使其在追求自身平等权利的同时从未赋予奴隶作为平等的人的权利。作为奴隶主,莎菲拉认为自己有权利以任何方式处置自己的奴隶,这是自己的权利,是不可侵犯的。因此,在没有权利话语的黑人奴隶面前,莎菲拉为所欲为地摆布南希,而南希则成为莎菲拉与亨利两性冲突的牺牲品。尽管传统的观点认为《莎菲拉与女奴》是薇拉·凯瑟“通过同情和理解来肯定生命”[3]的作品,但莎菲拉却是用“不同情”的报复心理一次次折磨着南希、亨利和自己。
三、女性与家庭的矛盾冲突
莎菲拉作为小说的核心人物,遭受着两个家庭的矛盾冲突的折磨。首先,在其原生家庭中,作为女儿,莎菲拉的个性与父母的期望格格不入,父母希望她能够像母亲一样成为一位典型的优雅的南方女性,在优渥的家庭中安稳体面地度过一生。然而莎菲拉却个性独立,精明能干,不想成为家庭生活的附属品。为了摆脱南方社会对未婚女性的歧视,违背父母意愿,下嫁到贝克克里克,这在母亲蒂尔看来,失去了尊贵的南方种植园生活的体面。在严酷的社会现实中,莎菲拉初步的独立的女性意识并没有掀起任何波澜,丝毫没有改变社会对女性的固有看法,并且与原生家庭的冲突与决裂也没能使莎菲拉过上幸福生活。其次,在与亨利结婚后,在这场女强男弱的婚姻中,莎菲拉并没有得到所期望的幸福生活。丈夫模糊的血统,以及称不上高贵的言谈举止,都让她觉得降低了自己的身分地位。此外,莎菲拉女强人的性格与丈夫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水火不容,而最重要的冲突则源于双方对蓄奴问题的不同看法。莎菲拉坚定地捍卫着自己的奴隶主的权利,而丈夫则不然。两人渐行渐远,分居多年。亨利独自住在磨坊,与莎菲拉只是偶尔一起吃饭时才见面。与丈夫的冲突和长期婚姻的不幸使莎菲拉变得更加片面、极端、不可理喻。莎菲拉与女儿的矛盾冲突主要集中在对蓄奴问题的看法上,莎菲拉是蓄奴制坚定的拥护者,而女儿瑞吉尔的废奴决心却比父亲亨利要坚决得多,母女关系非常冷漠,面对强势的母亲,瑞吉尔一直以来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快摆脱母亲,母女间第一次大的冲突就是瑞吉尔早早远嫁北方,逃离南方,逃离母亲。第二次则是在瑞吉尔的丈夫去世后,其不得不再次回到南方,偷偷帮助黑奴南希逃往加拿大。
四、女性与社会的矛盾冲突
小说中女性与社会的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上。蓄奴制的存在不仅是人与社会的主要矛盾冲突,也是对人性的拷问。美国自成立之初,便宣称人生来是自由而平等的。然而,有些人却是黑奴,他们是否能够自由?他们有什么样的平等权利?面对这样的问题,美国白人分成了三类。莎菲拉一家在这个问题上便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莎菲拉所代表的南方种植园主坚定地要求保留奴隶,在其眼中黑奴是排除在《独立宣言》之外的存在。另一类站在对立面上的人是女儿瑞吉尔所代表的坚决反对奴隶制的人,他们大部分是由北方人和一部分进步的南方人组成。最后一类,则是由亨利所代表的部分人,他们虽然对奴隶的境遇充满同情,但在行动上却缺乏勇气。在蓄奴制的南方,黑奴的生存状况完全取决于他们的主人,大部分黑奴都是生活在被主人随意打骂和变卖的毫无人格尊严而言的环境中。在小说开头,与风景如画的南方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奴隶制所带来的恐惧。瑞吉尔站在长长的走廊尽头,都能听到母亲莎菲拉对黑奴的冷冷训斥和梳子背重重地打在人的手臂和脸颊上的声音,被虐待和被殴打就是黑奴们的日常生活。小说中,南希的母亲用科尔伯特夫人的旧头巾为她改成了帽子,她觉得能带上这样的帽子就是人生的幸福时刻了,黑奴们从不敢奢望能有属于自己的东西,更不知“自由”为何物,在他们眼中自己最好的命运就是遇到仁慈的主人。而黑人女奴的境遇更是雪上加霜。在性别主义方面,小说中莎菲拉所处的美国社会,无论在蓄奴制的南方,还是在已经废除奴隶制的北方,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极其普遍,甚至在人们的眼中这种不平等是理所应当的。较之男性,女性没有平等的家庭地位、受教育权利、工作权利、平等获得报酬的权利等,更不用说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即便是像莎菲拉一样独立自主又有经济头脑的女性,在社会中也难寻立足之地。作为女性,她们的一切社会地位与社会属性都来自于原生家庭和自己的丈夫。因此,莎菲拉能够出生于南方种植园农场主家庭是与生俱来的一种“体面”,而下嫁于血统不够纯正的亨利则是失掉了一些“体面”。同样作为奴隶主,女奴隶主莎菲拉则没有权利变卖奴隶,必须经过丈夫亨利的同意才能把黑人女奴南希卖给邻居。另外,社会给予女性的工作机会少之又少,即使是在北方,女性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养活自己,无论女性多么有能力。瑞吉尔是一位思想解放、独立自主的女性,为了摆脱南方原生家庭的束缚,早早结婚,随丈夫来到北方。然而,丈夫去世后,瑞吉尔仍然无法靠自身的力量在北方生活,不得不再次回到南方父母的家中。女性所承受的痛苦与折磨远远不止这些,暴力与性侵十分常见。“白人男性就像捕食的野兽,而所有的女性都是他们的猎物”[4]。无论白人女性,还是黑人女性,都在性别主义的社会矛盾冲突中挣扎过活。莎菲拉的侄子马丁对黑奴南希百般纠缠,还玩弄了林格夫人家的两个女儿。比起白人女性,黑人女性的处境更加苦不堪言,在种族主义与性别主义的双重压迫下,黑人女性过着非人的生活。为了躲避马丁的魔爪,南希的精神几近崩溃,她不敢去打扫马丁的房间,却又不能违背主人的命令,她不敢走靠近小树林的路,害怕被马丁拉入树林深处羞辱,却又不得不按照主人的吩咐一次次走上这条幽灵之路。孤立无援的她幸得瑞吉尔的帮助才得以逃至加拿大,但能够得到帮助的黑人女性却只是个例,绝大多数黑人女性依然不得不生活在暴力与性侵的社会环境之中。种族主义与性别主义在蓄奴制的南方固然根深蒂固,在北方就会消失殆尽吗?其实不然。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人们将美国社会成员分成白人和黑人,而黑人女奴甚至还要排在黑人中的末位。
五、女性与自我的矛盾冲突
人与自我的矛盾冲突时常发生在人们因为无法同时满足个人的多个行为动机,而在选择面前难以行动,或选择之后遗憾后悔的情况。这时人们的内心便会产生一种以矛盾和斗争为主的心理失衡和情感困惑倾向。而女性在追求自我的成长过程中,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每做出一个选择都要在内心经历漫长而激烈的自我斗争。在小说中,女性与自我的矛盾冲突表现为社会自我与内在自我的冲突,以及伦理自我与欲望自我的冲突。莎菲拉的一生都在自我冲突之中度过。年轻时,莎菲拉以惊人的勇气,以为自己遵循了内心的渴望,摆脱了社会对其婚姻的偏见,毅然决然地搬到了贝克克里克。莎菲拉也曾为自己的精明能干和雷厉风行而骄傲,然而,婚后生活的不幸福,现实的不如意,使她一次次迷失在社会自我和内在自我的冲突之中,一遍遍地靠回忆过去聊以自慰。莎菲拉希望自己还生活在那个体面的南方种植园农场中,怀念自己在栗子山上的生活,遗憾自己太过刚强,而没能对残疾的父亲好一点,而所有这一切只有到她死亡之时,才回归到了她尊贵的种植园生活中去。作为奴隶主的社会身份,莎菲拉亦如其他奴隶主一般打骂黑奴,不择手段地折磨丈夫喜欢的黑奴南希,甚至让自己生性放荡的侄子马丁纠缠南希,马丁如果成功地强奸了南希,至少可以完成莎菲拉的两个目的:第一,报复丈夫亨利对南希的精神依赖;第二,获得自己作为奴隶主能够随意处置奴隶的满足感。当一切都按莎菲拉的心愿完美进行时,马丁对南希不断骚扰,已经把南希折磨得精神恍惚了。然而,就在事情即将成功之时,源自于莎菲拉内心的同情一遍遍地告诉她“It’s no affair of mine.”[5]仿佛在对自己说,一切都与自己无关,她只是请了马丁来做客而已,内心的良知与自己奴隶主的社会身份做着激烈的斗争。
此外,以拓荒者系列小说而出名的薇拉·凯瑟,实际上出生于南方。温暖的弗吉尼亚,有其美好的童年记忆。凯瑟对南方的情感本身就是矛盾而复杂的,一方面她深深地热爱着南方的景色、家族和文明。另一方面,成年后的她也清楚地知道南方的阴暗面。这种“近乡情更怯”的矛盾使她直到写作生涯的最后才勇于面对,写下了以南方为背景的小说《莎菲拉与女奴》,第一次直面自己的内心,将自己的南方情结和矛盾心理在小说中以众多矛盾冲突的形式展现给世人。凯瑟在自然风光迷人并且温度适宜的弗吉尼亚度过了她人生前九年的童年时光。南方对于她来说,就像故乡温暖的阳光和她快乐的童年一样美好,是她“生命最本质的东西形成的”[6]重要时光。凯瑟祖父与母亲都是典型的南方贵族。祖父血统高贵、事业有成,母亲迷人美丽、矜持高傲。南方生活以及南方家人对凯瑟的影响形成了她最初的种族意识,即血统高低的认识。在搬离南方的最初一段日子里,凯瑟家依然有女仆像在旧南方一样服侍他们,这种主仆关系在无形中形成了她作为白人的优越感。此外,凯瑟曾在评论《傻瓜威尔逊》的文章中写道:“……就在那三十二分之一的黑人血液里,他已经感染了这个种族最坏的品质。”[7]与对黑人的偏见相对应的,是凯瑟搬到内布拉斯加后,西部大草原对她的影响,她在1902年的采访中曾经和读者分享过这种感受:“一大片的土地,几乎没有篱笆,我们越往乡间走,越发感觉到了世界的尽头一种身份被消弭的感觉。”[8]正是西部的大草原淡化了她的种族意识,成就了其后来的民主思想:一方面,她包容族裔文化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她也有深植于无意识中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种族优越性,凯瑟的这种矛盾性是其性情中民主主义与精英主义的矛盾在族裔思想中的反映[9]。
作为女性作家,薇拉·凯瑟在《莎菲拉与女奴》中并没有将女性权利放大,也没有站到男性权利之上来叙述,而是用一种平等的视角将人性的各个方面描写得淋漓尽致,男性也好,女性也罢,没有非黑即白,也没有非好即坏。她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人在伦理自我与欲望自我的冲突下的种种表现。在小说中,在莎菲拉尖酸刻薄的言语与吝啬的为人处事之下,丈夫亨利连伪善都懒得假装,也顾不得展示自己的基督徒美德。婚姻生活的压迫感令他窒息,让他早早地退回到自己的世界中,独自一人住在远离妻子莎菲拉的磨坊中。而年轻阳光的南希的出现,就像清晨的一缕阳光照进了亨利黯淡了许久的心灵,长期的性压抑使得亨利对南希的欲望与日剧增。当亨利意识到这一点时,他慌乱地逃避着自己内心的渴望,不让自己做出有违伦理的事来。但当亨利发现马丁对南希不轨的意图时,理性告诉他要去阻止马丁,于是他监视马丁的一切活动,揣测马丁的心理,用马丁的视角来观察南希。结果事与愿违,一方面,他并没有勇气去阻止马丁,保护南希;另一方面,他对南希的欲望不减反增。亨利甚至在自己睡觉时都觉得,马丁的感觉像一个黑色的符咒一样,出现在自己的身上。他惊慌失措极了,伦理与欲望的冲突时刻煎熬着他,他将自己埋首于约翰·班扬的《圣战》中,想借此逃避对南希的欲望,但书中魔鬼占据了灵魂城(the town of Mansoul)却正象征着亨利的内心已经被对南希的情欲所占据。
六、矛盾冲突产生的原因
小说中,女性与男性、女性与家庭、女性与社会,以及女性与自我的矛盾冲突产生的原因既有当时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也有个人原因。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南北方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经济形式。南方为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实行黑人奴隶制。南方种植园主为了出口大量农业原料,要求降低关税,扩大进口,增加奴隶数量,并想在西部建立新的种植园。然而,北方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实行自由雇佣制。北方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自由资本主义,要求保护关税,废除奴隶制,在西部建立自由州,以此来保护国内市场,保障原材料的供应。经济利益的冲突加剧了社会冲突,从而将奴隶制的存废问题推向历史的风口浪尖。小说中莎菲拉与女儿瑞吉尔对奴隶制的不同态度,正是这一社会矛盾的缩影。美国社会中种族主义与性别主义的存在由来已久,因此,黑人女性的境遇苦不堪言。有着近似金黄色皮肤的南希是黑白混血儿,父亲是街头画家,还是亨利的弟弟,她的母亲被强奸与否,读者们无从知晓,对此,南希也从未问过母亲。同样作为黑人女性,并且为母女,南希一方面不想让母亲因旧事重提而被揭开心灵的伤疤,另一方面,“性”这个话题,在19世纪的美国社会还是一个禁忌。大多数情况下,黑人女性的身体从未属于过自己,彼此间也会用心照不宣来掩饰内心的伤痛。黑人女性的状况只维持在活着,其他所有伤痛只能自己默默承受。此外,在作者自身经历方面,生于南方的薇拉·凯瑟对故土的情感本身就是矛盾而复杂的。凯瑟写了一系列拓荒小说,却迟迟没有描写自己回忆中美好的故乡,一方面在于人们往往对自己越珍视的东西越是慎重地选择情感表达的切入点,另一方面,当作者清楚地认识到南方的不完美甚至有其制度弊端时,这种对故乡的复杂情感成为作者内心的冲突,几经辗转,最终在其最后一部小说中呈现。然而,所有关于冲突产生原因的分析都来自于读者,作者薇拉·凯瑟在小说中从未正面提及,哪怕是对内战的社会环境的背景交代,也只是用短短的一个章节而已,这是凯瑟对美国政治所表现出来的最大沉默,同时,凯瑟对于女性主义的认知并没有直白的表达。
七、结语
作为薇拉·凯瑟的最后一部小说,也是唯一一部以南方为背景的小说,《莎菲拉与女奴》的基调并不似她之前的作品那般表现出积极乐观与渴望成功,这部作品反而有些阴暗与沉重,她在小说中抽丝剥茧般向世人展示了男权社会中女性所面临的矛盾冲突,无论是女性与男性、女性与家庭、女性与社会,还是女性与自我的矛盾冲突都是作者对人性和美国社会的反思与拷问。作为作者回归南方的作品,也是告别文坛的作品,小说中诸多矛盾冲突是作者留给世人的思考,既是女性直面社会传统思想的呐喊,同时也是女性在残酷现实中的无声啜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