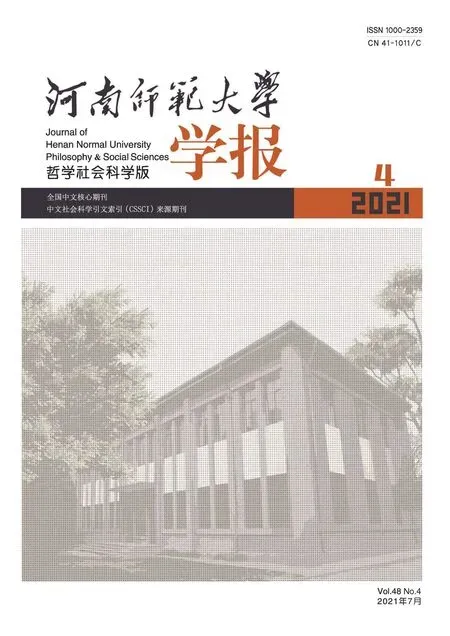论松本清张与鲁迅对“大团圆”思想的批判
2021-01-16李圣杰程一骄
李圣杰,程一骄
(武汉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松本清张(1909-1992)是日本二战后的著名作家之一,他开启了社会派推理小说的新风。鲁迅选择弃医从文之路,离开日本回国的那一年,正是松本清张的出生之年,而日后松本清张的创作也颇受鲁迅影响。藤井省三曾经指出,鲁迅“虽然是外国的文学家,但在现代日本是作为国民文学来对待,被人们接受的”(1)藤井省三:《鲁迅在日文世界》,《日本鲁迅研究精选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1页。。由此可见,鲁迅和他的文学在日本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力。在中日文学的对话和互鉴中,鲁迅与日本作家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中日学界关注的热点。
藤井省三在专著《鲁迅与日本文学:从漱石、鸥外到清张、春树》(东京大学出版会,2015年)、《松本清张的私小说与鲁迅的〈故乡〉——从〈父系的手指〉到〈跟踪〉的展开》(《文学界》,2012年)、《松本清张与鲁迅:〈骨壶的风景〉和〈朝花夕拾〉中的少时回忆》(《松本清张研究》,2014年)、《东亚的推理、超推理小说之系谱:松本清张〈眼之壁〉、莫言〈酒国〉与鲁迅〈狂人日记〉》(《文学界》,2020年)等论文中,对鲁迅和松本清张进行了比较研究。经考证,他发现松本清张的纪念馆书库中收藏有两册与鲁迅相关的书籍,“一册是1958年发行的《世界文学大系:鲁迅 茅盾》,该书收录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故乡》《阿Q正传》等主要作品;另外一册是由岩波书店于1956年10月发行的《文学》杂志的鲁迅特刊。连文学研究专业杂志的特刊都收藏了,由此可推测,清张对鲁迅怀有深切的关心”(2)藤井省三,林敏洁:《松本清张的初期小说〈父系之手指〉与鲁迅作品〈故乡〉——从贫困者“弃”乡的“私小说”到推理小说的展开》,《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3期。。据松本清张纪念馆的官方主页介绍,位于纪念馆一层、二层的书库,是按照1992年8月4日松本清张去世时的家中原样,迁移至位于作家故乡的纪念馆内的。除藤井省三外,南富镇也研究过鲁迅对松本清张的影响问题,他认为“代表日本和中国的国民作家鲁迅和清张,都处在以萧伯纳、木村毅、本间久雄、菊池宽、鹿地亘为媒介的相同思想的磁场中”(3)南富镇:《松本清张文学的叶脉:勒朋、鲁迅、李光洙、本间久雄、木村毅、萧伯纳等国际共同研究〈现代东亚文学史〉中的松本清张》,《松本清张研究》,2016年第17号。。以上是迄今为止学界对鲁迅和松本清张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本文拟在此基础上,从批判“大团圆”思想视角出发,对两人的创作再做进一步的分析。
一
“大团圆”思想,亦为“团圆主义”。有学者认为:“系统地提出‘大团圆’观念并真正引起反响者是王国维。”(4)李跃红:《“大团圆”:中国悲剧研究中误用的概念》,《江淮论坛》,2006年第1期。王国维认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5)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王国维文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42页。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大团圆”思想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许怀中对鲁迅在1920-1930年代批判“大团圆”思想的论述做了基本梳理,他认为从《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到《论睁了眼看》,鲁迅吸收同时代人的真知灼见,不断发展和完善了自己的观点(6)许怀中:《鲁迅论“团圆主义”和“教训小说”》,《福建论坛》,1981年第3期。;郝蜀山探讨了鲁迅反对“大团圆”的历史功绩及其片面性(7)郝蜀山:《论鲁迅的反对“大团圆”兼及悲剧的结局》,《黄淮学刊(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敖忠认为《论睁了眼看》是鲁迅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总纲,鲁迅对“大团圆”的批判具有独特的深刻性和战斗性(8)敖忠:《鲁迅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总纲:〈论睁了眼看〉》,《青海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鲁迅在《〈伪自由书〉前记》中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然而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9)鲁迅:《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在《论睁了眼看》中对文人、礼教提出批评:“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我们的圣贤,本来早已教人‘非礼勿视’的了,而这‘礼’又非常之严,不但‘正视’,连‘平视’‘斜视’也不许。”(10)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1页。接着,鲁迅指出这种礼教的不良结果是“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11)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4-255页。。在鲁迅看来,具有“大团圆”思想的作品大都是“瞒和骗”的作品,是麻醉剂,而这种不敢正视现实的态度则是“怯弱、懒惰而又巧滑”的国民性的反映。
对于传统文学作品,“蔡元培、胡适等人大多从男女婚嫁的视角批评‘大团圆’思想,故论述往往局限于《西厢》《红楼》等婚爱题材作品”(12)敖忠:《鲁迅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总纲:〈论睁了眼看〉》,《青海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鲁迅则将讨论延展到了更广的范畴,他指出,除爱情婚姻题材外,一些旧文人甚至罔顾关羽、岳飞被杀的史实,造出岳飞前世已造夙因、关羽死后成神的说法,易悲为喜。鲁迅曾说:“凡有缺陷,一经作者粉饰,后半便大抵改观,使读者落诬妄中,以为世间委实尽够光明,谁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13)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4页。“大团圆”粉饰太平、掩盖真实、弱化矛盾,它能麻痹人们的思想,也能磨灭人们的反抗精神,从而使得变革无从谈起。于是,鲁迅大声疾呼:“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它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14)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5页。从鲁迅的批判性文章中可以看到,传统文学中“大团圆”思想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大团圆”思想的流行,源自中国人不敢正视现实的国民劣根性;二、“大团圆”思想是一种广泛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主题倾向;三、“大团圆”思想是一种无视现实、自我欺瞒的精神麻醉剂;四、新文学创作应革除“大团圆”思想。
日本在二战后步入经济高速发展期,并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松本清张这个名字正是随着他揭示社会深层问题的作品不断问世而被人们所知道的,他由此也被贴上了“社会派”“叛逆者”的标签。从文学创作的内容上看,他关注现实问题、致力于揭露社会机制的阴暗面;从文学创作的态度上看,他则是一位富有反抗意识和挑战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家。“社会派”的内涵是洞悉社会,尊重真实,不作矫饰,不违良知。松本清张本人曾说,“社会派小说”就是描写“现代社会机制”,“给现代社会机制动手术”,重要的不是“作家的意图和姿态”,而是“作家的本质与追求”(15)志村有弘,历史与文学会:《松本清张事典增补版》,勉诚出版,2008年,第48页。。
松本清张在随笔中这样写道:“我认为,文学要有叛逆精神。对现有的道德反抗、对秩序反抗、对权力反抗,即便有多种形式的反抗,但文学的生命在于叛逆精神。”(16)松本清张:《松本清张全集:34》,文艺春秋,1974年,第457页。“反抗”和“叛逆”是松本清张文学的底色。连批判松本清张的大冈升平也承认他已被松本清张文学的“反骨”所吸引。大冈升平认为,自初期作品以来,松本清张一直秉承着反抗精神,但“松本的小说里,叛逆者最终只不过是对这些组织的恶行挥舞拳头。挥舞的拳头并非捣毁这些组织,也非策划以眼还眼的复仇。充其量不过是给对方的脸上抹黑的自我满足”(17)大冈升平:《常识的文学论(12)》,《群像》,1961年第12期。。大冈升平认为这种不痛不痒的反抗毫无意义,但也道出了一个事实,即松本清张笔下的小人物通常并未在反抗之后迎来“大团圆”的结局。对此,松本清张如是回应:“个人到底能用挥舞的拳头捣毁组织吗?……倘若这里个人的拳头具有狠狠破坏组织恶行的力量,或能策划以眼还眼的复仇,那才像是一场连拙劣的武打电影都不如的滑稽把戏。客观现实是,个人只有‘苍白无力的憎恶’。虽然如此,但不可断言:‘个人只对组织恶行挥舞拳头’是无现代意义的。”(18)松本清张:《大冈升平氏的罗曼蒂克的裁决》,《群像》,1962年第1期。大冈升平和松本清张此处所讨论的“个人对组织挥舞拳头”,是一种个体对群体的反抗。依照王国维的解释,倘若这样的反抗能够“捣毁组织”,则意味着个体的“大团圆”。松本清张将如此这般的“大团圆”视为“连一场拙劣的武打电影都不如的滑稽把戏”而嗤之以鼻。松本清张非常清楚,个人面对社会组织,其力量的悬殊不言而喻,别说去抗衡、捣毁组织恶行,就连“挥舞拳头”也需要足够的勇气。
鲁迅认为“大团圆”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流行源自民众的国民劣根性,他的这一“国民性批判”思想,其实受到了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朋的影响。鲁迅在《随感录》中曾引用勒朋的话:“法国G.LeBon著《民族进化的心理》中,说及此事道——‘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19)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29页。勒朋的思想也对与鲁迅生活于同一时代的本间久雄(1886—1981)产生了影响。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新潮社,1917年)第八章以“文学与国民性”为题,同样引用了勒朋的这一段话(20)本间久雄:《新文学概论》,新潮社,1917年,第100页。。《文学概论》(东京堂书店,1926年)为《新文学概论》的修订版本,保留了对这段论述的引用(21)本间久雄:《文学概论》,东京堂书店,1926年,第197页。。据南富镇考证,松本清张藏有包括《文学概论》在内的数种本间久雄所著(编)的书籍,并从中汲取知识用在了他的文学创作之中(22)南富镇:《松本清张文学的叶脉:勒朋、鲁迅、李光洙、本间久雄、木村毅、萧伯纳等国际共同研究〈现代东亚文学史〉中的松本清张》,《松本清张研究》,2016年第17号。,由此可推知,松本清张应该接触过勒朋的这一思想。
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抨击了社会中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国民劣根性,而松本清张所写的“社会派”推理小说也致力于揭露和挑战社会的痼弊。鲁迅将国民群体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审视,而松本清张所谓的“组织恶行”,其矛头同样指向与“个体”相对的“群体”。松本清张对于鲁迅批判“大团圆”思想所产生的共鸣,可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两人都主张文学创作要直面真实的社会,要敢于揭示“大团圆”思想中的自我欺瞒本质;第二,两人都关注到了“群体”的思想缺陷,并对此加以剖析审视,力图唤醒“个体”的反抗意识。
二
鲁迅和松本清张不但都曾旗帜鲜明地提出过直面现实的文学观,而且都将这一文学观念贯注到了他们的创作实践中。藤井省三在比较鲁迅《故乡》和松本清张《父系之手指》时指出,“《父系之手指》逆转了《故乡》中富裕的知识分子的视点,是从闰土及其儿子水生等穷人的视角重新叙述了的归乡故事”,换言之,闰土父子的形象与《父系之手指》中主人公父子的形象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松本清张后来因创作《跟踪》而走上了推理小说之路,恐怕已意识到《故乡》中与“我”处于对立地位的闰土父子,是“易堕落成犯罪者的贫者”,含有盗窃情节的《故乡》是“应该改写的盗窃故事”,而“正如通过用鲁迅《故乡》这条辅助线来分析清张文学从私小说转向推理小说的展开脉络一样,清张文学也启发了我们对鲁迅《故乡》的新读法——从私小说《故乡》到描述贫困者逻辑和情理的《阿Q正传》,这一鲁迅文学发展的课题”(23)藤井省三,林敏洁:《松本清张的初期小说〈父系之手指〉与鲁迅作品〈故乡〉——从贫困者“弃”乡的“私小说”到推理小说的展开》,《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3期。。刘建军在《阿Q与桑丘形象内涵的比照与剖析》一文中认为,阿Q的“Q”在结构上是一个封闭的圆圈,暗指中国农民的命运千百年来一直在历史的闭环中往复,鲁迅在创作中将它延展到其他阶层,“从而完成了对整个社会怪圈现象的审视”,各个阶层的反抗无不以失败收尾(24)刘建军:《阿Q与桑丘形象内涵的比照与剖析——兼论比较文学批评的一个视点》,《中国比较文学》,2011年第1期。。由此可见,阿Q这一形象富于典型性。
鲁迅在《阿Q正传》终章“大团圆”中,描写了充满人生苦难的阿Q,最后枉死在了“大团圆”的题下。这样的结局何其悲哀,又何其讽刺。阿Q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只不过是以自我麻醉的形式逃避现实的一种方法,这其实正是国民劣根性的根本所在。诚如有学者所说,鲁迅国民批判的根柢就在于对其劣根性的揭示,它以种种形式贯穿于民众的思想和行动之中,“到头来大概只能得到‘瞒’和‘骗’的自信”(25)张钊贻:《鲁迅“国民性”思想与中国文化复兴与自信》,《齐鲁学刊》,2019年第3期。。死到临头了,阿Q还以“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来安慰自己,可谓是愚蠢至极的“精神胜利法”。阿Q面对强者和弱者所拥有的不同心理和态度,是心灵上的扭曲,“精神胜利法”不过是他寻找自我安慰的借口罢了。《阿Q正传》最后一章以“大团圆”为题,却写了一个悲剧,它描写了阿Q在画押时画圆圈的场景,这圆圈恰似闭环的Q字。作家不写“大团圆”,毫无疑问是对传统叙述模式的反抗。
正如藤井省三所说,松本清张与《故乡》中的“迅哥儿”不同,他是从贫困者的立场出发进行创作的。平野谦说:“从岛崎藤村到太宰治,被害者意识是近代日本文学中的一个传统。而松本清张则不同,他始终怀着一种复仇和憎恶的情感去描写真正的受害者——底层人的真实生活状况。这是清张文学的最大优势,他以此为支撑,创作出所谓社会派小说这样的作品”(26)森信胜:《平野谦松本清张探求:1960年代平野谦的松本清张论和推理小说评论》,同时代社,2003年,第170页。。《父系之手指》是一篇以松本清张父子的人生际遇为题材的现实主义小说,也是一部表达了作者最本质的情感与思想的作品。作品中主人公父子两人的形象,是松本清张文学中各类社会底层人物形象的原点。
《父系之手指》1955年首次刊发在《新潮》9月号,初版使用的是第三人称,1956年修订时改为第一人称,收录于作品集《风雪》之中。本文所参照的是1972年由文艺春秋出版社发行的《松本清张全集》。小说的主人公“我”的父亲出生于一个叫“矢户”的地方,他本是富裕地主家庭的长子,后来因为被送到贫民家中做养子,而失去了原姓和优越生活。“我”的父亲崇尚学问,最喜欢被人夸作“博学”之人。“我”父亲半生飘摇、贫困不堪,而与他血脉相同的弟弟民治却功成名就;“我”的母亲目不识丁,民治的妻子却是教师;“我”与民治的孩子分别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轨道。“我”的父亲因被亲族疏远、遗忘而深感孤独,“我”则因与富裕的血亲差距甚远而深感自卑。《父系之手指》对父亲是这样描述的:“我父亲生于相当富裕的地主之家,且为长男。大约七个月的时候,就被送到贫穷的平民夫妇那里当养子,从此再也未能重返本家。”(27)松本清张:《松本清张全集:35》,文艺春秋,1972年,第397页。作者在小说的结尾写道:“我想:我回到九州后,不会给这位亲切的叔叔的遗族写一张明信片的。我才不会在矢户把父亲的墓和他们建在一处呢。”(28)松本清张:《松本清张全集:35》,文艺春秋,1972年,第420页。结尾看似是“我”有愤恨,断绝与血亲的联系。但事实上,“我”父亲被他的弟弟冷落已久,多次去信未得回复——亲情维系与否的主动权,事实上已经掌握在强势的血亲手中。阿Q出身贫寒,不被上层社会接纳,甚至连姓氏也要被剥夺。“我”的内心活动,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颇为神似,这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同样富于讽刺意味。
“我”的父亲失去了作为符号的姓氏的权利,本质上就是一个失去了富裕阶层身份而游离于其外的卑微个体。“我”的父亲与互相帮扶的其他亲族形成对立,穷困个体的微眇与掌握了诸多社会资源的群体之强大,形成了令人心惊的反差。鲁迅和松本清张毫不掩饰地呈现社会的冷漠和无情,乃至揭示了它不合理规则中的荒诞之处。在如此的境遇之中,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何来“始于困者终于亨”?“困者恒困”才是需要睁开眼看的真实状况。剖析其中的深层原因,唤醒读者的反思,正是鲁迅与松本清张共同的文学追求。
三
如前所述,大冈升平曾在1961年对松本清张提出批评。在大冈升平看来,松本清张在1961年之前发表的作品,大致具有“叛逆者最终只不过是对这些组织的恶行挥舞拳头”的特点。发表于1955年12月的《跟踪》是松本清张最早的推理小说。藤井省三指出,“鲁迅的《故乡》没有反映出贫困者的内心世界”,但《跟踪》则“精彩地描写了与法律和道德背道而驰的贫困者的逻辑和情感”,而他之后又发表的诸多推理小说,“像《砂之器》《零的焦点》等,由离乡、再会、‘弃’乡引发的案件不少”,这些案件“常常是悲剧性的结局”(29)藤井省三,林敏洁:《松本清张的初期小说〈父系之手指〉与鲁迅作品〈故乡〉——从贫困者“弃”乡的“私小说”到推理小说的展开》,《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3期。。《跟踪》中的石井久一背井离乡打工,失业、卖血,过着困窘生活,最终走上犯罪道路。《阿Q正传》中有一段极为相似的情节——阿Q调戏吴妈后,在未庄遭到排挤,无处谋生的他迫于生计而离乡进城,最后成为盗抢团伙的小喽啰。
继《某〈小仓日记〉传》之后,松本清张的主要系列作品有《菊枕》《断碑》《笛壶》《石骨》《装饰评传》《真假森林》,等等。这些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是日本俳句界、考古学界、历史学界、画坛、美术史界中的人物,他们的人际关系大都是分裂的。平野谦曾高度评价道,“即使他那庞大的长篇推理小说衰去,但这些系列作品将留存在文学史上”(30)森信胜:《平野谦松本清张探求:1960年代平野谦的松本清张论和推理小说评论》,同时代社,2003年,第115页。。这一系列作品均创作于1961年之前,它们几乎都描写了主人公充满挫折、并且未能“大团圆”收场的人生,是考察松本清张与鲁迅批判“大团圆”思想不可忽视的材料。
《真假森林》与前几部作品一样,以学艺世界为舞台,又加入了推理元素,可谓是该系列的集大成者(31)森信胜:《平野谦松本清张探求:1960年代平野谦的松本清张论和推理小说评论》,同时代社,2003年,第127页。。《真假森林》的主人公宅田伊作是一名才华横溢的美术史家,但是因为遭到学阀的排挤而过着落魄潦倒的生活。他偶然间结识了一名有潜力的仿画者,由此开始了复仇的计划:他要指导这名仿画者,让他仿造一批可以骗过那些根本不具备鉴赏能力的所谓专家权威的伪作,以达到让他们声名扫地的目的。然而,宅田伊作的计划最终功亏一篑。无论计划是否成功,他已无法迎来属于他自己的“大团圆”。评论家中野好夫指出,“无需赘言,问题不仅存在于这个世界里。清张本人在其他的作品里,也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其他的学界、政治界中的一样的虚伪(32)松本清张:《松本清张全集:37》,文艺春秋,1972年,第563页。”,将潜伏于社会深层的黑暗揭开,展示于读者眼前。《真假森林》打破了人们对于学界的一般认识,揭露了不具真才实学的所谓权威群体与怀才不遇的落魄个体研究者之间的对立,从而将无缘“大团圆”的人物形象延展至知识分子阶层。而《跟踪》和《真假森林》中的犯罪动机虽然大不相同,但犯罪者都陷于无法走出的困境之中,可谓“困者恒困”。在强大的权威面前,弱小的个体倘若能轻易地冲破困境,这作品无疑便沦为“瞒和骗”的文艺。这样的文艺正是松本清张所摈弃的。
倘若说闰土父子的形象,加入鲁迅的思考并经过艺术的加工后,演变成了阿Q形象,那么孔乙己便是阿Q进一步演变后的分身,他的出现表明无缘“大团圆”的人物存在于不同的阶层之中,他们在根深蒂固的社会机制和保卫这一机制的群体力量面前是无力抵抗的。松本清张的小说也是如此。以《父系之手指》中的父子形象为原型,松本清张笔下出现了从石井久一到宅田伊作等不同阶层的众多人物形象,他们甚至会被迫采用“犯罪”这一自毁式的极端手段,去做打破“困者恒困”的闭环的尝试,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他们的反抗同样是无力的。
松本清张是在获得芥川奖之后进入日本公众视野的。松本清张的创作精力旺盛,他的作品涉及历史题材、社会题材和犯罪推理,内容宽泛而丰富。以《跟踪》为分界线,他开始转向推理小说创作。推理小说大多以人物的犯罪行为为主线,揭示构成主人公扭曲心理并走向犯罪的根源。战后工业化的高速发展给新型都市的人们带来了红利,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同时也构成了很多想象不到的犯罪行为的社会之因,这些犯罪活动不仅打破了都市的宁静,而且危害了人们的富足生活。凡有利益驱使的地方就会有黑暗面,它们在阳光下暴露得越彻底,受到的批判就会越深刻。松本清张批判“大团圆”思想的文学内核始终如一。
《阿Q正传》的发表已逾百年,阿Q自卑下的傲慢心理,失落下的自慰心态,被鲁迅展现得淋漓尽致。鲁迅小说的价值不是对荒诞的揭示,而是对沉重现实的警示,对病疴社会的批判,正所谓“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33)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03页。。竹内好强调,要以自己的人生体验去阅读、理解鲁迅作品,用鲁迅的精神反省、批判日本近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困惑和问题。由此可见,鲁迅文学不仅在中国影响深远,而且在海外尤其在日本也流传甚广,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鲁迅和松本清张分别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甚至面对的受众也不同,但他们在文学创作的精神追求上却高度相似。文学家跨越时空的精神契合源于对社会的良知和责任。文化是有基因的,不会随时代的更迭而变异。关注社会是文学家的责任,有情怀有正义敢于斗争的文化人才是民族的脊梁。鲁迅影响着中日两国的后继者,松本清张正是其中之一。而松本清张的作品,又广泛传播于中日两国,势必也会对今后的创作者产生影响。这种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从中日文化交流互鉴的层面上讲,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