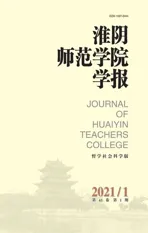周恩来与中共早期党组织的创建
2021-01-16汪浩
汪 浩
(淮阴师范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一、周恩来是中共早期“相约建党”的领袖人物之一
(一)中共党史已成共识的说法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道听途说”。意思是说,“相约建党”是“孤证,不足信”,中共党史强调“相约建党”说,有为自己“贴金”之嫌。这种说法是违背史实的。其实,从陈独秀1920年2月逃离北京,李大钊在护送途中,二人就“相约建党”了。其后,陈独秀在上海的家中与来沪送湖南籍赴法勤工俭学的毛泽东见面,陈委托毛回湖南筹建中共党组织。毛泽东回湖南后,又与在法国的蔡和森书信往来,谈建党的事。1920年冬,湖南长沙的中共早期组织在新民学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派魏金斯基到北京,约见了李大钊。经李大钊介绍,魏金斯基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戴季陶、沈玄庐等人。经两次座谈,于1920年8月在上海老渔里2号正式成立了上海中共早期党组织。此前因组织名称有分歧,陈独秀致信李大钊,后接受李大钊意见,将该组织定名为“共产党”。1920年8月,陈独秀写信给北京的李大钊、张申府,建议他们在北方发起建立中共组织。1920年10月,中共北方党组织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成立。1920年夏,李汉俊从上海写信给董必武,陈独秀也派刘伯垂去武汉。刘伯垂带着一份成立于1920年6月的“上海共产党”的党纲去见董必武。不久,在武昌抚院董必武的家中,武汉中共早期党组织成立。1920年陈独秀还致信谭平山、谭植荣、陈公博,约他们在广州组建党组织。陈独秀1920年12月到广州后,广州的党组织成立。还有,陈独秀1920年6月约旅日回国探亲的施存统(又名施复亮)加入刚成立的“上海共产党”。陈约施在旅日的中国学生中建党,并委派施与周佛海为“驻日代表,联系日本同志”。旅日党的早期组织于1921年4月在日本成立。在中共上海早期党组织成立的影响下,1921年春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成立了山东党的早期组织。以上事实散见于中共党史著作及《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等文献。事实说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通过不同途径、不同方式“相约建党”,虽然缺乏如石川先生所说的过硬的原始文献佐证,但“相约建党”是历史事实,不容怀疑。
周恩来参与了党的早期组织创建,是中共早期领袖人物之一。周恩来参与党的创建相对较迟。1920年12月,张申府受聘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任教,临行前与陈独秀见面,陈委托他筹建党的旅欧组织。张到欧洲后,先发展刘清扬、周恩来入党,后通过陈独秀与赵世炎、陈公培等人接上关系。不久,张申甫、赵世炎、周恩来共同努力,1921年春在法国创建了中共旅欧支部。赵世炎任书记,李维汉任组织委员,周恩来为宣传委员。他们是中共旅欧早期党组织的负责人。当然,周恩来介入“相约建党”的工作,有一个曲折的过程。这段故事还得从李大钊于1920年8月在北京陶然亭约周恩来等人谈“标明主义”的事说起。
(二)陶然亭五社团聚会是李大钊、周恩来等“相约建党”的一次重要活动。
1.这次活动是周恩来等觉悟社成员发起的,但研究者大都在认识和评价上没有将这件事提升到应有的高度。1920年8月初,觉悟社举办年会,出席者14人。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重在指出五四运动后应把全国青年进步组织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他把讲话的宗旨概括为“改造联合”4个字。8月16日,周恩来与觉悟社成员11人出席陶然亭五社团聚会。五社团为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青年工读互助团和觉悟社。石川的书中说“好像是由天津的觉悟社牵头”[1]105。实际上会议的程序也证明了这一点。会上刘清扬说明了宗旨;邓颖超介绍了觉悟社一年来的活动;周恩来作主旨发言,重复了觉悟社年会上“改造联合”的主张;然后请李大钊就五四运动后革命青年社团向何处去作指导——李大钊着重强调“标明主义”的必要;最后讨论通过《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并提出“到民间去”的号召[2]43-44。
2.陶然亭五团体聚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会议,它与中共成立前的“相约建党”有无关联?李大钊与俄方来华的代表是否参与了组织和安排?这从魏金斯基1920年8月17日给俄方领导的相关报告中可见端倪。报告称:8月16日至8月18日,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天津的觉悟社以及青年工读互助社等五团体,在北京陶然亭以及北京大学图书馆召开了发起“改造联合”的会议[1]105。魏金斯基当时在上海。他的报告写于会议进行中的8月17日。石川先生指出,这个报告有“预测”和“夸大”的嫌疑。然而魏的报告中时间、地点、会议主旨都与实际相吻合,这只能说明他与李大钊等人会前进行了协商并作了具体安排。韩素音的书中大致揭示了这种幕后的联系:“当年8月,周恩来和11名觉悟社社员到北京,在陶然亭公园里同少年中国学会……四个团体的青年一起座谈……李大钊……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讲话。周恩来的答词显得不太自然……李大钊征求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意见。周和其他潜在的共产党员被叫到北京大学会见一名俄国教师。恩来没有给这位俄国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于是,其他青年,而不是周恩来,被挑选送往莫斯科接受训练。”[3]53这段话中“共产国际代表”“莫斯科”等用词并不很准确,但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李大钊和俄方来华同志与五团体8月16—18日一系列活动的关系。
魏金斯基的报告另一个重点是,“一系列学生会议”旨在“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石川先生对这一名称有颇多微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会议的宗旨在于建立统一的青年组织。从魏金斯基的报告中“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步调确实加快了”这句话可以知道,一系列学生会议是为了给中国共产党成立作铺垫[1]104。
3.李大钊“标明主义”的指导意义本质上就是“相约建党”的明示,是目标鲜明的试探或动员。李大钊这样做的根据是,《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基本反映了当时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也接近在中国组建共产党组织和人员素质的要求。这一点在前引韩素音的那段话中已经揭示了。“改造联合”是周恩来在8月初觉悟社年会上发言的中心词。觉悟社年会与五团体聚会有怎样的关系,觉悟社怎么成为牵头单位,上述几种文献没有说明这一点,但仅从“改造联合”这四个字就可以看出周恩来发挥的重要作用。
4.“标明主义”是李大钊向周恩来等进步青年“相约建党”提出的建议,但因周恩来等未作出积极回应而未能达成“相约”目标。不论“相约”成功与否都有其特定的价值。周恩来面对李大钊的“相约”没有作出积极回应,与毛泽东这一年没有随同湖南籍蔡和森等一同赴法勤工俭学,一个是不盲从,一个是注重国内的事务;一个出国,一个不出国。虽选择不同,但共同点都是独立自主。石川先生说中共党史强调“相约建党”,“意图是”强调中共创建不是受共产国际指使,而是“自己努力的结果”[1]89。中国共产党早期两大代表人物建党初就表现出来的这一特征,虽然是小细节,但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这个重大问题上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一个道理:内因是根据,外因是重要的条件。这种独立自主精神,此后贯串中共百年历史。它的意义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史这个问题上,无须用“相约建党”说来为自己“贴金”。
总之“相约建党”是史实。南陈北李1920年有无“相约”并不是本质,本质是从此以后仅一年多时间,全国各地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纷纷建立起来了。不是南陈北李就是北李南陈相约,或是蔡毛、陈董、李董相约。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相约”中创立起来了,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二、周恩来为中共党组织的创建所作的贡献
(一)思想舆论方面的准备
周恩来在旅日期间,受新中会影响,参加其活动,并在该组织的学习活动中作过“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的演讲。不久回国,在五四运动中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宣传“民主: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我们的箴言”,率先举起陈独秀首倡的“民主科学”这面当时红遍中国的大旗。
五四运动期间(1920年5—6月),周恩来被捕。在狱中,他先后五次宣讲马克思主义,分别是5月28日、5月31日、6月2日、6月4日、6月7日。内容依次是:①经济史与马克思传记;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③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史;④资本论与剩余劳动、剩余价值;⑤资本论与资产集中论[2]41-42。
周恩来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宣传民主与科学、革心与革新,积极向《益世报》《新民意报》投稿,组织学生社团开展演讲、宣传与编演现代文明剧等活动,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做唤起民众的工作。旅法期间,他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时评,揭露北洋军阀政府向法国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印花税、验契税的阴谋,致使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他非常重视引导公众舆论的重要性以及在新闻媒体中塑造形象的巨大力量。
(二)组织与干部方面的准备
主要是组织学生社团活动。后来社团发展为革命青年知识分子的组织,聚集了一大批先进青年。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周恩来旅欧期间。觉悟社是五四时期天津革命青年的核心组织,当时一些社会活动家曾赞扬这些革命青年是天津的“小明星”。天津觉悟社与长沙《湘江评论》一南一北,相互呼应,产生很大影响。在中共早期烈士中,从觉悟社走出来的有多名,如黄爱、马骏、郭隆真、于方舟。旅欧党组织中则有蔡和森、赵世炎、王若飞、向警予、孙炳文、陈延年、陈乔年等人。旅欧党组织还为党和军队以及国家建设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材,如朱德、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李维汉、陈毅、蔡畅、李立三等。从这方面说,在中共早期党组织中,难以找到与旅欧党组织相匹敌的。这与周恩来非凡的组织才能与人格魅力有关。
觉悟社公开半公开的组织活动形式很特别,也很有见识,这为其后党组织的秘密活动积累了经验。
利用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习会,提高组织成员的思想理论素养,同时开展反对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费边社会主义、基尔特改良主义的斗争,特别是对中国的改良主义、保皇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是很有针对性的。它增强了组织的凝聚力,锻炼了成员的斗争精神。这种学习的、战斗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有力地促进了旅欧党组织的发展。
(三)大联合与统一战线的探索
在中共早期的领袖人物中,周恩来较早倡导大联合,倡导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周恩来积极串联法、德、比、英等国的中国学生,参加旅欧学生反对北洋军阀政府与法国当局相勾结的卖国行径;还与国民党派往法国组建国民党欧洲组织的代表合作,发展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提出“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的鲜明主张——这是建党初期反对党内关门主义与投降主义,正确阐述民主革命与共产革命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是中共早期在实践与理论上的一大贡献。《周恩来传》指出,年轻的周恩来“有如此深刻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4]95。
三、中共早期组织创建中周恩来表现出来的高尚革命精神
(一)探求比较、实事求是、绝不盲从的精神
周恩来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受封建文化、进化论、改良主义的影响较重。直到五四时期,他才比较系统地学习与宣讲马克思主义,但他当时并未下决心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与毛泽东大约同时,即到1920年春夏,还没有摆脱改良主义、进化论的影响。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前引1920年8月16日在觉悟社等平津五团体举行的陶然亭“茶话会”上,李大钊强调应标明“主义”[4]60,这其实是李大钊与周恩来等“相约建党”的指导意见,可惜当时周恩来因为纠结于中国革命应选择英国式的“渐进”,还是俄国式的“暴动”,没有积极回应李大钊。他也是因为这个问题下决心去欧洲考察学习的。前引韩素音的书中提到,李大钊与周恩来“相约建党”,对周恩来没有回应不满意,又通过共产国际代表再约周恩来等11名觉悟社社员去北大见俄籍教师柏烈伟。周的表现没有给这位俄国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但李大钊十分看重周恩来“这位年轻人潜在的组织才能,他的能言善辩和超凡的魅力对于一个正在酝酿中的政党来说是非常宝贵的”[3]53-54。为了回应李大钊和柏烈伟,周恩来下决心去了欧洲。但他到了欧洲,不去学校,不去工厂,却奔赴生活费最昂贵的伦敦,实地考察这个进化论发源地和“渐进式”议会民主的典型国度。经过实地考察,他认识到英国渐进式的道路“欲其求免于贫困也难矣”[4]65,显然不适合中国。英法等列强之间的相互争夺是“世界祸乱之源”,而“俄国则在以世界革命之思想,鼓动其民族之真正独立”[2]49。经过比较,周恩来最终确定“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4]71。周恩来对信仰的认定,从旅日到旅欧,中间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反复推求比较了好几年,才确定下来。他的推求,既有对他国如日本的、法国的、英国的推求,也有对中国国情的推求;他的比较,不仅有对他国与中国,而且有对他国与他国的比较。抉择的标准是看是否适合中国,能否解决中国贫穷进而腾飞世界的问题。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此后贯穿他的一生,这是他的成功之本,也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精神。有人认为旅欧支部的成立,受到了法国共产党的影响。韩素音指出,这种看法是“肤浅”的。因为当时法共内部分歧严重,为此曾受到过列宁的批评。在法共的文献中,只有一处提到周恩来等几人出席法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次会的开幕式。[3]72-73
(二)勇于担当、乐于奉献精神
周恩来不具备赴日、赴欧考察学习的家庭经济条件,是他经过多方努力,又得老师、亲友的资助才成行的。其间,他有一次比较好的就业机会。他从日本回国探亲,去了哈尔滨,他的弟弟周恩寿及南开同学引荐他去哈尔滨一所学校教书,薪水也很好,但周恩来婉拒了。其后赴日本便参加了新中会的活动。不久后“回国图他兴”。本想去南开大学读书,但他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五四革命运动,不久被捕入狱。他自己说“思想颤动于狱中”,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从此他就逐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4]60他的选择体现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济世穷”的勇于担当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这就是陈晋同志用周恩来自己的话所指出的“宁务其大,不务其小”[5]的道理。
1922年周恩来的女友张若名被选为代表出席俄共(布)代表大会,后身份暴露被追捕,加上来自党内“左”的同志追究其家庭出身的压力,她不听周恩来的反复劝告,愤而选择脱离中共早期组织“少共”。周恩来从革命大局着想,牺牲了他与张的恋情,转而与邓颖超通信。这一段故事,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的书中有记载[6]。生命与爱情,在革命者面前“二者皆可抛”,周恩来做到了!这种人生抉择,既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勇敢担当,也是不顾一切包括牺牲爱情的无私奉献。
(三)自觉革命、自我革命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从六个方面称周恩来是杰出楷模,其中就有这一条。在周恩来一生中,这是很突出的一个方面,也是他坚守朴实、追求崇高,最终走向人生巅峰的秘诀所在。自觉革命、自我革命精神的核心理念有三个关键词:选择、修正、完善。选择是实事求是地选择,要以客观实际为根据,大方向不能错。大方向不错不是说不需要调整,因为客观实际在不断地变化,需要因变化而作适当修正。完善也是修正,修正利于目标的实现。周恩来一生有六次重大选择:一是离家去东北,二是旅日,三是“回国图他兴”,投身五四运动,四是旅欧,五是认定马克思主义终生不变,六是恋爱婚姻的正确抉择。除了第一次属于被动性选择,其余五次都与他参与建党有关。尤其是在职业的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认定和爱情婚姻的抉择上,慎而又慎、独立思考、反复推求比较——包括普通职业与职业革命家的比较、英国与俄国道路的比较、革命者意志坚定与否的比较。在党的早期重要人物中,有些人凭一时冲动或者受裹胁,糊里糊涂地入党,结果有的不久便脱党、掉队或者走向反面。而周恩来一旦认定主义就“一定不变了”。如他自己所说,白色恐怖下没有胆怯过,没有动摇过,这与他最初的选择极慎重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慎初”的说法,周恩来行稳致远,道理就在于“慎初”——初心的慎重抉择。
选择(抉择)是一种理性驱使的判断。它标志着人生成熟的层次性,这种层次性取决于自觉与自我。周恩来的几次人生选择,第一次离家是自觉,但不能算自我,其余都属于既自觉又自我。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定,是自觉、自我的艰难抉择。选择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把自己的一生包括生命交给党和人民。有人说爱情是最自私的,可周恩来不是这样的。他寄给邓颖超暗示求爱的明信片印有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的照片,寓意是希望像他们那样一同走向绞刑架。这是一种高度自觉、自我的牺牲精神、奉献精神,也是担当精神。抉择是领导者最重要的能力,担当是领导者最可贵的品质,周恩来在建党早期,就锤炼了自己的这种领导者的风范。
周恩来的自觉革命、自我革命精神,还表现在他的人生成长模式的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完善上。俄国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倡导道德的自我完善的社会改良主义,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马克思主义者的自我完善是指革命者自觉地在革命实践、在群众斗争中“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其核心理念就是周恩来自己说的“自我”“自觉”“革心革新”。赴欧前夕,青年周恩来整理出青少年时期完整的人生档案(学习生活资料),交给一位同学保管,后辗转到同学柴孺瞻手上,新中国成立后经张济、刘焱等人转交给中央办公厅,周恩来逝世后由邓颖超交给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1)李海文:《关于周恩来日记等早期文献发现的经过》,《李海文致汪浩、张红安信》。周恩来早期文献表现了周恩来精于设计、精于总结的人生特点。“设计”“总结”,适时“修正”和“调整”,是共产党人自觉革命、自我革命必不可少的人生历练。
成为职业革命家的周恩来还把他的人生态度和人生模式带进了党的组织。他在处理顺直省委、江苏省委问题时,坚决地改变了向忠发、李立三追责与“打板子”的处罚性做法,代之以政治引领、大道理管小道理、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实际工作中总结和考验干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正确做法。后来他又将这一经验运用于处理“二月来信”到“九月来信”红四军前委领导层分歧问题,取得了我们党从古田会议的成功到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以及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第一次复兴的巨大成功。后来又在遵义会议上在这一经验基础上,用和平、民主、团结、批评、民主集中制方式,实现了党的最高领导层权力的交替——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抗日战争中,经延安整风,毛泽东将这一经验概括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成为中国共产党自觉革命、自我革命的模式。自觉革命、自我革命不仅是周恩来在党建思想方面的重要贡献,而且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