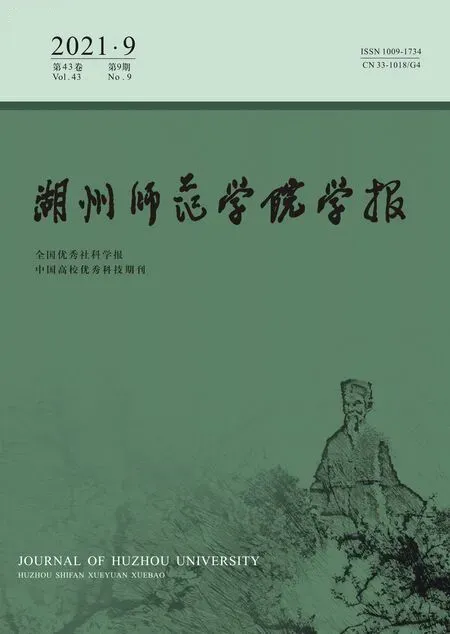阶层跨越、种族平等与国家正义的诉求:欧茨小说的政治伦理观照*
2021-01-15唐丽伟
唐丽伟
(广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1938-)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小说家、诗人和批评家,其小说以哥特式的棱镜折射美国现实社会,触及学术界、法律界、宗教界、政坛等多个领域,涉及“谋杀、暴力、混乱、贪婪、腐败、死亡和各种神秘事件”[1]120。欧茨也因此备受西方媒体和评论界的诟病。面对责难,欧茨坚定地回应称,现实世界比她所描绘的“更混乱、更血腥、更暴力”[2]201-206。对于欧茨而言,无论是对社会暴力或种族歧视的描写,还是对政治腐败的关注,都不过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使然。身为作家兼批评家的欧茨,同时也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其写作并不拘泥于专业领域,而是更多地介入公共生活,关注现实问题,并用振聋发聩的方式把“当代人在残酷现实面前惨遭蹂躏劫掠的生存困境展现给读者”,进而警醒混沌懵懂的现代人[3]201-206。面对美国日渐衰微的政府公信力、重新抬头的“白人至上主义”、愈演愈烈的司法腐败、无处遁逃的暴力侵袭和阶层之间的深厚隔膜,欧茨从未置身事外,多次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美国政府和主流社会,其终极目标在于引导人们认识到政治伦理缺失所带来的危机,促进公共话语的有效流通,从而改善社会现实。欧茨对美国底层民众阶层跨越问题、少数族裔种族平等渴望和普通民众国家正义诉求的关注,揭开了美国民主的虚伪面纱,暴露了“美国梦”的虚幻性和欺骗性。
一、底层民众的阶层跨越之梦
欧茨向来关注底层民众的生存境遇。她曾在一次访谈中说:“在美国,最伟大的历险就是社会阶层的提升。”[4]547无论是《他们》中的母亲洛蕾塔、儿子朱尔斯、女儿莫琳,还是《奇境》中的杰西、《浮生如梦》中的诺玛·珍,抑或是《狐火》中的狐火帮女孩,他们都体现了一群富有理想、永远天真和怀揣“美国梦”的底层穷苦白人对实现阶层跨越的渴望。他们在追逐“美国梦”的过程中不择手段,体现了底层民众幻想通过自身努力挣脱固有阶层,实现阶层上升的梦想。欧茨说:“我的作品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去描写底层人的抗争,……我曾生活在他们中间,理解他们对阶层跨越的渴望,以及他们为挣脱残酷现实所做的抗争。”[5]
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小说《他们》,讲述了温德尔一家三十年间在充满贫穷、暴力与动荡的“凶杀之城”底特律的痛苦挣扎。温德尔家两代人的命运沉浮是美国底层阶级生存的真实写照,他们的生活唤起了读者对底层民众生存状况的思考。这些被上层社会排斥的“他者”是被时代忽略、游走于社会边缘的无产者,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对生活的憧憬和对“美国梦”的追寻。他们凭着各自执着的精神和坚韧的意志力,在充满未知的困境中寻找人生的出路和成功的可能性。欧茨在谈及《他们》的创作时说:“小说名称‘他们’指的是特定的人群,这群人是美国社会特定时期特定阶层的人,他们备受‘美国梦’的诱惑,(这个梦)看似触手可及,实则是海市蜃楼,终究无法抵达。”[6]46
朱尔斯是“美国梦”的信仰者,无论通往上层阶级的道路如何坎坷,他始终不肯放弃。从孩童时期起,朱尔斯就多次离家出走,年幼的他天真地以为只要离开就能摆脱当下的困境。即使身处逆境,他依旧抱着一个信念,“总有一天,我会改变这一切的”[7]103。被学校开除后,没有一技之长的朱尔斯只能在饭店停车场工作。每当看到开着豪车、衣着华丽的富人从他身边经过时,朱尔斯便会莫名地兴奋,并“爆发出狂热的、缤纷的希望”[7]123。然而,这种希望又在瞬间化为泡影:富人们从饭店走向停车场是如此轻松自在,可是反过来,在停车场工作的“他们”想要迈入饭店的大门却是可望而不可即!停车场与酒店之间短短几百米的距离暗示着无法跨越的阶层障碍。正是因为这种不可跨越性,每当搀扶饮酒过量的富人上车时,朱尔斯都能意识到他们迈出的步子表面上是和自己一样的,实际上他们之间的距离却遥不可及。
朱尔斯与富家女娜达的相识重新点燃了他对“美国梦”的憧憬。娜达优越的家庭背景像是笼罩在她身上的光环,散发出的熠熠光辉吸引着朱尔斯以飞蛾扑火之势向她靠近。他相信自己命运的转机就要来临,他以为靠近娜达就意味着进入了她所处的阶层,她会带他走上底特律最宽广的“伍德沃大道”。事实上,娜达最初对朱尔斯的接受主要源于她对家庭的叛逆。当发现朱尔斯真正爱上自己时,娜达突然感到一种无名的威胁:与底层的穷苦人相恋是有辱自己身份的行为。短暂的激情过后,娜达陷入了恐慌,她害怕与朱尔斯的亲密关系会把她从安全地带推向自我毁灭的“雷区”,这条“界限”就是阶层的壁垒。虽然娜达也对朱尔斯产生了某种情愫,但一想到他的生活环境,浮现在她脑海中的场景全是疾病、混乱、暴力、黑人、卖淫女……娜达无法接受那样的生活,理智告诉她不能任由朱尔斯冒犯她的尊贵身份。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她扣动了扳机”,将子弹射向朱尔斯的胸膛,企图将他毁灭。幸运的是,朱尔斯活了下来,但娜达的这一枪终于让他明白:爱情终究无法带他跨越阶层。
《浮生如梦》是以好莱坞女星玛丽莲·梦露的生平为蓝本创作的一部“虚构性回忆录”,讲述了诺玛·珍(梦露的原名)的“美国梦”——对爱情、家庭和事业的追求。诺玛·珍是一个私生女,幼年时期饱尝生活的困顿和无助,但她一直渴望有朝一日能遇上自己的王子,过上公主般的生活。成名前,她结过婚,当过工人,做过模特,拍过裸体挂历。为了实现“美国梦”,诺玛·珍在政客、导演、制片人和经纪公司老板等男性的世界中周旋,历经无数磨难,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数重压力。成名之后,诺玛·珍成为上流社会男人猎艳的对象,她误以为自己终于从“灰姑娘”变成了“美丽的公主”,从此会有一个“王子”守护自己。然而,无论是她第二任的棒球运动员丈夫,还是第三任的剧作家丈夫,抑或是白宫的“神秘情人”,都没能给她带来幸福。因为多次流产丧失了生育能力,诺玛·珍苦苦追求的童话爱情和温馨家庭都成为泡影。求而不得,她把目标转移到演艺事业上。遗憾的是,消费社会对女性身体的商品化无情地抹杀了她追求表演艺术的努力,她渴望在事业上有所建树以赢得尊重的梦想也未能如愿。
与朱尔斯和诺玛·珍的命运不同,《奇境》中的杰西是成功实现阶层跨越的底层代表。《奇境》的故事发生在二战前后,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跨度中,随着主人公姓氏的三次变换,其生活境况也逐渐好转——从孤儿到养子再到著名的外科医生,他从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变成一位颇负盛名的外科医生。杰西上升的道路坎坷而具有传奇色彩,他先后四次被父亲、外祖父、姨父和养父抛弃,命运的磨砺使他领悟到一个真理,即“人应当认识自己,拯救自己,使自己成为应该成为的人”[8]142。大学期间,他没有任何时间娱乐休闲,除了兼职赚取生活费,他把所有时间和精力用在专业学习和实践上。因为表现突出,杰西受到医学院卡迪教授的关注,毕业后顺利迎娶卡迪博士的女儿,这段婚姻很大程度上为他后来事业的成功和阶层跨越奠定了经济和社会基础。饱尝底层生活辛酸的杰西,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为了稳住中产阶级的身份,婚后的杰西无暇照顾家庭,拼尽全力去稳固自己的事业,没日没夜地扑在工作上,事业成功的背后却是妻子的落寞和女儿的离家出走。然而,对于无数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杰西的成功就是他们的梦想。不管实现阶层跨越的希望多么渺茫,欧茨依然给读者保留一丝希望,杰西的成功就是给后来者的一道光亮,她似乎想通过杰西的逆袭来鼓励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依旧在努力拼搏并对阶层跨越怀有憧憬的人,只要不放弃努力,总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二、少数族裔的种族平等之梦
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由来已久,少数族裔长久的抗争使这一局面得到很大改善,但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在美国并未消失。发展到今天,美国的种族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单一问题,而是成为渗透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卫生、宗教、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结构性问题[9]82-86。种族歧视和偏见已深深植根于美国的社会和历史,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顽疾。欧茨身为犹太移民后裔,一直都关注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小说《因为它苦,因为它是我的心》“准确地描绘了美国种族仇恨的廓形图”,成功地刻画了“黑人和白人之间令人战栗的巨大鸿沟”[10]49。除此以外,欧茨在《我带你去那儿》《狐火》《中年》《黑女孩/白女孩》《掘墓人的女儿》《被诅咒的》和《迦太基》等多部作品中,都涉及少数族裔在美国所遭受的磨难、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冲突等问题。
小说《黑女孩/白女孩》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大学,故事以白女孩吉恩娜回忆十五年前的大学室友黑女孩米奈特的神秘死亡开场。米奈特与吉恩娜的第一次见面,因为英语发音不标准,吉恩娜不断对其予以纠正,这让米奈特深感自卑。米奈特是一个非常努力且独立的黑人女孩,但因为自己的肤色差异,语音语调异常而忐忑不安,她时常夜半三更“在客厅里自言自语,时而责备自己,时而祈求上帝保佑自己”[11]5。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米奈特总是独来独往,刻意和白人保持距离。虽说吉恩娜表面上同情米奈特,可潜意识里同样是抗拒这个黑人室友的。在吉恩娜眼中,米奈特形象丑陋邋遢,一张“毫无生机、又黑又大的圆脸”,“硬得像电线,闻起来有一股油腻气味”的头发,躲闪的目光,“贝壳粉的塑料眼镜让她看上去像小学生一样傻呆呆的”[11]10。吉恩娜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审视着米奈特,不接受米奈特的长相,因为她有一个潜在的女性评价标准——白皮肤、柔软的金发和苗条的身材,白人主流审美观念中的正常女性形象。
因为是黑人女性,米奈特在学校经常莫名其妙地遭受各种歧视和骚扰:她卧室窗户的玻璃三番五次被人打破,她的课本总是莫名其妙被丢到教室窗外或泥坑里,她的抽屉里时常被人塞进丑化黑人女性的漫画,不善言辞的她被白人同学和老师认为是态度“粗鲁且傲慢”,她去商店买东西总会招来白人售货员的警惕和怀疑……这些细节处处表明黑人在白人群体中备受歧视,也彻底成了被边缘化的“他者”。在白人室友吉恩娜看来,米奈特不受欢迎并非因为她的肤色,而是由于她自身怪异的性格特征。事实上,这些“看似平常的厌恶背后,隐藏着的是更深的、更邪恶和致命的种族仇恨”[11]128。来自白人同学的歧视、欺凌,加剧了米奈特的自卑感和孤独感。无助的她为了远离白人同学,想方设法搬到远离校舍的简陋小屋里,但终究没能摆脱白人的“围困”,在19岁生日的前一晚,她在睡梦中死于一场神秘的大火。米奈特的死亡暗示了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要将黑人赶尽杀绝的极端心态。
美国的种族歧视并非个别行为,而是一种全员参与的文化整合状态,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累积形成。这种文化模式是历史、政治、经济、教育和宗教等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从历史原因来看,正如小说中吉恩娜的父亲马克斯所说:“我们的种族从来就是奴役他人的,那些有色民族一直被我们奴役……我们的双手都沾着鲜血,我们是注定享有特权的白种人。”[11]93美国种族主义之所以大行其道,“并不是什么天生的黑白之别的产物,而是源于阶级偏见与歧视,是一种现实的进行控制的工具”[12]48。此外,基督教利用《圣经》中的故事宣扬黑人的贫穷是由于其懒惰愚蠢所致,为白人实施种族压迫和歧视找了一个借口。也正是因为这一谎言,大部分白人从小就对黑人产生偏见,并从内心深处埋下种族歧视的种子。尽管如此,欧茨还是对消融种族歧视抱着乐观的态度:小说标题是并置在一起的“黑女孩/白女孩”,这两个不同肤色的女孩同住在一套公寓里,白女孩吉恩娜努力地靠近、了解和关心黑女孩米奈特并对她的遭遇感到自责,整个故事表明欧茨在努力探索种族之间相互融合的可能途径。
美国虽然自诩是个兼容并包的“大熔炉”,但其深厚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从来就不信任犹太人,美国社会各阶层白人都把犹太人当作可恨的竞争者,因此,美国的反犹主义根深蒂固。小说《掘墓人的女儿》是对美国犹太移民生存境遇的关注,主要讲述了主人公丽贝卡在美国隐藏犹太身份、追寻美国身份到接受犹太身份的心路历程,反映了美国社会自二战以来对犹太移民的偏见与歧视[13]7。丽贝卡一家的遭遇是美国反犹主义的最好例证:三兄妹在学校饱受欺凌,学校的老师和领导对此听之任之,他们最终都被迫退学。一家人哪怕是龟缩在墓园,其藏身之所也在万圣节时被破坏得一塌糊涂。因为不堪当地白人的羞辱,大哥赫彻尔动手反抗,打伤他人后为躲避抓捕而亡命天涯。幸运的是,历经磨难的丽贝卡在故事的结尾嫁给了白人富翁加拉格尔,但其联姻成功也是以隐藏自己的犹太身份为前提的。结婚后,这一无法言说的秘密让丽贝卡终日惴惴不安,担心历尽艰辛所获得的一切随时会被剥夺。
《被诅咒的》是2015年出版的小说,故事的开始就是一对在路上行走的黑人姐弟被三K党无辜杀害,其时黑人姐姐正怀有身孕。普林斯顿大学白人青年教师雅格义愤填膺地将事件经过告诉时任校长威尔逊,希望他带领有影响力的学者们对三K党的这种罪行进行公开批判,以制造舆论压力,为黑人的基本权利进行声援。因为雅格发现“卡姆登县的警察们并没有阻止这样的谋杀,事后也没有去抓捕嫌疑犯人,甚至没有任何调查”[14]80。当时的南方,白人对黑人私设刑法是常见的事情,黑人命如草芥,“凶手从未被绳之以法”。美国作为有着众多基督徒的国家,表面上有着“爱邻如己”的信仰,但他们对黑人的不幸遭遇却常常保持集体缄默。因为在这个国家,几乎所有白人都赞同“不应造成种族混杂,要保持白人种族的纯净”[13]9,因此他们选择对三K党的罪行视而不见。对于政府的不作为以及小说中身居要位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缄默,欧茨的内心充满了愤怒和失望。
在小说《我带你去那儿》中,欧茨通过女主人公阿尼利亚的陈述表达了自己对美国政府在种族政策方面的鄙夷和不满。阿尼利亚因无力承受姐妹会的各项开支,为了找个理由退出,她谎称自己是犹太人的后代。当阿尼利亚把这个伪造的“事实”告诉她们时,她们吃惊地望着她,“好像我说了什么污言秽语,把她们那迷人的搽了粉的脸都弄脏了。她们红着脸摇了摇头,得体的装聋作哑。她们拒绝看我的眼睛,甚至也不敢相互对视,只想快点逃离”[15]108。最后,阿尼利亚因为“不诚实”被逐出姐妹会。后来,阿尼利亚爱上了一名黑人研究生,当他们谈恋爱的消息被公开后,她被学校相关负责人喊去训话,甚至还被指控为“有反社会倾向”。对此,阿尼利亚没有退缩,她强烈表达自己的抗议,“我爱谁是我的自由,你无权干涉!如果你们继续歧视我的朋友,继续威吓我,我将起诉你们,这是我作为美国公民的权利!”[14]209
对于种族平等的梦想,欧茨通常是将不同种族之间的爱情和婚姻作为沟通的桥梁。在《因为它苦,因为它是我的心》中,白人女孩艾瑞丝和黑人男孩金克斯苦苦相恋;《我带你去那儿》中的白人女大学生阿尼利亚不顾他人眼光和议论,无可救药地爱上了黑人马修斯;《黑女孩/白女孩》中的混血女佣吉纳瓦嫁给了她丧偶的白人雇主伊莱亚斯;《掘墓人的女儿》中犹太人丽贝卡和白人加拉格尔的联姻……欧茨期望用爱来弥合种族之间的创伤,缓和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终建立一个种族融合的“乌托邦”。
三、普通公民的国家正义之梦
正义是支撑社会大厦的顶梁柱,是社会得以存在的基础。亚当·斯密认为:“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关乎每个人的利益,因为它决定了个体的生存和幸福,而正义就在于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繁荣。”[16]61-66国家正义是一种等级秩序的正义观,它要求统治者、护卫者和生产者各司其职,不相互僭越,达到国家和谐[17]382。对于美国政府的公信力和国家正义问题,欧茨并不乐观,她在日记中写道:“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的政府和官员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都不值得信赖,因为他们既不诚实也不公正,甚至常常是谎话连篇。”[18]333欧茨的小说客观披露了美国执法和司法系统正义缺失的问题:一是警察的暴力执法,二是司法机构的腐败和职权滥用。
关于警察的暴力执法,小说《他们》中有多处描述。母亲洛蕾塔卖身的钱常被街上执勤的警察搜刮一空,讽刺的是她的丈夫温德尔生前也是这样一个经常勒索、恐吓妓女的警察。朱尔斯有一次夜间在偏僻的路上行走,无辜被警察毒打一顿,辛辛苦苦赚来的一点零钱也被搜刮一空。通过对警察利用公权力实施暴力抢夺场面的描写,读者了解到美国自我标榜的所谓“自由、平等”不过是一纸谎言。本应承担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责任的警察,反而成了暴力和恐惧的根源,他们的执法是将立法的暴力与护法的暴力混淆起来。在这些警察心目中,法律对他们失去了制约,他们本身成为了法律。“这也许是国家无能的体现,也许是由于某种法律制度内在关系的缺陷所致。”[19]10警察形象如此,美国各级政府在普通百姓心目中是怎样的存在呢?温德尔妈妈对市长、州长,乃至总统的咒骂就是答案。她称他们是“杂种”,指责政府的赋税过多,认为政府所谓的“社会保险”也是一场骗局,无奈身份卑微,没有机会去当面表达自己的诉求。
小说《狐火》再现了一幅底层美国少女在社会夹缝中艰难生存的图景。“狐火帮”女孩都来自不健全的家庭,她们从小生活在环境混乱不堪的下街区,时刻面临暴力和骚扰。在学校,丽塔遭到数学老师的性骚扰却无人主持正义。萨多夫斯基为丽塔打抱不平,与人打架却被胆小怕事只想推卸责任的校长直接开除。不仅如此,校长还利用职权“滥用公共基金”。因此,在这群女孩的心目中,老师是不值得信赖的,学校不是受教育和被庇护的场所,而是一个肮脏的地方。在美国官方的宣传中,管教所是失足青少年最后的港湾。然而,“狐火帮”女孩认为在外流浪也比被送进管教所要强。管教所不是流浪少年的庇护所,而是噩梦重生之地,她们亲身体验过那里比死亡更为恐惧的生活。一旦被送进管教所,“他们会用手铐拖”,“用警棍把你打得不省人事”[20]89-92。在管教所,她们所得到的不是教育和感化,而是“极度恐惧的滋味”。管教所的警察对送进来的青少年没有丝毫的关怀和同情,他们把里面的女孩“看作某类荡妇,或是廉价的娼妓”[19]106。萨多夫斯基在红岸管教所受尽了非人的折磨,狱警“强行脱光她的衣服,用带着油污的橡皮手套的手指戳进她的身体里,戳到她身体藏得最深的最隐秘的部位”,“每次洗澡,都有女警密切监视她……她们给她全身喷上消毒剂,就像给一个动物喷洒消毒剂那样”[19]108。在管教所的警察眼中,这些少年不过是一个名字、一个编号,他们不配享有基本的人权和生命的尊严,更不用妄谈其他权利。管教所的“管教”功能完全丧失,恃强凌弱却得到强化。生性善良的萨多夫斯基为懦弱的狱友打抱不平却屡遭“模范犯人”的报复,管教所的警察不主持公道,反而助纣为虐。管教和收容制度的正义性与工作人员的非正义行径相互矛盾,让人对“公平正义”从怀疑到绝望。本应维护正义的公职人员却利用自己的权力任意践踏正义。
美国的司法系统同样乱象丛生。小说《迦太基》在揭露美伊战争真实面目的同时,特别关注了美国的司法和人权问题,批判了现代民主社会标榜的公平正义之下暗藏的司法系统的黑暗和腐败[21]199。小说中的辛顿博士,某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一直致力于揭露美国司法系统的丑闻。他在2009年曝光了纽约长岛几名家庭法官的重大受贿案。这些法官与当地的私营管教所相互勾结,将一些本该只够判缓刑的少年犯送往管教所,以此向管教所收取贿赂。这些缺少家庭温暖和社会关爱的失足青少年,本不应遭受牢狱之苦,却最终成了管教所和法官们利益交换的棋子。一边是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法官拿着受贿的钱到处享乐逍遥,一边是被无辜定罪的青少年在管教所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甚至不堪折磨自杀死亡。
更让人愤怒的是,很多时候,犯人的生死并不取决于其所犯之罪的轻重,而是“取决于陪审团或法官的判决意愿”[22]239。根据小说中辛顿博士收集的数据,在21世纪的前十年,有260多名死囚犯后来被证明是无辜的。这一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把辛顿博士的目光引向监狱死囚室。不出所料,美国监狱更是黑暗和腐败滋生的黑窝。青少年犯人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生病的犯人得不到及时救治。“如果一个终身监禁的老年犯死在监狱的医务室,那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21]214犯人中有很多残疾人,他们大多是在阿富汗或伊拉克战争中受伤的黑人“退伍老兵”。即使是在监狱,“肤色决定一切”同样是“永远不变的法则”[21]216。
对于国家正义的缺失,欧茨和普通民众一样痛心疾首。小说《中年》中,律师罗杰的女儿对他提出质问:“为什么要制定法律,爸爸?主要是为律师赚钱。不是吗?……什么是文明?文明是一种权力结构,难道不是吗?也被人们称之为霸权,用来征服老百姓和妇女。像你这样的人当然喜欢‘法律’。‘法律’永远在你们这边。”[23]19在美国,只有手握权力的人才能真正享受“公平和正义”,他们是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也是受益者。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而言,法律更多的只是监督和制约。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欧茨创作了数十部小说,这些小说都与美国各种复杂的政治权力的分配有关。对于文学艺术的政治性,欧茨是持肯定态度的,她曾在对《洛丽塔》的评论文中强调过这一点。对于一个有着“巴尔扎克”式野心的作家,欧茨的写作通常是带着某种特定的期待,她期望通过自己的写作去一点一滴地改变这个世界。欧茨是白人,也是犹太后裔;她出生底层,最终成功跻身中产阶层;她是小说家,更是公共知识分子——大学教授。欧茨认为自己肩负着知识分子的使命,她有责任有义务为无法言说者言说,为不能发声者发声。“在我看来,这世界上很多遭受苦难、心存困惑和缺乏关爱的人,他们无法诉说自己的遭遇,他们需要有人替他们发声。”[23]19欧茨对美国民生的关注,对种族平等的诉求,对政治腐败的披露包含着她对自由的追求,对生命意识的反省,对生存境况的感受,对公平正义的执着,对伦理选择的自觉和对精神家园的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