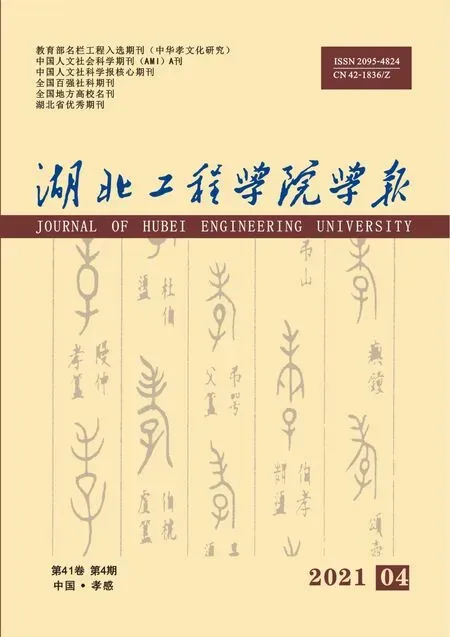《红楼梦》与《苔丝》季节叙事的意象性比较
2021-01-15李梅训
职 伟,李梅训
(1.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014; 2.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红楼梦》(下文简称《红》)作为中国古典小说集大成之作,季节叙事手法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研究《红》季节叙事的成果不少,主要论述了小说情节在四季背景下的设置方式、时空聚焦、文化意蕴等。放眼世界,一些外国经典小说中也有季节叙事的书写手法。英国十九世纪后期著名小说家托马斯·哈代的“性格与环境小说”,尤为注重四季环境的描写,其《德伯家的苔丝》(下文简称《苔》)的季节叙事堪称经典。而除偶有研究哈代小说象征手法的文章涉及到环境或季节的象征外,未见有着重论述《苔》季节叙事者。因此,不仅《苔》的季节叙事具有较大研究价值,而且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红》与《苔》季节叙事的意象性手法运用极为相似,二者季节叙事的比较也更具研究价值。通过比较二者季节叙事的异同,不仅可以看出中西方小说独特的艺术特点,而且能窥探中西文化的某些深层特征。
有些研究《红》季节叙事的文章,范围超出了季节叙事这一概念外延之所及,甚至与时空叙事、历史叙事等混为一谈。如果模糊了季节叙事与时空叙事界限的话,必然会消解季节叙事手法特有的概念内涵和艺术价值。有鉴于此,我们在比较《红》与《苔》季节叙事时,为区别其广义概念并突出“意象性”的独特内涵,即定义为“季节叙事的意象性”:每一季节本身为一意象,具有独特的寓意象征性;季节流转为一意象,暗示人事之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四季流转下的万物兴衰,与人生命运的悲欢离合有着难以言喻的必然联系,具有一定宿命论意味。而这所透露出的天命观,亦具有内在的悲剧意味,暗示了人生先验性的、不可抗拒的命运悲剧。此应是季节叙事艺术之指归。
《红》与《苔》虽是中西不同文化、不同时代之产物,季节叙事的意象性方法之运用却“异曲同工”。《苔》成书晚于《红》一百余年,首部较为系统的《红》英文摘译本于1892年开始陆续在香港出版,[1]而《苔》已于1891年发行。可知《苔》的创作并未受到《红》的影响,因而只能进行平行研究。
一、相似的爱情进程与叙事模式
《红》与《苔》主角的爱情由萌发、钟情、表白,到打击、死别的发展进程,都在鲜明的季节背景下演绎,各季节皆有独特的意象作用,二书爱情进程与季节意象之关系极为相似。
1.春季的爱情萌发与钟情。在宝玉、黛玉情感进入高潮前,暧昧的情节几乎都在春季。黛玉入贾府的首个春天,宝黛萌生爱意:“既熟惯,则更觉亲密;既亲密,则不免一时有求全之毁,不虞之隙。”(1)本文所引《红楼梦》的内容皆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的《红楼梦》,非特殊情況不再标注。其后宝玉春梦中与兼钗黛之美的兼美有巫山云雨之会。三年后的春天,宝黛始钟情。黛苏州治丧归来,二人爱慕之意加深。其后宝黛就香袋事闹矛盾,宝玉将黛所赠荷包珍戴衣内。女子赠情郎荷包、香囊等以表思慕之传统由来已久,后文潘又安与司棋亦表赠香袋私定终身,由此知宝黛感情于此春深化。次年春又集中写宝黛“意绵绵”,黛因不断试探宝玉而频生口角,反复写二人“情闷”,数次泄露春情。二十五回写黛三次情闷、三次因羞脸红。宝黛爱情在三个春天逐步深化,善用映衬手法的曹雪芹,还在宝黛钟情之春写小红、贾芸“遗帕惹相思”,以烘托宝黛爱情之萌生。
《苔》男女主角从初次邂逅萌生爱意到再次相遇而钟情,皆在春天。小说开始于英国五月的春季,克莱与苔丝一见钟情,在勃勃生机的春季萌生爱意。一面之缘后的第三年春二人再次相遇。而此期间,苔丝遭到亚雷诱骗,产一子夭亡。“转眼又是一番特别明媚的春光”,苔丝来到奶牛场,再次偶遇让她心动的克莱,二人如宝黛初会感到“倒像在那里见过一般”,爱火重燃,进而钟情。(2)本文所引《苔丝》的内容皆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英)哈代著、张谷若译的《德伯家的苔丝》,非特殊情況不再标注。
两对青年皆在生机盎然的春日情思蠢蠢、萌生爱意,并于下个春天钟情。作者既把春天作为意象以构建情节,也将人物纳入到自然环境中。他们的爱情表面为主动,实是难以抗拒的命运安排与自然之推动。
2.夏季的爱情表白与高潮。到夏天,两个爱情故事都发展到炽热化阶段,男主角都在热烈的夏季表白爱意。
宝黛夏季口角频繁,黛不断以此试探,宝玉也在劝解中越发直白地表露心迹。花朝节后的初夏,宝玉开始试探性表白:“我也和你似的独出,只怕同我的心一样”。到了三十二回宝黛关系达到高潮,宝玉情急之下对黛表白:“你放心。”从此二人心心相印。宝玉挨打后,宝玉送旧帕传情;旧丝帕的含义远比之前的荷包香囊丰富深刻得多。《诗经·野有死麕》写男女幽会,有“无感我帨兮”。“帨”训为佩巾。冯梦龙所编《山歌·素帕》:“不写情词不写诗,一方素帕寄心知。心知接了颠倒看,横也丝来竖也丝,这般心事有谁知。”[2]相赠旧帕分明表示两处相思依旧。在此躁动不安之夏,宝黛情感逐步深化,至高潮后进入相濡以沫的平静阶段。此夏作者省略了贾芸、小红的爱情进程,把贾蔷、龄官与宝黛相似的爱情高潮阶段穿插其中,侧面烘托夏季之惹人情感躁动亢奋。
《苔》主角的情感也在夏季达到高潮,克莱开始大胆追求,表白爱意。“那是六月里一个典型的夏季黄昏”,二人在交谈中彼此更加爱慕。“苔丝和克莱……正在一种不能抵抗的力量下,渐渐往一块儿相凑”,其感情就像夏天的植物不能自已地生发。苔丝虽然也像黛玉般不断试探,但仍抑制不住热烈季节推动下躁动的心之引力,“又正是夏季的时光……就是最飘忽轻渺的恋爱,也都不能不变成缠绵热烈的深情”。在自然力量下他们不得不顺应,终于克莱向苔丝表白。
曹雪芹和哈代都将爱情高潮安排在夏季。哈代每每强调自然环境对人物行为的主导作用,直接点明人物在环境影响下的心态与行为。如在克莱表白时叙述道:“这件事情里不同寻常、未容思索、完全受环境支配那种种情况,使他心神不定起来。”而《红》仅将环境作为背景,重点描写环境中人物的行为,将环境与情节融合,与人物情绪契合。叙述者忠实记录,从不介入点明环境的作用,而是通过精炼的环境描写,恰到好处地营造环境氛围。可知季节环境在两书爱情叙事中虽都承担着重要作用,但表现方式与侧重方面却不同。季节意象在《红》中起重要的烘托渲染作用,在《苔》中则起到极为关键的推动作用。
3.秋季的爱情收获与凄迷。到了收获与肃杀的秋季,两个故事进展到爱情收获的季节,随之也逐步呈现凄迷的前景。
自宝玉夏天表白后,宝黛感情在平静中深化。而到秋天黛病势加剧:“黛玉每岁至春分秋分之后,必犯嗽疾;今秋……觉得比往常又重。”黛深知己病:“我知道我这样病是不能好的了。”宝黛虽收获了爱情,却因黛加重的病情与寄人篱下的处境而预感到悲剧结局,情绪也因二人前景渺茫而愈加低落。黛诗《秋窗风雨夕》亦表现出不祥预感。
同样在《苔》中,经过了夏天的热烈追求表白后,二人在秋天收获甜蜜爱情。同时克莱因多次求婚不得而焦虑,苔丝为自己的失贞过往而忧虑,他们在幸福中深深感到不安。二人脆弱敏感的性格在秋季着重展现,为即将到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秋雨淅沥的夜晚苔丝接受克莱的求婚后,更加预感到不祥。二人感情越深,苔丝所受“疑虑、恐惧、郁闷、羞耻”的煎熬也就越痛。
在秋季,“悲凉之雾,遍被华林”[3],这两对情侣的不祥预感逐渐强烈。幸福甜蜜下忍受着当下的煎熬与对凄迷前景的恐慌。《苔》对不祥的强调更为明显,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愈加强大;而《红》则是在故事一开始就将先验的悲剧结局交代清楚,将一切发展纳入整体的宿命框架中,因此在叙述过程中避免了对天命因素的不断强调。人物在走向悲剧的过程中预感到结局,体验着悲凉的境遇。秋季里的残荷冷月、凄风苦雨等景象,及秋季自身的肃杀景况都对不祥进行着渲染。
4.冬季的爱情打击。冬天黛病情极重,未来之希望愈发渺茫;苔丝和克莱在成婚前不再是预感不祥,而是频繁遭遇不祥,直至除夕成婚之夜苔丝被抛弃。
《红》“琉璃世界白雪红梅”一回宝玉劝黛:“你瞧瞧,今年比旧年越发瘦了。”黛拭泪道:“近来我只觉心酸,眼泪却好像比旧年少了些的。”黛本为还泪而生,泪尽之日即身亡之时,其言泪少即暗示生命将尽。五十二回宝黛相顾无言的描写,不仅体现二人惺惺相惜,更传达出缠绵而又凄凉的心境。黛病危之势备添悲凉,他们视未来已渺茫无望,惟无奈静候悲惨结局。
而对苔丝二人来说冬季同样惨淡,甚至是致命打击。婚期越近,苔丝心理负担也随之加重。此冬种种不祥接踵而至:使苔丝胆战心惊的马车,不祥的鸡鸣,德伯家族的旧宅等。最终苔丝在坦言失贞后被克莱抛弃。她无法摆脱的德伯家族的幽灵与难以规避的宿命悲剧向她步步紧逼。
5.“又一春”里的爱情悲剧与希望延续。两个爱情故事都以春末女主角死去而走向悲剧终点。虽然《红》前八十回只叙述到次年秋,据众多伏笔可知黛应于次年或后年春离世。《葬花吟》“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等反复暗示“花落”之时即“人亡”之时。曹雪芹好友明义也应是读过《红》全书之人,其《题红楼梦》:“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自不知”[4]12。此外另有多处“诗谶”照应,可知“花落人亡”应是。故春末为二人死别之时。
同样,苔丝和克莱也是在春天死别。“山坡上面去年残余的荨麻,仍旧挺着灰白的秃茎,今年春天的嫩枝,都从枯老的根儿上重新发芽”,克莱抛弃苔丝一年后的春天,又归来寻找苔丝恢复旧情。苔丝在杀掉亚雷后与克莱在春天里逃亡被捕,处以绞刑。
就爱情故事发展与季节之关系而言,二书有极相似的叙事模式。人物皆在春天产生爱意,在三年后的春天继续萌发;接着在完整的一年之春夏秋冬四季里连续演绎萌发钟情、表白热恋、不祥预感、前景渺茫或悲痛分离;最终在一两年后的春末死别。就整体来看都遵循着“春夏秋冬又一春”的叙事模式。在“又一春”中,都以女主角的春天死别而走到爱情悲剧终点;春天有“复苏”意象,又都在春季通过另一位女性来延续终止的爱情。
《红》的爱情延续方式是“黛死钗嫁”。黛本还泪而生,在修完“木石前盟”后泪尽而亡;宝玉到成婚年龄自与宝钗始续“金玉良缘”。宝玉在五十八回所赞许续弦之论,即为娶钗作铺垫。陈蜕《忆梦楼石头记泛论》:“蕊官焚奠药官,芳官为道其故,并述藕官相继后诸人戏语,喻黛玉死后,钗、玉相爱时期,不忘黛玉。”[4]276宝玉爱黛亦爱宝钗。其对金玉之说多有憧憬,梦里情人兼美“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宝与黛木石前盟已尽,必与钗成金玉姻缘。
而苔丝杀死亚雷后料到不久将与克莱死别,便将妹妹许托克莱:“你不久就要看不见我啦,我只盼望,你没有我那一天,你能娶她。”苔丝死后克莱与苔丝之妹携手相爱:“这一对人里面,一个是安玑·克莱,另一个是克莱的小姨子丽莎·露;只见她身材颀长,像正要开放的花蕾……活活是苔丝的化身。”其爱情以“姐死妹代”的方式延续。
在季节叙事的意象性手法营构下,两对恋人在春天萌发爱意,在夏天热烈相爱,在秋天收获爱情的同时深感前景之凄迷,在冬天意识到或者接受了悲剧的结局。他们的情感与行动为季节环境所左右,关系随季节之流转而进展。季节环境与天命之间所存在的不可言辨之联系,共同形成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人物命运为其掌控。曹雪芹和哈代又都自觉地将死别安排在春末,一是借助春末百花凋零意象比喻佳人命薄,一是化用春天新生意象以象征爱情重生之希望。故有“黛死钗嫁”和“姐死妹继”的方式使爱情延续,喻示爱情如自然万物之兴衰。
二、相似的诗化特征和悲剧成因
二书在季节叙事方面,除爱情进程与季节流转关系紧密外,还有相似的诗化特征。“季节叙事具有鲜明的意象化特点和强烈的抒情色彩”[5],季节叙事的意象性更突出抒情性和寓意性,也天然地具备诗性特征。季节自然流转所引发的兴衰际遇、离合悲欢,及其所喻示的不可抗拒之神秘力量推动下爱情走向悲剧的宿命思想,无不增强了小说诗性内涵。
1.相似的诗化特征。曹雪芹与哈代在叙述中,强调季节景物的意象性书写,营造出了浓厚的诗意氛围。季节流转所延伸之家族兴衰、历史更替,发人兴叹。加之作者皆诗人,天性敏觉细腻,其季节书写诗意盎然。所引诗文皆具寓意性,或暗示故事发展,或象征人物命运。
季节叙事的诗化特征,主要表现为大量自然意象的书写,及用诗化的语言写景抒情。《红》四时节气等典型意象之描写皆细致生动。七十八回宝玉“因看着那院中的香藤异蔓,仍是翠翠青青,忽比昨日好似改作凄凉了一般,更又添了伤感”,宝玉眼中的景色描写,将其失落感伤心境完美展现,物是人非之凄凉氛围立现。《苔》之凄风浓雾、寄生草等大量季节性意象以苔丝不同处境而烘衬其心境。较大的意象密度,增强了小说的诗意性。“风力非常锐厉,连墙上那些长春藤的叶子,都叫风吹得变成了枯萎、灰白,他们互相扑打,老不停止”,诗化语言既写出棱窟槐恶劣的自然环境,也暗示苔丝生活处境之悲惨;长春藤叶象征其飘零凄苦命运,发人感怀。
其次是频繁引用、化用诗歌,增强诗意性。《红》中相比于“留得残荷听雨声”[6]539等引诗,更多的是叙述者和人物所作的大量诗词提升了作品的诗意,如黛玉葬花等情节无不“诗中有诗”。还有较多情节化用古诗意境,如史湘云醉眠芍药茵,便是化自唐诗“醉眠芳树下,半被落花埋”[7]等。《苔》也常引用民歌、诗歌,化用《圣经》歌谣等。如“一切有生之物,都有一种‘寻求快乐的本性’”,[8]228便是引自英国诗人勃朗宁的诗剧《帕拉赛勒塞斯》第一幕;苔丝回答克莱时所说“同时好像有好多好多的明天,通统排成一行,站在你面前,头一个顶大,顶清楚,越站在后面的就越小,但是它们却好像一概都是很凶恶、很残酷的”,即是对莎士比亚《麦克白》第五幕“明天,明天,再一个明天,一天接着一天地蹑步前进,直到最后一秒钟的时间”的化用。
2.相似的悲凉情调与悲剧成因。两对情侣在不可抗拒的命运面前都只能任由摆布。作者的悲观情绪和宿命论观念,使故事笼罩在悲凉的氛围中,字里行间流露出伤感情调。
《红》的还泪神话、《好了歌》等开宗明义地标示了作品的悲观色彩与宿命论思想。如黛所掣花签“莫怨东风当自嗟”[6]872,而原诗上句为“红颜胜人多薄命”[9],喻示黛玉命薄;书中所提及的《南柯梦》等曲目唱词,甚至寺庙的名字铁槛寺等无不有佛家思想之由来一梦、万事皆空的寓示性。
《苔》反复出现的马车意象及传说,使作品笼罩着神秘悲凉的气氛。刚开篇苔丝和弟弟的交谈即表达了消极的世界观:世界是“疤拉流星的”,“有那么些没有毛病的世界,咱们可偏偏没投胎托生在那样的世界上,真倒霉”。作者在第五版序言中引用《李尔王》:“神们看待我们,就好像顽童看待苍蝇;他们为自己开心,便不惜要我们的命。”[8]6体现了作者悲观主义思想和对上帝意志的质疑。还有对《圣经》的频繁引用、化用,如“还有一个令人难受的荆棘之冠,戴在她的头上呢”[8]225。“荆棘之冠”引自《新约·马太福音》耶稣被戴上荆棘冠冕为巡兵所嘲弄。苔丝的纯洁美貌是上天赋予的“荆棘之冠”,隐喻其被戏弄摆布的苦难命运。
作者的悲观主义情绪主导下营造出的悲凉情调,正如韩愈《荆潭唱和诗序》所言:“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10]因之增强了作品的诗意内涵。亚里士多德《诗学》言悲剧能够“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11]。宿命论思想下的悲剧演绎,将故事置于更广阔的艺术空间和更深刻的思想境地,其所呈现的悲剧意味也更动人。
三、季节叙事的意象性之差异性
《红》与《苔》在季节叙事意象性的书写方面虽都具有相似的爱情叙事模式和诗化特征;但二书毕竟是中西不同文化下不同时代的产物,在关注艺术上的相似性时,还应分析其内在本质差异。
1.季节叙事的意象性所承载的内涵不同。二书季节叙事都演绎了季节叙事下相似的爱情进程,恰如《苔》所引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中的“光景变迁,爱情也随着变迁”,季节流转的意象也喻示人物的悲欢际遇。季节流转意象下的人事兴衰也内含了悲观的宿命论。不同的是《红》的爱情悲剧是先验的,在爱情开始前就已注定了结局,天命使其历练红尘离合悲欢,以体悟世间万般诸色皆虚幻。《苔》的爱情、命运悲剧则是天命的肆意戏弄,也是德伯家族前世罪恶在苔丝身上之果报。“当初德北家是郡中望族的时候,一定有过许多次,曾把无地可耕的人,毫不客气地驱逐。不想这种情况,现在轮到他们自家的后人身上了”。家族罪恶竟让苔丝承担惩戒。
此外,二书还体现了相似的人生顺逆、家族兴衰之转换的“循环论”思想。《红》甄士隐由兴而衰,贾雨村由衰而兴;贾府由兴而衰;以贾府之功勋暗写朝代更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蕴含的是个人际遇、家族兴衰及大背景下的历史兴替。此外,还有色空的宇宙时空转变(虚实时空转换)。《苔》中真德伯家族由当年的赫赫大族沦落到家破人亡,成为德北;而新兴的资本家司托家却成了显耀一时的伪德伯。也如书中所言“本来天地之间,盛衰兴替,时起时落,一切全都一样”。《好了歌》言“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苔》约翰·德北的墓碑上刻着“一时之雄,而今安在”,皆在表达兴衰之叹。不同的是二书恰从正反两面书写家族兴衰:《红》以兴写衰,贾府繁华却见衰败之势;而《苔》是以衰写兴,描述德伯家族衰败状态,如巨大的陵墓、散落在各处的房子地产,以追溯古之繁盛。相比于《苔》季节叙事意象性所喻示的人生际遇、爱情悲欢、家族兴衰的内蕴外,《红》还有历史兴替与宗教思想之虚实色空的无常变化,内蕴更为丰富。
2.季节叙事的意象性体现了不同的悲剧观。《红》描写了宝黛由两小无猜的童年玩伴到青年的相爱缠绵,展现的是成长型、日久生情式的爱情,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理想爱情模式。在书写其爱情悲剧的同时,感叹青春流逝与成长苦闷。宝黛在红尘历练中体验了色空无常,以实现自身之解脱。《苔》描写男女青年在花季邂逅钟情,在爱情进程里演绎爱恨情仇、离合悲欢,生命因爱而荣枯。前者爱情在对命运、礼教的顺应中走向悲剧,后者则是在抗争中走向悲剧。前者哀而不伤、悲凉凄美;后者令人惊讶震撼,唤人反思抗争。前者的悲剧情调似在张爱玲小说中延续发展,凄清优美中透露出淡淡苍凉;鲁迅小说则似与后者相近,在悲凉壮美中激人奋起以反抗。
所以如此,是不同文化影响的结果。《红》哀而不伤的悲剧情调,深受“温柔敦厚”的诗学传统影响,无论《诗经》中的《氓》,还是《孔雀东南飞》的爱情悲剧,都是以较为平和的语气叙述主人公无可奈何的悲苦心境;梁祝等传统经典爱情悲剧中的人物,一般也未与外界进行抗争,至多以自身的毁灭以示愤懑。
不同于《红》宝黛之性格天生而就,《苔》作为“环境与性格小说”的代表,苔丝和克莱的性格随着环境与命运的变化而转变。哈代深受古希腊《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王》《美狄亚》等命运悲剧和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奥赛罗》等性格悲剧影响,人物在感知到悲剧命运降临时,积极抗争,直至以复仇与毁灭的方式表达对悲剧命运的强烈控诉,表现出英勇不屈的精神。哈代也深受近世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和雷奥巴狄的影响。其实哈代也并非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他在承认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的同时,并未使人物放弃抗争,而是在抗争与毁灭中实现悲剧的崇高效果。
此外,与《红》所阐发的佛家色空思想相似的是,《苔》也提到了基督教中万物虚空的思想:“苔丝……就说,‘凡事都是空虚’……如果凡事只是空虚,那谁还介意呢?唉,一切比空虚还坏——诸如不平、惩罚、苛刻、死亡。”[8]410“凡事都是空虚”引自《旧约·传道书》第一章:“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但作者在引出万物虚空后又将该思想推翻,认为一切并非虚空,反而比虚空更糟糕。哈代在1876年7月的日记里早已表达过同样的思想:“不过要是一切只是空虚而已,那谁还介意呢?唉,世界一切,往往比空虚还糟,往往是痛苦、黑暗和死亡。”可知其并不认可虚空理论,他眼中的世界、人生是彻底糟糕的悲剧。克莱抛弃苔丝时,作者将勃朗宁诗剧《琵帕走过去》中的“上帝身居九重天,世间万事尽完善”一句,化用为“上帝不在九重天,世间无一事完善”[8]377,表现其对上帝意志与不公命运的控诉。不同的是曹雪芹在看到糟糕的“痛苦、黑暗和死亡”后,精神从中超脱出来,进而觉悟佛家“诸色皆空”、人世“如梦幻泡影”的经义。二人思想之指归,一在入世,一在出世。
综上,在宏观比较文学视野下,以微观比较文学的研究形式,采取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对这中英两部代表性的经典著作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发现,《红楼梦》和《德伯家的苔丝》在季节叙事的意象性方面确实存在着较大相似之处,曹雪芹和哈代都自觉地以季节叙事的方式结构作品。季节的自然流转所引发的兴衰际遇、离合悲欢,及其所喻示的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推动下爱情故事走向悲剧的宿命论,也增强了小说的诗性内涵。由于时代和文化背景不同,季节叙事的意象性也承载着不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作者不同的悲剧观。
进而可知,在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作家思想观念和艺术追求虽不同,却非完全对峙,中西文化在深、浅层次里皆有相似性,以小说为代表的中西方文学艺术之发展规律亦有一定相似处,尤其表现为作家在创作方法的探寻与实验方面的部分趋同性。我们从中西文学的相似性方面,可以看到世界文学经典中所呈现出的一些共同的艺术发展规律;而通过进一步探究相似的表面之下差异的本质性,更能深刻地认识到不同文化之差异。认识文化差异性的目的,非是比较优劣,而是以宏观的视野,更全面客观地认识本民族文化的特性,增进对自我文化的认同,并促进对其他民族文化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