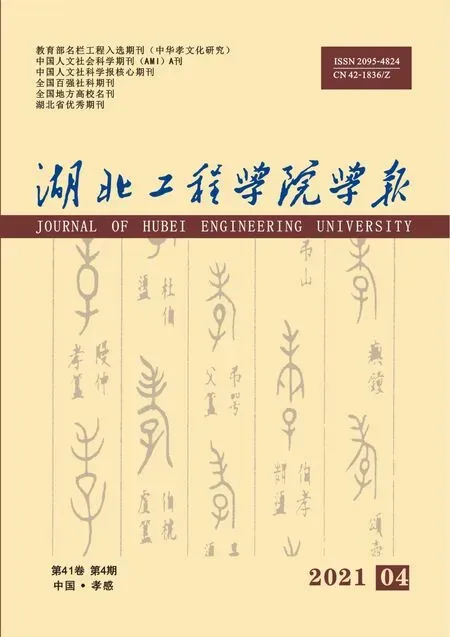试谈《水浒传》一百零八人的身份问题
2021-01-15蔺九章
蔺九章
(邯郸学院 文史学院,河北 邯郸 056005)
“判断一部作品写的是什么?究竟应该以什么为根据?”学者沈伯俊的观点当颇具代表性,他在提出这个问题后,说道:“是根据它的题材,还是根据作品所要宣扬的主题,抑或是根据作者在写人叙事中不时流露出的思想意识?很明显,主要根据作品的题材。”接着提出其中心论点:“判断《水浒》是否写的农民起义,也主要应该以它的题材为依据。”并进而得出水泊梁山“基本队伍显然来自农民”的结论。[1]应该说,根据题材等确定小说写的是什么,不失为一种路数,但不一定适合所有小说,比如《水浒传》。因为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和《水浒传》中所描写的梁山聚义,即历史的真实和小说的虚构,不完全是一回事。而且,剖析一部小说写的是什么,最绕不开的是它所塑造的人物。因为人物是小说的三大要素之一,甚至可以说是第一要素。分析小说撇开人物形象而谈论其他,并进而判断一部作品写的是什么,无异于隔靴搔痒,甚而缘木求鱼。因为分析人物形象才是读懂小说的基点和关键。
翻检有关《水浒》的论著,关注其题材、解读其主题思想的倒不少,但专门对其人物进行身份界定分析的几乎没有(本文主要讨论一百零八人,不论梁山上成千上万的喽啰),大多是在论述题材或主题思想时含糊笼统一带而过,且往往将水浒的“题材说”“主题说”与一百零八人的“身份说”相提并论。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从中洞鉴出他们对其身份的认知。关于一百零八人的身份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主流观点主要有两种,我们以发行量最大、综合权威性最高的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材来看,一是“农民说”,其观点主要出自游国恩以及袁行霈等分别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二是“好汉说”,出自最近面世的袁世硕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这两种主流观点和未进入主流的“市民说”“游民说”和“流氓说”等,虽各有其一套说辞,但都未对其身份进行认真界定,往往将出身、职业、成分与身份混为一谈。如此,难免得出一些似是而非、自相矛盾的结论。
一、水浒一百零八人的身份界定及其特点
身份不等同于出身,出身是指本人走向社会、取得独立经济地位时由家庭经济情况所决定的身份,主要由父辈生活的环境和从事的职业来定,是一种和个人能力无关的先天因素,如李逵、宋江以及史进、吴用、解氏兄弟、阮氏三雄等都生在农村(林、牧、渔都算在农业范畴),出身都是农民(或地主)。身份亦不等同于职业,职业是个人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营生,好多人的一生包括水浒一百零八人大都有过许多职业,像鲁智深,当过军人,做过僧人,还落过草,受招安后又为朝廷东征西讨,最后又遁入禅林,若将身份混同于职业,鲁智深的身份判定就会比较麻烦。身份也不等同于成分,成分是个人进入职场前的主要经历,如宋江、吴用、萧让、蒋敬、裴宣、金大坚等年少时应该都读过书,其成分当是书生,鲁达、武松等众多人物的成分则不易看出,较难确定。身份亦作身分,指人在社会上、法律上的地位或受人尊重的地位。可见,身份与出身、职业以至成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有着本质的不同。
简单分析可知,水浒人物的身份至少当具三个特性:一是普适性,或曰公认性。其定性最好能得到社会各界人士,即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草根细民、偏好阳春白雪的抑或下里巴人,的普遍认可。那么带有褒义的英雄、好汉、豪杰、豪侠,带有贬义的流氓、土匪、强盗、恶棍等称谓显然难于符合这个标准,比如武松,若说他是英雄豪杰,西门庆、潘金莲以及蔡京、高俅必定举双手反对,因为在他们看来,武松是凶犯,是暴徒,是破坏社会稳定的恐怖分子,故确定身份的词,最好是中性的。二是准确性。判断一百零八人的身份,不能纯看出身和成分,也不能单看职业,即既要看其外在的呈现,更要剖析其内在的能为、胆气等。故不能简单地说宋江是唯唯诺诺的胥吏、卢俊义是唯利是图的商人、吴用是迂腐刻板的塾师,更不能笼统地把他们都称之为农民、或市民、或流民、或游民、或流氓无赖。而要全面兼顾,综合考量,否则,就难免失之于偏颇或流于主观随意。三是概括性。一百零八人不仅个体的行为和经历丰富、复杂,而且群体的出身、职业亦是五花八门,“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第七十一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宋公明慷慨话宿愿”),所以把他们武断地都归入某一类别难度很大,这就需要在抽象的基础上舍弃次要的、非本质的属性,把主要的、本质的属性抽取出来,进而通过概括提炼出一百零八人的整体属性。德国哲学家赖欣巴哈曾说:发现的艺术就是正确概括的艺术。说明正确概括是多么的重要。
故笔者认为,一百零八人的身份不是单一的农民,亦不是纯粹的市民,也不尽然都是游民或流民,更不可能都是什么流氓。他们是一群武士,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武士。
二、“武士说”的提出及理由
“武士说”的提出,既不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也不是因为个人的好恶和匠心独创,而是源于小说自身。《水浒传》“引首”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
这仁宗,乃是上界赤脚大仙,降生之时,昼夜啼哭不止。朝廷出给黄榜,召人医治。感动天庭,差遣太白金星下界,化作一老叟,前来揭了黄榜:“能止太子啼哭。”看榜官员引至殿下,朝见真宗天子。圣旨教进内苑,看视太子。那老叟直至宫中,抱着太子,耳边低低说了八个字,太子便不啼哭。那老叟不言姓名,只见化一阵清风而去。耳边道八个甚字?道是“文有文曲,武有武曲。”端的是玉帝差遣紫微宫中两座星辰下来,辅佐这朝天子。文曲星乃是南衙开封府主龙图阁大学士包拯,武曲星乃是征西夏国大元帅狄青。这两个贤臣,出来辅佐。
这段话应当表达了作者几个重要的观点:
一是治国安邦,人才为要。
二是人才分为两大类:一文一武。文臣要像包拯,能治国理政;武将要像狄青,能定国安邦。“引首”结尾有一首诗,其尾联“细推治乱兴亡数,尽属阴阳造化功”,此间的“阴阳”二字,按照作者的观点应该是文属阴,武属阳,意指文、武两类人才。当然,这种分法也符合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人才观念,中国古代就专业角度讲,尤重两类人才,一是人文(政治)型人才,一是军事型人才,即文和武。
三是要国强民富,这一文一武两类人才都要重视,即“重文重武”是正确的。
可北宋在历史上却奉行“崇文抑武”的国策,对武士普遍猜忌并实行严格的管控、防范和打压,比如他们就曾迫害死了为人缜密寡言、位居高位却出身行伍的狄青。小说中则虚构了一百零八人,这些人被朝廷和文官集团视为洪水猛兽和乱世魔王,积年累月被锁镇在江西信州的龙虎山,恰如活在地狱一般。宋廷就是要让他们成为人下人,低眉顺眼,永世不得翻身,以确保赵宋王朝的长治久安。这些人的身份和狄青一样,都是武士。何谓“武士”,他们又有哪些特点呢?
查阅词典,武士大约有两种含义:一是古代守卫宫廷的士兵;二是有勇力的人。当然,武士在不同的国度和时代可以有若干意思:一是中世纪欧洲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骑士;二是古代日本的一种特殊的社会阶级;三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列国中的特殊阶层;四是中国后世泛指习武练兵之人。可见在古代,欧洲有骑士,日本有武士,那中国有什么呢?应当说,中国没有所谓的武士阶级,也没有类似于骑士的这样一个阶层,但却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基本散落在民间和社会底层,拥有某些共同的特质,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因某种机缘境遇或使命而聚在一起,我们可称其为“武士”(此“武士”不同于日本作为阶级而存在的武士)。
故一般来讲,“武”与军事、技击或行事勇敢、威猛有关;“武士”则泛指孔武善战、英勇无畏之人,这在中国古代,尤其到春秋战国以后更是如此。具体到《水浒传》中,哪些人属于武士范畴呢?单凭被天师锁镇的情况看,一百零八人,即被时人视作“魔王”的人,都是武士。这在“崇文抑武”的宋朝是容易理解的。
观照《水浒》中的一百零八人,武士大略具备以下五种元素:
武器。武器或曰兵器,是武士的生命,常随身携带视若珍宝。梁山好汉都有武器,如林冲的丈八蛇矛、秦明的狼牙棒等,连“智多星”吴用都有。吴用一出场虽似秀才打扮,生得眉目清秀,面白须长,却手提铜链。铜链和火眼狻猊邓飞使用的铁链一样,都是兵器。宋江使用的兵器比较杂,早年“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杀惜时用的压衣刀,杀人后逃命时拿的是一把朴刀,后来腰上常悬一把“锟铻剑”,可见他枪棒刀剑都会用;安道全在小说中好似没怎么提他的武功,但他至少是有兵器的,那就是银针和手术刀。小说第六十五回“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跳水上报冤”写道:“肘后良方有百篇,金针玉刃得师传。”堪称内外科的全才专家,尤其是他使用的手术刀是非常厉害的,刀刀惊魂,招招要命。与之相反,文官们都不喜欢舞枪弄棒,比如高太尉莫说平时,即使领兵出征也不带兵器,他带的都是美女,“天子降诏,催促起军,高俅先发御营军马出城,又选教坊司歌儿舞女三十余人,随军消遣。”(第七十八回“十节度议取梁山泊 宋公明一败高太尉”)
武艺。梁山好汉鲁智深、花荣哪一个不是绝艺在身,武功高强。吴用虽为书生,但他使用的兵器——两条铜链却很不一般,属于奇门兵器。这种软兵器非常难学,能使用这种武器的人,应该不是平庸之辈。小说写他出场,正逢赤发鬼刘唐和插翅虎雷横大战,吴用“便把铜链就中一隔。两个都收住了朴刀”,没两下子敢往正在打斗的虎狼中间插一杠子吗?宋江也会武艺,他还收了两个徒弟——孔明、孔亮。之所以很少见其出手,大概是“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吧。高俅倒是出过手,被俘梁山后自吹自擂,“我自小学得一身相扑,天下无对”,结果被燕青“只一交,颠翻在地褥上,做一块半晌挣不起”。有人认为高太尉当时喝醉了,不在状态。那武松醉酒打猛虎、醉打蒋门神又如何解释?当然,并不全然否定高俅有一定拳脚基础,只不过在武士面前稀松平常罢了。
武略。指军事谋略。若对宋江、吴用的武艺尚有质疑的话,那么对其军事谋略就不得不服气了。因为他们一路走来,可是久经沙场和战阵,斗官军,打田虎、平王庆、征方腊,基本做到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似高太尉之流,只会大言不惭,“非是高俅夸口,若还太师肯保高俅领兵亲去那里征讨,一鼓可平”,临阵却一筹莫展,黔驴技穷,只能一败再败,狼狈不堪。
武胆。指行武的胆力和气魄。一百零八人的胆气自不必说,他们成瓮喝酒,大块吃肉,风高放火,月黑杀人,打家劫舍,冲州撞府,武士的风范不容置疑。再看童枢密、高太尉之流,他们在官场上趾高气扬,耀武扬威,但在围剿梁山的战场上却很不给力,不是魂飞魄散,心胆俱落,就是六神无主,身无所措;在对外御侮上,更是采取鸵鸟政策,逃避现实,软弱无力,敷衍塞责,甚至弄虚作假,“话说当年有大辽国王,起兵前来侵占山后九州边界。兵四路而入,劫掳山东、山西,抢掠河南、河北。各处州县,申达表文,奏请朝廷求救,先经枢密院,然后得到御前。枢密童贯,同太师蔡京,太尉高俅、杨戬商议,纳下表章不奏。只是行移临近州府,催攒各处,径调军马,前去策应。正如担雪填井一般”(第八十三回“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陈桥驿滴泪斩小卒”),把大宋国威丢得一干二净。
武德。也称“武道”。华夏民族历来祟礼敬德,行医的讲求“医德”,从教的讲求“师德”,练武的则讲求“武德”。“武德”一词,早在《左传》中已有记载,楚庄王言:“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自古以来,一直把有无优秀的品德作为评价武林人物的重要标准。为了培养过硬的武德,好多门派制定若干条律来约束自己的门徒,如少林有“练功十忌”:“一忌荒惰,二忌矜夸,三忌躁急,四忌太过,五忌酒色,六忌狂妄,七忌讼棍,八忌假正,九忌轻师,十忌欺小。”《水浒》中最重要的“武德”,则是忌好色与尚义气。
忌好色。并非不色,而是指不过分迷恋、沉溺于男女情事。一百零八人中与“色”有缘即有过女人的亦有人在,如林冲、宋江、杨雄、卢俊义等,好色者如王英者则屈指可数。“就大体而言,梁山好汉大都是单身,至于已婚英雄,他们婚姻生活方面的事书中很少提及,除非他们因妻子遇到什么麻烦。”[2]88他们对女性是有排斥的,但并非“采取敌视的态度”[3],除非这些女人对不住武士在先。“对好汉最重要的考验是他必须不好色。”[2]88比如生铁佛崔道成、飞天夜叉丘小乙、飞天蜈蚣王道人等,他们的武艺和勇力远胜于一般人,就因有贪淫好色而不择手段之类的恶德恶行,被剔除在了武士行列之外。
与忌好色相比,梁山好汉更崇尚义气。说到一百零八人的义气,人们自然会想到义盖云天的九纹龙、侠气冲天的花和尚、扶危济困的及时雨、坚守人伦的武行者、为朋友置自己生死于度外的黑旋风、为挚交两肋插刀的拼命三郎等。与之相对的,是《水浒》里的官僚,如蔡京、高俅等,他们做事只讲私利,不讲义气,只顾个人欲求,不管他人感受。所以,李悔吾早就指出:“《水浒》的英雄们最讲义气……上自当朝皇帝,下至污吏贪官、土豪恶霸是最不义者。”[4]当然,《水浒传》里实际写的最不讲义气的人是蔡京和高俅的顶头上司——宋徽宗,只不过作者基于各种考虑,“没有公开给他栽上‘昏君’恶名”[5],对其薄情寡义也未作过多明显的交待。但若思忖一番不难发现,他穷奢极欲、劳民伤财征发花石纲、营建艮岳是不义;不理朝政偷挖暗道招妓嫖娼是不义;伙同手下对梁山好汉下阴招,卸磨杀驴是不义……与蔡京一伙相比有过之无不及。还有的在小说中虽未写,却清楚地写在史书中,亦可作为参照。如在处理辽国、金国等外部事务,臣僚、百姓等内部事务乃至儿子宋钦宗等家庭事务上都不讲义气,表现出极端自私的品性特征。徽、钦二帝最后被俘至北国,金人封其为昏德公和重昏侯,可谓知人矣。
需说明的是,小说中的蒋门神、栾廷玉、史文恭等也都是武林中人,甚至功夫精湛,神勇过人,却被摒于武士行列之外,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缺“义”。他们依附于官僚集团及其衍生物(祝家庄祝朝奉的“朝奉”是官名,光听他庄上的店小二一句话:“只我店里不比别处客店,拿你到庄上,便做梁山泊贼寇解了去”,即可知祝家庄有多么阴毒,显然是官僚恶霸;曾头市“曾家五虎”霸占金毛犬段景住的马匹,便属黑帮流氓行径),不辨香臭,为虎作伥,损德丧义,失掉了武士应有的道义担当和人格魅力。所以,他们,当然更包括其主子祝家三杰、曾家五虎都不够武士的标准;《水浒》里造反的王庆、田虎、方腊等人尽管也是武林中的不凡之辈,但都有篡弑之心,“终究够不上‘侠义’之士,走不上‘忠义’之路,只能是一个‘乱寇’渠魁”[6]。作者甚而将仗义疏财、刚正耿直却有叛逆倾向的晁盖都摒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其正统思想可见一斑。由“义”而放大到“忠”,也是武德的应有之义。
总的说来,身为武士的一百零八人,他们义薄云天,尽忠报国,彰显的是一种阳刚之气,男儿本色。当然,小说所描写的一百零八人由于家庭背景、生活经历、性格特点等的不同,个体差异也很大,即他们并非完人,并非个个无可挑剔,事事值得颂扬,如此眼光看他们也不合宜。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武士嘛,自有武士的特点。而且,作者在小说中对武士的不足并非未置一词,特别是对个别人滥杀无辜等行为是持反对立场的,读者只要留意是会察觉到的。
武器、武艺、武略、武胆、武德,诸多元素备于一身,称作武士当实至名归。但也要防止机械套用,力避简单化,因为具体人物的身份界定还需具体分析。虽然这五种元素对武士的特点做了外在、内在的观照,但这似乎还不足以凸显武士的特质,因为有时文字的繁富,反而不如简洁来得明晰干脆。我们可把五大元素熔铸为一个词——血性,武士最本真、最灵魂的属性当是血性。这可能也是潜藏于《水浒传》中的一个深层话题。
何谓血性?血性最基本的属性当是勇气。“夫战,勇气也。”(《左传·曹刿论战》)打仗,靠的什么?靠的就是敢打敢拼、一往无前的冲劲,靠的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失却血性,打仗必将溃不成军,一败涂地。不论在冷兵器年代,还是热兵器时期,这都当是一条铁律。血性不是欺软怕硬,不是遇险而退,不是懦弱逃避,逆来顺受;血性,更不是嗜杀,不是血腥,不是丧失理智的残暴。血性,就更高层面来讲,当是正气在胸,爱憎分明,扶危济困,慷慨仗义;是见义勇为,铁肩担责,除恶向善,舍我其谁;是面对奸邪,敢于亮剑,敢于刺刀见红,与凶恶残暴势力血战到底。孟子所说的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庶几与血性相似。
血性来自哪里?《水浒传》的作者应当很清楚,一个重要来源是武士。应该说,武士天然就是军人,但军人天然不一定是武士。因为军人可以个个手握兵器,可并非人人都有武艺、武略、武胆和武德,特别是有血性。尽管一百零八人起初不少人并未穿过军装,但其身上充沛的血性却昭示着他们是天然的军人。正如明朝“五湖老人”在其《忠义水浒全传序》里所言:“兹余于梁山公明等,不胜神往其血性,总血性发忠义事,而其人足不朽”[7],认为宋江等一百零八人是血性之人,血性之人方能成就忠义之事,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如此才能成为不朽之人。若一个国家没有一群血性弥满的武士,那整个民族的精神便也无从谈起。作者通晓古今,知悉辽、金等军队的强悍和宋兵的孱弱,痛定思痛,深感赵宋王朝在“崇文抑武”国策的浸染下,整个国家在暖风熏人的大气候、小环境中,臣民醉生梦死,疲软不振,最终折戟沉沙,永劫沉沦。北宋实行这一国策,产生了一个连制定者都始料未及的结果,即国家政权虽未被“家奴”篡夺,却为“友邦”劫掠。同样的江山易主,鼎革倾覆,二者所产生的悲剧性结局对赵氏家族乃至国人来说又有何异呢?作者肯定注意到,赵宋之前,军人拥兵自重,骄横跋扈,篡政夺权之事多发,此时血性总体上说来自本土;赵宋始,“崇文抑武”的国策将武士打入十八层地狱,阉割了国人的血性,本土自产自生血性的能量大大减弱,如此招致的后果难免很悲催,那就是没了血性的民族屡屡被血性十足的民族所侮所灭。正如有人所说:“今天你失却了血性,明天你必将招来血腥。”
笔者曾撰文讨论《水浒传》的主题问题,认为该书是“对北宋‘崇文抑武’国策的形象否定”说[8]。就表层而言,似有一定道理,但若进一步探究引申,《水浒传》的主题当为“血性”说。
关于血性,可以引发许多话题:血性该不该有?血性从何而来?血性如何保有?这些问题不知是否曾经翻腾于《水浒传》作者的脑海,但却是笔者阅读《水浒传》后的感受和体悟。笔者觉得作者不仅想了这些问题,而且想得很深,这可能正是《水浒传》塑造这一百零八人的真正命意所在吧。
三、与“武士”相对的“文士”及其在《水浒传》中的呈现
世间的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有“武”就有“文”,有“武士”便会有“文士”。什么是“文”和“文士”,只能说在中国古代,“文”和“文士”与书、读书、读书人有关,但要说清其中任何一个真正的内涵恐怕要废许多笔墨,而且啰唆半天也较难说清。既然如此,最好选择避开,我们还是揣测一下《水浒传》的作者对“文士”的理解吧。
笔者以为,在《水浒传》中,文士更倾向于指称那些跻身仕途的读书人,即那些读书人中的精英分子——由知识精英而权力精英。小说中没有只字描写书生“头悬梁,锥刺股”的苦读,也没有让他们整天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豪言壮语挂在嘴上,而是直接呈现他们在官场上多姿多彩的表演。毕竟加官进禄的文人多活跃于政治舞台,特别在科举制盛行并推行“崇文抑武”国策的北宋。为了表述顺口,文中用“文人”一词来代替“文官”。
杨三可表示,“瓮福做新品,关注的是内涵,是科技含量,必须服务于增产增收、减施增效、绿色环保,为农民创造价值。”他对在场的瓮福农资公司员工提出要求:“目前,集团在新型肥料研发、铁腕提质、服务提升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新突破,农资公司必须抓好试验示范田建设,针对不同的土壤、不同的作物,广泛开展试验示范,用实实在在的效果说话,同时也要配套好农化服务、农民培训等服务,打造幸福农业服务商。”
《水浒传》上的“文人”首先指文学之士。
小说第十九回“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林冲大骂(王伦)道:‘量你是个落第穷儒,胸中又没文学,怎做得山寨之主!’”这里的“文学”,当指经学。这和“孔门四科”以及《世说新语》里三十六门之一的“文学”意思一致,而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大异其趣。“经学”即指科举考试,说王伦“胸中又没文学”是说他是个落第秀才,是科考的失败者。原来到了北宋,王安石等人认为诗词歌赋华而不实,废除了唐代诗赋取士的旧制, 实行“经义取士”,可以说对科举考试作了革命性的变革。
“文学之士”即指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体制内的官员。小说中的这类官员,在朝廷的,主要有宰相赵哲、参政文彦博、参知政事范仲淹、太尉洪信、太师蔡京、中书梁世杰(后外放北京大名府)、殿前太尉宿元景等;在州府的,主要有东京开封府滕府尹、东平府尹陈文昭、兵马都监张蒙方、江州知府蔡德章、通判黄文炳、青州知府慕容彦达、东平府太守程万里、高唐州知府高廉、华州贺太守等;在县级或以下的,有郓城知县时文彬、清风寨知寨刘高等。这些官员应该都是“文学”之士或至少沾边的:历史上的蔡京、文彦博、范仲淹均是进士及第,是众所周知的;有的小说上已然点明他的文官身份,如黄文炳、刘高;有的虽未点明但看小说的描写即可看出他的文官身份,如兵马都监张蒙方,他是被武松不费吹灰之力杀死的;有的不用脑子想也知道他不是武士出身,如蔡京之子蔡德章、高俅堂弟高廉以及徽宗和蔡京们的亲眷、门生、故吏,如慕容知府、贺太守、程太守,他们即使不是科举出身,也绝不是尚武血性之人,因为该朝的国策是“崇文抑武”。
下面,我们解剖一下第一个隆重出场的洪太尉这个品阶甚高的武官是不是文人出身。
首先他身体虚弱。洪太尉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宣请嗣汉天师张真人,须表志诚之心,步行上山礼拜,叩请天师。你看他:
这洪太尉独自一个,行了一回,盘坡转径,揽葛攀藤。约莫走过了数个山头,三二里多路,看看脚酸腿软,正走不动,口里不说,肚里踌躇,心中想道:“我是朝廷贵官,在京师时重拥而卧,列鼎而食,尚兀自倦怠,何曾穿草鞋,走这般山路!知他天师在哪里?却教下官受这般苦!”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掇着肩气喘。(《水浒传》第一回)
如此走两步就腿脚酸软、上气不接下气的人,岂非二八娇娘,“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这是怎么造成的?太尉本人说得清楚,他每天在京师鲜衣珍馐,左拥右抱,生活逍遥快活。可见他养尊处优,懒得强身健体,由此推出他的另一个特点。
科举中人。洪太尉对龙虎山的道士们说:“我读一鉴之书,何曾见锁魔之法?”“鉴”,同“监”,指他把国子监所藏图书全部读完。这表明洪太尉一是受过正规教育,靠科举考试而成为达官贵人;二是寒窗苦读,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可洪太尉万卷经书读过,越读似乎胆子越小,这是他的第四个特点。
胆不配位。面对山里跳出的大虫和窜出的大蛇,“惊得太尉三魂荡荡,七魄悠悠”,“看身上时,寒粟子比滑灿儿大小”。见到毒虫猛兽,怕得要死,束手无策。洪信作为掌管全国军事的高级武官,与民间百姓武松、李逵、解氏兄弟相比,他们面对老虎是怎样的英雄气概和神勇之举,洪太尉表现如此不堪,与其职位极不相配,庶可佐证他与武士格格不入。
由以上四点综合判断,洪太尉出身于文学之士。
再者,《水浒传》上的“文人”还指文艺之星。
如果说文学之士是接受过正规教育、通过国家考试选拔得到官方认可的话,那么,文艺之星就是无师自通、靠自身才艺扬名立万的人。文艺当指文化艺术,文学、音乐、歌舞、书法、绘画、杂耍技艺等可包含在内,小说中的高俅就属于这样的文艺范儿:
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有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踢得好脚气球。京师人口顺,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球。后来发迹,便将气球那字去了“毛旁”,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水浒传》第二回)
高俅不仅喜欢文艺,而且玩出了水平和名堂。话说一日高俅奉驸马王都尉钧旨到端王府办事,恰逢端王正与三五个小黄门相伴着蹴气球。“也是高俅合当发迹,时运到来;那个气球腾地起来,端王接个不着,向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那高俅见气球来,也是一时的胆量,使个‘鸳鸯拐’,踢还端王。端王见了大喜。”端王大喜,是他“慧眼识人”,发现了一个能够叱咤球场的风云人物,端王发现这样一个人才太不容易了。好不容易发现了,岂能不让他陪伴左右?随着交往的深入,端王越来越喜欢高俅;随着端王变为徽宗,高俅便扶摇直上迅速成为大宋朝殿帅府的高太尉。
行文至此,可能有人依然执着于高俅的“好刺枪使棒”,认定他的武士身份,到底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其一,不要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应当通盘考虑,防止以偏概全,避免只盯芝麻,却忽略西瓜,更不能看见脸上趴着个苍蝇,就说这是苍蝇而不是脸。在留意表象的同时,更要考察其内在的品性,即不能仅看某人会耍弄枪棒,有些儿武艺,就把他视为与一百零八人等同的武士,这是很肤浅的,因为内在的武胆和武德,特别是血性才是武士最重要的属性。
其二,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勿被“好刺枪使棒”几个字遮住了眼,要注意高俅发迹变泰主要靠的什么——鸳鸯拐。这一脚,踢得当时的端王未来的徽宗心花怒放,踢得高俅芝麻开花节节高,踢得“人间万姓仰头看”。高俅的“高”是“球”高,而不是弓刀石、马步箭的武功高。“抬举高俅毬气力,全凭手脚会当权”,他是靠球技赢得了职场辉煌,走上人生巅峰。
其三,不要望文生义,强作解人。喜好唱歌,不一定是歌手;喜好涂脂抹粉,不一定是美容师;喜好舞文弄墨,不一定就是文人;喜好打几趟拳、踢几下腿,也不一定就是武士。陆游、辛弃疾驰骋疆场,人们却首先认定他们是文人而不是武夫。须知,高俅原是个四处游荡、不务正业、游走于黑白两道的无赖,“人在江湖漂,怎能没把刀”,不会两下子也不符合他“浮浪破落户”的身份。再如他的叔伯兄弟高廉亦能临阵上马,挥剑作法,但他主要擅长的是旁门左道,并不能据此而简单地将他划入武士行列。
其四,不要脱离历史,要还原当时的真实场景。有宋一代,是文人的天堂,“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以致“满朝朱紫衣,皆是读书人”。朝廷对他们宠渥有加,身份地位空前提升,幸福指数达到历朝之冠。文人们一边上朝议政,一边过着舒适逍遥的幸福生活,他们流连于“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享受于“重头歌韵响琤琮,入破舞腰红乱旋”,沉醉于“萧娘劝我金卮,殷勤更唱新词。暮去朝来即老,人生不饮何为”,糜烂于“萧娘敛尽双娥翠,回香袂,今朝有酒今朝醉”。可现实中的事情,往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特别在“崇文抑武”的北宋,文人春光灿烂,武士却进了地狱。朝廷不遗余力地削夺武将的权力,不失时机地贬抑武士的社会地位,使这些人不得不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几乎成了被全社会唾弃的群体。那高俅在宋朝被委以重任,军权在握,他不属“文”,还能是什么?只不过他有点儿特殊,是个“文艺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