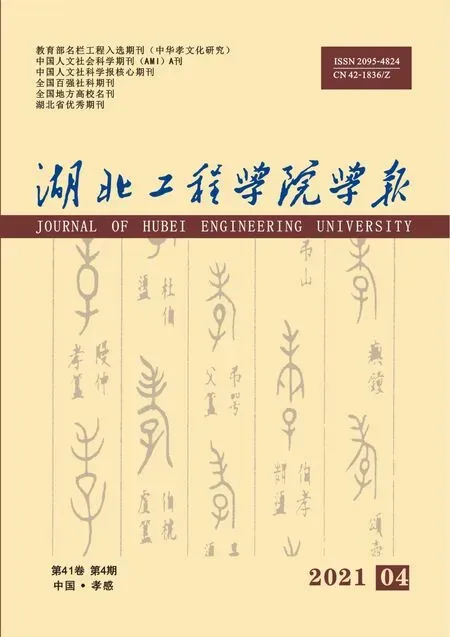论孝与治理规范
2021-01-15崔琳
崔 琳
(山东师范大学 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300)
近些年,因不孝而引发的社会争论日益增多。要破解这些问题,有必要借鉴孝的社会治理作用,去研究孝能否作为一种现代治理规范而存在,进而思考孝与治理规范(1)这里的治理规范适用既包含家庭领域也包含公共领域。的关系应呈现何种样态。
从治理规范维度研究孝的学者对此认知不一。观点一:有学者认为,当下孝不可以作为一种治理规范,持孝治终结论。如喻中[1]赞同法治取代孝治,随着家庭人身份向无涉伦理的社会人身份的转变,血缘伦理关系也向平等主体的法律关系转变。老年法的出现并非是孝道入法。相反,它意味家庭内部关系为法治所管辖,孝治宣告终结。
观点二:有些学者认为孝在当下可以作为一种治理规范。其一,方朝晖[2]认为孝与治理规范呈现出自治契合的逻辑,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之间虽然产生非血缘的空间——市民社会,但孝维护人的尊严、遵循天性、顺应自发需求与市民社会的自治与理性化特征相契合,有利于现代市民社会的自治。其二,有些学者认为孝在作为治理规范时呈现出泛孝逻辑,包含家国伦理。焦国成、赵艳霞[3]从历史的角度还原孝与治理规范的关系路径,认为孝是传统伦理的基德,是神本向人本、家庭道德向政治道德的变迁。王生云、周群芳[4]认为始于家庭而达于天下的孝道在国家治理中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治理队伍以及治理目的上,孝的官德要求利于建设治理队伍,孝还是达成和谐社会、人民幸福的治理方法。朱承[5]认为孝是一种双重规范,包含涉及社会、家庭中政治因素的公共规范与家庭互爱的私人美德规范。随着当下由顺从到平等互爱的语境转化,有必要弱化带有强烈胁迫色彩的公共规范,强化带有自觉色彩的私人美德规范。王承略[6]认为当下需要重新审慎以孝为核心的天人关系、君父关系、义利关系的家国治理逻辑路径。黄义英[7]赞同孝治模式是从家庭的孝延展至政治的孝,古代的孝与治理是建立在家庭道德与政治伦理有分有合并相互制衡的基础上,受到教育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孝治的尊老动力与协调尊老义务中的社会矛盾等是现代所需的。
笔者试图从历时性角度出发,梳理古今孝与治理规范关系的发展脉络,探究孝与治理规范的关系。在当下,孝能否作为治理规范存在,如果可以,孝应当呈现出何种治理规范模式。
一、古代的孝与治理规范
在古代,孝与治理规范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实际上,治理规范始终以人为中心,要想探讨二者的关系,就需要在与人联系最为紧密的家、国领域内,观察孝的内涵延展路径是否与治理规范相契合。
1.孝与治家规范。孝是以人为起点的道德伦理,这种道德伦理在治家中发挥着作用。事实上,古代的家通常是指家族。治家通常是指规范家族成员的行为与精神。虽然可以借助官方律法规范家庭成员的外部行为,但是同时规范家庭成员的行为、精神的孝伦理更契合家族治理理念。
第一,治家规范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赡养问题,孝以爱作为赡养动力。儿女对父母的孝是爱之天性。父母对子女有生养之恩,“父母生子,不劳而劳,自字及妊,自幼迄壮,心力所注,无有休歇”[8]。父母给予子女入世的载体——身体,还在其咿呀学语、匍匐学行乃至成家立业期间心不释护。基于感恩之心,子女自然会回馈父母的爱。再者,“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9],这是符合天道顺其自然的事情。父母给予子女无私的爱,按照“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的因果原则,子女也应当回报给父母至纯之爱。“凡为人子,当以二亲,体我心者,还体亲心”[9],说的正是子女必然要用父母养育子女之心,来对待父母。“众之本教曰孝,其行曰养”(《礼记·祭义》)。子女在孝养父母过程中,始终要以深爱作根。“人子之事亲也,事心为上,事身次之,最下事身而不恤其心,又其下事之以文而不恤其身。”[10]古代贤士将“孝养”分为四个等级,自上至下分别是 “事心”、“事身”、“事身而不恤心”以及“文而不恤其身”。四等孝养的区分标准是子女为父母付出的爱。子女在孝养父母的时候,应当尽力追求最高等级的孝——“事心”。《礼记》曾言:“作为子女,心即天理,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欲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只有深爱父母,才能和颜悦色地侍奉父母,并在考虑父母衣食是否充足的基础之上,进而考虑父母的心是否愉悦。
第二,治家规范需要平衡代际关系,孝的敬、谏内容可规制子辈与父辈的言行,避免代际冲突。子女不可鄙夷父母,要行之必敬,避免代际冲突。子女在孩提时期,要培养其亲爱之心,待其长大就要学会尊敬父母,这是由天性所决定的。孟子言:“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尊敬父母是一种义,这种义蕴含于良知、良能的天性之中。尊敬父母不过是顺人性。再者,礼者,敬而已矣。孝是一种子对父的礼,孝也就贯穿着敬的因素。“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10]。只有做到尊敬父母,才能做到色养父母。毕竟养身易,养心难。值得注意的是,“事亲以敬,美过三牲”,与哀丧严祭比起来,生前之敬比丧葬之敬更重要,敬重父母应当侧重生前之敬,要做到事亲以欢心,病则致其忧。最后,尊敬父母需要听从父母之命,顺父母之志。“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11],对待父母的命令应当遵从,不可推诿拖延。“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12],父母之好恶,子女也应当尽力去满足。“父母所欲为者,我继述之”(《格言联璧·齐家类》),即使父母去世,子女也要继承父母之志。如此一来,子辈的言行受到限制,减少了代际冲突发生的几率。但孝也以子女谏的形式来约束父母的言行。父母非圣贤,孰能无过。父母有过之时,子女应几谏父母,要通权达变,不可一味顺从。“父母有过,谏而不逆”[12],当父母出现过错,子女就要谏告父母,避免父母走向不义,《白虎通》曾言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子女与父母是最为亲近之人,若子女见父母有过,不加劝阻,反而纵容父母的不义行为,甚至触犯法律,遭受牢狱之灾,这不符合孝的顺从本义。子女对待父母之过,应当怡色劝谏,避免代际冲突。如“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弟子规》)。即使父母不听劝,也要几谏,哪怕遭到父母的打骂也不能有怨恨,要始终保持尊敬父母的态度。要而言之,孝的敬、谏是对上下辈的双向规范,平衡了代际关系,与治家理念相契合。
第三,治家规范涉及整个家族成员,孝也从纵向与横向涵盖整个家族成员(2)纵向来看,孝包含先祖、长辈、平辈与晚辈,横向来看,根据血缘、婚姻关系,划入家族范围。。孟子说“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孟子·离娄上》)。孝是避免家族灭亡、延绵血脉的重要保证之一。子女对上需要做到慎终追远、尊敬长辈。孔子曾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成公十三年》),祭祀先祖是孝的延续。孝是在祭祀先祖、感怀先祖德行中传承的。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与其说民众追远先祖表达的是崇敬,不如说是在继承先祖美好的德行。这种主动接受先祖美好德行的熏陶,最终融入民众自身的行为,是孝所特有的。当然,尊重在世长辈,亦是孝的要求。家族之中,长辈占据权力核心,家族的大事及纷争需要依靠族老主持。孝道也明确了平辈之间的相处之道。如手足相处兄友弟恭,“我有手足,父母一体,异母兄弟,总归天伦,恐有参商,残亲支体”[9]。兄弟亦是父母血脉的延续,发肤亦是受之于父母。兄弟阋墙是对父母不孝,犹如伤父母之身。又如夫妻相处相敬如宾。“我夫我妇,子媳之职,恐失和敬,致亲不安”[9]。夫妻之间若和睦,父母就不必为家庭焦虑,可以安心生活,这也是子女对父母养心。孝的规范也从夫妻领域延伸至姻亲领域,如“我有姻娅,数亲至戚,恐失夙好,致亲不宁”[9]。姻亲是家族延续的外动力,处在熟人社会中的家族不可能忽视姻亲的作用。与姻亲失和,父母必为家族忧心,是为不孝。最后是管束子孙,孝的目的是家族延续,对于家族延绵的重要对象——子孙,更要严加管教。“子孙后裔,恐失字育,断亲嗣脉,恐失教训,败亲家规。”[9]如果对子孙不加约束,德行有亏,败坏家规,最终因罪而丧命,这与孝是相悖的。概而言之,家之孝是建立在家族基础之上的,子女、儿媳等晚辈应当坚持尊敬长辈、兄弟友好、适度管教子孙、友好姻亲的规则。“诚使一姓之中秩序蔼然,父与父言慈,子与子言孝,兄与兄言友,弟与弟言恭”[13],无需父母操劳,达成家庭和睦,形成良好的家族秩序,这才是孝的重要内容。
孝作为一种家庭伦理,解决了赡养问题,平衡了代际关系甚至将整个家族纳入规范治理之中。由此可见,孝是建立在家庭伦理基础之上的治家规范。
2.孝与治国规范。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活动场所由家逐渐向外拓展有的至国。“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10]孝自然而然地从一种家庭道德伦理逐渐向政治伦理延伸,治家规范亦可转化为治国规范。孝作为治国规范需要规范君主、臣、民的行为,确保政治主体的全部参与,进而形成一个息息相关的政治团体。
首先,君之孝包含克己之道以及御下之道。君主的孝是自我约束,也是给臣、民起的示范作用。皇帝的谥号中,“孝”字是皇帝力求的,谥号中带“孝”字的说明皇帝具有仁爱、勤政等大德行。皇帝为获得“孝”的谥号,将会勤于朝政、遵循先祖遗训。先祖遗训往往对继任者提出德行要求。“三年无改于父道,可谓孝矣”,继任的君主基于孝的不可违逆性,恪守祖训,不敢随意乱政,忤逆先祖。先祖的命令(3)事实上,所谓的先祖命令,实际上是君主与大臣商议后的精英政策,是国家大政方针,借助先祖之志来延续政策,防止国家动乱是孝治的一个原因。往往以敕令的形式汇编留存于世,已然具有强制力,民众也习以为常,继任者往往难以更改。值得注意的是,先祖的遗训十分注重君主纳谏。根据《庭训格言》的记载,康熙曾言:“朕从不敢轻量人,谓其无知。凡人各有识见。常与诸大臣言,但有所知、所见,即以奏闻,言合乎理,朕即嘉纳。”纳群臣之谏,这正是借助孝保障君主稳定地治理国家的重要措施。通过先祖遗训,以孝的名义着重强调君主接受谏言,借助群臣的视角补偏救弊,以此延绵王朝的统治。御下之道包含对内御下臣民以及对臣属国的相处之道。对于臣民,君主借助孝约束其行为。“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10]孝是一切善行的根本,孝文化是符合自然规律的文化,君主不过是顺从自然之道,用孝教导民众分辨善恶。在孝环境的熏陶下,民众自然而然地远离罪恶,进而实现承平盛世。无需武力强制,无需酷刑威慑,仅通过内在的道德认同,君主便可让民心归服。可见,孝成了消耗最小、效果最佳的治国手段。孝还包含与臣属国的相处之道。“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10]。孝治要求君主以礼对待臣属,即使是小国之臣也需认真对待。对小国之臣这些弱者都施加恩德,不欺辱弱小,推至其他,亦是如此。正所谓“有觉德行,四国顺之”(《诗经·大雅·仰之》),君主具有这种层次的孝德之后,自然就会得到万国朝拜臣服,为世人所折服。
其次,臣民之孝既需要敬顺君主又需要忠于职守。《白虎通》中曾记载“王者父母地”,亦曰天子。君主是臣民的父母,自然而然,臣子需要敬顺君主。正所谓“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以孝事君则忠”(《孝经·士章》)。臣子事君应类于事父,恭敬之心也是相同的,因此用孝道来事奉国君就忠诚。臣子要对上不骄,谨慎守法,爱护民众。民对天子的孝与臣子之孝略有不同,在忠于职守上,基于物质条件的限制,主要是尽力耕种、节省俭约以养父母。孝将君主、臣子、民众三种不同身份的人联系起来了。换言之,孝将政治从一个笼统、缥缈的概念具体化成君主、臣子、民众各自遵从的规范,保障了政治规范的广泛执行性。此外,孝的修正性是政治领域所必需的。孝强调臣民在服从君主命令的同时,以另一个下对上的视角观察解决问题,弥补君主长期权力集中、消息闭塞或君主德行有失的短板。这是稳定王朝秩序的最佳策略。“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10],就是指出天子无德,但是借助臣子的力量来弥补统治的不足。臣子也通过忠于职守完成立身。
综上所述,孝根据人的活动空间由家拓展至国的逻辑,从家庭伦理转化为政治伦理。当孝作为一种治国规范时,自然而然地要以律法的形式保证国内政治主体的参与。
3.孝化解家国规范的张力。在家国之孝并存的双重阶段,存在着一个规范的张力[14],即孝亲与忠君的矛盾。古人云“忠孝难两全”,在亲与忠发生冲突时,孝借助一个价值目标追求——立身,将政治伦理转化成个人道德伦理,将百姓与政治参与紧密相连,很好地化解了二者的矛盾。
立身的实现方式体现了事亲治家与事君治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立身的实现方式是民众各尽其责。事亲侧重孝养。孝养分为物质赡养与精神赡养。在物质赡养中,“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10],顺应天时,耕种田地,获得赡养父母的物质基础——粮食。从这个家庭层面上讲,子女只有尽力耕种才是对父母的孝。但从政治领域来看,耕种成了国家兴盛的重要基础,如《商君书·农战》言 “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在古代,四民之中最重农民。农民与粮食是国家存亡的关键。在孝养领域,物质赡养需要耕种;在政治领域,治理国家提倡耕种,二者息息相关。这样一来,事亲的同时已然履行了事君的责任。在精神赡养中,孝要求子女养父母之心。孔子讲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子女不擅自出远门,一旦出远门就要向父母告知自己的位置。从孝养角度来看,子女陪在父母身边,才能了解父母;若远游他乡,不仅不能尽到赡养父母的责任,还会让父母担心,这不符合养心的要求。从政治领域来看,古代是农耕社会,强调耕种,不远游是让民众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为父母提供物质基础的耕种活动之中。再者,民众一旦投身于耕种中,就与土地有了持久联系,民众也就固定在土地之上。若民众出远门,也会告知父母,相当于民众的行迹是可以被掌握的。稳定性是古代君主维持统治的前提,君主最忌惮的就是流民,流民往往是国家的不稳定因子。入仕也是精神赡养父母的一种方式。从事亲角度来看,入仕可彰显父母之名,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同时也能光宗耀祖。“富贵不归乡,如锦衣夜行”(《史记·项羽本纪》)讲的是光宗耀祖对民众的重要性。古人向往“子孙继踵皆将相”(陆游《江东韩漕曦道寄杨庭秀所赠诗来求同赋作此寄》)的心理促使他们积极参与政治。从政治角度来看,朝廷的正常运行需要大量人才来维持,君主希望有才之臣来辅佐自己。“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陆游《金错刀行》)式的孝养观念与朝廷招贤纳士的思想相吻合。人才的选拔先经过了孝行的筛选,留下具有孝德的人员。元代郭居敬的二十四孝中江革“行佣供母”的故事就证实了这一点。这也说明事亲与事君是紧密相连的。“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10]民众尽其责,忠于君上是延绵家族、抚慰父母的最佳途径。民众通过这种立身方式,实现了事亲与事君的转化。事亲的责任意识对社会太平有促进作用。“父母既没,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13]这是要求子女不得做违法乱纪之事,辱没父母声名。这种责任意识是持久的,而非暂时的,自始至终都约束着子女的行为。因此,人人亲爱其亲,各尽其责,不辱长辈声誉,久之而天下平,在事亲的过程中实现政治上所追求的天下平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各尽其责意识是事亲与事君相互转化的重要手段。
从立身的价值目标来看,它要实现生命的最高价值——善。事亲治国亦有着共同的价值目标,那就是激发的民众天性——善。孝的本质是人的仁爱本性。无论是国家的政治治理还是事亲,都需要激发民众最天然的善。孔子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13],立身是为了追求至善之美。“父子之道,天性也”(《孝经·圣治章》),事亲是人的天性所为。事亲的外延包括对其他老人的尊重。“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10],一旦怠慢他人,父母就会遭受非议,这与孝亲观念不符。在这种观念下,社会就可形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良善之风。从政治角度来看,统治者采取刑罚或教化手段,是为了民众内心深处的善永存,确保社会安定。“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其所因者本也”[10],只有通过激发善,才可实现不教而知、不严而治,进而天下平。
孝根据个人在家、国领域的成长历程,沿着家庭伦理道德——政治伦理道德——个人伦理道德的循环演进路径,形成一套治理规范体系。由此可见,“孝治一身,一身斯立;孝治一家,一家斯顺;孝治一国,一国斯仁;孝治天下,天下斯升;孝事天地,天地斯成。通于上下,无分贵贱”[9]。这才是孝传承千年的重要原因。
二、近现代孝道的衰落对社会治理的影响
古代的孝沿着人的成长领域拓展,是家庭、政治、立身的伦理规范。那么,近现代孝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呈现何种姿态?孝到了近现代不断衰落,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非孝思想对社会的影响较大。至此,孝不再作为治家、治国的主要规范,而是作为一种提升自我的个人道德。时至今日,因孝道衰落而引发的问题不容忽视。
1.法律规范过度介入家庭纷争。自礼法之争后,带有独立、平等意味的个人概念与社会概念兴起,与孝紧密相连的家概念受到冲击,家与个人的联系不再紧密,新的社会理论认为家庭问题(4)这里的家庭问题是指无涉刑事的轻微家庭争执,且借助司法难以实际执行判决结果的问题。应当完全转化为去血缘化的个人之间的社会法律问题,原子式的民众与社会建立起新的规范,理性意味的法律规范代替情理意味的孝规范成为解决问题的主要规范。旧时,孝的敬与谏在家长与子女的权力张力中维持代际关系平衡。当前,敬被解读为逆平等的无限度服从,谏被认为带有政治的非平等性。此外,新式家庭中,子辈的权力扩大,父辈的权力缩小。[15]父辈的权力不足以满足其需求,子女一味排斥父辈权力,认为父辈的权力过大干涉到了自己。随着孝规范中的家庭道德意义的没落,敬谏失去作用,双方矛盾一触即发,代际关系失衡。为凸显平等与个人独立,新的社会理论主张这种由子与父权力对峙引发的家庭冲突应交由法律规范来解决。
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孝义衰落后导致法律被滥用。家庭领域的复杂性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法律问题无涉血缘亲疏,只追求正义。但家庭问题具有复杂性,有的家庭问题无法完全像法律问题一样,可以评判是非。争端的发起对象是具有血缘关系的,而且影响争端的因素很多,且无涉公平、正义之争,本质上是道德资本的博弈。[16]法律规范追求真正意义上的正义、公平,与家庭的最终目标——追求幸福所不同。因此,家庭问题完全转为社会法律问题,借助法律规范细致评判正义,不仅使判决难以执行,而且家庭稳定被破坏,亲情难以修复。这正是法律处理所有家庭争端的结果具有不稳定性的原因。此外,家庭中存在着一种“家庭政治”[17],无需法律规范介入,家庭中就有一套解决问题的规范——孝。孝具备了实现父慈子孝的一套规范体系,以维持家庭道德资本博弈的平衡。现代社会,孝的衰落迫使法律规范过度介入。法院接受家庭诉讼的量增大,表面看法律规范介入是在维护当事人的权利,实质上,这是一种过度介入。结果是法律一次次介入,判决难以执行,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法律应当是一种外在的预防保障与监督,只有涉及底线,才会介入。再者,多次采用强制执行,结果不尽人意。一是难以执行,孝道问题大多属于虚化情感问题,很少涉及实质的财物,并不像一些实质性的争端,可采取财物等经济手段来调节(5)虚化问题是指由孝产生的情感争端看不见摸不着,不同于人身伤害等实质性争端。。如精神抚慰如何强制执行难以量化,道德资本的博弈,各种感情夹杂其中加重了执行的复杂度。二是难以执行反映了法律介入的整个流程的失效。民众求助于法律大多是基于追求完美、理想化的结果。若民众多次求助法律未果,最终有损法律规范的权威性。可见,建立在家庭伦理上的孝规范不可或缺,敬与谏应当继续发挥平衡代际关系的作用。
2.孝的家国内涵隐没与情感淡化。清末以降,孝规范的家庭与国家道德内涵遭受抨击,移植西方规范体系的中国,强调个人与社会概念,摒弃了清末以前的个人无限融于家的孝,利于人格自由。但是个人无限疏离家,过分强调个人与社会的绝对紧密性,其直接后果是民众的亲情淡化。事实上,孝规范并非只具有规制作用,它还认同民众的情感是寄托在家国之中。
孝规范不仅是调解子女与父母的情感关系,它也确认了民众的情感是寄托在家庭之中。治家本质是调解父母与子女的情感关系。当代家庭的基本形态发生转变,由古代的大家族转向今天的核心家庭。精简化的家庭导致家庭情感矛盾更加集中,家庭中的道德资本博弈更加集中于血缘亲情。在情感博弈中,调解情感关系的孝规范如果衰落,敬、谏失范,子女就将自己定位为父母的竞争者。子女与父母的一次冲突会演变为连续性的争端,自然而然,子女与父母成为追求家庭争端胜利的竞争者。[17]无论子女胜利与否,这种竞争是在吞噬家庭情感。竞争如果成为家庭的核心主题,就取代了治家的主题——情感互慰,家庭分裂成为最终结果。作为家庭规范的孝失去生长土壤,家庭“战争”将进入恶性循环。子女对家的情感寄托随着这种“战争”的升级而淡薄,逃避家庭成为子女的最终选择。
失去情感寄托体——家,子女自然会寻求另外一种拟制的家。社会就成为民众情感寄托的主要场所。社会虽具有拟家性,但并不能成为情感升华的载体。孝作为政治规范时将立身与政治、家庭相结合,个人的情感也随之融入立身的活动中,进而个人与国家的情感联系随之增强,最后可以达到一种情感升华——生死与共,这点是社会所不能及。再者,当孝规范失去政治、家庭、个人道德的属性后,民众对国的情感寄托升华就不足,民众参与国家治理事务的积极性不高,爱国情感淡化,有的会崇洋媚外。
综上所述,孝的衰落直接导致家庭纷争的无休止与法律资源浪费以及民众的情感淡化,给国家治理增加了障碍。孝应当发挥其治理功能以便解决这些问题。
三、从国家治理角度思考孝规范的回归
近现代孝的衰落引发的社会治理问题已然说明孝并非是逆现代化的存在。在历史经验中,孝作为一种治理规范在国家治理中具有不可或缺性。对历史的梳理最终要回归当下,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出发,思考孝应当呈现何种治理规范样态。事实上,当代的孝规范应当继续坚持融合家庭道德伦理、政治伦理与个人道德伦理于一体。
1.孝道是倡导民众回归天性与后天自律的伦理规范。孝规范应当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不仅是建立在天性善的基础上,还应当做到后天自律。孝既与自然相符,又是讲求无愧于本心、顺应天性的道德。当下有些人过度追求个人私欲而抑制了人的天性——善,孝规范的衰落也导致人失去了寻找天性的动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缺乏诚信。因此,对善的追求是孝规范得以亘万世而不易的原因,当下孝规范的回归也应当强调对人的天性的追求。但这种天性需要后天的修为,遵守孝规范成为习惯——后天自律。“孩提之时,倘或不肖,则其父兄必变色而训之。语曰:少存若天性,习惯如自然。”(陆桴亭《论小学》)子女要从小培养尊守孝规范的意识,稳固天性的存在。[18]待其长大,这种孝意识已然成为行为准则,天性也随之留存。
孝规范在后天自律的具体设计中强调建设一个自律的孝团体。王国维曾讲:“昔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殷周制度论》)孝规范的回归是将领导者、普通工作人员、民众都纳入一个自律团体。值得注意的是,与旧时的非平等性不同,现代的自律团体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坚持自律原则,即领导者以身作则、工作人员尽职尽责、民众主动自律。
领导者应当以身作则,主动接受孝规范的约束。《孝经》云“《甫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孝经·天子章》)。只有领导者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民众可以最直观地领略到孝规范的内涵。“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10]领导者是社会风气的重要影响因素,领导者严明善恶,行之必孝,民众必定以孝为风尚,纷纷习孝,学孝。
普通工作人员是贯通上下的群体,其职责为:一是当好领导者的助手,积极参与、建言献策。二是认真贯彻政策,学会自我反思。“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10]孝规范要求国家工作人员要忠于职守,时常反思自己是否尽职尽责。[17]“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孝经·诸侯》)。学会自我约束,不因贪腐等违法行为招灾祸,不辱父母先祖之名。三是要爱护百姓。“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10]国家工作人员爱护百姓,遵守孝规范得到百姓的称赞,那么国家政策就能更好地执行。
对于民众而言,孝是一种内在的自我道德规范。[18]民众自律代表着民众要主动遵守一整套的道德规范。在家庭中,民众的自律表现为孝敬、劝谏父母,友好亲人,自觉遵守并践行孝规范。人的天性——善也作用于家庭之外:一是关爱老者呵护幼小。人人以善良之心待人,久之,尊老爱幼的风气就会在社会形成。二是遵纪守法。“一旦害至患生,使吾父子君臣夫妇昆弟朋友之将沦胥以亡也。”[19]违法犯纪,不止是让父母颜面无存,自身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2.孝规范有助凝聚力回归。当今寻根文化的盛行实质是人们看到了孝规范背后的凝聚力,将孤立的个体与家、国紧密相连,情感得到慰藉。
第一,孝规范的凝聚力体现为强调民众对家的认同。与其说孝规范教人如何对待父母、亲人,不如说是孝规范在强调人对家的认同。孝为人的行为提供的规范中,始终带有家的烙印。如要求民众孝养父母,事实上是对凝聚力的追求。父母给予子女生命,是子女生命的来源,是子女的根。子女的成长依赖着根,无论子女以后发展出多少枝丫,根对于子女才是最重要的。子女根据孝规范的指引,对根进行回馈。孝规范提供父母施恩与子女报恩的往来途径,家的凝聚力就得到巩固。这种凝聚力跨越时间,贯穿人的一生,具有持久性。受孝规范的引发,落叶归根、人死归乡也成为游子的最终愿望。同时,这种凝聚力也超越了空间,无论人身处何方,这种向心力始终牵引着众人归家的思绪。正如王安石所言:“月明闻杜宇,南北总关心”(《将母》)。民众在遵从孝规范时凝聚了整个家庭,有了归属感。可见,这种凝聚力超越了时空,安抚人的心灵。
第二,孝的凝聚力也体现了民众对国家的认同。国是千万家,也是民众的根。国家为民众提供了生存所必需的一切,包括维持社会秩序。社会稳定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民众是最大受益者。民众始终是与国家紧密相连的,“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20],二者相互依赖是凝聚力得以维持的原因。孝规范为这种相互依赖提供了行为范式,民众需要忠于国家,积极参与爱国事务,与国家融为一体。凝聚力最终的体现是“一”。“临患不忘国”(《左传·昭公》),孝规范强调的“一”,可以体现为生死与共的情感升华,这是其他方式所没有的。可见,孝规范是民众认同国家与国家融为一体的最佳途径之一。
3.孝规范倡导民众实现自身价值。孝规范激励民众在遵守治家规范与治国规范中实现自身价值。现代民众的生命意义依旧是实现自身价值——立身。孝规范将立身置于家国之中。家是民众实现自我价值的第一场所。孝规范为民众提供了两种行为预设:一是对己。民众实现自身价值就是在实现生命意义,要符合生命之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10],父母给予人生命,人需要珍稀自身的生命。[21]二是对长。基于生命之道,人需要回馈父母——事亲。事亲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需要做到生之孝与丧之孝。[22]现代意义上的丧之孝不同于古时的丧之孝。前者更注重民众从丧葬祭祀中传承积极文化精神,或者说是帮助民众找到自身的生命价值,并非是后者僵硬的繁琐仪式。在这连续性的事亲过程中,民众已然知晓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这种行为延伸到社会,就会产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尊老风气。孝规范还强调民众自身价值需要在事国中实现。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对民众而言,自我价值需要在建设祖国中实现。对于国家而言,民众的全面发展是国家繁荣昌盛的内在动力。由此可见,孝规范倡导民众实现自我价值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
要言之,孝规范要想融家庭道德、政治伦理、个人道德伦理于一体,就要回归人的天性,坚持后天自律,倡导家国凝聚力,亦或是实现人生价值。只有如此,孝规范才会发挥其社会治理作用。
四、结 语
孝是一种伦理规范,包含家庭伦理、政治伦理与个人道德伦理,作用于家庭、社会的治理。近现代孝衰落了,其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内涵隐没,个人道德伦理受到冲击。敬、谏的消逝导致法律规范过度介入家庭纷争,结果不佳的同时造成资源浪费。家、国概念的隐没,情感难以依附。这从侧面印证了孝作为一种治理规范而存在的必要性。孝亘古不衰必定有其优势所在,当下要重新审慎孝的意义。“必将因今之礼而裁酌其中,取其简易易晓而可行,必不至复取古人繁缛之礼而施之于今也。”[23]孝作为一种伦理规范,应当融合家庭伦理、政治伦理与私人道德伦理,在追求回归天性的同时严格自律,在凝聚力中寻踪情感寄托,最终达成立身价值目标,从而形成一个由己及外、再由外到己的循环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