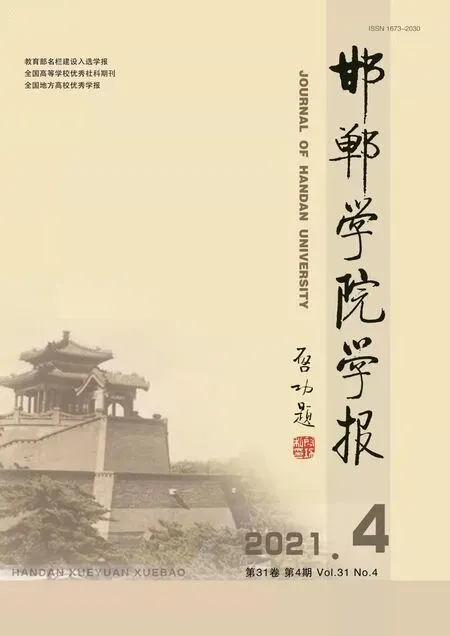荀子人性论的创造
——以“情性—知性”二元结构为线索
2021-01-15冯硕
冯 硕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梁涛先生认为《荀子·富国》篇(以下行文中《荀子》引文,只具篇名)提出了以“欲”“求”所代表的情性,和以“可”“知”所代表的知性[1]。“情性-知性”结构贯彻荀子各篇,只不过在提出“伪”概念以后,“情性-知性”结构过渡到了“性-伪”结构。通过分析“情性-知性”结构,我们认为在知性对治情性这一理路背后,还潜藏着情性和知性相互合作、配合而化性成善的理路,荀子其实对情、欲均持有正负性两种评价。最后我们集中分析了《正名》篇荀子对性、伪二义的界定,认为荀子的人性论由于知性具有后天完成性、集天性与人成于一身的特殊属性,没有安置在“性”中,而是被安置在“伪”中,由此引起了“伪”的提出和性伪之分、合的理论结构。在人性论的现代语境中,我们应该有意识地把“伪”中的知性部分还原到荀子的人性体系中来,以补全荀子的人性论。确切地说荀子人性论是一种性伪论,人性的先天所予性和后天完成性是统一的,这反映出荀子天生人成的理论面向。
一、从“情性-知性”结构到“性-伪”结构
梁涛认为《富国》《荣辱》是荀子早期的作品,在《富国》篇中,知性-情性说已经被提出,并都被看作是性。知性可以指先天的认知能力(能知),也可以指认知的后天运用(所知),前者属于性,而后者则不属于性。在《富国》篇中,荀子没有区分能知和所知,直到后来的《正名》篇提出“伪”概念后,才把前者称为性,而后者称为伪。然而,在《正名》和《性恶》篇,性往往指的是以情、欲为内容的情性,作为“能知”的知性和以情、欲为内容的、动物性的性似乎很难兼容。尤其是《性恶》篇的前半部分(即“仁义法正”之前)反复以“情性”为性,把性与情性相混同。如: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若夫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
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
《正名》篇也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 似这般用欲定义情,把情和欲结合一体;又以欲言性,把性、情与情性相混同;在《荀子》中还有多处,兹不悉举。然而,荀子重视知性,强调心知道、可道的能力。知性和情性构成人性内部的张力,知性可以对治情性,情性也可能冲破知性的约制。荀子在提出“伪”之前,把情、欲等生理欲望和心理归之于性,把知性归之于心;在提出“伪”之后,情性和知性的结构仍然得到了延续。可以说,“情性-知性”二元结构构成荀子人性理论的核心架构,贯穿了荀子的早期文本和提出“伪”以后的文本。
(1)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异也,知愚分。(《富国》)
(2)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荣辱》)
(3)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正名》)
(4)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正名》)
(5)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正名》)
(6)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性恶》)
(1)句所谓“同求”“同欲”即就情性而言,而“异道”“异知”则就知性而言。情性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知愚”的区分在于知性的后天运用。(2)句材性知能,是人人皆同的;“好荣恶辱,好利恶害”,则属于情性,也是人人皆同的;而人与人的区别在于“所以求之之道”。此道非知性不能知,非知性不能可。(3)句之“心为之择”,是知性的思虑和选择,是通向“伪”的必要环节;若无知性,人只能在“情性”的主宰下,就无法开出“伪”和礼义。(4)句“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说的是情性的欲求;“以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则是知性可道而求的能力。(5)句说,“治乱”不在于情性,不在于欲望本身,而在于“心之所可”,也即知性如何发挥其作用。可见,情性只是荀子人性内容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其中消极待治的部分。如果我们把情性及其流弊理解为荀子人性论的主体,也就舍本逐末,遗漏了荀子人性思想的核心。(6)句中“性”主要是指情、欲为内容的情性,而“学而求有之”“思虑而求知之”则是知性的后天运用。这些篇章,皆以情性与知性对举,呈现出明显的“情性-知性”二元结构。把荀子的“性”仅仅理解为情性,理解为以情为质,以情、欲为内容的性,有失偏颇,没有把握到荀子人性思想的要点。荀子提出“伪”以后,在“性-伪”的结构中,不难发现,知性是安排在“伪”中的。
尤其是《性恶》篇“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一核心论点,以往的理解多在“性恶”二字上。我们认为,“性恶”和“善伪”是同样重要的。沿用“情性-知性”二元结构分析可知,“性恶”是对应情性的,而“善伪”是对应知性的;“情性-知性”二元结构过渡到了“性-伪”二元结构。这种过渡的首要原因是“伪”的提出。在《富国》《荣辱》的文本那里没有明确说出“知性”,而是借助“知”“可”“材性知能”来体现;而到了《正名》《性恶》,知性其实已经安置在“伪”这个全新的概念中了。当情、欲和心对举时,知性在于心的认知、可道的能力,安置在“心”中;当荀子只把性和伪对举,而不言心,就像《性恶》篇那样,那么知性实则是安排在“伪”中的。由此荀子实现了从“情性-知性”到“性-伪”结构的过渡。
荀子的理论核心是礼治,而礼源自伪,伪之重要不言而喻。把伪理解为人为,并不透彻。梁涛认为伪是心为,伪要结合心来理解[2],此说甚是。伪如果离心而为,便是动物之为,不复是人为了。又如饮食睡眠等人和动物一般无二的作为,也并非荀子之“伪”所指涉。荀子的“伪”最能体现人的特殊性,只有人能伪,其余一切动物皆不能伪。在这个意义上,伪体现人类的本质和尊严。人之有礼义在于伪,伪就是人区别于禽兽的地方,与孟子的四端说相似,居于道德理论的核心位置。如果依“情性-知性”结构分析,那么亦可说荀子的心为之伪是知性之伪。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心伪也好,知性之伪也好,并非仅仅是心的内在活动,还通过心(知性)对情欲的约束,对官能、身体的主宰,而走向“能为之动”的实践活动。
礼义源自伪,伪是知性之为,所以荀子礼治理论的人性基础在于知性,并非人们所指责的那样“大本不立”。梁涛先生区分“能知”和“所知”是非常关键的,如此一来,心之“能知”代表的人的先天认知能力,就成了荀子人性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纠正了性恶说偏向情欲的单向度理解,为他提出心是道德智虑心并主张性恶心善说提供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荀子的“能知”还可进一步分析为:初始的知性和次级的知性。所谓初始的知性,是人人与生俱来的认知能力;所谓次级的知性,是初始的知性在后天环境中形成的二阶知性。初始的知性在反复使用中,在接触礼义教化后,逐渐形成次级的知性。初始知性和次级知性都是“能知”的范畴,而次级知性是经过“所知”的训练而形成的二阶知性。细细分析,初始的知性当属于性,而二阶的次级知性当属于伪。于是,“能知-所知”结构细化为“初始知性-次级知性-知性的实际运用”结构。初始的知性提供了人知道、可道的可能性,而次级的知性经过后天积靡、虚壹而静的工夫才能把知道、可道变成现实,进而化性成善。前者人人生而皆有,而后者人人可能因为后天努力程度的不同而有差异。
荀子所强调的后天学习和礼义师法之化,正对应于初始知性到次级知性这一阶段。因为初始知性是脆弱的,如果没有礼义、文化来保持、引导、培养,就像自幼长在狼群中的婴孩,难以发展次级知性来遵循礼义、修成君子。可以说,初始知性的脆弱性和荀子的性恶论关系颇深,正因为初始知性的脆弱性使得人更容易顺从情性而为,使人易于沦为禽
兽,使社会难成秩序。次级的知性,是在礼义、师法的引导中,在实际事务成败的历练中逐渐培养的,可以理解为先天知性的强化和社会化。学习并认同礼义使知性得以强化,那么知性便有充分的力量来对治情性,从而在个体层面成为隆礼之法士、礼义之君子,在社会层面纠正无序纷争而实现礼义的社会秩序。知性日益进,情性则日益合理、规矩,这构成荀子以心治性、以知性对治情性的重要理论向度。
此外,我们还须求证的是情性是否只能被治理,情性在成德成治中是否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二、从情性与知性的正反交互作用看性恶、性朴之关系
荀子以心治性的思想路向为学者所熟知,依照“情性-知性”结构,也可以说荀子的这一重要理论向度是以知性对治情性。知性对治情性,进而过渡到以伪治性、以伪化性,这一理路固然重要,而情性反过来对知性的影响却容易被忽略。其实,情性和知性是交互影响的,正如性伪有分,也可以言合。
正面的向度是学者所熟知的知性对治情性的向度,反面的向度是情性为知性提供原始材料、必要动机和情绪基础的向度。后者所反映的是情性对知性活动的必要性,知性活动不能完全离开情性、更不能吞噬、淹没情性。知性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合理满足人的情性,使人不伤其性。在正面的向度里,情性有无节制扩张之蔽,而健全无蔽的知性可以约制、克服此蔽,所反映出来的是知性约束、治理情性,使其合理化、规范化。在反面的向度里,当情性没有无节制扩张之时,那么人类天生自然的、不过分的、在礼义之内的合理欲望、正常情感表达和需要,乃是一种天情、天养,不但不能抑制,反而应该养育。所以,在《性恶》篇所说的“恶”的欲、情,在《礼记》篇却是“朴”性和须“养”的欲、情。其次,此情、欲非彼情、欲。我们不难知道有些情、欲乃是世界上最美、最有价值的情、欲,如爱美之心;有些情、欲却相当之丑陋而君子耻之,如嫉妒、贪婪。荀子素重礼治,礼本治情,绝不可无情。《礼记·礼运》云:“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治情如治田,情恶犹如以田为恶,这是说不通的,荀子绝不主张这种情恶论;纵情犹如不治田而田荒芜,此大略与荀子性恶的意思相符。
在《性恶》篇那里所凸显的情、欲,是无节制、超出礼义之外的情、欲,故而近乎恶(准确地说是在后天环境中引起恶);在《礼记》篇那里所呈现的情、欲,是未曾无节制扩张的、在礼义之内,甚至是礼义活动所必备的情、欲,故而近乎朴,甚至美。前者之情欲,如贪婪、疾恶、好色无节;后者之情欲,如必要、合理的饮食、睡眠、休息、男女之情爱、亲子之情等等,即孔子所谓食色性也;又如对去世亲人的“思慕之情”“孝子之情”(《礼论》)。凡读荀子者,莫不对荀子“顺是”无节的情、欲印象深刻,此固然是荀子在《性恶》篇所强调,但他并非没有注意到为礼治所必备的积极的情。如《修身》云:“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知若师也。情安礼,知若师,则是圣人也。”依照“情性-知性”二元结构来看,个体学习礼义达到圣人境界,不仅需要无蔽、明觉的知性,还需要和礼兼容相通而达到安适的情。固然荀子的情性显露恶的倾向在文本中比比皆是,然而细究之,荀子对欲主张“道欲”“节欲”“养欲”,对情则有“安礼”“爱敬”之情,故情性之恶绝非荀子唯一的理论向度。
首先,对于欲,《正名》:“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去欲”“寡欲”的主张是困于“有欲”“多欲”而不懂“道欲”“节欲”的缘故。治乱不在于欲之多寡,而在于“心之所可”。而“心之所可中理”,自然需要知性的“知通统类”(《儒效》)。又说:“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所欲虽不可尽,求者犹近尽;欲虽不可去,所求不得,虑者欲节求也。道者,进则近尽,退则节求,天下莫之若也。”(《正名》)可见荀子对欲有正反两面向度:一则在“节求”,节是因为“所求不得”,不节制就会生祸乱;一则在“近尽”,人们追求能得到满足、不引起祸乱纷争、在礼义之内的欲望,是再合理不过的。又《礼论》:“礼者养也。”礼本来就有节欲和尽欲两面,节欲是为了免祸除乱,尽欲是为了欲望能在合理的情况下尽量得到满足。综合起来看,满足欲望是为了养欲,节制欲望同样是为了养欲。人有相当程度和范围的欲望是合情合理的,也有部分欲望超出了礼义标准而成为恶的原因。那种认为荀子只看重“顺是”无节的欲(性恶说的关键)的看法显然是不合适的。其实,荀子对人类合情合理的欲望是极其重视,并力求其满足的。
其次,对于情,荀子也有正反两面看法。贬义的情为学者所熟知,此处不表。但从正面的向度看,除上文所述“情安礼”一证外,《礼论》有“两情”的说法,尤堪注意:“两情者,人生固有端焉。若夫断之继之,博之浅之,益之损之,类之尽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终始,莫不顺比,足以为万世则,则是礼也。”“断之”“损之”“浅之”的意思明显不过,而“继之”“博之”“益之”正说明“情”的正面意义。此情超出了礼的要求,当“断之”;合乎礼但有不足则当“继之”;此情,多则“浅之”“损之”,寡则“博之”“益之”,总之情乃礼所不能或缺。此外,礼也要求“情文俱尽”“称情而立文”(《礼论》)。情一方面有超出礼义的倾向,需要知性(心之所可中理的知性)、礼义来对治;另一方面如果无情、灭欲,则礼更无从谈起。又如《不苟》篇讲君子之“宽容易直”“恭敬繜绌”“敬天而道”“畏义而节”是先天的喜怒哀乐得到礼义教化(亦即次级知性之养成)而形成的;讲小人之“倨傲僻违”“妒嫉怨诽”“慢而暴”“流淫而倾”,是后天放纵无节导致的;不能说小人的恶有性恶的人性基础,显露了情的恶,而君子的善没有任何人性基础,不体现任何情的积极因素。君子小人的欲望、喜怒哀乐之情是一样的,君子从礼,小人不由礼;小人不由礼则情欲自然超出礼义而沦为恶,君子由礼则情欲自然在礼义要求之内而成其善。人的情欲一方面可以导致恶,另一方面任何礼义之内的活动必有合理的情欲为其基础。因此,情、欲都有其积极的一面。
对荀子来说,欲有两面、情也有两面。礼外之欲,放纵无节,引起纷争穷乱;礼内之欲,是人生存之本,是百姓生活之本,是合情合理的大义所在。礼外之情,是情过长、过多、过薄或者过于不足,因此悖于礼,当“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礼论》);而礼内之情,如丧亲时的哀敬之情,祭礼的思慕之情,岂全是外力所加而无先天之情?荀子甚至认为但有血气者即有积极的情:“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今夫大鸟兽则失亡其群匹,越月踰时,则必反铅;过故乡,则必徘徊焉,鸣号焉,踯躅焉,踟蹰焉,然后能去之也。”(《礼论》)鸟兽且爱其类,人岂不爱人?所以,虽然荀子文本中“情性”常为贬义,但他对情、欲的认识并非单向度的,而对两者的积极一面有着深刻的体察。以知性对治情性,知性为正面,以克制负面的情性,是人们所熟知的一个向度;荀子还有另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向度,即情、欲乃礼治不可或缺的基础,它们在礼义标准之内,没有逾矩,此时的情、欲便是合理的,将和知性共同作用、相互促进而生“伪”成治。
以心治性,以知性对治情性,这一理路所强调的是感性生命的理性化或者合理化,所反映的情性的缺失和不足;情性和知性相互合作、配合,情性提供必要的先天情感基础和内在动机,知性经过思虑、权衡做出道德判断,对先天之情欲做出合理的损益和选择,该理路所反映的是情性在道德判断和道德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以心治性的理路,对应荀子的性伪分理论;后一理路是心性统合,与荀子性伪合的理论相对应。故《性恶》篇的性恶善伪说,遵循的是前一理路,显露出情性顺是无节的弊端和缺陷;《礼论》篇的性朴说,遵循的是后一理路,情性乃是“本始材朴”,是“文理隆盛”的前提和基础。
在荀子看来,善恶的标准在于礼义,在客观之治乱;以此来看,那么性恶是从情、欲超乎礼义标准那一面而言的,性朴是从在礼义标准以内合理的情、欲那一面而言的;两者俱成立而所指不同。《礼论》篇强调的是和礼互通兼容、作为礼文基础的情,《性恶》篇强调的是超出礼义标准的“顺是”无节的情;也因此,《礼论》昌言性伪合,而《性恶》特标性伪分。性朴方能与伪合,未闻恶性而与伪合者;性恶方才与伪分,若无朴性,伪亦无根。可见,荀子对情、欲、心、性的理解十分复杂,性、伪的分合,体现了情性和知性相互对立又相互合作的两面性,最后具现为性恶和性朴两说的并存无碍。
三、《正名》篇“性”“伪”新释
《正名》篇对“性”“伪”的界定:“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梁启雄认为第一个性,是“天赋的本质,是生理学上的性”,第二个性是“天赋的本能,是心理学的性”[3]309-310。廖名春大体承认梁说,并以体训性,指出第一个性即人的形体器官,如耳目口鼻之类[4]68;认为第二个性是天官和天君综合作用产生的,认同其为心理学上的性[4]72。邓小虎继承了前两位先生的观点,进一步提出第一个性“并不仅仅指形体,而是泛指人类生命成为如此的一切自然质具”[5]53,而第二个性指的是,“自然质具的基础上所产生的自然反应和表现”[5]53-57,也就是情欲反应。笔者认为此一“生理-心理”解释体系并不合理,因为知性在这里找不到位置。
第一,把第一个性的含义往物质形体、自然质具上解释,“所以然”三个字所透显的向上、向天穷究的意味就被削减了。形体是已然、实然,并非“所以然”。形体可以是身体功能、官能的“所以然”,但形体的“所以然”依然可以穷究。“生之所以然谓之性”,是向天穷究,向上穷究,是追根溯源的、形而上式的、前经验的;这与《性自命出》的“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中庸》的“天命之谓性”意思相似。《正名》接着说:“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性者,天之就也”,可见荀子天人相分的那一面向在这里并不适用,而应该从天人相合的面向思索之。《天论》有段话和《正名》相仿:
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
廖名春引“形具而神生”,认为“形”就是第一个性,“神”就是第二个性,视之为这两个性定义的最好概括[4]70。可这并不符合《天论》这段话的逻辑。首先,“天职既立,天功既成”,是“形具而神生”的前提,人类的形体是天所生成,是“天职”“天功”的体现。第二,接下来所说的“天官”“天情”“天君”,都没有把人之形体、心、情与天割裂,而说天和人是联系在一起的。荀子接下来又说:“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天论》)。因此,溯及形体,尚显不足,当追溯于天。第三,《天论》主张人“不与天争职”,不是在割裂天与人的关系,而是说天与人各有其职:“天有其时”而“人有其治”(《天论》)。我们并不否认第一个性的意思包含人类的形体器官,乃至一切自然质具,而是补充“天职”“天功”在人的形体、质具中的体现,并强调第一义的性从生理再往上递进一层的意思来[6]203。韦政通认为向上递进一层的说法和荀子性论的本义不兼容,其所列证据在于《性恶》篇讲性都在生理一层,如果还有生理层向上递进一层的性义存在,则荀子的人性论,“必全部改观”[7]65。其实《性恶》篇的性恶之性只是荀子人性论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如果把性恶的性当做荀子人性论的全部,则性恶说不得不引起天恶说,这和荀子《天论》篇的本义才是不兼容的。此外,如果人性全恶,则礼义、化性理论确实无从开出。所以性恶之成立乃是有特殊语境和条件的,此有待作专文另述,此处不表。
廖名春反对徐复观把此性和天道相通,反对以理释性而主张以体训性,可第一义的性与天道接,对荀子的天人理论而言很有必要。“生之所以然”当然有理的意思,而不仅仅是物质形体;但如果纯然是理,又何以自然地过渡到“性之和所生”的经验层呢?所以,仅仅以理释性也不妥。第一义的性,是从天的角度对人性的规定,荀子文本中一切人性的事实及其所体现的功能、属性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据。《正名》后文“情然而心为之虑谓之择”中“情”和“心”,是涵摄在内的。《荀子》其他篇章中的“情性”“心知”“材性”“能”“志意”“能群”“有义”等等,都可以溯源于它;第一义的性可谓是性之全义。
具体分析,此性至少有四层意思——广泛义、潜能义、非经验义、根据义(本源义)。广泛义是指作为“生之所以然”的性,从其所开的人性内容方面来说并不仅仅限于情、欲、官能等某一特定方面;潜能义是指它有能开出实然的性的潜能;非经验义是指此性是经验前而非经验后的;根据义是指此性是经验后的人性诸事实的本源和理据。此性尤似种子、胚胎,唯此种子性,方能不局限于形体,又内涵向天穷究之义。它上究于天,下形于人,《荀子》文本中涉及的人性内容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据。第一义的性是天人相接的性,其中必有天的要素和意味,必兼具身体的形和精神的理。此性是后文的“性”“伪”“心”“能”诸概念的起点,是不可或缺的。考察至此,不难发现,此性虽然涵摄知性之可能,却完全不能显白出知性的功能及其作用。接下来,荀子迅速过渡到经验层的性。
“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是第二义的性。第一义的性,所追究者是生之“所以然”,具有从既定的人性向上追究其本源的倾向;第二义的“性”与前者相比,具有从第一义的性向下考察其经验之自然显现的倾向。“精合感应”尽显与外物接的经验含义。后文的“情”“知”“能”诸概念,都有两个界定,且均是前者体现潜能,后者体现实然。如“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的“情”尚属于潜能,而“情然而心为之择”之“情”则是已发了。至于“知有所合”“能有所合”之“合”都是经验接物之义,无须深辨。因此,第二义的性是经验的性,是实然的性,应该是可以成立的。从内容上看,第二义的性就是情、欲。“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正名》)这里的性和情、欲是一回事,指的是第二义的性,而非第一义的性。
第一义的“性”涵摄知性,因为人的知性作为一种潜在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没有理由排除在外。《解蔽》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心生而有知”,便是明证。可是,知性安置在第一义的性中并不充分,还须在经验世界中考察知性。此前的学者多注意到荀子在经验和实然的层面对情性的考察,但却忽略了知性在经验层显现的特殊性。
把第一义的性往生理、形体上解释,把第二义的性解释为心理上的,这样一来,知性就无从安置了。形体无法突出知性的能力;心理、情、欲更不反映知性。按照“情性-知性”的结构,我们发现荀子有着特殊的结构安排:(1)第一义的性作为前经验的根据;(2)情性在经验层的自然显现(第二义的性);(3)知性在经验层的运作(第一义的伪)。知性就体现在心的“择”“虑”上;与生俱来的知性在经验层的运作,开始对治情性,并与情合作、配合,进而产生伪。荀子的人性论不仅在性之二义,还必须把第一义的伪涵摄在内。按照上文对初始知性和次级知性的区分,则第一义的伪更多的是初始知性运作的结果。心之“择”与“虑”可以是初始的,也可能通过重复运作,而逐渐过渡到次级的。心之“择”“虑”最初是初始的,后来则可以是在学习了礼义,通过礼义师法之教化后而形成的进阶的“择”“虑”,此时的“虑”便是“虑积焉”之“虑”了。也因此,第一义的伪过渡到了第二义的伪。因此,知性在经验层的显现恰是伪,知性是安置在伪中的。
作为荀子人性论核心的知性,实际在“伪”,而不在“性”。把荀子的人性论追究于性之二义,往往只强调了情、欲或形体方面,这样解释不仅会造成知性不属于荀子人性范畴的认知偏差,还因为人们把“伪”仅仅一般性地理解为人为,而忽视了其背后知性的人性基础。如劳思光先生便认为荀子只肯定人的动物性,却对“创造文化、实现价值之某种能力”不察,“教化亦将无根”,又说“人只有动物性,又何以能成为圣人?何能自作努力,何来文化成绩?”[8]248-249
关于“伪”中蕴含“性”这一观点,廖名春先生早有所见,他在《荀子新探》一书中指出“性不足贵,是‘化’‘治’的对象,而后天的‘伪’,是‘人最为天下贵’者,是‘人之所以为人者’,是‘圣人之所以异于众人者’,所以,‘伪’才是人的本质。”[4]91又说“以我们今天的人性论观点来看,荀子的‘性’论及其‘人之所以为人’的‘伪’论都应列入其人性学说的范围。”[4]92廖先生的观点值得肯定。可为什么荀子提出“伪”,并把知性不放置在性,而放置在伪中,还有待进一步解释。
首先,情性接物和知性接物的情况完全不同:情性接物产生出自然的或者是人为放大的心理情感和欲望,并没有把人和禽兽区分开来,揭示人的本质;而知性接物则反映人的主体性,“欲过之而动不及,心止之也”;人皆有欲,心可道而求,知性体现人的自由,使人超脱自然情性的捆绑,把人从自然的存在拯救出来,一跃成为道德的存在。质言之,情性及物并不创造道德,人依然只是自然的、实然的存在,而知性之动,使人有了转化为道德的、应然的存在的可能。可见,对荀子来说,使人伟大的并不是性本有的“善端”,而是“伪”;人性中最伟大的不是先天的善,而是知性在后天的运作。因此荀子提出伪的第一个理由便是突出知性的核心地位——知性揭示人的本质,显示人的尊严。
第二,知性和情性不同,情性一动,人仍然是动物性的存在,亦是自然存在;而知性一动,便是人为,便是自然界中独一无二的活动,是人所独有的。情性属于性,情性在经验层显露出喜怒哀乐好恶,算不得伪,仍然属于性。知性一方面是与生俱来的,属于性的范畴,但是知性一动,就立即是后天的人为,属于伪的范畴。这就是知性相比于情性的特殊性。知性因此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它与生俱来,乃是天之所生,属于性的范畴;另一方面当考察它在经验的自然显现和运作的时候,便立即属于人之所为,不再自然,而归属于伪。静时初始知性属于性,知性一动就属于伪,有了后天的工夫和成果,此一特性使荀子不得不提出“伪”。
“伪”不是一般意义的后天的人为,而是知性的活动,也即心为。“伪”最少有三重涵义:一是先天的能力(初始的伪):初始的认知、思虑能力、心对身体各官能的主宰能力,心能对治情;二是后天的工夫的伪(次级的伪)。此对应着人的次级知性。人人皆有初始的伪的能力,而伪在后天得到积累和锻炼,形成工夫的伪,此伪在个体中是有差异的,因“积”之多少、“精”之程度而不同。三是作为成果的伪,尤其是能伪礼义的伪。经过不断的积累、转化和创造,圣人可以伪礼义,而农商工匠只能伪出一般产品。“伪”同时具有先天性和后天性,是先天知性也是后天工夫和成果。作为能力的初始“伪”,承载着知性,不在性外;作为结果的“伪”,是客观的礼义或产品,乃是性外的。
“伪”概念集中反映了荀子天生人成的思想,将源自天的先天知性能力和源自人的后天知性活动统一起来。讨论荀子的人性思想,不能遗漏“伪”,“伪”恰是荀子人性思想的核心。“生理-心理”解释体系把知性“遗忘”了,《正名》篇的结构应该是把前经验的第一义的性作为统领,考察情性和知性在经验中的显现,分别对应第二义的性和第一义的伪。第一义的性是从天人之际立论,是前经验的,是后天经验之性的根据;进入经验层考察性是荀子思想的性格使然,也是荀子考察的重点,其所依循的是情性和知性,其中情性的经验显现就是第二义的性,而知性的经验显现,已经不能用性言之,因为知性一动已经属于人为了,所以知性的经验显现使荀子不得不提出“伪”。因此,“前经验的性-经验的情性-经验的知性”似乎更合乎荀子人性体系的本义。
四、可能的反驳与回应
当我们质疑“生理-心理”解释体系,而主张把知性也纳入荀子的人性理论中的时候,有学者也许会质疑,荀子在《性恶》篇所谈的性都是情、欲为内容的性,是放纵无节的性,可见知性和荀子人性的本义不兼容。他们可能会认为知性属于心,而不属于性。心和性对荀子来说,分属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可混同。如果性指的是《性恶》篇的性恶之性,那么我们是可以同意心、性分属不同的概念的。但是,如果我们通观《荀子》全书,则会得出不同见解:《解蔽》云:“凡以知,人之性也。”如果此性仅仅指的是情、欲,又何以能知?《性恶》:“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人人皆有的“知仁义法正之质”岂能在性外呢?《荣辱》篇:“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与“仁义法正”之质、具大体一致。《天论》云:“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天官、天君都是生而有之的。尤其是《性恶》云:“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何以耳闻目见的本能属于性,心知的本能却不属于性呢?综上所述,说知性不属于情性,不属于性恶之性,是可以成立的;但说知性不属于荀子整体的人性论则不能成立。说心不属于性恶之性,是可以成立的,但说心的先天认知等不属于荀子广义的性,则不能成立。学者过于强调性恶之性,就难免对其余各篇与其不同的人性思想视而不见。我们考察的是荀子的人性论整体而非《性恶》篇部分句段的性。
第二个回应是针对一种误解的。一种观点认为,荀子提出性、伪两个概念,性属于人性,伪不属于人性,因此考察人性论当然只能考察性,而不能把“伪”视为人性。其实,在荀子这里,性有特殊的用法,伪也有特殊的用法。考察性字的字源和本义,或者套用告子、孟子的性,是无从接近荀子性的本义的,因为荀子可能和当时人们所理解的性以及荀子之前的各思想家所理解的性均保持一定的距离。荀子的性的特殊处,就源自他提出了伪。性的意思,一旦和伪对举,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按照《性恶》的界定:“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后半句的“学而能”“事而成”,难道没有性吗?用荀子自己的例子,陶人埏埴为器,器是人伪出的,这里的伪难道不依靠心能学陶艺,心能积累技术经验,手能精巧地操作,心眼手能合一这些基本的人性吗?所以,所谓伪是就是人性的伪,并不是空的伪。一切形式的伪,就是各种形式的人性的后天生成,而非脱离人性的伪。也在这一意义上,一切伪背后可见各种人的先天本性,并以性为基础。伪是性的后天生成,并不是任意的、无基础的。伪是站在先天的性之上再进一步,是对天生之后加以人成之力。所以,伪中必有性,而性必没有伪。从性中无伪、伪中加入人成之力的角度看,性伪是严格区分的,有本质不同;从伪中有性,伪以天生的性为基础的角度看,性伪是合的,伪是性的再进一步。我们说,知性在伪,而伪中有性,是站在后者的角度,认为为先天之性加入人成之力的关键在于人的知性。
第三个疑问是知性、情性之外,还有材性、耳目鼻口之类的官能和其他先天本能,为何选择“知性-情性”二元结构来做分析的线索?对此我们的理由有三:
首先,正如前文所述,此二元结构是遍见于荀子《荣辱》《富国》《正名》《性恶》诸篇的。此外《儒效》篇有:“人无师法,则隆性矣;有师法,则隆积矣。”《礼论》亦有:“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礼义、师法皆非性,而是伪出,属于性-伪分结构,实际仍然是“情性-知性”二元结构。荀子的目标在于达成礼治,礼义、师法是成果,强学、积伪是工夫,而知性便是人性基础。舍知性则无思虑之心,无知道之心,亦无学习之可能。可见,没有知性就无所谓伪,无所谓礼义,无所谓礼治。虽然知性并不是唯一的要素,却是荀子人性论和道德、政治理论的核心。知性恰是克服情性超出礼义而致恶的力量,是发挥那些本在礼义标准以内的情感、欲望积极力量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情性-知性”二元结构是荀子思想极为重要的致思线索。
其次,虽然官能的感知是心形成经验和知识的必要条件,但官能的知觉并非人形成道德判断的主体。“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北大荀子注释组把“能”解释为:“人体官能”[9]368。“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梁启雄认为第一个能是本能,第二个能是才能[3]310。熊公哲认为第一个能是本能之能,第二个能是成功之能[10]449。本文无意于深辨“能”之确义,我们只需知道“能”并不做价值判断,而是受“心”的指令行动的。“心虑”而“能为之动”;心不“虑”而顺乎情性,“能”也“为之动”。情性和知性是可能主宰人的唯二系统,至于官能和其他本能只能是被主宰的。人从善还是由恶,在于情性和知性,而不在于诸“能”和感官。
最后,现代认知神经科学的实证研究日益凸显了情感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如,格林(Joshua D.Greene)认为人在做道德判断时,理性和情感都扮演了关键角色,处理道德难题时两者是相互竞争的[11]389-400。认知神经科学为道德判断的情感作用找到了生物学和神经基础,这对西方传统理性主义伦理学构成了挑战,而我国传统伦理学素来重视情感在道德判断和修养中的作用,我国传统伦理学理论在这一方面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支持。荀子的“情性-知性”二元结构与神经科学的实证研究存在暗合之处,用“情感-理性”结构作为线索去重思荀子无疑也是有意义的。
小结
对荀子来说,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有知性;知性一方面对治情性,一方面配合情,进而主宰“能”而为即是“伪”,因此也可以说“伪”是人之所以为人者。世上唯有人能“伪”,禽兽、草木、瓦石均不能“伪”。因此对荀子来说,性并非本质属性,而是待化待治者,是未完成者,而能完成人性的是知性在后天的运作,即“伪”。荀子人性论的全貌是,用第一义的性,作为各种人性事实的根据;然后考察经验层的情性和知性表现,最后归结为荀子最终的核心——礼义。因此,《正名》篇的“二性”和“二伪”是一个有机整体。以往考察人性多注重在“二性”,实际割裂了《正名》开篇这段话的整体意涵。毋宁说“人性论”这个概念对荀子不适用,更合适的说法是“性伪论”,也就是说,在荀子看来,对人性的考察不是对人性先天现成所予的性的静态考察,而是把性之所是与性之所能结合起来,强调性在后天之所能为——伪。尤其是荀子注意到了先天的知性如何在后天经验中发挥作用并引起了人类道德和礼义,因此,荀子的人性论超出了一般意义的人性论范畴,具有把先天之性和后天之“伪”融为一炉、将先天之性加以后天人成之力的性伪合一的特殊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