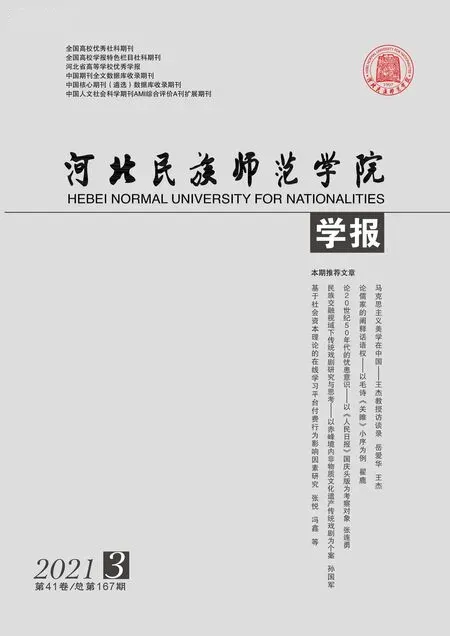论英诗汉译的继承与创新
——以彭斯《我的心在高原》九个新译本为例
2021-01-14王密卿吴雅丽
王密卿 吴雅丽
(河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罗伯特·彭斯(1759-1796)是苏格兰著名的民族诗人,也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上的先驱性人物。作为苏格兰本土农民诗人,虽未接受过系统的正规教育,但他却以天才般的灵感与独特的视角创作出了无数经典的诗篇,因此被誉为“有天赋的农夫”(heaven-taught ploughman)。彭斯热爱苏格兰的土地和人民,向往自由民主的生活。他通过巧妙的诗歌语言,把对故土独有的热忱与温情付诸于纸上,创作出了大量诸如《我的心在高原》等优秀爱国怀乡诗。《我的心在高原》是一首经典的故乡颂歌,诗人的心儿追随着奔跑中的麋鹿与野狍,回到了美丽的苏格兰北部高地上。全诗语言优美、行文流畅,不仅赞颂了高原上的山川丛流、人杰地灵,还展现了诗人深厚的民族情怀与真挚的爱国情意。自20世纪初彭斯诗歌首次被译介到中国学界以来,《我的心在高原》便受到了多位翻译名家的青睐。近年来,不断涌现的新译文更是扩大了该诗在学界的影响力。本文从中诗网选取了关恩亮、王成杰、晚枫、王毅、郁序新、于岚、张琼、赵宜忠、李正栓九位译者的《我的心在高原》最新汉译版本,对该诗的译介历史、译者们的翻译策略、翻译风格及亮点进行了比较分析,进一步探索了彭斯诗歌新译过程中的继承与创新。
一、《我的心在高原》译介历史
土地是农民生活的依托,国家是民族精神的保障。在《我的心在高原》中,彭斯对土地、对苏格兰山河的赞美与热爱渗透在诗歌的每一个字里。原诗如下:[1]
My Heart’s in the Highlands
My heart’s in the Highlands, my heart is not here;
My heart’s in the Highlands a-chasing the deer;
Chasing the wild deer, and following the roe,
My heart’s in the Highlands, wherever I go.
Farewell to the Highlands, farewell to the North,
The birth-place of valor, the country of worth;
Wherever I wander, wherever I rove,
The hills of the Highlands for ever I love.
Farewell to the mountains high cover’d with snow;
Farewell to the straths and green valleys below;
Farewell to the forests and wild-hanging woods;
Farewell to the torrents and loud-pouring floods.
My heart’s in the Highlands, my heart is not hear;
My heart’s in the Highlands a-chasing the deer;
Chasing the wild deer, and following the roe,
My heart’s in the Highlands, wherever I go.
这首诗赞颂的是苏格兰北部高原地区的美丽景色。彭斯年轻时曾到这里游历,被高地上分裂的高原、奇峻的峡谷、清澈的流水和壮丽的湖泊深深吸引。这里是欧洲风景最优美的地区之一,也是苏格兰英豪的出生之地。全诗共四节,每节四行,诗行整饬,音韵流畅。诗人首句便直抒胸臆,“我的心在高原,不在此时此处”。它热烈跳动着,跟随着同样活泼悦动的小鹿奔跑在记忆里的高原上。接下来,通过具体意象的陈列,诗歌营造出如同电影剪影切换般的场景,情感上层层递进。尾行看似与首行重复相似,实际另有深意。首尾相连的结构如同一个稳定、闭合的圆环,如此精巧的结构安排体现了诗歌语言独特的美感。
《我的心在高原》的译介历史与彭斯诗歌的中国译介发展史息息相关。受晚清西学东渐的影响,来自国外的翻译文学骤然闯入国人的世界。20世纪早期的彭斯作品译介专注于诗歌中民主主义、自由博爱精神的宣扬[2]。该时代的译者们受限于中国传统诗学文化语境的影响,译诗多采用古体诗形式,内容大多不离原意,但对原诗语言、风格的把握稍有不实。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的普及给外国文学译介带来了新的机遇。旧有的文化翻译范式受到冲击,新的文化翻译体系开始建立。于是,彭斯诗歌的译者开始关注原诗的意义表达以求达到“信”的翻译实践标准。此时的译文无论是在内容、句式还是在音律上都更加贴近原文,做到了忠实原诗精神。1944年,诗人袁水拍在《中原》杂志上发表了“彭斯诗十首”译文,并从数百首诗作中精心挑选了30首彭斯经典诗歌翻译成册,出版了第一部彭斯个人译诗集《我的心呀,在高原》。以《我的心呀,在高原》命名诗集意义颇深,一方面该诗立意深刻、朗朗上口,是彭斯爱国诗篇里的经典佳作;另一方面,同红玫瑰般的爱情相比,诗歌所体现的民族情怀、爱国精神是更为深厚的群体情感,能够激发国民斗志,产生民族共鸣。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对彭斯诗歌的关注热度不减。1959年,王佐良、袁可嘉两位学者为纪念彭斯诞辰200周年,响应中国的新民歌运动,分别出版了译诗集《彭斯诗选》[3]与《彭斯诗抄》。王佐良、袁可嘉的这两本译诗集都重新选译了具有较强凝聚力的诗歌《我的心在高原》,他们的诗歌译文不仅忠实通顺、深情炙热,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苏格兰民歌独有的艺术特色,避免了翻译腔和语言生硬等问题,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80年代后期至今,随着“文学主体性”思想观念深入人心,“带着镣铐跳舞”的时代已经过去。译诗着重表现在语言层面上的审视和翻译思想的转换,更加尊重原作所承载的内涵[4]。因此译者也可以不再受传统诗学、时代特色及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的束缚,能够进行“雅”的探索,现代诗歌译作的艺术魅力及创造张力得以展现。2016年,李正栓出版了诗歌译著《彭斯诗歌精选(英汉对照)》,再次重译了这首诗歌,推动了彭斯诗歌译介在中国的发展。2020年,由中诗网主办的第二十六期“英诗同题翻译活动”征集到了大量关于My heart’s in the Highlands优秀诗歌译稿,本文所比较分析的九个最新汉译本也选材于此。
二、《我的心在高原》诗歌新译中的继承
诗歌翻译是一门艺术创作,它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相互沟通的结果,更深层次地涉及不同文化间与思想间的交流碰撞。由于译者们本身具有时代性和独立的文化审美能力,因此文学翻译活动并不是简单机械的模仿与复制,而是一个在继承与发展中不断焕发生命力的过程。此次彭斯诗歌新译“竞赛”接下了彭斯经典翻译最新一轮的接力棒,吸引了海内外多位译者积极参与。译者们在继承“忠实通顺”的翻译原则之上,完整保留诗歌原意、传达诗人情感,对原作的语言风格、目标读者的审美期待等方面都进行了全面审视,创作了诸多有价值、有亮点的优秀译文。
忠实原则一直是中英文本互译的第一原则,也是评价译作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翻译家林语堂认为,翻译忠实观里的“忠实”是指译者要对原文负责。这并非要求译文与原文逐字逐句完全对应,而是需要充分理解原文、考虑文化间的背景与差异,灵活处理译文[5]。在《我的心在高原》的九个新译本中,译者关于“忠实”标准的体悟首先体现在对原诗字与句的推敲琢磨之中。以诗歌标题“My Heart's in the Highlands”中介词“in”的翻译理解为例,“in”是英语中常见介词,本意为在…里面、以…方式。多数译者如郁序新、晚枫等选择忠实原诗,保留“in”的原意,译为“吾心在高原”“我的心在(苏格兰)高原”。译文中的“在”字不仅在语言层面上强调心存在的位置,还突出了“in”作为方位介词的语法作用。译者王毅细心揣摩诗歌原意,将“in”处理为“向”,译文为“心向高原”。心向高原的“向”字取向往、偏向之意,在地理上区分了诗人与高原之间的物理距离。诗人虽然身在异乡,心却向往着高原上的美景,于是思绪开始跟随着奔跑的小鹿回到那片广袤的土地,这进一步凸显了他对高原的怀恋与渴望之情。同样具有深意的译文还有赵宜忠的“心驻高原”。“驻”,止也,指主观上的停留而不愿离去,该字的妙处在于译者关注到诗人在时间维度上动态的情感变化,从初次游历高原到如今的深切思念,诗人的身虽远离,但心却长驻与此,与高原上的美景同游同在;译者王成杰选择活用“系”字寄托情思,将之译作“魂系高原”。“系”字原指捆绑、系绊,也有牵挂、系恋之意。译者在这里一语双关,巧妙地将两个主体用“系”字捆绑相连,于是诗人与高原之间天然的联系跃然纸上,之后的魂游故地也显得顺理成章。此外,王成杰并未将诗题中的“heart”译为“心”,考虑到目标读者的阅读感受,将之处理为“魂”。与西方文化中的“ghost”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魂”指附于人体的精神灵气,它可脱离空间限制,代替肉身游于体外。“魂牵梦萦”“梦魂萦绕”都是魂游的体现,常常用来形容人对某物或某地心之所向、日夜牵挂,进而达到痴迷的地步。在这里,译者灵活运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使用一个“魂”字贯穿全文,既生动又达意。
在盛赞了高原丰饶的土地之后,诗歌第二节开始渐入主题,关注到苏格兰北部英雄的人民。诗歌第二节第一句写道“Farewell to the Highlands, farewell to the North, The birth-place of valor, the country of worth”[1]。译者李正栓的译文为:再见吧,高原,再见吧,北方,你是品德的家园,是勇士的故乡;译者王毅的译文为:后会有期,高原北方,人杰之地,物华之乡;王成杰的译文为:别我高原,别我朔方,勇者故土,美善之邦;关恩亮的译文为:再见了高原,再见了北方,这勇武之地,这财富之乡[6]。从内容上看,这四个译本在选词和风格上都各有特点。在选词上,诗人抛砖引玉,通过大量重复“farewell”以抒解其钦慕之意。“farewell”是英文中正式的告别之辞,常用于诗歌或书面语中。李正栓在忠实对等[7]的前提下,保留了“farewell”原意,将之直译为“再见吧”。再见是与原文相对应的中文书面告别语,无论是在翻译风格还是情感深度上都与原诗对等,再加上语气词“吧”的使用,诗歌情感中的哀伤以及些许叹惋之意跃然纸上。译文“再见吧”既抒发了诗人对高原美景、北方英雄的热爱与怀念,又表达了其身处异地难以返乡的无奈与释然,读起来通顺自然;译者王毅对原诗语序稍作调整,将两个“farewell”合并提前,译为“后会有期”,使得抒情对象“高原”与“北方”得以独立成句,形式十分新颖。成语“后会有期”是分别时的安慰之词,常指短暂的离别,暗示还有再见面的机会。诗人能否故地重游暂且不提,译文“后会有期”更多带来的是一份慰藉与期待,足以体现诗人对高原的不舍与深深的眷恋之情。译者王成杰的译文只取“别”字,简洁明了。他选词讲究,将“north”处理为“朔方”(北方),译诗风格偏向古体,使得他的译文不仅忠实原文,还颇具中文的语言美感。此外,四位译者对诗句“the country of worth”中“worth”的理解也不尽相同。“worth”本意为价值、财产。李正栓、王成杰认为,这里的“价值”应该承接上文的“valor”(勇气),暗指伦理层面也就是品德上的高尚,精神上的价值。李正栓的译文“你是品德的家园”可谓善美。“家园”与“故乡”相互对应,都是美好品质的起源以及出生之地。译者通过使用重复的修辞手法再次强调“家”的概念,这不仅暗示了高原人民高尚的精神世界,还传递了诗人“高原即家园”的重要情感思想。王成杰将之译为“美善之邦”也是出于对品德价值的考虑。美善是中国文化中最高的道德评价,用来形容高原之德十分恰当。译者王毅、关恩亮则更加赞同“worth”为财力、物质价值。他们认为,前文已经提到勇气的精神,后文的价值应特指物质层面也就是经济上的丰饶。王毅的译文为“物华之乡”,关恩亮的译文为“财富之乡”。两位译者都取其物质丰饶之意,这也有迹可依。原诗第一节便细致地描写了高原上奔跑的野鹿和狍子,随之第三节诗人又详尽地罗列出高山、丛林、石瀑、泉水,这些都是生命的象征、生物多样性的体现,译者取物质价值之意合情合理。笔者认为,无论是精神价值还是物质价值,都有可取、可学、可评、可点之处,并没有违背原诗本意。在诗歌新译的过程中,译者可以在忠实原诗内容的基础上,发挥其独立性、自主性;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可归化也可异化,尽量做到灵活处理译文。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们对诗歌情感的还原再现也是继承忠实原则的重要体现。苏格兰北部高原地区是彭斯歌唱的地方,这里不仅是英雄的诞生地,还是“我”心中的家乡。于是,彭斯继续写到:“Wherever I wander, wherever I rove, The hills of the Highlands for ever I love.”[1]无论在何处徘徊,在何处徜徉,高原群山永远印在心上。这里是诗人的感情高潮,他将永恒的热爱留存于字里行间,让这不朽的情感得以在世间传唱。郁序新的译文“任凭吾漂泊,任凭吾流浪,高原之群峦,永爱吾心上”,[6]清新洒脱、气势磅礴。“Wherever”译作“任凭”,有一股不怕击打,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气势。“Hills”在此译为“群峦”,译出了“s”(复数)可谓精准。与此同时,译者巧妙地调整原诗语序,译文将“永爱”提前,情感上更加强调了高原在“吾”心中的首要位置。王毅的译文:“无论海角,无论天涯,高原群山,心之所向”,则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省译了“wander”“rove”的内容,而使用“天涯海角”来描述自己即使身处极端之境、心仍忠于这里。成语“天涯海角”家喻户晓,意为极遥远的地方。早时用来表达一种乡土情节,具有丰富的中国文化内涵。使用了相同翻译策略的还有译者赵忠宜,在处理诗句“The hills of the Highlands for ever I love”时,赵忠宜使用了中国读者所熟知的成语“天长地久”来诠释“永恒”的概念。“天长地久”指与天、地的存在的时间一样,多用来形容永久不变的感情。由此可见,归化翻译策略的巧用不仅忠实地传达出了原诗的情感,还有助于帮助目标语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增强诗歌欣赏性和可读性。综上所述,在诗歌情感的体悟方面,译者们能够充分理解原诗意义、揣摩诗人创作心理,将诗歌的情感融入中国语言,这样既保留了原诗真情实感,也体现了中国文字之美。
三、《我的心在高原》诗歌新译中的创新
诗歌风格是诗人将对语言和美的独特感知转化为个人创作的体现。诗人赋予诗歌独有风格,同样译者也赋予译文其特有的风格。《我的心在高原》是彭斯以其擅长的苏格兰方言写成,具有深厚的民族艺术特色。全诗大量使用了重复、对照、排比等修辞手法,将诗人对故乡深刻的热爱与眷恋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外,诗歌的节奏鲜明、语言流畅自然、体裁偏民歌形式,十分适合吟唱。在《我的心在高原》诗歌翻译实践中,译者们在形式上进行了创新,充分体现了诗歌译文的“形式美”。诗歌“形式美”指译文诗歌的内部结构之美,包括诗歌的段落数、字数等等,能在视觉上令读者“乐之”。与外国诗歌不同,中文诗歌按照形式可分为古体诗、近体诗、新诗(白话诗)等。古体诗包括古代诗、楚辞与乐府诗,形式押韵较自由;近体诗又叫格律诗,形成于初唐之后,对诗歌的平仄、对仗和押韵等都有严格的要求;五四运动以后的新诗则选择用白话文创作,不拘束于字句的长短,打破了旧时传统格律的限制。在《我的心在高原》的九个新译本中,译者于岚、王成杰、赵宜忠选择了用古体诗或格律诗进行创作,张琼、晚枫、关恩亮、郁序新、李正栓五位译者则采用了白话诗诠释原诗。
译者于岚选择用古体形式译诗。由于原文诗歌每行基本上有十一个音节,若以六音节、五音节分为前后翻译,读之便与带“兮”字的“屈原体”很是相似,颇有“楚辞之风”。以诗歌的第三节为例,于岚的译文为:“依依告别高山兮,雪之所覆。依依告别山地兮,葱葱绿谷。依依告别丛林兮,野木森森。依依告别激流兮,虎啸龙吟[6]。”该译文视之则诗行齐整、读之则气势磅礴。译者在充分尊重诗歌原意的前提下,灵活使用古体“骚体”创作,形式上可谓创新,令人眼前一亮。王成杰、赵宜忠两位译者均选择使用格律诗体来诠释此诗,四字格律形式语言简洁、凝练,读起来朗朗上口,颇有诗经的美感。王成杰认为四言格律诗具有回环往复、一咏三叹等特点,能够更好体现原诗的音韵。但是,格律诗也会受到律诗字数和平仄的限制,需要调整句序,灵活地进行增译和减译,而对于原作修辞和回环结构应尽量保留。关恩亮、李正栓等译者则认为白话诗体更符合彭斯“农民诗人”的文学身份,也能够更好地保存彭斯诗歌里的民歌元素。值得一提的是,译者关恩亮并未将诗分节分段,他的诗行句完整、一气呵成。从内容上看,译文语言精准、朴实,忠实诗歌原意也没有过多的赘述,从形式上看,诗句里长句短句结合、相间,前五句为短句,第六、七、八句译为长句,式样上好似高原上连绵起伏的山峦,令人影响深刻。关恩亮的部分译文如下:
我的心在高原上
我的心不在这里
我的心在高原上逐鹿
追寻那野鹿香獐
无论我走到哪里
我的心都在那高原上
再见了高原,再见了北方
这勇武之地,这财富之乡
无论我在哪里徘徊
无论我流落何方
我永远热爱那高原的山冈。
此外,为保留诗歌的民歌特色,译者们还灵活使用了“啊”“吧”“呀”等语气助词。这些语气叹词在句中起到了标记停顿,弥补译介缺失并忠实传达诗人情感的作用。以李正栓的第一节译文为例:“我的心啊在高原,我的心不在这里;我的心啊在高原,追逐着鹿群。”在译文中译者使用了感叹词“啊”来传达诗人高涨的民族情绪。短促的“a”音强调了前文存在的主体对象,保留了原诗的深厚的情感,使得情绪在此酝酿回转,等待着新一轮的释放。
除此之外,独特的音韵美也是此次彭斯诗歌新译的一大亮点。诗歌语言的音乐性除了表现为有强烈的节奏外,还在于它有优美悦耳的韵律[8]。诗与乐虽属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却在起源和性质上相接近。音乐用声音传达情感,诗歌用语言传达情感,二者甚至可以相辅相成,通过“节奏”[9]谱写一场“诗”与“歌”盛宴。音律是彭斯诗歌的灵魂,他的诗歌几乎每一首都可用于传唱,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应注意诗歌的韵律,尽量保留诗歌“音韵美”。《我的心在高原》富有鲜明的音乐性和节奏性。全诗共四节十六行,每行约十一个音节,节奏上大致属于是四音步抑抑扬格,全诗韵脚为aabb/ccdd/bbee/aabb。与此同时,诗人还大量使用“重复格”的修辞手法,加强了诗歌的音乐性。在《我的心在高原》九个新译本中,译者晚枫保留了原诗的韵律样式,译诗的韵脚与原诗基本一致。其它几位译者虽未完全遵循原诗的格律,在诗歌韵律上也颇下功夫,力求保留了诗歌的音韵美。值得注意的是,译者郁序新、赵宜忠还灵活运用了叠词以增强译文诗歌的韵律感。叠词并不是简单的文字重复,它可模拟声音、模拟颜色,也可模拟事物的状态。恰当运用叠词可使译文诗歌中的描述对象更加确切化、形象化、生动化。在诗歌第三节的翻译处理上,译者郁序新巧用四对叠词来描绘高原上具体的景物,译文如下:“辞别那高原,你白雪茫茫,辞别那壑谷,你绿色葱葱,辞别那森林,你叶茂煌煌,辞别那川流,你洪湍隆隆!”。“茫茫”白雪摹写了高原群山上的皑皑堆积的白雪,从侧面描写出雪的颜色与厚度;“葱葱”壑谷摹写了高原幽谷的深与绿;“煌煌”表现出森林树叶蓬勃向上的生命力;而“隆隆”更是生动摹写了洪湍激流隆隆的声响,让人有身临其境、逼真之感。无独有偶,译者赵宜忠同样选择用叠词表现诗人情感,他的译文“别了高山,皑雪茫茫。别了河谷,碧涧苍苍。别了森林,丛林荡荡。别了山洪,波涛汤汤”语言更加简洁、凝练。通过描写高山上的皑雪、河谷中的碧涧、森林与丛林、山洪里的波涛,他用更少的语言精准表达出了对象的状态及对象间的从属关系,再加上叠词的灵活运用,增加了诗歌的动态感,使译文具有更强的艺术性。
结语
土地是人民的归属,是人民生命中抹不去的烙印。《我的心在高原》是罗伯特·彭斯歌颂苏格兰、歌颂高原土地的代表之作。全诗内容丰富、感情真挚,不仅传递了诗歌的语言之美,更深刻激发了那片土地上人民的爱国之心。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学者们开始广泛关注并译介彭斯诗歌,这不仅是因为他朴实的农民身份、高超的语言艺术,还有他忠实国家、热爱本地文化、敢于讽诫、敢于抗争的精神。诗歌《我的心在高原》拥一段有丰富而悠久的译介传播史,从早期的古体诗风格到中期忠实原诗的白话文诗体,再到如今多样化的诠释,彭斯的诗歌译文逐渐从青涩走向成熟,从单一走向多面。在这个过程中,译者们勇于承担时代使命,不断探索、成长,创作出了无数优秀的译本。本文所摘选的九个彭斯新译文本继承了前人“忠实通顺”的翻译原则,在形式上追求创新,音律上追求完满和谐,译文令人赏心悦目。值得一提的是,译者们还以文化使者的身份将彭斯的爱国之火传递到了当代,实在可敬可叹。在全球化趋向成为定局的今天,爱国主义、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已经是现代人必备的精神品质。因此,彭斯的诗歌创作在给予读者美的享受的同时,也给予了他们精神上的供养,这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