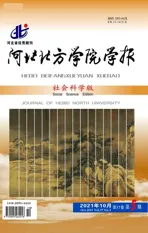后唐大赦及其效果论析
2021-01-12韩新芝
韩 新 芝
(安徽大学 历史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后唐是原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存勖建立的王朝,自同光元年(923)十月到清泰三年(936)十一月,共存在13年。后唐初年国力强盛,北抗契丹,西服秦岐政权,西南灭前蜀,唐明宗时号称“小康”。然内部纷争不断,终为后晋所灭。为缓和矛盾,安抚民心,后唐多次颁行大赦之诏。
一、后唐大赦的颁布
后唐历经4帝,13年间共施行7次大赦,其中:庄宗2次,明宗3次,闵帝和废帝各1次。五代时期,由于皇帝多以武力取得皇位,因此局势动荡不安。后唐大赦多在皇帝即位、改元和南郊时施行。
(一)庄宗即位改元大赦
后唐庄宗于同光元年(923)和同光二年(924)两次施行的大赦成为证明后唐建国正统性和处置后梁伪官的重要手段。同光元年(923)四月,庄宗称帝,“大赦,改元”[1]44,此次大赦成为构建后唐政权正统性的重要一步。为证明政权的正统性,庄宗父子除否定伪梁正统外,还不断弱化其沙陀特征,以李唐宗室身份积累政治资本。通过沿用李唐正朔,“求访本朝衣冠”[1]812与宦官遗绪入外朝内廷的方式继承李唐的政治遗产。天祐十八年(921)正月,在炮制出李唐玉玺重新现世和诸镇三上表劝进[2]397-398事件后,又经过两年筹备,李存勖以李唐继统者的身份于魏州即位,定国号为“唐”,史称“后唐”,并实施大赦[2]402-403。作为构建其政权正统性的关键一步,庄宗在赦文中对后唐政权的正统性和其本人即位的正当性进行了全面总结,着重宣扬了其行军事吞并目的在于“誓雪耻于君亲,欲再安于庙社”[1]1013,建国则是“籍系郑王,志存唐室,合中兴于景祚,须再造于洪基”[3]1013,并“改天祐二十年为同光二年(924)”[3]1013,大赦天下。然而后梁尚在,两者皆宣称自己为李唐正统继承者,可见一场即位大赦并不能充分证明后唐政权的正统性。
(二)庄宗南郊大赦
同光二年(924)二月,“已巳朔,(庄宗)有事于南郊,大赦”[1]47,进一步强化其政权的正统性,并处理后梁官员。同年十月,身处弱势的李存勖对后梁首都汴梁实施偷袭,击败了与后唐对峙十数年的后梁。在北方,后唐暂时成为唐王朝基业的唯一合法继承人。此时,如何加强后唐政权合法性以及处理伪梁官员成为后唐面临的重要问题。在文人精英支持下,隆重的南郊大赦成为庄宗的首要选择。同光二年(924),一场煊赫的祭天仪式于南郊举行,祭祀流程大体遵照李唐旧例。南郊与大赦的结合具有重大的政治宣传效应,它不仅是君权神授的体现,也是儒家所推重的皇帝以“仁政”与“礼法”治国的体现,在知识精英与百姓间具有极强的舆论效果。大赦不仅针对普通百姓,更是对后梁官员既往不咎的政治宽宥。通过大赦和后续对后梁官员的任命,庄宗成功地把后梁官员吸纳至自己的统治集团中。郊天与大赦相结合使后唐把对继承李唐合法性的证明变为一场全天下的狂欢。
(三)明宗即位改元大赦
在庄宗初步巩固了后唐政权后,证明即位的正当性及稳定政局成为后继皇帝的重要任务。随着政局的变化,明宗分别以即位、南郊和册尊号为由3次施行大赦。
天成元年(926)四月,“甲寅,大赦,改元”[1]56,此次大赦是明宗证明其即位合法性和重整政局的重要步骤。同光三年(925),庄宗对伐蜀功臣郭崇韬及其亲故老将的血腥残杀使政局不断恶化,并波及全国。河北驻军叛乱后,镇压叛乱的李嗣源反而与叛军合作,挥师回朝夺取政权。进入洛阳后,在文官集团与太后和明宗3方合作下,明宗策划了一种证明其合法性的即位方式:首先,在太后的支持下以监国推让帝位,表示其对皇位并无觊觎;其次,“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礼”[2]8993以示其得位之正;最后,在文臣集团辅助下,称“朕昔奉武皇,而幼承明训”[3]1019,举兵不过为“冀成于靖乱”[3]1019,即位不过是“群情见迫,众意相推”[3]1019,以强调其在继承皇位上有绝对的合法性。明宗并非合法即位,朝野人心不定,地方节度使多有反心。面对乱局,明宗即位后想重设匦函,谏议大夫萧希甫建言:“匦函一出,投诉必多,至于功臣贵戚,有不得绳之以法者。”[1]315于是,明宗诏令天成元年(926)四月二十八日昧爽以前,大辟以上,皆赦除之,然后出匦函以示众。唐明宗是五代少有的明君,然五代特殊的社会环境决定了统治阶层的腐朽,唐明宗实行大赦不仅是对下层的宽恕,更是对统治阶层的保护。大赦避免了上层的政治动荡,为重整朝纲重奠新基。
(四)明宗南郊大赦
长兴元年(930)二月“乙卯,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1]61,此为明宗施行的第二次大赦。此次南郊大赦是在冯道等文臣的熏陶下,明宗对郊天的重要性有了一定了解后进行的,除为宣扬其即位乃膺受天命外,亦在于震慑地方。与受中原文化浸染较深、熟悉中原体制及正统意识浓厚的庄宗不同,戎马出身的后唐明宗目不识丁,对中原文物制度缺乏了解。明宗登基时于庄宗柩前行即位礼,并未行郊天礼。明宗即位后,冯道和赵凤等文臣精英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进入政治核心,在冯道等的潜移默化下,明宗渐知天命对君王即位的重要性。此外,占据东西两川的董璋和孟知祥专横跋扈,借助南郊大礼向两川征收助礼钱以削弱两川势力也是重要原因。天成四年(929年),明宗以南郊为藉口“令西川献钱一百万缗,东川五十万缗”[1]799。在南郊赦文中,明宗首次把其即位与天命相联系,强调其即位乃是“上承玄祐”,“下念黔黎”[3]1023。
(五)明宗加尊号大赦
长兴四年(933),明宗加尊号并于“八月戊申,大赦”[1]65,此次大赦有两重意蕴,一则夸耀功绩,一则稳定政局。明宗在位时期兴利除弊,创造了自唐末离乱后难得的“小康”之局,正如其在诏书中所言:“革彼积弊,成斯小康。”[3]1024然而,当时局势也如厝火积薪。将藩镇精兵收归中央禁军虽稍损藩镇兵力,但也导致明宗后期禁军骄横。禁军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巩固皇权,震慑地方,但相比藩镇军队,由于禁军更迫近腹心,因此对中央的威胁也更大。在政治上,内有王淑妃与孟汉琼用事,外有两川孟知祥谋求自立,加之东北契丹屡欲入寇,河西诸镇阴藏勾结契丹之志,银、夏诸镇李彝超不奉朝命,天下人心骚动,稳定政局迫在眉睫。面对内外困顿的局势,明宗借加尊号实施大赦以重振皇威,抚绥人心。
(六)闵帝改元大赦
闵帝是后唐唯一一个以正当方式即位的帝王,其即位大赦更多的是一种例行公事。闵帝于应顺元年(934)正月“戊寅,大赦,改元,用乐”[1]70。
(七)废帝改元大赦
应顺元年(934)四月,潞王李从珂入洛阳监国,随后即位称帝,“乙酉,大赦,改元”[1]72,定年号为清泰。李从珂与明宗相似,皆是以先皇义子的身份通过武力夺得大位。但与依靠地方藩镇即位的明宗不同,李从珂是借助禁军军乱夺得皇位。清泰元年(934),从厚即位,主少国疑。从厚与从珂上下猜阻。从珂以朱弘昭等“乘先帝疾亟,杀长立少”[4]9015妄图倾覆社稷为名清君侧,禁军累降,又得康义诚以禁兵迎降和曹太后废帝令其监国乃得皇位,其皇位也来之不正。于明宗末期出现的禁军之害到末帝之时也发展至顶峰,当时的形势较长兴末年更为不稳,安抚禁军和普通百姓势在必行。因此,末帝迫切需要实施大赦以稳定政局。
二、后唐大赦的政治背景
后唐先后施行7次大赦,政令频繁。虽然后唐中央政府对大赦大力宣传,不断完善大赦条目并申饬地方执行大赦命令,以保证大赦的贯彻执行。但整体而言,地方权力格局的改变和中央权威的削弱极大影响了大赦的贯彻落实。
(一)后唐执行大赦的政治推力
为保障大赦的实施,一方面后唐中央政府借助政治力量使大赦信息能够迅速地传达到地方,另一方面敦促地方政府向百姓宣传大赦信息,并执行大赦政令。
地方是否贯彻朝廷旨意和百姓能否及时了解朝廷旨意都仰赖信息的通达。在唐五代中央与地方的沟通中,传驿为传递文书的重要机构。后唐战乱频繁,军机要务紧切重大,政府对驿站的建设较为重视。同光元年(923),郓州大胜,明宗飞驿告捷[3]602;天成二年(927)九月己亥,明宗令即日驰驿赐任圜自尽[3]5182,这些均可证明驿站在后唐仍是重要的通信渠道。为保证赦书的时效性,后唐政府通过传驿使“赦书日行五百里”[3]1024,以便大赦信息可以迅速传达至地方。
对大赦进行宣传,使百姓知悉赦书也是政府保证大赦实施的重要一环。后唐政府在州县的驿铺、渡津、山谷及道口设立粉壁,以张贴诏敕[3]414。大赦时,朝廷除把大赦消息由中央下达到地方政府外,还要求地方官员于要道关津等消息通达之处的榜壁之上张贴赦书,使普通百姓知悉。天成元年(926)四月,在明宗即位赦书中即要求“条件仍于要路牓壁,贵示众多”[3]1020。
为保证大赦能迅速实施,后唐政府明确规定赦书到达地方后“限一月内便需施行,不得遗漏”[3]1020。中央政府在实施大赦时还不断对其内容进行完善,若赦文中有条款未详该者“即仰所司条件录奏”[3]1014。为敦促地方执行大赦,明宗多次下《谕三京诸州府敕》[4]630等敕书申饬地方长吏遵照赦书施行大赦,不可挠阻。为避免中央及地方政府受赦前状词,皇帝除数下敕书禁止诸道、州和府受理关涉赦前之事外,还规定后唐建国以来所颁发的赦书、德音,御史台及三京、诸道、州、府等受理状词之场所皆须“具此令文榜壁,各令详审,无致逾违”[6]656,如公然受理赦书、德音及恩敕前事,则处理案状的官府“并当勘责,以故违敕命律格科罪”[6]656。
(二)后唐执行大赦的政治阻力
大赦的执行需中央和地方相互协作,地方是否配合中央是大赦能否贯彻落实的关键。传统行政制度的隳坏、行政流程的废弛和地方权力构成的变化使中央失去了对地方的掌控,大赦在实施中阻力颇大。
1.政府机构废弛,官员素质低下
自唐朝起,大赦在推恩功能外又发展出了申禁功能,大赦成为国家处理政务和厘革时弊的重要手段。赦书的庞杂繁复决定了只有依靠政令贯通的政府机构和政务娴熟的地方官员才能对其贯彻落实。后唐政治机构的废弛和地方官员的素质低下使大赦难以贯彻。
一方面,在大赦所涉及的公文传递、判署和执行等各环节中,政府军政系统、司法系统和监察系统均牵涉在内,大赦的实施需要中央和地方各机构之间保持政令贯通。大赦执行时,中央大理寺、刑部和监察院以及地方道、州、县等不同机构之间需要进行大量的文书和人员往来,程序复杂。然而,由于自唐末以来持续战乱,后唐政府机构“诸司减丧人吏,曹局亡失簿书”[3]5381,以至“官坏政荒,因循未补”,“官僚中有不知所掌之事者”[3]5381,人手缺乏和机构职能废弛使中央及地方各机构之间很难进行高效的政务沟通。
另一方面,官员素质低下也阻碍了大赦的实施。赦文作为国家政务的纲领性文件,条目往往流于简略,在具体施行时需要地方官员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权变。且涉及内容复杂,需官员娴熟朝廷条文规制,谙于政务方能应对。仅赦罪一项便极为繁杂,就罪犯处理而言需要判定已发觉、未发觉、已结竟和未结竟几种情况。对罪犯赦免时需考虑罪犯的主刑和从刑关系,如罪犯所犯之罪需除名和免官等,遇赦后仍除名和免官;罪犯在赦罪后能补救或改正的仍需补救或改正,如同姓为婚或其为婚扰乱人伦者“虽会赦,各离之”[5]1034。然而,与繁重的事务相抵牾的是负责执行大赦的地方官员来源杂芜且素质低下,以至地方政府多为小吏弄权。州县长官多为藩镇节帅弄权所设的试摄官,“大抵武夫悍卒,皆不知书,必自署亲吏代判,郡政一以委之,多擅权不法”[6]150,官员“既不拘于考绩,惟掊敛于资财”[3]8757。后唐地方官员难以承担如此繁重的大赦任务,导致在实施大赦时“官吏但习旧风,百姓罔知亲命”[3]1020。
2.藩镇及军将专横任情
唐末五代时期,道、州、县三级行政取代州、县二级行政机制,节度使和观察使成为地方政务的实际掌管者,节度使在地方拥有独立的权力空间,道成为朝廷政令下达的关键环节。然而,中央和地方利益分歧的增大和地方权力格局的改变使大赦难以在地方顺利施行。
一方面,道掌握了专奏权。在中国古代金字塔模式的官僚体系中,政令的运行依托于一整套文书系统。在后唐,地方藩镇通过其所掌握的进奏院基本垄断了地方与中央的沟通渠道。同光初,庄宗重申了“制敕不下支郡,牧守不专奏陈”[4]8825的原则,道成为传达中央政令和接受地方信息反馈的关键环节。中央文书需通过道一级方可继续下达州县,赦书亦是如此,它使中央赦令需经过节度观察使等的下达方能进一步施行。尽管后唐中央政府在宣布赦书时多次强调“赦书所至,仰三司诸道丁宁宣布,限一月内便须施行,不得遗漏”[3]1020,然并无成效,藩镇长官多稽留赦书,“不与宣行”[3]1020。道一级对于信息的垄断也使地方州县官员无法越过他们进奏中央,这加重了中央和地方信息的不对称程度,大赦的实施情况难以通过地方反馈至中央。
另一方面,藩镇长官通过实力攫取了本属中央的官员任免权。州县官员受藩镇限制远大于中央,节度使等以自身政治利益为导向,对大赦进行有选择性的实施。在后唐居轻驭重的政局下,“诸道多是各列官衔,便措州县”[3]7603,节度使等地方长官对所属支郡的委任权被正当化,如“张全义为(河南)尹,县令多出其门,全义厮养蓄之”[1]249。大赦等朝廷政令落实的基层——县一级行政区划亦被破坏,镇将和县令一起成为地方政务的掌管者,出任镇将者多为藩镇州将的腹心将校[9]72-75。实力强盛的藩镇甚至可以逼迫中央以获得行墨制的权力,全权掌管地方事务。李克用之婿孟知祥占据两川后即通过威逼明宗获得权行墨制的权力[6]626。地方权力格局的改变和道对中央离心力的增强使地方在施政时以增强自身力量为导向,在“兴亡以兵”[1]279的政治局势下不恤民事,专务聚敛成为后唐地方政治的重要特征。州县官员在节度使和观察使等的压迫下或与道亦步亦趋,或“不务守官,咸思避事”[3]5379。节度使等地方官以自身利益为导向对来自中央的大赦条令在地方有选择地施行,如天成元年(926)大赦中规定“应随驾并内外将校职员许奏名衔”[6]644,此项条目虽奏荐人数极多且已施行数载,但仍尚有官员奏陈乞恩,有关民生的赦文或被“迟留稽改,利在虐人”[3]1020,或“多因州使倖门,淹留敕命,或公然隐匿,全不施行”[3]1020。
3.中央权力的衰落和对地方的妥协
中央监察职能的弱化和中央在权衡之下对地方的妥协也使大赦难以贯彻。后唐中央政府努力改善文治,完善政府职能,试图通过重振中央监察系统来加强对地方官员的掌控。同光二年(924)五月,御史台奏请恢复御史台的分察功能,“当司六察合行职务条例”,重新担负起察访网举中央和地方官员之责。而御史台“刑察应刑部,司法律、赦书、德音,流贬量移、断罪重轻合报察使”[6]344的职责使其在大赦施行时需对官员“严加访察,无纵稽留”[3]1024。然而,皇权的衰微使依托皇权开展工作的朝廷监察体系实际上难以发挥作用。后唐御史台官员多迂阔懦弱,尸位素餐,且人吏常常缺额,导致公事废弛。除中央监察系统外,后唐的考校系统亦徒具虚名。后唐政府虽每年令有司明定考校,然而“两班考绩,虚有其名”[3]7357。由于中央鞭长莫及,藩镇、州、县内部负有监察职能的军事判官、州县判官与主簿等也选择包庇地方官员。中央和地方监察职能的失灵使地方官吏在执行大赦时失去限制。
另一方面,中央政权向地方妥协。就后唐中央而言,大赦的根本目的在于进行政治宣传,调整政治关系以巩固统治,大赦是否在基层贯彻对政局影响极小。与即位礼和南郊礼结合的大赦通过煊赫隆重的大赦仪式、波及全国各州县的赦令传达过程及中央和地方重臣所上的《贺赦表》,皇帝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和威严仁慈的政治形象已借此从朝堂传达至乡野。就后唐中央而言,维持政局稳定是其政治目的,皇帝虽出于为维护中央权威的目的,以赦令的方式敦促地方实施大赦,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和问责机制,对于地方毫无威慑,而敦促地方贯彻大赦的成本远高于对于地方政府的放任。中央暗中姑息放任使地方对贯彻大赦采取敷衍迁延的态度。
正是由于中央和地方对于大赦的漠视,大赦被隐瞒和淹留的情况层出不穷。天成元年(926),后唐明宗在《赦宥系囚敕》中指出,地方政府仍旧受理赦前案件。由此,被赦免的囚犯仍旧被重新定罪,甚至“或蒙赦宥已被诛夷”[3]7079。
三、后唐大赦的效果
虽然有诸多因素阻碍大赦的施行,但在后唐混乱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大赦发挥着稳定社会秩序、改善司法及巩固政局的重要作用。
(一)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
五代时期,战乱、天灾和政治腐朽导致大批反叛、遣散、逃亡的士兵以及犯罪或流移的人民甚至普通百姓成为盗贼。“州县百姓,早因危岁,小寇连绵,旧染成非,习性难改,逃刑网外,作患民间”,“法缓则潜藏军旅,法急则流散藩方”[3]5378。盗窃的突发性、盗贼来源的广泛性及其分布于全国各地、机动性强和数量多的特点使后唐政府难以通过严刑重典和武力征剿消灭盗贼,大批盗贼潜藏于山中不仅骚扰普通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影响社会治安,也减少了壮年劳动力,影响农时,耽误生产。除招抚外,政府通过大赦赦免盗贼能在节省政府资源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使被迫成为盗贼的百姓改过自新。如面对后梁遗留的因“拔队斩”和文面而导致的士兵“亡者皆聚山谷为盗,大为州县之患”的社会问题,后唐政府即通过大赦赦免士兵罪责,允许其返乡,从而使“乡里盗减什七八”[1]1325。
(二)改善司法,疏理刑狱
大赦在改善司法方面亦成效显著。一方面,五代武将专横,后唐虽尽力举行科举,选拔文人为亲民官,然“诸州长吏多武夫”[4]8757,主狱官员法律素养低下导致“典刑废弛”,后唐尤其是明宗时期虽废除后梁重法,遵用唐法,使律法设置轻重得宜,然法律仅是简单的文字条款,武人断事多不遵条令,“率恣意用法”[8]46。随武人主狱而来的是重刑、滥刑和用刑惨酷,“州镇专杀,而司狱事者轻视人命”[11]4。武人对司法审判环节的漠视和对司法权力的滥用导致大量冤狱发生。州县官员在位期间“不务守官,咸思避事,每睹微小,刑狱皆是”[3]5379,这使囚犯的淹停严重。中央政府出于敬惜民时的考虑,令地方州县在处理百姓关于土地财产的纠纷时,“二月一日后,州县不得受状,十月务闲方许论对,准格据理断割”[6]637,这使相关纠纷被迫集中于4个月内解决,加重了案件的积压。官员的推诿和案件的积压增加了地方的司法压力。大赦可以缓解由于政府重刑和滥刑带来的社会矛盾,还可以减少武人主狱下冤狱案件的发生,对于疏理刑狱和减轻司法压力亦作用不小。
(三)稳定政局,巩固统治
通过后唐庄宗的两次大赦,后唐建立了政权的正统性,成为李唐王朝的合法继承者,而明宗以后的继任者也通过大赦宣扬了其即位的合法性。就稳定统治而言,大赦在上层的贯彻一方面使后唐皇帝能以和平高效的方式吸收前朝或前代遗留的政治力量,重塑政治格局,实现政权的平稳过渡,稳定政治局势;另一方面,通过大赦对“有不得绳之以法”[1]315的功臣贵戚既往不咎,能迅速清扫政局,使皇帝能在新的基础上整顿统治秩序。对底层百姓而言,大赦确实可称为“仁政”。由于连年战乱和政府腐败,后唐社会上下层之间矛盾尖锐,盗贼蜂起与叛乱屡生就是后唐社会矛盾激化的反映。通过大赦施恩,无疑可以达到缓和社会矛盾、安抚百姓和消弭动乱的作用。
政治性和实用性突出,大赦名目稀少是后唐大赦的重要特点。一方面,后唐剧烈的皇权争夺和频繁的皇权更替使政局难以稳定,后唐大赦多为与皇权更替相关的即位和改元大赦。此种大赦多致力于整顿和补救政局,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突出的实用精神。另一方面,后唐社会动荡,礼制隳坏,皇帝无暇他顾。与前代以立后、建储、封禅、巡狩和灾祥等各种名目为由施行大赦的朝代相比,后唐大赦名目稀少,并不符合“乱世赦频”的整体规律,后唐平均每1.9年一次的大赦频率低于唐宋时期每1.5年一次的大赦频率[12]。虽然大赦在执行过程中面临各种问题,但它在弱化后唐政权的沙陀特征和塑造皇帝形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大赦是由汉族政权创造的重要行政手段,后唐沙陀皇族对大赦的继承和使用是其膺服并继承汉族政治文化的重要体现,它淡化了沙陀和汉族之间的种族与文化矛盾。在大赦被视为仁政的传统思维下,后唐汉族精英统治集团显然对大赦抱有很大的期待。大赦是“慎刑”和“恤囚”法律思想的体现,由其带来的短暂的“无讼”和“狱空”效果更是儒家仁政理想的虚假实现。它借助皇帝即位、改元和郊天等重大活动,通过盛大的大赦仪式塑造了皇帝代天理政的政治形象,迎合了普通民众对仁君圣主的幻想与期待,对民间普通百姓和知识精英而言具有极强的煽动力。
在后唐复杂的政治变局下,大赦作为一种“非日常”的急救手段,对迅速稳定政治局势和推行国家政令具有重要作用。大赦对巩固统治尤为有力,它能够迅速重塑由频繁改朝换代所带来的混乱的国家政治关系,稳定政治秩序。而且,由于后唐地方权力过大,在中央对地方日常政务难以正常开展的情况下,借助承载皇帝权威的大赦政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整饬国家政治,调整社会矛盾,它是五代中央政权重要的施政方式。碍于后唐混乱的政治环境,大赦虽很难被贯彻实施,但其在稳定社会、改善刑狱和巩固统治等方面的作用仍极为突出。但在五代“兵乱相乘,王纲大坏,侵欺凌夺,有力者胜”[1]315的环境下,后唐中央在缺乏相应实力的情况下,想要利用大赦所建立的政权合法性收拢地方的目标注定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