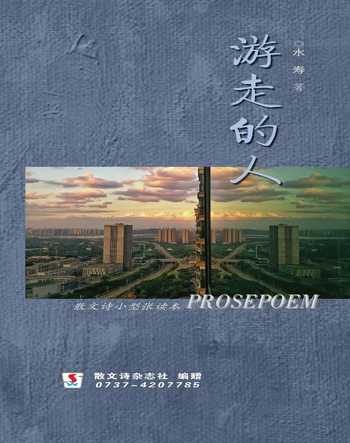大家说
2021-01-11尹红颜炯傅舰军王鲁湘彭代英萧红亮
尹红 颜炯 傅舰军 王鲁湘 彭代英 萧红亮



王鲁湘:可以这么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人心目中都隐隐然期许着湖南人能以铁血精神和大无畏的牺牲勇气,扛起民族崛起的重任。湖南人亦是这般自许,杨度就在他的《少年中国歌》中慷慨高唱:“中国苦为德意志,湖南当为普鲁士”“若教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死光!”尤其在湖南士人身上,这种原始的野蛮性同湖湘文化的“衡山正气”结合起来,竟然充溢着奇特的精神张力,发散出令人着迷的人格魅力。齐白石之所以在旧北京文化人的圈子中获得激赏,并最终征服整个士林,其实就因有这样的背景。
你看小奇笔下这三个老倌子,多惬意,多自在,不仅眉眼嘴角鼻翼有表情,所有肢体都在释放信息,连脚趾头也在说话。我们也看到,小奇的笔墨也似乎受到这三个老倌子的情绪感染,不由自主地洒脱摇曳起来,笔墨语言与人物性格完全合二为一,它们同时迸发出快活的信息,尺幅不大的画面居然有了一个气场,潇洒诙谐,像快乐的湖南花鼓戏,让我们身体里快乐的多巴胺源源不断分泌。
彭代英:《失眠者》以一种先锋、前卫、鲜明的态度,张扬水墨的表现主义,如席勒式的大胆直白、犀利冷峻、洞穿人性,又坚守着水墨艺术的蕴藉空灵、神秘浪漫与内在张力,化三维空间为二维平面,创造了一种独具意味的现代水墨图式……内部结构的枯荣穿插,空间留白的式样对比,线条组织的疏密,画面构图的完整与残缺,点线面与黑白灰的碰撞与交错,有如骑士般纵横驰骋,以一种震彻心灵的节奏,奏响了一曲东方文化殿堂里的《命运》。
失眠者头上那抹令人惊悸的蓝,让人想起《百年孤独》,马贡多小镇那个传染了失眠症的布恩迪亚家族特有的表情,那是一种天生惊讶的目光和孤独的神情……《失眠者》颠覆了常见的绘画作品中的文学意义上的叙事性表达,通过对人物形象符号化的刻画与表达,特别是眼神中所透析出来的空茫、无奈、惶惑、惊悚、惆怅、疲惫、忧伤,直接叩问人的内心,撞击人的灵魂。这种独特的符号化释义,表达的不只是作为个体的人的现实意义上的失眠,更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的精神意义上的失眠。
在艺术的殿堂里,小奇是一个失眠者。他始终保持一份繁华背后的冷寂与孤独,有如一条寂静深邃的河流,赋予了他的画作苍凉深沉的底色;而对于艺术,他又深怀一种宗教信徒般的忠诚与炽热,执著地在探索的暗夜里仰望灿烂的北斗,那北斗,其实就是自己的内心,这是失眠者的灵魂,也是艺术的灵魂。
正因为有了灵魂,所以,失眠者不朽。
萧红亮:以苦涩为底色的浪漫的表达,是成熟男性画家站在高处的艺术剪影。我用两个词进行概括,一个是“诗人”,一个是“歌者”,这是诗意的引入和歌者的呐喊。
尹红:整个长卷用传统的笔墨方式传达出一种现代人的生活感悟和体验。画面通过粗细长短曲直干湿浓淡变化不一的线条组合,构成画面节奏,并巧妙、自由地运用这些线分割成的面,以一种类似蒙太奇的方式,将不同时空的人和事、历史人文、风土人情,神秘而合理地统一在一起,画面中出现的带有传统文化符号的划龙舟的龙的形象、传统样式的石狮形象、年画中的门神形象……这些夸张的人物造型、平面带有装饰感的场景,充满着浪漫、神秘、豪爽、诡异。
颜炯:那貌似纵情粗放的笔墨间,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跃然纸上,或男女老少、渔樵耕读、士子商贾,或沧桑已久、梦寄春秋、春怀荡漾,或蹈舞恣意、醉眼迷离、南柯初就……须臾间,一河江水,一世情愁,由一个个形象次第演绎。
傅舰军:读陈小奇的画,总有一种强烈的代入感。因为生活的年代差不多,又有一样的故鄉,我们怀有同样的乡愁,他画中的人物、场景和细节,我感觉那么熟悉和亲切。
他画过一组《乡村乐队》。我总觉得那个鼓起腮帮子吹唢呐的,就是我二爷爷;那个打鼓的,就是我父亲。父亲的鼓点坚定而连贯,鼓槌起落间,下巴同步微微上下,目光扫视左右,所有动作和表情绝对都在同一个节奏上。乐队的每一个人都随着他,时而如热锅炒豆,时而如细雨滴答,时而声震如雷,时而如窃窃私语,结尾处总有一声清脆而短促的鼓点,除拇指和食指外,其余三指顺势按在鼓皮上,所有响器齐齐地,戛然而止。我在《乡村乐队》里清晰地看见了自己的亲人。
陈小奇曾经是乡村乐队里的重要成员,撞铃、木鱼、鼓手、小锣、大锣,甚至二胡、唢呐、笛子,乐队里哪个位置缺人,他就顶哪个位置。操钹的有两个,一个叫牛四卵弹,一个叫猫屎,都凶神恶煞,照那脸相画下,贴在门口可以当门神。吹唢呐的叫细山癫子,两条瘦长腿,走起路来像搓草绳,家里出身不好,爱骂冲天娘,要是喝二两,会骂个通宵。打大锣的叫二驼子,平日里,除了拾狗粪,便是打大锣,50岁了,光棍。陈小奇画的是自己的乡村乐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