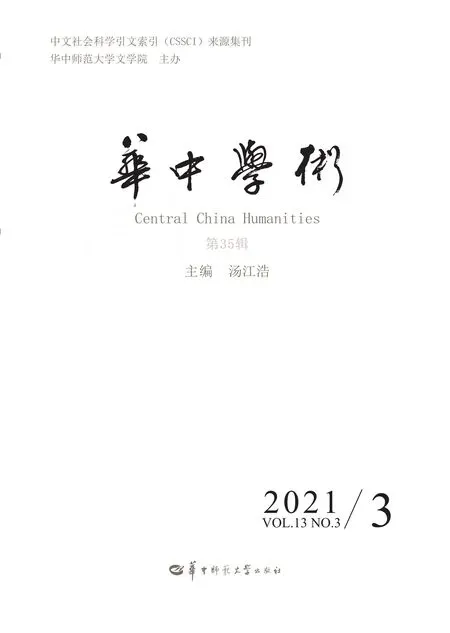理查德·罗蒂的文学伦理观
2021-01-11谢梅
谢 梅
(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是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构建了反本质主义、反表象主义、反基础主义的新实用主义文学哲学思想。在探究哲学问题时,他的通常做法是与文学、语言学、政治学、美学、伦理学等进行结合,以跨学科方法在多学科之间对问题展开多维度研究。在对伦理相关问题进行讨论时,他创造性地将其与文学、哲学相结合,进而从文学家文学创作的德育责任、文学作品的伦理品性和读者的阅读伦理三个层面形成了独特的文学伦理观。如果说罗蒂之前的哲学家们视伦理为哲学内部的主要问题域之一,进而对伦理的概念及本质从哲学层面进行探究,那么罗蒂与他们最大的不同在于看待伦理的眼光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罗蒂看来,传统哲学家们在形而上思路指导下的伦理研究是关于伦理的普遍性、历史性和合法性等的学问,这种“真理”追问是脱离生活的,远离现实的,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毫无指导意义。作为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说:“伦理乃是一组我们的实务所构成,只有具有实践意义的伦理才是真正值得我们珍视和坚持的。”[1]罗蒂一再强调我们不要再去纠结伦理是什么,我们需要探讨的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伦理及什么伦理对于个体完善和公共团结才是有益的。伦理在罗蒂的研究里不再是一种关于真理的理论,而是成了一个有关实践的问题。
国内外学者关于罗蒂的文学伦理思想仅开展了零星研究,比如国外的罗蒂研究专家波普瑞尔在《罗蒂的责任伦理》和《重视他者:罗蒂的伦理选择和伦理责任》等文章中,主要讨论了“新实用主义是罗蒂强调伦理责任感的哲学根基”[2],提及虚构文学是提升责任感的方式。国内的新实用主义哲学研究专家陈亚军、张国清、汤拥华等人在研究罗蒂道德哲学时也提到了道德进步依赖于时代精神代言人之一的文学家。遗憾的是,他们都未对罗蒂的文学伦理观展开具体论述,学界也还未出现对此形成完整、系统论述的成果。本文以散见于罗蒂哲学专著中多次有关文学伦理的讨论为基础,试图归纳出罗蒂文学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即文学家是最好的德育教育家,文学作品极富伦理品性,阅读文学作品有助于读者的道德进步。在罗蒂看来,在文学家创造的极具想象力和隐喻的作品世界里,个体遭遇他者,对他者的遭遇产生共情,学会包容和理解他者,进而将他者纳入“我们”的范围,成为具有团结意识并对他者困难具有感受力的“新”人。可以说,罗蒂的文学伦理观不仅关注个体道德进步与公共团结的关系,而且重视文学对于民主社会共同体构建的意义。
一、文学家也是德育教育家
罗蒂把作家分为自律作家和正义作家两种类型[3]。他视两种作家之间的关系为两种不同工具之间的关系,就好像画笔和铁锹的关系,他们没有好坏之分,不过是两种不同的工具发挥着不同的功能而已。两类作家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背弃理论,转向叙事,重视伦理。借助作家们的想象力,他们把陌生人想象为和我们处境类似、与我们休戚相关的人。罗蒂将普鲁斯特、海德格尔和纳博科夫看成自律型作家,认为他们的用处在于“他们是人格的模范,告诉我们自我创造的、自律的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4]。在他们身上,我们了解到具有公共性的社会品德不是品德的全部,品德应该也必须包括私人的个人品德,而且有些品德重新创造了他们自己。从这类自律型作家的身上,我们仿佛也有变成一个“新”人的需要,想要变成一个我们还没有语言加以描述的人。另一类作家,比如狄更斯、施赖纳和赖特等,则是作为社会精神代言人和公共知识分子角色,共同参与到努力使我们的社会或制度更加公正无私、减少残酷暴虐的社会任务中。这类被罗蒂视为正义型的作家们具有高度的社会道德责任感,他们不是通过讨论伦理道德的理论概念,而是在想象力丰富的小说中详细描述陌生人或者重新描述我们自己的生活,把我们向来没有注意到的人们所受的各种苦难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
文学家的德育教育不是天生的,而是创造出来。罗蒂曾说:“好奇而敏感的文学家是道德的典范,因为他们是随时留意一切事物的人。”[5]文学家的专长就是注意到大部分人没有注意到的东西,比如对善的行为之要求。文学家不仅自身会对于普通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感到好奇,而且能够对于他人视为重要的东西有所通感,比如能够敏锐地察觉到他人对于善恶所产生的意象。换句话说,文学提供了自我描述的模型,唤起人们对他者困难的关注,并寻求避免羞辱。透过好奇而敏感的文学家的创作,我们对其他不熟悉的人所承受的痛苦和侮辱的详细原委提升了感应相通的敏感度。一旦我们提升了道德敏感度,我们就很难把他者加以边缘化,因为我们不会再以为他者的感觉和我们不同,也不再默认既然苦难必然存在,为何不让他者受苦。在罗蒂看来,文学家的文学作品让我们加强了对他者的感同身受,我们逐渐把文学中的他者视为“我们之一”,而这个认知转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详细描述他者和重新描述自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学家取代牧师或者职业的德育工作者,创造出了德育教育,完成了德育教育,并成了最有影响力的德育教育家。
小说是文学家开展德育教育的主要媒介。罗蒂提出:“虚构文学尤其是小说,作为最独立、最灵活、最庞大的文学形式,对年轻人的德育教育起到了核心作用。”[6]小说取代布道或专业理论论述,成为促成道德进步的手段。罗蒂的论点是身处“后”学时代的我们可以不需要理论的抽象,形式主义的分析,或超越历史的道德原则,但是作为可塑的人类,我们需要讲故事。对于道德教育而言,讲述一个漫长悲伤的故事远比柏拉图、康德对道德法则、道德义务的追求更有用。在《作为小说典范的詹姆斯和普鲁斯特》一文中,罗蒂详细论述了两位作家在其崇拜者生活中扮演的德育教育家角色。为实现“教育和启迪我们”[7],亨利·詹姆斯和普鲁斯特作为世界知名作家,使来自世界范围内说着不同语言、有着不同宗教信仰、肤色各异的读者们都喜欢反复阅读小说中他们喜欢的人物和场景,喜欢提起他们最喜欢的章节,喜欢讨论各种人物的善举和恶行,更重要的是他们让我们突然之间想象力都得到了扩展,时刻都能敏感地觉察到自我中心的危险。比如在小说《奉使记》和《盖尔芒特家那边》中,随着小说达到高潮,越来越频繁出现的那些改变生活且具有启示意义的事件,让我们更强烈地意识到他人的需要,更清晰地渴望走出自我中心。即使詹姆斯和普鲁斯特的读者很难说清楚在小说中悟到了什么新真理,但他们会坚持认为自己和小说或者小说家之间形成了某种亲密关系或私密对话,这种关系让他们有一种变成另一个“新”人的欲求,这个“新”人通过小说中的人物或故事强烈感受到了他人的需求,渴望自我救赎,这些小说“帮助我们成为了现在的自己,我们的感激之情依然强烈”[8],正如约翰·贝利对詹姆斯的评价:“他通过语言模式对潜在的读者传达一种几乎可触碰的亲密关系。”[9]詹姆斯和普鲁斯特从不刻意为读者提供新知识,而是通过情感达到对人的塑造和教化,让读者发现自己受到了感染,主动关注到个体性与公共性的关系、自我与道德、社会与道德等伦理问题,自觉地将社会现实与公正联系起来使之服务于个体生活实践,进而实现了德育教育。
罗蒂在《偶然、反讽与团结》一书中将狄更斯、奥威尔、赖特等作家评价为具有高度社会道德责任感的文学家,避免残酷和为人类自由服务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他认为,这些作家的主要课题不是自我创造或自律,而是从受害人的视角来描写残酷。狄更斯以雾都孤儿奥利弗的悲惨身世及遭遇描写了人性和社会的残酷,赖特从“坏黑鬼”别格·托马斯的视角书写了身处种族主义社会底层阶级黑人生存环境的残酷,也反思了这种成长环境造成黑人自身性格残忍的悲剧性。阅读这些作家的作品时,“你无法对那使你生命垂危的疾病,采取一种纯粹美感的态度;你无法对持刀要割你喉咙的人,感到漠不关心”[10]。作家们成功地搭建起了小说与我们道德之间的启发式关系。小说家一方面阐明了我们现实的制度与事务并没有达到伦理理想的标准;另一方面也提醒人们向善行善义务之所在,并鼓励义务之实现。他们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下的种种残酷,我们在文学作品中有关残酷的情节中体验残酷,重新反思残酷,达成对自己道德感的反思,并努力实现自我救赎,这对于减少未来的苦难和服务于人类自由意义重大。
二、文学作品极具伦理品性
受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思想、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和海德格尔的“生活世界”思想的影响,罗蒂的文学伦理思想关注“此在”生活世界,而非沉溺于过去,他的目的是面向未来,为未来社会寻求解决伦理问题的方案。在罗蒂的视野中,文学作品的重要性体现在其对个体日常生活实践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介入、参与和指导,文学与我们渴望构建一个民主共同体社会的愿景紧密关联。在后哲学文化语境中,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哲学主张背景决定了他对文学作品的思考一定是关乎社会实践、服务生活的。文学,“作为一种希望”[11],肩负着形塑个体和影响社会的使命,“对于个体公民和社会共同体都有其根本的伦理功能”[12]。文学的伦理品性有助于人们意识到人类社会发展和他者生活经历的残酷性,进而学会理解和包容他者,减少残酷,担负起私人层面自我完善和公共层面社会团结的双重使命。这种强调个体对自我和他者的双重道德责任感的文学伦理思想体现出罗蒂对文学的伦理品性关注优先于对文学的文学性关注。
罗蒂将文学伦理划分为公共的和私人的两种类型,并试图以文学替代哲学,承担起伦理教化和提升道德能力的任务。公共伦理指向的是意见一致达成促成的更多的协同性,私人伦理则依赖于对协同性的认知,主要表现为个体的自由反讽。自由反讽者既能理解公共协同性,但是同时以“终极语汇”保持和进行自我创造。终极语汇与罗蒂的语言观则有紧密关联。罗蒂坚持语言是一种隐喻。语言的隐喻和“本义”(literalness)的区别在于“对杂音和记号之惯常使用与不惯常使用”[13]。沿着这种逻辑,语言A对于语言B的替代或再描述就不再取决于它们谁更好、更准确地表象了大写的实在,而在于偶然的机缘和语言所处的使用环境。如果上述关于语言的看法可以成立,则柏拉图-康德的道德哲学传统势必受到严重的挑战。语言的偶然性、非表象性,使我们无法穿越大写实在(善)的神秘面纱。文学伦理中的关键词,诸如“善”就不再是一个名称,而是一个形容词,一种和“真”一样的赞语。就像“‘什么是真命题’再也不能指望‘与一个大写对象的接近’来衡量一样,‘什么是善的行为?’也不再能用‘符合大写实在(善、上帝、理性)’来决定”[14]。在文学作品中,我们不是发现了什么是善,而是把某种行为举止说成是“善”,我们的“说”取决于我们的需要和我们的环境,它完全是一种偶然的行为。能创造终极语汇的往往是“强力诗人”[15],强力诗人拥有足够强的智力和创造力来创造足够有力的词汇对文化和对话的转向产生影响力。因此,强力诗人们创造出的文学作品极具伦理品性,不仅有助于个体审视自我,而且有助于共同体成员对于伦理问题达成共识。罗蒂认为语汇的创造和更新在小说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个体借助文学语汇被引入对他者痛苦的体验之中,进而对他者产生共情,清晰地意识到自我中心的危险,最终实现对他者的同情、理解和包容,达成公共团结。在这一意义上,文学扩展了我们的伦理视野,增进宽广的人类协同性,有助于在公共层面形成伦理共识。
文学,尤其是小说,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熟悉他人的终极语汇,而且还使我们关注与社会实践有关的一些奇异的文化多样性。罗蒂认为小说不仅是用于表现或再现世界,而且是用于处理世界的。他以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为例,表达了对其中有关伦理现象的探究和关注。罗蒂首先通过对小说中政治、伦理现象的再描述,认为这些小说试图让读者对残酷和羞辱的影响更加敏感,表现了对现实生活中潜在的政治、伦理等残酷现象的批判。比如,在奥威尔的笔下,奥布莱恩折磨人的手段和极为刻薄的语言是残酷的。他有意让温斯顿意识到摧毁他的信仰欲望之网、剥夺他的话语权力简直易如反掌,奥布莱恩的种种残忍使人们意识到一个人的个人特质可能对他人产生潜在的残酷影响。接着,罗蒂对小说中的文学语汇进行了一番分析,表明了文学语汇很好地论证了他的反本质主义哲学思想,即语汇本身是偶然的、可变的。本着语言意义源于实践的立场,罗蒂指出,创造什么样的语言,用什么样的语言框架,是我们人类自己的事情,取决于人类的目的。小说中的语汇或者语言不仅是一种描述社会现实问题的工具,而且是人物生活的内容,帮助人们将周围的自然事物纳入人的生活活动之中。当社会问题和个人存在问题不能用旧语汇表达时,就应该采用或创造新的语汇进行再描述,以便更好地服务于读者对自我和社会的认知。在这个创造过程中,语汇得到不断更新,帮助个体摆脱旧语汇的同时,也获得一些描述新事物新问题的新词语,进而使读者个体获得一种全新的感受,最终脱离了“旧”我。罗蒂再次以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的“残酷”情节为中心,通过用自己创造的语汇对洛丽塔和韩伯特之间的不伦之恋、朱丽娅和温斯顿之间的迫害之恋等“残酷”情节展开描述,使人们注意并反思现实生活中类似的“残酷”行为。从他的描述中,我们形成对小说中相关人物韩伯特、洛丽塔、温斯顿、朱丽娅的道德评价,进而对善恶、责任、权利与义务等伦理问题有了新的理解。
罗蒂还坚信文学对于人类的道德反省与道德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他甚至说过:“道德进步是文学成就的历史。”[16]文学在罗蒂看来从来就不是用于追求永恒的真理,而是借助文学语言以偶然性的现实情境为背景,充分发挥文学的想象力来叙述人类的各种困难,达到对这些困难的感同身受,从而推动人类关于道德的思考,进而不断拓展“我们”的范围。“文学作品能使人浏览其他方式的人生。”[17]言下之意,通过文学作品,我们认识了更多的生存方式,进而有利于自我道德的完善和美化,达成对他者的理解,允许差异的存在和发展,这正是民主、公正、自由的共同体社会的目标。罗蒂在《哲学、文学和政治》中,以狄更斯的文学作品为例澄明了文学的伦理教诲作用,因为他坚信“小说,而不是道德性的文章,是道德教育最有用的方式”[18]。通过阅读狄更斯的小说,人们能够学会欣赏不同的人按照个人意志进行选择和生活,不同类型的人学会和谐相处,实现“我们”范围的扩大,最终实现民主、自由的社会。小说取代了神学、道德性的论文,不去直接寻求关于人类的本性、人存在和人类生活意义的本质答案,而是通过文学语汇启迪阅读者如何实现人与人的共存与和谐相处,如何用行动实践去开创民主社会,小说为当今社会类似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了可能性的启发,而非唯一的肯定的绝对的方案。
面临当今的社会、政治、性别和种族问题,罗蒂认为哲学早已不能为人类日常生活提供绝对的指导原则了。文学作品成了思考和满足社会伦理需求的有效途径,因为文学不仅愉悦我们,还能教导我们,甚至治疗国家。毕竟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本质上是一种私人的沉思活动,借助感受他人的遭遇或痛苦,扩大“我们”的维度。罗蒂就曾坦承自己是通过小说进入世界的,他对他者的了解和世界的认识离不开年轻时读过并爱上的那些小说。文学作品借助作家的想象力构造出充满隐喻的世界,作家通过语汇创造从不同维度书写或描述人类所经受的屈辱与侵害,揭示出人类遭遇的复杂道德伦理困境。我们通过文学作品与作品中的人物产生共情,进而实现伦理反思,减少残酷,促进自我改造完善,实现公共团结。
三、阅读文学走出自我中心
罗蒂认为文学阅读和文学创作一样,不可回避伦理问题。他坚决反对文学阅读沉迷于揭示文本的生产机制或揭示文本的结构机理,也反对阅读时过度倾向于探究文本如何揭示了阶级、种族、性别的权力关系等文化研究的问题域。在罗蒂看来,这些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揭示文本的文学性,还是没有跳脱出从现象中寻找“真理”或本质的“科学研究”思维。罗蒂坚信文学阅读伦理在于坚信文本能够也必然教给我们什么的信念。当然,必须指出的是:罗蒂从不认为小说能够提供具有本质意义的道德指导原则,这与他反本质主义的哲学观一脉相承。他认为小说作品的伦理品性是偶然的、历史的。也就是说,每一个文学阅读者,根据自身所处的现实环境的差异性,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存在巨大差异。
罗蒂始终坚持新实用主义哲学主张在文学阅读中的践行。新实用主义者们一再强调有什么样的目的和需要就有什么样的方法,因此,文学阅读也不是为了再现真实,探究或阐释本质上就是对文本一种使用方式而已。文学需要阐释,阐释中获得的思想是读者与作品偶然擦出的火花。阐释行为本身就说明我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现有的、已经发现的机制,以及对这种机制的说明。文本阅读时阐释实践将会对读者带来令人激动、令人信服的感受,或是对作者或文本充满敬意的体验,这些体验绝不是作者的某个意图或者文本内在结构带来的,而是语境的碰撞与叠加。阐释和新阐释的过程就是继续实践和使用的手段。罗蒂又进一步指出,文学阅读不应该以阐释为终点,文学阅读不断警醒读者“生活不只是我们想象的这些”[19],文学阅读应该服务于自我的更新,更应该服务于“我们”共同体的扩大。
在罗蒂看来,阅读人类学研究成果、新闻报道、喜剧书籍特别是文学小说,才能有助于我们体验异国文化的历史和特殊性,发掘社会化的个体的人的多变性、可塑性、创造性、娱乐性和反讽性等,借此途径才能获得提升道德的能力。他说:“真正有助于正派和好心的,是一个人能够以某种程度上的道德敏感性对待那些具有特殊性的人……一个人越是能够使自己成为某种文化的历史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就越是能够发展出一种道德感。这并不是要创造出一种全新的道德能力。这是一种习得的回应能力,人们主要是从阅读、观看以及其他人交往的活动中获得这种回应能力的。它是通过发展更丰富、更生动的想象力而获得的。”[20]可以看出,罗蒂把道德感看成一种从文学阅读中获得的回应能力。首先,阅读人类学研究成果、新闻报道、喜剧书籍,特别是虚构文学,有助于我们体验异国文化的历史和特殊性,借此途径我们使自己成为某种文化或历史生活的一部分,具备发展道德感的基础。其次,作为对阅读文学作品的回应,个体回归对自我存在的关注,不断揭示流动的、偶然的、暂时的、非终极性的此在状态,以获得不断更新的自我审视。此外,罗蒂理解的道德进步是一种想象力的增长,而不是为了更逼近于大写的“真”“善”或者“正确”。想象力在罗蒂的文学哲学中是一个关键词汇,它被罗蒂视为文化进化的边界,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能力和力量,能使人类未来比过去更加富裕。他坦承:“充满想象力的作品或充满想象力的联系能够延伸我们对于有用事物的概念,所以,有时候你事先不知道什么会有用。”[21]但他坚信大量的文学阅读积累一定会让读者有所改变,这种改变体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改变一个已被广泛接受了的分类,或者可以给已经讲述过的故事增加一些新的东西;另一方面,读者与作者、人物、情节等偶然“相遇”,使其改变了关于他/她本人是谁、对他/她什么有利、他/她想怎样对待自己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反过来,他/她的改变又会促发他/她的意图或目的的改变与调整。罗蒂还进一步强调说,想象力是共同体用不同方式描述新概念的源泉,正因为想象力,牛顿、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共同具有的东西是用不熟悉的术语重新描述熟悉的事物的能力。因此,“我们最好把道德进步看作一项增进敏感性的事情,一项增进对越来越多的人和事的反应能力的事情”[22]。道德进步不是一个增加理性的问题,而是能够对广大人民的各种需要作出反应的能力。
对于新实用主义者来说,阅读的旨归为使用甚至是实用。据此,罗蒂进一步提出,文学阅读作为一种救赎方式有助于阅读者走出自我中心主义,实现自律自我与生活形式的选择,服务于读者的日常生活实践。通过讨论欧文·豪、马克·吐温、托马斯·品钦和诺曼·梅勒等作家的作品,罗蒂指出,个体通过阅读实现了对文学作品的参与和对文学角色的承认。罗蒂又以《安妮日记》《男人成长记》等分别涉及犹太人、黑人和同性恋者的作品为例,表明文学作品借助叙事打破道德直觉和偏见,而其具有的教化价值使得个体在承认他者的同时承认自身。通过他者,个体体验歧视和他者苦难,获得救赎的可能性。个体与他者的关系使个体提出寻求协同性与构建宽容意识的伦理诉求,个体通过承担对他者的责任,实际承担了对自我的责任,进而承认自身,获得救赎。总之,借助文学作品对日常经验的开放性,个体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美化和公共团结,并最终走出自我中心。
总之,罗蒂的思想非常丰富,其独特之处在于文学伦理思想是其阐释哲学主张的新路径和新方法,他的文学伦理观与哲学主张呈现出互为依托、相互观照的内在逻辑统一关系。基于新实用主义重视实践及其后果的立场上,罗蒂认为讨论文学的伦理品性旨在使它更适当地满足我们的各种需要,实现道德进步。罗蒂对文学尤其是小说的思考,是以文学发生实践功能的方式为中心的,他坚信文学不论是对于私人领域的个体还是公共领域的社会都有着伦理教诲功能,正如他自己所言:“现在的文学批评家不应该再从事所谓‘文学性质’的挖掘和阐述,而应该建议如何修正道德示范和顾问的准则,建议如何缓和这种传统中的张力,或如有必要,加剧这种张力——来促进人们的道德反省。”[23]文学阅读帮助我们关注他者的命运和痛苦,体认生存方式的多样性,我们唯有接纳、包容和理解差异性的存在和发展,才能够实现各种文化或族裔人们的对话和沟通,扩大“我们”的共同体成员,最终实现共识的达成。在这一维度上,道德进步和“我们”共同体范围的扩大成了罗蒂文学伦理思想的核心诉求。罗蒂文学伦理思想始终关注个体与他者的关系、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并指出个体如何通过阅读文学作品进而遭遇他者,走出自我中心,实现个人完美和社会团结。这些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为当今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的共存与多族裔人们的相处提供了现实借鉴方案。
注释:
[1] 王莉:《从“自我”观评罗蒂的伦理思想》,《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29~32页。
[2] C. Voparil, “Taking Other Human Beings Seriously: Rorty’s Ethics of Choice and Responsibility”,ContemporaryPragmatism, Vol. 11, No.1, 2014, pp.83-102.
[3] [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许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页。
[4] [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许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页。
[5] [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许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23页。
[6] [美]理查德·罗蒂:《哲学、文学和政治》,黄宗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76页。
[7] [美]理查德·罗蒂:《哲学、文学和政治》,黄宗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83页。
[8] U.Schulenberg,RomanticismandPragmatism—RichardRortyandtheIdeaofaPeoticizedCultur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159.
[9] [美]理查德·罗蒂:《哲学、文学和政治》,黄宗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84页。
[10] [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许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05页。
[11] G. E. Dann,ThePossibilitiesforEthicsandReligiousBelief,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0, p.74.
[12] 参见赵彦芳:《文学的伦理:个体和共同体之间——从罗蒂的文学思想谈起》,《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第124~128页。
[13] [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8页。
[14] 陈亚军:《非形而上学的伦理学何以可能?——论罗蒂新实用主义道德哲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55~62页。
[15] U.Schulenberg,RomanticismandPragmatism—RichardRortyandtheIdeaofaPeoticizedCultur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5, p.155
[16] U.Schulenberg,RomanticismandPragmatism—RichardRortyandtheIdeaofaPeoticizedCultur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5, p.154.
[17] [美]理查德·罗蒂:《哲学、文学和政治》,黄宗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05页。
[18] [美]理查德·罗蒂:《真理与进步》,杨玉成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19] A. Malachowski ed.,ACompaniontoRorty, Hoboken: Wiley Blackwell, 2020, p.181.
[20] [美]理查德·鲁玛纳:《罗蒂》,刘清平译,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82~83页。
[21] [美]理查德·罗蒂:《哲学、文学和政治》,黄宗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02页。
[22] [美]理查德·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张国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61页。
[23] [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