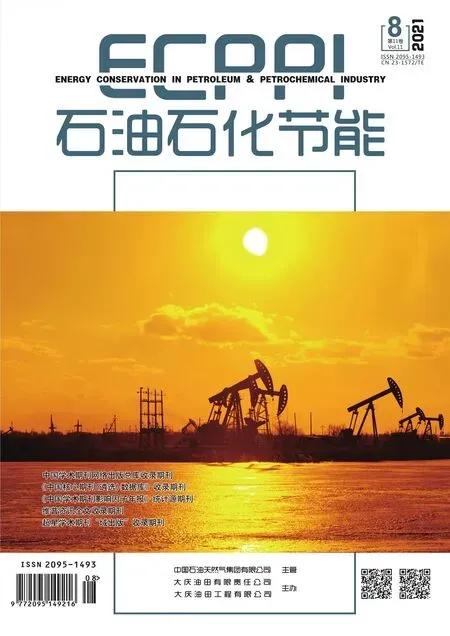氢能事业的发展与前景展望
2021-01-11柏锁柱赵刚中国石油国际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柏锁柱 赵刚(中国石油国际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能源利用从薪材到煤炭,再到油气,不断向更高效、更便捷和更清洁化方向发展。二十一世纪数字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正不断缩短能源替代周期,加速能源消费变革,能源利用趋于多元化。
近些年,氢能扮演能源角色逐渐崭露头角,在全球和中国发展速度日新月异,作为终极清洁能源,其发展对中国乃至世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1 世界氢能发展概况
欧洲、日本、澳洲、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都颁布了各自的氢能战略[1],因各国或地区资源禀赋不同,其氢能布局的方向明显不同。德国于2020年6月10日公布了《国家氢能战略》,定位发展氢能消费市场;日本于2017年12月26日公布了《基本氢能战略》,2019年3月发布了新版《氢能与燃料电池电池路线图》,定位发展氢能消费市场和获取氢能资源;澳大利亚于2019年11月22日公布了《澳大利亚氢能战略》,定位向亚洲市场出口氢能;加拿大与2020年12月17日公布了《加拿大氢能战略》,定位发展供氢能力。可见,化石资源禀赋较好的澳洲、加拿大,自身定位偏重于氢能上游产业,而日本、德国等资源禀赋差的国家地区更注重氢能下游市场的开发。
氢资源是发展氢能事业的资源基础。利用可再生能源生产氢气(绿氢)现阶段成本高。据相关数据,如不考虑碳成本,天然气重整制氢(蓝氢)成本约2~3美元/kg,绿氢成本6~9美元/kg,绿氢成本远高于蓝氢[2]。核能制氢(核氢)成本略高于蓝氢。伴随技术进步以及碳交易入市和碳税开征(后两者文中统称为“碳成本”),蓝氢、绿氢成本差距逐渐缩小,核氢基本没有碳成本,绿氢显然是碳成本最大收益者,而核氢是潜在受益者。
相关专家认为,2020—2025年全球以蓝氢和工业副产氢(灰氢)为主,2035—2050年以绿氢为主,蓝、灰氢为辅[3]。如果2030年全球平均碳税达到40美元/t,绿氢成本才可与蓝氢+碳封存和捕集技术(CCUS)竞争[4]。目前全球大约94%氢来自于化石能源,其中,由天然气、石油和煤炭制氢的比例分别为54%、31%和9%,绿氢占比不超过6%。蓝氢、灰氢是现阶段氢气主要工业化来源。
2 中国氢能发展概况
中国氢气主要来自于天然气或煤制氢、工业副产氢等,绝大多数是蓝氢和灰氢。绿氢项目现阶段处于示范阶段。2018年,中国生产氢气约2000×104t。99%以上为灰氢和蓝氢。氢气消费结构中合成氨、甲醇、石油炼化占99%以上,用于燃料电池的能源氢消费不足0.1%[5]。
随着中国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产业不断发展,中国氢能政策导向及产业定位逐渐明朗。2019年10月召开的国家能源委员会会议指出,探索先进储能、氢能等商业化路径。根据《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到2035年我国燃料电池商用车将实现规模化应用。2020年,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首次将“氢能”纳入能源范畴,而此前氢能一直被定性为“危险品”。中国大部分省份均已发布氢能规划,2020年9月21日,国家财政部、发改委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氢能燃料电池示范应用推广的通知》后,以奖励替代补贴的形势支持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和示范。
近几年中国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显著。能源公司和汽车制造企业都开始试水氢能交通能源和物流市场。2021年2月上旬,中石油在张家口合资建设一座加氢站投产。截至2020年底,中国已建成130多座加氢站,初步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及中部地区等产业集群和示范应用。
3 氢气生产技术路线及储运方式
3.1 工业化制氢
氢气获取主要途径是化石原料制氢,主要讨论天然气制氢(蓝氢)以及工业副产氢。煤气化制氢不在讨论范围。
天然气制氢分为蒸汽重整技术、部分氧化技术。其中蒸汽重整技术采用的是甲烷和水蒸气发生重整反应生成合成气后再通过变压吸附装置进行工业提纯的生产过程。国内天然气蒸汽重整制氢技术成熟。部分氧化技术是通过甲烷和氧气高温下发生氧化反应生产合成气的工艺过程。为克服重整反应强吸热导致生产过程需要外供大量的热量,提出重整技术与部分氧化技术进行耦合制氢技术,包括联合自热转化技术和自热重整工艺技术。此外,还有天然气化学链制氢,目前尚不成熟。蒸汽重整制氢方式成熟度高,被工业广泛应用[6]。
工业副产氢是石油化工、煤化工、焦炭等行业所产氢气经过深冷分离、变压吸附或膜分离手段提纯的氢气。据相关数据[7],工业副产氢目前成本约在2元/m3。我国每年工业副产氢总量虽然有千万吨,但面临着实际富余氢气越来越少,例如炼油装置面临油品升级对加氢要求越来越高,其重整氢都被用来加氢,氯碱行业副产氢60%以上氢气被配套的盐酸、聚氯乙烯、双氧水消耗等。如考虑碳成本,其成本将增加。
3.2 潜在制氢竞争技术路线
以核能为主的热化学制氢技术在经济、环境和效率上都具有大规模制氢的潜力,将来有可能逐渐取代蓝氢成为工业制氢的主流技术[8]。核能既能为大规模电解水提供电力,又提供高温热源,核氢就是将核反应堆与采用先进制氢工艺的制氢厂耦合,进行大规模氢气生产。核氢主要方法包括高温电解水、热化学分裂解水碘硫循环、热化学裂解水溴钙循环和甲烷直接裂解。
近些年来,随着光伏发电成本不断降低,其制氢竞争力也在不断提升。然而,生产太阳能电池过程产生大量的酸性废气及各种废水,光伏板使用过程中产生光污染、热污染都需要有效防治[9],如果考虑治理成本,光伏发电制氢的成本竞争力将有所削弱,其绿色环保性值得商榷。风能发电的成本也逐年下降,但风能项目只能布局在风力资源丰富的地区及海上,其布局受制于地域,风车会对所在地区大气环流造成影响,对当地局部气候造成改变,风力发电的环境友好性受到质疑。
更重要的是太阳光和风力都无法保证24h连续供应,风光发电生产的电力只有通过电力储能装置才能实现24h为电解水制氢连续供应能源。相较于蓝氢、核氢,风光发电制氢受制于不连续供应的自然资源因素制约,使其发展和布局更需考虑地域性因素,这导致氢气运输至消费市场的成本因素是无法忽视的。综上,风光发电目前只能作为补充能源使用。
总而言之,绿氢需要不断提高制氢效率和降低氢气单位成本,能否大规模商业化应用取决于技术进步和碳成本政策导向。
3.3 氢储运
3.3.1 氢储运方式
氢储存和运输,简称“氢储运”,方式有带压储运(气氢)、液氢储运(液氢)等物理方式和有机液体氢储运(化学氢)等化学方式。
3.3.2 长距离氢储运
1)液化氢方式。尽管将温度冷却至-240℃后将氢气液化的单次氢运输效率很高,然而,氢气液化温度远低于液化天然气的-160℃,技术难度大、能耗高、装备要求高、投资大,对液氢储罐的绝热性能要求更高。因此,通过液化氢实现长距离跨境运输比液化天然气更困难[10]。也许随着未来发展和市场的需求出现,液化氢技术问题会解决。
2)化学氢方式。化学氢方式是借助有机液体储氢,利用不饱和液体有机物催化加氢和脱氢的可逆反应,通过加氢反应实现氢储存,高温下脱氢反应实现氢释放,由于其富氢有机载体常温常压下为液态,易于处理,应该会成为未来氢长距离运输重要商业化候选技术。
尽管目前有机液体储氢存在诸如脱氢反应温度高、能量大,脱氢过程常伴有副反应,氢气纯度不够,脱氢催化剂成本高、寿命短等问题,但其优势也非常明显,现有液体运输船或罐车经过改造后方可使用,储运压力低,安全性高,储氢量大,储氢成本低,液体运输远比高压气体或低温液体运输更易操作和计量,加氢和脱氢设施属于化工反应和分离设备,加氢和脱氢过程属于常见化工过程,各类操作经验和研究人才从化工行业容易获得。
3)管道方式。氢气管输的一种方式是利用现有天然气管网,将氢气和天然气掺混运输,由于每个天然气管道项目的标准、材质、工艺设备不完全相同,为防止氢脆,每个项目允许的最高掺氢比例不同,只能评估才能考虑能否掺氢。
第二种方式是选用合适材质建设全新氢气管线运输纯氢,这样不用担心氢脆。现今使用的检验方法足以控制氢气的运输风险与天然气的运输风险等级在同一水平。干线输氢和中国西电东送、西气东送类似,和未来的西氢东送都属于国家战略能源运输,在未来会支撑起中国能源的骨干体系。氢气配送管道建设成本较低,但氢气长输管道建设难度大、成本高,目前氢气长输管道的造价约63万美元/km。管道运输对运输规模非常敏感,是现有的化工氢主要运输方式,输氢量在5×104m3/h以上,有比较好的经济性。欧洲大约有1500km的低压氢气管道,美国现有的氢气管道超过1400km。世界最长的氢气管道位于法国和比利时之间,长约400km。可见,氢气干线管道运输成本有待下降以提高竞争力。
3.3.3 短途氢储运
短途氢储运主要解决的是国外进口到岸氢以及国内自产氢的储运问题。目前,技术相对成熟、运行相对可靠的是采用高压长管拖车将氢气配送至加氢站,与加氢设施连接后,为车辆加注。
4 中国氢能供应市场未来发展前景
中国碳市场交易系统已经基本建设完成,相关的规则制度也已经完备,2021年6月底之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要上线启动已基本确定。
4.1 能源央企将作为引领者,构建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新局面
4.1.1 碳成本加速构建能源产消新局面
国家借助碳成本,控制能源公司CCUS项目投资以及可再生新能源发展节奏。碳成本越高,传统能源被新能源替代速率越快,CCUS项目上马速度越快。碳成本有可能为央企创造廉价甚至是1元收购体制外炼厂股权历史机遇,体制内、外炼化企业人财物资源加速融合,促进能源下游混改提速。
4.1.2 区域性布局蓝氢产业
2030年之前仍处于碳达峰阶段,传统能源企业配套CCUS处于起步发展阶段。2030年后,受到碳中和目标制约,CCUS项目将显著提速。通过在产业集群内布局蓝氢项目,实现产氢+储运+售氢的区域性产业链条布局。除了向产业集群内布局外,在天然气产区或油田伴生气富集区布局蓝氢项目并配套二氧化碳驱油项目,发挥项目间协同效应。
4.1.3 重视工业副产氢作为能源来利用
能源企业炼化行业将更加注重产氢和用氢。为多产氢和顺应油转化发展趋势,可借助增加石脑油外采量或降低中国出口周边国家汽油量来补充国内重整石脑油短缺,提高重整装置负荷,扩建重整装置加工能力,增加天然气采购量,制氢装置能力扩建等一系列手段来实现。另外,中国东部地区丙烷脱氢项目等副产氢石化类项目也将进一步提速,在生产更多化工料同时提供更多工业副产氢资源。
4.2 氢储运商业化应用突破
氢储运技术(海运、铁路、公路陆运)成功商业化应用案例出现。最有可能首先应用的应该是化学氢方式。有机液体氢储运能耗、选择性持续得到改善,将导致市场对芳烃需求量增加,国内炼厂加大国际轻烃及石脑油的采购量或降低汽油出口,增加氢气供应及芳烃类有机物载体供应。不排除跨境液氢运输和长距离管输案例出现,主要还是看市场对氢的需求强烈程度。
4.3 产业集群争夺氢资源,能源央企可能加速布局氢能产业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及中部地区等产业集群之间对氢气资源的未来争夺加剧。取决于碳成本高低,随着2021年6月底之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上线,碳市场开始实质测试,能源央企布局加氢基础设施的速度可能会提速,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推出氢能汽车的速度可能会加快,氢能汽车保有率目标可能会提前实现。
5 结束语
双碳目标将加速能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化石以外的能源比例上升是必然的。除电能外,氢能也是传统能源公司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国家加强能源治理的重要途径,是能源央企不得不面对的一项重要发展课题。
在可控核聚变实现连续商业化运行前,氢能事业将为中国发挥后发优势、实践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