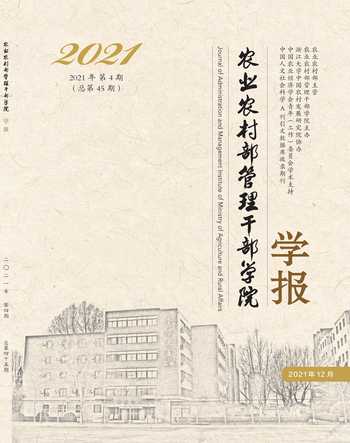党建统领:社会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
2021-01-10姜裕富
摘 要:中国特色的政党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决定了党在三者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必须坚持党建统领,这是符合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要求的。党建统领是指党对一切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党建统领社会治理包括强大的政党、总体性社会、整体性治理和科学的统领机制等四个构成要件,按照从政党的政治功能到治理功能提升的逻辑运行。浙江衢州开展“党建治理大花园”活动基本逻辑是:把基层党建融入乡村振兴的各项工作之中,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功能,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把治理优势集中在大花园建设之中。实践证明,“党建治理大花园”活动与党建统领社会治理具有高度的逻辑契合性,把党的建设、社会治理与乡村振兴融合在一起,深化了对社会运行规律和治理规律的认识,提升了社会治理效能。
关键词:党建统领;“党建治理大花园”;社会治理;政党—国家—社会
一、研究综述与问题提出
为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目标,需要整合各种组织、人才、技术、政策等资源,重心下沉到基层社会。中国特色的政党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决定了党在三者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中国语境下的社会治理,必然是政党统领之下的运作。学界关于政党统领社会治理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从政党建设角度研究党建统领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后,“新的社会权力结构”正在形成,如果党建无法适应社会结构的变化,将在社会治理中失去主导作用。吴新叶提出要实现党建由“组织引领”向“功能引领”的转变,必须通过政治功能引领、整合性引领、动员功能引领、沟通功能引领等机制,才能占据社会治理体系中主导地位。在如何实现党建与治理融合的问题上,叶敏提出,要发挥好社会治理的价值倡导和行动倡导、政治整合和资源整合以及利益协调和组织协调的作用。韩福国、蔡樱华认为,基层党建面临制度叠加的“创新内卷化”、多元人群参与的不均衡、空间治理滞后、组织激励不足与治理“碎片化”等困境,无法有效融入社会治理之中,必须将开放式党建“嵌入”到具体社会治理中,形成一个“党社双向开放”结构。
二是从社会建设角度研究党建统领社会治理。改革开放后,“由于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联结机制——中介组织的解体或缺失而产生的个体孤独、无须互动状态和道德解组、人际疏离、社会失范等社会危机”,维系传统权威体制的科层制度和一统观念制度都受到了多重挑战,“科层制度承担越来越多的治理功能,不堪重负;一统观念制度受到多元社会的碰撞挑战而难以为继”。传统社会结构趋于瓦解、社会价值日益多元化,逐渐出现了按照市场逻辑组织起来的分化的“异质性”社区。赖以构建治理格局的社会基础正处于重建之中。有学者提出要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视角,以社会再组织化为路径,重构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分工与合作关系,实现服务型社区治理目标。
三是从政府角度研究党建统领社会治理。代表国家承担社会治理责任的政府,在治理理念的形成、治理能力的提升、治理制度的建构等方面,都无法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无法为党建统领社会治理提供足够的支持。外部性治理体制一旦变动,没有内生的社区组织来承接原由行政化组织所承担的事务,农村再次陷入一盘散沙的“治理真空”境地。税费改革后,农民的流动性加剧,外部力量对农村社会的整合能力减弱,内生的经济社会组织独立性和凝聚力不强,导致农民更加离散化。低组织化状态下,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缺乏,与基层政府之间缺少有效的缓冲,基层治理成本高且效果不理想。在农村党建与社会治理中存在“两张皮”的现象,割裂了两者的联系,结果双双受损。
政党—国家—社会关系分析框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必须看到它的内在逻辑是把政党变成国家,把国家变成无所不包的‘党国体制’,既泯灭了政党的原始机制——政党的功能高度行政化,政党偏离了政党的角色,又消泯了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国家全面扩张最终吞噬了社会,反过来抽调了国家建设的物质和政治基础,导致国家政权建设的全面困境”。政党与国家和社会关系应该是有各自独立的活动空间,又有复杂的依赖关系。理论与实务一般用“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來描述两者关系,“引领”并不能充分表达出党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统领”包含有“集中统一领导”之意,“党建统领社会治理”更能恰当地描述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政党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2019年,浙江衢州开展的“党建治理大花园”实践活动诠释了如何实现基层党组织、基层政权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其间重要的机制就是“党建统领社会治理”,该活动吸引了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的高度关注。党的建设、社会治理与乡村振兴是一个政策过程的三个不可分割的环节,“党建治理大花园”模式完美地将三种目标融合成一个共同的追求:把党的建设融入社会治理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在基层治理过程中实现党的建设和乡村振兴的目标,在乡村振兴中加强党的建设和社会治理。本文将分析党建统领的理论假设、构成要件、运作逻辑等要素,并用党建统领理论分析“党建治理大花园”的实践过程以及与党建统领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
二、作为社会治理分析框架的党建统领
改革开放,主要是改革政党、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体制,国家权力有序地向市场、社会开放,形成了政党、国家、市场与社会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格局,也导致了分散性治理体系。从逻辑上看,这种国家与社会适度分权符合多元社会的需要。但是,不同治理主体遵循各自的运行逻辑,治理的分散性特征愈加明显,如果国家治理能力不高、市场机制不完善、社会发育不充分,会使社会治理陷于混乱局面。一个强有力的政党能够统领国家、市场与社会,实现社会治理从无序走向有序化、法治化。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和社会的特殊关系,使其有资格、有能力、有责任承担起统领社会治理的使命,制止分散性治理后果扩大化。
(一)党建统领的理论假设
党建统领是指党对一切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党建统领社会治理的基本假设:一是执政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满足人民对秩序的需要是政党统领社会治理的最大动力;二是社会治理是个系统工程,尽管解决问题的资源绝大多数掌握在政党和国家手中,单凭政党力量也无法实现治理,政党、国家、社会相互合作是实现社会治理的需要;三是中国政党的性质决定了其在合作治理中的统领作用。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查摆问题、集中资源、协作治理,整合一切组织、人才、資金、政策等资源,实现有效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必然选择。
(二)党建统领的构成要件
1.一个强大的政党
亨廷顿认为,“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那些在实际上已经达到或者可以被认为达到政治高度稳定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与西方历史中“先有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形塑现代国家,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孕育现代政党”的过程完全相反,我国是“党建国家,国家创造社会”模式。葛兰西认为,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差异化、碎片化的众多个体如何变成具有凝聚力、团结感和集体认同感的政治主体。他提出,任何集体性的社会行动主体都是被以政党为代表的政治组织和政治领袖塑造出来的。葛兰西强调了政党组织及其领袖在转型时期“塑造议题”的重要性,依靠“议题”指导群众在混沌之中看清问题、在迷茫之中找到方向,实现从“数量转为质量”。如中国“先有政党后有国家”模式中的政党,拥有强大的议题建构能力而彰显其强大,政党的统领力量表现在政治忠诚度、思想统一度、组织覆盖面、行动的一致性、群众美誉度等方面。
2.总体性的社会基础
总体性一般指称政党、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社会特征。高度一体化并非是僵化,在不同主体之间有良性互动的机制,这种一体化格局“实际上是党通过自身的领导体系和组织体系对国家、对社会实行集中统一领导,从而把国家和社会全面整合进党的领导体系和组织体系之中”。社会决定国家,政党的功能是整合社会力量,制约国家权力的构造与运行,通过各种机制实现对社会的重组。我国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造成了个体的“原子化”,国家政权的上浮和基层党组织的弱化以及社会组织的不发达,导致基层社会失去凝聚力。如果一个高度分散的社会,政党无法通过国家实现对社会的领导,政党统领社会治理就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全方位的覆盖以及强大的组织力,已经把趋于分散化的基层社会整合为一个有别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新的总体性社会。
3.整体性的社会治理
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造成了社会治理碎片化,整体性治理应时而生。它“着眼于政府内部机构和部门的整体性运作,主张管理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这种政府融吸社会的整体性治理,强化了政府中心地位与治理力道,完善政府与社会的制度化联系与协商机制。政府融吸社会不仅仅表现为社会治理走向开放的过程,也表现为社会走向能动的过程,政党作为国家与社会的联接者、引领者,借助国家与社会的开放机制渗入其中,国家与社会凭借能动机制影响政党政策。政党创建国家之后,通过国家整合社会,最终实现政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政党的功能是统领一切组织、制度、价值、物质等资源,引导各种国家与社会力量集中在自己预设的目标之下。通过整体性治理,实现政党与国家和社会相互间的赋权与增权,政党也成功地实现对国家与社会的领导。
4.科学的统领机制
统领指的是在一个组织或一次行动必须遵循统一意志、统一目标、统一规范等。政党以下的所有国家和社会组织都成为政党意志的执行机构,任何违背政党意志的行为都被视为对政党的不忠诚;任何偏离政党指示的资源流动,都是缺乏大局意识的表现。作为政治组织的政党,要实现统领目标,一要依靠组织统领,国家一切的政治组织、社会力量都要服从党的领导;二要依靠价值统领,以党的先进性武装全党,以核心价值观引领各种社会思潮,提高政党认同、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三要依靠制度统领,党建统领社会治理是制度化的治理,构建以党章为中心的党内法规体系和以宪法为中心的法律体系,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全过程,用科学的制度来整合资源与民主协商机制,实现从政党治理到社会治理的发展;四要靠信息技术的统领,信息化时代制造了社会的“碎片化”,但信息技术也能创造新的整合机制。只要政党积极应对技术时代的挑战,引导治理理念、制度、方式的适应性变革,技术治理必然是政党统领社会治理的重要机制。
(三)党建统领的运行逻辑:从政治功能到治理功能的提升
习近平指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其中有三层含义:第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政治优势;第二,政治优势不等于社会治理优势;第三,把政治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需要一个转化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能否设计出将我国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的机制,这也是政党统领社会治理实现与否的关键,即实现从党的政治功能到社会治理功能的提升。
1.从价值、组织、行动三个维度认识政治优势与治理优势
政党和公民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政党是公民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公民社会发育程度的高低,制约着政党活动的水平和范围。政党来源于社会,政党以社会为基础,政党服务社会,社会借助政党组织实现自身发展,简言之,社会决定政党,政党引领社会。政治优势可以转化为治理优势,政治优势决定了治理优势。政治优势表现在价值上坚持以人为中心的理念,满足人民对秩序的需求;政党拥有一个严密的组织体系,对国家和社会的全覆盖;党有着严密的纪律,在行动上保持高度的一致。从社会层面上看,治理优势需要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充满活力的组织建设、以服务与自律导向的行动方式。
2.通过整合与协商机制,实现从政治优势到治理优势的转化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的政治优势,最大的政治优势是紧密联系群众。执政党应从组织网络、组织制度、政治角色、意识形态等方面着手,建构起以利益整合为核心、以制度整合为保障、以价值整合为基础、以组织整合为依托的“四位一体”的社会整合机制。党的基层组织与群众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将党和国家与社会的各种资源进行整合,增強社区公共服务能力,形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既展示了党的政治优势,又实现了社会治理。社会是由不同利益主体构成,持有不同的价值观念,政党统领过程中会产生利益与价值的冲突。一个有效的协商机制,可以让各方相互尊重,平等、和谐进行沟通,在协商过程中达成共识,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3.形成政治忠诚意识和实现善治目标
实现政治忠诚与善治是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的标志。在西方政治学看来,政党具有“冲突的力量”和“整合的工具”双重功能。在革命时期,党主要作为一种冲突力量,在阶级对抗中夺取政权;在建设和开放时期,党整合不同阶层、利益群体,构建和谐的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政党统领社会治理第一个目标是实现党内的政治忠诚。“无论农村社会结构如何变化,无论各类经济社会组织如何发育成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不动摇、战斗堡垒作用不削弱。”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忠诚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保证。第二个目标是实现社会善治。善治的本质是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新构造,国家与不同社会组织在合作中实现公共利益最大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没有自己特殊利益追求的政党,具有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天然优势。在充满活力与和谐有序的社会建设中,始终做到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强化互联网思维、合作共治思维,推进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
三、衢州“党建治理大花园”的实践描述
农村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没有哪个政党可以忽视农村。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伟大事业的成功都是从农村开始的,党的方针政策必须与农村实际保持高度一致,否则,社会主义事业将遭受重大挫折。衢州“党建治理大花园”是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下开始布局的,把美丽大花园建设作为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的载体,实现了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建设。
(一)衢州“党建治理大花园”建设提出背景
2018年4月,衢州市委制定了“活力新衢州,美丽大花园”发展战略,把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作为大花园建设的重点内容。一年来,聚焦于乡村振兴,牵住农房体系构建和风貌提升“牛鼻子”,以拆违治乱、集镇整治、全域土地整治、乡村振兴党建示范带等为重点工作,开展系列现场互学互看推进会,促成文旅融合、农旅融合、三产融合,打造一批有乡土味、烟火味、人情味的美丽乡村。通过“互联网+政务服务”“党建+基层治理”“制度+技术”等机制,将全市县乡村四级9097名党员干部纳入网格化管理,建成了党建统领基层治理体系。选派900多名干部组建15个专班到项目一线工作,形成有效工作与激励制度体系。
实践中,衢州“民情档案、民情沟通、全程为民服务”的党建模式面临转型升级问题;“枫桥经验”所依赖的行政村、自然村早已不是原先的村落,如何发挥网格的治理功能也面临着现实挑战。为了解决发展中面临的问题,2019年6月中共衢州市委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党建治理大花园”建设目标,就是把基层党建、社会治理与乡村振兴融合一体的方案。
(二)衢州“党建治理大花园”的行动体系
实践中,衢州“党建治理大花园”围绕着乡村振兴总目标,具体分解为三个方面的行动体系:党的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和“美丽大花园”建设。其主要做法如下。
1.以党的建设统领乡村振兴的组织体系
衢州市围绕着乡村振兴设计了一个庞大的行动组织方案,称为“三个三”党建工程,即落实乡镇(街道)的主体责任、发挥村(社)组织主体作用、激发党员群众主体意识的“三大主体工程”;组团联村全覆盖、网络支部全覆盖、党员联户全覆盖的“三个全覆盖”;乡镇(街道)党(工)委的服务指数、村(社)党组织的堡垒指数、党员先锋指数的“三大指数”。衢州全市共建成1579个服务组团、9097名组团联村,每个网格建有支部,每个党员联系网格中的农户。全市1482个村(社)、4191个网格,以村(社)“两委”班子成员为主体的38,000多名干部队伍承担起引领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网格员、网格党组织承担了乡村振兴中所有行动的组织、执行工作,网格也成为考察与锻炼干部的主要载体。衢州出色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被中组部列为“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全国地方8个典型之一。
2. 以效能转化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点
通过做好“党建+基层治理”大文章,把党建与乡村治理结合成“一张皮”,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首先,构建基层治理运行机制,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整合县级党委政府部门的资源力量,关口前移、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权力下放;乡镇(街道)打破条块分割的现状,实行属地统领、捆绑考核。建立村级网格、做实网格。依靠现代信息技术线上线下联动指挥,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其次,打造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社会治理格局,促成社会治理的网络化、网格化、扁平化、一体化、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促使社会治理从突击运动变常态长效、事后变事前、治标变治本、被动变主动,实现管理变治理、民主促民生。再次,在项目建设中提升党员干部乡村治理能力。项目是党员干部执行力、党性修养、服务力得到检验和锤炼的大考场。“支部建在项目上”、 党员“1+N”联户机制、“红手印+网格竞争性拆违”工作法等做法实现了基层组织由“零散化”到“一体化”的转变,促进了由“等着干、摸着干”到“主动干、规范干”的转变,引导党员由“跟着走”向“靠前站”转变。
3. 以项目支撑“大花园”建设工程
根据浙江省委、省政府对衢州提出“在推进乡村振兴、高水平建设美丽乡村上走在前列”和“当好诗画浙江大花园建设的先行者”的要求,衢州的“大花园”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党建与社会治理最终落脚于乡村振兴之中。“大花园”建设中着重抓三件大事:第一,打造“衢州有礼”诗画风光带,建成乡村振兴样板带。利用衢州自然资源优势,把“衢州有礼”诗画风光带建成未来社区先行地、幸福产业大平台、改革创新试验区。第二,打好农房整治攻坚战。以农房体系构建和风貌提升为突破口,盘活宅基地、闲置农房和集体资产等要素资源,促进要素集约、产业集聚、人口集中,加大美丽环境向美丽经济转化力度。第三,突出土地综合整治,重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产业振兴+风貌提升+农村改革”统筹发力;通过对“山水林田湖草路村”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生态治理,串点成线、连线成片,重整乡村景色;通过土地整治与土地流转,实现文旅融合发展。
(三)衢州“党建治理大花园”的内在逻辑
“党建治理大花园”体系设计的科学性,在于党建、社会治理与大花园建设内在的逻辑性:把基层党建融入乡村振兴的各项工作之中,充分发挥党建统领功能,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把治理优势集中在大花园建设之中。
1.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党建统领功能
面对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中出现“两张皮”现象,跳出党建抓党建、结合乡村振兴工作抓党建,是发挥党建引领功能、实现党建创新的突破口,使党建与乡村治理和大花园建设的深度融合。首先,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功能。以党组织为核心,从各部门抽调人员组成的服务团队在短时间内就化解矛盾纠纷1.8万余起,彰显了政党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其次基层党建示范带建设。全市谋划了320个基层党组织示范创建项目,把全市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政治功能突出、基层治理有效、服务中心有力、紧密联系群众的坚强战斗堡垒。分散在全市各地的党建品牌,基于共同的主题串联起来,不同的示范带又并联成一个个条块结合、点面相融的党建共同体,通过网络把乡村振兴各项工作融合起来。
2.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促成乡村有效治理
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在于坚持党建“三个用来”原则,即党建是用来统领基层各项工作的;党建是用来为中心工作服务的,特别是用来克难攻坚的;党建是用来充分体现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的。在农村社会治理实践中锻炼党员干部,在服务群众、解决群众现实利益的过程中提高了对党的认同。各种组织、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下沉后,重组的网格不再是一个户与户组合的空间单位,而是在网格支部的领导下,以网格员为主导、农户参与、多方协同的社会治理、大花园建设服务團队。通过党建引领下的网格,治理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衢州获得了“中国基层治理最优城市”“中国营商环境最优城市”“国际花园城市”等称号。
3.发挥社会治理效能,全面推动“大花园”建设
有效的社会治理促进了“大花园”建设,把乡村的自然环境保护和人文环境建设结合起来,诠释了“美丽浙江”,乃至“美丽中国”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双重内涵。党建治理大花园的实践,重构了乡村振兴大花园体系。数字经济智慧产业、美丽经济幸福产业、农房体系构建和风貌提升的推进,在乡村振兴大道上迈出了扎实的步伐。5年来全市经济增幅首次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增幅名列全省第一,生态环境质量持续走在全省前列,城镇化率提高幅度名列全省第一,城市吸引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满意度名列全省第一。
四、衢州“党建治理大花园”与党建统领社会治理的契合
党建统领社会治理借鉴了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分析理路,利用新兴信息技术重新整合组织、资源、制度等,以便适应新技术下的治理要求。党建统领社会治理机制犹如一台机器,由动力、操作和控制三大系统构成,衢州“党建治理大花园”实践与党建统领社会治理三个层面的逻辑契合:满足人民的需求是动力机制,网格化管理是运行机制,制度建设是保障机制。从理念到行动再到制度建构,遵循了党建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规律。
(一)党建治理大花园的动力机制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我党的执政理念,是评价执政行为的重要标准。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以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为目标,是“党建治理大花园”的出发点。将服务重心下沉到基层,及时回应群众的利益需求,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人民需求决定了大花园建设项目的取舍、治理机制和监督机制的建构,引导全市党员干部集聚力量、集中资源、精准定位、找准目标,投身于乡村振兴战略之中。
利益调整总是与秩序形成相关。“一个社会,当它不仅旨在推进成员的利益,而且也有效地受着一种公共的正义观调节时,它就是一个良序的社会。”在衢州,也发现有些村书记不关注村民利益、村集体利益,而是借助书记头衔插手工程,违规捞取个人利益,甚至沦为黑恶势力,成为农村混乱的根源。而有的村组建网格党员“生产队”,把网格党员和农户结对联系、利益捆绑,党员认领管理,合理分成,村民、集体、党员各方利益均得到增长。以利益为纽带,促成了秩序的形成。
利益调整与政党认同联系在一起。一个政党整合功能危机的起点是意识形态对党员和普通民众影响力的下降。党员对本党的纲领和章程所确立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动摇、转移,是对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提出的最严重的挑战。通过“党建治理大花园”活动,实现了党组织与群众无缝对接、解决了关系群众利益的烦心事、根本上改变了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通过党建引领,拉近了党群距离、密切了党群关系、提升了党员干部形象,村民感觉到身边党员干部真正为民谋利,最终转化为对党的认同。
(二)党建治理大花园的运行机制
整体性治理的成功关键在于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没有高度发展的电子化政府,就无法跨越政府的层级鸿沟,也无法将数量庞大的行政机构和单位用电脑连接起来,以便向民众提供整合性的服务。”党建治理大花园依靠信息技术把党的建设、基层治理、乡村振兴三大任务融合在一起。
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党的统领功能就是依靠现代治理技术来贯穿的。活跃在衢州市各村社的网格支部、网格长、网格员,通过“网格+调解”“网格+警务”“网格+服务”等机制建成的网格,成为分布在全市各地的乡村治理、大花园建设的基本单元,又整合成一个集体,构成了党的建设厚实的社会基础。
通过党的基层组织,把党和国家掌握的各种资源,在全市范围内,集聚各种人力、物质、技术资源,依靠现代技术在市域统筹联动,凝聚成整体发展的合力。乡村振兴大花园建设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只有统起来,才能融起来、串起来、深下去。衢州市加强全市域统筹规划布局,串点成线、连线成片,发挥集聚效应、放大效应;全市域统筹政策资源,打通市县乡村、打通部门单位,改变以往“撒胡椒面”、天女散花、遍地开花的政策扶持方式,整合各方面资金、要素和项目,集中力量办大事。
(三)党建治理大花园的保障机制
党建治理大花园是制度化治理体系,关键是有一套完善的协调与整合机制。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构建党建治理大花园体制机制,在实践中,进一步形成了《关于全面开展“组团联村(社)”工作的通知》《关于实行“周二无会日”制度的通知》《关于全科网格规范提升工程实施方案》等从组织建设、工作程序、主体责任、监督保障等内容完善、相互协调的制度体系。
1.组织保障
流传于衢州各村社的“头雁勤,春风一夜到衡阳;头雁懒,万里寒云雁阵迟”诗句,揭示了“领头雁”与乡村治理和大花园建设各项工作之间的密切关系。“培养一支怎样的村支书队伍,怎样选优配强村支书队伍,怎样把村支书的作用发挥好”是衢州市委推动新时代党建工程所思考的基本问题。從党性、民情、激情、能力、底线等五个方面培养能胜任引领乡村治理、大花园建设的村支部书记群体,通过实施“村支书能力素质提升工程”使其真正适应“党建治理大花园”工作的需要,通过“严管+厚爱”“激励+约束”等机制提高村支书的责任感与积极性。
2.要素支撑
坚持整合优势资源投入到大花园建设中,形成齐抓共管的格局。习近平提出,要深化拓展网格化管理,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使基层有职有权有物,更好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和管理。积极推进党建下移、网格治理、组织再造、精英整合和村企结对等形式,引导不同的社会力量参与到乡村治理和大花园建设中,整合不同资源、形成“党建统领,多元联动”的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注入了新的内容。
3.规划导向
衢州“党建治理大花园”的成功,关键在于利用衢州生态资源优势,集数十年发展之力,抓住农房整治“牛鼻子”,把党的建设与乡村治理和大花园建设深度融合。从“三民工程”到“基层党建三个三”、从“枫桥经验”到“党建+治理”、从“千万工程”到“活力新衢州 美丽大花园”,是历届党委政府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年接着一年抓,集聚资源、分类推进、精准靶向、狠抓落实才取得显著成效。
五、结语
在中国的国家构建和治理中,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具有决定性作用,一方面党统领国家与社会,另一方面党又是国家与社会的联结中介。在三者关系中,政党是具有支配性地位的,党建统领社会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优势向治理优势的转化。衢州“党建治理大花园”是社会治理的理念、体制机制、方法手段的创新,深化了对社会运行规律和治理规律的认识,提升了社会治理效能。政党统领实现了政党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高度一体化,并不意味着可以抹杀三者之间的边界。“党建治理大花园”实践中也存在这种现象:当土地征用、违章拆除、环境治理等具体任务下达后,组建一支涉入其中的党员突击队,放下手头工作,全力投入该工作中,任何拒绝服从或参与不力的党员将给予严厉的处罚。很多时候,机关企事业工作人员和村社党员干部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事实上,如果过度强调党的干预性而忽视边界的存在,可能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是社会治理主体迷失与社会治理陷入困境。党和国家掌握了社会治理的各种资源,完全有能力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掌控。作为自治主体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如果完全依附于模糊边界的政府,相应的社会秩序将陷入僵化状态。政党统领社会治理的范围和程度将是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课题。二是社会治理的行政化趋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应该是强调整体性和协同性的统一,是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治理。政党统领很大程度上依靠行政命令、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方式,留有浓厚的压力型体制烙印,社会自发性参与治理不足。发挥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并不意味着政党和政府就要撤离社会,腾出空间留待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来弥补。社会治理创新本质上是政党、国家、社会之间关系的合理建构。在中国语境下,政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关系,决定了中国社会治理创新必然是政党引领下的三者关系重构。这是与党的性质与使命、传统文化相适应的,党建统领社会治理如何与协商性民主、国家治理现代化相一致,是一个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 王沪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要求:新权力结构[J].社会科学,1993(02):3-7.
[2] 吴新叶.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趋势及其应对[J].国家治理,2017(01):30-37.
[3] 叶敏.新时代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格局的实现路径[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04):18-24.
[4] 韩福国,蔡樱华.“组织化嵌入”超越“结构化割裂”——现代城市基层开放式治理的结构性要素[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5):47-57.
[5] 崔月琴.回到社会:非政府组织研究的社会学视野[J].江海学刊,2009(05):116-120.
[6] 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J].开放时代,2011(10):67-85.
[7] 李强,葛天任.社区的碎片化——Y市社区建设与城市社会治理的实证研究[J].学术界,2013(12):40-50.
[8] 杨君,徐选国,徐永祥.迈向服务型社区治理:整体性治理与社会再组织化[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3):95-104.
[9] 徐勇.农村微观组织再造与社区自我整合——湖北杨林桥镇农村社区建设的经验与启示[J].河南社会科学,2006(09):8-11.
[10] 李庆召,马华.价值与限度:农民再组织化与村级治理组织体系再造——基于广东省梅州市F村基层治理改革的思考[J].社会主义研究,2017(02):112-118.
[11] 陈明明.共和国制度成长的政治基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55.
[12]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377.
[13] 任剑涛.政党、民族与国家——中国现代政党—国家形态的历史—理论分析[J].学海,2010(04):103-115.
[14] 葛兰西.葛兰西文选[M].李鹏程,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17.
[15] 林尚立.领导与执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的政治学分析[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1(06):37-44.
[16] SIXP. Holistic Government[M].London:DemosPress,1997:26.
[17] 曾盛聪.迈向“国家—社会”相互融吸的整体性治理:良政善治的中国逻辑[J].教学与研究,2019(01):86-93.
[1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84.
[19] 王长江.政党政治原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267-270.
[20] 王韶兴.政党政治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472.
[21] 王邦佐,谢岳.社会整合:21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使命[J].学术月刊,2001(07):3-8,84.
[22] 刘惠.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与机制创新[J].重庆社会科学,2013(05):104-109.
[23] 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M].张华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37.
[24]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684.
[25] 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5.
[26] 王邦佐.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66-267.
[27] 彭锦鹏.全观型治理:理论与制度化策略[J].政治科学论丛(台湾),2005(23):61-100.
[28]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27.
[29] 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157.
(中文校对:黄玉玺)
Leadership of CPC Construction :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ocial Governance
JIANG Yufu
(Party School of Quzhou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Quzhou Zhejiang 324002)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mong the Party , the state and society determines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Party. The social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ust uphold the leadership of CPC, as it is a system of Party Committee leadership, government in charge,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social coordina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legal protection,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port. The CPC leadership means that everything i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the social governanc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PC includes four elements: a strong political party, an overall society, a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and a scientific leadership mechanism. It operates logically from the political function of the party to the improvement of its governance function. The basic logic of CPC Leadership and Social Governance Activity in Quzhou is to integrate the grass-root CPC leadership into Rural Revitalization, making full use of the leading function of the Party and transforming the advantage of CPC leadership into the advantage of governance.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Activity has a high logical consistency with the social governanc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PC. It integrates CPC leadership, social governanc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performance and governance so a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ocial governance.
Keywords: CPC leadership; CPC Leadership and Social Governance Activity; social governance; party-state-society
(英文校譯:陈琳)
收稿日期:2021-05-11
基金项目:浙江省党校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2020年课题“技术治理视角下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实现机制——基于龙游‘村情通’的研究”(ZX22223)。
作者简介:姜裕富,男,政治学博士,浙江衢州市委党校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发展、当代中国政治方面研究,E-mail: quzhoujyf@163.com。
姜裕富.党建统领:社会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以衢州为例[J].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1(04):7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