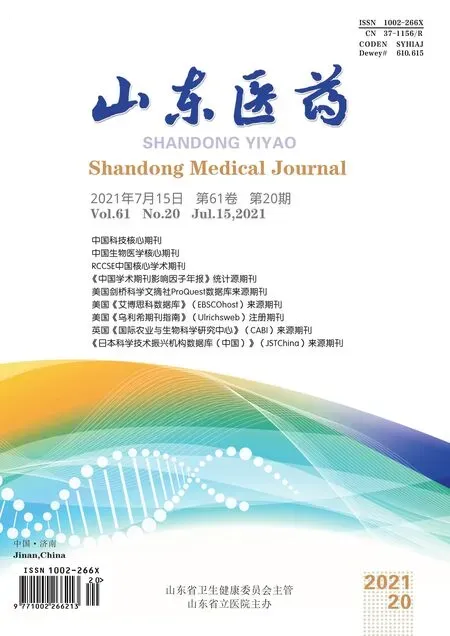肠道菌群变化与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发病的关系及相关治疗研究进展
2021-01-10李媛媛吴禹佳郑玲玲
李媛媛,吴禹佳,郑玲玲
1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预防保健科,重庆400037;2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是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常见的精神发育障碍性疾病。世界范围内,儿童ADHD 发病率约为7%,且呈逐年增高趋势[1]。学龄前儿童ADHD 症状主要表现为运动不稳定、攻击和破坏性行为,随着年龄增长,过度活跃、任性、冲动行为等会逐渐得到控制或减弱,但注意力不集中症状会长久保持,甚至持续终生[2]。ADHD 发病机制尚未明确,主要与遗传易感性、环境因素有关。近期研究发现,肠道菌群与大脑之间的双向交流可通过代谢途径、迷走神经途径和免疫途径等机制影响ADHD 的发生和发展,通过益生菌和饮食干预调节肠道菌群以治疗儿童ADHD 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现就肠道菌群变化与儿童ADHD发病的关系及相关治疗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预防或治疗儿童ADHD提供新的思路。
1 ADHD患儿肠道菌群变化
肠道菌群是人类肠道中大量存在的微生物,数量是人体细胞的十余倍。肠道菌群在2~3 岁时建立,因此生命早期和儿童时期肠道菌群的相关研究对于探索人体疾病的发生与发展过程至关重要[3]。近年来,多项研究表明,ADHD 患儿肠道菌群的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提示肠道菌群在ADHD 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AARTS 等[4]通过 16 S rRNA 基因测序研究了荷兰19 例ADHD 患儿和77 例对照组肠道菌群组成情况,对基因序列V3~V4 区域扩增和测序分析,发现ADHD 组患儿粪便中双歧杆菌属数量显著增加,是对照组的1.4~1.6 倍;该研究还发现ADHD 患儿粪便中环己二烯脱水酶(CDT)表达显著增加,且与双歧杆菌丰度增加显著相关。CDT 是一种单胺前体,参与苯丙氨酸的合成,而苯丙氨酸是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前体,神经递质水平表达有可能参与了ADHD 的发病。JIANG 等[5]分析了来自于中国的 51例ADHD 青少年和32 例健康对照组的肠道菌群组成情况,测序结果显示,ADHD 患者粪杆菌显著减少。张珊等[6]研究发现,ADHD 患儿与健康儿童的肠道菌群α 多样性一致,但在菌属水平上粪杆菌属明显降低,而肠球菌属、气味杆菌属增高;在菌种水平上发现ADHD 患儿的普氏栖粪杆菌、毛螺科菌及活泼瘤胃球菌显著减少,而拟杆菌、木假单胞菌及小韦荣球菌显著增多。PREHN-KRISTERSEN 等[7]研究则显示,ADHD 患儿肠道菌群α 多样性降低,且α多样性与多动症评分呈负相关,但α 多样性与注意力问题、冲动和临床症状之间没有相关性;该研究还发现ADHD 患儿肠道拟杆菌的相对丰度与多动、冲动水平呈正相关。
目前已知ADHD患儿肠道菌群的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但当前研究结论不一致,共识较少,ADHD患儿的肠道菌群变化特征仍不明确。分析原因:①入组年龄不同,例如AARTS 等[4]的研究中对照组年龄明显大于ADHD 组,由于双歧杆菌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减少[8],两组之间的年龄差异可能是重要的混杂因素。②研究设计不同,如粪便样品的制备方法、核酸提取和生物信息学分析技术不同,也可能导致肠道菌群研究的整体可比性较低,多数学者选择对 16 S rRNA 的 V3 和 V4 区域进行扩增[4-5],也有学者扩增的是 16 S rDNA 的 V1 和 V2 区域[7],这可能也会产生结果的差异。③大部分研究样本量偏小,并且是在不同国家、地区和种族之间进行的,饮食习惯可能也是影响肠道菌群的重要因素,导致不同研究结果之间可比性降低[9]。
2 肠道菌群变化在ADHD发病中的作用机制
肠道菌群的改变或失调可通过肠-脑轴而影响神经系统的发育与功能,继而导致ADHD 的发生和发展[10]。目前研究认为,肠道菌群变化参与ADHD发病的可能机制包括代谢途径、迷走神经途径和免疫途径。
2.1 代谢途径 代谢途径是宿主的微生物组、表观组和代谢组通过神经递质和代谢物的合成而发生的相互作用。有研究表明,与ADHD 症状有关的神经递质可由肠道菌群产生,例如双歧杆菌属可产生多巴胺,多巴胺缺乏会导致小鼠社交行为受损[11];乳酸菌属、链球菌属、埃希菌属、摩根菌属及克雷伯军属可产生血清素,血清素是与记忆有关的重要神经递质,主要调节情绪和认知能力[12];双歧杆菌属、乳酸菌属、埃希菌属可产生γ-氨基丁酸(GABA),可以舒缓或抑制过度兴奋和激烈的神经信息传导[13]。虽然还没有证据表明肠道中神经递质能穿过血脑屏障或直接与ADHD 患者的大脑功能产生联系,但肠道菌群可增加由乳酸菌、链球菌等产生的色氨酸(血清素前体)的循环利用率,循环中的色氨酸会穿过血-脑屏障,影响大脑中血清素的合成[14]。SWANN 等[15]的研究也表明,许多肠道菌群的衍生代谢物如丙酸咪唑能够以活性或前体分子的形式穿过血-脑屏障,供宿主大脑神经递质的进一步处理和利用。此外,肠道菌群产生的维生素B6、短链脂肪酸(SCFAs)等代谢物也可能对肠道、大脑和行为产生影响[16-17]。磷酸吡哆醛(PLP)是维生素B6的一种代谢活性形式,是去甲肾上腺素、色氨酸、血清素、多巴胺和GABA的重要辅酶。DOLINA 等[16]研究发现,ADHD 患儿 PLP依赖酶的活性受损,认为维生素B6代谢紊乱可能是导致ADHD 发病的重要生化紊乱。SCFAs(如乙酸、丙酸、丁酸等)是厌氧菌群对肠道内膳食纤维和抗性淀粉发酵的主要代谢产物,SCFAs 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肠-脑轴和大脑功能,用丙酸处理的大鼠可表现出认知受损和运动活动水平增加等ADHD样行为[18]。总之,神经递质通过代谢途径可作为细胞间的识别因子而影响神经系统功能,未来的研究需要减少代谢分析中的混杂因素,为ADHD 建立广泛和有代表性的生物标志物。
2.2 迷走神经途径 迷走神经是副交感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第10 对脑神经,由连接胃肠道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前后两部分组成,参与调节人体心率、呼吸和情绪、免疫反应、消化等功能。肠道菌群通过迷走神经向中枢神经系统传入信号,产生相应的神经元兴奋或抑制作用。例如长双歧杆菌可通过激活迷走神经通路,向中枢神经系统发出信号,降低肠神经元的兴奋性[19];刺激肠道迷走神经传入纤维会影响脑干的单胺能系统,该系统在情绪调节和焦虑症等精神疾病的发生中发挥重要作用。BREIT等[20]报道称肠道菌群对ADHD患者的情绪调节是通过影响迷走神经的活动而起作用的。持续的迷走神经刺激,即通过手术植入电极对迷走神经进行电刺激,可以增强大鼠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神经元功能[21],但目前还没有研究直接评估迷走神经刺激对ADHD 患者的临床影响。此外,三叉神经刺激的作用方式与迷走神经相似,有研究表明,使用三叉神经刺激治疗ADHD 患儿4 周后,临床症状明显改善且患儿耐受性好、风险性小[22]。上述研究表明,迷走神经途径是介导肠道菌群对大脑功能和行为影响的基础,该通路刺激不足可能是ADHD 发病的一种潜在机制,随着对肠道菌群-肠-脑轴研究的不断深入,针对迷走神经调节相关肠道菌群从而延缓ADHD 相关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发病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2.3 免疫途径 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学说认为,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的细胞间可通过直接接触传递或产生释放活性因子进行信息沟通,细胞因子不仅是免疫调节网络的中心环节,对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的功能也有调控作用。已有研究表明,肠道菌群通过免疫途径与ADHD 存在密切关联,肠道菌群失调导致肠道通透性增加,继而引起免疫失调[23]。在ADHD 患者中,炎症可导致血脑屏障和神经信息传导破坏,循环中的促炎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IL)-13、IL-16 和肿瘤坏死因子α 水平升高与ADHD 症状相关,导致ADHD 患者特应性疾病(包括特应性皮炎、变应性鼻炎、湿疹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率增加,研究者推测肠道菌群在特应性疾病和ADHD 的共同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24]。此外,肠道菌群的代谢产物如SCFAs具有抗炎作用,反过来可影响肠道菌群组成和宿主免疫系统的动态平衡,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肠-脑轴和大脑功能[25];SCFAs 可与肠上皮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等免疫细胞发生局部相互作用,影响肠上皮屏障功能和免疫耐受[26];SCFAs 也可直接到达大脑并作用于抗原递呈细胞,在维持中枢神经系统稳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7]。关于肠道菌群通过免疫途径靶向干预对ADHD相关临床症状(如情感和认知功能)的影响及机制尚需更深入的研究。
3 针对肠道菌群的治疗方案在ADHD 治疗中的应用
目前ADHD 的主要治疗方法是行为和药物疗法。哌醋甲酯是治疗儿童ADHD的首选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其常见的不良反应是失眠、厌食、腹痛和头痛[28]。考虑到精神兴奋剂的安全性和治疗依从性不佳,益生菌和饮食干预等非药物治疗AHDH 的方案备受关注。
3.1 益生菌 益生菌是对宿主健康有益的活性微生物,可通过多种方式影响宿主,包括调节肠道屏障的完整性和酶的形成、有机酸和抗菌化合物的产生、与肠道微生物相互作用及调节免疫功能等[29]。啮齿类动物相关研究发现,益生菌可增加皮质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功能,提高认知能力[30]。有学者对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使用益生菌辅助干预发现,益生菌能改善行为和神经生理状态,患儿的执行能力和注意力显著提高[31]。此外,有小样本研究显示,生命早期补充益生菌可降低ADHD的发病风险[32]。实际上,补充益生菌并不是作用于大脑影响行为,而是通过肠道菌群平衡改善肠-脑轴的相关功能、调节免疫来治疗ADHD,或可作为ADHD治疗的新思路。
3.2 饮食干预 饮食模式与ADHD 存在显著关联,高糖饮食和饱和脂肪酸过量摄入会增加ADHD的发病风险,而锌、铁、不饱和脂肪酸可减少或延缓ADHD 发病。与肠-脑轴相关的肠道菌群可能在ADHD 的饮食干预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33]。WANG等[34]研究显示,ADHD 患儿肠道菌群中的萨特菌属与乳制品、坚果、豆类、铁蛋白和镁的摄入量显著相关。STEVENS 等[35]对 17 例 ADHD 患儿进行为期 10周的随机对照研究发现,与安慰剂对照组相比,补充微量营养素可显著改善ADHD患儿的注意力和情绪调节能力;通过16 S rRNA 测序发现,补充微量营养素后患儿粪便中放线菌门丰度显著下降,很大程度归因于双歧杆菌增加,从而确认了双歧杆菌和ADHD之间潜在的关联,同时也说明使用微量营养素调节肠道双歧杆菌丰度,对减轻ADHD 患儿的多动行为有益。总之,饮食干预通过改变营养素的可利用性来调节肠道菌群,治疗ADHD 相对安全,无不良反应,更易被患儿家长接受,但进一步临床应用还需要更多的循证研究支持。
综上所述,ADHD 患儿的肠道菌群发生变化,异常的肠道菌群可能通过代谢途径、迷走神经途径和免疫途径调节ADHD 患儿的中枢神经系统、胃肠生理、免疫状态,继而导致ADHD相关行为的发生。通过益生菌或饮食干预可改善ADHD症状。随着肠道菌群在ADHD病因学和作用机制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预防或治疗ADHD的新靶点、新方案都将得到快速的探索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