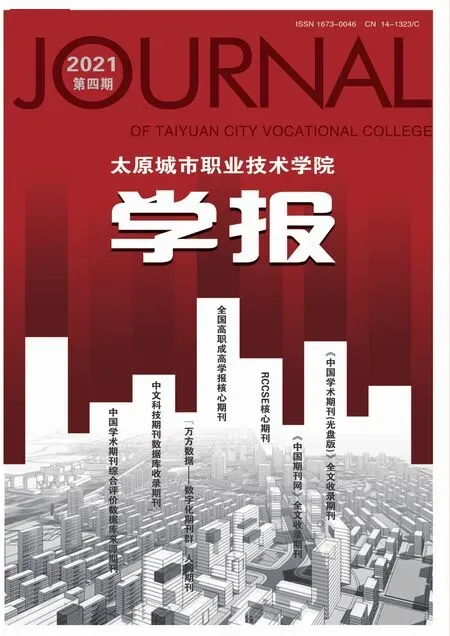论《古诗十九首》中人的自觉
2021-01-08黄红日
■韩 娜,黄红日
(新疆理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新疆 温宿 843100)
《古诗十九首》产生于社会混乱、政治动荡的东汉末年。它的作者多是处于社会下层的文士。他们在东汉末年天灾频频、战祸连连的环境下背井离乡、游宦无门,因而发出了韶华易逝、人生无常的感叹。同时,由于常年颠沛在外、流离失所,这些文人们也开始意识到了人的独立性,颠覆了传统“天降大任,动心忍性”的观念,高喊出及时行乐的诗句——“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生年不满百》)。文人们逐渐脱离了先民混沌无知的蒙昧状态,带领时代步入人的自觉的时代。《古诗十九首》可谓是“人的自觉”时代的滥觞之作。
王守国、卫绍生曾在《酒文化与艺术精神》中写道:“作为人的自觉的重要标志,就是全社会对人自身价值的再发现与再认识,以及文人士大夫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个性精神的追求,对人物品行的评判,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对人生短促的感伤”[1]。综合以上观点,笔者认为所谓人的自觉,就是指人类认识到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它明显的标志则是人类对生命的重视,对人生孤独的体悟,追求人的个性化,并以人为中心对世间价值观进行再判断。《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便是通过对生命价值进行再发现、再认识,来探求生命的意义,这正是“人的自觉”。
一、对生命的重视
《古诗十九首》通过对人生中各式各样悲苦的描述,反映出汉末布衣、将相忧生惧死的情感,勾勒出身处乱世的汉末文人对生命的深层焦虑,体现了东汉文人们对生命的重视。《古诗十九首》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展现其对生命的重视。
(一)离别之苦
《古诗十九首》中描写得最多的就是生离之苦,其中又以思妇之诗居多,如“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行行重行行》),诗句开篇便写到妇人“与君生别离”,别离之苦虽常有,但对于妇人而言在东汉末年这样一个战乱时代,士子或游宦在外,或流离颠沛,归期实难测。“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行行重行行》),夫妻双方生而不得见,这不仅造成了游子的痛苦,更成为了家中妻儿的悲哀。又如“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冉冉孤生竹》),妻子在家中痴痴地守候,盼望夫君早日归来。不知旅居在外的游子境况如何,“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凛凛岁云暮》),寒风凛冽,游子是否穿上了御寒的衣物。惟祈“愿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凛凛岁云暮》)。
游子在外,未必都是不能归,亦有不愿归的。且看这首诗“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青青河畔草》),倡家女子嫁做人妇本难觅得好人家,白居易《琵琶行》中便有“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之句。嫁做商人妇已属末流,更何况是以荡子为夫。作为倡家女能够脱离欢场泪歌的生活已属不易,妇人内心委实渴望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然而荡子却在外花天酒地,有家不归,妇人明明已嫁做人妻却不禁要问“谁适为容”?空床难独守,妇人面对“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青青河畔草》)的美丽景色,离别之思不禁涌上心头。无尽的孤独与妇人“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青青河畔草》)的明艳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令人不得不感叹“女为悦己者容”,妇人今日梳妆又有何人欣赏。
尽管思妇形象是《古诗十九首》描写的主要对象,但这并不代表这部作品只诉说了妇人之思,它还从妇人的角度看到了游子对家乡妻子的思念。“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孟冬寒气至》)“长相思”“久离别”是男方之语。这份鸿雁传书说的正是在外的丈夫对久别未见的妻子的思恋。男子对家人妻子的眷恋与思妇对游子的苦苦相思遥相呼应,令这份生离之悲更加动人心魄。
离人之诗中,有一首诗最为特别,它不同于《古诗十九首》中其他离人诗的因时而发,因事而发,而是借由牛郎织女星的传说生发开来,“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迢迢牵牛星》)。诗中运用比兴手法描绘了牛郎织女生而不得见、脉脉遥相望的哀婉缠绵的离人之悲,以此来比喻现实生活中的离别,跨越了时间与空间,超越了现实,愈发显得感人至深。
有了生离,自然就有死别。但与大量描述生离的诗相比,《古诗十九首》中只有区区一首关于死别的诗——《西北有高楼》,显得格外稀少。“死别之苦”不同于“死亡之苦”。“死别之苦”的重点在“别”,强调的是亲朋因死亡而分开,自此再无希望相见的伤痛;而“死亡之苦”则代表着人类对死亡的畏惧,与对生命的留恋。这里先来体味《西北有高楼》中的“死别之苦”。诗中运用杞梁妻临尸哭夫的典故——《礼记·檀弓》中曾子曰:“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叹道“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诗人将“杞梁妻”之悲与“弦歌声”之悲结合在一起,更加展现了“死别之苦”的伤痛。
(二)韶华易逝
东汉末年的一众文人在颠沛流离中已经对自己的生命存在有了明确的认识,对“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2]的“死亡之苦”充满无奈。韶华易逝,不同于《老子》中“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的宇宙全局观,《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立足于自身,面对人生短短数十年的生命,发出了“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今日良宴会》)、“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东城高且长》)、“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等等人生苦短的悲凉感慨。
从以上诗句可知,《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多关心四季时空的流转、景物的变化。同时,《古诗十九首》的作者通过对时空流转、万物更替进行不断地吟咏,来感知宇宙时空的永恒及人生时空的迁逝无常。宇宙无始无终、万物凋敝再生,昼夜迭代,四季轮回永无休止,而人生却不同于世间万物,人生只能一刻不停地向前行走,生命短促,何时消逝,亦不是人所能控。“这种宇宙无限之深层时空的体悟,唤醒了诗人敏感的心灵关于人生的迁逝之悲,更痛苦、更清醒地意识到生命一寸寸老去的悲伤,而这种悲伤,又把人们的目光投向自然界的深层”[3]。诗中用“陵上柏”“涧中石”“金石”“白杨”等长久稳定的自然形象与人的生命做对比,体现生命倏忽而逝,人难与天地同寿。人生已若烟花般短暂,各人的盛衰荣辱还不相同。文人士子羁旅一生却“盛衰各有时”(《回车驾言迈》),未必都能封侯晋爵,立于朝堂之上,也许是落魄一生,找不到归属之地,如陈祚明所述:“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于是生出了人生如寄、命运无常的忧思,这也成为了《古诗十九首》贯穿始终的情感基调。
二、对孤独的感悟
《古诗十九首》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其深刻反映了汉末下层知识分子的离愁别绪、苦闷彷徨,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汉末文人们在动荡不安、流离失所的乱世之际对生存意义、生命价值的追问和思考[4]。生命短促,充满了生离之悲、死别之伤,人由生至死,终究孑然一身,汉末文人终于意识到生命无法与人共享。笔者认为这在《古诗十九首》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对“故乡遥”的慨叹
故乡指出生或长期生活过的地方,是有亲人朋友所在的地方。对“故乡遥”的慨叹,其实就是对亲朋不在身边的感叹。如同前文所述,东汉末年,阉党作乱,战争频频,汉末文人身处乱世,流离在外,有些甚至客死异乡,妻儿父母终不在身边。“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客从远方来》),这不仅是思妇的感叹,也是游子的相思,游子身处异乡思念家乡妻儿才会万里托客人“遗我一端绮”(《客从远方来》)。“思归故里闾,欲归道无因”(《去者日以疏》),作客他乡的游子盼望回到故乡,去感受乱世中的团圆之乐,然而归乡之路却阻断重重。诗人“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明月何皎皎》)夜不能寐,揽衣徘徊,终只能无奈地喊出“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明月何皎皎》),旅居他乡虽然快乐,不如早点回到故乡。然而“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涉江采芙蓉》),远望返还故乡之路,路途漫长且遥远。
从以上众多诗句可知,汉末文人们为了能够历金门上玉堂,无奈远离家乡亲朋、游历在外,在动荡的社会中无法回归故土、无法把握人生,孤独之感油然而生。由于孤身在外,社会动荡不安,理想难以实现,汉末文人在生与死的挣扎中,内心的痛苦无人能体会,这令他们逐渐认清了生命的孤独与不可替代——“我”是唯一的,无人能携手与共,更没人能替“我”承担生命的苦楚。
(二)对“知音稀”的感伤
《古诗十九首》更进一步地通过对知音难觅的描写,体现了汉末文人们对人生孤独、人是独立个体的体悟。譬如在《西北有高楼》一诗中,诗人感叹了无知音之苦更甚于死别——“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皆是伤知音之不存,此处诗人通过“愿为双鸿鹄”来展现对知音的渴盼,通过“知音稀”来展现对个体孤独的感伤。文人自古惜知音,对于体悟到人生孤独的东汉末年的文人更是如此。魏晋是个性张扬的时代,东汉则是这个时代的开端,对于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的认识,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愈发疏远,在这样的环境下,知音仿佛能够温暖孤寂的灵魂,成为飘零人生的一个心灵归属,显得尤为难得珍贵。刘勰也在《文心雕龙·知音》中道:“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想来当时文人当叹:“数十载之生命,竟无伴我者。一曲高山流水之调,全无相和人。人生独悲,人生独悲!”
远去的故乡、知音的稀少是汉末文人感知孤独的重要来源。这些人生孤独之感使汉末文人们渐次向内探寻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开始意识到个体的存在与个体的重要性,这无疑成为“人的自觉”的重要体现。
三、社会价值观的主体化
生命短促,汉末文人们对于生命的认知致使他们更加珍惜生命,从而使他们自身的价值取向更加主体化、个性化。总的来说,汉末文人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
(一)功利化的入世观
黑暗的现实、残暴的政治,使文人们的仕途之路更加艰难,同时也颠覆了一些士子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岁月如梭,面对生命的飞速流逝,人类作为孤独的个体,人生无法让他人延续,世人更加注重今世的荣耀功名,如“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回车驾言迈》),诗人感叹生命短暂,不如早取荣禄功名。“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今日良宴会》)。此诗不仅表达出诗人对功名利禄的渴望,同时也尽显对贫贱的鄙弃“无为守穷贱,轲长苦辛”(《今日良宴会》)。通过诗句可知诗人们继承了西汉《战国策》所宣扬的追名逐利、一切以利为先的人生价值观。如清代学者陈祚明所述:“人情莫不思得志,……虽处富贵,犹嫌不足”,一旦富贵,他们甚至可以“逐臣弃妻与朋友阔绝”,如“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明月皎夜光》)。昔日的同窗好友一旦取得功名,便不念及曾经的友谊,就像丢弃脚印一般把我丢弃了。这看似毫不经意的比喻,不仅将昔日同窗的卑劣之态刻画出来,也将诗人内心的悲愤之情表达了出来,同窗如此,世态亦如此。
人生的短暂、社会的动荡、灾祸的频发,使得汉末文人更加关注当下生命的价值。这种功利的入世观便是文人们价值取向主体化的体现,文人们跳脱儒家思想的束缚,通过诗文更加直白地表达对富贵的渴慕,更加大胆地表达对荣名的追求。
(二)远离尘嚣的出世观
社会普遍价值观的功利化,撕碎了诗人的主体理想与对社会的期待,功利的社会与诗人传统的主体价值观产生了冲突,一些文人对炎凉世态忿忿不平,发出了“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明月皎夜光》)的感慨,表达了诗人对友情不在的哀伤、对世态炎凉的悲痛。有别于前述的追名逐利的士子,这些本是满怀抱负的文人们,面对孤独的人生,反而决定远离尘嚣,“将息交与绝游”,做到“养性延寿,与自然齐光”。“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明月何皎皎》),诗人直接描写了自己想要返乡归田与家人团聚的欲望,体现了与功利化的入世观截然相反的观念,这也成为魏晋文人如陶渊明等人归隐田园观念的萌芽。
作为“五言之冠冕”的《古诗十九首》用质朴自然的语言倾诉了末世文人们烦生畏死的苦闷、对生命的重视,它继承了不追问为何而生的中国传统哲学,在感叹人生无常后,没有进一步尝试去追究、去破译虚无,反而话锋一转,诗人吟唱出“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行行重行行》)、“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驱车上东门》)等的诗句,规劝世人珍惜生命、珍惜眼前,及时行乐。告诫人们“如何生”这一点,是对儒家《论语》“未知生,焉知死”的实用理性思想的继承。李泽厚说《古诗十九首》“在表面看来似乎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
《古诗十九首》作为汉末文人的人生悲歌,以其“直而不野”的语言,诉说了诗人们对生活执着的追求与留恋,生命无法替代,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人对“我”这一个体的珍惜,致使人的价值判断更加主体化、个性化,社会价值观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向。这种价值观的分化,正是《古诗十九首》作为“人的自觉”时代滥觞之作的有力证据。
《古诗十九首》语言率真、情感真挚,深刻再现了汉末文人的思想情感。同时,《古诗十九首》通过细腻的笔触抒发了汉末文人对人生百态的体察、对“我”的再认识。钟嵘《诗品》称《古诗十九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今日读来,读者除了能感受到汉末文人们细腻的情感、意境的悲远,更能够通过其对生命的重视、对孤独的感悟来感知汉末文人们的个体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