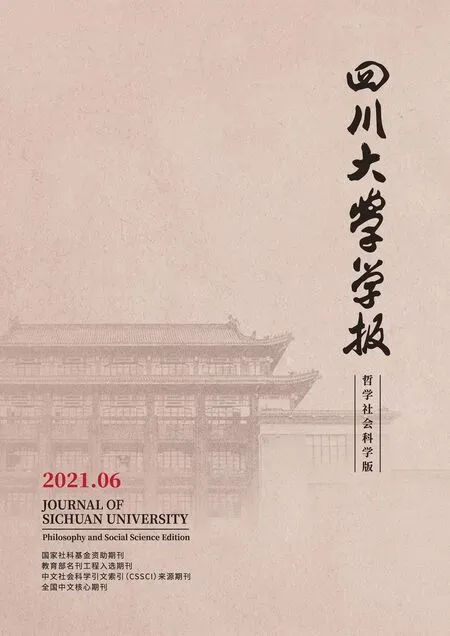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思想体系的历史建构
2021-01-08张德建
张德建
中国古代学术从先秦“孔门四科”逐渐演变形成了一个共有模式,即呈现为或文章、训诂、儒者,或道德、政事、文学,或道德、经义、文章,或道德、气节、文章,或学问、经济、文章,大体可以概括为道德、政事、文学的三分模式。这一模式涵括了儒学思想、社会治理、文学表达,三者呈竞争态势,但话语权和学术处境并不一样。道德、政事、文学构成一个内在自足的整体的学术体系,在唐代开始出现,到宋代得以完善,在元明清三代成为学术共识,这是自春秋以来学术分裂之后的又一次统一。当然,这只是表现在对体系的共同认可上,而不是思想的一统。宋代有道学、政事、文学三派,明代则可分为三个时期,前期以政事为中心,形成道德、政事、文学的学术体系;中期以文学为中心,怀疑虚伪化道德,摒弃了政事而代之,形成气节、文学同构的学术体系;后期在心学影响下,心性之学是当然的中心,强调政事、文学合一。清代学术在这个三分体系下进行调整,到了康乾之际形成两大流派:考据学派和桐城派。戴震提出以考据为中心的体系:义理、制数、文章;姚鼐提出以文章为中心的体系:义理、考据、辞章。随着盛世幻影的消失,桐城一派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为近代学术变革提供了巨大空间,先是义理之学再兴,直至康有为今文经学体系建构;再是重提经世之学,经济之学概念取代政事之学;最终,道德、政事、文学体系在近代新学术思想面前解体,但仍有影响力,例如牟宗三就提出了新三分体系。(1)牟宗三明确提出,“夫既曰外王,则其不能背乎内圣亦明矣。并列言之,曰政道、曰事功、曰科学;总持言之,皆赅于外王”;“又以‘民主政治、事功、科学’为三分”。参见牟宗三:《政道与治道》,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序言”,第2页;“新版序”,第17页。
由学术三分体系出发,我们可以深入探讨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这一学术体系,解释它是在什么样的思想背景下形成,其特质和新变在哪里,以及应该如何认识这些特质和新变?换言之,桐城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在整个学术思想史上处于什么地位?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一个宏大的学术史视野,而不能仅仅从文学层面的分析入手,本文即尝试从中国古代学术三分体系这个宏大叙事切入,讨论桐城学术在清代学术体系建构中的作用和意义。
一、道德与政事之学的衰退
清朝初期,随着政权的稳定,以士人为主导的道德、政事、文学三位一体的学术体系逐渐被消解,这首先表现为道德之学中“道”的解释权完全归于帝王,体系取消了士人之学的本体建构,学术由宋学转向汉学考据学,以知识的增加和细化取代道德本体和思想创造;其次是政事之学从国家治理的大政方针、精神建构等层面逐渐下衰至政务、地方治理层面,学者成为专制体制下揣摩圣意、看风使舵和维持地方秩序的行政官员。由此,一套形态完全不同的学术体系建立起来。
(一)道德之学的两个变化
道统之建构一直被视为士人权力,士子们以道自尊,以道自任,勇于直言极谏,敢于对抗皇权。这种情形在清代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意义与影响不亚于明清鼎革。从此,中国传统思想史被改写。如经筵制度是道权的体现,程颐有言:“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惧,莫敢仰视,万方承奉,所欲随得。苟非知道畏义;所养如此,其惑可知。”(2)程颢、程颐:《论经筵第三劄子》,《二程集》上,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39页。这种气度和自信在明代尚存,吕坤即言:“故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3)王国轩、王秀梅译注:《呻吟语正宗》,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82页。理势之中,理更高一层,势依理而存,甚至“有时而屈”,故儒者“敢于任斯道”,显示出士人掌握道统话语权的高度自信和坚定的使命意识。但在清代夷夏之防被打破、大一统的理论建构完成、道权归于皇权、道统与治统合一的大背景下,士大夫丧失了这种自尊和自信。
对于理学,康熙推崇并承认朱子之学得“内圣外王之心传”,但他突出的是“忠君爱国之诚,动静语默之敬,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4)《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四集卷二十一《朱子全书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34-535页。即合乎统治的一面。他说:“本之以建皇极则为天德王道之纯,以牖下民,则为一道同风之治,欲修身而登上理,舍斯道何由哉?”他对心法、道法的强调是为了“建皇极”,成为帝王之学,即其所谓“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5)《康熙帝御制文集》卷十九《性理大全序》《日讲四书解义序》,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第303、305页。周公之后,孔子称素王,有道权而无治权,而后士人虽然受到势的挟迫,仍坚守道权。至此,道权完全归于帝王。乾隆也提出“治统原于道统”,(6)《乾隆五年十月十二日内阁奉上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第1册,第648页。强调治道合一,他对宋人“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深表不满,认为惟有帝王才应该掌握道统之权:
古昔圣王之治民也,渐之以仁,摩之以义,节之以礼,和之以乐,熏陶涵养,使德日进而道自修。……故君师之责修,而道乃不虚。(7)《修道之谓教论》,故宫博物院编:《皇清文颖》卷十一,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227-228页。
修道即是教,二者是二而一的关系,别无所谓教,其权则归于“君师”。(8)参见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283-284页。于此,臣子亦审时度势地提出“道与治之统复合”,“任斯道之统”,如李光地在《进读书笔录及论说序记杂文序》中云:
臣又观道统之与治统,古者出于一,后世出于二。孟子序尧舜以来至于文王,率五百年而统一,续此道与治之出于一者也,自孔子后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年而至贞观,贞观五百年而至南渡。夫东汉风俗一变至道,贞观治效几于成康,然律以纯王,不能无愧孔子之生。东迁朱子之在南渡,天盖付以斯道而时不逢,此道与治之出于二者也。自朱子而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岁,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伏惟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统以升于大猷,臣虽无知,或者犹得依附末光而闻大道之要,臣不胜拳拳。(9)李光地:《榕村集》卷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4册,第669-670页。
此“古者出于一,后世出于二”的历史梳理,意在为康熙复合道、治而为一做铺垫,突显帝王“承天之命”的伟大,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道”归帝王之后,士人真的就只能“依附末光”了。
清代考据学兴盛,阮元说:“我朝列圣,道德纯备,包涵前古,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圣学所指,海内向风。”(10)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序》,《揅经室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7页。这种学术导向虽然提到了宋儒性道之学,但如陈康骐所言:“乾嘉以来,朝士宗尚汉学,承学之士,翕然从风,几若百川之朝东瀛,三军之随大纛。”(11)陈康骐:《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28页。考据学派尊奉顾炎武为开创者,但在精神上却完全不同,钱大昕已言:“经以致用,迂阔刻深之谈,似正实非正也。”(12)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序》,《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86页。放弃了“迂阔深刻”,就能得其正了吗?其所谓“正”,不过是自觉地与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以求自保,进而得其所得。这种对“圣人之道”的阐释权自觉放弃,实际是放弃了儒家士人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即刘师培所言:“清代之学迥与明殊。明儒之学用以应事,清儒之学用以保身。明儒直而愚,清儒智而谲。明儒尊而乔,清儒弃而湿。”(13)刘师培:《清儒得失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6页。明儒应世,表现为气节、结党、清议,其间虽不免装扮与矫饰的成分,但尊大自我之中保有坚定的信仰和操守。清儒退而自保,放弃对道的追求,学术变成了工具,混同世俗。
考据学“实事求是”,凌廷堪说:“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义理之学是也。”(14)凌廷堪:《戴东原先生事略状》,《校礼堂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17页。即是说,既然虚理不定,各执己见,就应该弃之以求实理。这种“实理”渐发展而为“实学”概念,考据成为进入圣人之经的必由路径,戴震在论述中将故训与理义对立起来,抓住理义之学的弊端并将其放大,认为唯有故训之学可以去除这种弊端,经明则理义明,但这实际上是将方法与目标等同,虽然最终仍是明理义,但却悄悄地将解释权放弃,仿佛故训明而理义自明。(15)戴震:《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戴震集》文集卷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14页。焦循更在《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云:
经学者,以经文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术算、阴阳五行、六书七音等为之辅,汇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训故,核其制度,明其道义,得圣贤立言之指,以正立身经世之法,以己之性灵,合诸古圣之性灵,并贯通于千百家著书立言者之性灵,以精汲精,非天下之至精,孰克以与此!
他甚至继续说“惟经学可以言性灵,无性灵不可以言经学”,(16)以上参见焦循:《雕菰集》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13页。虽用“性灵”概念,但与晚明性灵观念完全不同,亦与理学心性学说风马牛不相及,其义不过指人心而已。他坚持“求其训诂,核其制度,明其道义”,但在最后一环上也仍是含糊不清。故曾国藩说:
嘉道之际,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袭为一种破碎之学。辨物析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千万言。繁称杂引,游衍而不得所归。张己伐物,专抵古人之隙。或取孔孟书中心性仁义之文,一切变更故训,而别创一义。群流和附,坚不可易。(17)曾国藩:《朱慎甫遗书序》,《曾国藩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14册,第194页。
考据之学最终成为“破碎之学”,试图通过“变更故训”来阐释“理义”的路是走不通的。
(二)政事之学的沦落
“政事”包括广义的治国理政之道术,也包括地方治理的吏治,既可称之为“实政”,也可称之为“事功”。就社会而言,关注世风、风俗教化理论的流变,亦是政事之应有内容;而就个体道德境界而言,气节又是政事的变体。清代政事之学发生巨大变化,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礼学复盛。清初发生的“古礼”复兴,是士人“以宗族、家族为基本单位修复文化的根基”,是清廷上层“提倡以孝治天下的统治原则”,“导致清初遗民的道德自觉的行动更加无法逾越清朝统治者所构成的意识形态重建的巨大网络的控制”。(18)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第61页。对于礼治的重要性,清代统治者都有认识并大加倡导,雍正说:“朕愿与大小诸臣交相儆勉,详思礼义廉耻之大者。身体力行,则人心风俗,烝烝日上,而唐虞三代之治,庶几可以复见也。”(19)《清世宗实录》卷五十八“雍正五年六月壬寅”条,《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册,第891页。乾隆也说:“朕欲爱养足民,以为教化之本。使士皆可用,户皆可封,以臻于唐虞之盛治。务使执中之传,不为空言;用中之道,见于实事。多士学有所得,则扬对先资,实在今日,其直言之,勿泛勿隐。朕将亲择焉。”(20)《清高宗实录》卷十六“乾隆元年四丙寅”条,《清实录》,第9册,第428页。教化是正风俗之本,是礼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礼学事关秩序、等级,但自发的反思和建设与专制的介入并取得控制权不同,礼学为治术中的一部分,不是建立在道德自觉的基础上,而是作为权力附属品,以礼取代理,将秩序放在第一位,即方东树所言:
自古在昔,固未有谓当废理而专于礼者也。且子夏曰礼后,则是礼者为迹,在外居后,理是礼之所以然,在内居先,而凡事凡物之所以然处皆有理,不尽属礼也。今汉学家厉禁穷理,第以礼为教,又所以称礼者,惟在后儒注疏名物制度之际,益失其本矣。使自古圣贤之言,经典之教尽失其实而顿易其局,岂非亘古未有之异端邪说乎?夫谓理附于礼而行,是也;谓但当读礼,不当穷理,非也。(21)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上,《汉学师承记(外二种)》,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94页。
理是根本,“在内居先”;礼为行迹,“在外居后”,当二者关系被颠倒,视秩序为首而置思想的承传与阐释于后,这就消解了士人所据以立身行事的思想力量,“惟在后儒注疏名物制度之际”的汉学,不仅又将道统拉低了一个层次,更有陷于失去其作为思想根基的可能。
二是讲求实用实行。在对晚明文化的整体反思氛围中,清初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环境:“强调这一文化中支持服从权威的那些主题,描绘了一幅完全堕落的晚明宗派主义的图画,并且鼓励好的官员不要与其他人建立共同的目标,而要管好自己的事务,在政府的政策上效忠君主。”(22)倪德卫:《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页。康熙一方面尊理学,一方面又说道学家言行不一,不能求实用:“古今讲道学者甚多,而尤好非议人。彼亦仅能言之耳,而言行相符者盖寡。是以朕不尚空言。”这实际上把道学架空,从而政事之学也就没有了着落。他接着说道:“由此以观,不在空言也。故君子先行后言。果如周、程、张、朱,勉行道学之实者,自当见诸议论。若但以空言而讲道学,断乎不可。”(23)《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一十六“康熙四十三年六月丁酉”条,《清实录》,第6册,第190页。如此一来,政事之学也从士大夫手中落到皇帝手上。在帝王的权威下,臣子亦大谈力行实用,如汤斌在致黄宗羲信中说:“窃以学者要在力行,今之讲学者只是说闲话耳。诋毁先儒,争长竞短,原未见先儒真面目。学者不从日用伦常躬行实践,体验天命流行,何由上达天德?何由与千古圣贤默相契会?”(24)《交游尺牍·汤斌》,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1册,第403页。这就把思想的力量等同于治理事务的能力,表面上看似有理,实际上放弃了思想建构而遵从皇权政治的要求。
三是精神由刚毅转为靡弱。明代前七子以理想主义精神、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高尚人格的追求和对道义的坚守,形成了讲求气节的品格,取代了台阁文学时期的政事之学,盛行一时。在中国古代,气节更多地表现在政治活动当中,可视为政事的流变。(25)详参张德建:《论明代学术思想体系的建构与分裂》,《求是学刊》2014年3期,第137-147页。气节是天地正气,欲救天下,必须有“伏清死节”之士起而矫之,不仅关乎邦家兴亡,更关乎宇宙之存在。但清初学者的反思却偏向了另一边,如顾炎武说:“吾异日局面似能领袖一方,然而不坐讲堂,不收门徒,悉反正德以来诸老先生之夙习,庶无遗议于后人。”(26)顾炎武:《与潘次耕札》其三,《顾亭林诗文集》,华忱之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68页。这段话蕴含顾炎武因强烈的亡国之痛而引发的反思,而这种观点竟然自然地“与清官方的论述达成了惊人的一致性”,形成“江南士人与清朝帝王无意识的合谋”。(27)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第83、84页。清朝统治者一直以来就把结党结社视为明代颓风,康熙说明末之人“从师生、同年起见,怀私报怨,互相标榜,全无为公之念。虽冤抑非理之事,每因师生、同年情面,遂致掣肘,未有从直秉公立论行事者。以故明季诸事,皆致废弛。此风殊为可恶,今亦不得谓之绝无也”。(28)《康熙起居注》“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525页。乾隆在对东林党的评价中更是直奔核心:“即如东林诸人,始未尝不以正,其后声势趋附,互相标榜,糅杂混淆,小人得而乘之,以起党狱。是开门揖盗者,本东林之自取,迄明亡而后已,何取乎帝后殉节为有光哉!”(29)《御制文二集》卷十八《题东林列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1册,第394页。朝廷视士人结党为可恶可恨之事,务摧抑士气,统一官场,不得私议讲论,更不得上疏论列,官员奉旨而行,民间结社者无闻,所谓气节消失得无影无踪。当这种矫正之主张变成钳制人心统一舆论的政策,就必然充满危险,林昌彝说:“大臣无权,而率于畏偄;台谏不争,而习为缄默;门户之祸,不作于时,而天下遂不言学问;清议之持,无闻于下,而务料策营货财,节义经纶之事,无与于其身。”(30)林昌彝:《与温伊初论转移风俗书》,《林昌彝诗文集》,王镇远、林虞生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10-311页。在中国古代,政治活动中不讲节义,必然在官场上陷于“畏偄”“缄默”;对个人而言,则惟务“策营货财”。这个预言最终在清末得到证实,消弭了门户朋党,连清议也一并去除,自然不会有“节义经纶”。
四是实学递降而为治术。清代士人以道自信意识消失的同时,放弃了政治精神、思想与观念的建构,转趋于一种治理的技术路径,讲求所谓实政。政治精神、思想、观念即牟宗三所言“政道”,政道既不能建立,在理与势之间,权力的天平必然倾向于势。而且,这个势逐渐集中在一人身上,无人能与之抗衡,政事之学亦必衰落,乾隆说:
至名臣之称,必其勋业能安社稷方为无愧。然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国家之福。况历观前代,忠良屈指可数而奸佞则接踵不绝,可见名臣之不易得矣。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何则?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31)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历史资料丛刊:清代文字狱档》下册,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第597-598页。
于是,“自两汉以来,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都能够在中国社会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但乾隆却以虎视之态把四海治乱、生民利病划出读书人的思考范围,森森然剥夺了儒学赋予读书人的悲天悯人之权”。(32)杨国强:《世运盛衰中的学术变趋》,《晚清的士人与世相》,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50页。在传统社会中,入仕为官就要讲求治理,任何政事都须落实在治理层面,明清士人称为实政。丘濬的《大学衍义补》和吕坤的《实政录》是讲实政的代表作,前者讲经世之学,后者讲地方治理之术。吕坤及其《实政录》在清代极受推崇,如郑端的《政学录》大幅引用《实政录》,尹会一刊印的《实政录明职》中辑有《吕语集粹》,陈宏谋编刻《实政录》部分、从《呻吟语》摘为《吕子节录》等,而这些重视的起点皆在于“实政”价值。(33)参见解扬:《治政与事君:吕坤〈实政录〉及其经世思想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由此可见,清代政事之学已经沦落为注重政务处理的治术。
在孔门四科之中,道德之学是本体,政事之学是实用。政事是义理指导下的政治思想建构与实践活动,当思想的权力完全归于统治者,没有了本体支撑的政事之学就必然会沦落为治术。表面上看,考据盛行之时,汉学派也没有将政事完全抛开,如阮元《汉读考周礼六卷序》说:
政事之学,必审知利弊之所从生,与后日所终极,而立之法,使其弊不胜利,可持久不变。盖未有不精于稽古而能精于政事者也。……盖先生于语言文字剖析如是,则于经传之大义,必能互勘而得其不易之理可知。其为政亦必能剖析利弊源流,善为之法又可知。(34)阮元:《揅经室集》卷十一,第241-242页。
但刚讲完政事之重要,就转入到“精于稽古”才能“精于政事”的论证,如果勉强找关系的话,也只是汉学考据与政事“剖析利弊源流”法式样的相通,这不过是建构了一种偷换了概念的论述逻辑,而与事实相悖。
二、文学的空间:桐城派学术体系建构
在道德、政事、文学三分体系中,道德之学崩坏不堪,政事之学又衰萎不行,剩下的就只有文学了。在此背景下,桐城派于理学衰落之际坚守义理主张,以文学主持义理而兼考据,树立起桐城学术的大旗而风行于世。桐城学派建构出具有开放性结构的学术体系,使得它在晚清的大变局中成为主导资源,并且能够随时代变化而做出调整,这是其风行于世的关键所在。对比道学家和考据家普遍以辞章为载道或表达考据结果的工具,认为辞章本身没独立自性,排斥辞章甚至说“作文害道”,结果却往往是“拙于为文”“窒于文词”,(35)姚鼐:《疏生墓碣》《谢蕴山诗集序》,《惜抱轩诗文集》,刘季高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67、55页。桐城派以姚鼐为代表,一方面以开放的胸怀努力将考据、辞章融而为一,另一方面又大力倡导和坚持义理取向,既校正了文学空疏之失,也为文学注入了思想的活力。学界对桐城派文学体系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无需赘述,本文所关注的是其学术体系的特点及思想史意义,具体而言,就是桐城派何以有能力承担起重振学术的任务?本文以为,原因正在于桐城派所建构的义理、考据、辞章的体系,为学术实践提供了可能的空间。总体而言,这个体系具有以下特点:
(一)批判性
桐城学术的批判性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论争,而在于其不屈从于考据风行之现实,从观念和思考的立场树立起义理大旗,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资源。不屈从于时风,有独立思考和观念坚守,这本身就是建立在批判精神基础上的。
姚鼐早年倾慕戴震考据学,颇有同道之感,拜师遭拒后并未影响姚鼐对考据的兴趣,他投入大量精力研治训诂、舆地、礼学,学问的重心从辞章转向汉学考据。(36)参见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14-22页。但他不久就意识到了考据学的弊端:“立人通天地,斯足为大儒。多闻阙其疑,慎言而非迂。两汉承学者,章句一何拘。硁硁诚小哉,贤彼不学徒。”小大之间,其境界立现不同。姚鼐认为程朱之学“言之精且大而得圣人之意多也”,因而他选择程朱之学,认为程朱之学得孔孟之旨,虽有失不必曲从,但不允许诋毁:“儒者生程、朱之后,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犹吾父师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岂必曲从之哉?程、朱亦岂不欲后人为论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诋毁之,讪笑之,是诋讪父师也。”在他看来,“继孔、孟之统,后世君子必归于程、朱者,非谓朝廷之功令不敢违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无愧于圣门,而其论说所阐发,上当于圣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为大且多。使后贤果能笃信,遵而守之,为无病也”。(37)姚鼐:《漫咏三首》其二、《复曹云路书》《再复简斋书》《程绵庄文集序》,《惜抱轩诗文集》,第419、88、102、268页。这种选择在汉学盛行之际,不啻空谷足音,同时也承受了相当大压力。但姚鼐不仅坚守义理之学,还不断强化对汉学的批判,如其《赠钱献之序》云:
宋之时,真儒乃得圣人之旨,群经略有定说;……明末至今日,学者颇厌功令所载为习闻,又恶陋儒不考古而蔽于近,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蒐而遗其钜,夫宁非蔽与?(38)姚鼐:《惜抱轩诗文集》,第111页。
在突出宋儒得“圣人之旨”后,便集中于对“今日”学者的批判,指斥他们专求名物训诂,不讲义理;反对他们对宋儒的态度,指其不惜“窥隙攻难”;认为考据学只求枝叶,唯琐细是求。可以说,姚鼐对汉学的批判抓到其要害,此后各家的相关批判基本都在姚鼐范围内。批判性是保持学术生命力的核心,在道德、政事、文学三分体系中,思想层面的反思与批判尤为重要,在清代的政治氛围中,桐城派亦少有义理的精深与直面政治斗争的可能,但桐城派对考据派学术的批判,以及对义理的坚持与强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保留了政事之学的血脉,在特定的社会和学术背景下可以引发新的进一步的思考和批判,引领学术的变化。
(二)开放性
开放性是学术活力的保障,一个学术体系只有保持开放,才能不断适应新变,而这些都源于基本理论建构本身。桐城学术的开放性,正体现在其对义理、考据、辞章的兼容并包。
戴震《与方希原书》云:“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其弟子段玉裁亦云:“始,玉裁闻先生之绪论矣,其言曰:‘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考核之学。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39)参见《戴震集》文集卷九,第189页;“附录”,第451-452页。从表面看,戴震的主张与姚鼐十分接近,但实际他所建构的学术体系却是封闭的,义理、文章都被排除在外,形成“制数”“考核”独尊的局面。余英时即指出:“东原在理论上以义理为第一义之学,考证次之,文章居末。在实践上,东原则从事于考证之学,欲以之扶翼程朱之义理。因为此时他在义理方面尚无心得,并未深感程朱义理与六经、孔孟之言有歧也。”(40)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135页。在戴震的学术体系中,不仅义理是虚悬的,同时又是反对文学的:“仆尝以为此事在今日绝少能者,且其途易岐,一入岐途,渐去古人远矣。”之所以入歧途,其理由是:“自子长、孟坚、退之、子厚诸君子之为之,曰:‘是道也,非艺也,以云道。’道固有存焉者矣,如诸君子之文,亦恶睹其非艺欤?夫以艺为末,以道为本。诸君子不愿据其末,毕力以求据其本,本既得矣,然后曰:‘是道也,非艺也。’”(41)戴震:《与方希原书》,《戴震集》文集卷九,第189页。这就把文学降低到技艺层面,而全然不顾文学对道的强调和尊崇。王鸣盛在此基础上加上了经济之学,以“夫天下有义理之学,有考据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词章之学”。(42)王鸣盛:《王戅思先生文集序》,《西庄始存稿》卷二十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26-327页。虽说“义理之与考据常两相须”,但在汉学中二者并没有可以相联的途径,义理终究无法落实;经济可以“泽物”,却无实践空间,也只是“枝条”,是“事为之末”;文学则是“润色”,只是“波澜”,更是等而下之。因而,牟宗三说“这个要求事功的传统再转而为清朝乾嘉年间的考据之学,则属要求事功观念的‘变型’”,“骨子里还是以有用、无用的事功观念为背景”,“音读《训诂》、《说文》、《尔雅》之学,托汉学之名以张门户,自鸣为实学、朴学,以排宋学,殊不知其为帮闲清客之污习,乃不实不朴之尤者”。(43)牟宗三:《政道与治道》,第2页。总之,在以考据为中心的学术体系中,虽然理义、制数、文章,再加上经济,四者备具,但因其排斥文学,虚悬义理,经济亦无着落,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具有强烈的排他性。
姚鼐建构的桐城学术体系却有着根本不同。首先,他置义理于首位,认为“夫古人之文,岂第文焉而已,明道义、维风俗以昭世者,君子之志;而辞足以尽其志者,君子之文也。达其辞则道以明,昧于文则志以晦”;(44)姚鼐:《复进士汪辉祖书》,《惜抱轩诗文集》,第89页。又说“第自得程朱所解,学者依以为成己之序,义理当而道术明,垂世立教,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斯亦足矣。其得失非以区区章句间也”。(45)姚鼐:《中庸指归中庸分章大学发微大学本旨》,《惜抱轩书录》卷一,清道光十二年毛岳生刻本,第7页。在姚鼐这里,义理并不是虚悬的,他建构的是一个体用兼具的体系,尽管如研究者所言,姚鼐没有形成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46)吴微:《姚鼐的宋学情结与文章风度》,《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第17页。但这仅是就其学术成就而言,而非指桐城学术体系,“姚鼐论述义理、文章、考证三者关系时,与诸家最大的不同是,他把躬行为己视为第一义谛”,“比起躬行为己来,义理、文章、考证均在第二义以下”,(47)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第172页。他说:
言义理虽未逮于躬行,而终于躬行为近。若文章、考证之事,举其极亦未必无益躬行也,然而以视义理之学,则又远矣。子曰:学之不讲,吾忧也,非义理之谓乎?(48)姚鼐:《复林仲骞书》,稿本,安徽省博物馆藏。转引自王达敏:《曾国藩总督直隶与莲池新风的开启》,《安徽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第61-70页。
这种躬行的主张在儒学史上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在悬置义理的时代,则有着保存义理、坚守儒学思想实践性的价值。强调“躬行”,一方面缘于对汉学诸家忽略人品修养的不满,(49)参见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第174页。同时也在于它合乎清朝的统治政策。清代皇帝在谈到儒家常说时,往往强调躬行实践,反对义理阐释,桐城派提倡躬行既是理学思想自然延伸,也让“义理”拥有了正当性,不仅为后世理学的复兴保存了思想的种子,更为桐城派的盛行奠定了一个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使桐城派在长期的学术演变中总能保持活力。
义理是根本,文章、考证是辅助,三者可以相济而生,姚鼐《述庵文钞序》云:
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闻而浅识者,固文之陋也。然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以为文之至美,而反以为病者何哉?其故由于自喜之太过而智昧于所当择也。夫天之生才虽美,不能无偏,故以能兼长者为贵,而兼之中又有害焉。岂非能尽其天之所与之量而不以才自蔽者之难得与?
他在《复秦小岘书》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鼐尝谓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必兼收之乃足为善。……天下之大,要必有豪杰兴焉,尽收具美,能祛末士一偏之蔽,为群材大成之宗者。”(50)两文参见姚鼐:《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四、六,第61、104-105页。可以说,姚鼐所建构的桐城派理论体系是一个“尽收具美”,兼容并包的系统,依然沿续着学术三分的基本特征,即以德行为中心,辅之以躬行、文学。
(三)发展性
理论体系的开放性,不仅在基本理论层面为当世提供了可以不断挖掘的资源,借助于这个资源或者某种启发,后世还可以拓开空间,向不同方向发展。道德、政事、文学的三分体系在历史发展中不断调整,形成一个以对道德的推尊为根本,或强调政事,或突出文学,根干完全、体用并举的具有实践性的学术体系。离开了道德、义理,这一体系就成了无根之木,陷入没有思辨和实践的僵死状态。桐城派思想史意义就在于它对义理之学的坚守,为学术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可能。正如美国学者倪德卫所观察到的,“朱子学虽然仍是正统——至少对于应对科举的问题是如此,但在它思辨一面的兴趣则变得不再时兴。朱子仍然在某些特定的文学圈有其影响,著名的有18世纪的桐城”。(51)倪德卫:《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杨立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页。桐城学术这种发展性特征,我们可以举两个例证:一是章学诚学术思想中的桐城影子,尽管章学诚建构的体系有着强大的逻辑,非桐城学派所能比肩,但可证桐城学术空间的可延性;二是曾国藩承桐城衣钵,发扬变革,为桐城派注入新血液。
章学诚对考据学也深表不满,他说:“古人本学问而发为文章,其志将以明道,安有所谓考据与古文之分哉?学问、文章,皆是形下之器,其所以为之者,道也。彼不知道,而以文为道,以考为器,……其谬不待辨也。大抵彼本空疏不学,见文之典实不可凭空造者,疾如讐仇,不能名之,勉强名之为考据(天下但有学问家数,考据者乃学问所有事,本无考据家),因而妄诽诋之。”(52)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与吴胥石简》,《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79页。由形上的体用关系入手,章学诚迅速抓到了考据学的要害,并建构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他通过历史的方法屏除了道的绝对性和神秘性,认为道存在于历史和事物之中,不能被抽象出来加以阐释。在他看来,孔子“尽其道以明其教”,是述而非作,由于六经是在治教分离背景下孔子加以整理的结果,而道是不能脱离事物“呈示自身”的,后人要想理解道,必须进行艰苦的经学研究。而经学研究又存在着三种类型:文本研究、哲学分析和技术细节上的训诂学研究,但三者各是其是,“门径逾岐,而大道逾隐矣”。为了抵达整体化的、原初的道,研经者必须回到对“文”的理解之中。在章学诚的认识之中,文包含着三个层次:文、事实和法则,三者是合而为一的。由此,他建立起一个以“文”为中心,包含理解经典手段的研究即训诂学和哲学分析即对道的体悟与把握的学术体系。(53)详参倪德卫:《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第79-101页。当然,章学诚所说的“文”已经不同于其所处时代普遍的理解,这是他要回到远古传统和原初认识的一个主要原因。桐城派的文章、文辞自然不同于古代的“文学”,二者有着广狭之别,但不可否认它们又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建构的体系,与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有异体同工之妙。
三、何以启发新变:晚清桐城派的学术调整
乾嘉以来,考据派占据学术高地几十年,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学术潮流,曾国藩描绘说,“嘉道之际,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有宋诸儒周、程、张、朱之书,为世大诟。间有涉于其说者,则举世相与笑讥唾辱”。(54)曾国藩:《朱慎甫遗书序》,《曾国藩全集》,第14册,第194页。尽管期间也有袁枚、翁方纲等的批判和调和,包括其后来的追随者凌廷堪、焦循、许宗彦、夏炯等,如凌廷堪认为唯尊考据会使“天下不见学术之异,其弊将有不可胜言者”,(55)凌廷堪:《与胡敬仲书》,《校礼堂文集》,第206页。。许宗彦指斥考据“施诸当世,无一可用”。(56)许宗彦:《寄答陈恭甫同年书》,《鉴止水斋集》卷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4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02页。但随着社会变化,越来越多的学人开始反思和批判考据之学。嘉道之际,清王朝已呈衰败之象,引发了士人的忧患意识,促使他们关注和反思现实的弊端,而这种反思一般始于对士风、官场的批判,进而从更高的学术层面展开,如梅曾亮《复姚春木书》云:“然说经者自周秦以来,更历二三千岁,其考证、性命之学,类不能别出汉唐宋儒者之外,率皆予夺前人,迭为奴主,缴绕其异,引伸其同,屈世就人,越今即古,多言于易辨,抵巇于小疵。其疏引鸿博,动摇人心,使学者日靡刃于离析破碎之域,而忘其为兴亡治乱之要最、尊主庇民之成法也,岂不悖哉!”(57)梅曾亮:《柏枧山房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5年,第22页。虽拉上了“性命”作为批判对象,但仍沿着乃师姚鼐的路径,主要指斥汉学之失。桐城派对考据学的批判在方东树手中达到高峰,他宣称“要之文不能经世者,皆无用之言,大雅君子所弗为”,批判汉学说:“行义不必检,文理不必通,身心性命未之闻,经济文章不之讲,流宕风气,入主出奴,但以一部《说文》即侈然自命绝业。”(58)方东树:《复罗月川太守书》,《考槃集文录》卷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07册,第222-223页。认为汉学之失在行检、文理、性命,更在经济,这也仍是沿续着姚鼐的理路,只不过危机意识更加浓重。当我们以后学之明看待方东树时,王汎森的看法很有见地,他说方东树“代表着道光间一大批希望转弦易辙的士大夫共同的想法”,“他们想追求一种理想的人格,简言之,一种整合政事、文学与道德为一的整体观念”。(59)王汎森:《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第19页。于是,便有了曾国藩的学术重建。
曾国藩的学术思想有四个特点:一是将汉学与宋学联结起来;二是重视史学;三是会通理、礼;四是不废陆王。(60)参见武道房:《汉宋之争与曾国藩对桐城古文理论的重建》,《文学遗产》2010年第2期,第136-146页。这些都缘于曾氏与桐城派的“冥合”,共宗程朱理学,共主汉宋调合,理学经世。(61)曾光光:《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福建论坛》2004年第12 期,第60页。曾国藩正是在姚鼐义理、考据、辞章体系的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的学术体系。他是晚清较早将后世学术体系联系到孔门四科的人,其《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云:
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
对此不可小视,此前清人很少做这样的追溯。这样一来,桐城学术中政事、经济之缺就被补齐,从而既为他重建一个体用皆备的学术体系找到了思想支撑,同时,也找到了历史支撑点。他接着又说:
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曷尝舍末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观其雅言,推阐反复而不厌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62)以上参见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第14册,第486-487页。
这段文字系统地阐释了义理之学与经济之学的关系,比之桐城派的义理论述单纯地强调躬行实践要更加深入、全面。同时,曾国藩重视词章,认为“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63)曾国藩:《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曾国藩全集》,第20册,第49页。也重视考据,他说:“余观汉人词章,未有不精于小学训诂者,如相如、子云、孟坚于小学皆专著一书,《文选》于此三人之文著录最多。余于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马迁、韩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于小学训诂,不妄下一字也。……自宋以后能文章者不通小学,国朝诸儒通小学者又不能文章。”(64)曾国藩:《谕纪泽》(同治元年五月十四日),《曾国藩全集》,第21册,第23页。在承续桐城体系的同时,最大的变化是重提经济,强调义理与经济二者不可分,只有体用之别和顺序差异。
曾国藩借助桐城资源“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而合辙首先是突出义理,由强调义理之学自然延伸到强调经济之学,曾国藩认为“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义理是根本,“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65)以上参见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日记》《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第14册,第205页;第16册,第92页;第20册,第49页;第14册,第487页。经济之学该括于义理之中。姚鼐的学术体系中是不包括政事的,涉及社会实践和应用层面的内容,被转移到个体的“躬行”之中。曾国藩之讲经济是从讲义理中延伸出来的,正可见桐城学术体系的可发展性,由考据是不可能发展出“经济”来的。
在曾国藩的影响下,其后学对“经世”十分重视,黎庶昌《庸庵文编序》云:“道光末年,风气薾然,颓放极矣。湘乡曾文正公始起而正之,以躬行为天下先,以讲求有用之学为僚友劝,士从而与之游,稍稍得闻往昔圣贤修己、治人、平天下之旨。而其幕府辟召,皆极一时英隽,朝夕论思,久之窥其本末,推阐智虑,各自发摅,风气至为一变。”(66)黎庶昌:《拙尊园丛稿》卷四,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256-257页。桐城学派所建构的是一个开放、发展的体系,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经济之学,但并没有完全放弃。方苞就提出“明诸心,以尽在物之理而济世用”,强调“无济于用者,则不学也”,(67)方苞:《传信录序》,《方望溪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第298页。并且“方苞之论经制,论地丁银两,论常平仓谷、漕运、荒政,皆有关财赋也;泽望之征,苗疆之议,塞外屯田,台湾建城,皆有关边阃也。……议开海口,论治浑河,议黄淮,议圩田,论禁烟酒,皆吏事也”。(68)吴孟复:《方望溪先生遗集序》,《方望溪遗集》,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前言”,第1页。姚鼐也认为文章应该表现“忠义之气,高亮之节,道德之养,经济天下之才”。(69)姚鼐:《荷塘诗集序》,《惜抱轩诗文集》,第50页。从方苞到姚鼐,虽然从财赋、边阃、吏治的具体行政层面跌落到个体躬行层面,毕竟还在坚守义理,也未废经济之学。到了晚清,以文学为中心的学术体系启发了曾国藩,经济之学兴盛,学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然,晚清学术的这种变化是建立在整体学术反思基础上的,它的形成是时人不约而同的选择,并非只展现在曾国藩一人身上。陈澧以为“德行、文学,即宋学、汉学两派也”,(70)陈澧:《与徐子远书》,杨志刚编校:《东塾读书记》,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269页。提倡四科之学是对圣人之学的继承,因为“学问当各专一门,分之,则人各不同;合之,则于圣人之道无所缺矣”。(71)陈澧:《东塾杂俎》卷十二,黄国声主编:《陈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92页。意思是说,各人治学虽自专一门,但在圣人那里却是一个整体,因此要放开眼界,注意到专门之外的整体。这是针对考据派唯我独尊的一个指控,意在调合汉、宋。故钱基博说:“陈氏何为而作《东塾读书记》也?曰以救敝也。”(72)钱基博:《古籍举要》,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前言”,第1页。救弊的内容很广,就学术而言包括救考据派之弊,而提倡四科之学无疑有着强烈的针对性。康有为曾概括朱次琦论学大旨说:“先生壁立万仞,而其学平实敦大,皆出躬行之余。以末世俗污,特重气节,而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其教学者之恒言,则曰‘四行五学’。”(73)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6-7页。所谓“四行”,指敦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指经学、文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在这里,朱次琦不仅重提“性理之学”,也加入了“掌故之学”即经世之学的内容,与陈澧、曾国藩如出一辙。
以上诸家之中,只有曾国藩承桐城衣钵,陈澧、朱次琦与桐城并无关系,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桐城派开启了晚清新变的认识。桐城派建构了一个以文学为中心的学术体系,它以义理为本,以考据为补充,虽然只是强调躬行层面,缺乏政事实践空间,但其体系具有开放性和发展性,有便于后世开拓的空间,其对义理的坚守也为后世理学的复兴保存了思想的种子,在适当的土壤中就会发展开来,晚清义理之学的再兴就证明了这一点。而由义理延伸到经济,是学术的自然延展,于是我们看到经世之学在晚清的兴盛。而这些,都可以追溯到桐城派所建构的学术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