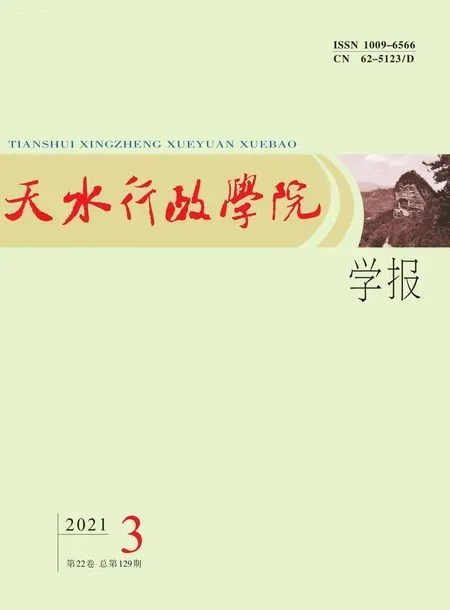基于广告代言人的视角审视带货主播的法律责任
2021-01-07刘博
刘 博
(上海政法学院,上海201799)
网络带货行业最近异军突起,然而其所引发的法律风险也在加剧。当消费者从带货主播处购买到假货甚至遭受产品质量侵权时,能否要求带货主播承担广告代言人对商品的连带责任便是当下讨论的热点话题。笔者将通过阐述广告代言人的要素及其连带责任理论依据,详细的讨论带货主播的身份属性及其法律责任。
一、《广告法》规制下广告代言人的构成要素
《广告法》关于广告代言制度的立法逻辑是“主体—行为—责任”,其蕴含的逻辑关系便是符合特定条件之人实施代言行为才能被定性为广告代言人,进而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这样的规范逻辑,广告代言人适用范围便直接取决于主体要素和行为要素的概念涵射范围。
(一)代言人的主体要素
广告代言人是不直接隶属于广告发布者和商家并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主体,其作为广告宣传活动的重要参与者,须要求行为人在相关受众中具有知名度才能满足主体要素。根据学术界主流观点“产品符号说”,商家将具有社会知名度的明星或者公信力的专家作为代言人,通过将其人格特征与商品的卖点进行连接和隐喻,最终将他们塑造成商品的代表符号。这便能够激发消费者对知名人士与商品之间的记忆节点,使代言人与所代言的商品合二为一,极大地增强了消费者对商品的感性认识。兰博基尼跑车与其代言人梅西之间的关系即为证明,通过代言所引发的强烈暗示,消费者不反将梅西的成功和足球赛场的迅猛与兰博基尼跑车的奢华、尊贵和风行电掣的速度相联想,进而幻想如果拥有一辆兰博基尼跑车就会成为像梅西一样的成功人士。相反如果兰博基尼跑车聘请默默无闻的一般民众作为代言人,便难以达到如此理想效果,更不能有效地赢得消费者的青睐。因此,无论基于理论分析还是日常经验,具备较高知名度是广告商选择广告代言人的前提,其对广告代言人的重要意义便不言而喻。
实践中代言人的知名度界定标准却很难判断,目前关于“代言人”较为权威的释义应当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限缩解释。它将以能否被观众辨别身份作为评判知名度的准则。这便产生了广告代言人和广告演员的辨认标准:一是在广告中明确注明身份或者虽然没有标注身份,但是能被该领域的观众识别之人,应当属于广告代言人。二是在广告中没有标注身份且不能被观众识别的人应当属于广告演员。前者利用自己的名誉为商品提供推荐和保证,不仅提高商品宣传效果而且增强消费者对商品质量的认可度,而后者难以影响观众的购买信赖,因此前者理应受到《广告法》的约束。
(二)广告代言人的行为要素
行为要素是指行为人以自己的名义及其形象为商品、服务提供推荐效果的代言行为,即《广告法》第二条第5款中“推荐”“证明”之意。而这通常属于民法之信赖保护原理能够引发信赖利益的典型表意行为。由此看来,行为人在广告中能否起到诱发合理信赖的推荐、证明作用便是认定代言行为的关键所在。
根据民法表意行为的理论,代言行为应当包括两个具体特征:一是意思表示;二是效果意思。前者指行为人须作出对商品品质、美观等“担保”的主观意图,该表示应当从代言人的语言、肢体动作和表达方式多角度综合判断。后者便是指通过意思表示诱发相关受众产生合理的信赖效果。实践中存在大量的广告便可表明商家利用名人的社会公信力和推荐、证明行为引发消费者信赖,进而使其商品获得较多竞争优势。如果知名人士没有表达对商品购买推荐的独立表示,只陈述商品客观既定事实或者尽管有代言的意思但是不能使消费者产生合理的信赖,便难以归属于《广告法》中“代言”的概念涵射范围之内,将其定性为引人注目的宣传行为更为恰当。因此代言人是否欲表露独立的主观推荐并使受众引发合理信赖的表意行为便是甄别代言行为的焦点。由此可鉴,知名度和代言行为是广告代言人不可或缺的要素,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关键,二者共同构建起广告代言制度的核心。
二、从保护信赖原则的角度阐述广告代言人的连带责任
社会各行业知名人士的独特品质都代表着社会公众所喜爱或者偏好的某种符号意义,广告代言行为便是将公众所青睐知名人士的某种符号意义或者品质特点附加到了商品,通过新闻传播媒体反复播报,不断刺激社会公众的主观印象,激发公众知名人士与商品之间的记忆节点,使这种联系在消费者潜意识中稳固建立。一旦这种联系被确立以后,消费者对名人的好感和信赖也便成功的转移到了商品上。由于知名人士代言效果会无形中增加消费者的信赖,从而较大地影响消费者购买商品的决策。这种因果关系早已被广告心理学中“意境迁移理论”所充分论证:通过将代言人的人格形象与商品的市场定位相连接,稳固打造二者之间产品符号联系,以此迅速增强商品在消费者内心的认可程度和主观印象,进而将消费者对代言人的好感迁移到商品之上,最终使得商品赢得消费者的信赖。这种“意境迁移”不仅奠定了广告心理学的理论架构,同时也阐述了名人代言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逻辑基础,即因信赖而购买的因果关系。当今尤其是知名度比较大的网络主播,当他们为消费者推介商品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利用了自身的影响力和积累的人气来帮助商品推介给更多的消费者。消费者在选择购买商品之时,大多情况下不是基于对产品质量的信赖,而是凭借着自己对网络主播的信赖和好感,即消费者将对主播的信赖和好感转嫁到了产品上。广告代言正是凭借着这种类型的推广增加了商品的产品曝光度和观众好感度,从而帮助商家促成更多的交易机会。
根据信赖原理,因合理信赖而付诸于实践之人,不应当因对方反言、欺诈或过失等过错,使其丧失所期待的正当利益。为保护由此引发的信赖关系,虚假允诺便不依赖契约关系随之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责任。正因如此,消费者被诱发的合理信赖构成广告代言的法律评价之基础,这也是《广告法》五十六条第2款规定代言人对虚假代言商品承担连带责任的理论依据。
三、网络带货主播的广告代言人身份之审视
网络带货的模式有自主带货和受托带货之分,前者指商家聘用主播并利用商家媒体账户开展直播等活动宣传销售自己的商品,即自产自销;后者指主播通过接受商家的委托,利用自身媒体账户对商品讲解和介绍,推荐销售者购买,从而在成交额中收取一定的佣金。无论采取何种带货模式,只要带货主播符合广告代言人的构成要件便具有相应的法律地位,因此其应受到《广告法》五十六条第2款的规制。根据上述代言人的主体要素要求,像李佳琦、薇娅、罗永浩等这样的知名主播才能被观众自发的辨认出身份,进而具备适用广告代言制度的前提;而其他知名度较低,观众也难以识别的带货主播很难定性为代言人,因此他们不应当承担广告代言人的责任,笔者重点讨论符合代言人身份的知名主播之行为模式。
在实践中,这些主播对商品所采取的推广方式不尽相同,有的陈述、介绍商品外观、功能等特征,而有的则使用张皇铺饰的辞藻和语气烘托良好的购物氛围。这种推广方式的差异所诱发受众的信赖程度有所区别,进而也会影响其法律地位和责任。倘若他们只对商品的客观属性做宣传,而没有夹杂个人的主观性推荐,那么仅能将其认定为充当着“扩音器”的角色,而不能定性为代言行为。因此如果不详细辨别推广行为的性质,便要求符合代言人身份的主播对所推广全部商品都要承担连带责任,这样的判断和处理未必周延,因此对带货主播所采用的推广行为开展研究也便有了意义。
(一)网络带货主播推广模式的分类
通常而言,带货主播的推广行为主要可以区分为代言行为与销售导购行为。如前所述,代言行为主要聚焦于代言人的自身魅力,他们常利用自身在社会上的信誉和形象对商品进行推介,从而使社会大众产生名人效应和移情效应,其强调利用知名人士的知名度或者声誉来帮助产品推销进而获得消费者的信赖,给消费者带来强烈的主观印象,同时提高订单成交概率和数量。而销售导购行为是指销售导购员按照客户实际购买的需要,向客户讲解商品的使用功能、制造材料等外在特征,然后让消费者购买到其所需要的商品。相比之下,销售导购行为更加注重商品的实用功能、效果、制造工艺等方面的客观性表达,而不是根据行为人的偏好或者使用心得使消费者产生购买信赖的主观性推荐。
根据主播推广行为的不同,网络带货的推广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产品介绍类”。其主要将商品的外部包装、使用功能和原材料等进行陈列和介绍,宣传的主要内容也是对销售折扣和质量进行讲解。比如“我们的果汁绝不使用任何防腐剂”。第二,“体验指导类”。该主要指带货主播中亲自尝试、使用商品,加入一些可视可听的因素帮助消费者感受到商品的品质等相关特征。比如带货主播亲自品尝水果,并向观众赞美水果的汁甜肉脆的味道。第三,“情感共鸣类”。该类广告在我们生活当中并不少见,带货主播拍摄剧情短视频,并且采用剧情植入的方式将商品特征与剧情主旨相得益彰,利用幽默或者爱心等普世价值观,让消费者看过之后达到感同身受的效果,以此来达到情感共鸣。
(二)从理性人的角度判断带货主播的推广行为
由于这三种推广模式所包含的主观推荐程度不同,导致消费者所产生购买信赖也有所差异,因此对主播行为的定性也应因时而宜。然而在实务中,带货主播推广模式较为复杂,销售导购和代言行为之间的鉴别有时也是较为模糊的,尽管带货主播在直播的商品介绍中也略有主观性评价,比如“谁用了都说好”“大品牌,值得信赖”等,但这并不能将此断定为代言,这时带货主播是否具有代言表意行为便难以甄别,因此需要根据《民法典》一百四十二条第1款所确立的“温和表示主义”的解释规则进行解释,即原则上采用表示主义的立场,例外的采用意思主义的立场。
当主播真实意图与客观的外在表示之间有歧义时,消费者通常无法知悉带货主播内心欲想发生销售导购还是代言行为的意思表示,此时消费者除外观表示之外,不享受其他途径知晓主播内心真意,这便使得消费者对外在表示客观含义的合理信赖应当优先于主播的内心真意得到保护,即适用表示主义的视角来解释。消费者合理信赖的判断指其内心状态,即消费者对信赖的产生是否足够谨慎,此处仍以假设理性人是否因主播的推荐而产生购买信赖作为区分的关键点,并结合个案中主播的所采用的表达方式,肢体动作等因素综合判断。换言之,通过假设一个在相关领域拥有特定知识和经验的理性人,将其置于同样的场景之下是否会产生信赖心理,例如一个经常购买化妆品的女性的理解能力可以作为化妆品带货主播是否构成代言行为的评判标准。
据此,笔者认为在第一种带货模式下通常主播对商品的客观性介绍比较多,其推荐意图也较少,难以引发消费者购买信赖,因此将该类主播认为销售导购行为较为合理。在第二种“体验类”的带货模式下,在大多数情况下主播使用自身体验感影响消费者的感官,通过刺激视觉或者听觉使消费者感受到商品的品质和特点以博取消费者感性体验,其中暗含着较多的推荐意图,因此通常应当认定为代言行为。第三种情况下,主播从消费者情感需求为出发点,通过剧情演绎使商品卖点与消费情感需求相连接,增强消费者好感的同时,也加深了代言的记忆点,因此该类带货模式下主播的主观推荐程度最高,应当将其定性为代言行为。
由此可见,如果具备较高知名度的带货主播采取“体验指导类”和“情感共鸣类”的带货行为,他们便需要对虚假代言的产品承担连带责任。而采用“产品介绍类”的主播实质充当了“扩音器”的作用,将其定性为商品吸引流量销售行为较为合适。
结语
综上所述,广告代言人包括知名度和代言行为,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关键。知名带货主播具有能诱发受众合理信赖的代言行为之时,才能周延地满足广告代言人的定义。保护消费者被引发的信赖利益,便构成带货主播虚假代言可归责性的理论基础。不具备较高知名度的带货主播或者即便具有较高知名度但被定性为销售导购行为的带货主播,不应承担《广告法》五十六条第2款的连带责任,而要求其承担销售者的责任更为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