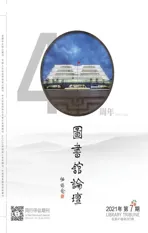巴黎吉美博物馆藏王重民致伯希和书信四通考释*
2021-01-07刘蕊
刘 蕊
法国国家图书馆中文拓片收藏始于18 世纪,彼时拓片混藏于中文古籍,尚未独立分类。直至1910 年4 月,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从中国搜购到的拓片归入法国国家图书馆写本部,才被视为法国国家图书馆真正意义上的拓片典藏的开端[1]48-49。这批拓片主要是由伯希和于1908年8月末至9月初在西安书坊购得,而伯氏在西域探险(1906-1908)途中一直热衷于搜集拓片,并尝试自行拓印。完成西域考古调查至西安时,他汇集的古碑拓片就有数千份,并计划在北京继续从事这项工作。在伯氏看来,对于研究历史学的汉学家来说,“这是对一座大图书馆所必不可缺的补充”,他自信“在欧洲任何一个首都,都不存在这样的图书馆”[2]。
1934年10月12日,国立北平图书馆与法国国家图书馆联合签署交换馆员和出版物的协议。王重民以交换馆员身份被外派到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3]4。王重民(1903-1975),字有三,我国著名目录学家、文献学家、敦煌学家。他于1934年9月下旬抵达巴黎,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整理伯希和特藏中的金石拓片和沙畹(E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捐赠的拓片,并编纂目录。沙畹拓片是法国汉学家沙畹于1907年春至1908年在中国北方进行考古调查时获得,主要为元代的宗教敕令和泰山题铭。返回法国后,一部分拓片赠予法国国家图书馆,大部分入藏法国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王重民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期间,通常以书信方式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伯希和商讨和交流。伯希和去世后,其手稿、笔记、书信等作为档案保存在吉美博物馆。笔者在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du Collège de France)访学期间,于吉美博物馆的伯希和档案第Pel.D38号卷宗中获见数十通王重民来函,其中4通书信内容涉及金石拓片的整理与编目,到今尚未向外披露。笔者誊录书信原文①,加以考释,籍此了解王重民编纂《伯希和拓片典藏目录》(Catalogue de la Collection Pelliot du fonds d’Estampages)的具体方法,以及对目录细节的处理方式,有助于学界更为深入地理解王重民的目录学理念。
信一
伯希和先生道席:
国家图书馆所藏先生金石拓片,已整理完竣,刻正从事于沙畹氏所藏者。沙畹氏所有不多,三四日即可结束。兹先拟出编目样式三种,谨呈先生,敬祈审核。如有不当之处,请用书札定期召重民前往面谕,或用书札说明,均所感荷!
编制方法,即遵先生意旨,在目录上约表明下列数项:(一)汉文碑名;(二)法文音译碑名;(三)法文意译碑名;(四)碑所在地及碑之撰人,书写人,建立时代等。(然有磨灭不能考时则缺之,内有人名地名年代等专名词,均用汉字注明法文音译。)
年代一项,先生欲就陈垣氏《朔闰表》对照,俾年月日均有西历。重民谨按碑志上有月日者半,无月日者半;有月无日,不能定其相当于西历之何月,有年无月,照以西年,时亦有错误者,因碑若立于中历之十一二月,往往则相当于西历之次年一月矣!今拟于碑之有年月日者则完全照以西历,无日则不用月,无月或可用年也。未审尊意如何?
馆中无陈氏《朔闰表》,请先生设法转借一部,或令馆购买一部,为祷!(附上卡片所写中西年月日,均虚拟。)
又先生所藏拓片与沙畹氏所藏者,是否编成一目?又将来排次,按年代抑按旧有次序,均请示知!
又宋代以前石刻,完整者无几,故整理时审辨颇费时间;内尚有昭陵碑三种,不能定其名目,先生如藏有罗振玉《昭陵碑考》一书,请假作参考,无任感谢!
立碑年代,宋以前者,因磨灭过甚,已多不见原碑,重民或据《金石录》《金石萃编》等书,补其一二;然考据之学,后来居上,如近罗振玉氏所考,其说或有与前人不同者。限于时间与环境,不能参稽众书,奈何!奈何!
即请
著安!
后学王重民敬上
十一月十日(1934)
Wang Chung-mien
17 rue Git-le-Cœur,Paris VIe。
王重民写此信时,方才整理完伯希和拓片,继而开始沙畹拓片的整理工作。并计划将伯、沙二氏所藏拓片合编为一个目录,再按照年代或者依照原有次序排序。事实上,沙畹拓片最终是以附录形式附于《伯希和拓片典藏目录》之后。需要指出的是,王重民编纂拓片目录的基本程序是先制作目录卡片、分类排序,最后清抄。而王氏彼时的整理主要是制作卡片和分类,并编拟了3种目录样式,请伯希和审核。
至于拓片目录的编制方法,显然伯希和此前已和王重民做过讨论,且确定了基本方案。王氏遵照“先生意旨”,目录涵盖的内容主要包括汉文碑名、法文音译碑名、法文意译碑名,以及碑所在地、撰写者、书写者、立碑时代,等等。目录的细节处理上,对碑文漫漶不可考时,则从缺;碑文中的人名、地名、年代等,均采取汉字注明、法文音译的方式。
再者,碑志上的时间依据陈垣《朔闰表》转换成西历,相互对照。但是对未篆刻月、日的碑文,由中历转换为西历时容易出错,特别是中历的十一、十二月,往往相当于西历第二年的一月。对这一点,王重民的解决方法是:碑志有年月日的,完全转换为西历;没有日期的,则不用月;没有月份的,可以选择只用年份。陈垣编撰的《朔闰表》,全称《二十史朔闰表》,是一部中历、西历、回历对照互换的年表。1925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一经出版,便轰动学界。胡适称赞其“这是一部‘工具’类的书,治史学的人均不可不备一册”,“此书在史学上的用处,凡做过精密的考证的人皆能明瞭,无须我们一一指出”[4]。是以,伯希和令王重民对照陈垣《朔闰表》转换碑志上的日历为西历。
由于宋代以前的石刻磨灭严重,极少有完整的,不易辨认。王重民在整理这部分拓片时主要借助《金石录》《金石萃编》等作为参考。另外,罗振玉有关石碑考据的著述,较之前人多有突破。即如伯希和拓片中的三种昭陵碑,就需要借阅罗振玉的《昭陵碑考》来定名目。但在当时的法国,诸如《朔闰表》《昭陵碑考》这类文献尚不易获得。吉美博物馆另存有1935年2月5日王重民致伯希和信件一封,提及昭陵碑中《周道务》《房仁裕》《越过燕太妃》3种尤为稀见[5]②。可见,本文所录“信一”略早于1935年2月5日信,据此,笔者推测,“信一”当写于1934年11月10日。
信二
伯希和先生道鉴:
先生所藏金石目录,编译草稿已略具,谨择录数种付清抄,呈请审核!
此目将来排次,是否拟按年代?如按年代,则原来次序与号码,均不能用,统要重编!
原来次序,虽不按年代,然同在一地,或同一性质者,排列均相近,似亦有保存之必要。依愚见:拓片可不乱原来次序,而标注原来号码于各该目下方,(如第一目下方所示。)阅者依此号码取拓片,可不另编号码;则目录虽按年代排次,与拓片存放之位置无关也。(先生藏书AB 二库,将来重编新目,如改为四库分类法,亦可用此法。即书架上之原来排次不变动,而于目录之每书名下方,注名Pelloit A 某号,Pelloit B某号,俾阅者据此号法取书;此虽与图书馆之编目法不相同,然亦颇为便利也。
重民翻译此目时,力求名词上之统一。如墓铭,石阙,神道以及僧塔等均用Épitaphe;德政遗芳诸碑,凡属颂讃之类,均用Monument;造像用Estampage;其余各种,均用Inscription,而加en—,pom—,以区别各小类,不知先生以为何如也?
此草目尚须重校一次,清抄一次,再请先生审定!然其中尚不无待补之处,如(N.6;E.59)似先生在新疆亲手所搨者,因残碎太甚,不能定其名,拟借罗振玉《西陲石刻录》一参稽。又如毛公鼎出土较晚,馆中无书可考知其历史,拟借一考释该鼎之书,俾撮录其事迹于目录下。又有数种如“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文”之类,苦不得适当译语。凡此种种,将来又均有待于先生之教正者也。
此目共包拓片374种,清抄后均可得百叶(feuilles)上下。如付印,每页(Page)约能容四五目,亦可得七十页上下。
现因学习法语,且手续不谙熟,故工作较迟。一月以后,法语可稍告一段落,即可专力编目,进行当能较速矣!
如何之处,重民愿面承指示。暇中赐予接见,甚所愿也。惟重民仍不能说法语,且因口吃,一时亦不敢说,望暂以华语赐谈为祷!即候
著绥!
后学 王重民敬上
12月14日(1934)
17 rue Git-le-Cœur,Paris VIe。
此信主要讨论的是伯希和所藏金石拓片目录的分类和翻译问题,即目录的编写体例。整个草目共包含拓片374种,王重民先择选了10种金石目录的编译草稿,请伯希和审核,并解释在翻译金石目录时尽量使名词统一而采取的方法。这10种编译样稿包括《东汉益州刺史杨府君石阙》《三国李苞通阁道题名》《北魏樊奴子造像记》《唐褚亮碑》《唐房玄龄碑》《唐端州石室记》《唐代国长公主碑》《唐创建清真寺碑记》《唐福林寺戒塔铭》《宋重修中岳庙记》,随附于信后。
关于目录的排序问题,伯希和早前整理这批拓片时,主要按照拓片所属地点、性质排列。王重民认为,如果重新按照时代编次,则需要重新编写全部号码。他建议可以在不打乱原来次序的同时,将原来号码标注在各新编目录下方,即新旧号码并存的方式。这样既方便读者根据原号码索取拓片,又不至于因按照年代重新排次而造成存放位置发生调整。同时,王氏认为该方法也适用于伯希和A藏B藏的编目整理工作。
另外,为考释拓本中残损难阅者,需借助诸如罗振玉《西陲石刻录》等著作为参稽。
由该信可知,彼时王重民正在学习法文,以便于此后编目之需。后来王氏编纂完成的《伯希和拓片典藏目录》与《伯希和A藏B藏目录》正是用法文书写,人名、地方等处附注中文。
此外,该信所署地址与“信一”相同,且刚刚完成金石目录的编译草稿,由此推测该信的书写时间当为1934年12月14日。
信三
伯希和先生道鉴:
两周前,先生到图书馆,祗以小恙,致失迎迓。又因先生所嘱千佛洞题壁史料,所得不多,心中仄歉,以为无颜谒见,故久缺拜访!近观此种材料,多关本地掌故,欲求其精,非一一证以写本材料不可。张氏曹氏索氏令狐氏等世族无论矣,如开元时人之题壁,若证以开元时敦煌十三乡户籍,必能得其履历与籍贯;都头押衙之类,多与其长官同署名,写本文件内,出其手者甚多,如阎海员、张庆达之流,刻已能知其仕履。重民深幸工作期间延长,先生再肯假以时日,将来或能作到相当满意!
所编两目录,已开始清钞,兹谨将拟就分类表呈上,请审定可否应用?钞写时每类为一起端,尊意有应移改之处,甚易之也。
预计九月内钞完,则十一月份可开始另作新工作。(拟九月十五至十月十五日休假。)其待编目录者,尚有N.F.连此次送来之《四库珍本》在内,谅不久即可出齐。现在手术较熟习,以后工作,便可事半功倍,书虽不少,想数月可竣。又《敦煌书目》,有先生及那波先生两底稿,若从新改作一次,亦不难,同时再将每卷涉阅一次,于题壁史料之考证,可收莫大效果也。且不可辨识之卷子,重民已找出原书不少,而三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关敦煌论文,重民亦已搜罗略备。又其为罗振玉及日本人所印行者,重民亦十之八九找出原卷,兹凡改编此目,一一注明于各该卷之下,于阅者可得莫大便利。以后应如何工作,请先生先计画一下。
拙作《敦煌尚书六跋》一文,请教正。前曾彚去年所作,选出四十篇,邮交北平,印为单本,七月底八月初可出版,出版后再奉赠。
北平图书馆近出刘修业女士所编之《国学论文索引四编》一册,敬赠。
李俨在关中得元人梵文诏版一对,将拓片寄来请先生指教并考证!
《四库珍本》内有《六艺之一录》一书,其卷124(?)③为《沙洲碑录》,载《李氏两修功德记》,为据雍正时汪德容在安西写定本,似为首先箸录此两碑者。以校罗氏《西陲石刻录》,知罗氏移写,实多不忠实之处!
即请
箸安!
学生 王重民上
六月二十八日(1936)
该信主要涉及3方面内容:一是王重民对于千佛洞题壁史料的看法。千佛洞壁史料是伯希和在考察千佛洞石窟时亲自誊抄的,因故无法拍摄的那部分洞窟的赞、铭、叙、题款等,这些史料不仅能够补充敦煌写本的缺漏,也是研究中国西北地区历史的重要资料。王重民认为千佛洞题壁史料大多与当地掌故相关,须与写本材料相考证,才能精确,并列举了唐开元年间题壁的例证。实际上,由于多种因素,千佛洞石窟内的题壁正在不断消磨,伯希和誊抄的这部分史料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部分后来逐渐佚失的文献资料,其价值尤为珍贵。
二是编目工作的进展情况。王重民负责编纂的《金石目录》和《伯希和A藏B藏目录》已经进入清抄阶段,预计当年九月内完成,特请伯希和审定草拟的分类表。在王重民为巴黎敦煌写本编目前,法国国家图书馆已有两种《敦煌书目》:伯希和自己编写的“伯2001-3511 号”;那波利贞编写的“伯351-5541号”。那波利贞(1890-1970),号城轩,出生在儒学世家,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1931年8月作为文部省在外研究员赴欧,主要在法国调查和研究敦煌文书[6]。王重民认为,如果在以上二种目录的基础上重新改作,并非难事。借此机会再逐一阅览每一卷文书,亦将有益于考证题壁相关史料。另外,对于不能辨识的卷子,王氏已经找出不少原书,而近30年来中日学者关于敦煌的论文,以及罗振玉、日本人所印行的敦煌遗书的原卷,也基本查找完备。以上这些都将用于改编敦煌目录,并逐一注明在各卷之下,方便读者。
三是《四库珍本》中《六艺之一录》卷123《沙洲碑录》,所载《唐京子陇西李氏功德碑记》和《沙州千佛洞唐李氏再修功德碑》(即《李氏两修功德记》),所依据的是清雍正朝汪德容在安西的写定本。据王重民研究,《沙洲碑录》应是最早载录此二碑的文献。将之与罗振玉《西陲石刻录》对校,可知罗氏《西陲石刻录》实为移写,而非完全依照原本。
据刘修业《国学论文索引四编》的出版时间为1936年6月,信中言“北平图书馆近出”,推测“信三”当写于1936年6月28日。
信四
伯希和先生道席:
前者上一函备述金石目编译状况;而次日又在楼上书库内找出先生所藏拓片三大箱,其分量与前者略相等,刻已开始依前样编目矣,敬闻!
即颂
著绥!
后学 王重民上
据吉美博物馆所藏1935年2月5日王重民致伯希和信件所言:“第二次续编之金石三箱半,现已编完,共有936种,刻已译出六百种,全编日内可蒇事矣。第一次所编为374种,全数共为1320种。”[5]这里的金石三箱半共936种,应当就是信中的“次日又在楼上书库内找出先生所藏拓片三大箱”。“信四”又言“前者上一函备述金石目编译状况”,前者一函当指上文“信二”。故而,推测该信当写于1934 年12 月14 日后与1935年2月5日前这段时间。
王重民编写完拓片目录后,经杜乃扬(Marie-Roberte Guignard,1911-1972)校正法文后抄录在纸上,最后装订成册,目录后附有杜乃扬编订的打字索引[3]22。1938 年 2 月 19 日,王重民完成金石拓片法文目录《伯希和拓片典藏目录》,而《沙畹拓片典藏目录》作为附录形式收于内。王氏在目录前写道:“本简要目录是伯希和于1909年从中国带回拓片的完整名录。该目录按照中国皇帝在位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经书及佛经集中在后面叙述。我列出每张拓片的作者、书法家、立碑日期(根据阴历转换成阳历)及地点。附录部分有《沙畹拓片典藏目录》:主要是元代的宗教敕令和泰山题铭。王重民,1938年2月19日。”[1]52这段题识概括性地介绍了拓片的来源、内容,目录的编写顺序与体例,类似序文,读者据此可了解目录梗概。
王重民治学严谨,著述丰富,刘修业《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学术活动年表》后附王氏《著述目录》[7],其中有关金石碑文者有《道德经碑幢刻石考》(1926)[8]、《毛凤枝金石萃编补遗稿本》(1935)[9]、《跋伪本虞恭公温彦博碑》(1945)[10]三种。遗憾的是,由于战乱、经费等多重因素,《伯希和拓片典藏目录》最终未能付印,一直以手写本的形式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写本部,以至于学界对王重民在金石拓片方面的研究与贡献所知有限。通过披露和考释以上书信,不仅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王重民编写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沙畹典藏拓片的过程与方法,这也是研究王重民学术生平及其与伯希和往来的重要一手资料。此外,王氏的编目体例与思想对于编纂域外汉籍书目亦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注释
①原书信均以中文繁体字书写,部分词汇为法文,笔者完全依照原文誊录为简体字。
②陈恒新《王重民在法国期间致伯希和四信考释》信二所署时间为1938年2月5日。然该信结尾言:“重民现在住址如下:30,rue St-André des Arts。”此地址为王重民1935-1938年间租住处所在,既然着重注明地址,应为乔迁新居后不久,地址有变。信中又言:“闻大驾行将辱临鄙国,……以后继编Pelliot A.B两库书目,其编制方法与体制,仍愿面承教诲……”可知此信写于伯氏来华前,且王氏尚未正式开始编纂Pelliot A.B书目。经查,伯希和最后一次来华是1935年5月至6月,而王氏《伯希和A藏B藏目录》于1935-1939年编纂完成,也就是说该信当写于1935年5月前。综上所述,陈文所录信二时间有误,应为1935年2月5日。
③卷124,误,经查应为卷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