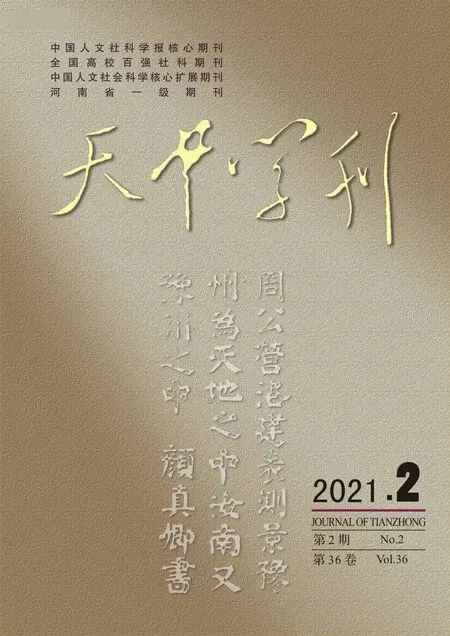作为一种方法的“诗胎考据”
——钱钟书诗学考据学论略
2021-01-06项念东
项念东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钱钟书与陈寅恪的诗学研究恰好构成诗学研究的两个基本范式。与陈寅恪坚守“诗史释证”,矢志接续知人论世、比兴说诗的学术传统不同,钱钟书侧重属词比事的视角,将中国古代诗评诗话传统与西方现代新学相融合,开创了以现代语言学、心理学、哲学和艺术学理论相贯通以说诗的另一路径[1]。陈寅恪谨守说诗考史“第一义谛”,发明诗人之心以彰显诗意所存,钱钟书则立足“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2]1,在“连类举似”之间掎摭诗艺。尽管二者学术性格、学术问题领域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很相似,即都在考据之学被批评的学术氛围中以切实的研究为考据作了忠实的辩护。
钱钟书的《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均是富含考据气息的著作,其中《宋诗选注》与《管锥编》完成于“对实证主义造反”的历史年代。《宋诗选注》著于1955―1956年,1957年出版;《管锥编》主要写作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于1979年①。从这三部书的写作体式看,《谈艺录》采用的是传统诗话体,《宋诗选注》是注释体,而世人传诵的《管锥编》乃是一部庞大的“读书笔记”。如果用当下流行的夹叙夹议式的“论著体式”来衡量钱钟书著作的话,这三部书均近乎考据而远于“论著”。
1978年9月,在欧洲汉学家第26次会议上,钱钟书在以《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为题的发言中提出,“文学研究是一门严密的学问,在掌握资料时需要精细的考据,但是这种考据不是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不能让它喧宾夺主、代替对作家和作品的阐明、分析和评价”,新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实证主义的造反”之后,“考据在文学研究里占有了它应得的位置,自觉的、有思想性的考据逐渐增加,而自我放任的无关宏旨的考据逐渐减少”[3]。那么,什么才是钱钟书认为的恰如其分的考据呢?从发言中他举例批评陈寅恪对“杨玉环入宫时是否处女”的考证来看,钱钟书欣赏的不是陈寅恪式的“诗史释证”,尽管后者通过考证杨妃入宫是否处子之身最终考见的是李唐王朝“胡汉”杂糅背后的文化精神。毕竟,钱钟书始终强调与“诗眼文心”的“莫逆冥契”,故“作者之身世交游”之类的历史考据只能被置于“余力旁及”的地位[2]346。钱钟书对文史文献可谓谙熟,著作中也多有精细的文献考据案例,其对语词的敏感及训诂方法也多可称道,但无论是诗学历史考据,还是文献与语词考据,均非其着意所在。实际来看,钱钟书的诗学考据可称之为一种“诗胎考据”,即在错综排比之中考探诗学文本的“诗胎”所在,并批评其艺术得失,按《管锥编》的提法,也可称之为“连类举似而掎摭”[4]860。
一、从“蓟丘之植植于汶篁”的解释说起
“蓟丘之植,植于汶篁”,语出乐毅《报燕惠王书》。这句话如何理解,写作上有何艺术特点,陈寅恪与钱钟书都曾谈及,从中约略可见二者诗学考据方法的不同,以及钱钟书“诗胎”考据的着眼点之所在。
1931年,陈寅恪曾发表《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之最简易解释》一文,篇幅不长,但考证工作背后的意味颇为深长。
《史记 · 乐毅传》录有《报燕惠王书》,在“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一句下,裴骃《集解》引徐广曰:“竹田曰篁。谓燕之疆界移于齐之汶水。”而司马贞《索隐》曰:“蓟丘,燕所都之地也。言燕之蓟丘所植,皆植齐王汶上之竹也。徐注非也。”后此学者大多尊司马贞之说。俞樾《古书疑义举例》认为,这句话乃是句式倒装,应当改为“汶篁之植,植于蓟丘”。杨树达《词诠》则从文字训诂的角度认为“于”“以”同义,此句实为“蓟丘之植,植以汶篁”[5]297。陈寅恪认为,前此解释中以俞、杨二家之说“最精确”,但同时指出:“夫解释古书,其谨严方法,在不改原有之字,仍用习见之义。故解释之愈简易者,亦愈近真谛。并须旁采史实人情,以为参证。不可仅于文句之间,反复研求,遂谓已尽其涵义也。”[5]297按照不改原有句式及用字的原则,他认为此句可理解为“蓟丘之所植乃曾植于汶篁者”。看似差别不大,但陈寅恪将问题重点落到了“汶篁”二字的理解上来。
司马贞将“篁”解释为汶上之“竹”,而《集解》所引徐广的解释中却提到“竹田曰篁”,后者恰是《说文解字》的解释:“篁,竹田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证《西京赋》《汉书》中的记载,指出“竹田曰篁,今人训为竹,而失其本义矣”。此后,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等接续了这一解释。陈寅恪指出,应参考段玉裁及曾国藩的意见,“‘蓟丘之植,植于汶篁’既非倒句之妙语,亦不必释‘于’与‘以’同义。惟‘篁’字应依《说文》训为‘竹田’耳”[5]298。因为,“竹”与“竹田”虽仅一字之差,但文意表达却有很大差别:
自来读乐毅此书者,似皆泥于上文“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于燕”之语,谓此句仅与“齐器设于宁台”“大吕陈于元英”等句同例,而曲为之解。殊不知植物非财宝重器,可以“收入于燕”之语概括之。其实此句专为“故鼎返乎磨室”句之对文……盖昌国君意谓前日之鼎,由齐而返乎燕,后日之植,由燕而移于齐。故鼎新植一往一返之间,而家国之兴亡胜败,其变幻有如是之甚者。并列前后异同之迹象,所以光昭先王之伟烈。而己身之与有勋劳,亦因以附见焉。此二句情深而词美,最易感人。[5]299
诗文属对最讲究精切。燕曾大败于齐,其国之重器珍宝曾被作为战胜国的齐所劫掠,而今转败为胜,自然会将失去的一切“物”重新夺回。因此,“竹田”二字相对于“竹”而言,更是隐指家国之领土,唯此才足以与作为国家政权之象征的“旧鼎”对仗成文。且如此行文,才更足以彰显乐毅此文意在表彰己身功绩的用意。这是陈寅恪认为“篁”应释为“竹田”的原因所在。更重要的是,“旧鼎”由燕至齐而今返归燕国,而燕国竹田(亦可谓之燕篁)所植之物其实原本就来自于齐,而今又反以胜利者的姿态,重新移栽于战败国齐之旧域(汶篁),其一往一复之间,世事沧桑、家国兴亡之感自可一览无余。尽管这在乐毅,不过是胜利者一方的嘲笑,但燕齐之间胜败转换的历史变迁则足以引发后人的无限唏嘘。
再看钱钟书对“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一语的解释。
《管锥编》第三册中有一篇关于乐毅此语的专论。文章同样引证司马贞《索隐》的意见“古人诧为倒装奇句”,然钱钟书以《困学纪闻》卷一七引楼昉《太学策问》“夷门之植,植于燕云”为例指出,此一句式后世“不乏祖构”。而且,钱钟书特别提到周振甫的意见:“不必矫揉牵强,说为倒装。末‘于’与前两‘于’异,即‘以’也。”[4]857周振甫所说,实际上与杨树达的意见是相同的。钱钟书并未就“以”“于”互训的问题展开讨论,而是将关注点落在了类似乐毅此语的句式倒装现象的艺术价值上:
又有进者。此语逆承前数语;前数语皆先言齐(“大吕”、“故鼎”、“齐器”)而后言燕(“元英”、“历室”、“宁台”),此语煞尾,遂变而首言燕(“蓟丘”)而次言齐(“汶篁”),错综流动,《毛诗》卷论《关雎 · 序》所谓“丫叉法”(chiasmus)也。聊复举例,以博其趣。[4]858
在钱钟书看来,“植于汶篁”对“蓟丘之植”的“逆承”,形成了一种文辞表达的“错综流动”之美。而这种语言表达现象,在中国诗文中不乏其例。这里提到的“丫叉法”,钱钟书在《管锥编》第一册中谈及《关雎》时已分析过,指诗文写作中安排前后呼应时,“应承之次序与起呼之次序适反”的方法。如《毛诗序》云:“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钱钟书指出:“‘哀窈窕’句紧承‘不淫其色’句,‘思贤才’句遥承‘忧在进贤’句,此古人修词一法。”[6]66正因为是“古人修词一法”,钱钟书同时举了很多类似用例:《卷阿》“凤凰鸣兮,于彼高冈;梧桐出兮,于彼朝阳;菶菶萋萋,雍雍喈喈”,以“菶菶”句接梧桐,以“雍雍”句应凤凰;《史记 · 老子韩非列传》“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以走、游、飞,倒换次序分别接兽、鱼、鸟;谢灵运《登池上楼》“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惭渊沉”,以“云浮”先接“飞鸿”,再以“渊沉”接“潜虬”;杜甫《大历三年春自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无;曲留明怨惜,梦尽失欢娱”,以“明妃之曲”接“昭君”,以“高唐之梦”接“神女”。最后他提道:“其例不胜举,别见《全上古文》卷论乐毅《献书报燕王》。”[6]66
在钱钟书看来,这种“丫叉法”最大的好处在于可以有效避免文字表达的呆板,而通过词序交错则可增强文辞回环跌宕的美感。缘此,钱钟书在《管锥编》第三册谈到乐毅“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一语时,与陈寅恪关注乐毅此语背后的家国兴亡之感不同,他的兴趣乃在此语以及类似用例的属词比事之技巧。所以,紧承其提到“丫叉法”之后,他梳理了大量诗文用例,“聊复举例,以博其趣”。不过,钱钟书不是为了展示知识的广博,而是为了进一步指出,看似相类的“丫叉”用法中还存在具体表现上的细微差别。
钱钟书举例说明“丫叉”用法的差别,将之归纳为六种交错类型②:
1.词序交错。《论语 · 乡党》“迅雷风烈必变”,《楚辞 · 九歌 · 东皇太一》“吉日兮辰良”。“‘风’、‘辰’近邻‘雷’、‘日’,‘烈’、‘良’遥俪‘迅’、‘吉’,此本句中两词交错者。”
2.句式交错。《史记 · 平津侯主父列传》载严安上书“驰车击毂”,而《汉书 · 严朱吾丘等传》下作“驰车毂击”,“于义为长,非徒词之错也”。《汉书 · 王莽传》下载“桃汤赭鞭,鞭洒屋壁”,不曰“洒鞭”而曰“鞭洒”,先以“鞭”紧承“赭鞭”,后以“洒”间接“桃汤”。
3.语句交错。《列子 · 仲尼》篇:“务外游不务内观,外游者求备于物,内观者取足于身,取足于身,游之至也,求备于物,游之不至也。”第二、三句于第一句顺次申说,第四、五、六、七句于第二、三句逆序申说。王勃《采莲赋》:“畏莲色之如脸,愿衣香兮胜荷。”杜甫《有事于南郊赋》:“曾何以措其筋力与韬钤,载其刀笔与喉舌。”王勃上句先物后人而下句先人后物,杜甫反是。李涉《岳阳别张祜》:“龙蛇纵在没泥涂,长衢却为驽骀设。”上句言才者失所,下句言得位者庸,错互以成对照。
4.诗意表达中情思的交错。韩偓《乱后却至近甸有感》:“开中却见屯边卒,塞外翻闻有汉村。”“中”虽对“外”,而“塞”比邻“边”,“汉”回顾“中”,谓外御者入内,内属者沦外,易地若交流然。李梦阳《艮岳篇》:“到眼黄蒿元玉砌,伤心锦缆有渔舟。”出语先道今衰、后道昔盛,对语先道昔盛、后道今衰,相形寄慨。韩愈《奉和裴相公东征途经女几山下作》:“旗穿晓日云霞杂,山倚秋空剑戟明。”风物之山紧接云霞,军旅之旗遥承剑戟。
5.谋篇布局中的交互成文。“并有扩而大之,不限于数句片段,而用以谋篇布局者。如诸葛亮《出师表》‘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云云,承以‘臣本布衣’云云,继承以‘受命以来……此臣之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承以‘至于斟酌损益……则攸之、祎、允之任也’,终承以‘不效则治臣之罪’,承以‘则戮允等以章其慢’;长短奇偶错落交递,几泯间架之迹,工于行布者也。”
6.隐藏的交错。“至若《焦仲卿妻》……江淹《恨赋》……《文心雕龙 · 指瑕》……王维《送梓州李使君》……常建《送楚十少府》……胥到眼即辨。沈佺期(一作宋之问)《和洛州康士曹庭芝望月有怀》……同此结构而较词隐脉潜。”
这六种用例,不仅可以见出古代诗文写作中交错成文之际所展现的语词表达艺术,更可看出后来者的表达随着文学创作的发展更趋复杂,甚至这种表达有意以一种近乎隐含的方式呈现出来。
由此可见,钱钟书由“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一语之解释,关注到中国古代诗文创作中的句式倒装现象,再由这些类似的语言现象,深挖“交错成文”的创作传统在中国诗文写作中的不同表现类型及其艺术巧思之所在,这就是他所说的“连类举似而掎摭焉,于赏析或有小补”[4]。应该说,钱钟书以其充满艺术发现的眼光,梳理清楚了各种“交错成文”现象中作者在遣词命意、谋篇布局乃至艺术构思上的巧妙之处,以及由此表现出的文辞之美。
就此而言,如果按照本文开头提到的钱钟书对考据的分类,陈寅恪的考据近于“有思想的考据”,钱钟书的考据则更近于“诗眼文心”的考据,亦即在“连类举似”中发现不同诗文“诗眼文心”之所在,由比较而见其遣词命意之美。所以,钱钟书考据工作的着力点,不在诗人意图,也不在时代背景、文献版本、语词训诂,而在诗人的某一艺术构思——包括字眼句法、遣词命意等——在文学史中的因与革,既观其“影响的焦虑”,又发现其艺术独创的匠心。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诗胎”——宋人所说“夺胎换骨”之诗“胎”——的考据。
二、“诗胎”考据与诗艺“掎摭”
“诗胎”之“胎”,即“夺胎换骨”之“胎”,主要指前人已有的诗意构思。
“夺胎换骨”,出自惠洪《冷斋夜话》所引黄庭坚语:“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说文》曰:“胎,妇孕三月也。”段玉裁注:“《释诂》曰:‘胎,始也。’此引伸之义。”《增韵》曰:“凡孕而未生,皆曰胎。”因此,所谓“诗胎”实际上就是一种诗意原型——某种现成的可以艺术再加工的诗思原材料,它可以是一种具有特殊美感表达的句法结构,一个美典,一个意象,一个母题,一种人生的情境,一种情感,等等。比如,黄庭坚《戏答王定国题门两绝句》之二:“颇知歌舞无窍凿,我心块然如帝江。花里雄蜂雌蛱蝶,同时本自不作双。”雄蜂、雌蝶“同时”却不同类,帝江乃传说中的神鸟,虽无七窍,面目混沌,但颇识歌舞。因此,黄庭坚此诗乃是以蜂、蝶之不同类,喻自己虽如帝江颇知歌舞,但早已过了歌舞少年的心境,“我心块然”即心已木然,一如帝江之“无窍凿”。对于后二句,任渊注引李商隐《柳枝》词曰:“花房与蜜脾,蜂雄蛱蝶雌。同时不同类,那复更相思。”李诗即以蜂与蝶喻人生暌隔、相思之苦。钱钟书在此基础上,又考及李商隐《闺情》“红露花房白蜜脾,黄蜂紫蝶两参差”,指出这本是“汉人旧说”,并举多例加以说明,如《左传》僖公四年“风马牛不相及”服虔注“牝牡相诱谓之风”,《列女传 · 齐孤逐女传》“牛鸣而马不应者,异类故也”,《易林 · 大有之姤》“殊类异路,心不相慕”,等等。钱钟书认为,李商隐诗取旧说为诗材,“一点换而精彩十倍”,然冯浩注李商隐诗,任渊注黄庭坚诗皆未能“推究本源”[2]9-10。《谈艺录》的这番考证,由黄庭坚到李商隐,一直追到《左传》中的“风马牛不相及”,实际正是在考探黄、李诗中“同时异类的暌隔”这样一种人生情境的意义原型——一种“诗胎”。
值得注意的是,钱钟书在上述考证中,不只是对“诗胎”作原始要终式的详细追查,也是在考察此诗作何种再创造更能展现诗艺塑造之美。李商隐对“汉人旧说”的“点换”,才是钱钟书“诗胎”考据的真正关注点。这与他对宋诗的认识有关。
前引黄庭坚的诗学思想中,相对易其辞而不易其意的“换骨”而言,“夺胎”法更看重在前人诗意基础上的新变,“窥入其意”是发现旧有“诗胎”,“形容之”则是在此基础上必需的艺术改造,亦即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中所说的“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因此,“夺胎换骨”的目的在于“以故为新”“点铁成金”,而这正是宋诗的一个重要艺术特征。
在中国诗学史上,宋诗的地位一直不高。尽管有晚清“同光体”的极力提倡,但轻视宋诗的倾向在20世纪前半叶的学者中仍较常见。所以,在《谈艺录》中,钱钟书即明确提出“诗分唐宋”,而且“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2]2,明确将唐诗、宋诗并提。这可以说是20世纪前半叶为宋诗做出的最有力的辩护。至写作《宋诗选注》的年代,“筋骨思理”的问题不便多谈,所以钱钟书又从写作技巧的角度再次谈及宋诗的艺术独特性:
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我们可以夸奖这个成就,但是无须夸张、夸大它……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记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摹仿和依赖的惰性。瞧不起宋诗的明人说它学唐诗而不像唐诗,这句话并不错,只是他们不懂这一点不像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宋人能够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疏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险开荒,没有去发现新天地。用宋代文学批评的术语来说,凭借了唐诗,宋代作者在诗歌的“小结裹”方面有了很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譬如某一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彻,某一个字眼或句法从唐人那里来而比他们工稳……[7]
在批评宋诗具有“摹仿和依赖的惰性”的同时,钱钟书也指出,正因为面对唐诗所提出的挑战,宋人“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可以把一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彻”,可以借用唐人的某个“字眼或句法”,但又可以写得比唐人“工稳”。这实际上也就是宋诗注重“夺胎换骨”“以故为新”的创作取向。正是在对旧有“诗胎”的“点换”中,宋诗相对唐诗更注重“诗法”,艺术技巧也更趋精熟。
因此,钱钟书的“诗胎”考据,就是要通过追查“诗胎”来考证诗人的“点换”技巧,发现其在诗歌“小结裹”方面的艺术经验。譬如,补注黄庭坚诗是钱钟书极为关注的一个题目,从大学时代研读山谷诗任渊、青神二注,到欧洲游历归来“获读”冒疚斋《后山诗注补笺》后补订山谷诗,所作订补60条收入《谈艺录》后又多次再作补注、新补③,可见其心力。其中,考据“诗胎”正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兹举一例。黄庭坚《演雅》诗:“络纬何尝省机织,布谷未应勤种播。”任渊注“但释虫鸟名”,至于引杜诗“布谷脆春种”无关诗意发明。钱钟书首先补注了山谷词意所本之“诗胎”最早者即《诗 · 大东》:“皖彼牵牛,不以服箱。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至于《抱朴子》外篇《博喻》“锯齿不能咀嚼,箕舌不能别味”一节,《金楼子 · 立言》篇九下“全袭之,而更加铺比”。钱钟书由此指出,“山谷承人机杼,自成组织者,所谓脱胎换骨是也。”[2]6所谓“承人机杼”,乃是对现成“诗胎”的运用,而“自成组织”则是对旧有“诗胎”的艺术再创造。而要发现其“再创造”的秘密,则须考其“诗胎”,亦即考其诗意原型之所在。
但必须指出,钱钟书的“诗胎”考据不同于文学批评中的“原型批评”。“原型批评”的重要奠基人诺思诺普 · 弗莱认为“原型”是“在文学中极为经常地复现的一种象征,通常是一种意象,足以被看成是人们的整体文学经验的一个因素”④。从“极为经常地复现”、成为一种意义基型的“象征”而言,“诗胎”就是一种“原型”,无论是一种句法结构、一个典故、一个意象或一个文学母题,常常会以某种类型化的结构形态、程式化的言说方式,反复出现于不同的文本之中。但是,“原型批评”的落脚点是从“杂多”中见“统一”,即通过研究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各种意象、叙事结构或人物类型,去发掘其背后某种普遍的心理经验。而钱钟书的“诗胎”考据,则是从“杂多”中归纳出一种基型,再由此基型反观“杂多”自身的艺术特征或审美价值,亦即从辞章学的角度,在“连类举似”大量“诗胎”中,“掎摭”其“夺胎换骨”的“点换”艺术,揭示其遣词造句与诗意表现的艺术变化。钟嵘《诗品序》曰:“辨彰清浊,掎摭利病。”“掎摭”就是批评、鉴赏。因此,“连类举似而掎摭”,乃是通过对类似例证的分疏将语言现象举例与艺术美感鉴赏融合在一起,是举证分析,同时也是诗歌鉴赏。
这种“诗胎”考据的方法,在《宋诗选注》与《管锥编》中都有大量运用,《宋诗选注》尤为明显,几乎贯穿全书,如第一篇柳开《塞上》,钱钟书注后二句“碧眼胡儿三百骑,尽提金勒向云看”曰:
三四两句的句调可参看唐人李益(一作严维)《从军北征》“碛里征人三百万,一时回首月中看”。[7]1-2
最后一篇萧立之《偶成》,钱钟书注后二句“城中岂识农耕好,却恨悭晴放纸鸢”曰:
城里人不知田家盼望下雨,只恨天公不做美,不好放风筝。参看唐人李约《观祈雨》:“朱门几处看歌舞,犹恐春阴咽管弦”;曹勋《松隐集》卷十《和次子耜“久雨”韵》第二首:“第忧沉稼穑,宁问浸芙蓉”;陆游《剑南诗稿》卷十五《秋雨排闷十韵》:“未忧荒楚菊,直恐败吴粳”……也都写出了对天雨天晴的两种立场。刘克庄《朝天子》:“宿雨频飘洒,欢喜西畴耕者……老学种花兼学稼,心两挂:这几树海棠休也”;林希逸……又要写同时抱有两种态度的矛盾心理,但是语气里流露出倾向性。[7]292-293
至如宋诗中的名句,考据“诗胎”更是明显,对陆游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游山西村》),钱钟书先后举证王维《蓝田山石门精舍》“遥爱云木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清流转,忽与前山通”,柳宗元《袁家渴记》“舟行若穷,忽又无际”,卢纶《送吉中孚归楚州》“暗入无路山,心知有花处”,耿《仙山行》“花落寻无径,鸡鸣觉有村”,周晖《清波杂志》卷中载强彦文诗“远山初见疑无路,曲径徐行渐有村”,以及王安石《江上》“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指出这些作品都写到了“疑无路”之际的某种转机,但“要到陆游这一联才把它写得‘题无剩义’”[7]176-177,即不仅可见一种转折之际的跌宕起伏,更有一种人生寓意、诗意的回环。对叶绍翁《游园不值》“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一联,钱钟书认为:“这是古今传诵的诗,其实脱胎于陆游《剑南诗稿》卷十八《马上作》:‘平桥小陌雨初收,淡日穿云翠霭浮。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不过第三句写的比陆游的新警。”紧接着又举张良臣《偶题》“一段好春藏不尽,粉墙斜露杏花梢”,认为“第三句有闲字填衬,也不及叶绍翁的来得具体”。此外,他又列举唐人温庭筠、吴融、李建勋等类似的句子,指出这些句子要么和其他景色掺杂排列,要么没有放在一篇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位置,都不及叶绍翁写得醒豁[7]266。
至于《管锥编》,“诗胎”考据的例子同样俯拾满眼。
例如,古来送别诗之祖《燕燕》中的“瞻望勿及,伫立以泣”一句,钱钟书考证了大量祖构此句的例子,通过比较显现各家写作艺术之优劣。许剀《彦周诗话》引述了张先《虞美人》“眼力不如人,逮上溪桥去”以及苏轼《与子由》“登高回首坡珑隔,惟见乌帽出复没”。钱钟书指出:张先词原作“眼力不知人远,上江桥”,许剀虽误引,然“如”字含蓄自然,实胜“知”字,几似人病增妍、珠愁转莹;相比邵谒《望行人》“登楼恐不高,及高君已远”,张先《南乡子》“春水一篙残照阔,遥遥,有个多情立画桥”、《一丛花令》“嘶骑渐遥,征尘不断,何处认郎踪”等,“许氏所标举者语最高简”[6]78。不仅如此,他又举证朱超道《别席中兵》、王维《齐州送祖三》《观别者》、王操《送人南归》、梅尧臣《依韵和子聪见寄》、王安石《相送行》以及何景明《河水曲》等诸多远绍《燕燕》、“与张词、苏诗谋篇尤类”的例证,指出梅、王诗“说破着迹”,而宋左纬《送许白丞至白沙,为舟人所误,诗以寄之》“水边人独自,沙上月黄昏”,“庶几后来居上”[6]79。
再如,对《诗 · 陟岵》中“远役者思亲,因想亲亦方思己之口吻”的考证,钱钟书举了大量“机杼相同,波澜莫二”[6]113的例子,如:
徐干《室思》“想君时见思”;高适《除夕》“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韩愈《与孟东野书》“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悬悬于吾也”;刘得仁《月夜寄同志》“支颐不语相思坐,料得君心似我心”;王建《行见月》“家人见月望我归,正是道上思家时”;白居易《初与元九别,后忽梦见之,及寤而书忽至》“以我今朝意,想君此夜心”,又《江楼月》“谁料江边怀我夜,正当池畔思君时”,又《望驿台》“两处春光同日尽,居人思客客思家”,又《至夜思亲》“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游人”,又《客上守岁在柳家庄》“故园今夜里,应念未归人”;孙光宪《生查子》“想到玉人情,也合思量我”;韦庄《浣溪纱》“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阑干,想君思我锦衾寒”;欧阳修《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遥知湖上一樽酒,能忆天涯万里人”;张炎《水龙吟 · 寄袁竹初》“待相逢说与相思,想亦在相思里”;龚自珍《己亥杂诗》“一灯古店斋心坐,不是云屏梦里人”。[6]113
接着又以古乐府《西洲曲》为例,指出《陟岵》的这种写法,不仅用于远行思亲,更扩及男女相思之例。在钱钟书看来,这些诗作均属“据实构虚,以想象与怀忆融会而造诗境,无异乎《陟岵》焉”。而且,后世写作中更由“我思人亦如人思我”,变化为“我见人亦如人之见我”这样的写作手法:“分身以自省,推己以忖他;写心行则我思人乃想人必思我,如《陟帖》是,写景状则我视人乃见人适视我,例亦不乏。”[6]114故紧接其后,钱钟书又以王维《山中寄诸弟》《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以及包融《送国子张主簿》等诗为例指出,金圣叹评《西厢记》揭示出的“倩女离魂法”正是上述写法的继承。此外他又指出,辞章中“写心行之往而返、远而复者,或在此地想异地之思此地,若《陟岵》诸篇;或在今日想他日之忆今日,如温庭筠《题怀贞池旧游》……一施于空间,一施于时间,机杼不二也”[6]116。
值得注意的是,在随后的讨论中,钱钟书又列举杜牧《南陵道中》、杨万里《诚斋集》卷九《登多稼亭》之二、范成大《望海亭》、辛弃疾《瑞鹤仙 · 南涧双溪楼》、翁孟寅《摸鱼儿》、方回《桐江续集》卷八《立夏明日行园无客》之四、钟惺《隐秀轩集》黄集卷一《五月七日吴伯霖要集秦淮水榭》、厉鹗《樊榭山房续集》卷四《归舟江行望燕子矶》、《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四卓奇图绝句、罗聘《香叶草堂诗存 · 三诏洞前取径往云然庵》、张问陶《船山诗草》卷一四《梦中》、钱衎石《闽游集》卷一《望金山》、江湜《服敔堂诗录》卷三《归里数月后作闽游》之十、王国维《苕华词 · 浣溪纱》等多个诗例,认为这些作品“词意奇逸”,篇幅虽不及阮元《揅经室四集》卷一一《望远镜中看月歌》、陈澧《东塾先生遗诗 · 拟月中人望地球歌》、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卷七《七洲洋看月歌》等诗,但其艺术水平却是“以少许胜多许”,且黄公度《人境庐诗草》卷四《海行杂感》第七首“亦逊其警拔”[6]115。从这里,鲜明可见钱钟书“诗胎”考据中的“掎摭”眼光。
凡此,可见钱钟书由“诗胎”考据而见词旨再造之美的诗学考据方法,“连类举似而掎摭”之中既有一种诗学创造的智慧,更有一份艺术发现的巧心。
三、“易”象“诗”象之别与“诗胎”考据及“诗史”批判
上文提到,钱钟书的“诗胎”考据不同于“原型批评”,很重要的一点即在于“原型批评”关注的是某种定型化的“意象”背后所体现的普遍的心理经验,而“诗胎”考据追问的是这种看似定型的“意象”在此后诗人笔下的艺术新变。这与钱钟书对文学意象特殊性的认识有关。他在谈及“易”象与“诗”象之别时提道:
《易》之有象,取譬明理也,“所以喻道,而非道也”(语本《淮南子 · 说山训》)。求道之能喻而理之能明,初不拘泥于某象,变其象也可;及道之既喻而理之既明,亦不恋着于象,舍象也可。到岸舍筏、见月忽指、获鱼兔而弃筌蹄,胥得意忘言之谓也。词章之拟象比喻则异乎是。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变象易言,是别为一诗甚且非诗矣。故《易》之拟象不即,指示意义之符(sign)也;《诗》之比喻不离,体示意义之迹(icon)也。不即者可以取代,不离者勿容更张。[6]12
“易”之象实为讲明某种道理的事象,道理是普遍的、相对稳定的,而作为讲说此道理的载体则可以更换。譬如,同样表达对光阴流逝的感叹,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论语 · 子罕》有“逝川”之象:“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庄子 · 知北游》有“白驹过隙”之象:“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曹操《短歌行》曰“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李煜《浪淘沙》则以“落花”为喻:“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所以,“易”象乃是一种指示意义的符号。而且,在钱钟书看来,道理离不开言说,我们对言说内容的理解建立在语言或语词理解的基础上,而语词既有其理解的普遍性,也存在当下的特殊性,因此一意数喻有助于以言说的多元消弭理解的固化或错误。“古之哲人有鉴于词之足以害意也,或乃以言破言,即用文字消除文字之执,每下一语,辄反其语以破之。”[6]13
然而“诗”象则不同。如果说“易”象是一个可置换的概念,“诗”象则是一个独立自足的艺术世界。也就是说,诗是一种借助语言塑造意象的艺术,即便蕴含的思想意涵相类,不同的语言表达所塑造的“诗”象本身却是独特的“这一个”。韦庄说“但见时光流似箭,岂知天道曲如弓”,虽然也感叹时光流逝之迅疾,但更强调其“曲”行的一面,从而照应人生的坎坷,这与曹操的朝露之叹、李煜的落花之感是不同的。所以,在钱钟书看来,每一个“诗”象都是“依象而成言”的“这一个”,其中固然有意义的体现,但其关注点不在对意义的指示,而在其语言构造本身的美感。因此,每一个“诗”象都是一个独特的艺术结构,“变象易言,是别为一诗甚且非诗矣”。
在钱钟书看来,诗乃是一种艺术,而艺术形式、艺术表达本身有着不可忽略的规则:“诗者,艺也。艺有规则禁忌,故曰‘持’也。‘持其情志’,可以为诗,而未必成诗也。艺之成败,系乎才也……虽然,有学而不能者矣,未有能而不学者也。大匠之巧,焉能不出于规矩哉。”[2]40诗人融汇才、学入诗,且做到“深藏若虚”,离不开对“诗艺”技巧的琢磨和提炼⑤。所以,他讲宋诗相比唐诗而言,虽乏大判断,但正因为宋人多注意“诗艺”层面的“小结裹”,故而宋诗能有其独到价值[7]11。《谈艺录》中还特别提到诗的艺术结构问题:
诗者,艺之取资于文字者也。文字有声,诗得之为调为律;文字有义,诗得之以侔色揣称者,为象为藻,以写心宣志者,为意为情。及夫调有弦外之遗音,语有言表之余味,则神韵盎然出焉。[2]42
这里,钱钟书将诗之创作析分为“语言、形象、情感、意蕴”四个层面,这四层的关系既可视为一首好诗创作过程的层深结构,亦可看作才质不同的诗人的分野——诗人因艺术修养不同在创作中融涵这四者的水平亦不同。所以,正是从诗自身的艺术特性着眼,钱钟书的“诗胎”考据特别注重“连类举似而掎摭”,在比较中见其诗艺得失与艺术高下。
值得注意的是,强调“易”象与“诗”象不同,即是强调诗与哲学有别。甚或可以说,钱钟书此说乃是反对以一种追求“普遍性”的哲学思维来看待文学。这背后,有其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思维大于形象”这一思潮的反拨,他在《管锥编》中提道:
是故《易》之象,义理寄宿之蘧庐也,乐饵以止过客之旅亭也;《诗》之喻,文情归宿之菟裘也,哭斯歌斯、聚骨肉之家室也。倘视《易》之象如《诗》之喻,未尝不可摭我春华,拾其芳草……哲人得意而欲忘之言、得言而欲忘之象,适供词人之寻章摘句、含英咀华,正若此矣。苟反其道,以《诗》之喻视同《易》之象……以深文周纳为深识底蕴,索隐附会,穿凿罗织,匡鼎之说诗,几乎同管辂之射覆,绛帐之授经,甚且成乌台之勘案。自汉以还,有以此专门名家者。[6]14-15
正因为每一个独特的“诗”象往往都有其感性面相,都与诗人的现实生活有联系,所以一旦过于深文周纳“诗”象中的现实思想指向,则难免造成“乌台之勘案”。而且,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即便面对同一时代背景,也会有作者感悟之不同、艺术心灵表现之多样。这一点,钱钟书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中就特别提及:
当因文以知世,不宜因世以求文……每见文学史作者,固执社会造因之说,以普通之社会状况解释特殊之文学风格,以某种文学之产生胥由于某时某地;其臆必目论,固置不言,而同时同地,往往有风格绝然不同之文学,使造因止于时地而已,则将何以解此歧出耶?……鄙见以为不如以文学之风格、思想之型式,与夫政治制度、社会状态,皆视为某种时代精神之表现,平行四出,异辙同源,彼此之间,初无先因后果之连谊,而相为映射阐发,正可由以窥见此种时代精神之特征;较之社会造因之说,似稍谨慎(略见拙作《旁观者》),又有进者,时势身世不过能解释何以而有某种作品,至某种作品之何以为佳为劣,则非时势身世之所能解答,作品之发生,与作品之价值,绝然两事;感遇发为文章,才力定其造诣,文章之造作,系乎感遇也,文章之造诣,不系乎感遇也,此所以同一题目之作而美恶时复相径庭也。[8]
钱钟书自始至终对“诗史释证”多有批评,典型地体现在《宋诗选注 · 序》中对“诗史”说的批评⑥。钱钟书固然反对文学研究偏向史实考证以致忽略自身的艺术问题,但其《宋诗选注》却有不少“以史证诗”的例子。因此,理解钱钟书所说的“‘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不应忽略这句话的特殊历史背景⑦,以及钱钟书对当时文学研究所面临问题的考量。
注释:
① 详情见张文江《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钟书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92―93页、112―113页。
② 见钱钟书《管锥编》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58―860页。
③ 详见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23页、314―344、346页。
④ 见诺思诺普 · 弗莱《批评的剖析》(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69页。
⑤ 如《谈艺录》批评黄公度诗和往昔“学人之诗”以及赞赏静安35岁之后的诗,均可见一斑。见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26页。
⑥ 参见拙文《诗史释证与审美想象的历史还原——戴鸿森〈宋诗选注〉补订读后》,载胡晓明主编《中国文论的思想与智慧(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四十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4―470页。
⑦ 杨绛曾回忆道:“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钟书1956年完成的《宋诗选注》,1958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钟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见杨绛《我们仨》(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