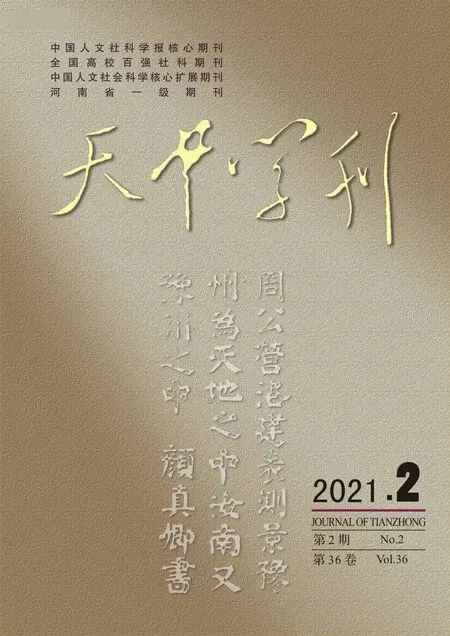《吊屈原赋》的改写定型及作品理解
——以赋作录本与集本的差异化对读为路径
2021-01-06刘明
刘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吊屈原赋》是汉初贾谊创作的一篇赋作,是贾谊存世作品里的名篇,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汉初骚体的楚辞逐渐变化,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故贾谊的赋兼有屈原、荀卿二家体制。”①[1]通过此篇作品,可以看到“楚辞”体对汉初赋篇创作的文学影响,但它同时也有来自荀卿创作的影响,而非单纯的楚辞影响。而有文学史家认为:“前半多用四言句,后半多用楚辞式长句,可见他在学习楚辞的同时又能有所变化。”[2]186其实,贾谊是在继承秦代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比如荀卿、李斯的影响,又受到了南方楚辞传统的影响,《吊屈原赋》是两种文学传统影响下的产物。通过《吊屈原赋》,还能够据以体认汉初流传的屈原形象,这也是文学史中有关屈原的最早书写。因为,屈原的生平资料虽以《史记 · 屈原贾生列传》为最早,但诚如有文学史家所指出的那样:“似乎存在错乱,有些地方不易读明白。”[2]141加之清末民初以来廖平、胡适等对屈原的质疑,屈原是否“真实”地存在成为一个待解的“悬案”。《吊屈原赋》产生在司马迁之前,又是独立于《楚辞》之外的文学材料,虽不见得能够解决屈原的存在问题,但可以雄辩地证明司马迁撰写《屈原列传》之前就流传有屈原的材料。故很有必要对《吊屈原赋》进行一番细致地文本阅读,以充分认识该作品的创作、流传及被阅读理解的诸多细节。由于该篇主要收录在史传(《史记》和《汉书》贾谊本传)和《文选》中,也载于贾谊本集中,姑且分别称之为录本和集本。通过对读不同载录形态的《吊屈原赋》,会发现一些差异。这些差异首先表现在同一篇作品存在不同的文字面貌。导致此种差异的原因是由于后人不同的改写,使得《史记》《汉书》中所录的《吊屈原赋》分化为两种文本系统。其次差异还体现在不同录本里的赋序,这同样是由于改写的原因,亦涉及对赋作主旨的理解。另外,对读古人对《吊屈原赋》的注解,也会发现一些差异。对读这些差异,既有助于我们了解《吊屈原赋》文本的传播与流变,又可加深我们对作品内容的理解。
一、《吊屈原赋》之赋序改写与主旨理解
据《史记》和《汉书》本传,贾谊是洛阳人,自年轻时便展现出卓异的政治才能,文帝元年(前179年)被汉廷召为博士,因出色的政治才干,一年之内又“超迁”至太中大夫,但随之也遭到嫉妒打击,由于周勃、灌婴等人的谗言而被文帝疏远,文帝三年(前177年)谪出长安任长沙王太傅,时年24岁。可以想见,这时贾谊的内心是极度抑郁的,因为他富有政治才华加之年轻气盛,或许还带有几分自负,显然承受不住这样的遭遇。在赴任途中经过湘水时,触景伤怀,念及与自己身世相仿的屈原,不禁悲从中来,情郁于衷,写下了这篇《吊屈原赋》。
《史记》在贾谊本传中对《吊屈原赋》的创作背景是这样描述的:“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适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3]3022但同样的语句又出现在《鸟赋》的创作背景叙述里,即云:“贾生既以适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3]3026清人梁玉绳注意到了这里可能存在文字窜乱,其《史记志疑》卷三十一曰:“贾生因鸟入舍,故以为寿不得长,非但因卑湿也。此乃下文之复出者……应衍‘辞’字至‘又’字十五字。”尚不清楚这种窜乱发生在司马迁笔下,还是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班固在修贾谊传时,则如此描述:“谊既以适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为赋以吊屈原。”[4]2222自“以适去”至“为赋以吊屈原”共17字,与《史记》完全相同。可以断定,班固参考了司马迁纂修的贾谊传,但也适当有所改写,如以“谊既”两字取代了《史记》自“贾生既辞往行”至“又”共18字。梁玉绳称:“《汉书》改曰‘谊既以适去’,甚当。”梁氏认为班固看到的此处文本就是窜乱的,故有此改写。但班固接下来还做了进一步的改写,没有拘泥于司马迁的“框架”,而是进一步坐实贾谊创作此赋与屈原之间的关系:“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其终篇曰:‘已矣!国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谊追伤之,因以自谕。”[4]2222经此改写,相较于《史记》增益41字,推测据自刘向的《别录》,依据是《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云:“因以自谕自恨也。”出现了同样的“因以自谕”4个字,而且这段增益的改写与班固的《离骚赞序》差异较大。萧统编《文选》收录该篇题“吊屈原文”,在篇题下小注“并序”,将此小序在形式上作为赋作的组成部分。实际此小序乃据自《汉书》,只是略有个别文字的改写,并不影响文意。如“谊既以适去”改写为“谊为长沙王太傅,既以谪去”(依据胡克家刻本《文选》,下同),“已矣”“国亡人”各改写为“已矣哉”“国无人兮”,“遂自投江而死”改写为“遂自投汨罗而死”,“因以自谕”改写为“因自喻”。其中“江”改写为“汨罗”,当据自《史记 · 屈原列传》“(屈原)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但如果不读《史记》《汉书》,《文选》的处理容易造成贾谊撰有赋序的“印象”,实际是《文选》编者依据《汉书》略加处理的结果,刘跃进即指出:“乃史家所作,非贾谊自作明矣。”[5]11935此可视为史笔“窜”为作家作品附属内容的用例。
朱熹《楚辞集注》也收有此篇《吊屈原赋》,篇首同样撰有小序,属朱熹以“注”的方式交代该篇的创作背景,云:“《吊屈原》者,汉长沙王太傅贾谊之作也。谊以适去,意不自得,及过湘水,时屈原沉汨罗已百余年矣。谊追伤之,投书以吊而因以自喻。后之君子,盖亦高其志,惜其才,而狭其量云。”朱熹所作此注没有像《文选》那样直接依据《汉书》,而是进行了一番出自己意的改写,特别是对贾谊还做了评价。《汉书》《文选》和朱熹《集注》里的这三篇小序,都使用了相同的一组词“因以自谕(喻)”,即均认可刘向《别录》的解读,将该赋的主旨理解为贾谊以屈原自况。但司马迁并不是这样的解读,在《史记》贾谊传篇末的“太史公曰”中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3]3034可见司马迁借《吊屈原赋》读出的是对屈原的理解,他没有给出如何看待贾谊的明确看法。这似乎印证司马迁载录《吊屈原赋》全文,有将之作为补充屈原事迹史传材料的意图,恐怕也是将处在不同时代的屈原和贾谊进行合传的原因。司马迁之后的刘向,则对贾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当然也有惋惜,云:“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4]2222这段话出自班固《汉书》贾谊传末的“赞曰”,应该是据自刘向《别录》。刘向以为贾谊的遭遇与屈原相同,遂得出贾谊作《吊屈原赋》是“因以自谕”的见解,影响后世至深②。班固一方面接受刘向“因以自谕”的见解,一方面却并不认同“悼痛”的看法,他说:“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其术固以疏矣。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就是说贾谊的一些政治主张,文帝也有所采纳执行,怎么能说是“不遇”呢?到了朱熹作注,又提出了“狭其量”的看法,认为贾谊心胸度量不够大。这意味着在朱熹看来,贾谊出任太傅不见得文帝不再信任他,也可能是文帝对贾谊的一种政治锻炼,说不定还是一种“曲线救国”的方式③,何必如此悲天悯人呢?
以上是结合录本中此赋小序文本的承继与改写情况,谈了前人对赋作主旨的理解,至于集本则是另一番面貌。当然,早期贾谊集的编本已经不传,现存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贾谊集,是明人张燮编的《七十二家集》本《贾长沙集》。该集收录的《吊屈原赋》据自《楚辞集注》,将赋作明确由“吊屈原”题作“吊屈原赋”,此外既未保留朱熹“注”性质的小序,也未载《汉书》或《文选》中的小序。这反映了明人在编贾谊集时的文献处理方式,其优点是避免了“他者”叙与作家作品之间可能产生的“著作权”混淆。
《史记》《汉书》明确称“为赋以吊屈原”,显然将之视为赋作,这是此篇在后世普遍称以“吊屈原赋”的依据。但萧统编《文选》称之以“吊屈原文”,作为吊文的第一篇收在卷六十(据李善注本)。可见,随着载录形态由史传变为总集,文体的属性也相应发生了游移。清人梁章钜《文选旁证》云:“序明言为赋,昭明以为文,何也?”刘跃进认为:“从史叙看,此文本确实为《吊屈原赋》,《文选》却将之归入文类,并命名为《吊屈原文》,盖以内容考虑而非文体分类。”[5]11933按萧统的这种安排,应当是受到了刘勰的影响,按《文心雕龙 · 哀吊》云:“自贾谊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刘勰即将此篇视为吊文,而且还认为是吊文的“首出之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推测萧统或许就接受了这种见解,既然在所编《文选》里设立“吊文”一体,《吊屈原赋》又是该文体的“首作”,就不仅要收录此文,还将篇题易名为“吊屈原文”,而不再收在赋体里。应该说,萧统既有对其内容的考虑,也着眼于“吊文”的文体,因为篇题里还有一个“吊”字。至于篇题明确称“吊屈原赋”源自何时,尚不好判断,有可能南朝时流传的贾谊集里便已经出现该称。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南宋流传的《贾子》已将此篇称之为“赋”,不过篇题作“吊湘赋”(据《索隐述赞》“百年之后,空悲吊湘”之语,似乎唐代此赋即题“吊湘赋”),而且还作为了该书的“压轴”之篇,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对此说得很清楚④。朱熹撰《楚辞集注》收录该篇称《吊屈原》,既不称“文”,也不称“赋”。明刻《李卓吾先生批选晁贾奏疏》及张燮本贾谊集都称以《吊屈原赋》,袭用至今,一般不再称“吊屈原文”,完全视为一篇赋作。
二、《史记》录本《吊屈原赋》文字面貌的改写与定型
讨论了《吊屈原赋》的小序和篇题、前人对贾谊的评价及对该赋创作主旨的理解,接下来再结合录本及集本所载的作品本身进行细读。阅读中如果考虑作品的载录形态,即它所借以“寄存”的不同文献载体,会发现同样的一篇作品会存在各种差异,比如最为直接的文字差异,还有句式的不同、注释的异同等。即以《史记》和《汉书》而言,班固距离司马迁不过一百多年,即便不考虑后世流传过程中出现的文字变化,恐怕两者所载的《吊屈原赋》在当时即已经存在差异。兹以两种录本对读(包括注释在内),《史记》文字面貌依据中华书局最新整理本,《汉书》依据中华书局整理本,会得出《史记》录本《吊屈原赋》存在着明显的改写和定型的过程,而《汉书》录本则保持着稳定,也正是这种稳定性映照出《史记》录本的文字面貌的变化过程。具体而言,表现在下述五个方面:
(一)《汉书》所载的《吊屈原赋》更接近原本面貌
可证之例,如“共承嘉惠兮”,《汉书》“共”作“恭”,按《史记集解》引张晏注云:“恭,敬也。”似表明至迟在南朝之前的《史记》传本即作“恭”,同《汉书》,此后却改作“共”。又“俟罪长沙”,《汉书》“俟”作“竢”,颜注:“竢,古俟字。”“侧闻屈原兮”,《汉书》“侧”作“仄”,颜注:“仄,古侧字。”另“呜呼哀哉”,《汉书》“呼”作“虖”,颜注虽未注古字,但据《集韵 · 模韵》称“乎,古作虖”,“虖”当亦“呼”的古字。这表明《汉书》录本《吊屈原赋》保存了部分古字面貌,而《史记》录本在流传过程中则改写为通行之字或者说是俗字,印证《汉书》的《吊屈原赋》文本更为接近原本之貌。
(二)《史记》所载的《吊屈原赋》文本存在自南朝至唐代逐渐定型的过程
可证之例,如“弥融爚以隐处兮”,《汉书》“弥融爚”作“偭獭”,《史记集解》云:“徐广曰:一云‘偭獭’。”又“摇增翮逝而去之”,《汉书》作“遥增击而去之”,《史记集解》云:“徐广曰:一云‘遥增击’也。”此两例表明至迟在南朝宋时《史记》传本开始出现“弥融爚”“摇增翮逝”的异文,徐广所称的“一云”,不清楚指的是《史记》别本还是《汉书》,可以确定的是《史记》所载《吊屈原赋》的文字面貌在产生变异。又“夫岂从蚁与蛭螾”,《汉书》“蚁”作“蝦”,按《史记集解》云:“《汉书》‘蚁’字作‘蝦’。韦昭曰:蝦,蝦蟇也。”明确南朝宋时的《汉书》录本《吊屈原赋》,与《史记》录本存在着文字差异。这意味着以南朝宋为节点,《史记》已经出现与《汉书》录本《吊屈原赋》不同的异文,从而在作品层面形成了两种文本系统。
又根据《史记索隐》及《汉书》颜注,《史记》所录《吊屈原赋》的文本似乎“定型”在唐代。如“独堙郁兮其谁语”,《汉书》“堙郁”作“壹郁”,《史记索隐》即云:“《汉书》作‘壹郁’,意亦通。”又“夫固自缩而远去”,《汉书》“缩”作“引”,《史记索隐》即云:“缩,《汉书》作‘引’也。”又“亦夫子之辜也”,《汉书》“辜”作“故”,《史记索隐》即云:“《汉书》‘辜’作‘故’。”又“瞝九州而相君兮”,《汉书》“瞝”作“历”,《史记索隐》即云:“瞝,丑知反,谓历观也。《汉书》作‘历九州’。”此四例表明司马贞确实对校过《汉书》里的《吊屈原赋》,他对两种录本之间存在的差异有着充分的认识,并以注释的形式一一予以揭橥。又“般纷纷其离此尤兮”,《汉书》“尤”作“邮”,《史记索隐》云:“尤谓怨咎也。”颜注:“邮,过也。”从注文也可确证唐代两种录本的该处差异。上述《史记》诸条异文就注家而言,集中出现在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而没有出现在《史记集解》中,不具备更早注家的背景。此恰可证这些异文至迟出现在司马贞时,据此可以视为《史记》所录《吊屈原赋》在唐代基本定型。这种定型的获得,可以表述为两种路向:其一,《史记》录本《吊屈原赋》原貌与《汉书》录本基本相同,只是在此后的流传过程中出现异文的改写,而渐致有别于《汉书》录本,改写至唐代(最迟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时)得以定型。其二,《史记》录本《吊屈原赋》原貌本来就与《汉书》录本有差异,只是缺乏更早传本的依据,只能通过注文拟定这些差异出现的下限时间。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揭示《史记》录本的《吊屈原赋》更为复杂,文字面貌有着明显的“流动性”,而《汉书》录本《吊屈原赋》则保持着稳定性。
(三)两书所录《吊屈原赋》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性较大的异文
可证之例,如“世谓伯夷贪兮,谓盗跖廉”,《汉书》作“谓随、夷溷兮,谓跖跷廉”,《史记》是两个人即伯夷和盗跖,《汉书》却变成了四个人,即卞随和伯夷,盗跖和庄跷。《史记索隐》云:“案:《汉书》作‘随、夷溷兮跖跷廉’,一句皆兼两人。”司马贞所引《汉书》此句,与今本《汉书》稍异。据《史记》此句仅有司马贞作注,推证此则异文至迟出现在司马贞时,应该是唐代才产生的异文,《汉书》更为近古。照此类推,“沕深潜以自珍”,《汉书》“深”作“渊”,似当以作“渊”为是,作“深”者应是避唐高祖名讳而改,是《史记》录本在唐代定型的又一佐证,这种痕迹保留至今。
(四)两书所录《吊屈原赋》句式存在差异
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兮”字的分句位置不同。如“斡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罢牛兮骖骞驴,骥垂两耳兮服盐车。章甫荐屣兮,渐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汉书》作“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牛,骖骞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父荐屣,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刘跃进称:“按照骚体赋的通常做法,兮字或居中,或置于句末。但《文选》《汉书》本篇各句‘兮’字的位置变乱无常,而《史记》尚保留统一居中的体式。”[5]11944这里暂不讨论两种句式哪种更为近古,笔者认为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与一定时期内“兮”字体作品的阅读方式有关。不同的阅读方式,导致“兮”字的位置发生移动。笔者认为,《汉书》录本的句式更接近《吊屈原赋》的原貌,四字一句的句式更可看出荀卿、李斯创作对于贾谊的影响,《赋篇》和李斯刻石文辞均为四字句式,铿锵有力,很有节奏的气势感。故怀疑《史记》录本《吊屈原赋》,可能是在贾谊创作此赋乃受到楚辞影响的认知下进行改写的结果,即按照“楚辞”体诵读的语气习惯予以调整“兮”字的位置。这种变动涉及如何认识贾谊创作此赋所受到的文学影响问题。笔者认为贾谊的创作受秦代文学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 · 诠赋》说:“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辞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后来又受到南方楚辞的影响,主要表现就是出现“兮”字,用以舒缓节奏性强的四字句式的语气。不知为何,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编的几种文学史著述,都对刘勰的这段论述不加引述,将贾谊创作的《吊屈原赋》想当然地视为完全是楚辞影响下的产物,只有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敏锐地看到了荀卿文章体制对后世的影响。
(五)两书的个别异文导致对文句的理解出现分歧
此类之例,如《史记》“亦夫子之辜也”,《汉书》“辜”作“故”,两字相通,《说文通训定声 · 豫部》:“辜,假借为故。”即缘故之义。《史记索隐》以“辜”字为据注云:“夫子谓屈原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凤翔逝之故,罹此咎也。’”指屈原因不能做到“远浊世而自藏”的缘故,以致遭此诸般磨难。颜师古以“故”字为据注云:“此说(指李奇注)非也。贾谊自言今之离邮,亦犹屈原耳。”指贾谊遭到贬谪赴任长沙王太傅,情形与屈原相同,故以屈原自况。颜师古没有注“故”之义,但按照他的理解,“故”很明显不是缘故之义,而似乎是故交、故友之义,即贾谊将屈原视为与自己遭遇相同的故交。前人已指出颜师古理解的错误,如北宋人刘邠即称“颜说全失”。实际上,颜师古之后的李善和五臣作注时,都理解为缘故,颜注可谓一己之见。结合《吊屈原赋》全文来看,第一部分交代屈原所处的是一个黑白颠倒、贤愚不辨和忠奸不分的环境,贾谊深为同情屈原的遭遇,发出“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的慨叹。第二部分则对屈原又有所责怪埋怨,以比兴的手法说凤远去浊世,神龙潜在九渊以自珍,屈原为何不像龙、凤那样“远浊世而自藏”,不然的话,何以离尤遭难呢?再次发出“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的慨叹。接着申述责备屈原的理由,天下之大何处不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何必执着于楚国?这就好比凤凰见人君有德则翔于世间,但若遇到险难之兆便逝而远去。如果不这样,别看是微不足道的蝼蚁,也会妨害鳣这样的大鱼。单从字面上来讲,全篇都是在讲屈原,贾谊并没有在文中直接表露自己的心迹。所以司马迁读《吊屈原赋》,读到的全部是屈原,对贾谊与屈原之间是否存在关系未做评论。但若说贾谊没有情感投射到赋作中,似乎也不合事实。贾谊正是在遭到权臣嫉贤妒能而贬谪的心境下,才创作出《吊屈原赋》,贾谊肯定与屈原的形象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共鸣。这是刘向“因以自谕自恨也”的依据,反映了古人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观,这种看法成为理解《吊屈原赋》主旨的主流意见。
附带而谈的是,贾谊在赋中所描绘的屈原形象来自何处呢?《史记》明确说贾谊“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点明了写作的地点是长沙附近的湘水一带。贾谊可能在这里做了短暂的停留,据赋中“侧闻屈原兮”,停留期间贾谊听闻了当地流传的有关屈原的说法。这些传闻建构了贾谊的屈原形象认识,并以文学手法书写在《吊屈原赋》里。大概屈原的事迹,早期主要在江淮一带流传,这是贾谊创作此赋的地理背景。贾谊仅依凭了传闻吗?是否也读过屈原的作品呢?从赋中“讯曰:已矣,国其莫我知,独堙郁兮其谁语”“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等文句来看,与《离骚》末尾的“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极为相似。《史记集解》引张晏语即云:“讯,《离骚》下章乱辞也。”有理由相信贾谊接触过屈原的作品,但这些作品是在停留湘水期间所接触,还是贬谪之前就读过,不得而知。现存可信为屈原创作的诸篇作品,在作品的内部并没有出现“屈原”的字样,这篇《吊屈原赋》应该是最早的一篇明确提及“屈原”的作品,也描绘出了最早的屈原形象,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料价值。
三、文本形态与注释理解:选本与集本里的《吊屈原赋》
《吊屈原赋》脱离史传进入文学总集,现存最早的录本是南朝梁萧统所编的《文选》,还有一种是朱熹的《楚辞集注》,两者都可视为文学选本。其中《文选》里的该赋字句,既有与《史记》相同者,如“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和“呜呼哀哉”等,也有与《汉书》相同者,如“莫邪为钝兮”等。相较而言更多的是与《汉书》相同,印证了选本祖出《汉书》录本。选本《吊屈原赋》也有与《史记》《汉书》录本字句均不相同者,如“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跷为廉”,较《汉书》又溢出两个“为”字。清人王念孙《读书杂志》认为:“本无两‘为’字,今有之者,后人以下文云‘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故加之也。”又“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史记》作“使骐骥可得系羁兮”,《汉书》作“使麒麟可系而羁兮”,《文选》此句似乎是糅合了《史记》《汉书》两种文本。这反映出《文选》编者对《吊屈原赋》部分文字的改写,当然也可能是承继了所依据的某一底本的面貌。
此外,唐代李善注《吊屈原赋》也有个别值得注意的细节,如“谊追伤之,因以自喻,其辞曰”句下善注引《风俗通》云:“贾谊与邓通俱侍中同位,数廷讥之,因是文帝迁为长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吊书曰:阘茸尊显,佞谀得意,以哀屈原离谗邪之咎,亦因自伤为邓通等所诉也。”所引见于该书的《正失篇》。李善未引《史记》和《汉书》贾谊本传相关事辞作注,绝非不清楚贾谊本传有关贬贾谊为长沙王太傅的记载,弃而不用可能缘于李善认为《风俗通》的记载与《吊屈原赋》中“阘茸尊显,佞谀得意”的文义更符合。《史记》和《汉书》贾谊本传称“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皆功臣,无论如何与“阘茸”之辈不能等同。而邓通收在《佞幸传》,谈不上有显赫的身世背景,只是因与文帝所梦者偶合而得宠居高位,以之注“阘茸”确比较适合。当然,《风俗通》称“贾谊与邓通俱侍中同位,数廷讥之”云云,恐亦与史实不合。按《史记 · 张丞相列传》称“(申屠)嘉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隆爱幸,赏赐累巨万”,申屠嘉任丞相在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年)张苍罢相之后,则邓通受文帝宠幸亦在此前后数年间。再者,贾谊卒在文帝十二年(前168年),自文帝三年至十二年的十年里基本在外地任职,似乎谈不上与邓通“俱侍中同位”,又何言“数廷讥之”呢?但这也只是推测,不宜武断地否定《风俗通》的记载。邓通作为文帝的佞臣,《史记》《汉书》均为之立传,其中是否存在因顾忌文帝而曲为讳笔的情况呢?对于这一点,《佞幸传》称邓通“愿谨,不好外交”,“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看来他做事谨慎,似乎还与人为善,与《风俗通》所称的“数廷讥之”倒是相矛盾。除了奉承迎合文帝外,邓通确实也谈不上有什么“祸国殃民”的品性,史笔是否有所隐晦就很难说了。《风俗通》的记载,提供了另一面的邓通形象,还最适合用以注释文句。应该重视李善的这条注文。
李善注《吊屈原文》多引及《史记》,如“方正倒植”句中的“植”字,善注云“《史记》音值”;“世谓随、夷为溷兮”句中的“随”字,善注云“《史记》‘随’字作‘伯’”;“斡弃周鼎宝康瓠兮”句中的“斡”字,善注云“《史记》音乌活切”;“凤漂漂其高逝兮”句中的“漂”字,善注云“《史记》音漂,匹遥切”;“遥曾击而去之”句中的“击”字,善注云“《史记》‘击’字作‘翮’”;“横江湖之鳣鲸兮”句中的“鳣”字,善注云“《史记》鳣,张连切”,共计上述六条。李善注除一处明确引及《汉书音义》外,没有参考《汉书》,而是较多地参考了《史记》。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与《文选》所录《吊屈原文》文句大都与《汉书》相同有关系,于是将《史记》所录的《吊屈原赋》作为另外一个版本进行对读,并作为注释的依据。以善注所引《史记》注音四条,均不见于今整理本《史记》。所称异文即《史记》作“伯”“翮”两条,《汉书》分别作“随”“击”,也再次印证上文中提出的推论,《史记》里的《吊屈原赋》定型在唐代。
除《史记》《汉书》和《文选》外,朱熹的《楚辞集注》卷八也收有《吊屈原赋》,题“吊屈原”,同样属于该赋的一种录本。朱熹集注云:“故特据洪说(指洪兴祖认为《惜誓》属贾谊之作)而并录传中二赋,以备一家之言云。”《四库全书总目》亦云:“是编并削《七谏》《九怀》《九叹》三篇,益以贾谊二赋。”[6]该录本《吊屈原赋》文字面貌同《汉书》,故朱氏集注亦与颜注有着密切的关系,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直接袭用颜注。如“阘茸尊贤”句中的“阘茸”,集注云:“下材不肖之人也。”又“子独壹郁其谁语”句中的“壹郁”,集注云:“犹怫郁也。”此两条注与颜注完全相同。又“袭九渊之神龙兮”句中的“九渊”,集注云:“九旋之渊,言至深也。”颜注“渊”作“川”,疑避唐高祖讳而改。其二,隐栝颜注及所引的旧注。如“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句,集注云:“默默,不自得意也。生谓屈原也,言其无故而遭此祸也。”《汉书》此句注作“应劭曰:默默,不得意也。邓展曰:言屈原无故遇此祸也。师古曰:生,先生也”。其三,对颜注有所选择,如“遭世罔极兮”句中的“极”字,集注云“止也”,颜注云:“极,中也,无中正之道。一曰极,止也。”附带一说的是李善注“罔极”云“言无中正”,似乎也是袭用了颜注。
正因为《集注》依据的是《汉书》录本《吊屈原赋》,所以朱熹集注便与《史记》录本该赋对读,并以之作为注释的内容之一。如“莫邪为钝兮”,集注云:“钝,《史》作顿。”又“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牛,骖骞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父荐屣,渐不可久兮;嗟若先生,独离此咎兮”诸句,集注云:“《史》此一节‘兮’字皆在句中,‘宝’上有‘而’字。”检日本汲古书院影印的宋代黄善夫刻本《史记》,其中有“而”字,今整理本无此字。又“夫固自引而远去”句中的“引”字,集注云“《史》作绝”。检黄善夫本作“缩”,今整理本同,则朱熹所见本《史记》作“绝”。又“偭獭以隐处兮”句中的“偭獭”三字,集注云“《史》作‘弥融爚’,又作‘弥蝎虫龠’”,检黄善夫本作“弥融爚”,今整理本同,朱熹所见《史记》尚有作“弥蝎虫龠”者。
以上是录本里的《吊屈原赋》,下面再来看集本即张燮编刻本《贾长沙集》里的此赋。张燮《贾长沙集引》云:“采其骚赋及疏牍散见《传》《志》或他书者,为《长沙集》。”《吊屈原赋》所据的“他书”是《楚辞集注》,而未采纳《史记》《汉书》及《文选》所录的《吊屈原赋》。原因可能在于该赋的内容既然是凭吊屈原,又是一篇“兮”字体的赋作,所以首先想到了《楚辞》,特别是影响力很大的朱熹集注的《楚辞》。需稍做说明的是,张燮偶有纰缪,将朱熹集注误当作“王逸注”。上文已经提到,《楚辞集注》里的《吊屈原赋》及注文,均依据颜师古注本《汉书》。这意味着《汉书》录本《吊屈原赋》经《文选》再到贾谊集本,始终占据了主导性的文本地位。相较于《史记》录本,代表着更接近原本面貌的《汉书》录本系《吊屈原赋》,成为通行的文本面貌。故张燮之后的张溥辑本《贾长沙集》里的《吊屈原赋》,仍依据《汉书》录本;以至清人严可均校辑《全汉文》“贾谊”条依据的虽是《文选》录本,但其文本面貌仍主要反映《汉书》录本。附带一提的是,清人何绍基批读张溥本贾谊集中的此赋,针对“袭九渊之神龙兮”至“固将制于蝼蚁”一段,留下了“曲折尽致,甚为雄矫”的评点。该段上半部分依次以神龙、圣人、麒麟为喻,阐述“远浊世而自臧”的道理,也为责怪屈原不能做到这一点而遭受忧难做了铺垫,即“般纷纷其离此邮兮,亦夫子之故也”。后半部分则分别以凤凰、吞舟之鱼和鳣鲸为喻,委婉地给出解脱之法,即“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不然的话,就会像吞舟之鱼和鳣鲸那样,受制于小水流和蝼蚁,而且还反为所害,再次呼应“般纷纷其离此邮兮,亦夫子之故也”之句。正反比较说理,环环相扣,都在烘托该段的中心旨意即“远浊世而自臧”,确可谓“曲折尽致”。在托物起喻上,相继使用神龙、圣人、麒麟、凤凰和大鱼一系列的形象,与物之小者如獭、蝼蚁等形成鲜明的对比,又确可谓“甚为雄矫”。至于明人陈仁锡评论该赋,称“语语悲咽,句句牢骚,备千古之感慨”(载清刻《汉魏六十名家》本《贾太傅书》中),纯以一己之感发论,远不及何绍基批读深刻而周致。
四、结语
综上所述,将《吊屈原赋》不同的录本与集本对读,关注诸如赋序、文字面貌、作品理解及古人注释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有助于我们了解作品的深层世界,使研究不落入泛泛而谈。笔者认为,《吊屈原赋》的小序并非贾谊所创作,而是史笔,但《史记》和《汉书》两者的史笔又存在着差异。这印证其中存在着部分改写,至《文选》而定型,但也造成创作自贾谊之手的假象。在文字面貌方面,《汉书》录本《吊屈原赋》不仅更接近赋作的原貌,而且在后世流传过程中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并为《文选》《楚辞集注》和贾谊集本所继承,充分说明《汉书》录本具备《吊屈原赋》通行文本的功能。而《史记》的情形就不同了,根据《史记集解》和《史记索隐》的注释,至迟在南朝宋时已经开始与《汉书》录本存在差异,此后差异还在不断出现。其实这也可视为一种改写,这种改写至迟在唐司马贞时才得以定型,形成今所见《史记》录本《吊屈原赋》的基本面貌。另外“兮”字句式与《汉书》录本的差异,可能与古人的阅读方式或对文学传统的认知有关。例如在理解作品方面,司马迁和刘向对赋作的理解路向是不同的:司马迁把《吊屈原赋》视为理解屈原的史传材料,而刘向则是“知人论世”的思路,将屈原视为贾谊本人的自况。刘向的观点影响了后世对《吊屈原赋》主旨的理解,特别是被班固采纳到《汉书》贾谊本传里,形成主流的意见,而宋代朱熹在《集注》里又做了进一步的发挥。细读前人的注释,也牵扯对作品的理解,如李善注贾谊作《吊屈原赋》本事不引《史记》和《汉书》,而引《风俗通》,便应据作品的文句细致加以诠释。这些都是启发我们研读古人作品的一种路径,即将版本的范式引入作品中,通过不同版本作品之间的差异化阅读,发现形式上的诸多不同,然后再思索造成这些不同的原因。由此将文本的形式与内容、文献的阅读与理解充分结合起来,庶几可创造出汉魏六朝诗文集研究的新气象。
注释:
① 《吊屈原赋》多为四字句式,与荀卿杂赋和秦代李斯的刻石文一脉相承,代表的是秦代杂赋的文学传统;而用“兮”字则又是南方楚辞体的影响,故该赋是典型南北两种文学体制影响下的产物。
②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即认为:“虽痛逝者,实以自悼。”(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页)。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也认为:“名为吊屈原,实是自吊。”(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页)。其他的理解还有如称:“贾谊同情屈原,但他和屈原的价值观、人生观是不同的。”参见袁行霈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
③ 刘跃进认为:“文帝派遣贾谊作长沙王的太傅,固然是为了缓解周勃等人对于贾谊的不满,并化解一些朝廷内部的矛盾,减少对统治的政治压力。而从当时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上说,不妨看作是对贾谊的一种实际锻炼和考验。对于年轻气盛的贾谊来说,未始不是一件好事。”(《回归与超越:漫议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历史感问题》,载于《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④ 陈振孙称:“今书首载《过秦论》,末为《吊湘赋》,余皆录《汉书》语,且略节谊本传于第十一卷中。”,参见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