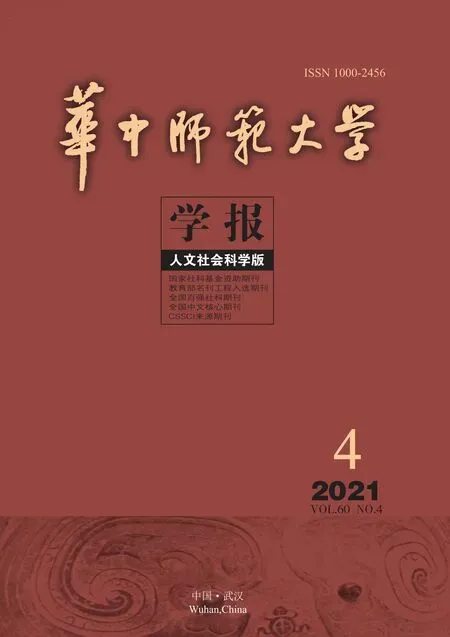胡风手稿《关于丁玲作品的札记》考论
2021-01-06刘卫国黄海丹
刘卫国 黄海丹
(中山大学 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胡风“1930年前后”曾写过一篇读书札记,评论丁玲的小说集《在黑暗中》,但当时没有发表。80多年后,胡风女儿晓风女士收集了胡风的一些未刊手稿,在《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3期以《胡风未刊稿一束》为名发表,其中,第一部分名为《关于丁玲作品的札记》。文末注释说:“梅志《胡风传》中曾提道:‘他在20年代就读了丁玲的小说,那时想写篇读后感式的文章,连要点都写好了,后来搁下了。’本篇底稿从所用稿纸(上海正午书局精制)及文风上看,应该就是当时所写的这篇‘要点’,写作年代应是在一九三○年前后。现依底稿原文抄录。”①
胡风这篇手稿面世以后,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重视。丁玲晚年秘书王增如女士非常看重这篇手稿,多次呼吁学术界进行研究。②本文试图对胡风的这篇手稿阐幽发微,考订其写作时间,分析其行文风格,揭示其价值和意义。
一、手稿究竟写于何时
据晓风女士的说法,胡风的这篇手稿写于“1930年前后”。又据梅志《胡风传》:“他在20年代就读了丁玲的小说,那时想写篇读后感式的文章,连要点都写好了,后来搁下了。从读小说到见到本人,所以不感陌生。”③胡风与丁玲1932年冬初次见面④,那么,这篇手稿应写于1932年冬之前。
“1930年前后”和“1932年冬之前”,这两个时间段仍然较有弹性,能否确定到具体哪一年呢?
值得注意的信息,是胡风手稿所用的稿纸为上海正午书局精制。上海正午书局1931年7月26日在上海《申报》上曾刊发开业酬宾广告,辞曰:“上海正午书局开幕特别减价 七月念六起 机会不可失 二十五天”。换言之,上海正午书局于1931年开业。那么,从手稿所用稿纸判断,胡风的这篇手稿不可能写于上海正午书局开业之前,只能写于上海正午书局开业之后。
又查胡风当时行踪,他于1929年9月赴日留学,1931年夏胡风从日本回国,后又经上海重返东京⑤。胡风1931年夏天曾在上海逗留,在此期间,他完全有可能购买了正好开业的上海正午书局精制的稿纸。
综合以上信息,可以初步判断:胡风这篇手稿写于1931年。
1931年,对于胡风来说,是一个有着纪念意义的年份。1936年,胡风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文艺批评文集《文艺笔谈》,在该书序言中,胡风这样说:“直到1931年遇到了几个给我以启蒙的艺术理论教育的友人以前,我和文艺的交涉差不多只是限于满足自我的欲求,在文艺世界里发现自己,提高自己。那表现之一是我非常地鄙视‘文艺批评’。在他人底心血结晶上面指手划脚,说好说坏,我以为那是最没有出息的事情。”⑥胡风将自己从事文艺批评的时间定于1931年。
不过,《文艺笔谈》中的文章,全都写于1933年至1935年间。胡风在每篇文章后都署上了写作时期,如《林语堂论》写于1934年12月11日,《张天翼论》写于1934年4月,时间最早的一篇《秋田雨雀印象记》写于1933年6月30日。
在1933年6月30日前,胡风也写过文艺批评文章。1932年12月出版的《文学月报》1卷5、6期合刊上发表了胡风的《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用〈现代〉第一卷的创作做例子,评第三种人论争中的中心问题之一》。此文文末胡风自注:“12,16,1932,写毕”。另据研究者发现,胡风在1932年至1933年间,用日文写作并发表了两篇文艺批评文章。一是《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诸成果之“中国”篇》,发表于1932年日本艺术学研究会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学研究》第二辑,此文评论了1932年5月发表的葛琴小说《总退却》和文君的《豆腐阿姐》,故只能写于1932年5月之后。二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发表于1933年日本《普罗文学奖作》第三卷,此文文末也署上了写作时期:“1932年9月18、19日”。这两篇文章后来都收入《胡风全集》补遗卷。
胡风自承从1931年开始从事文艺批评,但以上三篇文章均写于1932年,1931年胡风到底写过什么文章?用排除法来推断,只能是这篇评论丁玲《在黑暗中》的手稿。
这篇手稿是不是胡风最早的文学评论尝试呢?很遗憾,不是。胡风在1928年10月曾计划写作《略评近年来的文艺论争》,该文先写了引言一节,发表于1928年10月15日出版的江西《策进周刊》3卷55期。文章开头说:“说是‘评’,却也并非想把现代文坛上的各派加以陈述或研究,追溯它们底源流或变迁,比较它们主观的观点和客观的影响之不同,再来加以批判,哪是对的,哪是错的,文艺家应当做些什么,怎样做,等等;这样浩瀚的工作尽由那些能干的所谓‘文艺批评家’之流去做,我没有时间,尤其重要的,我从来对于这样的工作没有什么好感。”⑦这篇文章是胡风的第一次文艺批评尝试,但看起来更像是硬着头皮接受的任务,而不是胡风自己想写的,因此写起来有点“咬牙切齿”,胡风在行文中还明确表示自己对“所谓文艺批评家”的工作“没有什么好感”。之后,胡风“勉强写成”第一节,发表于1928年10月22日出版的《策进周刊》3卷56期。第一节写完后,胡风自感“问题太浩瀚,讨论起来太吃力”,因此决定“其余的不再写了”⑧。胡风对这篇文章也不重视,未将此文收入自己的任何一本著作,任其散佚(这篇文章是后来被研究者辑佚收入《胡风全集》补遗卷的)。胡风在出版第一本文艺批评著作《文艺笔谈》时,又将自己从事文艺批评的时间延后到1931年,而不是确定为1928年,显然并不看重这篇初试啼声之作。
如此说来,这篇手稿应是胡风的第二次文艺批评尝试,但由于胡风的第一次文艺批评尝试失败了,因此,第二次文艺批评尝试就显得格外重要。胡风对这一篇的态度与第一篇截然不同,胡风一直保留着手稿,未将其丢弃,未任其散佚,显然很看重第二次文艺批评尝试。
二、胡风如何分析作品
胡风1931年所写的这篇手稿,用的是札记体,记录了自己阅读《在黑暗中》的感受和看法。按照胡风夫人梅志的说法,胡风这篇手稿只是记录了一些要点,最终想写成一篇读后感式的文章。先写札记,记下要点,为写成正式文章做准备,可见胡风积极主动、严肃认真的态度。这篇札记内容详实,观点也具有洞见,其学术质量比起他人发表的评论文章不遑多让,甚至更胜一筹。
在胡风之前,毅真曾评论丁玲的《在黑暗中》⑨,这里不妨拿来比较。毅真的文章开头这样写:“丁玲女士是一位新进的一鸣惊人的女作家。自从她的处女作《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等在《小说月报》上接连地发表之后,便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这段开场白写得较有气势,也有水平。不过,接下来的作品分析部分,就显得较为一般。如对于《梦珂》,毅真的分析是这样的:
《在黑暗中》共包含小说四篇,《梦珂》是描写一个女子被环境压迫因而堕落的故事。女主人公梦珂幼年的环境便是与一位失意的老父相处,每日过那喝酒下棋的颓废生活。到了学校,那黑暗的学校生活,压迫得她只得退了学寄住在姑母的家里。然而姑母家里的更黑暗了一层的生活,她是更受不了的,最后,迫得她走投无路,便往社会的大漩涡中深深的堕落下去,而去作那所谓“电影明星”的生活去了。
胡风手稿开头就是对《梦珂》的分析:
主人公由破落了的农村地主社会走到黑暗的学校,由学校再走到虚伪的资产(或小资产)阶级社会,再从这社会走到丑恶的流氓社会。这些现实生活在作者纤细的神经上起了强烈的振动。和现代一切只在恋爱本身的幻变上织故事的女作家不同,作者底女主人公是被现实社会的冷浪由“一枝兰花”炼成一个隐忍力“更加强烈更加伟大”的能对生活不败的人了。这表示了作者向现实社会走的最初的姿势。——和一切作恋爱故事的女作家不同,这里只有各种黑暗势力对于一个女子的影响,绝对嗅不出一点人生变幻无常、恋爱多苦难的气息。当然,封建势力的重担在这里没有看到。作者底神经是非常纤细的,只是由对于现实生活的感受而生变化,绝对没有使她底人物成为一个表现哲学的工具,如冰心等作者。49页关于恋爱的谈话,可更证实了她对现实的正视。因了她这纤细的神经,作为“decadent”生活之基素的官能享乐生活,对于自己底美的陶醉和物质生活的变态,也相当强烈地表现了。这不仅是为了对照,应该当作作者初期生活里固有的一面之反映。
两相对比,毅真只介绍了《梦珂》的故事情节,胡风除了概括故事情节,还对梦珂这个人物的心理变化过程进行了分析,并由此触及作者丁玲对现实的态度。这种写法显然更鞭辟入里。
对于《暑假中》,毅真这样分析:
《暑假中》是描写职业女子的苦闷的,背景是武陵县的一个小学校,人物是几位富于感情的女教师。以女子写女子间的高度的苦闷,那样周到,深刻、透贴、细腻,我们除了惊服之外,真是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而胡风这样分析:
中间层女性在沉滞社会中的生活之无出路。当然,作者在这里面是想说明婚姻对生活的重要的,但她底笔却使她把沉滞社会中的女性的生活写得非常有力。一方面,对于凡庸生活的厌恶,一方面,虽然晓得她们“缺少着一种更大的更能使她感[到]生命的力”,却没有一个人有明确的路。因之,对于地主阶级生活强烈的眷恋(嘉瑛),对于结婚生活的观念式的评价(德珍的幸福和承淑的懊悔与志清的情绪),表明了作者认识上的限度。
这小说,一方面说出了凡庸与不耐,一方面依然流露出了作者纤细的柔美的神经。
两相对照,毅真似乎“真是没有什么话可说”,其分析实在浅显,而胡风既概括了作品的主题,又分析了人物的心理,既看出丁玲“写得非常有力”,又指出丁玲的“认识上的限度”。
关于《阿毛姑娘》,毅真只说了简单一句话:“《阿毛姑娘》是描写乡村妇女的心理的。”胡风的分析则更为全面和深入,首先把整部作品定性为悲剧,接着分析了悲剧产生的原因,还揭示了丁玲在创作人物上的得失。
这个阶级社会里可怜的女性底悲剧。那原因是在经济制度,作者底意图是明白的。但她并没有想从这里面去创造她底人物。她只是注重人物性格随环境的变幻而生的变化。而且,只注重心理的描写和纤细的感觉的表现上,反而把这一本质上的关系掩住了,使故事带着有命运气息的悲剧空气。作者在这里面所吐露的无智的或者反而有福以及阿毛所羡慕的能干女人也过着很苦的生活(这不是拿来说能干女人无出路之所以而是拿来说明阿毛的奢望是“错”),和阿毛对于童年故乡回顾上,都表明了作者在“消沉”空气里认识上的限界。
《莎菲女士的日记》是《在黑暗中》的重头戏,毅真认为最能代表丁玲女士的作风。毅真先是概述“《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主人公即是莎菲女士,一个患有肺病的女子,她的恋爱的故事,绝不是平平凡凡的你爱我,我也爱你的故事,也不是你爱我,我不爱你,或我爱你,你不爱我的Trouble,更不是简单的几角恋爱。她的爱的见解,是异常的深刻而为此刻以前的作家们所体会不到的”,然后摘引了莎菲日记中的四段记述,最后加以这样的评价:“这些率直的女性的心理的描写,真是中国新文坛上极可骄傲的成绩。我们只要读了上面所引的几小段文字,对于近代的新女性,已经了然大半了。”
而胡风的分析更为深入与透彻。他首先概括了《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主题,并对作品表达的思想进行了定性和评价:
对于凡俗不洁的社会——生活的厌恶,对于内容与形式统一的“美”——理想的追求。真实的个人主义精神底表现。但在被限定了的五四高潮后的是中国社会,这追求不能成为一个明确的社会实践态度,没有“出路”,因而把问题移到了人生无常和生命短促(姐姐底死和自己底病)等主观方面来了。这作品是民主革命失败后的最悲痛的呼喊,她是抱着向光明的飞跃的心对着污秽的现实人生痛哭了的。
接着,又比较了莎菲和梦珂之异同,并由莎菲的人生观分析丁玲的创作心理:
她以为,梦珂由惨败里得到了胜利,莎菲在胜利中惨败了。但我以为,这是很难说的。梦珂底胜利不过是建筑在苍蝇蛆虫的上面,她并没有反抗的一念,她所静待的成功不过是表明作者对人生的憧憬而已。而莎菲,虽然败到倒到污泥里了,但并不屈服,她宁愿把生命当作“玩品”“浪费”,宁可到“无人认识的地方”,甚至“怜惜自己”,这里表明了她一直保持着对人生的厌恶。这表示了她(作者)更肉搏近了现实,表现了她在丑恶的现实里无论如何要坚持着爱人生的心(虽然是消极的),双足滴血。
莎菲,在社会实践上,是一名废兵,但在人生行程上,是一个殉难的节士。这矛盾,说明了作者当时社会的沉滞和她底生活,也说明了她后来的何以能够那样地前进。
对作品的阅读与分析能力,是文艺批评家的基本功,从胡风的札记看,他对作品读得非常细致,分析更具有穿透力。一篇札记,写得相当扎实,也相当流畅。胡风在写第一篇文艺批评文章《略评近年来的文艺论争》时,感觉“讨论起来太吃力”,文章虽然发表了,但事实上是失败的,从事文艺批评的自信也受到了挫折。胡风的第二次文艺批评尝试,虽然未能整理成文发表,但在这次尝试中,胡风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文艺批评能力,恢复了从事文艺批评的自信。胡风之所以一直珍藏这份手稿,恐怕有此缘由。
三、胡风对丁玲的欣赏
应该说,胡风1931年评论《在黑暗中》,已经失去时效性。《在黑暗中》192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之后丁玲又有更多新作问世。1929年5月,丁玲的第二本小说集《自杀日记》由上海光华书店出版。1930年9月,丁玲的长篇小说《韦护》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1930年下半年,丁玲发表了中篇小说《一九三○年春上海》(一、二)。1931年7月,丁玲又发表了短篇小说《田家冲》。从事当代文艺批评,一般要赶热点,讲究时效性,胡风为何还要在1931年评论丁玲1928年出版的《在黑暗中》呢?
对于文艺批评家来说,作家的第一部作品是认识这个作家的原点或坐标。《在黑暗中》是丁玲的处女作,要全面、完整地认识丁玲,显然应该从这部作品谈起。这应是胡风关注《在黑暗中》的第一个原因。当然,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丁玲的《在黑暗中》确有吸引胡风的东西。接受美学理论认为,读者在接受一部作品时,总是带着自己的期待视野,如果作品不符合自己的期待视野,读者往往不能接受这部作品,胡风之所以关注丁玲的《在黑暗中》,还因为《在黑暗中》的一些信息与胡风的期待视野实现了“视界融合”。
细读胡风的手稿,不难发现一个关键词“社会”。“社会”指的是丁玲作品中所描写的世界。胡风用这样一些词汇形容这个世界:“破落了的农村地主社会”“黑暗的学校”“虚伪的资产(或小资产)阶级社会”“丑恶的流氓社会”“封建势力的重担”“凡俗不洁的社会”“丑恶的现实”“社会的沉滞”“沉滞社会”“阶级社会”。胡风还说,丁玲所描写的文明社会有两面,一是物质的官能享乐一方面,一是颓废的虚伪的一面。这些词汇和句子,都是胡风从丁玲作品所写的世界中概括出来的。看得出,丁玲所描写的社会,符合胡风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即与胡风的视界实现了融合。没有这个视界融合,以胡风的个性,肯定会批评丁玲描写的世界不真实。
在这方面是有例子的。胡风1935年曾怒怼李长之,只因为李长之发表了一篇《大自然的礼赞》⑩,号召人们到大自然里去寻找归宿。这篇文章与胡风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严重不符。胡风从当时报纸上摘取1935年长江水灾的悲惨记事,愤怒地指摘道:“在这里,‘人类的母亲’的大自然给我们的并不是‘种种暗示,种种比喻,种种曲折而委婉的辞令’,却是直截了当的毁灭一切有生无生的暴力,完全不是‘你瞧罢,雪,红叶,秋霁的天岚,夏木的浓荫……’的那付慈颜了。”胡风还怼过京派。1935年,胡风在评论澎岛的小说集《蜈蚣船》时,副标题取名为“‘京派’看不到的世界”。胡风发现,《蜈蚣船》里所描写的世界,里面毫无“京派”的“雅”处,如《蜈蚣船》写内河里的屁股帮和霸占航路的蜈蚣船间的斗争;《围困》写学生的反抗和悲惨的失败;《席苇捐》写席民们对于苛捐的反抗;《偷堤》写大水时的恐惧使农民们决定去偷堤的经过;《隔邻》写富农和他的儿子苦心图谋邻人的房产;《火灾》写小煤油商人父子俩在世界的新旧煤油势力竞争下破产,放火烧店自杀;《一天》写在城里当学徒的儿子给敌人捉去活埋,年老的父亲愤而加入义勇军。胡风评论道:“这里面找不出一丝一毫的‘名士才情’,更没有什么‘明净的观照’,但这种‘粗鄙’而热辣的人生,却是这个世界里的事实。我们懂,我们关心,对于那里面的人物和事件我们也就能够说出平凡的观感。”胡风非常认同澎岛小说所描写的世界,因此给予其作品好评,并顺便刺了京派一枪,因为京派对社会的看法并不符合胡风的期待视野。
其实,《在黑暗中》中的各篇小说,写的都是青年女性人物的生活,这对当时的胡风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但胡风觉得,丁玲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与自己有着一致性,这让胡风感觉“气味相投”,因此主动关注丁玲的创作。
胡风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及自己青年经历时曾说:“在国内读到的创造社的作品,几乎都是大而空的‘意识形态’的表演,没有普通人民的感情;茅盾的作品有具体描写,但那形象是冷淡的,或者加点刺激性的色情,也没有普通人民的真情实感的生活。”胡风当时对国内的文学状况有所不满。创造社和茅盾的作品都不符合胡风的期待视野,丁玲的《在黑暗中》出现了,它不是“大而空的意识形态的表演”,且“写出了普通人民的真情实感的生活”,正好符合胡风的“期待视野”。
胡风在写这篇手稿时,与丁玲素未谋面,但批评家可以“以文观人”,因为“文本诸人,乃作者取诸己以成文”,言为心声、书为心画。通过揣摩作家写什么及怎么写,批评家能够深入到作家的心灵世界,把握作家的个性性格。
胡风在手稿中,从作品对丁玲的心灵世界进行了揣摩。他几次用“纤细”一词来形容丁玲,如“纤细的神经”,“作者底神经是非常纤细的”,“纤细的柔美的神经”。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说,神经可能确实要纤细一些。说丁玲神经纤细,并不会错。但胡风又用“柔美”、“柔软”一类词来形容丁玲,实话说,这并不完全符合丁玲的个性。
沈从文是丁玲的好友,他对丁玲的描述是:“大胆地以男子丈夫气分析自己,为病态神经质青年女人作动人的素描,为下层女人有所申述,丁玲女士的作品,给人的趣味,给人的感动,把前一时期几个女作家所有的爱好者兴味与方向皆扭转了。他们忽略了冰心,忽略了庐隐,淦女士的词人笔调太俗,淑华女士的闺秀笔致太淡,丁玲女士的作品恰恰给读者们一些新的兴奋。反复酣畅地写出一切,带点儿忧郁,一点儿轻狂,攫着了读者的感情,到目前,复因自己意识就着时代而前进,故尚无一个女作家有更超越的惊人的作品可以企及的。”沈从文强调丁玲有“男子丈夫气”,应该说是“知人之言”。胡风说丁玲“柔美”、“柔软”,这显然并不准确。
不过,胡风虽然不像沈从文那样熟悉丁玲,但他看出了丁玲具有“向光明”、“并不屈服”、“坚持”等气质,这又比沈从文所说的“带点儿忧郁,一点儿轻狂”更为准确。胡风这样评价《梦珂》:“梦珂虽然实际上惨败了,但作者并不承认,说她‘更加伟大’。说明了作者当时的‘消沉’和‘不能说是灰心’,说明了以后的路径。”胡风肯定丁玲在“消沉”中的“不灰心”,又这样评价《莎菲女士的日记》:“这作品是民主革命失败后的最悲痛的呼喊,她是抱着向光明的飞跃的心对着污秽的现实人生痛哭了的。”胡风肯定莎菲“虽然败到倒到污泥里了,但并不屈服”,赞扬莎菲“肉搏近了现实”,“表现了她在丑恶的现实里无论如何要坚持着爱人生的心”,又赞赏丁玲“和一切作恋爱故事的女作家不同”,在丁玲所写的恋爱故事中,“绝对嗅不出一点人生变幻无常、恋爱多苦难的气息”,换言之,胡风认为:丁玲的人生态度,是严肃的,战斗的,并不“忧郁”,也不“轻狂”。沈从文可能太熟悉丁玲了,熟人眼里无伟人,用“忧郁”、“轻狂”来形容丁玲,显得有点贬低了,反不如胡风这个陌生人看得准确。
在《关于丁玲底作品的札记》中,胡风注意到当时有人对《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指责,他为之辩护说:“有人说这作品是写五四解放后对于肉的追求,这完全是对作者的侮辱。我想,这里面没有一丝一毫肉的追求。”客观地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并非“没有一丝一毫肉的追求”。莎菲初见凌吉士,觉得“那高个儿可真漂亮”,丁玲马上写道:“但我知道这个社会里面是不会准许任我去取得我所要的来满足我的冲动,我的欲望。”这一句明确袒露了莎菲的“肉的追求”。当然,莎菲的“肉的追求”是与灵的追求融合在一起的,莎菲期待的是灵肉一致的爱情。但要说莎菲内心中“没有一丝一毫肉的追求”,那是不准确的。看得出,胡风实在太欣赏丁玲了,容不下一丝一毫对丁玲的负面评论。
其实,写《在黑暗中》的丁玲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具有这个阶级特有的动摇性和多变性,但是,《在黑暗中》对社会的描写让胡风深有同感,而从这些描写中,胡风感觉到丁玲的人格是“严肃的”、“不屈服的”、“向光明的”,因此胡风认为,丁玲即便遇到认识上的限度(或限界),也能继续前进。应该说,胡风“以文观人”,尽管细节上略有瑕疵,但大体把握住了丁玲的个性心理,也把握住了丁玲趋向进步的思想线索。
这篇手稿,可以说是胡风与丁玲的一次“神交”。1932年冬,胡风从日本回国,“在东京见过的华蒂(以群)引我去参加了左联(书记丁玲)的一次日常性会议。和丁玲也是一见如故”。胡风为什么和丁玲一见如故?因为他仔细阅读并分析过丁玲的《在黑暗中》,与丁玲的世界观一致,对丁玲的个性心理有一定了解,换言之,胡风对丁玲神交已久,见到真人之后,自然有故人的感觉。
四、批评风格的崭露
在这篇手稿中,胡风使用了“阶级社会”“经济制度”“封建势力”“个人主义”等概念,这些概念均是马克思主义常用的概念。这一事实可以佐证胡风当时已经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在1928年的革命文学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正式登上文学批评的历史舞台,并在20世纪30年代引领文学批评的风骚,造就了“红色的三十年代”。胡风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阵营的生力军。
但从这篇手稿看,胡风与其他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有着不同的批评路子和批评风格。在胡风评论丁玲的《在黑暗中》之前,钱杏邨曾评论过《在黑暗中》,在此之后,冯雪峰在评论丁玲的新作《水》时曾回溯过《在黑暗中》。钱杏邨和冯雪峰都是马克思主义阵营中鼎鼎有名的批评家,出道都比胡风早,在1930年前期,也比胡风影响更大。这里不妨将钱杏邨、冯雪峰两人与胡风的文艺批评风格进行比较。
钱杏邨对《在黑暗中》的总印象是这样的:“总结这二百七十面的创作,作者只送出这样的一种哀喊,‘社会是黑暗的,生是乏味的,生不如死’,所以,这些人物便乐意的把‘生命当做自己的玩品,要尽量的浪费掉’,而把一切的幸福看作‘水月镜花’。但是,作者不会指出社会何以如此的黑暗,生活何以这样的乏味,以及何以生不如死的基本原理,而说明社会的痼疾的起源来。”对于丁玲笔下的人物,钱杏邨认为:“作者所表现的人物,对宇宙是不求解释的,大都是为感情所支配着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她们需要感情,她们需要享乐,她们需要幸福,同时也需要自由。然而,社会什么都不给与,无往而不使她们失望。她们只有极强烈的感受性,没有坚强的抗斗的意志;她们只有理想的欲求,不肯在失败的事件中加以深邃的原理的探讨。结果,便自然的产生了厌世的倾向,在有生的时候,把自己的生命尽量的玩弄一回,——这就是作者从客观方面所表现的人生。”钱杏邨对此评价不高:“《在黑暗中》的人物,就是在消极一方面说,也还是懦弱的,还没有站在社会的面前,公开的作践自己而无悔的勇气。对于社会是绝望了,把人生是看得那样黯淡,然而,站在社会的面前,终不免于颤抖。她们的生活,从这一点看去,似乎还没有正式敌视社会的精神,而挣扎在冲突矛盾的现象之中。而她们的感情与理智也时时的在冲突。前面说过,她们都是为感情所支配着的人物,在最后,都是感情战胜了理智,事实征服了理想,命运打败了创造,虽然她也曾送出最后的挣扎,如《莎菲女士日记》。我看了莎菲之与凌吉士,我有了《灰色马》里的佐治抱住女人在膝上的怀疑的联想。作者的思想,确实的有一点着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最后,钱杏邨做出判断:“《在黑暗中》是一部写实主义的创作,以个人为出发而仍以个人为终结的第一期写实主义的创作。作者微微的具有世纪末的病态。《在黑暗中》所表现的,当然是渴望自由与幸福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的思想,有着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在这样的人物之间,有向上的积极的求出路的一面,也有消极的走向灭亡的一途,作者所表现的人物,是代表了后者。《在黑暗中》只表现了作者的伤感,只表现了这一种人生。作者对于文学本身的认识,仅止于‘表现’,没有更进一步的捉到文学的社会的意义。作者只认识‘文学是人生的表现’的一个原则,忘却了‘创造人生’的一面。”总之,钱杏邨认为,丁玲的思想观念还不够进步,停留在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水准,有着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距离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水准还差得远,其创作仅止于“表现”,没有进一步捕捉到文学的社会的意义。
冯雪峰的文章主要评论丁玲的新作《水》,但先对丁玲的创作历史做了一番回顾,回顾中这样评论丁玲的《在黑暗中》:“且说丁玲原来是怎样的作家呢?丁玲在写《梦珂》,写《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及写《阿毛姑娘》的时期,谁都明白她乃是在思想上领有着坏的倾向的作家。那倾向的本质,可以说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性加流浪汉的知识阶级性加资产阶级颓废的和享乐而成的混合物。她是和她差不多同阶级出身(她自己是破产的地主官绅阶级出身,‘新潮流’所产生的‘新人’——曾配当‘忏悔的贵族’)的知识分子的一典型。在描写一个没落中的地主官绅阶级的青年女子,接触着‘新思潮’(‘五四’式的)和上海资本主义生活时所现露的意识和性格的《梦珂》里,在描写同样的青年知识女子的苦闷的,无聊的,厌倦的不健康的心理状态的《莎菲女士的日记》里,在说述一个贫农的女儿,对于资本主义的物质的虚荣的幻灭的可怜的故事《阿毛姑娘》里,任情的反映了作者自己的离社会的,绝望的,个人主义的无政府的倾向。”
钱杏邨和冯雪峰的批评,涉及作品内容和作家思想倾向两个层面。在作品内容上,钱杏邨认为丁玲只写出了社会黑暗的一面,但没有指出“社会何以如此的黑暗,生活何以这样的乏味,以及何以生不如死的基本原理,而说明社会的痼疾的起源来”。这是以社会科学家的标准要求作家,有点强人所难。冯雪峰也认为,丁玲描写的不是没落的地主官绅阶级的生活,就是颓废享乐的资本主义的生活,或者是对资本主义物质生活的幻想。从作品内容推断,两人的批评最后都落脚于作家的思想倾向,都认为丁玲的作品表现出“个人主义的无政府的倾向”,这种倾向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因此两人都对《在黑暗中》持否定态度。显然,在评论丁玲的作品时,两人心中已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学的标准,然后拿着这个标准衡量丁玲。两人的批评姿态也是居高临下的,对作家颐指气使,提出各种要求。其实作家只能按照自己所体验或了解的生活去写,这种生活不一定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本质性要求,但它是鲜活的,生动的,有真情实感的。如果丁玲真按照钱杏邨和冯雪峰所要求的那样,写出的东西难免模式化。
茅盾后来在回忆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艺批评时曾说:“健全正确的文艺批评尚未建立起来,批评家尚未摆脱旧的习惯。所以作家们写出作品,听到的每每是‘从大处落墨’的空泛论断,什么‘没有把握时代的精神’,‘无视了许多伟大的斗争’,‘没有写出新时代的英雄’等等,却很少见到作具体分析的评论,也很少听到对作家创作甘苦表示体恤的。”茅盾这里所谈论的左翼文艺批评,应该也包括钱杏邨与冯雪峰在内。钱杏邨和冯雪峰在评论丁玲的《在黑暗中》时,都是“从大处落墨”,他们关注的主要是作品的内容是否满足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本质性,作家的思想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正确性。至于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如何处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作家的创作心理如何,其中有何甘苦,有何得失,他们几乎不予理会。
钱杏邨和冯雪峰的盲点正是胡风文艺批评的切入点,胡风格外关注的是作家的创作过程,是创作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联结状况。首先表现在作家的主观如何选择、把握和熔铸题材;其次,胡风又从作家的选择、把握与熔铸方式,反观作家的人生态度、揣摩作家的创作心理,把握作家的个性风格。与此同时,胡风也指出作家的局限与不足,但他不拿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性、正确性这些标准来要求作家,而是期待并鼓励作家自我反思、自我醒悟与自我突破。如在评《暑假中》时,胡风发现了“作者认识上的限度”,在评《阿毛姑娘》,胡风又看到了“作者在‘消沉’空气里认识上的限界”,但胡风并不耳提面命,而是帮作家分析原因:“那原因是在经济制度,作者底意图是明白的。但她并没有想从这里面去创造她底人物。只是注重人物性格随环境的变幻而生的变化。而且,只注重心理的描写和纤细的感觉的表现上,反而把这一本质上的关系掩住了,使故事带着有命运气息的悲剧空气。”这样的批评,深入到作家的创作心理,能体贴作家的创作甘苦,也能引导作家找到真正的症结和今后的突破口。这种批评风格可以弥补钱杏邨和冯雪峰的局限。胡风之所以能在20世纪30年代迅速崛起于左翼批评界,自成一家,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这篇手稿中,胡风还表现出创造概念的能力。如“沉滞社会”“凡庸生活”等概念,就是胡风发明的概念。众所周知,胡风后来还创建了“主观战斗精神”“客观主义”“主观主义”等概念。胡风称赞丁玲“更肉搏近了现实,表现了她在丑恶的现实里无论如何要坚持着爱人生的心(虽然是消极的),双足滴血。”这种表述方式,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胡风后来提倡的“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可以说,这篇手稿中也潜藏了胡风后来“主观战斗精神”理论的某些因子。
概而言之,这篇写于1931年的手稿,虽然不是胡风初试啼声之作,但在胡风的文艺批评生涯中也有其重要地位,它是胡风第一次文艺批评失败之后的第二次尝试,这次尝试让胡风重拾了从事文艺批评的信心。这篇手稿对丁玲的《在黑暗中》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它是胡风与丁玲一见如故的友谊见证,也崭露了胡风文艺批评上的个性风格。
注释
①晓风:《胡风未刊稿一束》,《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3期。本文所引胡风评丁玲语,皆来自此文,不再一一注释。
②笔者2018年11月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丁玲与上海”学术会议上听到王增如女士讲话,受其启发,撰写此文,特此致谢。
③梅志:《胡风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31页。
④⑤晓风:《胡风年表简编》,《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4期。
⑥胡风:《文艺笔谈·序》,见《文艺笔谈》,上海:文学出版社,1936年,第1页。
⑦⑧胡风:《略评近年来的文艺论争》,见《胡风全集》补遗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1页,第68页。
⑨毅真:《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妇女杂志》第16卷第7号,1930年7月1日,下文所引相关评论文字,皆引自该版本,不再一一注释。
⑩李长之:《大自然的礼赞》,《星火》第1卷第2期,1935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