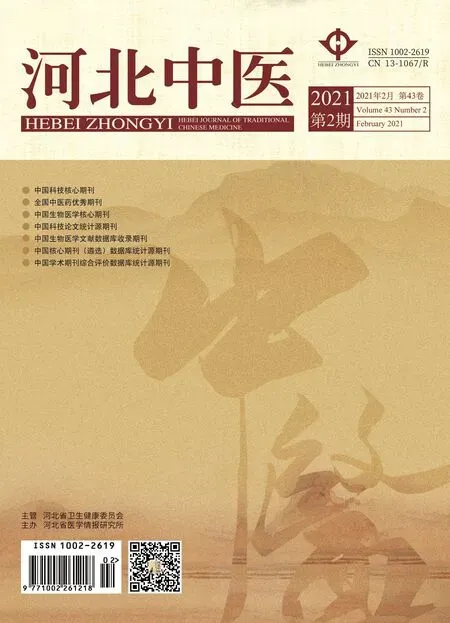中医外治法干预结直肠癌围手术期研究进展※
2021-01-05梁伟健杨得振冯飞雪侯俊明
梁伟健 贾 勇 杨得振 冯飞雪 侯俊明
(陕西中医药大学,陕西 咸阳 712046)
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是21世纪以来对人体危害较大的一种恶性肿瘤。一项估计2018年全球186个国家36种癌症疾病新增病例情况的研究结果显示,结直肠癌在所有新增癌症总病例数中排第4位,致死率达9.2%,分别是男性和女性因癌症而死亡的第三大和第二大疾病[1]。结直肠癌的治疗多采用化疗、放疗、外科手术、免疫治疗、靶向治疗、多学科协作及中医药辅助治疗等,其中手术治疗是目前根治结直肠癌的主要措施之一。但由于结直肠癌对患者的肠道消化功能带来一定损害,手术又对患者带来一定的创伤,导致一系列并发症,给患者围手术期康复带来不良影响。研究显示,围手术期的管理对于患者手术的顺利进行及预后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快速康复外科(ERAS)而产生的围手术期管理模式引入我国已有十余年,并广泛应用于肝胆外科、胃肠外科、骨科等临床[2]。虽然这一模式较传统围手术期管理方式疗效更佳[3],但多以西医治疗为主,缺乏中医辨证论治,在促进人体正气恢复、加快自愈方面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而患者围手术期的某些过程中无法口服中药这一情况限制了中医药作用的发挥,这一问题亟待解决。中医外治法以中医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为指导,通过扶助正气激发机体的抗邪能力,较好地弥补了以上不足。本研究对中医外治法在结直肠癌围手术期中的应用及效果进行综述。
1 对于中医外治法、结直肠癌及围手术期的认识
1.1 中医外治法的概念及发展过程 中医外治法是以脏腑经络为理论,应用中药、手法或适当的工具作用于机体上相应的部位、经穴等,以达到疏经活络、调节阴阳、扶正抗邪等作用的方法。战国时期的《五十二病方》载有多种多样的治疗方法,尤以外治法最突出,载有贴敷法、熏蒸法、灸法、砭法、药浴法、按摩法、角法等十余种外治法[4],对中医外治法的发展有积极的引领作用。东汉张仲景首创猪胆汁灌肠导滞、汗出过多温粉扑之等外治法。清代医家吴师机的《理瀹骈文》系统详细地介绍了数十种外治法,后世称之为“外治之宗”,外治法的理论进一步成熟。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外治法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并发展,多种学术交流会议和学术组织涌现[5]。当代,吴震西、吴自强著有《中医内病外治》,该书反映了近半个世纪中医外治法发展的概貌,提倡外治法在内、妇、儿等科疾病中应用。当今中医外治法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临床,根据作用途径的不同,分为皮肤黏膜治疗、整体治疗、经络腧穴治疗及其他治疗4种,但各分类之间多有交叉,不能截然分离。随着科技的进步,各种声、电、磁类新技术、新方法、新工具也逐渐与手法、工具类的外治法相融合;药物外治的剂型也变得简便易得,具有健康、简便、安全、有效的优点[6]。
1.2 中医对结直肠癌的认识 中医古籍对结直肠癌的认识多为“肠蕈”“脏毒”“积聚”“锁肛痔”等。《血证论》载:“脏毒者,肛门肿硬,疼痛流血,与痔漏相似。”《普济本事方》说:“如下清血色鲜者,肠风也;血浊而色黯者,脏毒也。”《外科大成》中论述锁肛痔的表现为“锁肛痔,肛门内外如竹节锁紧,形如海蜇,里急后重,便粪细而带扁,时注臭水,此无法治”。关于其病因病机,《灵枢·水胀》载“寒气客于肠外,与卫气相搏,气不得荣……恶气乃起,息肉乃生”,《太平圣惠方》载“大肠中久积风冷,中焦有虚热……风冷热毒,搏于大肠,大肠既虚,时时下血,故名肠风也”,《丹溪心法》载“肠胃不虚,邪气无从而入。人惟坐卧风湿,醉饱房劳,生冷停寒,酒面积热,以致营血失道,渗入大肠,此肠风脏毒之所由作也”,张从正曰:“积之始成也,或因暴怒喜悲思恐之气。”以上可见,结直肠癌系六淫外侵,或七情内伤,或饮食不节,或劳倦内伤,导致脾胃失和,痰湿内生,郁而化热,湿热下注肠道,气机郁滞,血运不畅,瘀毒内停,湿、热、瘀、毒互结,日久而成。脾肾亏虚、正气不足为病之本,血瘀、痰凝、湿热、热毒为病之标[7]。
1.3 围手术期 也称手术全期,包括手术前、手术中及手术后。手术成功与否与围手术期的治疗有关[8]。其中,中医外治法在术前和术后应用较为广泛,术中以西医调护为主。
2 中医外治法在结直肠癌围手术期中的应用
2.1 术前 结直肠癌因癌肿的发生使肠腔狭窄,会合并不完全性肠梗阻,导致手术成功率降低。中医学认为,肠腑之气以降为顺,不通则痛,气机逆乱,上发为呕吐,治宜通导化积,调畅腑气。孙柱[9]采用大黄汤保留灌肠治疗结直肠癌术前不完全性肠梗阻30例,并与0.9%氯化钠注射液灌肠治疗30例对照观察。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93.33%)明显高于对照组(70.00%,P<0.05)。
2.2 术后 结直肠癌术后,由于人体受到机械损伤和二氧化碳气腹、残存麻醉等影响,会产生一系列的并发症,不利于患者康复,降低了患者生活质量。常见的并发症有睡眠障碍、胃肠功能紊乱、腹泻、吻合口炎及尿潴留等。
2.2.1 睡眠障碍 手术作为一种有创的疗法,不可避免的会有出血,气随血脱,人体正气受损,气血两虚,机体阴阳失衡,阴虚阳无以入,则夜不能寐。另外,手术导致的胃肠损伤也会导致失眠,即“胃不和,卧不安”。陈荣等[10]应用基于Roy模式的中医综合干预方案干预36例结肠癌术后患者,并与术后常规治疗方案干预36例对照观察。中医综合干预方案包括耳穴贴压(主穴选心、枕、神门、内分泌和皮质下)、艾灸(选双侧足三里)、吴茱萸热奄包脐周外敷。结果显示,观察组失眠症临床观察调查(SPIEGEL)总分及各维度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对睡眠质量的改善效果更佳。六阳经和六阴经分别直接或间接交于耳,选取耳穴的相应反应点进行刺激能起到调整阴阳、安神助眠的作用。赵姣妮等[11]采用耳穴贴压(穴位取耳中、肾、内分泌、心)对40例直肠癌围术期患者进行干预,并与围手术期常规护理40例对照观察。结果显示,观察组失眠症状消失时间短于对照组(P<0.05),睡眠时长明显长于对照组(P<0.05)。
2.2.2 胃肠功能紊乱 胃肠功能紊乱是结直肠癌术后患者常出现的问题。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气机升降的枢纽。结直肠癌本易导致脾气亏虚,正气不足,加之手术术中又损伤胃肠气机,肠道传导失司,大便及肠腑之气不畅,气聚而胀,而发腹胀、腹痛;或患者担心肿瘤复发等问题,导致情志抑郁,肝郁气滞,胃失和降,则痞满胀痛、食欲不振等。术前应用麻醉剂、镇静剂、镇痛药等在减少腺体分泌的同时,也可能导致术后胃肠功能紊乱。术后尽早恢复胃肠功能有助于加速患者康复,恢复的标准多参考术后腹胀减少、术后首次肠鸣音恢复时间及排气排便时间缩短。谭双[12]将60例大肠癌根治术后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2组。对照组30例进行常规治疗和护理,包括术后禁食、持续胃肠减压、吸氧、心电监护、进行补液和营养支持、术后早期活动等;治疗组30例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耳穴贴压(取穴:脾、胃、大肠、十二指肠、交感、三焦)结合足三里针刺治疗。结果显示,治疗组肠鸣音恢复时间、首次肛门排气时间以及首次排便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P<0.05),术后72 h腹胀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术后住院时间少于对照组(P<0.05)。提示耳穴贴压联合足三里针刺治疗能有效促进大肠癌术后患者胃肠功能恢复。王小英等[13]应用中药穴位贴敷(将小茴香、乌药、枳实、玄明粉、冰片、生大黄、槟榔研磨成粉后用15 mL蜂蜜调匀,贴敷于神阙、足三里)干预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21例,并与术后常规护理干预20例对照观察。结果显示,试验组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排便时间及患者首次进食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P<0.05)。提示穴位贴敷能显著促进结直肠癌术后患者胃肠道功能恢复。翁丽丽[14]将23例接受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的患者按随机信封内的随机数字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8例采用一般处理+安慰剂敷脐干预,试验组15例予一般治疗+醋甘遂敷脐。结果显示,试验组肠鸣音恢复时间、首次排气时间及首次排便时间均早于对照组(P<0.05)。黄文英[15]对30例结直肠癌术后患者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手法按摩手部穴位胃肠、脾、大肠痛点治疗,并与常规治疗干预30例对照观察。结果显示,治疗组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排便时间均较对照组明显缩短(P<0.05),术后第3 d及术后第5 d腹胀痛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肖超[16]将90例结直肠癌术后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Ⅰ、对照组Ⅱ和试验组。对照组Ⅱ(30例)予术后常规处理,对照组Ⅰ(30例)在常规处理的基础上术后24 h后予针刺双侧足三里及上巨虚干预,试验组(30例)在常规处理的基础上术后24 h后予电针(取双侧足三里、上巨虚,选择疏密波模式)干预,连续治疗5 d。结果显示,试验组术后肠鸣音恢复正常的时间、肛门第一次排气、排便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Ⅰ、对照组Ⅱ(P<0.05),术后第3 d、第5 d腹痛、腹胀、胃肠反应评分均优于对照组Ⅰ、对照组Ⅱ(P<0.05)。提示电针足三里、上巨虚能有效地促进结直肠癌术后患者胃肠功能的恢复,而且能改善患者术后腹痛、腹胀、胃肠反应等情况。周雪玲等[17]以温水足浴+咀嚼口香糖干预结直肠癌腹腔镜术后患者60例,并与常规护理干预60例对照观察。结果显示,试验组患者术后肠鸣音恢复时间、首次肛门排气和排便时间均早于对照组(P<0.05),术后72 h腹胀发生率、住院时间和住院费用均低于对照组(P<0.05),患者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郑晔辉[18]采用中药封包外敷(药物成分包括厚朴、吴茱萸、大黄、肉桂及少量冰片,于中脘、神阙及足三里处外敷)干预老年结直肠癌术后患者38例,并与术后常规干预38例对照观察。结果显示,观察组术后肛门排气时间、肠鸣音恢复时间及排便时间均较对照组短(P<0.05)。
2.2.3 腹泻 结直肠癌患者术前已脾气亏虚,中气不足,加上手术耗气,导致患者正气受损,脾虚无以统摄及运化水谷,肠失固摄,引起泄泻。姜家康等[19]采用耳穴贴压(取耳穴大肠、直肠、脾、胃、交感)联合参苓白术散治疗脾虚湿盛型大肠癌术后泄泻45例,对照组45例予盐酸洛哌丁胺胶囊治疗。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95.56%)明显高于对照组(82.22%,P<0.05),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刘朝阳[20]应用穴位贴敷(肉豆蔻、诃子、雄黄共研细末,用陈醋搅拌调成糊状,贴敷于神阙、关元)联合真人养脏汤加减治疗结直肠癌术后腹泻44例,并与对照组34例盐酸洛哌丁胺治疗对照观察。结果显示,2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观察组复发率(13.16%)低于对照组(55.17%,P<0.05),远期效果较好。王益等[21]对直肠癌Dixon术后腹泻患者进行治疗,对照组35例采用生物反馈训练治疗,试验组35例在对照组基础上加艾灸关元、神阙、天枢等治疗。治疗后1个月结果显示,试验组控制排便能力、排便次数、排便时间等评分及肛门总功能指数改善均优于对照组(P<0.05)。
2.2.4 吻合口炎 中医学认为,结直肠癌术后吻合口炎的病机为手术导致气血亏虚,瘀血凝滞,湿热下注。直肠给药可通过肠静脉直接吸收药物作用于病变局部,避免了肝脏的首过效应,治疗结直肠癌术后吻合口炎有较好的疗效。李艺等[22]采用自身对照的方法观察清肠汤(药物组成:黄芩、黄连、黄柏、苦参、侧柏炭、马鞭草、马齿苋、虎杖、槐花、山土瓜、木香)直肠滴注治疗结直肠癌术后吻合口炎77例的临床疗效。结果显示,77例患者治疗后Karnofsky评分、症状总积分、T淋巴细胞亚群水平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近期有效率为83%,疗效显著。杨得振等[23]采用莪黄灌肠液(药物组成:莪术、昆布、大黄、薏苡仁、人参、当归、黄芪)灌肠治疗直肠癌术后吻合口炎67例,14 d后有效率91%,且具核梭杆菌感染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0.05)。其研究认为,莪黄灌肠液能有效调节结直肠癌术后肠道菌群,改善肠道内微环境,降低肠道黏膜通透性,从而减少并发症感染几率[24]。
2.2.5 尿潴留 结直肠癌术后患者气血虚弱,加之局部脉络受损,气血运行受阻,阳气无以发挥温煦功能,致使膀胱气化不利,开阖失司,水液停聚,出现尿潴留。严银波[25]以针灸(针刺取合谷、血海、足三里、阴陵泉、三阴交、太冲,艾灸取关元、神阙)干预15例腹腔镜下经腹会阴联合切除术后直肠癌患者,并与术前宣教、术后夹闭尿管训练等常规干预15例对照,观察对患者排尿功能恢复的作用。结果显示,试验组膀胱残余尿量、排尿状况等排尿积分,膀胱残余尿、术后排尿功能等级均优于对照组(P<0.05)。施钰岚等[26]采用电针(取穴气海、关元、足三里)治疗直肠癌术后尿潴留患者30例,并与夹闭尿管常规治疗30例对照观察。结果显示,治疗组尿管的保留时间及重复插入尿管的情况均明显少于对照组(P<0.05)。韩旭等[27]采用针刺手法(取穴:中极、关元、水道、足三里、阴陵泉)联合电针(取穴:中极、关元,断续波,频率2 Hz)治疗直肠癌术后排尿功能障碍38例,并与盐酸坦索罗辛缓释胶囊治疗38例对照观察。结果显示,治疗组排尿功能和膀胱功能评分均优于对照组(P<0.05)。近年来,中医外治法治疗术后尿潴留多用于肛肠手术,用于结直肠癌术后尿潴留的研究更多的见于10年前的文献,这可能与近年来腹腔镜等手术方式的改良及其他疗法的应用,大大降低了其发生率有关。结直肠癌手术术式及操作的特殊性,使得其尿潴留的机制不完全与肛肠手术一致,但当尿潴留发生时,可以进行借鉴与创新。
3 小结
中医外治法在结直肠癌围手术期中的治疗作用多体现在术后,对术后睡眠障碍,多采用耳穴贴压调节阴阳;对术后胃肠功能紊乱,多采用针灸、穴位贴敷、耳穴贴压等方法疏通经络,调畅气机;对术后腹泻,多采用艾灸、穴位贴敷等温阳健脾;对术后吻合口炎多采用灌肠给药,直接作用于局部活血化瘀,清热利湿;对术后尿潴留,多采用针灸温阳补虚,化气利水。近年来,基于ERAS理念的围手术期治疗在临床应用广泛,在结直肠癌围手术期的研究成果也颇多[28],中医外治法的宗旨与ERAS理念存在相通之处,都着重于减轻机体的负担,强调人体自身的恢复能力。临床研究证实,中医外治法联合ERAS可更有效地促进结直肠癌根治术围手术期患者康复[29],减轻患者术后炎性反应,解决了ERAS治疗术后并发症的不足[30]。但目前ERSA理念更多的是西方模式的直接应用,需要有更适宜于我国的围手术期快速康复管理模式。将现代医学模式与中医学结合并创新将是我们研究的方向,且目前关于结直肠癌围手术期基于ERAS理念联合中医外治法应用效果的系统总结和评价较少,需要临床进一步探索和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