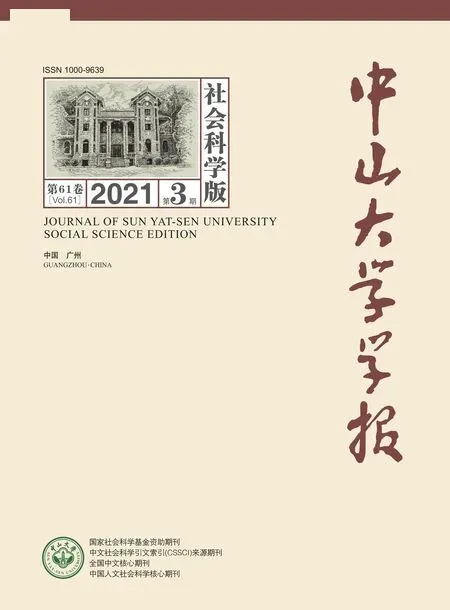檀郎与谢娘*
——论唐宋词中的类名现象
2021-01-03张仲谋
张仲谋
古典诗词中的男女情侣,往往会有一种类型化的称名方式,比如在唐宋词中,出现比较多的就是檀郎和谢娘。当然,这里说檀郎和谢娘也只是一种代表性的说法,实际诗词中的男性情侣也可能是阮郎或萧郎,女性也可能是萧娘或秋娘。在古典诗词中,尤其是在唐宋词中,因为伤春、伤别已成为基本主题,这种檀郎与谢娘的对应关系亦成为固定搭配。生活中本是赵、钱、孙、李,常用姓氏不下百数,可是在诗词中成双作对出现的往往是檀郎与谢娘。如果说中学英语教材中的李雷与韩梅梅不过是教材编者偶然杜撰的结果,而檀郎与谢娘的出现却是在长期的诗词创作中约定俗成的。如此的不约而同,如此的高频率出现,显然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和词学现象了。
关于文学中的类名现象,前辈学者曾经作过探讨。一般来说,我们把生活中实有人物的名字称为专名,而把文学作品中那种类型化的人物名字称为类名。现代学者中,顾颉刚称为私名与通名,许地山则称为私名与类名。顾颉刚在谈到孟姜女的名字由来时说:“当时齐国必有一女子,名唤孟姜,生得十分美貌。因为她的美的名望大了,所以私名变成了通名,凡是美女都被称为孟姜。正如西施是一个私名,但因为她极美,足为一切美女的代表,所以这二字就成为美女的通名。”①顾颉刚撰,钱小柏编:《顾颉刚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14页。这里所用的私名与通名,本为逻辑学概念,但各人理解亦有不同。比如许地山曾经著文谈中国古典戏曲与梵剧之区别,其中云:“中国剧本对于互相称谓底方法也略有一定,如‘员外’、‘相公’、‘小姐’、‘主上’等,为通名;私名,则老者常名‘大年’,婢女名为‘梅香’、‘春梅’,役人名为‘张千’之类都是。”①许地山:《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郑振铎主编:《中国文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28页。这是许地山的理解。而在我们看来,私名指具体人的名字,通名指类型化的名字。古典戏曲中婢女多叫“梅香”,役人多叫“张千”,此正是通名或类名,而“员外”“相公”则只是身份称谓而非人名了。
一、溯源:孟姜与罗敷
为了对古典诗词中类名现象的来龙去脉有所积累,让我们暂时搁置唐宋词中的檀郎与谢娘,先从早期类名现象的发生说起。首先进入我们考察视野的,是先秦时期的美女孟姜。
一提到孟姜,人们首先会想到孟姜女的传说,想到万杞梁,想到哭倒长城八百里的悲情故事。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感天动地的故事流传极广,另一方面是因为现代的顾颉刚、魏建功、刘半农、郑振铎等一批知名学者都对孟姜女故事作过研究,所以在大小文化或雅俗文学的两个层面,都会熟知这个古老而哀怨的故事。实际上,虽然同样叫孟姜,《诗经》中的美女孟姜,和传说中的杞梁妻孟姜,其实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一个是诗性文化中抒情的、唯美的美女形象,一个是叙事文学中世俗的传奇故事中的悲剧人物。从文学形象的产生年代来看,诗中的美女孟姜出现在春秋时代,而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大致形成于南宋时期。这就是说,诗歌中的孟姜和传说中的孟姜不仅分属于两种文化,在产生年代上前后相差也有近二千年之久了。
孟姜在《诗经》中出现有两处。一是《诗经•鄘风•桑中》:“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②聂石樵主编,雒三桂、李山注释:《诗经新注》,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104,169页。另一处是《诗经•郑风•有女同车》中的“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彼美孟姜,德音不忘”③聂石樵主编,雒三桂、李山注释:《诗经新注》,济南:齐鲁书社,2 0 0 0年,第1 0 4,1 6 9页。。这两首诗都是爱情歌曲,背景都在中原一带。在《诗经》十五国风中,鄘、邶、卫三国同属一个地区,即原来殷商的首都地区,在今河南安阳、开封一带。所以本为鄘风,故事的发生地却在卫国。诗中之沫为卫国城邑,桑中、上宫与淇水亦均在卫国,即今河南淇县一带。因为姜为齐国贵族之姓,所以历来解读《桑中》篇者,都意识到这里可能存在某种问题,即齐国的贵族女子,何以会千里迢迢跑到卫国去与情人约会?其实不仅是孟姜,孟弋也有问题。据钱大昕考证:“《诗》‘美孟弋矣’,弋即姒。”④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2,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266页。姒为莒国贵族之姓,莒国在今山东的东南部,跑到卫国也不容易。只有庸为卫国贵族之姓。顾颉刚《古史辨》就说:“是否这三国的贵族女子会得同恋一个男子,同到卫国的桑中和上宫去约会,同到淇水之上去送情郎?这似乎是不会有的事实。”⑤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三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据朴社1931年版影印本,第632页。事实上岂止是不会有,这种想法本身就有问题。简单地说,姜就是美女的合体字,孟姜就是美女的通名或类名,一定要说孟姜为齐国的贵族之女,就和后人斤斤于考证谢娘就是指谢道韫或谢秋娘一样,同样犯了胶柱鼓瑟之病。比较通达的解释见于朱自清的《中国歌谣》,他说:“我以为这三个女子的名字,确实只是为了押韵的关系……那三个名字,或者只有一个是真的,或者全不是真的——他用了三个理想的大家小姐的名字,许只是‘代表他心目中的一个女子’。”⑥朱自清:《中国歌谣》,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167页。《桑中》三段,从韵部来看,唐、乡、姜为阳部;麦、北、弋为职部;葑、东、鄘为东部,所以朱自清说这三个女子的取名是出于押韵考虑,是可信的。但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在《诗经》重叠复沓的章法背景下,总是第一次(第一段)出现的字面出于主动选择而具有实际意义,以下各章的用字才是出于随宜趁韵之变化。因此孟姜、孟弋、孟庸三个名字,只有孟姜是既定而不可改易的,而孟弋、孟庸则是随韵部生发出来的。可以是孟弋、孟庸,也可以是孟姬、孟芊、孟嫣、孟姚等先秦古姓。因为都是以声为用,随韵转移,根本不用考虑何姓属何国以及道里方域等问题。
孟姜之所以会成为早期美女的类名,清代的《诗经》学者姚际恒给出了一种解释。其《诗经通论》卷5《有女同车》揣度曰:“是必当时齐国有女美而贤,故诗人多以孟姜称之耳。”①姚际恒:《诗经通论》卷5,清道光刻本。博闻而好辩的顾颉刚对此甚表赞同。他说:“这话甚为可信。依他的解释,当时齐国必有一女子,名唤孟姜,生得十分美貌。因为她的美的名望大了,所以私名变成了通名,凡是美女都被称为孟姜。正如西施是一个私名,但因为她极美,足为一切美女的代表,所以这二字就成为美女的通名。”②顾颉刚撰,钱小柏编:《顾颉刚民俗学论集》,第114页。这虽然只是一种揣测之词,却不失为一种合乎情理的推断。
一代有一代之美女。时光荏苒,《诗经》时代的美孟姜,到了汉乐府中就一变而为秦罗敷了。天下竟有这样巧的事,汉代乐府诗中两首最有名的叙事诗,其中都有一个美女秦罗敷。在乐府古辞《焦仲卿妻》(即《孔雀东南飞》)中,焦母劝仲卿休掉刘兰芝,然后给他介绍一个更漂亮的女子。说是:“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③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780,380,336,336,336,341页。这当然只是一个过场式的人物,不太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在另一首叙事名篇《陌上桑》中,罗敷就是当仁不让的故事主角了。《陌上桑》开头写道:“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④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1 6年,第78 0,38 0,3 36,3 36,3 36,3 41页。美女登场,接下来故事就开始了。因为这首诗写得实在精彩,罗敷的形象更让人惊艳而叹赏,于是关于罗敷的背景、身世及其得名等等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探索。晋人崔豹《古今注》卷中“音乐”条曰:“《陌上桑》,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嫁邑人千乘王仁为妻。王仁后为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饮酒欲夺焉。罗敷乃弹筝,作《陌上歌》,以自明焉。”⑤崔豹:《古今注》卷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页。此类乐府诗本事,其实和后来的宋词本事一样,大都出于好事者附会。因为是据诗的文本敷衍而成,所以粗看上去蛮是那么回事,实际对于诗歌文本的解读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
关于罗敷故事的渊源流变,值得关注的是法国汉学家桀溺的长篇论文《牧女与蚕娘——论一个中国文学的题材》⑥该文收入钱林森编:《牧女与蚕娘——法国汉学家论中国古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我们这里感兴趣的倒不在于作者的跨文化比较,即把汉乐府《陌上桑》与欧洲12世纪普罗旺斯行吟诗人马卡布律的牧女诗比较,而是他能别出心裁地把《陌上桑》与此前提到的《诗经•桑中》联系起来。他引录了《桑中》“爰采唐矣”一段之后,认为这正是后来秋胡故事或桑园故事的原始雏形。这种源流关系因为西汉刘向《列女传》卷5《鲁秋洁妇》的故事而更加凸显。相比之下,《鲁秋洁妇》显然为《陌上桑》故事之所本。同样以桑园为背景,以错认为故事情节的核心节点。不同的是故事的结尾,《列女传》以表彰节烈为动机,所以是悲剧;而《陌上桑》把它变成了喜剧。因为同出一源,所以在乐府诗史上,《陌上桑》和《秋胡行》往往互为交集。如南朝梁王筠《陌上桑》“秋胡始停马,罗敷未满筐”⑦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 6年,第7 8 0,3 8 0,3 3 6,3 3 6,3 3 6,3 4 1页。,是把罗敷与秋胡之妻绾合为一;而李白《陌上桑》“使君且不顾,况复论秋胡”⑧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780,380,336,336,336,341页。,更是把这两个同源异流的故事中的人物形象纽结到一起。另外在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陌上桑》系列中,鲍照的《采桑》亦值得注意。诗中既曰“采桑淇洧间,还戏上宫阁”;又曰“卫风古愉艳,郑俗旧浮薄”⑨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780,380,336,336,336,341页。,都是在揭示《陌上桑》与《诗经•桑中》的源流关系。另外萧子显《日出东南隅行》“女本西家宿,君自上宫要”⑩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780,380,336,336,336,341页。,后句即从《桑中》“要我乎上宫”变化而来。此皆可佐证《陌上桑》与《诗经•桑中》的源流关系。
当然,故事情节的因袭与人物之得名并没有直接的连带关系。孟姜自孟姜,罗敷自罗敷,虽然都在桑园中,却是不同时代的美女类名。金性尧说:“自从《陌上桑》流行后,罗敷便成为美人之代名。”⑪金性尧:《金性尧全集》第五卷,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年,第19页。这其实是把先后源流关系搞颠倒了。从表面上看,在后《陌上桑》时代,确实涌现出一批歌咏秦罗敷的作品。包括《陌上桑》的仿拟之作,如傅玄《艳歌行》“秦氏有好女,自字为罗敷”①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第339,340,295页。,高允《罗敷行》“邑中有好女,姓秦字罗敷”②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第339,340,295页。。另外也有不少非《陌上桑》系列的作品,如徐陵《骢马驱》“诸兄二千石,小妇字罗敷”③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第3 3 9,3 4 0,2 9 5页。,沈约《少年新婚为之咏》“羞言赵飞燕,笑杀秦罗敷”④沈约著,陈庆元校笺:《沈约集校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66页。,杜审言《戏赠赵使君美人诗》“罗敷独向东方去,谩学他家作使君”⑤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以下凡引唐诗皆据此本,不再另行出注。,等等。这些当然足以证明《陌上桑》的魅力与影响。然而若论源流先后,恐怕不是《陌上桑》成就了罗敷之名,而是早在《陌上桑》之前,罗敷已成为美女之代名,所以这篇带有民间文学意味的歌诗才会信手拈来。比如大约同时的《孔雀东南飞》中就有“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的诗句,可知秦罗敷作为美女之代名,那时已经约定俗成了。
二、谢娘形象之流变
在唐宋诗词中,檀郎与谢娘是最常见的情侣之类名。檀郎为诗词中男性情侣之类名,具体又有檀郎、阮郎、萧郎等不同称谓,既各有渊源,角色内涵亦有微别。谢娘为女性情侣之类名,具体又有谢娘、萧娘、秋娘等微妙变化。这些类名及形象之间,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前后流变,抑或同中有异。这些形象在初起时或有出典,但在诗词创作发展过程中早已形成特定的人物意象,与原来的谢道韫或潘岳、阮肇等没有多少内在关系了。有些注疏往往笼统解会,看似追根溯源,实际不得要领。这里试作梳理。
谢娘的形象流变,在唐宋诗词中,大致可分为三个层面。
其一,在晚唐以前的诗中,谢娘与谢道韫渊源较近,形象的基本内涵是才女或大家闺秀。如韩翃《送李舍人携家归江东觐省》:“承颜陆郎去,携手谢娘归。”因为是送友人归家省亲,所以诗中以三国时怀橘孝亲之陆绩代指李舍人,谢娘即代指李氏家眷。可知谢娘在彼时尤为美称,而这种用法在晚唐以后是不可想象的。又或称“谢女”。如刘禹锡《柳絮》:“萦回谢女题诗笔,点缀陶公漉酒巾。”因为诗题是《柳絮》,这里的谢女显然是指咏絮才女谢道韫。又如李绅《登禹庙回降雪五言二十韵》:“麻引诗人兴,盐牵谢女才。”咏雪而提及“盐”字,这里的谢女当然也是指谢道韫。又或称“谢家”。如白居易《奉和思黯自题南庄见示兼呈梦得》:“谢家别墅最新奇,山展屏风花接篱。”李端《题元注林园》:“谢家门馆似山林,碧石青苔满树阴。”杨巨源《夏日裴尹员外西斋看花》:“芳菲谁家好?惟是谢家怜。”卢纶《题李沆园林》:“愿同词赋客,得兴谢家深。”这些都是题咏朋友家的园林,谢家就是借东晋时的名门大族谢家来比拟友人之家,和五代张泌《寄人》诗中的“别梦依稀到谢家”的谢家不同。
其二,晚唐诗中的谢娘或谢家,往往指妓女与妓院。晚唐诗如罗虬《比红儿诗》:“谢娘休漫逞风姿,未必娉婷胜柳枝。”杜红儿、柳枝皆为妓女,这里取譬连类,谢娘显然也是妓女。唐彦谦《离鸾》:“庭前佳树名栀子,试结同心寄谢娘。”因为诗中有“尘埃一别杨朱路,风月三年宋玉墙”,可知谢娘是一位风尘女子。又如刘沧《代友人悼姬》:“萧郎独宿落花夜,谢女不归明月春。”温庭筠《赠知音》:“窗间谢女青娥敛,门外萧郎白马嘶。”萧郎、谢女已成固定搭配,也隐约透露了谢女的平康女子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诗词中的谢娘、谢女隐指妓女,未必如当下诗词选本所称,是因李德裕所宠爱的名妓谢秋娘而起。李贺《牡丹种曲》:“檀郎谢女眠何处,楼台月明燕夜语。”宋代吴正子注曰:“唐诗中有称妓女为谢女者,大抵因谢安石蓄妓而起,始称谢妓,继则改称谢女,以为新异耳。”⑥吴正子笺注,刘辰翁评点:《李长吉歌诗四卷》,此处转引自张先著,吴熊和、沈松勤校注:《张先集编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0页。这就是说,唐宋诗词中的谢女,其出处既不是才女谢道韫,也不是中唐名妓谢秋娘,而是从《晋书•谢安传》所载谢安携妓游东山轶事而来。李白《忆东山》:“我今携谢妓,长啸绝人群。”白居易《奉和裴令公新成午桥庄绿野堂即事》:“花妒谢家妓,兰偷荀令香。”李贺《昌谷诗》:“泉尊陶宰酒,月眉谢郎妓。”皮日休《奉献致政裴秘监》:“黄菊陶潜酒,青山谢公妓。”从这些诗例来看,晚唐以来诗词中的谢女、谢娘或隐指妓女,很可能不是因为李德裕与谢秋娘,而是从谢公妓演化而来的。
其三,唐宋词中的谢娘,已与才女谢道韫或谢公妓渐行渐远,而主要是作为恋人或意中人的符号化类名出现的。试选若干首,以便下文展开讨论。温庭筠《更漏子》:
柳丝长,春雨细。花外漏声迢递。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香雾薄,透帘幕。惆怅谢家池阁。红烛背,绣帘垂。梦长君不知。①曾昭岷等编著:《全唐五代词》,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以下凡引唐五代词皆据此本,不再另行出注。
韦庄《浣溪沙》:
惆怅梦余山月斜。孤灯照壁背窗纱。小楼高阁谢娘家。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枝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
顾敻《浣溪沙》:
惆怅经年别谢娘。月窗花院好风光。此时相望最情伤。青鸟不来传锦字,瑶姬何处琐兰房。忍教魂梦两茫茫。
孙光宪《浣溪沙》:
桃杏风香帘幕闲。谢家门户约花关。画梁幽语燕初还。绣阁数行题了壁,晓屏一枕酒醒山。却疑身是梦魂间。
晏殊《望汉月》:
得、醉中攀折。年年岁岁好时节。怎奈尚、有人离别。②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以下凡引宋词皆据此本,不再另行出注。
晏几道《鹧鸪天》:
千缕万条堪结。占断好风良月。谢娘春晚先多愁,更撩乱、絮飞如雪。短亭相送处,长忆
小令尊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春悄悄,夜迢迢。碧云天共楚宫遥。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贺铸《摊破浣溪沙》:
双凤箫声隔彩霞。朱门深闭七香车。何处探春寻旧约,谢娘家。旖旎细风飘水麝,玲珑残雪浸山茶。饮罢西厢帘影外,玉蟾斜。
高观国《玉楼春》:
多时不踏章台路。依旧东风芳草渡。莺声唤起水边情,日影炙开花上雾。谢娘不信佳期误。认得马嘶迎绣户。今宵翠被不春寒,只恐香秾春又去。
以上选相关词8阕,唐五代4阕,宋词4阕。这其中,高观国的《玉楼春》,因为首句点出了“章台路”,可以说是明确暗示了谢娘的妓女身份。晏几道词中,“碧云天共楚宫遥”,用楚襄王与巫山神女为云为雨典故,或亦可作为把谢桥理解成妓家的依据。其余各篇中的谢娘、谢家、谢娥等,皆可理解为女性情人之所在。然而因为此前已有谢家妓或谢秋娘的说法,一般选本或论述仍然习惯上把谢娘说成是妓女。比如吴世昌就说:“端己《浣溪沙》有‘小楼高阁谢娘家’句。按‘谢娘’,顾敻《浣溪沙》有‘惆怅经年别谢娘’句,孙光宪《浣溪沙》有‘谢家门户约花关’句,可知‘谢娘家’非指一般女子所居,乃当时倡家之通称也。”③吴世昌:《罗音室词札》,《吴世昌全集》第五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4页。这里“可知”二字下得有点费解。从哪里看出谢娘家非指一般女子所居呢?是因为“谢家门户约花关”,想见一面不容易吗?“约花关”,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5释“约”为“拦”,其说曰:“孙光宪《浣溪沙》词‘桃杏风香帘幕闲,谢家门户约花关’,言拦着花而关也。汪莘《好事近》词,《春晓》:‘诗人门户约花开,蜂蝶误飞了。’约花义同上,按均犹云门户沿着花边。”①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5,北京:中华书局,1953年,第651页。这样说“谢家门户约花关”和顾敻“月窗花院好风光”相似,不过是美化之词而已。总之,除了先入为主的影响之外,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把谢娘看成妓女之代称。
事实上就词论词,这些词中着力渲染的是谢娘之美。最突出的是韦庄《浣溪沙》,“一枝春雪冻梅花”,既写出其如花美貌,又见出超凡脱俗气质;“满身香雾簇朝霞”,用渲染烘托之法,使谢娘的形象明艳而温馨。另外如史达祖《绮罗香·咏春雨》:“隐约遥峰,和泪谢娘眉妩。”《玉蝴蝶》:“一笛当楼,谢娘悬泪立风前。”也都是词句与形象双美之例。与谢娘之美相伴的,还有那挥之不去的绮怨与惆怅。如温庭筠《河渎神》“谢娘惆怅倚兰桡”,韦庄《荷叶杯》“惆怅晓莺残月”,孙光宪《河传》“谢家池阁,寂寞春深”等。这实际是对面着笔,两面兼写。既写出谢娘的惆怅与寂寞,自然也写出了才子词人的多情与相思。
我们也注意到,和早期的美女类名孟姜或罗敷相比,谢娘作为美女情人的类名,其专名意味更淡,类名意味更强。这就意味着,谢娘作为类型化人物之名,其个体的符号意义已被最大程度的淡化了。比如说,我们把唐宋词中凡是出现“谢娘”之处,一律换成“美人”或“玉人”,几乎丝毫不影响词意的解读。反之亦然。如温庭筠《杨柳枝》:“正是玉人肠绝处,一渠春水赤栏桥。”《河渎神》:“蝉鬓美人愁绝,百花芳草时节。”韦庄《菩萨蛮》:“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酒泉子》:“月落星沉,楼上美人春睡。”假如把这些词中的“美人”“玉人”字样一律改成“谢娘”,解读时也同样妥帖顺畅,丝毫不影响原词的内容与情趣。又如温庭筠《归国谣》“谢娘无限心曲,晓屏山断续”,把这里的“谢娘”改成“美人”或“玉人”,似乎也同样熨帖自然。由此可见,谢娘作为一个美女恋人的类名,已经摆脱了一般专名所有的个性化内涵。她是一个女人,一个年轻的、美丽的、惆怅的女人,一个爱惜流光、恐美人之迟暮的多情善感的女人,一个男性心目中梦魂萦绕渴盼见到的恋人。刘熙载《艺概》说:“温飞卿词精妙绝人,然类不出乎绮怨。”②刘熙载:《词概》,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689页。其实绮怨不是飞卿词的专利,而是晚唐北宋词的基本调性,同时也可以作为谢娘形象的审美特征。
和谢娘形象内涵相近的还有萧娘,在唐宋词中也是作为美女情人之类名出现的。
如孙光宪《更漏子》:
听寒更,闻远雁。半夜萧娘深院。扃绣户,下珠帘。满庭喷玉蟾。人语静,香闺冷。红幕半垂清影。云雨态,蕙兰心。此情江海深。
晏殊《采桑子》:
樱桃谢了梨花发,红白相催。燕子归来。几处风帘绣户开。人生乐事知多少,且酌金杯。管咽弦哀。慢引萧娘舞袖回。
周邦彦《浣溪沙》:
不为萧娘旧约寒。何因容易别长安。预愁衣上粉痕干。幽阁深沉灯焰喜,小炉邻近酒杯宽。为君门外脱归鞍。
康与之《应天长》:
管弦绣陌,灯火画桥,尘香旧时归路。肠断萧娘,旧日风帘映朱户。莺能舞,花解语。念后约、顿成轻负。缓雕辔、独自归来,凭栏情绪。楚岫在何处。香梦悠悠,花月更谁主。惆怅后期,空有鳞鸿寄纨素。枕前泪,窗外雨。翠幕冷、夜凉虚度。未应信、此度相思,寸肠千缕。
这些词中的“萧娘”,基本都是女性恋人之类名。关于萧娘的来历,相关工具书或引《南史》萧宏传所载“不畏萧娘与吕姥”之说,或称南朝齐梁时萧为著姓,后因称年轻女子为萧娘。其实前后并无因果关系。
近人李冰若《栩庄漫记》云:
唐人诗词尝用萧郎萧娘字以代少年及少女。如《全唐诗话》云,崔郊有婢鬻于连帅。郊有诗曰:
“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杨巨源《崔娘》诗云:“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又
如词中之“贪与萧郎眉语,不知舞错伊州。”又“半夜萧娘深院”,皆是。但不知惯以萧氏为代,其意何在,岂以萧为望族故耶?①李冰若校注:《花间集评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00页。
李冰若不知为不知,虽然有“以萧为望族故”之揣测,却未径下断语,比那些望风捕影之说显得更为矜慎。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引唐代杨巨源《崔娘诗》,明明写的是萧娘,为何题名《崔娘诗》呢?又所谓“肠断萧娘一纸书”,这一纸书又何所从来呢?试查验其文本所出,原来这首诗出于元稹的《会真记》(即《莺莺传》),其结尾处在引录“崔氏缄报之词”(即崔莺莺给张生的回信)之后,写道:“张生发其书于所知,由是时人多闻之。所善杨巨源好属词,因为赋《崔娘诗》一绝云:‘清润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消初。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②王实甫著,王季思校注:《西厢记》附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02页。由此可知,题中的崔娘即指崔莺莺,“清润潘郎”与“风流才子”则明指张生,潜指元稹。而“萧娘一纸书”即指崔莺莺所写之情书。因为《莺莺传》影响广泛,所以宋词中写到萧娘者,如周邦彦《四园竹》:“肠断萧娘,旧日书辞犹在纸。”赵闻礼《鱼游春水》:“过尽征鸿知几许,不寄萧娘书一纸。”如此之类,曰“肠断萧娘”,曰“一纸书”,均可见《莺莺传》中杨巨源《崔娘诗》的影响。假如离开了《莺莺传》的特定语境,“一纸书”就没有着落了。
三、檀郎、阮郎、萧郎
作为女性之恋人的类名,唐宋词中出现较多的有檀郎、潘郎、阮郎、刘郎等。本来檀郎就是著名的美男子潘岳,因其小字檀奴而称檀郎。但关于潘岳还有另外一个典故,即因其《秋兴赋》而来的“潘鬓”,又称潘郎鬓,所以唐宋诗词中提到潘郎,可能是指作为美男子的女性恋人,也可能是借潘郎鬓以叹老。如史达祖《夜合花》:“柳锁莺魂,花翻蝶梦,愁染潘郎。”周密《声声慢》:“休缀潘郎鬓影,怕绿窗、年少人惊。”这里均是词人自伤老大,不是女性眼中的情郎。又刘郎和阮郎本来同一出典,即刘义庆《幽明录》所载刘晨、阮肇入天台山的故事。但唐代刘禹锡《玄都观桃花》诗有“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之句,又有《再游玄都观》“种桃道士知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其强项不屈的人生态度对后人尤其是宋人影响很大,所以宋代诗词中的刘郎,或指传说中的刘晨,或借刘禹锡诗以自指。因为有这诸多的干扰因素,就为唐宋词中相关词语的检索分析带来了麻烦。比如说,“潘郎”,《全唐五代词》中有5例,《全宋词》中有43例,但其中相当数量是写潘郎鬓;“刘郎”,《全唐五代词》中有9例,《全宋词》中更多达184例,但其中有相当数量是写观桃之刘郎,还有一些是意在写逍遥世外的桃花源。因为一一举例分说则不免繁杂,不加区分又容易缠夹不清,所以在这里,我们主要分析意蕴比较单纯的檀郎、阮郎和萧郎。
在唐宋词中,檀郎和阮郎作为类型化人物之名,其相同处在于他们都是词中女性相思相恋的意中人,在这一方面,他们是相通相近的。然而逼近考察,这两个类名又同中有异。其主要区别是,檀郎似乎总是在恋人身边耳鬓厮磨、风流调笑的“暖男”角色,而阮郎则因袭了传说中的冶游元素,始终是一个漫游不归、春尽不还家的荡子形象。
先来看檀郎的形象。兹按年代先后选录数首。
和凝《山花子》:
银字笙寒调正长。水文簟冷画屏凉。玉腕重□金扼臂,淡梳妆。几度试香纤手暖,一回尝酒绛唇光。佯弄红丝蝇拂子,打檀郎。
李煜《一斛珠》:
晓妆初过。沉檀轻注些儿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罗袖裛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涴。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
柳永《促拍满路花》:
香靥融春雪,翠鬓亸秋烟。楚腰纤细正笄年。凤帏夜短,偏爱日高眠。起来贪颠耍,只恁残却黛眉,不整花钿。有时携手闲坐,偎倚绿窗前。温柔情态尽人怜。画堂春过,悄悄落花天。最是娇痴处,尤殢檀郎,未教拆了秋千。
张先《菩萨蛮》:
牡丹含露真珠颗。美人折向帘前过。含笑问檀郎。花强妾貌强。檀郎故相恼。刚道花枝好。花若胜如奴。花还解语无。
邓肃《临江仙》:
夜饮不知更漏永,馀酣困染朝阳。庭前莺燕乱丝簧。醉眠犹未起,花影满晴窗。帘外报言天色好,水沉已染罗裳。檀郎欲起趁春狂。佳人嗔不语,劈面噀丁香。
康与之《采桑子》:
晚来一霎风兼雨,洗尽炎光。理罢笙簧。却对菱花淡淡妆。绛绡缕薄冰肌莹,雪腻酥香。笑语檀郎。今夜纱厨枕簟凉。
赵彦端《虞美人》:
断蝉高柳斜阳处。池阁丝丝雨。绿檀珍簟卷猩红。屈曲杏花蝴蝶小屏风。春山叠叠秋波慢。收拾残针线。又成娇困倚檀郎。无事更抛莲子打鸳鸯。
张孝祥《浣溪沙》:
日暖帘帏春昼长。纤纤玉指动抨床。低头佯不顾檀郎。豆蔻枝头双蛱蝶,芙蓉花下两鸳鸯。壁间闻得唾茸香。
以上选唐五代及两宋词凡7首,其中《菩萨蛮》(牡丹含露真珠颗)一首,或作唐无名氏作,或作宋张先作。从这些词来看,檀郎的形象是相当统一的。这里已看不出檀郎与潘岳的任何联系,词中也无意强调其美男子形象,他就是一个情郎,一个如意郎君,一个供女子打情骂俏、撒娇卖嗲的意中人。唐宋词中多伤春伤别之作,其中写羁旅别情者多,写男女两情相悦又终朝耳鬓厮磨的甚少,而檀郎就正是这一类词中的主角。除上引数词外,如张耒失调名残句:“手把合欢彩索,殷勤微笑殢檀郎。低低告,不图系腕、图系人肠。”也是本色佳句。唐宋词中,写檀郎而流荡不归者,《花间词》中只有毛熙震《木兰花》上片:“掩朱扉,钩翠箔,满院莺声春寂寞。匀粉泪,恨檀郎,一去不归花又落。”宋词中只见过杜安世的《山亭柳》:“玉容淡妆添寂寞。檀郎孤愿太情薄。数归期,绝信约。暗添春宵恨,平康恣迷欢乐。”像这样一去不归、恣迷平康的薄幸檀郎,在唐宋词中是比较少见的。另外,从檀郎系列词来看,因为李煜之作在先,而且早成经典,后来的檀郎词往往受其影响。尤其是邓肃《临江仙》“佳人嗔不语,劈面噀丁香”,张孝祥《浣溪沙》“壁间闻得唾茸香”,更无异于主动交代其与李煜词的源流关系。
阮郎的形象既出于刘晨、阮肇入天台山的游仙故事,在唐宋词中仍保留着漫游忘归的原始基因。
如温庭筠《思帝乡》:
花花,满枝红似霞。罗袖画帘肠断,卓香车。迴面共人闲语,战篦金凤斜。惟有阮郎春尽,不归家。
和凝《天仙子》:
洞口春红飞蔌蔌。仙子含愁眉黛绿。阮郎何事不归来,懒烧金,慵篆玉。流水桃花空断续。
李珣《定风波》:
又见辞巢燕子归。阮郎何事绝音徽。帘外西风黄叶落。池阁。隐莎蛩叫雨霏霏。愁坐算程千万里。频跂。等闲经岁两相违。听鹊凭龟无定处。不知。泪痕流在画罗衣。
晏几道《阮郎归》:
旧香残粉似当初。人情恨不如。一春犹有数行书。秋来书更疏。衾凤冷,枕鸳孤。愁肠待酒舒。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
上引词中,阮郎都是漫游不归的荡子形象。李珣词中的“音徽”,犹言音讯。魏承班《谒金门》:“雁去音徽断绝,有恨欲凭谁说。”晏几道词中并无“阮郎”字样,但他这首词可以视为咏本调,即以调为题。所谓“一春犹有数行书,秋来书更疏”,即未归来,即绝音徽也。另如顾敻《酒泉子》,曰“谢娘敛翠恨无涯”,又曰“堪憎荡子不还家”。此处“荡子”可替换成“阮郎”,因为一去不回家的总是阮郎,换成檀郎则不可。在唐宋词中,萧郎颇与阮郎相近,也是女性伤别与怀思的情郎形象。
如李珣《中兴乐》上片:
后庭寂寂日初长,翩翩蝶舞红芳。绣帘垂地,金鸭无香。谁知春思如狂,忆萧郎。等闲一去,程遥信断,五岭三湘。
朱敦儒《浣溪沙》:
碧玉阑干白玉人。倚花吹叶忍黄昏。萧郎一去又经春。眉淡翠峰愁易聚,脸残红雨泪难匀。纤腰减半缘罗裙。
周密《清平乐》:
晚莺娇咽。庭户溶溶月。一树桃花飞茜雪。红豆相思暗结。看看芳草平沙。游鞯犹未归家。自是萧郎飘荡,错教人恨杨花。
这些都是思妇怀人之词,抒情主人公是思妇,萧郎只是其怀思的对象。周密的“自是萧郎飘荡,错教人恨杨花”,是别出心裁的名句。其意是说应该恨的不是那些牵绊萧郎的风尘女子,而是忘恩负义的萧郎。因为同样是远游不归的情郎形象,这些词中的萧郎和阮郎也是可以互换的。
四、唐宋词类名的文化意味
在以上缕述举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唐宋词中的类名现象试作归纳分析。
其一,唐宋词中的檀郎、谢娘等类型化人物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音乐文学的产物。古典诗词中的有名姓的人物,大概可分为三类。一是历史人物。如李白《永王东巡歌》:“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杜甫《咏怀古迹》:“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辛弃疾《贺新郎》:“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这类人物形象多出现在咏史、怀古类作品中,或用作典故,或借对古人的选择认同以自况。二是作者身边实有的人物。如杜甫《饮中八仙歌》中的贺知章、崔宗之、张旭等人;柳永《木兰花》四首中的“心娘自小能歌舞”,“佳娘捧板花钿簇”,“虫娘举措皆温润”,“酥娘一搦腰肢袅”;晏几道《小山词》中时时出现的四个歌女莲、鸿、、云等人。当然也包括诗词中出现的题赠对象,如李白《赠汪伦》“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刘过《沁园春•寄稼轩承旨》“须晴去,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这是生活中实有的人物,这些名字也是个性化的专名。三是本文所探究的类名化人物。如《诗经》中的孟姜,汉魏乐府诗中的罗敷以及唐宋词中屡屡出现的檀郎与谢娘之类。这些虽然只是类型化的人物形象,但不像乐府民歌中那样称郎称妾,或现代民歌中的阿哥阿妹,而是赋予其一个类名;虽然这个类名就像山西民歌中的兰花花或苏联歌曲中的喀秋莎一样,亦不免于虚构拈连,但既有此名目,就比泛泛而言的郎情妾意更多了一些真切具体的个性化意味。
唐宋词本来就是乐府之属,而乐府与徒诗的主要区别:一是音乐性,二是叙事性。明代徐祯卿《谈艺录》云:“乐府往往叙事,故与诗殊。”①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69页。许学夷《诗源辨体》说:“盖乐府多是叙事之诗,不如此不足以尽倾倒。”②许学夷:《诗源辨体》,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67页。清代沈德潜《古诗源》卷首“例言”中云,乐府和古诗“较然两体”,而“措词叙事,乐府为长”③沈德潜:《古诗源》,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卷首第1页。,都是在强调乐府诗的叙事性特色。对于汉魏乐府或唐宋词而言,“角色即叙事”,即设为人物口吻,以特定视角来观察或抒写自己的感受。即使像汉乐府《上邪》或敦煌曲子词《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那样通篇都是呼告式抒情,因为那是人物角色之心理口吻,所以也仍然具有极强的叙事性。葛晓音教授因此给它们拟定了一个看似别扭实则精准的概念,曰“叙事体的抒情诗”①葛晓音:《论汉乐府叙事诗的发展原因和表现艺术》,《社会科学》1984年第12期。。尽管檀郎或谢娘等等几乎算不上真正意义的人物,词人甚或无意于叙事,但既有名姓,又有人物关系,这些形象也就因而具有一定的“角色”意味,这些词也就成了“代言体”。谢娘是男性眼中的情侣,檀郎也是女性恋人眼中的情郎。当张泌《浣溪沙》满含憧憬地描绘“小楼高阁谢娘家”,晏几道《鹧鸪天》自我忏悔说“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时,词人本身就扮演了檀郎的角色。如果借用浦江清常用的“以曲释词”之法,唐宋词中的那些伤春伤别之作,也可以说是由小生、小旦组成的“二小戏”。词的文本中可能只写了一个美丽而感伤的谢娘形象,而画框之外总有一个含情脉脉的檀郎在;反之亦如是。这种抒情与叙事相兼的表现手法与审美意味,与一般的徒诗或文人叙事诗是判然有别的。
其二,不同文体有不同的类名人物,彼此具有不同的表现功能和审美效果。类型化的人物不仅出现在古典诗词中,在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叙事作品中也存在。比如衙役中的董超、薛霸,在宋元话本《简帖和尚》,元杂剧《包待制智赚灰阑记》,明代小说《三遂平妖传》中都曾出现过。在《水浒传》中更是前后出现两次,第八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鲁智深大闹野猪林》中押解林冲的就是他们两个,那时候他们两个是开封府的解差;到了第六十二回《放冷箭燕青救主,劫法场石秀跳楼》,押解卢俊义的还是他们两个,这回他们是大名府的衙役。为了弥缝他们从开封府到大名府的蹊跷,《水浒传》作者还特地加了说明:“原来这董超、薛霸自从开封府做公人,押解林冲去沧州,路上害不得林冲,回来被高太尉寻事刺配北京。梁中书因见他两个能干,就留在留守司勾当。”②施耐庵:《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799页。其实为了两个路人甲乙式的边缘人物,本来用不着专门交代,只是这董超、薛霸似乎已成衙役之通名,所以不吝笔墨来疏通前后。
更为典型的类名形象是说媒的王婆。宋元以来的小说戏曲中,媒婆几乎都姓王。如《京本通俗小说》中的《西山一窟鬼》写道:“吴教授看那入来的人,不是别人,却是半年前搬去的邻舍王婆。——原来那婆子是个撮合山,专靠做媒为生。”③《京本通俗小说》第12卷《西山一窟鬼》,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第5页。盖自此以后,媒婆就基本上被王姓所垄断了。元杂剧中如《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叮叮珰珰盆儿鬼》等剧中都有王婆,但那个“隔壁王婆”基本就是路人甲,在推动剧情发展方面作用不大。而到了《水浒传》中,那个撮合宋江、阎婆惜的王婆,和那个帮西门庆笼络潘金莲的王婆,就不仅是一般意义的媒婆,而兼有助推叙事的特定功能了。在晚明时期的话本小说“三言二拍”中,王媒婆的形象愈见其稳定。如《喻世明言》中的《史弘肇龙虎风云会》,《警世通言》中的《玉堂春落难逢夫》,《醒世恒言》中的《闹樊楼多情周胜仙》,《拍案惊奇》中的《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韩秀才乘乱聘娇妻,吴太守怜才主姻簿》,其中的王婆都是以说媒为生的。要研究中国古代的婚姻现象,王婆应是不可回避的人物。
两相比较,可知同为类名化人物,诗词与叙事性的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固自有别。诗词中的孟姜、罗敷是美女之类名,唐宋词中的檀郎与谢娘等是男女情侣之类名,基本上是取代南朝民歌中的“郎”“妾”之称,此外并无多少社会内涵。而小说、戏曲中的董超、薛霸、梅香、张千以及王婆之类,则多是世俗社会中某一阶层或某一职业人物之类名。这些类名所负载的是人物的等级身份以及世俗生活气息,为主要人物及故事情节营造一种“接地气”的环境氛围;而诗词中的类名人物则已然诗化,它们代表着生活中某一类人物的形象特点,除了一般姓名的个体性符号功能之外,所具有的主要是由长期的创作与阅读积淀而形成的某种文化意义和审美意味。它像一个“语码”,因为某种音韵效果和长期的审美积淀,看到它就会涌起一些美好的、优雅的联想。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的崛起,雅俗文学两大阵营中的类名也会出现交融互渗现象,一些常见于通俗文学的类名也会出现在诗词中。如明代著名小说家吴承恩,其《射阳存稿》中有词近百首,不仅词风近俗,其中出现的人物也时时透露出作者的小说家身份。如其《点绛唇》:“待月心情,只恐红儿解。”《菩萨蛮》:“徘徊罗幌曙,闲共红儿语。”《蝶恋花》:“忽地一声闻宝钏,隔帘弹出飞花片。”①饶宗颐初纂,张璋总纂:《全明词》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84、985、987页。这里的红儿、宝钏之类,就是通俗文学中常见的丫鬟之名,和过去诗词中的檀郎、谢娘迥异其趣。这就像某些侠客或武士,虽然可能十八般武器样样皆通,但林冲最擅长的还是枪,关胜最擅长的还是大刀。明清小说家、戏曲家写词,总不免带有一定的情节性或戏剧性,像吴承恩的这些词就颇有戏曲片段的意味。
其三,唐宋词中人物类名之形成,虽然不无历史人物的因缘附会,但主要是出于审美效果之考量。我们在考察中发现,檀郎与谢娘等类名的形成多有相似之处,比如说都是从历史人物生发出来,然后在创作与阅读实践中由专名到类名,由历史人物衍化为诗化形象。也正因如此,人们在解读诗词时往往着意疏通还原其历史原型及本事,而事实上这些类名的约定俗成,起决定因素的不是其历史背景,而是由字面或音韵唤起的审美意蕴。孟姜就是先秦时期美女之类名,而与齐国贵族孟氏的女儿没有直接关系;罗敷就是汉魏时代美女之类名,而与邯郸千乘王仁的妻子无关。同样,唐宋词中常见的谢娘就是男性所怀思的女性恋人,与名门闺秀谢道韫或谢安所携之妓或李德裕侍妾谢秋娘等等也无甚关系;檀郎也是词中女性相悦相恋的情郎形象,与其蝉蜕而出的原型人物西晋文人潘岳也并无多少关系。
然而,人们总不免数典追踪索引推求的癖好。比如,唐宋词中美女恋人的类名,为什么是谢娘、萧娘而不是别的名姓?如果说谢娘有才女谢道韫的原型影响,那么历史上的才女还有很多。比如说,至少在唐代以前,就有既浪漫多情又有文采的卓文君,有继承其兄班固之志续撰《汉书》的女学者班昭,有长篇《悲愤诗》的作者蔡琰,有成就卓著的女诗人左棻和鲍令晖,还有作回文《璇玑图诗》的苏蕙,等等。可是在唐宋诗词中,并没有形成班娘、蔡娘、左娘、鲍娘之类的类名。尤其是卓文君,既有与司马相如之间凤求凰的风流韵事,又有《白头吟》诗的附会传说;还有苏蕙,既有织锦回文的《璇玑图诗》,又有与丈夫窦滔因缘离合的爱情故事。这都是非常适合拿来打造美女恋人形象的原型,可是也没有形成卓娘、苏娘的类名。所以回头想来,这可能不是历史才女的原型问题,而是姓氏音韵的声情意境问题。唐宋词是歌辞,是音乐文学,尤其注重声韵效果。盖谢字、萧字,为小口形、细声韵,其音轻柔圆润,听其声即有要眇宜修之美感,即可感知其窈窕淑女的温婉形象。这不是哪一位诗人偶然的发现或规定,而是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众所认可约定俗成的结果。
又比如关于萧郎,旅居马来西亚的作家兼学者萧遥天所著《中国人名研究》中专有“萧郎与萧娘”一节,其中写道:“萧郎与萧娘,在旧文学上带有很浓厚的浪漫气氛,常见于诗人的吟咏,而吟咏中所指的男性与女性,也不必须姓萧,已成为情郎与欢女的代词了。”这是说得很对的。但他接下来说:“按这些诗都以萧郎、萧娘比人与自况,都不必是姓萧的,则称萧郎萧娘当有来源。原来在魏晋六朝时代,萧氏阀阅很高,习俗以萧郎萧娘称男称女,相当高尚,犹如今天的称少爷小姐。”②[马来西亚]萧遥天:《中国人名研究》,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第206、207页。这种看法我们不大赞成。尽管魏晋时萧氏为门阀世族,当时抑或有此风俗,但从唐宋诗词中的萧郎来看,与魏晋时的萧氏家族已无任何关系。更大的可能还是出于刘向《列仙传》所载萧史和弄玉的浪漫爱情故事。如唐代施肩吾《赠仙子》诗:“凤管鹤声来未足,懒眠秋月忆萧郎。”宋代袁绹《传言玉女》:“宴罢瑶池,御风跨皓鹤。凤凰台上,有萧郎共约。”刘仙伦《鹧鸪天》:“凤箫声彻瑞烟浮,萧郎玉女来相会。”这些诗词中每提及萧郎,总与凤凰台或箫声为伴,足证萧郎形象出于萧史之传说。传说当然不如史实更有说服力,但传说更善于营造浪漫的爱情氛围,这才是萧郎胜出的重要原因。另外从声韵角度来说,唐宋诗词中本来也有从韩寿偷香而来的韩郎,从卢家子弟而来的卢郎,因风流俊赏的杜牧而来的杜郎,因韦皋与玉箫故事而来的韦郎等等,但这些都不过旁见侧出而已,唯有萧郎较为常见,则除了萧史弄玉故事的浪漫因素之外,萧字的音韵美很可能也是重要原因之一。